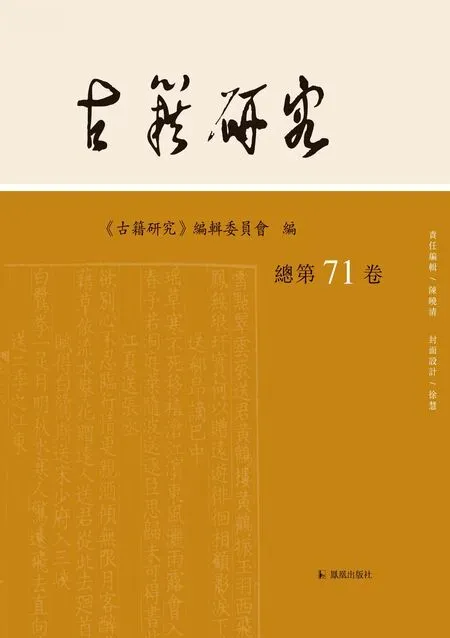王樹枏《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的文獻價值*
韓世穎
關鍵詞:王樹枏;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文獻
王樹枏(1)亦有王樹楠、王樹柟、王樹枬,本文據《陶廬老人隨年録》《陶廬叢刻》作王樹枏,引用段落仍依原文用字。(1851—1936),字晋卿,晚號陶廬,河北新城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官至新疆布政使。傳記見《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陶廬老人隨年録》(以下簡稱《隨年録》)。《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中評價王氏:“經術精湛,兼長史學,善爲詩文,著述甚多。”(2)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2册,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 674頁。尚秉和于《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狀》称:“公秉承家學,復得學古堂山長黄編修彭年爲師,爲文華贍藻麗,詩出入于韓昌黎、李長吉二家,而博識强記,凡經書滯義,古籍錯訛,訓詁考訂,精賅允當,突出前人。一時名宿睹所著,皆願訂交。”(3)(清)王樹枏撰:《陶廬老人隨年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97頁。可見王樹枏經史詩文皆有所長,且著述宏厚,在當時影響較大。筆者經檢,目前學界對王氏的研究集中在其史學方面,對佔據其著作較大比例的經學却關注甚微,有必要填補這些不足。《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以下簡稱《校正》)爲王樹枏經學代表作,對研究《大戴禮記》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即擬以此書爲切入點,以期管窺王樹枏治經路徑和治學思想,彌補既往研究之闕。
一、 清代禮學和《校正》
清代是古代學術的總結期,“隨着對儒家原典的日漸重視和逐步、逐部的整理,清代學術又轉向禮學的復興,並轉向學術的整體繁榮:一方面對禮的義理和制度的研究日漸深入;另一方面隨着考鏡源流的發展,由宋溯唐,由唐溯魏晋,由魏晋而漢,由漢而先秦諸子……《大戴禮記》這樣一個從文本上看與《禮記》頗多淵源,從編撰者來看同受學于後蒼,從内容上看亦多可采的禮學著作,受到普遍關注……也是水到渠成”(4)孫顯軍著:《〈大戴禮記〉詮釋史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頁。。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戴禮記》在清代得到長足的研究,校勘、考訂、訓解者衆多,其中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尤受學術界重視:“近儒治三禮學者,……後有凌廷堪、胡培翬、以廷堪《禮經釋例》爲最精,任大椿(作《釋繒》、《弁服釋例》)、阮元(作《車制考》)、孔廣森(作《大戴禮記補注》),咸從戴震問《禮》。”(5)劉師培:《近儒之〈禮〉學》,選自羅志田導讀,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217—218頁。“十三經除《禮記》《穀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大戴禮記》則有孔廣森《補注》、王聘珍《解詁》焉。此諸新疏者,類皆擷取一代經説之菁華,加以别擇結撰,殆可謂集大成。”(6)梁啓超著,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頁。“《大戴禮》舊惟北周盧辯一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訛脱亦不少。乾嘉間戴東原、盧抱經從事校勘,其書始稍稍可讀。阮芸臺欲重注之,未成,而孔巽軒(廣森)著《大戴禮記補注》,汪少山(照)著《大戴禮記補注》,二君蓋不相謀,而其書各有短長,汪似尤勝也。”(7)梁啓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第202頁。劉師培和梁啓超總結清代禮學時繞不開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以下簡稱《補注》),《補注》上承盧文弨、戴震的研究成果,對《大戴禮記》進行系統梳理,奠定研究基礎,下啓後人對《大戴禮記》的研究,王樹枏的《校正》就是在孔廣森已有的學術成果上完成的。“王樹枏《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收集各家之説,對《孔》書進一步考補,資料最爲詳備。”(8)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0頁。《校正》援引衆家之説以校正孔氏之説,可謂是一部集大成著作。《隨年録》交代:“季春余回志局,余素喜考訂之學,局中若崔芋堂乃翬、蔣侑石曰豫、袁爽秋昶、方子瑾恮、丁聽彝紹基,皆方聞博雅之士,朝夕過從,質疑問難,獲益良多。”(9)《陶廬老人隨年録》,第23頁。可知王氏喜愛考訂,與衆多學者交流有所感悟得以成書,此爲《校正》成書。
《校正》兩册十三卷,初版爲清光緒九年(1883)陶廬叢刻本,此版湖南省圖書館有藏。《隨年録》記載《校正》成書于光緒四年(1878),《校正》跋中明該書于癸未年(1883)刊刻出版。“今王君文泉有《大戴禮記補注》之刻……各爲卷帙,附于其後”(10)(清)孔廣森撰:《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89頁。,王文泉《畿輔叢書》收有此書,《續修四庫全書》收有此版影印本,列于經部第108册。1939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收有此書,1985年中華書局根據商務印書館本重印(11)王豐先於《大戴禮記補注》校點説明中提到《校正》版本流傳:“是書最早於光緒九年刊刻出版,並收入《陶廬叢刻》中。後又收入《畿輔叢書》,由定州王灝謙德堂於一九一三年刊刻出版。一九三九年,商務印書館據《畿輔叢書》本排印,收入《叢書集成初編》,而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又據商務印書館本重印。”。2004年三秦出版社,黄懷信主撰的《大戴禮記匯校集注》援引了王氏的校正。2008年中華書局,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收録有王氏《校正》的内容。2013年中華書局出版孔廣森的《補注》後附有王氏的《校正》,由王豐先點校。可見王樹枏《補注》價值頗高,有一定的流傳度和影響力,對後世研究大戴禮記有重要的作用。
二、 校勘方法
“雖名《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實乃對《大戴禮記》舊本進行全面校勘,而且間能有所發明。”(12)黄懷信主撰:《大戴禮記匯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54頁。《補注》不僅對孔氏之説進行校正,更對歷來《大戴禮記》的研究梳理考訂,校勘内容詳實,校勘方法嚴謹。王樹枏常用的校勘方法爲本校法、他校法、對校法、理校法。
(一) 對校法
“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别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别録》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13)陳垣:《校勘學釋例》卷六,臺北:學生書局,1971年,第144頁。對校法是《補注》中使用的基本校勘方法,運用的版本有蔡文範本、盧本、戴本、汪本等。
千步而井 (《王言第三十九》) 。
戴校云:“井九百畮,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汪本用戴説,改作“方里而井”。案:《家語》亦作“千步而井”,蓋其誤久矣。(14)《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61頁。
對校法通過不同版本的互證以正訛誤,戴本認爲‘千步’是‘方里’之訛,改“千步而井”爲“方里而井”, 汪本採用此種説法,王氏遵之,並改《家語》之誤。
(二) 本校法
“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15)《校勘學釋例》卷六,第145頁。程千帆、徐有富在陳垣的基礎上提出“據文義校勘”(16)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第400頁。的本校方法,即通過疏通著作的上下文文意進行校勘。
任善不敢臣三德(《曾子本孝第五十》)。
此句與上下文不貫,應有誤。尋文義,“任”字涉上注而衍,“善”字在上句“食”字上,或校書者以“惡”字注于“善”字之旁,後人因以“惡”字入正文,而移“善”字于下,此文遂顛倒錯亂而不可讀矣。“不敢臣三德”,當在“君子之教也”下。古多以君子指君言。“以正致諫”上,當有“卿大夫之孝也”六字,誤入注中,而又衍一“諫”字,删“之孝也”三字。蓋自“君子之孝也”以下,皆由上遞及,不應至末始言天子之孝。以文義觀之,當是如此。存是説以諗知者。(17)《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358頁。
王氏察上下文不連貫懷疑有誤,通過“細觀一段中前後文義,以意逆志,發現出今本訛誤之點。”(18)《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39頁。考“任”字衍,“善”字錯亂,並且通過文義梳理混亂文句,有理可依。
(三) 他校法
“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爲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爲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19)《校勘學释例》卷六,第146—147頁。凡書采前人或被後人所引用可用作他書校本書。
立不蹕《保傅第四十八》。

(四) 理校法
除了上述三種方法,理校法亦是王樹枏常用方法。“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爲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爲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21)《校勘學释例》卷六,第148頁。
過于樂也(《保傅第四十八》)。
孔蓋據《通解》改盧本仍作“湛以樂”,戴本作“湛以樂也”。今案:以當爲“亦”,湛爲 “媅”之借字。《説文》:“媅,樂也。”此文應作“湛”,亦樂也。(22)《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327頁。
此處王氏運用古文字知識校勘,王氏認爲湛爲“媅”之借字,根據《説文》 “媅”爲“樂”之意,故改“過于樂也”爲“湛亦樂也”,文義亦相通。
(五) 各種校勘方法結合
運用多種方法多層論證是校勘有力的重要保障,王氏採用各種校法相結合,使得校勘更加嚴密、嚴謹。
1.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王言第三十九》) 。
各本“聞”作“閑”,汪校云:“閑,馬作‘問’。”今案:聞,讀爲“問”。聞、問古字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釋文》:“聞,本或做‘問’。”《檀弓》“問喪于夫子乎”,《釋文》:“問,本亦做‘聞’。”《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皆其證。言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問,無問及于王言者。此正引起問王言之意。(23)《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59頁。
此句經文,王氏先運用古文字知識校勘,認爲“聞”與“問”古字通,“聞”讀爲“問”,其次列舉《論語·公冶長》《釋文》《檀弓》《荀子·堯問》,楊注的“問”與“聞”的釋義佐證,再通過上下文義,考“問王”的文義,將理校法、他校法和本校法相結合,論而多證,環環相扣。
2. 而志不邑邑(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荀子》作“心不知色色”,“色” 爲“邑”字之誤。楊倞注:“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奸惡也。”大謬,宜據《大戴》改“邑邑”。戴云:“邑、悒古通用。《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俞樾云:“‘而志不邑邑’,本作‘志不而邑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而即能也。淺人不知妄改,則與上句不倫矣。今案:此“而”字與下句“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句法蓋同,皆承上之辭。蓋“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與“不能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以爲己憂” 爲對文,俞以“口不能道善言”與“而志不邑邑”爲對文,非是。(24)《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65頁。
王氏認爲《荀子》中的“色色”是 “邑”字之誤,楊倞所注謬誤,應該根據《大戴》改成“邑邑”。對于俞樾“‘而志不邑邑’本作‘志不而邑邑’”,從句法和對文兩方面進行反駁,王氏將他校與本校結合起,辨俞之非。
三、 學術思想
(一) 批判《補注》之失的懷疑精神
王樹枏在跋中指出孔氏缺點:“往往拘守古本,穿鑿附會,以成其失。”具體指出兩點不足, 一是“曲爲之説,不肯依他書更正”。二是對于“顯然脱誤者,孔皆以仍舊文,未加釐訂,故王懷祖先生以‘守殘之癖’譏之”。“補漏訂譌,以引伸孔氏之所未備。”(25)《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489頁。明其成書緣由是爲了對孔廣森《補注》詳加勘定,查漏補缺,訂正訛誤。孔氏之書在清代是學術大著,王樹枏向此書發起挑戰,見其不盲信權威的批判精神。王氏對孔氏的校正内容爲正非和補缺。
1. 得夫子之閑也難(《王言第三十九》)。
戴校云:“閑,古莧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案:閑,讀如《孟子》“連得間矣”之“間”,戴校是。孔謂閑暇也,非。《家語》作“閑”。(26)《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59頁。
王氏認爲孔氏謂“閑暇”不正確,採用《孟子》“閑”讀如“間”,戴本所校正確。
2.及其明德也。(《王言第三十九》)
孔氏未注解篇名《曾子天圖第五十八》《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王氏注解,補上空缺。對于經文中孔氏未注也盡力補上,《曾子立孝第五十一》“况以所不能”“莊敬而安之”“聽從而不怠”“盡力無禮”“致敬而不忠”“夙興夜寐”幾句没有注解,王氏皆注解。(28)《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359—360頁。王樹枏不僅對孔氏進行校訂,對于其他諸本也並不盲信,進行釐清訂正。如:“雖有博地衆民。”(《王言第三十九》),王樹枏校正“沈本‘地’訛作‘施’。”(29)《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59頁。“敬以入其忠。”(《曾子立孝第五十一》)王樹枏校正:“朱彬曰:‘‘入’,當作‘全’。’非是。”(30)《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360頁。此注解駁朱彬解“入”爲“全”。
(二) 運用《家語》和日本書籍進行校對的創新精神
與王樹枏批判精神對應的是他的創新精神,王氏批判孔廣森的因循守舊,原因在于王氏自身力圖創新。王國維認爲清代學術經三變,以國初、乾嘉、道咸三個節點劃分:“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31)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25—26頁。道咸之後學術以新求變,晚清内憂外患的時局促進了憂患思變的思想。“憂患意識是變易觀念的前提和基礎。在晚清‘内憂外患’的局面下,王樹枏産生一種變革意識是必然的,在思想上要求變革,要求改變社會原來的現狀,在當時具有一種革新進步精神。”(32)劉芹著:《王樹楠史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頁。時代思想促進了其學術思想的形成。《孔子家語》在清代普遍被認爲是僞書,梁啓超言:“《孔子家語》及《孔叢子》。乾隆中葉問題完全解决,公認爲王肅僞撰。”(3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71頁。孔廣森《補注》亦不取《家語》。
孔子曰:“吾欲以顔色取人,于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于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五帝德第六十二》)
【補】《弟子傳》曰:“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以言貌取人,或失之賢,或失之否,詞同而旨異。王肅《家語》輒反之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望文構造,毁誣賢哲,可嗤憫也。(34)《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136頁。
此段經文,《家語》與《弟子傳》解釋有所出入,孔氏批判《家語》,見其對《家語》不取態度。王樹枏亦云:“孔氏作注,不取《家語》,惡其僞也。而王肅所據《大戴》乃是魏以前本,其中異文,多可取證,故並出之,以質世之讀是書者。”(35)《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55頁。王氏不議《家語》是否爲僞書,因王肅《家語》根據的《大戴》版本更爲古遠,有一定可信度,便取之而用。對于學界普遍認爲的僞書,王氏大膽採用。《王言第三十九》列經文32條,提到《家語》24次,《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列經文31條,提到《家語》21次。校正經文時也多採《家語》之言:“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寬于刑(《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王樹枏:《家語》‘勿’作‘無’。‘無’字是,與上下文一律。”(36)《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420頁。“其信可復(《王言第三十九》),王樹枏校正:《家語》作‘其言可復’,‘言’字是,據改。”(37)《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62頁。
衽席之上還師(《王言第三十九》)。
王念孫云:“‘還師’上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揚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即用《大戴》之文。”案:《家語》作“則必還師衽席之上”,上句作“則必折衝千里之外”,點竄此文,專以儷偶爲工,足徵漢以後人僞造無疑。(38)《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60頁。
《家語》中“則必還師衽席之上”與“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工以駢儷,王氏認爲此句爲漢代之後僞造。雖然多引《家語》,但是王氏對于《家語》並不盲從,有所辨别。
“鴉片戰争發生後,他們主張抵抗侵略,反對妥協集團,並要求了解西方國家情况,學習外人‘長技’,改進防禦力量。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和早就開始談論實際問題著有《安吴四種》的包世臣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39)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3頁。晚清時期,内憂外患,一部分知識分子尋求救國之路,主張經世致用,開眼看世界。龔自珍、林則徐、魏源開此局面,後繼學者不絶。李肖聃先生在《湘學略》中言及“國人承風,争習外事”,以王先謙、王樹枏、黄遵憲、傅雲龍作品爲典範。“王先謙爲《五洲地志》《泰西通鑒》《日本源流考》,王樹枏爲《希臘春秋》《歐洲列國紀事本末》,黄遵憲爲《日本國志》,傅雲龍爲《日本圖經考》。”李肖聃先生對上述學者的作品價值予以肯定:“此其有功於外事也。”(40)錢基博、李肖聃著:《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161頁。除了李肖聃先生提及的兩部作品,王樹枏另有三部西洋史作品:《彼得興俄記》《歐洲族類源流略》《希臘學案》(41)學界對王樹枏西洋史著作有一定研究成果,如劉芹《王樹楠史學研究》的第二章《歐洲史著編纂》,新疆大學陳偉楠碩士論文《王樹枏著西洋史五種研究》。。王樹枏的西學視野不僅體現在他的西洋史專著中,在言及時政的文章中,他将中國與西方比較,如論及學蔽:“然比不獨中國然也,亦非余一人之固見也,今試舉英國通儒之言,英國教育者證之……”中國和西方國家面臨相似的教育弊端,王樹枏以西方國家爲鏡,吸取經驗教訓:“斯賓塞爾譏其國之教育,重才不重德之失,如此,今乃取其國之所謂失者而學之。”(42)(清)王樹枏:《學弊篇》,選自《陶廬外篇》,宣統二年陶廬叢刻本。王樹枏學習西方的目的是“保種”“保教”“保國”(43)“乙未之秋,余在南皮張香濤尚書幕中,有浙人某。欲盡廢中國之書,及中國之字,謂爲無用,不若盡從西人,悲夫,存吾種者教也,存吾教者國也,故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 (清)王樹枏:《歐洲族類源流略》卷一,光緒壬寅年陶廬叢刻本。,並付諸行動,落實到實踐中。王樹枏在新疆爲官時期,學習西方貨幣思想,提出幣制改革方案(44)見張新革:《試論王樹枏的貨幣思想及造幣活動》,《新疆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3卷第1期。,對新疆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君既通知外事,而受知大府,欲有所爲,宜獻其所有,統關内外而一視之,興務作業,疆弱富貧,不必仰給於他行省,邊備已隱然可恃,遠人不敢生心,而朝廷無西顧憂,斯乃不負所學。”(45)(清)賀濤著,祝伊湄、馮永均點校:《賀濤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8頁。
王樹枏多交外國好友,其中以日本人爲主。王氏在詩文中記録他和日本友人的往來,如《送日本上原英東之伊犁序》(46)見(清)王樹枏:《陶廬文集》卷三,民国四年陶廬叢刻本,安徽省圖書館有藏。《日本慕勝君林出賢次郎來遊隴上,將有新疆之行,席中賦贈》(47)見(清)王樹枏:《陶廬詩續集》卷二,民国六年陶廬叢刻本,安徽省圖書館有藏。《林出慕勝從余遊三年,將東歸,賦詩贈别二首》《席中贈慕勝》(48)見《陶廬詩續集》卷四。。1926年,王樹枏赴日本開文化會,以詩記録在日本的行跡,如《駿河即今静岡》《過静岡濱名湖是日大霧》《相模即神奈川縣》《奈良》《京都即山城國》《乘高綫鐵路電車登比睿山至絶頂》《東京二首》等。王樹枏對日本進行實地考察:“吾觀其國,實業盛興,學堂林立。都中只十字街口設一巡兵,仿周禮秋官野廬氏之職,以備車馬轚互叙行之事,余則不見一巡兵。風俗嚴整,凡遊玩之處,高下皆有鐵路。皇室簡樸,不及中國一富室。西京風尚尤古樸,時大修孔廟,建立漢文大學。”(49)《陶廬老人隨年録》,第84頁。王樹枏睹日本經濟、文化的興盛,思及本國不禁痛心感慨:“從來禦外侮,發憤責爲雄。”(《東遊日本》)(50)《野言集》,《陶廬詩續集》卷十二。
桐城派名家賀濤稱讚王氏:“而於外國載籍,搜討尤勤,嘗欲取彼制度器物,提扼綱領,推類以求,包括萬有……”(51)《賀濤文集》,第138頁。王樹枏著五種西洋史,廣羅外國資料。《歐洲族類源流略》引述23種外國歷史地理書籍(52)見喬治忠、劉芹:《史家王樹枏及其〈歐洲族類源流略〉》,《史學月刊》,2007年第8期,第6頁。,《希臘春秋》中的人名地號“以日本岡本監輔譯文爲定本,而附注其不同者以爲備閲者考訂”。(53)(清)王樹枏:《希臘春秋》序,光緒年間陶廬叢刻本。王樹枏採用資料,視野廣博,在治西洋史之前,他已經採用日本書籍注解《校正》。《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篇目注解中,王樹枏曰:“日本國《群書治要》並引此篇目作《修身》,與今本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列經文110條,提到《群書治要》22次,《曾子立孝第五十一》經文18條,提到《群書治要》9次。經文注解採用《群書治要》,如:“見惡思垢(《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王樹枏校正:《群書治要》‘惡’作‘難’。”(54)《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345頁。“身勿爲能也(《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王樹枏校正:《群書治要》‘能’上有‘可’字,與下文一律。阮本從之,今據增。”(55)《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354頁。王氏所提《群書治要》有阮元本校勘所引,亦有自己所徵引的,都表達了他對《群書治要》材料價值的認同,除《群書治要》外,王樹枏另引柏木探古唐寫本《玉篇》用以追溯唐以前《大戴禮記》版本。
玄校。《夏小正第四十七》
(三) 不立門户,博采衆家,兼收並蓄
“三禮都是鄭康成作的注。在康成畢生著述中,也可説是以這三部注爲最。所以‘三禮學’和‘鄭學’,幾成爲不可分的名詞。”(57)《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00頁。梁啓超認爲禮學和鄭玄密不可分,鄭玄在禮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孔廣森《補注》序中言《家語》:“《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肅横詆鄭君,自爲聖證論,其説不見經據,皆借證于《家語》。大氐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奥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説若和符券,其爲依托,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並列爲成王《冠頌》,是尚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况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于《家語》殊文别讀,獨置而弗論也。”(58)《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15頁。孔氏不取《家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爲王肅與鄭玄之説相悖,以《禮》是鄭康成之學,爲免生異端,擱置《家語》而不論。“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尊漢儀鄭,援據精深”(59)《〈大戴禮記〉詮釋史考論》,第254頁。“儀鄭依然有利于堅守家法師承,尊漢儀鄭由此成爲孔廣森治經的一大特色。這在《大戴禮記補注》中突出地表現爲:其一,凡《大戴禮記》與《禮記》文有重叠,因而有鄭注可依的,必先援引鄭注,《哀公問于孔子》引‘鄭君曰’14條,《朝事》引‘鄭君曰’9條,《投壺》引‘鄭君曰’15條。其二,凡鄭玄其他注疏可以參證的,《補注》或直接援引‘鄭君曰’以爲注,或以‘鄭君曰’作爲重要依據。”(60)《〈大戴禮記〉詮釋史考論》,第267頁。尊漢儀鄭是孔廣森《補注》的一大特點,如:“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孔廣森補注:“鄭君曰:‘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小戴記》‘忤’作‘午’,‘古’作‘昔’。”(61)《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7頁。王樹枏是黄彭年弟子,在《清儒學案》中被歸入陶樓學案中,《清儒學案》中對陶樓學案的治學評價是“陶樓爲學根本盛大,無門户之見。入建讜言,出宣善政,皆折中經術,體用兼賅。”(62)徐世昌編纂:《清儒學案》第9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16頁。“這樣以黄彭年爲中心形成了晚清時期折衷經術,無門户之見,體用兼備,宣導實學的陶樓學派。”(63)《王樹枏史學研究》,第58頁。王樹枏的《校正》,博采衆家之長,没有明顯的傾嚮。王氏博采衆家,言之有理者則被録入,“復與廣稽群籍,參互諸家”(64)《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489頁。。正如馬其昶在《陶廬文集》序中評價王氏經學:“其釋群經諸子,實事求是,一本之故訓。”(65)(清)馬其昶:《陶廬文集序》,《陶廬文集》。王氏《校正》引名家有張爾岐、顧炎武、朱軾、段玉裁、郝懿行、汪中、孫志祖、錢大昕、劉台拱、梁玉繩、汪喜孫、陳觀樓、朱筠、朱駿聲、桂馥、黄叔琳、戴震、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阮元、俞樾等;引著作有《史記》《論語》《家語》《釋文》《荀子》等;引用版本有蔡盧本、戴本、汪本、《群書治要》《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白孔六帖》《玉海》《漢書》《魏書》等。(66)參見王豐先《大戴禮記補注》校點説明,《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8頁。
四、 小結
王樹枏《校正》因其校正全面,治學嚴謹受時人稱讚,張之洞:“貴門人王晋卿大著數種均收到。公暇流覽,誠不愧北方學者。大戴禮校補極詳審,某亦有十數條,擬補入書中,以備一解。其所擬送窮文,别闢蹊經,詞亦雅而有趣。”(67)(清)張之洞:《致黄子壽》,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册,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第11頁。王氏也通過《校正》校勘别書之脱誤,爲其他書籍的校勘提供方向,如:“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王言第三十九》)?《家語》作‘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荀子作‘與之治國,敢問如何之邪’。據《大戴》與《家語》,則《荀子》‘之邪’上脱‘取’字。”(68)《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63頁。“今夫端衣玄裳(《王言第三十九》)。此‘今夫’二字,正應上‘今夫’。哀公以‘今夫’問之 ,孔子即以‘今夫’答之,文義甚明。《荀子》、《家語》俱脱‘今’字,宜據《大戴》增。”(69)《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第264頁。上例兩條經文,王氏通過《大戴》校《荀子》《家語》 之脱。“從考據學的整個歷史發展來看,清代考據學是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考據學者的每一項成果,都借鑒吸收了大量前人的觀點和材料,是不斷積累的結果。”(70)郭康松著:《清代考據學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1年,第215頁。王樹枏承前人研究菁華,成《校正》一書,亦啓後人之學,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採王氏之説,如“何以謂之居(《夏小正第四十七》),王樹枏:‘何以謂之居’,與下文‘何以謂之雷’,篇題下‘何以謂之《小正》’句法正同。向東案:此説是。”(71)《大戴禮記匯校集解》上,第147頁。在《大戴禮記》的彙編匯校中,《校正》佔有一定的地位,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對于研究《大戴禮記》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