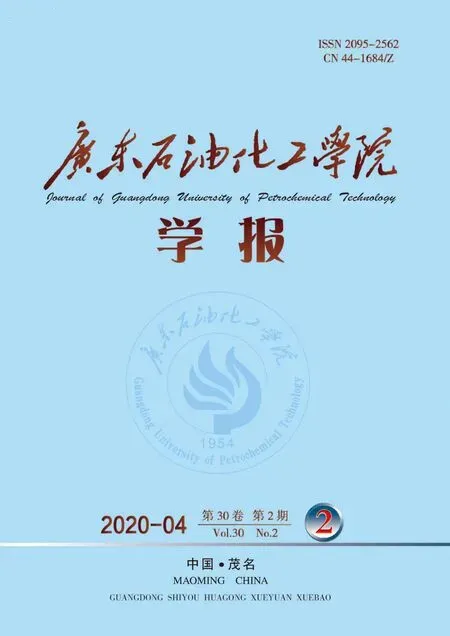场域互动视域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本研究①
李丛立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外语系,广东 湛江524094)
《了不起的盖茨比》 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不仅在美国享有极高的文学声誉,而且早已成为世界级的经典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者不断地从多个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在中国知网以关键词 “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搜索,研究论文多达1500多篇,从作品主题、艺术特色、表达技巧的纯文本研究到运用各种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批评理论进行研究。相对于文学界热火朝天的研究局面,学界对其译本的研究却稍显冷落。以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翻译”进行搜索,论文只有80多篇,而且大多数论文只是从翻译文本的角度进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方面只有寥寥几篇,较有影响的有刘士川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孙毅泓的“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多次重译的评析”;黎蕾的“论《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根据孙毅泓统计,截止到2009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中文译本就已多达32个[1]。 近些年来新的译本更是层出不穷,如2016年出版的吴建国的译本、2017年童继平的译本、2018年张炽恒的译本。不同译本是不同社会时代、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各有其特色。在众多译本中,巫宁坤译本作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译本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对该译本进行宏观研究,通过梳理《了不起的盖茨比》 巫宁坤译本产生的历史历程,分析影响译本产生的潜在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
1 场域中的社会实践活动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社会实践论认为,实践者在一定的社会场域,在惯习的支配下携带资本从事社会活动即社会实践,其分析公式可以表达为[(惯习)(资本)]+ 场域 = 实践[2]。翻译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那么布迪厄的分析公式对应到翻译领域即:“译者带着惯习(由一系列译者定势组成)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3]”场域、惯习、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行法则的社会空间”[4],它“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5]。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发生在一定场域,有多少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多少种场域,整个社会是由大大小小不同的实践场域构成的。正如布迪厄所言: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 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 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6]这里所说的社会世界就是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即布迪厄所称的“权力场域”。“权力场域可以看做是一种元场域”[7],任何场域都处于权力场域中并受其影响和制约。权力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如政治、教育、文学、翻译等子场域即社会小世界只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同社会实践场域之间处于互相影响和制约中。那么就翻译实践而言,文学翻译活动不仅仅受翻译场域运行规则的制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权力场域及文学场域的影响和制约。
2 权力场域、文学场域及翻译场域的互动
各个社会实践场域只是相对独立,不同场域由于影响力不同,彼此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对译者而言,翻译场域位于权力场域中,但在权力场域内处于被统治地位。而文学场域则相对更接近权力场域的统治级。”[8]翻译选择即选择翻译哪个国家及哪个作者的作品,不仅仅是由翻译场域的各因素决定和促成,而且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学场域,例如文学准入标准会影响译本选择,这是因为虽然文学翻译行为属于翻译场域的社会实践活动,但翻译的成果毕竟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要在中国的文学场域被接受、阅读和传播,必须要符合中国文学场域的运行规则。如果翻译场域的文学翻译选择不符合当时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译本就会遭到文学界的排斥与批判,从而影响其接受和传播。而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不仅涉及到特定时期文学场域衡量作品的文学标准如作品的文学价值、艺术特色等文学要素,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受到权力场域的制约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一定时期的文学趣味、文学风气、文学主题和内容,甚至不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就是非法的、反动的,会受到压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会随时代而变化,从而影响甚至主导文学场域准入标准的变化,如《简爱》《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等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曾被视为“优秀”和“进步”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又变成了批判的对象,不再属于‘优秀’‘进步’作品之列了。”[10]这是因为“按5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尺度,所谓‘优秀’和‘进步’的作品,就是指在思想性上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10]
权力场域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出于自身需要产生对某类文学作品的喜好倾向从而影响文学场域的文学生产。虽然文学场域有其独立的运行法则及场域自主性,但文学场域毕竟是处于权力场域中,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会一定程度上迎合权力场域去生产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作品。当文学场域生产的文学数量满足不了权力场域需要时,经常就会借助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促进翻译场域翻译行为的产生。再者,虽然相对于文学场域,翻译场域更远离权力场域的统治极,但翻译场域也处于权力场域中,所以也会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翻译符合权力场域需要的作品。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对东欧、东德以及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的文学作品具有极大的翻译热情,“其目的不在 ‘文学’ ,而是将翻译作为增进友谊、加强国家之间亲和关系的手段。同时,借助对这些国家文学的翻译,来丰富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10]
3 场域互动视域下巫译本的产生历程
翻译文学虽然是权力场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互动的产物或结果,但在这种循环互动中文学场域经常处于中心地位。权力场域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文学场域进行的。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经常是由文学场域发起且译本的选择往往首先取决于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译本的传播和接受及其文学地位的确立也深受文学场域诸多因素(如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文学场域为契入点来梳理巫宁坤译本的产生历程从而分析场域间的互动。
3.1 从被拒于国门之外到获得合法的译介资格
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文最早问世于1980年,连载于《世界文学》的第5、6期,这也是此小说译文在中国大陆的首次问世。巫宁坤当时是受《世界文学》杂志主编的邀请翻译的这部小说。巫宁坤之所以翻译这部小说是由文学场域发起的。文学场域之所以想译介这部小说当然是对其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即这部作品符合当时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 《了不起的盖茨比》于1925年4月在美国正式出版,至20世纪60年代完全确立了其在美国的文学经典地位而且享誉世界。既然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早已得到欧美世界各国的认可,为何在中国大陆直到1980年才有译介呢?
权力场域影响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从而影响翻译场域的翻译选择。(中国长久以来无论是本国的文学创作还是译介的外国文学,重视的要么是服务于政治如新中国成立前的二三十年“对文艺政治功利性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1],要么是服务于社会如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的是文艺的无产阶级性即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而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却居于次要地位。)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下,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充满了描述20世纪2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歌舞升平、酗酒作乐场景的作品是根本无法在中国被接受即在中国文学场域无法获得准入资格。尤其是原版书的封面画的是手指甲涂的鲜红的一位美女的手,手里拿着一杯香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这明显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这与当时中国极左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思想状况是不相容的。巫宁坤教授在20世纪 50 年代初“由于无意中将他从美国带回中国的英文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借给了个别学生,竟然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判,并背上了‘腐朽新中国青年’的黑锅近 30年。”[12]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被打上了反动的标签,尤其是巫宁坤教授的遭遇更使得这部作品令人望而止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任何译介。
文学场域的文学评价标准影响文学翻译的选择,促进了译介活动的进行。1979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集刊》第一辑中,董衡巽发表了《艺术贵在独创》一文,明确提出“评价外国文学时最好两头都能兼顾,既分析思想内容,又顾及艺术特征”[13]。 这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场域的宣言即摆脱权力场域的过度影响,追求文学场的自主性。董衡巽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外国文学的译介及评价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对权力场域长期以来影响文学准入标准及文学评价即过于重视思想价值的一种拨乱反正,为包括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内的很多曾经被拒绝于国门之外具有很强文学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奠定了基础。
3.2 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影响作品评价及其文学地位
权力场域主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影响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而且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也会影响作品评价及其文学地位。1976 年 10 月,随着“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迎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号召人们打破思想僵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因循守旧。权力场域的这种主导思想的变化势必影响到文学场域评价标准的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新时期的到来,大多数人逐步摆脱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去审视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
虽然文学场域的准入标准会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改变,但文学场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是一个缓慢而渐变的过程,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学场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的评价是新旧交替的时期。赵一凡在 《“迷惘的一代”初探》一文中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和抨击更为深刻有力”[14]。很显然,赵一凡仍然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即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来审视这部作品的,但他看到的是这部作品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一面。而美国史研究专家黄绍湘编著的《美国通史简编》 中指责菲茨杰拉德把盖茨比“这个秘密酒贩投机商吹捧成英雄人物,加以颂扬”,并把菲茨杰拉德定为“是20年代垄断资本御用的文艺作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化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大资本家罪恶勾当的吹鼓手”[15]。这完全是站在阶级对立的角度对菲茨杰拉德进行批判,对这部作品的主人翁及思想价值进行否定,这是五六十年代极左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延续。赵一凡和黄绍湘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和评价侧重的都是其社会意义,但却褒贬不一,而且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了不起的盖茨比》 的文学价值获得中国文学场域的认可并最终确立其在中国的文学地位,董衡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董衡巽1978年出版的 《美国文学简史》 中称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不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16],首次肯定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学地位,还第一次深入分析了该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把“既在事内又在事外”的叙事手法称为“双重看法”,这些真知灼见对后来的中国学者研究这部作品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16]。在1979年发表的《艺术贵在独创》一文中,董衡巽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欢迎而成为现代文学名著,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优美而奇特的文体”也是一大原因[13]。董衡巽注重作品文学价值的正面评价对人们如何看待这部作品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了新时期对这部作品的认识基调,激发了人们阅读及了解这部作品的欲望,从而呼唤了译本的诞生。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主动邀请巫宁坤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显然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说,权力场域与文学场域合力促成了翻译场域翻译实践的发生,催生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本。但《世界文学》作为杂志,传播范围毕竟有限,所以这部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读者群可能不太广泛,其经典文学地位的确立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3.3 译作出版背后的场域间互动
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巫宁坤等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杰拉德的其它八篇著名短篇小说,合集为《菲茨杰拉德小说选》。这本合集也被列为上海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是文学界的盛事之一。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中文译本在中国大陆以书籍的形式首次正式出版,书籍的出版是权力场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互动的产物和结果。
“文革”开始之后,中国对于世界文学的翻译介绍逐渐被中断。“四人帮”对外国文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由此隔绝了中国与世界文学的联系[17]。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即权利场域影响下的文学场域死气沉沉,鲜见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评论。翻译场域更是一片冷清,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作品的正式译介。新时期以后,文学领域出现了新的面貌,翻译也逐渐出现了全面复苏。为了缓解“文革”以来的书荒,尤其是1977年和1978年,对一些外国文学名著进行了重印和出版,但这仍然难以满足文学读者的需要。陈思和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那年5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出售经过精心挑选的新版古典文学名著《悲惨世界》 《安娜卡列尼娜》 《高老头》等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抢购的局面”[18]。当时的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如饥似渴,为了抢购书甚至半夜开始排队于书店前,拿到书时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继续加大重印出版数量外,开始考虑系统的外国文学的出版计划,因此做出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的出版规划,介绍各国的经典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 《了不起的盖茨比》名列其中,一方面是此书自身文学价值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促成的。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友好外交关系的建立,美国文学与文化得到了中国的重视,更多的美国文学作品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新时期文化场域的宽松氛围,使得人们能够从思想层面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这部作品去了解美国的社会思想状况、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正确欣赏和评价美国文学。如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的扉页中就明确写明了此套丛书的目的,“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19]”巫宁坤在《菲茨杰拉德小说选》的前言中也高度评价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才能,“菲茨杰拉德的风格凝炼而富有浓郁的抒情气息。他从来不凭借细节的铺陈和堆砌,而善于抒发每一个特定细节内在的感情和诗艺。这在美国现代小说家中是自成一格的。”[19]可见,无论是出版者还是译者都已彻底摆脱了五六十年代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对立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部作品了解美国文化及文学。 随着巫宁坤译本的出版,更多的读者能够接触到这部作品。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学价值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可,逐步确立了在中国的文学地位。
4 结语
《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本产生的历程表明: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只有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国文学作品才可能获得中国文学场域的准入资格;而文学场域的正面评价促使翻译场域进行译介;翻译场域的译介又会进一步促进作品在文学场域的传播和接受。权力场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处于不断循环互动中。
外国文学译本的产生并不仅仅出于译者个人喜好的选择,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不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国文学作品,尽管其有艺术价值,但一定时期可能不会有其译本产生,更不用提进入中国文学场域。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会受到特定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会随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