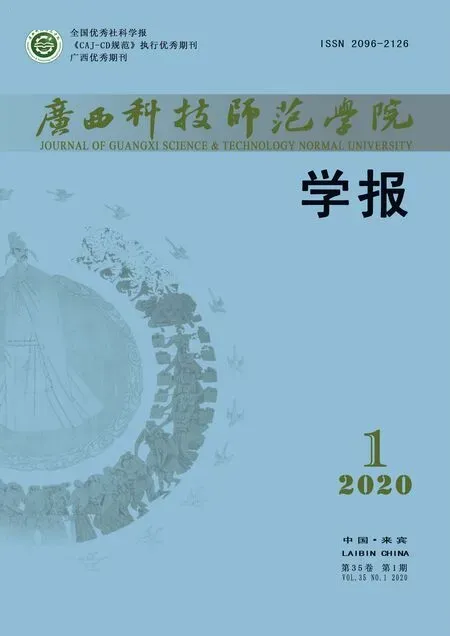“多头怪”形象的文化意蕴
瞿宏州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多头怪”形象因其外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特殊性,成为了民间文学中的一种艺术形象。这种形象的生成有其社会现实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多头怪”形象承载着人类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从民族学、哲学、伦理等维度,对“多头怪”形象展开探索,意在对形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行揭示。
一、原始形象的世界观
处于蒙昧时期的先民,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多头怪”形象正是先民心中对以往所经历的战斗场景的一种扭曲的记忆,折射出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原始的世界观。
蒙昧时期的先民最先面对的是与自然界的矛盾冲突。对原始先民而言,自然界的毒蛇猛兽、洪水干旱、风云雷电、雨雪冰霜、深山峡谷、急流险滩,乃至于人类社会的疾病伤害等都是令人恐怖的威胁。韩非子曾这样说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以伤腹胃,民多疾病。”[1]这种充满着致命威胁的原始群体记忆以早期的神话故事形式保留下来。《淮南子》书中这样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2]107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进入文明时代后,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部落之间的吞并,战争的频繁与规模的巨大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自剥林木以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3]。可见,早期先民们无论是人与自然的抗争,还是人与社会之间的战斗,均充满血腥的历史艰辛。
早期先民们经历的这段历史在民间叙事作品中以“多头怪”形象留存下来,敌对的一方(人或者自然)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被己方妖魔化,敌方的首领或者崇拜的神灵,则会被转化为一个个凶恶的魔鬼形象,倘若是曾经战胜过自己的部落,那么,妖魔化程度也将随之提升。且在“数、质互渗”的原始思维的运演过程中,被转化为更加凶暴残忍的多头巨魔。这样在“多头怪”形象的民间叙事作品中,展现的是“英雄与魔鬼”黑白分明的世界。
代表黑暗势力的“多头怪”在神话传说故事中,其形象总是狰狞恐怖、畸形怪诞。时而为两个头、三个头,时而是五、七、九个头,最多的竟然有成百上千个头;而且这些头颅要么是蛇头,要么是兽头,也有鸟形的头颅,千奇百怪,难以概述。它们一般都有着血盆大口,獠牙森森,口中总是吐着毒焰邪火;其身躯一般都十分庞大,或如山岳,或长数丈数十丈。总之,全身上下,无不显露出狰狞、丑恶、恐怖。而当“多头怪”出现时,也总是伴随着血腥暴力和人间的巨大灾难,以天地隐晦、日月无光,或草木焦枯、洪水泛滥,或攫食人类、白骨累累,生命绝灭如地狱般等图景呈现。而代表着光明势力的“英雄形象”,一般均以正常人的面貌出现,只不过形象要英俊一些而已。他们不仅拥有一颗勇敢的心,而且还具有不畏邪恶、不畏艰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他们或具有无穷的力量,或者得到神灵的帮助,或拥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宝物,或得到异人的指点等图景呈现……这既是他们取胜的根据,同时也是人们希望的寄托。在这种黑白对立的世界中,代表正义、善德的“英雄”与代表邪恶的“多头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往往这种力量的对比,在民间叙事作品中被无限夸大,强弱力量相差极为悬殊,乃至英雄经常被虚构为一个年幼的小孩。不过,这种力量对比的艺术构思,正是人们对当时世界的一种理性的认识与反映,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斗争的一种形象化写照。
总之,人类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冲突的战斗史,民间叙事中的“多头怪”形象中的狰狞恐怖、邪恶无比、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等表现,其实就是当年仇敌(自然、社会)形象的一种妖魔化,是先民们对以往所经历的战斗场景的一种扭曲的记忆。有关这种人与妖的战斗记忆作为民间叙事被传承下来,它本身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原始的世界观的折射,即在现实生活中,充满着种种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这种朴素世界观的认知,后来在民间叙事中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甚至被模式化、定型化,乃至于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促成早期世界观的形成。
二、原始朴拙的道德观
任何艺术形象的创造,不仅熔铸着创造者内心的审美意识,同时也渗透着人们的道德意识。人们对自己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进行审美判断时,自然也对其进行一定的道德评判,尤其是在文学发轫初期,这种道德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叙事中,有关“多头怪”形象的传说故事就蕴含着这种原初的道德意识。
就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道德意识就一直与人类相随相伴。在原始神话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意识的萌芽。就我国的神话而言,无论是女娲补天、女娲造人,还是鲧禹治水、尧舜禅让、炎黄之战,其中都隐约地露出道德意识的最初痕迹。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也许不是人类最原始的神话,但神话所叙述的事实却关涉到人类的起源这一原初问题。在神话时代,女娲造人的行为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是“善”,其后的而洪水泛滥,毁灭人类的行为是“恶”。再到后来,女娲炼石以补苍天的行为同样是善……尽管神话本身并没有对女娲的行为作出任何有关道德判断,但叙述本身的这一行为已经表现了这种原始朴拙的道德意识。
换句话说,人类道德意识的发生,最初当与人类心中的功利主义观念紧密相连。人类从功利的角度来评判行为和事物的“善”与“恶”,对自己或者对自己所在的部落集团有利,就视为“善”,反之则归为“恶”。为此,西方伦理学家穆尔曾这样论述:“在这个世界中,自愿行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造成了最大程度的快乐;而且还断言说,在任何可想象的情形中也同样如此,即在任何可想象的世界之中,如果一个可想象的生物面临两种选择,一种能比另一种造成更多快乐的话,它的义务便永远是选择前者而非后者,完全不必考虑它的世界在其他各方面与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和不同。”[4]穆尔认为能给自己造成最大快乐的事物,自然是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事物,他以是否能给自己造成最大快乐来界定善恶,其实是关于“功利”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在原始人类的“词典”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善恶”观念,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关于“善恶”的初步认识,只不过他们将这种道德意识化为善神、英雄或者恶魔等形象。这些善神、英雄就是“善”的化身,而妖魔则是“恶”的化身。可见,“善”与“恶”之间界限从来就没有被混淆过,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原初的道德意识逐渐分明,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这种原始朴拙的道德意识,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叙事中以“多头怪”形象的传说故事得以表述。
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民间叙事的故事中,描写英雄与“多头怪”搏斗的场面十分简短,英雄总是非常轻松地杀死了“多头怪”。譬如我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羿”的故事:“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2]125袁珂先生认为,其中的九婴,“当是九头怪兽、怪蛇之属,能喷水吐火以为灾”[5]。作为我国神话中的英雄羿单枪匹马,诛杀群凶,其战斗场面仅仅一笔带过。这种英雄轻松获胜的神话叙事,它不仅仅只是表达了人们善良的愿望,而且还隐藏着人们的一种道德评判,即“恶行”是短命的,是会受到应惩罚的,而“善德”是崇高的,是会战胜邪恶的,是需要发扬光大的。其中,“善”战胜“恶”的过程描述得较为简短,并不艰难,这本身蕴含着“善”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而“恶”的力量是渺小的。
由此可见,民间叙事作品中“多头怪”形象,往往被描述为给人类带来痛苦、灾难和死亡等人间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罪恶”与“邪恶”。相反,与“多头怪”英勇搏斗、为民除害则被描述为英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希望和依赖,是“正义”与“善德”的化身。这就是早期先民原始朴拙的道德意识在神话中的反映。
三、原始质朴的价值观
在“多头怪”形象的民间叙事中,“英雄”经过“多头怪”英勇搏斗取胜的这一事实,彰显的是对人的力量、人的智慧、人的价值的一种全面肯定,体现出早期人类原始质朴的价值观念。
在民间故事关于“多头怪”的描述中,展现了诸多“英雄”与“多头怪”格斗的场景,这些“英雄”其实就是人的化身。故事中以“多头怪”的失败反衬出“英雄”们的强大,表示对英雄的崇拜,“任何一个民族的英雄崇拜并非为崇拜而崇拜,而是视英雄为本民族最高德性的典范,并希望通过这种崇拜使自己与英雄相接近,努力像英雄那样建功立业,以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人们崇拜英雄,是将英雄视为个人或族群的精神支柱。这样,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凭借本民族英雄精神的支撑与激励,以英雄般的刚毅与坚韧意志,战胜艰难,获取胜利”[6]。当然,这种英雄崇拜的渲染,其实是对人的力量、人的价值张扬。
所有关于“多头怪”的故事,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故事。在故事的传承加工过程中,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多头怪”是凶残无比的野兽,迅捷灵活的飞禽、阴险毒辣的蛇蝎,空灵迷幻的幽冥等狰狞凶悍的化身,只要“多头怪”出现,就马上给人类带来腥风血雨、天昏地暗的灾难。如壮族神话《石良》中的“九头毒蟒”:“自从出了这条九头毒蟒,壮乡的山不青了,壮乡的水不甜了,壮乡的树不绿了,壮乡的花不香了。白天看不见人们的笑脸,夜晚听不到人们的歌声。”[7]418又如满族传说《完颜部的来历》中的“九头妖怪”:“忽然,一股旋风呼天号地顺着山谷刮过来……只见旋风里有一个九头妖怪,抱着一个姑娘向东逃去。”[8]373这些神话故事中所描绘的“多头怪”,不仅行动迅速,快如闪电,而且魔力超凡,口吐毒烟,力量巨大,刀枪不入,表现出了“多头怪”的狞恶。一般的人自然不是它的对手,这就成了“英雄”获胜道路上的一面倚天绝壁。
然而,在所有这类民间叙事中,不管“多头怪”如何强大,如何恐怖,如何不可战胜,但它们最后均被“英雄”战败。如古希腊英雄神话《赫拉克勒斯》中,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了能永无休止地长出头的“多头怪”许德拉。“这是一个长着许多头的、看上去像巨大的章鱼的魔鬼。他用剑砍下他一个个头来,但是每砍掉一个就又长出一个新的头来。多亏和他在一起的朋友伊俄拉俄斯在这魔鬼隐藏的森林里放了一把火,否则他将永无休止地砍下去。赫拉克勒斯砍下许德拉头的伤口,立即被火烤干,这样,就再也长不出头来了。”[9]364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英雄都以获胜来结束故事,有的英雄则是与魔怪同归于尽。如我国壮族传说《石良》中的英雄石良,在与“九头毒蟒”的搏斗中,“斗了三个白天,战了三个夜晚,石良砍掉了毒蟒的八个脑袋。”石良也昏迷过去。但他苏醒后,“纵身一跃,骑在毒蟒的七寸上,使出全身力气,双手死死箍住了它的脖子。……从山坡滚到山沟,从山沟又滚到山坡。……石良和毒蟒滚过的地方全是鲜血。石良和毒蟒最后都死了。”[7]420有的英雄则是在重创“多头怪”后,悲壮的死去,如满族传说《冰灯的来历》的结局就是如此。英雄巴图鲁在斩断“九头鸟”九个脑袋以后,以为它已经死了,“不料九头鸟忽然喷出污血,溅到巴图鲁身上带着连在肉筋上的大脑袋,逃出山洞,飞跑了。九头鸟的污血最脏,落在地上,传播瘟疫;溅到人畜身上,溃烂死去。英勇的巴图鲁拯救了全噶珊的人,他自己却被污血害死了。”[8]509在故事中,即便是“英雄”只是重创了“多头怪”,但是,经过重创后的“多头怪”再也不能伤害人类了,这本身就是胜利的表现。因此,在这种英雄最后死亡或失败的结局的“多头怪”故事里,我们所体味到的不是悲观绝望,而是一种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正如高尔基所说:“民间文学是与悲剧绝缘的。”[9]4尽管这样悲剧性结局的故事在同类故事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这类故事中“英雄”无论是与“多头怪”同归于尽,还是重创了“多头怪”以后才壮烈死去,都依然显示出了人的力量和价值。
总之,在民间叙事中,“多头怪”的魔力、心性都是具有扭曲、奇异、令人恐怖的特征。正是这种对“多头怪”的邪恶与凶暴大力渲染,更加突出“英雄”们的力量与价值。在这样的英雄身上,人们不仅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自身强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这蕴含了早期人类原始质朴的价值观。
四、结语
在人类产生的初始阶段,人类需要面对气候、地理、猛兽、毒蛇等险恶自然的巨大威胁,而当时生产力相对低下,人类应该如何应对,这既迫切地需要人类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法,也要求人类对自然做出一定的解释。基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界的认识探究,“多头怪”的形象既有人们对现实困境的思索与迷茫,也有用借助邪恶的“多头怪”的情节展示民众不屈从自然和命运的摆布,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美妙憧憬。由此可见,在民间叙述的“多头怪”现象中,蕴含着早期人类在认识自然与社会时,所体现出的原始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深层的文化内涵,这些认知正是早期人类认知自然与社会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