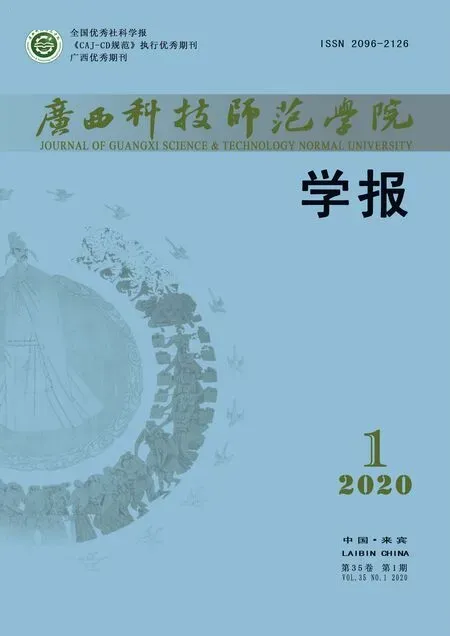论柳宗元的为人与为文之峻洁
董灵超
(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一、“不自贵重顾籍”该作何解
韩愈为柳宗元写了三篇祭文:《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祭柳子厚文》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①姚令威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为国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刘梦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侯于便道。’其后《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祭文盖谓此也。”具见《唐宋文醇》(上册)卷七,马清福主编,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柳子厚墓志铭》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②《祭柳子厚文》,马其昶注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为国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具见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2014年版第361页。韩愈任袁州刺史的次年,即公元820年。。《柳州罗池庙碑》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③其时韩愈在京师长安任吏部侍郎,他应魏忠、欧阳翼之请,再次为柳宗元撰写祭文,以书其事于石、满足柳州百姓求乞柳宗元神灵护佑之诚。《柳州罗池庙碑》载:“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柳宗元元和十四年(819)死于任上。此文作于他死后第四年,即公元823年。具见《唐宋文醇》(上册)卷七,马清福主编,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各有侧重而独立成篇的三篇祭文虽出于不同的撰写背景和书写目的,但韩愈对柳宗元的评价却一以贯之。
《祭柳子厚文》是韩愈惊闻柳宗元逝世、极度悲痛下的突然反应。这种情形下的情感抒发,往往不待思虑而其情直生。“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1]364,是何等沉痛。“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木之灾。……子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1]364历历陈说柳宗元的不平遇见,字里行间尽是对挚友柳宗元大才不展的深切惋叹。为了从深沉的悲痛中挣脱,韩愈又宽慰自己道:“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1]364通篇来看,《祭柳子厚文》是对柳宗元的一腔追悼,对柳宗元的人品才质没有丝毫引人争议之言。《柳州罗池庙碑》是韩愈应魏忠、欧阳翼之请所写,全文旨在称扬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功绩,也无可争议。
唯一引起歧义,是《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言:“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1]318此处的“不自贵重顾籍”[1]318成了后世文人攻击柳宗元性情率然、行事鲁莽的口实,成了柳宗元个性张扬、人品激进的标示。如《邵氏闻见后录》言:“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志,意欲著其父虽不显,所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2]黄震《黄氏日抄》曰:“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而非徒曰并称。然此犹以文论也。若以人品论,则欧阳子谓‘如夷夏之不同’矣。”[3]邵博、黄震的观点,都是在韩愈称柳宗元“不自贵重顾籍”基础上的“发明”。
然究其实,此种误读非但不解柳宗元,且也不解韩愈以及韩柳的知谊之情。韩愈所说“不自贵重顾籍”并非意在指责柳宗元为人躁进,而是感慨时境。诚如他在《祭柳子厚文》中所言:“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1]364正是因为韩愈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对自己的前途也有隐忧。须知,韩愈本人也屡遭贬谪。才为世用、道行于时需要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显然“韩柳”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不容他们乐观,这由他们的屡屡遭贬即可深得其味。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的仕途做了一番假设:“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1]318很明显,韩愈想表达的意思是:柳宗元若仕途顺利,必会有大的政治作为。如此,其目的在于对柳宗元政治才干的肯定;退而言之,即如柳宗元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也能于文学创作上开辟出一方天地。这正是对柳宗元文学才华的称扬。这里,韩愈对柳宗元的文章可以照耀一世且“必传于后”给予了完全的笃定和预见。
后人解读韩愈此文之所以歧路分径,就在于错认为这是韩愈对柳宗元政治冒进的指责。要知道,《柳子厚墓志铭》全篇行文的重点是肯定柳宗元文章创作方面的成绩。诚如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所言:“嗟惜子厚,只以其文,志墓亦此意。若此文,明云‘非我知子’矣。”[4]1093的确,处于唐宪宗庙堂上的韩愈无法公然称颂柳宗元的永贞革新,只能婉言委屈地对柳宗元的政治失落加以维护。即如柳宗元的另一挚友、在永贞革新事件中与柳宗元共进退的刘禹锡,其《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序》称:“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5]864在这首诗作中,刘禹锡何等自信他们的事业与人品之正,却也不得不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提到柳宗元“以踈隽少检获讪”[5]236。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言:“志者,记也;铭者,名也。”[6]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7]可见,在寻常情况下,墓志铭断然不可称说人的差失:“志”述死者生平,“铭”对死者进行褒扬悼念。那么,韩愈又何以会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生出“不自贵重顾籍”的批评之意呢?这等叙述,不过是一面为搪塞当时政治现实、为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乃出于政治不成熟作一种说法,另一面则是为下文称赏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张本罢了。
早期柳宗元在政治上“勇于为人”[1]318,出类拔萃。被贬永州之后,他的生命价值由“利安元元为务”[8]407的立功转到了“立言传世”上来。他清醒地看到古人“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8]432的规律,认识到“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8]432,开启了对自己人生前路的另一种追求:不得志于时,便当垂名后世;不得出将入相,便当文华流播。致力于为文着实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的自觉行为,他“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1]317-318。这种自觉与付出,被韩愈看到了,也被刘禹锡看到了。
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言:“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5]236-237同样高度称颂了柳宗元的文章功业。的确,终唐一代也只有韩、柳跻身于文章八大家之列。若只以柳宗元是靠文学排遣其政治失意来度量其文,就太低估了他为文的意义。
《唐宋文醇》中有这样一段评论:“人或良才美质,自天畀之而不学,不问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以至灭天理,而穷人欲,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滛佚慝乱之事,以之终身而不变。人曰天之生是使然也,奚知其质美才良,克念即可作圣耶?其与佳景瑰观清泉美石之汨,于荒区蛮域恶木毒莽之中,与为终古者奚异?宗元为上官作记,故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读之,知修身焉。”[9]对柳宗元为文的教化意义给予了深入发掘与重视,将《永州新堂记》这类游记提升到善读而知修身的高度。应该说这绝非偶然:即从柳宗元的为人来看,他也当得这等评价。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特为在言柳宗元“不自贵重顾籍”之前,插叙了柳宗元欲为刘禹锡以“柳州易播州”的侠义之举。须知,这是柳宗元从永州回长安后再次遭贬柳州,而这次遭贬并非柳宗元“不自贵重顾籍”的结果。在面临关键考验之时,柳宗元的侠义深情与为人笃诚再次一览无余:“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1]318面对柳宗元的大义无私之举,韩愈不吝感慨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1]318这里,韩愈对柳宗元的风义何等激赏!这个真实的柳宗元就是如此胸次磊落、行事利落的人。韩愈深谙柳宗元的性情:“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1]317“俊杰廉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1]317,不正是柳宗元为人性情的显著特征吗。柳宗元就是一贯地那么爽利、直截、有力,而这个柳宗元和为刘禹锡“以柳易播”的柳宗元是一体、一致的。不但柳宗元如此,他的父祖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品性情!“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柳宗元的曾伯祖柳奭、父亲柳镇也都是这样刚直不阿、仕途上坚守原则的人。刚正、爽利、不患得失是他们家族的由来风习。“众谓柳氏有子矣”[1]317,难道仅仅是指柳宗元的才华出众,而与他立身行事上的道德卓异并无关联?显然不能这样臆断。可以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不自贵重顾籍”[1]318的说法,恰恰是对柳宗元才不为用的惋叹和对柳宗元高贵人品与爽利个性的特别表达。
而柳宗元的文章,尤其是他最富盛名的山水游记作品之特以“峻洁”著称,虽然离不开他在文章创作方面的自觉追求与技法修炼,但内在支撑恐怕还是源于他“不自贵重顾籍”[1]318的放逸豪侠、爽利明净的人品性情,是“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8]461的结果。
二、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峻洁
何焯《义门读书记》曰:“《愈膏肓疾赋》,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4]341反说出柳宗元后期的作品具备“谨洁奥峭”的特点,即当今学界所共识的柳文峻洁、雄深、雅健。
黄震《黄氏日抄》亦曰:“柳以文与韩并称焉。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碑碣等作,亦老笔与俳语相半;间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惟纪志人物,以寄其嘲骂;模写山水,以舒其抑郁,则峻洁精奇,如明珠夜光,见辄夺目。此盖子厚放浪之久,自写胸臆,不事谀,不求哀,不关经义。又皆晚年之作,所谓大肆其力于文章者也。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而非徒曰并称。然此犹以文论也。若以人品论,则欧阳子谓‘如夷夏之不同’矣。欧阳子论文,亦不屑称韩、柳,而称韩、李,李指李翱云。”[3]659这里,即如黄震对柳宗元人品与文章的评论如此苛刻和偏颇,却也绕不开其写山水之作“峻洁精奇,如明珠夜光,见辄夺目”[3]659的客观事实①按:对柳宗元的人品之论怕是未当,毕竟,时世之不同,主观选择又各自相别,这一点下文将作详论。。俞琬《席上腐谈》曰:“作记之法,《禹贡》是祖。自是而下,《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记仪》为第一。其体势雄浑庄雅,碎语如画,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记,法度似出于《封禅仪》中,虽能曲折回旋作碎语,然文字止于清峻峭刻,其体便觉卑薄。”[10]俞琬认为柳宗元的文字太过清峻峭刻,并因此不喜,这只是他个人审美好尚的问题。无论是欣赏还是菲薄,诸家却都认定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峻洁”特征。
这种“峻洁”特征的形成离不开柳宗元的自觉追求和主动学习。柳宗元在《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中说:“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8]336柳宗元从读者的阅读诉求出发,提出时文的创作应以简洁为上。其实,他所关注到的阅读者面对于浩浩文章的感受即使在今天也十分适用:给予读者阅读快感,这是适应读者需要,同时也是文章表达所应具备的素养。而文字的简练明达、立意集中、文简而巧,是一种需长期锻造方能达到的功夫。而在追求文字表达效果方面,柳宗元是长期自觉学习的。
刘禹锡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5]237这正是柳宗元在早期于文章研习方面的努力所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以后,不但自己于文章创作方面更为深入地研磨:“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1]317-318且用心力指导他人的文章:“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318而柳宗元提倡行文峻洁,不只是于“时文”下功夫,更是渗透到对一切文章美感的自觉追求中。为获得这种美感,他极力主张向前人、尤其是向谷梁子和太史公学习。他说:“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8]461这一主张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肯定,黄伯思说:“柳子厚云‘《谷梁子》甚峻洁’,又云‘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信哉!”[11]洪迈曰:“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12]
柳宗元向前人学习的结果如何呢?宋人李如篪评论道:“韩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论,则退之为首,而子厚次之。二人平时各相推许。退之论子厚之文,则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论退之之文,则曰:‘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之文,与退之固相上下,如扬雄《太玄》、《法言》,退之不作,作之加瑰奇。’详究其文,二公之论,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间亦有小疵。至于子厚,则惟所投之,无不如意。”[4]635韩愈说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迁,李如篪觉得韩愈所论甚当。柳宗元文章“惟所投之,无不如意”[4]635的影响力,正是他长期对司马迁文章苦心记诵、自觉学习的成果。不但如此,较之司马迁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另一类写作题材的拓展,是柳宗元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峻洁”创造性地、活泼地运用到他的山水游记中。明人王鏊说:“吾读柳子厚集,尤爱山水诸记,而在永州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读《元次山集》,记道州诸山水,亦曲极其妙。子厚丰缛精绝,次山简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后也。唐文至韩、柳始变,然次山在韩、柳前文已高古,绝无六朝一点气习,其人品不可及欤。”[4]224足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精品地位在后世文人那里已然不可撼动。王鏊论文更是将文章与人品给予密切联系,由行文品格上升到对柳宗元为人品格的高度肯定,王鏊所论是敏锐而具穿透力的。
“峻洁”既是宋人尤先用以褒贬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然而“峻洁”在宋人那里的所指如何?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峻洁”该作何解?这很值得细究。我们不妨从“峻洁”在宋代的指意入手来探析这一问题。
在宋代,“峻洁”可被广泛用来指称自然物象的特征。韩元吉《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曰:“然予尝游天台,至石桥,爱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洁,以求望见所谓方广寺者。”[13]180(《全宋文》216册)宋人张嵲《梅花赋》曰:“潘骑省之植花,氛氲河县;桓司马之种柳,依依汉南。未若兹梅之峻洁,远自托于层岩。格侔蕙茝,志傲冰霜。青枝瘦而依荫,乱蕊繁而向阳。风披逸态,月射孤光。挺出尘之绝艳,吐超世之奇香。”[14]无论是这里所写的泉石还是托于层岩的梅花,它们的峻洁之姿给予人的都是突立、清爽的视觉传达与心理感受,这即是自然物象的“峻洁”特征。晁公遡《王修职墓志铭》更由物之“峻洁”延伸到对人的评价,称赞王湘:“对大官不慑,蹈蛮貊不惧。其得士之正乎!清夫之家,藏其陨齿,有累然璀璨者五,不必验诸浮屠氏。盖如刚松之峻洁,入于地为虎珀者,犹真劲乎!所为至于斯,而不克以受福,其后之人,尚有庆乎!”[13]73(《全宋文》212册)特以“刚松之峻洁”来譬喻王湘的人品。值得玩味的是:即如脱离这一具体语境,“梅”与“松”也一直因其是贞洁刚劲、生命磊落凛然的物象而拥有高贵人格的取譬特征,并一直被视为君子品质的固有象征。此处的“峻洁”,给人以岁月淘洗而不衰的力度之感。
“峻洁”也被广泛用来直接称颂人物的人品、道德、操守。刘克庄称赞汤仲能:“性极高明,行尤峻洁。群谢诸王之外,诚家世之鲜俦;二苏三孔以来,复弟兄之竞爽。”[13]292真德秀《荐知信州丁黼等状》则曰:“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资耿介,履行端庄,出自名家,老于州县,精明峻洁,意气不衰。”[13]291朱长文称赞范师道曰:“范丞相至和中始除文正公之丧,会其族兄龙图公贯之讳师道,自许州通判召为御史,作诗三篇以送之。贯之之孙耕欲刻石,愿有述也。长文窃观贯之精忠峻洁,其为御史,当仁祖之时,中外穆清,而能危言直绳,诋相使罢去。而天子畴咨旧德,登用文、富,继以韩公。”[13]157包恢《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言:“回视公之介焉如石,一砚不取之事,岂不为之愧死欤!仕者苟知此一节,即知公节操政事之峻洁,殆与彼闻风贪人廉,懦夫有立志者几矣,府博士之为是合祠也,孰不曰宜。”[15]。洪咨夔《送监丞家同年守简池三十韵》则称其同年:“或如汉汲黯,抗直敢掁触,又如唐真卿,峻洁不受辱。”[16]121综上,用“峻洁”称述人物的品质道德操守,往往旨在说明这人行事光明磊落、为人性情耿直忠正。可以说,这是充满了褒赞和肯定的用词,并且,宋代以“峻洁”推崇对方人品也多出现在官方公文之中。刘攽《试太学正叶涛可瀛州防御推官监苏州籴纳仓彭汝霖可并太学博士太学录李格非可太学正真定府真定县主簿卢䜣可太学录制》曰:“太学贤士之关,博士正录,皆师表之任也,非其经术修明,内行峻洁,不足以当是选。尔等籍甚士林,或已试庠序,并从迁擢,以究职业。”[13]272洪咨夔《再辞免奏(除翰林学士知制诰)》亦言:“繇唐以来,俱号妙选。学士尤为贵重,自非风裁峻洁,文词尔雅,负王佐器略,罕有迭践二职之真者。”[16]303由上所载,足见宋人对于人物“峻洁”品质的推重与崇敬。
“峻洁”还被宋人广泛用来评述诗文特征。秦观说:“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17]南宋陈造《题〈月溪辞〉后》则称颂“《九辩》《招魂》,峻洁厉严”[18]4443。宋代文人不但多加注目于前代诗赋的“峻洁”之致,同时热衷于品评当时诗文的“峻洁”之胜。陈元晋《跋赵寺丞公茂诗》称:“得公茂所寄吟稿,其间佳处,窃以为深厚如懒庵,峻洁如紫芝,清切如仲白,盖兼儒藻宗英之长。”[18]5115何梦桂《〈王蒙泉诗〉序》曰:“《蒙》取象山泉,盖山下出泉,蒙而始达,泉之本性未失也。蒙泉自号盖取诸此。蒙泉家深谷,日招青山,歃泠泉,寄兴于吟,心静而思清,其得句亦峭刻峻洁如此。”[18]1752他们不但在“序”“跋”中常用“峻洁”概括所评对象的特征,且细审不同作者作品“峻洁”之致的细密区别所在。欧阳修《与陈之方书》曰:“某白陈君足下:某忧患早衰之人也,废学不讲久矣。而幸士子不见弃,日有来吾门者,至于粹然仁义之言,韪然闳博之辩,蔚然组丽之文,阅于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变动往来,有驰有止,而皆中于节,使人喜慕而不厌者,诚难得也。”[13]98显然,欧阳修评价陈之方文“峻洁而舒迟”“有驰有止”,较其称扬葛侍郎“词章峻洁”多了层可寻究的意味。王柏《复天台陈司户书》曰:“足下潜心今古,识见迥特,议论淳正,比苏氏尤为峻洁。苏氏之传惟《伯夷传》实以夫子之言,此为最淳,其论亦简明,抑扬顿挫,有余味也。”[13]114也在“峻洁”中添加了一重“可深味”的要求。朱松《上赵漕书》曰:“窃观执事大笔余波,溢为章句,句法峻洁,而思致有余,此正如韩愈虽以为余事,而瑰奇高妙,固已超轶一时矣。非深得夫圣人所取于诗之意,与夫古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19]显见,宋人所称扬的诗文之“峻洁”,总体要求是言简明而意深厚、有可加追思的余味。
刘克庄《网山集序》曰:“余尝评艾轩文高处逼《檀弓》、《谷梁》,平处犹与韩并驱。它人极力摹拟,不见其峻洁而古奥者,惟见其寂寥而稀短者。纵使逼真,或可乱真,然虎贲之似蔡邕也,优孟之似叔孙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20]又《杜尚书》曰:“公讳杲,字子昕……公淹贯经史,博记多能,《孙》《吴》《申》《韩》《岐》《扁》《严》《李》之学靡不研究,为文初不抒思,俄倾成章,皆丽密峻洁,无一字陈腐。五七言精深,四六高简,散语尤古雅。”[21]黄干《申两司言筑城事劄子》道:“至于都统太尉台判以为‘新城规模乃受敌于堂隍之间,大别山所筑实拒盗于门墙之外。’似此数句,语意峻洁而精到,有非常人所能及。窃以为堂隍周密,则敌不可窥,门墙罅隙,则盗不可拒,此又不可不深思者也。”[13]346(《全宋文》287册)则是要求在表达上“峻洁”,即言明而意锐,见解立出,由一点穿入而可得全局灵透的意思。由此,可见“峻洁”在宋人心目中地位至重,是当时文人自觉的审美追求和对他人诗文加以审美评价的重要标准。戴栩《乐清王次点东岩记》曰:“王君次点,以诗书周官太史班范书束向为人师者二十年。其学长于讲说,引类贯伦,敛博归约,为文峻洁雄特,下笔不自休。走京邑,咸愿馆之。”[22]这种现象,当是宋代文人追求为文“峻洁”的一个小小的生动体现。如此,则黄震所称柳宗元文章“惟纪志人物,以寄其嘲骂;模写山水,以舒其抑郁,则峻洁精奇,如明珠夜光,见辄夺目。”[3]659(《黄氏日抄》)依“峻洁”在宋人诗文评论中的重要性和被推崇程度来看,该是多么高的评价。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峻洁”非惟在宋代获得高度推许,且更如老醇之酒,历久弥香。元人虞集评其《始得西山宴游记》曰:“公之好奇,若贪夫之笼百货,而文亦变幻百出。”[9]619清人储欣称其《游黄溪记》:“所志不过数里,幽丽奇绝,政如万壑千岩,应接不暇。”[9]624又称其《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旷如奥如,至今犹奉为品题名胜之祖。”[9]643清代乾隆皇帝称其《永州万石亭记》:“体物之妙,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于心矣。”[9]603又曰:“郦道元《水经注》,史家地理志之流也。宗元《永州八记》虽非一时所成,而若断若续,令读者如陆务观诗所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绝似《水经注》文字,读者宜合而观之。”[9]624近人孙宝瑄称:“柳所作《浯溪》及《钴鉧潭》诸记,其于刻画山水,状写溪壑,为善绘者所不到。”[23]显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峻洁”既为后世文人所共识、具备言简而意味深远的特质,也是其作品魅力亘久的根源所在。
用“峻洁”评论文章亦源自柳宗元,他评价司马迁文“甚峻洁”[8]461,并向司马迁学习。应该说,他学到了司马迁文章“峻洁”的精髓。但与此同时,柳宗元固然有向前人古文学习的自觉性,其文章“峻洁”特质的形成从根本上更离不开他本人的人格支撑。“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8]461,柳宗元对行文本质的充分认知与实践,达到人与文的浑融才是其文章本色化和久动人心的根源所在。
三、“文以行为本”的认知与实践
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8]461,说明他深谙为人与为文须统一的真谛。这种人、文一体关系的剖析很有代表性。王之望《回张司户手书》亦言:“司马子长为人峻洁,如其文词。自战国之后,士皆溺于权利。子长疾之,发愤着书,以伯夷为传。首凡高奇廉节之士,喜为之称道,如乐毅之去燕,虞卿之亡魏,皆反复以致其意。而于鲁连之说,尤所张大盖,皆有激而云,又性颇爱奇故。所称或过其实,如鲁连之却秦军之类,是大要之必有,所不屑而后可以有为,则一也。”[24]专门剖析了司马迁为人、为文的“峻洁”一体。这与柳宗元“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的认知高度一致。而司马迁与柳宗元文章的“峻洁”,都根源于其人格的峻洁。
宋人评价人物“峻洁”,意在称说其人行事光明磊落,性情耿直忠正。为人峻洁,就是要在人格上保持干净纯粹。司马迁喜为称道“高奇廉节之士”,正在于作者与所称扬对象之间达到了人格上的沟通。柳宗元也不例外,其《段太尉逸事状》曰:“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8]97这里,柳宗元不吝笔墨地称颂段秀实的卓识远虑与所立不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段秀实奇异识见的无比钦敬,又何尝不是一篇推重高奇廉节之士的杰作。这种钦敬的生成和发诸书写,同样源于柳宗元自身所持的忠直原则与人格认知。他称扬仗剑行义的韦道安“一闻激高义”“义重利固轻”[8]617的侠士风度,衷心哀悼苌弘、乐毅等以志节著称的先贤。就连他的山水游记所写风景,也无不饱含着他的人格寄托。或然,清代学者对柳宗元人、文的“峻洁”一体洞察更透。王渔洋说:“贞元、元和间,韦苏州古淡,柳柳州峻洁。二公于唐音之中超然复古,非可以风会论者。”[25]沈德潜也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26]这里,不但指说柳宗元诗作峻洁,且以指说柳诗的“峻洁”正是得其性之所近,无异于是说柳宗元人格峻洁。薛雪《一瓢诗话》称:“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勑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27]更是将诗作风格与诗人的气质禀性做了严密对应。以上虽是论柳宗元诗作与人格的对应,却同样适用于柳宗元人、文的“峻洁”一体。
不止如此,柳宗元文章的“学骚”,也是他和屈原在“峻洁”人格上高度相通所致。柳宗元是受着敬慕的驱动去学习前贤文章、实现人格沟通的创作欲望。诚如清代著名古文家林纾所言:“乃知《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后人引吭佯悲,极其摹仿,亦咸不能似,似者唯一柳柳州。”[28]何以他人摹仿而不能似,唯有柳宗元可似?恐怕正在于柳宗元诚意在心,而与屈原达到了内在相通。刘安称屈原“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9]486。柳宗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称扬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8]282,也正是他自己人格的真实写照。
《旧唐书·柳宗元传》称:“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30]严羽《沧浪诗话》亦言:“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31]沈德潜《唐诗别裁》也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32]柳宗元、司马迁、屈原的“峻洁”,都是为人、为文一体化的结果。柳宗元向屈原和司马迁学习,是异代知音激励的结果,是“峻洁”人格让他们之间超越了时空限制所产生的精神沟通和情感亲近使然。
柳宗元从贬地永州写给朋友的信中明确表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8]409的确,柳宗元贬谪永州后的文章创作多是源自他追求人品“峻洁”的贤者定位而发,也正是将肺腑之情融入创作的成果,是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的文论观的典型体现。而至于宋人对他人格“峻洁”的褒贬取向,则是见仁见智的另一个问题。
宋人程珌在《回交代启》中说:“恭惟某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载难逢之会。章明竑伟以养其器,峻洁廉厉以方其身。小试锋芒,胜有声价。……忝窃一官,徘徊十稔。懔后图之莫计,赖前事之可师。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岁寒松柏,当益观风谊之高。”[13]348-349包恢《州学沂泳堂记》亦言:“其下而藕生污泥中,疑脆弱易污染者,乃反中虚外净,而色纯白,其操同冰雪,若峻洁士处污世不易者。”[33]陆游《与何蜀州启》言:“共惟某官旷度清真,高标峻洁。体道自得,有见于参倚之间;受气至刚,不移于毁誉之际。顾公言之允穆,知追诏之方行,敢意穷途,猥尘上佐。”[34]杨天惠《房季文诔》言:“季文蹷然起,为一再试学官,皆异等。后三年,访予于郫,文益工,行益峻洁。又二年,从予府城之客舍,则胜言翛翛逼人。予曰:‘子何自得此?’季文曰:‘彪比师耆而友谦之二子,皆大士也,请介以交于先生。’”[35]宋人既然在行文中如此推崇这些磊落正直、不流于俗的“峻洁”之士,赞美他们操同冰雪、立世不污的精神品格。又何以会在现时、现世、现实生活中对“峻洁”之士的情性横加指摘呢!其实,综观宋代,虽有欧阳修、黄震等人对柳宗元情性的批评,却也不乏对柳宗元为人、为文“峻洁”的赞誉之声。
郑刚中《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称:“公解褐入仕,历五朝六十年而归禄告老。绍兴乙卯,某为温州判官。公之子行中通守是邦,决除粃政,利敏难事,而又论议踔厉,志行峻洁,无一分巧宦计,僚士窃议是必名教积习所致者。或曰:‘此南丰符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静退,雅不与躁进者争急流,至其耿耿胸次者,则贲、育不能折。”[13]337这里,符行中的论议踔厉、志行峻洁、无巧宦计,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的评价何其相似。显然,无论是这样的符行中或是柳宗元,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行程中都是必要也是必须的存在。
或许倡导情性温醇敦厚代表了宋人的主体审美,但诸如柳宗元、符行中这种有着耿介孤洁性情之士的人格魅力也不会完全沉迹。正如屈原在刘安、司马迁笔下“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9]486,却成了班固所批判的“露才扬己”[36]。
固然,柳宗元的为人“峻洁”不必受到所有人的肯定,但他为人、为文的“峻洁”一体所生发的文章魅力却成了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