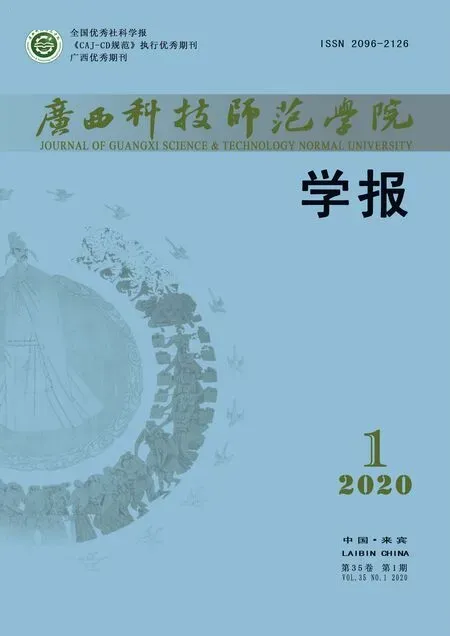创意阅读与创意写作的文本互动
刘 伟
(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海南三亚 572022)
阅读本质上就是一个从符号系统中提取信息并处理的过程,它的内涵和外延都经历了不断地泛化。但不论是通过耳朵还是通过眼睛,是阅读泥板上的图像还是比特化的字符串,阅读作为获取文本信息的方式,一直与写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人脑如同一台计算机,那么阅读与写作就好比录入和输出的过程,阅读以及其他的学习过程为人脑提供各种加工材料,通过创造性的处理,再用写作等表达形式呈现出来,而写作的产品又为下一步的被阅读提供对象,这样完成一个完整的“阅读—写作”闭环。对于阅读而言,写作提供了最为主要的阅读对象。而对于写作而言,在这个链条中,阅读分为前端和后端,对于后端阅读,绝大多数的写作都是为了被阅读,这样文本才能真正敞开和实现完整地符号过程。而写作必要的素材积累、技能习得、经验获得等往往都是通过前端阅读来完成的。
人类经验分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直接经验主要来自写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而阅读则提供了间接经验获取的路径。个体在有限的生命时空中获取直接经验的机会和途径非常有限,而通过阅读中展示的无限时空获取他人讲述的间接经验,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最好的补充。这种间接经验既包含写作内容,即人生故事、生命体验、情感再现、专门知识等,也包括写作的技能习得,通过阅读获得的写作经验和隐性知识。
当然写作只是阅读的目的之一,阅读的最终产品也不一定是通过写作来呈现,但我们讨论的是在完成的“阅读—写作”闭环中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尤其是在写作学视野下,向写作敞开的阅读行为的功能与作用。作为一种创造性和创意性的活动,写作需要什么样的阅读支持,既然写作或者创意写作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精神层面的创造行为,是对文本的创造性处理,那么为写作提供文本支持的阅读活动,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改造,甚至为这些潜在的文本提供“预处理”。由此一种创意的阅读方式,在今天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下就显得尤为重要。
创意写作领域内所谓“创意阅读”(Creative Reading)和创意写作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至少在语源学上追溯,“创意阅读”和“创意写作”都是艾默生(Ralph Emerson)在1837年在相同的语境下提出,某种程度上就是将传统的阅读和写作行为都赋予了创造性特质,由此在写作领域,创意写作兴起并蔚为大观,而作为创造性符号行为的另一端,也就是阅读,理应也成为一种更具创造性,更富有创意元素的过程。从而成为“适应今天无比丰富的创作经验、文本形态、表现形式和创新机制,适应日渐觉醒与提高的艺术欣赏水准,超越传统的阅读方式,赋予‘像作家一样读书’新内涵,形成于这个时代匹配的创意阅读。”[1]
一、创意阅读对创意写作的影响
创意阅读对创意写作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意阅读是通过创造性阅读活动,习得一套文本符号系统及其编码规则,为写作提供一种“潜在文本”和“互文本”。按照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的观点,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那么新文本之所以能纳入到一个文本网络中去,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阅读以及在阅读基础上的写作实现的。如果写作创造了文本,那么前端的阅读就是文本背后的整个互文系统,是通过阅读打造的文本编织物。
其次,创造性的阅读提供了最初的文本生产动力。某种程度上“互文圈”(intertextuality loop)的形成正是通过阅读实现的,也就是“作者作为其他文本的读者,从而使‘读者行为’成为‘在互文系统中的动力要素’”[2]。通过前端的阅读进入到文本网络之中。没有这一过程,写作是无法完成的。而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的写作又是摆脱阅读影响的过程,这也就是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后辈作家总是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促使后辈作家尽力学习传统,这种传统学习就是通过阅读完成的,但传统又成为了他摆脱不掉的阴影,从而在内心充满着“焦虑”。“影响的焦虑”某种程度上暗合着弗洛伊德所谓的家庭罗曼史,前辈作家、文学传统以及经典作品通过阅读成为了新作家写作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父亲”背影。这个背影异常高大有力,随时随地给人以压迫和恐慌[3]。一方面“父亲”的权威非常牢固,他总在引导我们向前走,阅读产生的文本规范和符号技巧约束着新的创作;另一方面面对这种无形的压力而产生的“焦虑”使得后辈中的那些“强力诗人”们并不甘心做“小某某”或“某某第二”,他们试图战胜这些阴影,获得“新生”。“强力诗人”不断地挑战经典和修改传统,从文本网络中挣脱出来,最终通过创造性的“误读”(misreading)和个人才能形成自身的个性化风格。在这里,“误读”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创造性的阅读方式,它将阅读和写作有效连接起来,并通过创造性的形式完成阅读到写作的转换过程。
再次,文本的理想读者本来是由写作过程建构的,写作中建构能够将文本具体化的预想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就是理想读者,他对文本有着完整充分的把握和清晰的认识,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式,对文本全方位的占有。理想读者对作者写作目的、方法、动机等百分之百了解,因此理想读者也只是一个文本阅读的理想状态,并不真实存在。即使作者本人作为文本的第一读者,也并不是理想读者,因为一旦创作完成,作品就是客体化了,中断了和作者之间的联系,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体间的对话关系,而变成主客体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生物实体的作者肯定会丢失很多创作的初衷,对自己的作品也变得陌生起来。但总体而言,原本的理想读者还是更像作者,至少是写作过程中即时即地的作者。但在创意写作中,由于它具有的市场属性,使得它所建构的“隐含读者”并不是面向作者,而是面向市场中读者,我们从读者的阅读趣味、阅读倾向、阅读能力出发建构起一个集体的读者形象。作为写作的“隐含读者”,我们的写作要根据这个“隐含读者”的身份、能力、情感取向等进行写作技巧的调整,所以“隐含读者”反向影响到了写作过程。这种市场读者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作者的前端阅读(尤其是对畅销作品的阅读),建立起“市场读者”的想象,并最终作为写作文本的“隐含读者”,而这种想象包括了对阅读趣味的把握,阅读倾向的研判和阅读能力的考察。
最后,早在新批评兴起的时候,就通过“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误”(the affective fallacy)分别切断了文本和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联系,文本变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某种程度上,的确文本意义并不是先于文字,而是文字先于意义。也就是说不同的作者写作与表达能力是有差别的,下笔成文时有可能存在词不达意或词不尽意的情况,因而作者的意图与文字传达的意义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同样读者感受的个体性差异造成读者的解读与文本意义也存在差别。所以作者所谓的编码规则也就是写作的方式与意图,并不一定能通过类似的解码规则破译出来,之所以没有破译,与读者的阅读水平有关,也与作者的写作水平有关。一个人的写作水平某种程度上就反应在阅读水平上,反之亦然,阅读的水平也影响着写作的水平。而在新批评和形式主义兴起之后,写作过程、阅读过程与文本本身变得疏离而陌生,阅读与写作虽然在学理逻辑上相关联,但在美学效果上已经丧失了联系。在创意写作的同时提倡创意阅读就是通过刻意训练来重新建立写作与阅读的美学联系,不只是我们能够作为读者更多了解作者和文本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我们作为作者在阅读中汲取更多营养。
二、创意阅读对创意写作的支持
在中观和微观的操作层面,创意阅读又在哪些方面影响着创意写作过程呢?或者反过来,创意写作又要求什么样的创意阅读支持?
首先,通过创意的阅读为创意写作提供文本组织形式,这也是最为常见的影响关系。阅读者通过创造性的阅读,在文本网络中习得了阅读对象的文本编码方式,写作时参考借鉴了这种文本组织方式,这里既有对文体的继承,对类型的把握,也有对叙事方式的借鉴,对风格的承续。在文学史上这类影响比较多见,某一流派或者某一团体其实都是一种“阅读—写作”的共同体。当然也可能是一种逆向的影响,也就是通过“误读”形式,完成对前人的超越和改造,新的文体创造、新的类型拓展,新的叙事方式的采用,新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这种逆向的影响。
其次,创造性的阅读为创意写作提供内容和素材。这种影响关系非常常见,就是前文所说的通过阅读来获取间接经验,积累知识、信息、经验和情感,在写作的时候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与运用,最终成为文本内容。这时候创造性的阅读就是一个过滤器和处理器,将通过阅读收集的信息加以选择、梳理和分析,并最终转化为输出文本。不同于上一种影响关系侧重于文本形式,这种影响突出的是文本内容方面。在这一类型的影响关系中,并不需要阅读文本与写作文本之间质性统一,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阅读对象中获得写作元素和原作材料,并通过加工转换构成文本要件。
这种内容上的影响最典型的形式就是续作。因为文本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阅读可以将它展示给更多的读者,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更多的读者会对文本产生兴趣,对文本内容产生情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延续文本作为自己的志业,于是产生了很多续作。文学中的“粉飞客”(源于英文Fanfic,即fans和fiction的缩略词)就是一些读者/观众痴迷于某些虚构的小说或影视剧,热衷于对该作品的续写、改写,同人文学就是这样直接的承接关系。比如美国作家迈克尔·查邦谈到他十几岁时第一次读到福尔摩斯《波西米亚丑闻》的反应是,应该写自己的福尔摩斯故事。后来他真的出版了一部福尔摩斯小说并获得成功[4]。类似的例子在网络文学中不胜枚举。
创意阅读对创意写作的影响一方面是传统的阅读对写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创造性特征,从不同的方向也影响着写作,比如通过“误读”来实现对文本的改造和突破,摆脱“影响的焦虑”。而创意阅读对阅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止包含了基础阅读(elementary reading)和检视阅读(inspectional reading)这样的基础阅读方式,也包含了分析阅读(analytical reading)和主题阅读(syntopical reading)[5]这样创造性的阅读行为,在更为高级的阅读行为中,阅读具有更多的面向,读者的身份也是多元的,包括了“玩味的读者”,也就是第一层次上服从文本指示,主动配合文本中的意图,参与阅读建构的互文网络。还有“释义的读者”,倾向于意义的研究,多重理解文本,能够通过互文网络有效链接其他文本,“同时看出该段文字在被借文本中的意义,在借用文本中的意义和在二文之间流动的意义”[6]。最后是“非时序论的读者”,在连续的阅读中,将文本非时段化,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每一次接受的经验都更新了记忆,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一个事件”[6],从而将阅读变成一个动态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并有效影响到写作过程。
三、创意写作过程对创意阅读的影响
在创意写作与创意阅读的关系上,对对方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创意性的写作过程也会影响到阅读。
首先是通过创意写作训练充分了解文学符号系统的编码过程和编码规则,掌握文本的创意方法,从而在阅读中更容易理解文本表述中记忆、象征与模式,能够更多元实现对作品的阐释[7]。
其次,作者通过创意写作实践发现自身在语言和知识结构中的不足,并通过前端阅读有意识地加以克服与弥补,这样又为写作提供了新的起点。
最后,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通过创意阅读塑造文本生产过程中“隐含读者”和“理想读者”,写作中的“隐含读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阅读经验进行动态的调整,进而调整写作策略,实现读者视野和作者视野之间的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