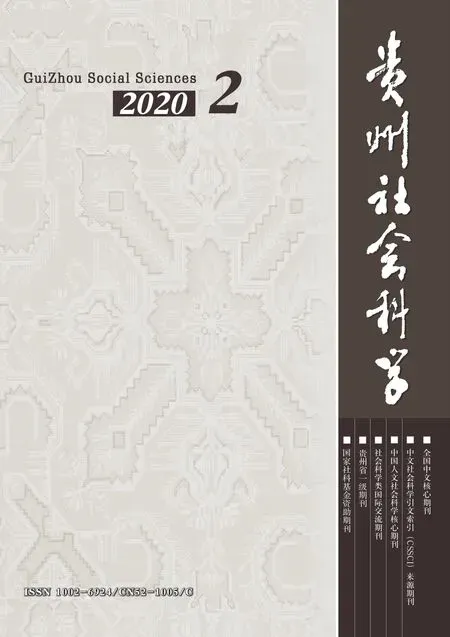从“四书”学的确立看朱熹经典诠释的三重逻辑
尉方语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四书学”实现了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
宋代,从二程首倡“四书”学,到朱熹“四书”体系的构建完成,其根本原因即是排佛斗争的需要。
宋代之前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五经系统,在经学史上,西汉的今文经专注经典的微言大义,但多穿凿附会;东汉的古文经则着重在对于经典的章句训诂与繁琐考据。由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经学依然固守着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解经传统,注重对经典文本的字句解释,而不去进行经典文本中的义理阐发,导致经典诠释停滞于文本的字句本身,只去注解疏义,缺乏理论的创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达鼎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对传统儒学的威胁与冲击是巨大的。佛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即和儒学相结合,吸收儒学的某些因素,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完备形态的理论体系。中唐时即出现“十族之乡,百族之闾,必有浮图”[1]的景象。由于其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不仅获得了下层民众普遍的信仰与支持,而且在统治者高层也获得了某种支持和关注。此时中国本土的道教由于皇室认老子为祖先,更是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也日益扩大,中唐时甚至“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2],朝野上下一时热衷道教成风,道教书箱亦与儒家经典相比肩。此时的儒学虽仍是主流的文化形态,其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依然影响着社会的文化精英,但事实上唐代已然形成三教并存的格局。
从中唐起,士大夫们便对传统儒学进行反思,希望重建一种积极向上的儒学文化形态以与佛教相抗衡。中唐以来,由于佛老思想对儒学的巨大冲击,更由于儒学本身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缺乏对现实的考量,没有精致的理论体系和佛老相抗衡,因而影响日渐式微。对此,一些社会精英人士表示了强烈的担忧。要恢复儒学的权威,改变儒学中衰的局面,就必须拒斥佛老,尤其是要反对外来的佛教思想。可是,以章句注疏及名物训诂为表现形式的儒学的旧有形态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而儒学首先需要对自身的旧有形态进行改造,突破原有的思想体系,重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从中唐以来儒家中的有识之士就出现了一股疑经惑传的风气,同时也开始了对佛教及道教的发难。韩愈是第一个向佛教发难的儒家,他作《论佛骨表》,痛批佛教,认为佛教弃仁义、毁伦常、尚虚无,而反佛教的目的就在于“匡救政俗之弊害。”[3]但他对佛教的批评,缺乏哲学的思辨性,措施也过于简单化,主张“人其人,火其书”。相对于韩愈,李翱对佛教的批判思考的较深一些,主张援佛入儒,而不是简单的排斥。李翱作《复性书》,以思孟学派的思想为根基,主张性善,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4]6人性无差别,人人可以成圣,而“情者,性之动也”[4]6,“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4]12,人可以通过修养工夫,复归到善性。很明显,李翱的复性论融合了佛教的某些理论和修养方法,是在哲学上对儒家性情理论所作的一次创新尝试。
至宋代,赵皇室历代皇帝多为佛教徒,大都对佛教采取了扶助的政策。当时的文人雅士甚或高层政治人物都和一些高僧往来密切。朱熹曾感慨:“某尝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甚害事。”[5]4145“皇帝崇信释氏,士大夫好禅,这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6],因而宋代在思想领域依然面临继续辟佛的任务。
北宋张载﹑二程等辟佛,和唐代韩愈等辟佛不同,不同佛教正面交锋,他们开始从心性理论驳斥佛教。至南宋,佛教依然盛行,朱熹承担起了辟佛的重任。朱熹说:“儒之不辟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不必治。”[5]3963朱熹辟佛和唐代及北宋诸儒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他已不再象前人那样仅仅停留在表层,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吸收了佛教的某些理论成果和精致的思辨形式,和佛教针锋相对地进行心性论方面的论战,在性与天道等理学范畴内对异端进行了批判。
朱熹之所以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构建起“四书”体系,原因在于这四本书是论述心性理论的。朱熹认为,由“四书”生发出的心性理论是足以和佛教理论相抗衡的,亦足以夺回被佛教占领的心性领域。
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始于二程。至南宋,朱熹继续重视“四书”,在绍兴末年同安任上,始编撰“四书”集解,《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经修订后成为《论孟精义》;《大学集解》和《中庸集解》修订后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经不断删改完善,淳熙四年(1177年)定为《四书章句集注》。至此,“四书”学思想体系基本确立。淳熙九年(1182年)首次将“四书”合为一编,刊于婺州,“四书”之名正式出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著作中刊印次数最多、流行最广的一种,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
在“四书”中,《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思想的重要著作,二程认为“《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矣。”[7]44朱熹也非常重视《论语》,对《论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万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此以为学,其卒非离此而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身而已矣。”[8]3615
《孟子》一书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其对儒家的心性理论作了发展,因而受到二程的推崇。《孟子集注》记载二程评价孟子:“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9]244对儒家心性理论的阐发,是后世把《孟子》从子学提升到经学并进而由朱熹把它列为“四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四书”中,《孟子》因其心性理论而备受朱熹的重视。朱熹认为“《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隠、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9]245朱熹看重《孟子》,就在于其中有理义大体,于义理发挥上有益。他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10]644
《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是“五经”之一《礼》经中的一部分。在二程看来,《大学》是对学者进行道德修身教育,由内圣而开出外王的基本教材。在“四书”中,二程极力表章《大学》,强调:“《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7]18又说:“《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7]1204朱熹认为《大学》不仅为“四书”之首,而且是整个治学之先务。因为《大学》提出了儒家学说极为重要的三纲领八条目,系统论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次序。他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10]419又云:“《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9]245
《中庸》重在讲性与天道,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涉及到理学家关注的心、性、道、教等重大问题。朱熹认为此三句“是乃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人若能体察得,方见得圣贤所说道理,皆从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5]3836理学家所进行的心性理论的探讨即是围绕着《中庸》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
这样,通过表章并集结“四书”,最终以“四书”系统取代传统的五经系统,朱熹成功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文本的重心转换。而《四书章句集注》是对二程倡导的“四书”学的一个历史总结,是“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其本身又是朱熹经典诠释的代表力作之一,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经学形态,其主要特点就是发挥义理,不在名物训诂上下过多工夫。《四书章句集注》以新的范畴、新的观念及新的解释方法,表达了诠释主体的创新精神,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
二、通过“四书”系统建立起经典诠释形上本体
宋代,佛学对儒学的严重威胁和儒学的式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学在形上层面上的不足。两汉时的佛教,其理论形态并不完备,当时的社会影响也不大。但经魏晋时玄学家们对“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的争论,使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能力大为增强,并且玄学的这些哲学范畴与佛学的“万法皆空”、“涅槃寂静”等理论存在某种程度的相通之处,这样,佛教便通过玄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在理论思维形态层面上高于儒学。同时,由于儒家自唐代以来长期的排佛,使得佛学自身也不得不作出某种改变,不断调整与儒家的关系,隋唐以来事实上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流派。
宋初的理学先驱们看到,强调伦理道德及心性修养的儒家传统经世思想,由于其思辨理论上的疏略,导致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构建一种新的思辨儒学形态,以与佛教相抗衡,就成了理学先驱们的当务之急。在与佛教的斗争过程中,理学家们为了重新确立儒家的权威,首先要构建一种新的经典文本体系,实现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至南宋,朱熹“四书”体系的确立完成了这个任务;其次是要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对儒家的经典文本重新解释,以突破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以义理说经,这就需要有一种形上的本体的依据。
宋代理学家们为了构建一种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是借鉴佛、道二教本体论理论上的成果,二是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找寻构建形上学的因素,《论语》、《孟子》、《中庸》中关于性与天道的探讨,都是他们借鉴的因素。在吸收这些外来的和传统成果的基础上,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形上学本体概念,如太极、太虚、天理、心等。北宋在程颐之前的诸儒,有的也论及到理,但都没有把理上升到本体的高度,而是把“理”理解为文理、条理及事物之规律性等,直到二程,才开始把理上升到本体的高度,视为宇宙的本原。程颐首倡“天理”说,认为“天者,理也。”[7]132“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7]424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天理是最高本体,程颐以天理为宇宙之本原。南宋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二程的天理观,建立起系统的天理论的思辨哲学体系。“天理”这一本体,是理学家们经典诠释活动的根源,是理解活动的支撑,也是他们诠释活动的形上依据,在朱熹看来,天理、圣人之言、圣人之意三者三位一体,经典是圣人之言,体现了圣人之意,同时也是天理的体现,必须以天理为形上依据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符合天理的即是合理的诠释,否则就是对经典的误解。
在构建理本体论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朱熹首先分析了佛学的高明之处及儒学在理论方面的欠缺。他指出:“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何故?盖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自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禅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得入,则前后际断,说得恁地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也去,此却是他实要心性上理会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5]3959朱熹认为“吾道之衰,正缘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11]2268朱熹看到了佛教的高明之处,也对儒学中衰的事实从自身寻找了原因,应该说,朱熹也找到了辟佛的良方,即从心性上理会,而且这种心性理论不必外求,儒家的经典文本中自有心性理论的思想资源。因而重新诠释“四书”,利用其心性理论创建一个思辨性的哲学体系以与佛教相抗衡,就成了宋代理学家们的迫切任务。
我们知道,孔子不但“不语乱、力、怪、神”,而且就心性而言也很少涉及,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9]103此处之文章,主要是有关诗书礼乐的学问,包括语言、行为、举止及待人接物等德性外在形式表现,而内在的人性、天理、天道的学问,由于理解者悟性不足等原因,很难听得懂领会得好。对于这些“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朱熹为什么如此重视呢?很明显,朱熹是想从性与天道入手,创构一个思辨的形上哲学体系以与佛教相抗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朱熹将汉代作为传记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提升为独立的儒家经典,并最终取五经而代之,其因即在此“四书”主要讲述了儒家的心性天道理论以及伦理准则,而尤在义理层面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朱熹出于构建理学形上体系的需要,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四书”中的义理作了不同的阐发。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又精致严谨的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四书章句集注》集中阐发了其哲学思想。
在“四书”中,朱熹非常看重《大学》,通过其中的三纲八目,朱熹阐述了穷理、正心、修身治国之道,而且他还作“格物致知”论,作为《大学》的补传,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9]20可以看出,朱熹天理论的思辨哲学体系涵盖了宇宙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等几个方面,从而使得其思想体系相对完整。
《论语》记载着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的体现,在《论语集注》中,朱熹用天理、人欲、本心等概念对《论语》作了理学的诠释,这种诠释的思想观点已与经典文本本身的原意甚远,体现出朱熹正是根据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而对经典文本做了符合自己需要的理解。
朱熹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与心性理论密切相关,在《孟子集注》中,朱熹利用《孟子》中的心性论、天道观、人性论、道统论以及本心、修身、仁政等思想,阐述了他的天理论、心性论、修身论等理学思想,将儒家的政治伦理提升到哲学高度,其对义理的阐发比《论语集注》更为突出。
《中庸》一书语义深奥且富有哲理,其探讨的性、道、教以及儒家道统心传等问题是理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从唐中叶韩愈、李翱到北宋理学先驱,都极为重视《中庸》,《中庸》中的深奥思想正可以为理学形上思辨体系的建构提供思想素材。理学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哲学化表述,可以看到,《中庸章句》正是朱熹构建他的理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展开论述了他的理气论、理一分殊、人心道心等理学思想,说明至此他以天理为本体的思辨哲学体系已变得精致严密。
朱熹在对“四书”的重新诠释中形成的《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成为“义理之学”的代表作,是因为朱熹新的理学思想体系与新的经典诠释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结合社会现实,通过重新诠释“四书”,朱熹建构起了一个能在心性领域和佛教相抗衡的思辨哲学思想体系。
三、兼取汉宋的“四书学”经典诠释方法
对于朱熹而言,“四书”作为理学的经典文本,是理学体系建构的文献依据,理学思想体系即是从“四书”中引申出来并经过发挥而建构起来的。“四书”是孔子及其后学在先秦时代即完成的一整套有关社会政治伦理、文化及教育等在内的学说体系,它如何适合于千年之后的两宋文化思想的需要呢?问题在于,必须对“四书”重新进行诠释,从中整理出一套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理论体系,这即是理学。可以说,没有对“四书”经典文本的重新诠释,就没有理学的产生。
从对经典的诠释而言,理学是一种义理之学。宋代义理之学取代汉唐训诂章句之学,实际上是经学形式的转变。宋代,理学家已由汉儒对圣人的盲目崇拜转而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圣人。事实上,从汉代王充起即批评汉儒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12]宋儒从周敦颐开始,认为圣人可学而至。二程则更进一步,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认为“人与圣人,形质无异,岂学之不可至耶?”[7]203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理学家们逐步摆脱对圣人的盲目崇拜,开始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以自我为中心重建适合现实需要的精神道德体系,程颐说:“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7]671在程颐看来,经是圣人载道之书,求圣人之道必由经。但学者为什么“不得其门”而入呢,原因在汉之训诂章句之学,未由经及道。因而要探究圣人作经之意,必须寻求对经典文本的全新解释,这种新的解释不同于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它重在发挥经典文本中的义理,把握圣人作经之道。张载说:“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13]儒家释经的逻辑前提是经典的先验正确性,因为经典乃圣人所作,是神圣不容置疑的。而章句训诂之学的繁琐容易导致歧义多出,且得到的往往是文本的字面意义,很容易偏离文本本意。因此在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中,重章句训诂的汉学一直受到重义理的宋学的非难。
朱熹作为宋学的代表,重视宋学对经典文本的义理阐发,但他也同样重视汉学章句训诂的方法,可以说,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是兼取汉宋,在他看来,章句训诂和义理阐发只是揭示经之本意的手段,重要的是求得本文本意,得圣人之指。他说:“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11]2213那么如何才能求得本文本意,得圣贤之指呢?朱熹谈到自己解释《孟子》的体会时说:“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14]1352朱熹此处提出解经分为三步骤,首先是对经典字面意义的解释,其次是对经典文本本意的解释,三是根据文本本意进而阐发出新的义理。
无论是求得经典的字面意义还是文本本意,都是通过文本的语言去解释文本,这是一种语言解释。经典文本就是由文字语言固定下来的作品,对经典文本的语言解释便是解释文本的重要环节之一。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15]“惟本文本意是求”,说明朱熹相信经典文本有一个原意、本意,而且认可语言是通达本意的桥梁。
在追求文本本意的语言诠释过程中,训诂是必要的手段。朱熹重视汉学训诂考据的方法,肯定其在训诂考据方面的成果,认为“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8]3631而朱熹本人于训诂考据所下功夫也颇多,他说:“某所集注《论语》,至于训诂皆子细者,盖要人字字与某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闲看过了。”[10]349训诂考据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8]3583汉学章句训诂的释经方法寻求的往往是文本的字面意义,容易忽视对文本义理的把握。而朱熹则认为训诂不仅能把握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还是达到文本义理的重要手段,因而对汉学只重训诂考据而不及义理甚或忽视义理探求的解经倾向提出批评,朱熹说:“圣人教人,只是个《论语》,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论语》须是玩味。”[10]652又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之归”[8]3640,“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5]3600。朱熹的“四书学”,在经典诠释方法上,将汉学章句训诂的方法与宋学义理的方法加以综合,认为“《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8]3630,因而诠释儒家经典,重在阐发义理,朱熹在对“四书”的诠释中处处体现了这一解经原则。
对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是义理阐发的前提,义理阐发并不能完全脱离章句训诂之学。但自北宋诸儒以义理之学取代章句训诂之学后,尤其二程之后,以己意解经风气日盛,以至其弊日显。对此,朱熹深感不安,他说:“近世儒者,不将圣贤言语为切已可行之事,心于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论,屈曲缠绕,诡秘变怪。不知圣贤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转相授受,复以欺人。某尝谓虽使圣人复生,亦只将六经、《语》、《孟》之所载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为。”[5]3612至南宋,此风日盛,有些学者甚或“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8]3640,“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传注”[16],在释经时完全舍弃汉学训诂考据的工夫,置经典文本于不顾而空衍义理。对此,朱熹认为训诂考据是义理阐发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8]3831,“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5]4028由此朱熹对张栻的《孟子解》提出批评说:“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辗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14]1352
朱熹重视对经典文本的义理阐发,同时又不废章句训诂,这是朱熹的经典诠释原则,也是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这一方法使义理探求与章句训诂相结合,也使得朱熹超越了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的狭隘局限。这一解经原则,在朱熹对“四书”的诠释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朱熹重视训诂考据,并力求在此基础上阐发义理。朱熹说:“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17]。朱熹在谈到《论语训蒙口义序》的编写时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8]3614这样,对文本通其训诂、正其音读的工作便与对义理的发挥相结合,从而避免了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的弊端,使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达到新的高度。
四、结语
朱熹以其新的“四书”系统取代旧有的五经系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新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新的文本系统,是对当下现实的考量。新的文本体系的确立,面对的是社会现实。新的“四书”系统是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典范,在新的文本基础上,朱熹还论证并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据此建立了完备的理本体论的哲学体系,这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在此基础生发出的一系列兼取汉宋的经典诠释方法,则为创建中国经典诠释学提供了完备的素材,也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