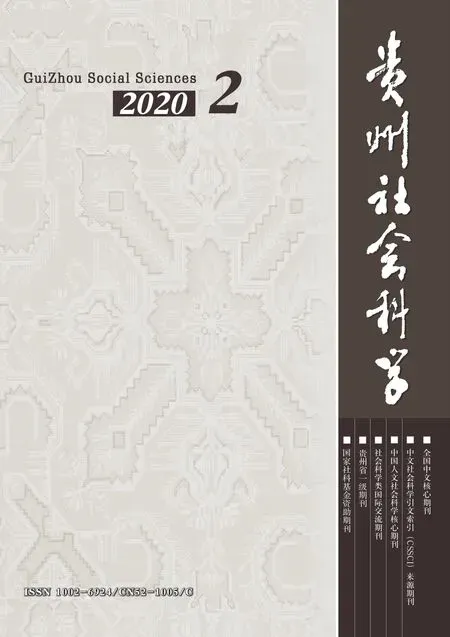从科层化到网络化:重大疫情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朱海龙 唐辰明
(1.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2. 湖南大学,湖南 长沙 3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2月,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2020年2月8日经国家卫健委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至2020年2月初,感染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期间,虽然相关部门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了疫情的防控,但仍然暴露出诸多矛盾与困境,如志愿服务与慈善服务信任结构不稳定、疫情相关谣言屡禁不止、网络诈骗频出等,导致相关防控效率降低。在重大疫情发生之时,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了医学、生物学及化学等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关注度居于其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重在解决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直接问题,针对疫情与病毒等传染源本身,从医学与生物学等角度发掘控制、监测、治疗等多方面有效防控手段。但重大疫情防控效果的根源问题研究,也应包括政府治理能力分析、社会舆情引导、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人文社科方面理论与实践创新对于重大疫情防控的根源性、促进性与引导性作用,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总的来看可归纳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三类主要疫情治理模式。
首先,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自上而下,主要是以国家手段为基础进行治理与防控,体现的是国家力量的行使,主要表现为行政与法治治理,即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法治、政府与相关部门治理能力与治理模式创新。如李凌等分析了重大疫情背景下行政强制的法治创新必要性与其独有特征[1]、李燕凌等基于博弈论视角,分析了政府干预在疫情防控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正负效应。[2]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突出了国家力量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中心化特点;其次,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一些学者十分重视基层组织与机构在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王静认为基层人员的素质与综合管理是防控全国性重大疫情的最重要因素之一[3];李凌认为,基层模拟演练是重大疫情防控中应急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4]。该类研究注重基层工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基层的工作效能需要层层上传至国家中心,不仅体现了中心化的工作特征,还表现出层级化的缺陷。再次,上下结合的模式。上下结合,即国家力量与社会公众力量之间的融合,加入社会公众力量、舆情力量,则更多地体现出伦理、道德方面的特征。即从伦理学、社会舆论等方面出发研究了人文情怀与舆论引导的启示等,如 Theodore强调,舆论不能仅仅与商业利润挂钩,[5]Parick阐述了舆论与权利、特权之间的关系,[6]徐林林以山东甲型H1N1流感中某感染者遭受网民“炮轰”事件为例,分析了网络环境下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7],这是较早地将疫情、舆论监督、网络社会特征等方面相结合的新的社会背景下舆论监督理论的创新性研究。
综合看来,三种模式总体上均为科层式社会治理模式。科层式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集权式管理模式,特征在于多层次的信息传递机制、中心化的管理体制、单一化的衔接方式。其早期起源于企业管理的理论体系,且多用于股份制改革时期企业的主要分析内容,其前提是集权体制的形成,如权力转换、动员模式等存在着“伞状”的形态;[8]同时依赖着领导中心的权威、层级之间协作等基础以进行运营[9]。而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因素开始融入社会,乃至智慧化概念的提出后,该理论体系开始体现出其不适应之处。网络化与数据化的内容包括数据技术、多元化联系、隐性风险与共享性行业特质[10],具体体现在网络化背景下的诸多社会规律与行业领域特征都发生的巨大改变,如网络化导致的民众思维与观念的转变[11]、经济领域开放性新格局与多元性平衡局面的形成[12]等,其特征包括多元化、扁平化、去中心化及云连接,同时其运行基础在于数据互联、网络空间,而非科层式中的集权基础。
在这种网络化社会变革背景下,集舆论引导、社会服务与工作动员、经济与行业配合为一体的疫情治理模式,理论上也将发生巨大的特征变化,如治理模式总体框架中,疫情防控工作手段的变革[13]、疫情信息传递模式的改变等等。[14]另一方面,传统疫情防控手段体系与治理模式在当下的疫情特征面前适应性不强。传统疫情防控中,以SARS防控经验为例,2003年SARS病毒传播性与感染性强、病死率高等特征,是当时防控工作中最主要的难点之一,[15]而当下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防控过程中的背景、特征、应用手段均有所不同,首先,高铁的开通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交通效率,民众移动与联系的特征与2003年有所区别;其次,网络化社会变革过程中疫情信息传递、相关舆论引导等数据性工作开展特征较之2003年非典时期也有所变化。总而言之,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的重大疫情防控与治理模式相关理论应当更为充实、适应与有效。
故具体来说,已有研究具有以下可完善之处:其一,舆论监督与引导的网络化与数据化理论体系需要进行更新。本世纪初的网络化舆论引导虽然提供了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启示,但大数据环境下的各类思想、言论、行动特征都与之有所区别,需要基于数据化特点进行相关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扩充;其二,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工作开展与当下人口流动、思想传播的特征也不相适应。学者们对基层工作的开展、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分析,虽然挖掘出相关治理能力的缺陷,但其与数据化社会运行特征的矛盾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其三,新的社会背景下新科技引发的诸多重大疫情防控矛盾化解战略并没有纳入新科技本身的治理效果。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数据驱动的信息交互效率性、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并未得以系统的应用。虽已有文献提出了一些系统性观点,但呈现出来的却是碎片化的思想。基于此,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重大疫情防控,需要进行以下研究予以应对:一方面,传统疫情科层化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逻辑特点,其与现实防控需求之间存在怎样的不匹配;另一方面,应当构建怎样的网络化模式,来进行创新的、科技的、高效的应对。
二、现有科层化疫情治理模式的基本逻辑
为探索重大疫情背景下的多方面矛盾的本质,防控过程中遵循的基本逻辑应是关注重点。通过分析可知,病毒防控需求、民众情绪引导、物资调配与具体防控工作开展等多方面诉求体现出的分布式、指数性特点,与实践操作中的科层化模式存在着极大的不匹配,并因此造成了防控效率的下降。
(一)管理体制的中心化
中心化是现有疫情治理模式的首要特征之一,即资源分配、战略控制、过程调整等行动均以中心化调控机制为主进行,以物资分配为例,2020年1月底2月初,网购平台“口罩类”物品开始限制购买,转由官方优先控制并予以具体分配。该做法原意为优先供给武汉等重点区域,但却被部分商家等供应者钻了空子。一些供应者哄抬价格“发灾难财”,更有一些供应者用回收的手段提供劣质甚至极具危险性的口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控制力度被防控疫情本身所吸引,相关惩治力度难以到位,另一方面则是中心化物资分配模式的低效缺陷。如上文所述,物资、信息等方面的需求是相联系的,都具有分布式、指数式的规模扩张,中心化的物资分配模式需要经过至少两个步骤即统一收纳、定点分配,这一过程在分布式的需求面前极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心化的治理在现实中面临的矛盾主要包括信息提供与物资分配两方面。信息方面,疫情相关信息诉求的满足来自于外部,人们对相关疫情信息、居家防控指南、权威医学指导等信息具有诉求,这些诉求在当下急需满足,另外疫情相关谣言、利用疫情进行诈骗等的控制与处理,亦对当下防控工作体系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这些信息诉求,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在疫情初期都呈分布式、爆炸式和指数式上涨,原因是互联网环境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导致的需求增长。物资方面,因为传染人数逐渐增多、增速提高,又因为权威信息与谣言夹杂,物资需求可能并非完全合理,且诉求进一步增加,增速也有所提高。如“戴三层口罩有利于进一步预防感染”等谣言可能使得民众口罩需求瞬间提高两倍;对“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病情”中的“抑制”一词理解不到位,也可能对并不那么急需的物资提出不必要的需求。同时,志愿者行动、慈善捐赠等物资与服务公信力不足,公众对其信任度较低,信用结构趋于不稳定,需要进行控制与完善。结合看来,信息与物资等多方面诉求也呈分布式、指数式上涨。传统中心化的治理模式与这种分布式与指数式的需求增幅不相适配,将产生较低的防控效果。
(二)信息传递的层级化
现有的疫情治理模式中,信息传递、指令下达、工作开展的另一个基本逻辑特征即为层级化。以信息上报为例,疫情爆发以来,民众对武汉方面信息传递、疫情上报情况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与相关评论,尤其在病毒感染人数、防控手段等方面,武汉政府遭到了较大责难。事实上,若仅关注技术性问题,层级上报的信息互通手段、数据交流方式在该疫情背景下也是不适用的。分层式信息管理模式本质上也是中心化的管理方式,需要逐级上报,在上报的过程中,时间、效率方面都与病毒传播的速率不相匹配,容易造成信息交互不及时、防控效果不达标等后果,并可能因此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现实情形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疫情信息采集方面,当下的信息采集方式一般最低以村镇为单位,并逐级上报县、市,上级再据以作出相应决策;同时,封村、封城等“休眠式”防控手段在不同区域步调不一,防止人口流动的目的可能难以达到。例如,相邻县市的封城情况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传染者进行流动,又如禁入、禁出的不统一,也可能造成潜在感染者的出现。但基于现阶段的信息交互思维,步调一致又将重新陷入层级化的窠臼。
以舆情引导为例,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为恐慌情绪及其指数。恐慌指数即所谓疫情背景下的恐慌,是普通民众对于该病毒的恐惧、担忧心境,讨论该恐慌的意义在于,信心是打好防控疫情战役的重要部分。恐慌情绪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民众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配合度,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疫情工作开展的效率。谣言四起、经济停滞等多方面问题恰是因为恐慌情绪的存在才会大规模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恐慌情绪的扩散与传播,可能较之病毒本身更为严重。病毒的人传人特性因交通、春节集聚而得以分布式扩散,但该恐慌指数的上涨幅度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数据的传播而提高的。众所周知,在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速度甚至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间隙,呈现出高流动性、无边界性的大数据,使得相关恐慌指数上涨形式较难控制与引导,在该信息与数据层面,层级化的信息交互模式实难适配、应对。
(三)联系方式的单一化
单一化一般指的是传统的防控工作过程中,对接方式一般是点对点的、具有单一匹配性。与上文层级化驱动不同,点对点模式的管理模式的主要缺陷集中在成本方面。如物资分配、指令下达等,不仅具有层级化的缺陷,也具狭窄性缺陷,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与资源共享单位量不成正比。尤以信息资源为例(如防控信息、工作安排信息等),点对点模式中的提供需要较大的管理工作量,信息交互困难较大、工作成本较高。
现实中,从疫情防控的现实需求看,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分布式、指数式的特征,这一特征为现实防控模式的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单一化防控工作模式难以应对。具体而言,其一,传染人数方面,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背景较之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具有不同的特征。我国高铁的兴起提高了交通速率与人口流动、接触的频率,加之首例冠状病毒传染事件发生在临近春节这一特殊时点,人口流动频繁,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概率大规模上涨。同时,因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病理性特征,人传人的传染模式极易产生无症状感染者,亦增加了防控的难度。钟南山院士提出,2020年2月6日(即第一次全方位隔离后14日)可能不会出现增速下降的情况,并可能存在第二阶段的潜伏期。这一第二阶段的潜伏期的存在原因,有相关学者提出“ABCD模式”进行解释,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潜在感染者B这一群体的不确定性,加之该病毒的传播特性,决定了这一次病毒感染人数的分布式、指数式增加特点,防控难度较大,单一化模式已难适应。
三、重大疫情治理模式的网络化变革
新背景下的重大疫情应对因加入了网络化引发的信息互通、高铁开通等交通因素引发的人口流动特征改变,其分布性、指数性与网络性,与传统管理模式、科层式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心化、层级化、单一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不适配。应当将传统模式中的中心化、层级化与单一化向去中心化、扁平化、多元化转变,其中较为科学、有效的技术手段,则为运用引发现实社会变革的科技因素,即大数据驱动、区块链与云计算等,以满足适配当下具有科技化、网络化社会特征的新型重大疫情防控需求。
(一)区块链:中心化向去中心化转变
根据上文所述可以看出,防控效率的提高、信息交互模式的创新、物资与数据分配的合理性完善,需要从中心化向去中心化转变,也需要从层级化向分布化、网络化转变。这一特征的启示,是新技术的转化应用,即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区块链技术,主要是以区块的形式,对不同时间点、不同类型的交易、合同等事件进行记载,并按照时间等要点进行排序,形成链条。同时,在链条中介入复数计算机系统对其进行记载、储存、更新、认证,并形成账簿,且该类账簿与计算机系统一一对应,形成复数系统,即“分散式”账簿系统,体现的是分散化、去中心化、稳固化的特点,其运用优势在于去中心化的分散式账簿难以篡改,不易发生记载错误,并将传统的中心价值予以弱化,用以弥补上文所述的缺陷。同时,预设的算法使得相关活动可以自动运行,并可由主体自行验证,在争议、救济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实践中,可以采取区块链技术,将每一地区单位作为一项账簿记载在相应的链条上,并以相关计算机系统予以存储,预设相应的算法进行物资分配、隔离观察等行动,同时可以将不同账簿与民众诉求等方面进行交互,一方面可以稳固相关防控行动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可以满足民众的信息、数据等需求。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等方面也可因区块链的不可更改性而提高稳定性、增强公信力,完善现有信用结构与机制。
(二)数据驱动:层级化向扁平化转变
层级化管理的缺陷,在多学科中都有所体现,如管理学、法学等,层级化主要因其信息交互速度缓慢以及信息传递失真等而使得各方面管理效率降低,层级越多,金字塔形管理结构越为陡峭,信息传递困难则越大。在重大疫情背景下,该缺陷因现实需求的紧迫性,将体现得更为突出。故应将传统的层级化管理模式、信息传递模式变更为扁平化、网络化模式,采取的转化手段则为新型数据驱动理论及应用工具。
数据驱动即为“社会物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数据化社会运行、管理体系,其以彭特兰为代表,其核心为大数据与移动设备等智慧化因素的转化应用,即利用大数据的交互驱动力,推动社会各领域之间的数据互通、信息互联,促进社会各层之间的供需、运行形成协同效应,同时破除传统普惠性、单一性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个性化精准匹配。[16]彭特兰的基本原意在于利用可穿戴设备等智慧化工具采集信息并利用数据驱动手段进行信数据信息归类、分析、导出、运用等,其在管理层级与模式、疫情防控过程中也将大有可为。如搭建相关数据中心或平台,利用相关数据设备收集信息与数据,形成扁平化数据共享体系,使得疫情数据、管理信息等通过数据平台进行调取、归类与传递,实现数据信息的交互高速化、效率化、真实化与动态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数据中心与数据平台并非前文所述缺陷体系中的中心化信用体系、中心化管理结构,而是指数据和信息在数据中心与数据平台中经过云计算过程,并进行导出与交互,该“中心化”是技术化的中心,而不是管理化的中心,不具备中心化管理模式具备的效率缺陷,反而将提高相关效率、科学性。
(三)云交互: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针对疫情治理的成本方面,应当将单一化模式转变为网络化管理、交互模式,以满足网络背景、大数据背景下的多方面诉求。而“网络”的另一个称谓,则为“云(计算)”。关于云计算,现阶段至少可以找到上百种解释。较为权威的,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定义为:云计算是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分配的网络访问模式,事实上,“云”本身就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称谓。云计算又可称谓并行计算(Parallel Computing)、分布式计算(Distributed Computing),据此可分析其特点,包括共享、精准匹配、管理投入成本小、交互量小,但信息资源分配、储存效率较高。云与网络化计算的并行性和分布性,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是现阶段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化模式创新的有效手段。[17]首先,其适配了现阶段舆论引导、网络化治理的数据性需求,可以有效应对网络化与数据化背景下的社会特征[18];其次,云计算的应用有利于反向促进上文所述的扁平化变革与去中心化转变,并且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方面的运行基础。最后,云计算的虚拟化与规模性可以大幅降低实践中的管理投入,并在紧急情况下有效地进行事件的预防与控制。
四、结语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型科技因素,不仅带来了社会发展新机遇,也带来了诸多现实性矛盾,在重大疫情的背景下,感染人数、舆论传播、恐慌情绪、谣言与诈骗信息等问题即为其体现。上述科技因素也同时提供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体系与思维、理论体系。中心化向去中心化、层级化向扁平化、单一化向网络化等方面的转变,是新科技因素提供的自我调控机制,在现实中则需要专门机制将其防控价值释放出来。具体到重大疫情防控背景中,疫情防控工作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舆论特征与科技特征,高铁、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因素融入社会各领域后,重大疫情的特征也随之改变,需要利用新型科技本身的特征予以应对与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