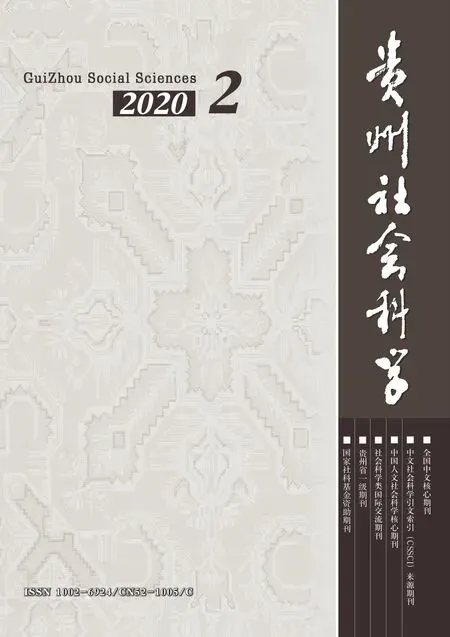《周易》铸就中国文化三大传统
卢祥运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不断理性化的“巫史传统”,是从文化传承和族群信仰层面对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作出的理论诠释。巫术和各种卜筮活动是“巫史传统”的核心。作为上古卜、筮活动的资料汇集和系统总结的《周易》,一方面,上承“巫史传统”,系统荟萃了上古以来的巫术及卜筮活动的经验成果;另一方面,在其长期的成书演变及传播过程中,形成铸就了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文化形态的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以及民间社会层面上的吉凶文化传统。《周易》在演变中形成铸就中国文化三大传统,充分体现了其对于中华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一、“巫史传统”及其理性化进程
中华上古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脉所在,如何描述和说明中华上古甚至远古以来的文明发展进程,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论题。李泽厚先生对此提出了两大理论诠释:“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1]33“巫史传统”是从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层面对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作出的理论概括。同许多古老文明一样,巫术也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文化形态。“巫史传统”之“巫”,在上古有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这种“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亦即神人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取代神权,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1]34-37。由“巫”而“史”的转化,是巫史传统形成的关键。《礼记·礼运》说“前巫而后史”,上古时期,“史”是继“巫”之后进行卜筮和祭祀活动而服务于君王的总职称。卜筮活动与原始巫术直接相关,可以看作是由原始巫术发展出来的一种静态形式。由原始巫术中群体(或个体巫师)常常带有舞蹈动作的动态活动,演化为卜筮活动中带有个体相对静止的数字演算形态,标志着由“巫”到“史”的逐步转化。卜、筮活动脱胎于更为原始的巫术礼仪,但仍然保存了原始巫术礼仪中的许多特质。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始终有理性化进程相伴随,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巫史传统,也始终伴随着“巫”的理性化进程。“巫”的理性化,是指原巫术活动中的各种神秘的情感、感知和认识,日益取得理性化的解说方向,其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消减,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增强的过程。上文提到,卜、筮活动的出现,是巫史传统中由“巫”到“史”的关键,也是“巫”的理性化过程的重要环节。“筮,数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汉书·律历表》)。筮即是数,《周易》中的八卦是由数演变而来。《周易》当是上古卜、筮活动的资料汇集和系统记录。我们今天还能透过《易》中的卦爻辞保存下来的许多上古时期的资料和史实,隐略窥见当时卜、筮活动的一些概貌。《周易》中八卦数,六、九数、天地数等都表明,数在卜、筮活动中十分重要,而正是卜、筮活动中的数字演算和卜骨纹路的符号判别,使卜、筮活动本身具有了更多的理性认知的成分。周易的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其中记载的历史的经验和史实,仍然与原始巫术活动中的“神示”“天意”的观念混合在一起,这是“由巫而史”的理性化过程显示出的突出特点。
传说中所谓诸“圣人”作“河图”、“洛书”、作八卦、作周易等等,正表明巫师和巫术本身的演变发展。这也就是“巫术礼仪”通过“数”(筮、卜、易)而走向理性化的具体历史途径。……总之,本在巫术礼仪中作为中介或工具的自然对象和各种活动,都在这一理性化过程中演化而成为符号性的系统和系统操作。它日益对象化、客观化、叙事化,却又仍然包含有畏、敬、忠、诚等强烈情感和信仰于其中。[1]47
巫史传统中的理性化,不仅使原始巫术活动中的许多方面日益对象化、客观化、叙事化,亦即渗入更多人间的、现实的、理性的成分,而且仍然保存着它的一些带有超越性的情感和信仰。
巫史传统揭示中国上古思想史演进的历程大致经由自然思想到鬼神思想,再到人文思想三个不同的时期,易学的发展也与之相偕而行。对应于三个时期,易学也由伏羲时的符号易,演进到文王时的筮术易,最后发展到孔子为代表的儒门易时期。符号易时期,易学只有八卦符号,无文字,这表明当时人们的思想更多的是自然思想。筮术易时期,易学被用于占断吉凶,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有了卦爻辞,君王借神道以设教,人们相信鬼神,用卜卦预知吉凶。儒门易时期,此时人智大开,孔子以哲理赞易,援易人儒门,借易阐扬其人文道德理想。此时易学除儒门易外,尚有老子的道家易与残存的筮术易,此三支并立,经由后来各自的不断演化,形成了本文所说的三大文化传统。
李泽厚认为,如果说儒家着重保存和理性化的是原始巫术礼仪中的外在仪文和人性情感方面,老子道家则保存和理性化了原巫术礼仪中与认知相关的智慧方面。《老子》书中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绵绵若存”等语句,闪烁出的正是神秘的巫术礼仪的原始面貌[1]65-66。我们认为,就《周易》言,如果说儒家着重通过“吾求其德”“和顺于道德” (《周易·说卦》)汲取了其中的顺时应变的思想和道德精神,道家(尤其道教)则透过八卦系统对应的自然之象及其所寓含的占断吉凶的功能而汲取了其中的自然主义和生机主义的原始智慧。而筮术易后来逐渐下沉到民间,形成了内容更加庞杂的以各种术数为核心的吉凶文化传统。这三大传统都与《周易》的成书及传播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
二、和顺于道德:儒家的道德主义传统
作为卜筮活动记录文献的《周易》铸就儒家文化传统的突出体现,是原始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巫史传统。巫术和各种卜筮活动是巫史传统的核心,正是原始儒学产生的文化源头。孔子所开创的原始儒学仍然带有上古时期巫史传统的许多痕迹,所谓“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马王堆帛书<周易>·要》)儒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儒的职业和原始儒学的产生,都与古代的巫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儒的职业与原始的祭祀活动有关。有学者认为,儒本出于“需”,乃是具有一套专门技能而执行求雨礼仪的巫舞者[1]60。孔子儒学中所倡导的“仁”与“礼”等观念,都与上古巫术活动内容的演变有直接关联。“仁”这一范畴,是对上古巫术礼仪中的敬、畏、忠、诚的情感素质及心理状态的理性化的提升、概括和改造。孔子所复之“礼”,首先是由原巫术祭祀活动而来,经由三代的历史损益,逐渐衍生为对有关重要行为、活动、语言等一整套的细密规范。“礼数”原出于巫术活动中的身体姿态、步伐手势、容貌语言等,它所蕴涵的神圣性、仪式性、禁欲性都来自巫。总之,孔子通过强调巫术礼仪中敬、畏、忠、诚、庄、信等基本情感、心态而加以人文化、理性化,并放置在世俗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而使生活和关系本身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可以说,如果周公“制礼作乐”,是在外在社会规范方面促进了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进程,孔子的思想则更多地从人的内在心性情感方面促进了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进程。孔子儒学正是在对原始巫术观念的超越扬弃中获得了自己思想的本质规定性。
《周易》铸就儒家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孔子开创的原始儒学与《周易》具有的渊源关系。孔门儒学与《周易》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个互动的过程,二者在价值观上都共同以继善崇德为追求目标。一方面,《周易》古经卦、爻辞曾经对孔子及其门人产生了明显影响(《论语》中的《述而》《子路》《宪问》诸篇及《史记》等均有相关记载),另一方面,后者通过对古经的阐释丰富了《周易》的文本内容,揭示了古经的哲理内涵。史传孔子作《十翼》,尽管有不同看法,孔子及其弟子研学并诠释过《周易》,却几乎已成学界共识。《十翼》与孔子原始儒家思想高度契合,共同体现了继善崇德的道德主义精神,所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说卦传》)等等表述,表达的正是《易传》的道德追求。《系辞》崇尚道德,以德行为首出,是其重要特点,所谓易为君子谋是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善成性,崇德广业,是《系辞》释易的显明旨趣。重视德行同时也是《大象传》的显著特点。如《讼·象》:“君子以作事谋始。”《既济·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其他如《损》《益》《大壮》《晋》《咸》《大有》《大过》《蒙》《小畜》《蛊》《豫》《渐》《夬》诸卦之《大象传》,以及两处《文言》中强调“进德修业”,都体现了儒家以“德”释易的道德主义精神和传统,进一步开掘了《周易》古经的人文价值。
孔子思想与《周易》的渊源关系,学界从不同角度亦多有论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说儒学“游文于六经”之中。而六经之中,“易为之原”。基于此,孙熙国认为,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儒家,其源头就出自《易经》[2]。“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思维可以说是源于《周易》,立基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又通过易儒互动过程展开的。”[3]王新野认为,“写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不仅接受而且发展了孔孟思想,是当时受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4]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周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来源,孔子通过援易人儒门,以阐扬其人文道德理想,同时也通过诠释《周易》,使其弘道立德的人道思想借《周易》平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周易》铸就儒家文化传统还体现在,不仅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后来的历代儒家也都尊崇《周易》,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智慧,以延续儒家文化传统。孔子以后,荀子和子思一脉的儒家,对《周易》的诠释也都承袭了孔子的道德主义传统,重在义理而不在占筮。荀子言“善为《易》者不占” (《荀子·大略》)即是明证。秦代焚书,《易》以卜筮之书得以幸免。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汉武帝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立于学官,置“五经”博士,《周易》的传授被正式纳入官学传统。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六经之首”的《周易》从此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传播的当然之选。后来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周易》的传播更是得到了历代官学体制的有力和长远支撑。这些都是《周易》承载、延续儒家文化传统的证明。《周易》延续儒家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官学体制方面,在思想阐释方面,历代儒者通过尊经、注经的方式,通过对《周易》的阐释,汲取其中的思想智慧,实现了儒学的传承以及不断的创新转化,使儒家文化传统得以传扬。以宋学为例,周敦颐、邵康节、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无不各有著述阐释《周易》思想,发掘《周易》智慧。周敦颐、邵康节以象数言伏羲画卦之根本次第;程颐作易传,重性命道德以传辞;朱熹作易本义,主易归卜筮;张载作易说,以证气之本体,诸家释易,均各有特色路数。就《周易》对宋学的影响言,我们甚至可以说,程朱理学的形上建构,《周易》尤其《易传》的思想为其提供了顺畅的逻辑理路,是理学形成的一大源头。
总之,《周易》铸就儒家文化传统,一方面体现在原始儒学直接孕生于以巫术和卜筮为核心内容的“巫史传统”(《周易》在其中承前启后);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周易》为后来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和创新转化提供了智慧源泉,已然成为其传统的重要承载甚至可以说是组成部分。钱穆先生曾有一个观点:“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5]《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代表中华文明的经典,也为儒家所尊崇。其中,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原始儒学的创生方面,也延及后来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演变当中。就历史渊源和影响程度言,《周易》对于儒家文化传统,言其具有开启铸就之功并不为过。
三、观变于阴阳: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
《周易》铸就道家思想文化传统首先表现在,同原始儒家一样,老子原始道家同样渊源于“巫史传统”。老子道家渊源于“巫史传统”,着重保存和理性化了原巫术礼仪中与认知相关的智慧方面。对李泽厚先生的这一论点前文已有提及。《周易》(主要是《易经》)作为“巫史传统”重要环节的文明成果,是渊源久远的卜筮吉凶文化的代表。其内蕴的义理精微,广大悉备,不愧为一座可从多个方面开掘的宝藏,所谓“《易》为天地鬼神之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子道家从中汲取思想智慧也是顺理成章的。“道家思想底渊源也与儒家一样同出于《易》。”[6]《易经》的卦爻符号和卦爻辞所呈现的阴(爻)阳(爻)相对,以及诸多对立观念(如天地、大小、往来、明晦、枯华、进退、出入、上下、先后、吉凶、损益、否泰、君臣、夫妻、君子与小人等等),形成《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易经》设卦立象的“象其物宜”的思维方式,与《老子》有关“象”的应用和表述;《易经》八卦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取象与《老子》“道法自然”的天道观等等方面,多有相通之处。在文体及文句的表达上,《老子》与《周易》也有借用的情况。如《周易·困卦》的“有言不信”与《老子》的“美言不信” (《老子·八十一章》);《周易·节卦》的“不出户庭”与《老子》的“不出户” (《老子·四十七章》);《周易·中孚卦》的“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与《老子》“夫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老子·二十九章》)等等。可以说,老子道家从《易经》中汲取思想智慧,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自然趋势。
《周易》铸就道家思想文化传统最突出表现,还在于解释《易经》的《易传》中渗透着明显的道家思想,老子之后的庄子学派、稷下学派及黄老道家通过《易传》对《易经》的解读,形成并延续了道家的文化传统。《易传》中渗透了明显的道家思想。
首先来看《易传》中创作时间较早的《彖传》。在天道观和辩证法方面,《彖传》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如在万物起源方面,《乾·彖》《坤·彖》《咸·彖》《姤·彖》《泰·彖》《解·彖》《否·彖》等,都有天地交感而生化万物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完全是自然主义的,丝毫不带神秘色彩,这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旨趣极为相似,从发展线索看,明显是受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彖传》的作者还把天地变化看成一个消息盈虚、终始循环的过程,主要见于《丰·彖》《剥·彖》《损·彖》《蛊·彖》《恒·彖》《复·彖》的记载,这与老子以道的运动循环往复的思想如出一辙。如《老子》所言:“周行而不殆。”(《老子·二十五章》) “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等等,都表证了其循环论思想,这与上列诸卦《彖传》的记载多有相通相似处。尽管用阴阳二气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有更久远的史官传统,“观变于阴阳”却是原始道家思想的显著特色。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四十二章》),《庄子》书中则有更多有关阴阳的记载,如“阴阳之患” (《庄子·人间世》) “阴阳之气”“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庄子·大宗师》)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天地有官,阴阳有藏。”(《庄子·在宥》)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庄子·田子方》)等等。以阴阳观念解释事物的构成和变化,是道家思想的突出倾向。以阴阳解《易》,更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内涵和特色。在《泰》《否》两卦的彖辞中,就有以阴阳解卦的记载: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这是将《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两卦划分阴阳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地天泰》卦(上、外为《坤》,下、内为《乾》)和《天地否》卦(与《泰》卦相反),故有内阴外阳、外阴内阳、君子小人之说,这应是《易传》以阴阳解《易》的最早记录。与阴阳解《易》类似,《彖传》的作者还以柔刚解《易》。柔刚或指卦象,或指爻象。《周易·说卦》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的说法。《系辞下》说:“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乾坤(天地)为“易之蕴”,即在于其阴阳柔刚。《老子》书中也有多处柔刚并举,如“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思想主张。上述柔刚弱强对应的表述,其内在逻辑为《易传》作者用柔刚来解释卦象和爻象,提供更具普遍性的解析方法,再自然不过了。
其次,《系辞》也明显渗透着道家思想。钱穆先生曾经选取了“道”“天”“鬼神”三个语词,通过比较其在《论语》与《系辞》中的不同内涵,认为“《易系》里的思想,大体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易系》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他的宇宙论可以说是唯气之一元论,或者说法象的一元论”[7]。《系辞》的主体思想是其道论和太极说。其道论无论是阴阳观或道器说都渊源于道家。“太极”观念见于《庄子》。帛书《系辞》中“太极”作“太恒”(“恒”是《老子》中的重要范畴),更能显示出其与老子之“道”观念的联系。就阴阳观念言,其始于西周以来的史官,春秋以降被道家和阴阳家所继承和发展。《系辞》里“太极”“两仪”的思想明显是受道家或阴阳家思想影响的结果。《系辞》“天尊地卑”“原始反终”的思想也明显渊源于道家。《系辞》中的黄老道家思想也很突出,胡家聪先生曾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定《系辞》思想与《管子》中道家黄老思想及帛书《经法》等四篇黄老思想声息相通[8]。总之,就思想史意义而言,《系辞》的思想并非纯粹儒家,而有综合、总结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阴阳家思想的特点,而道家思想在其中占有很重的份量。
其三,《易传》中的道家思想,还表现在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道家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某些概念的使用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夫易者,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与《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用人事来证天心,以人道为立足点,求“性命与天道相贯通”(上达)的思维方式不同,道家的思维方式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下沉的,由天及人)。这一思维方式自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开其端,后为庄子与黄老道家所发扬,并为《易传》所继承。《泰》《否》《豫》《观》《剥》《颐》《咸》《恒》《革》等卦《彖传》都体现出这种思维方式。《系辞上》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则更突出地表达了这种思维方式。另外,在概念的使用方面,《易传》与道家著作中的记载多有相同或相似处。如“天行”概念在《蛊·彖》《剥·彖》《复·彖》都有使用,而这一概念在道家著作中更常见,帛书《黄帝四经》之《正乱》篇云:“夫天行正信”,《管子·白心》云:“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其在《庄子》书中也多处出现。再比如,《乾·文言》的“云行雨施”,在《庄子·天道》中为“云行而雨施矣!”;《乾》卦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与《庄子·渔父》“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也很相似。此外,有关“精、气、形、神”“中和”“时中”等用语,《易传》都明显地于道家思想有所承袭。总之,《易传》深受道家思想影响[9],或者可以说《易传》与道家思想,多有共通处。这一实情表明,《周易》之《易经》对道家思想确有生成铸就之功,因为毕竟《易传》是用来解释《易经》的,其义理之源仍在《易经》。
《周易》铸就道家文化传统,还表现在《周易》的思想后来深度渗透到道家及道教文化传统的传承演变当中。老子的思想孕生于“巫史传统”自不必说,后来的《易传》与庄子学派、稷下道家、黄老道家的思想都有相互阐发或吸收借鉴的情形。《庄子》《列子》《吕氏春秋》说《易》或引《易》以描述“道体”者比比皆是。到三国时,因为思想上的内在接近相通,《易》《老》《庄》并称三玄,相互阐发形成了玄学。《魏氏春秋》称何晏善谈《易》《老》,而王弼注《易》,黜象数,阐义理,多以《老》学之旨解《易》。产生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其信仰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后来的道家思想文化传统也主要通过道教得以传承延续。道教自其产生,《易》就成为道士手中之至宝,或注释,或引申,或改造。以《易》解“道”成了道教易学的显著特色。这种情况到了宋元之际可谓达到了高峰。比如,以葛洪《抱朴子》为例,其《道意》篇云:“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其《明本》篇云:“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其《辨问》《杂应》等篇亦多引大《易》之言以答疑。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与张伯端著的《悟真篇》,以易卦解释丹道,为内丹学的重要经典。总之,“道教徒不单纯是注《易》,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它当作基础的经典而广为应用。《周易》从内容到形式都为道教所汲取,它渗透到道教的基本信仰、神仙体系、方术仪式、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10]可以说,道教的三洞经书到处都可以找到从《易》脱胎而出的痕迹。
道教“贵生”,以修道养生、全性保真、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要旨,体现了生机主义的价值追求。如《太上老君内观经》云:“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云笈七签>(一)卷十七 三洞经教部·经八》)“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太平御览·道部·养生·太清真经》)“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 (《太平御览·道部·养生·集仙录》)等等,都是道教“贵生”的表达。道教“贵生”,其要义也在于探究生命修炼之法,保有生命长生之机,故“生机”理念可昭示其价值追求。道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生机主义”的宗教。道教重视“机”,多见于其经典及著述当中,如“乘机”“灵机”“道机”“枢机”“玄机”“要机”“天机”“机妙”“杀机”“盗机”“死机”等等。对道教而言,“机”是事物变化的关键,决定了事物最终的盛衰存亡。而确保“生机”是其修道长生的根本,因此,可以说,道教体现了生机主义的价值追求。道教的生机主义要旨在其重要经典《黄帝阴符经》中更有突出体现。这部“辨天人合变之机,演阴阳动静之妙”的经书,深契于《周易》“极深研几”“知几其神”的要义,体现了道教“顺时隐显,应机行藏”的生机主义内核。历来注解此书多达四十余家。其《张果注》云:“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注解《阴符》的《天机经》多引《周易》之言,以解经书主旨,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阴阳不测之谓神。”“乃顺承天,待时而动。”等等。这些表述足见经书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这应当是《周易》铸就道教生机主义文化传统最显明的实例。道术一词源于《庄子·天下篇》,秦汉时演为“方术”“方技”,后其内容逐渐为道教所吸纳,称其为“仙术”。道教的道术很多,如占卜、符篆、祈禳、禁咒、内丹、外丹、炉火黄白、辟谷、行跷、房中、仙药、服气等等,可主要分为山(仙)、医、命、卜、相五类,故称五术。五术的产生也主要源于《周易》之发用流行。
总之,《周易》铸就道家、道教的文化传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老子原始道家孕生于巫史传统;其二,《易经》影响了道家后来的庄子学派、稷下学派、黄老道家的自然主义文化传统;其三,《周易》铸就了道教的生机主义文化传统。
四、八卦定吉凶:民间社会的吉凶文化传统
吉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就事物的变化状态而言的。一切事物变化必趋于旺衰存亡,旺、存为吉,衰、亡为凶。吉凶更多是针对生命体而言的。于植物而言,吉凶表现为一种延续生命的自然需求,阳光、水、养料等生命要素得到为吉,反之为凶,生长荣茂为吉,枯灭为凶;于动物而言,吉凶表现为一种逃生的本能,避开捕杀为吉,反之为凶,于其生命顺生为吉,夭亡为凶;于人而言,因其为万物之灵,它方能说是一种观念和文化。吉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一切寓有趋吉避凶、远祸纳福的观念、习俗及活动。除渊源久远的有代表性的多种巫术与卜筮活动外,吉凶文化的范围很广,从符瑞到谶纬,从避讳到祈福,以至于后来形成的诸多术数种类,都可归入吉凶文化之列。而基于《周易》衍生的各种术数,正是中国古代吉凶文化的核心。早期阐释《周易》的“象数”与刘歆图书分类的“术数”,以至汉代的“方术”,其涉及的内容大体相近。《后汉书·方术列传》云:“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以术数为核心的吉凶文化,曾经流播于中国传统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是中国古代吉凶文化的代表。“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周易·系辞》),相较于儒、道两家对《周易》的义理发掘,《周易》最早是被用于占断吉凶的。作为占断吉凶的卜筮之书,《周易》在演变中形成的趋吉避凶的文化传统比儒、道两家的文化传统也更古老。《易》作为卜筮之书比作为哲理之书更古老。“易以卜吉凶”才是《周易》之源。正如《管子》所言,“《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周易》成书的过程,同时也是吉凶文化传承演变的过程。《汉书·艺文志》认为《周易》的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最初伏羲始画八卦,用于部族趋吉避凶,不仅开启了华夏民族的人文之旅,亦可看成吉凶文化最早的源头。据《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记载,上古时期神化传说的巫师、巫神(神话传说往往人神不分)帝江、句芒、祝融等,他们无不各具神通,主宰护佑一方一域。其巫术活动无不蕴含着古老的吉凶观念和意识,传承着古老的吉凶文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礼记·表记》),殷周以来流行的尊神敬鬼的文化习俗,使“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的《易经》八卦,成为天子王庭沟通神人、求解狐疑的工具。因之,能够“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周易》卜筮,自然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并得以传承。殷墟出土的甲骨占卜记录,已经是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成熟的吉凶文化的典型形态。周代的蓍卦筮法也是对殷商甲骨龟卜的继承演变。文王拘而演《周易》,使古《易》的文本更加丰富完备,使其占断吉凶的卜筮之用得以显扬。
《周易》最早被用于天子王庭,而后下沉到民间,铸就了民间社会的吉凶文化传统。《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殷周时由史官掌管并主要用于“祀与戎”的国之大事。春秋战国时,它也主要在上流社会流传,《左传》《战国策》等书有关卜筮的记载有二十处左右。自春秋始,尤其秦汉以后,《周易》逐渐下沉到民间,为百姓所传用,经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了民间社会层面的吉凶文化传统。《汉书·艺文志》云:“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汉书·儒林传》说费直“长于卦筮”,高相“专说阴阳灾异”,两家易学均在民间流传。汉代盛行古易筮法,孟喜、梁丘贺、焦延寿、京房、虞翻、郑玄诸家治易,各有创见。汉代易学家以《周易》《河图》《洛书》《先后天图》等为基础,推演出一套阴阳、五行、三才、四象、八卦、九官、十二辰、二十四气等为符号的象数体系,为后来多种术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形成于汉代的卦气说、爻辰说、纳甲筮法等,丰富了《周易》的象数体系,为后世各类术数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汉代诠释盛行各种术数。《汉书·艺文志》将汉代术数之书分为六类,一天文,二历谱,三五行,四蓍龟,五杂占,六形法。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当时的术数门类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等。《四库提要》云:“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汉代,以诠释《周易》的象数体系为骨架形成了多种术数类型,又以多种术数为支撑,形成了符瑞、灾异、卜筮、谶纬等形态的吉凶文化一时繁盛的局面。
两汉以后,以各种术数为核心的吉凶文化代有传承,广泛盛行于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术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容十分庞杂的门类,多为“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以其为主要支撑的吉凶文化历代传者不绝。唐代《艺文类聚·方术部》曾经将方术划分为养生、卜筮、相、疾、医五类。宋代《太平御览·方术部》则分为养生、医、卜、筮、相、占候、占星、占风、占雨、望气、巫、厌蛊、祝符、术、禁、幻等类别。《四库全书》的划分则更趋专精缜密,将古天文和古算数书归入天文算法类,术数类则收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属,存目又增杂技属。今人于“术数”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生类,主要有养生、医药、气功、炼丹、房中、服食、辟谷等。第二类是预测类,有卜筮、易占、杂占、择吉、三式、占梦、测字、堪舆、占星、占候、相人、算命术等。第三部分是杂类,有幻术、招魂术、禁咒术、巫蛊术等。狭义的术数,主要指上述第二类。术数多以《周易》之“象”“数”“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为分析方法,通过推演阐释,以求占验吉凶,预测灾祥。在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各种术数广为流传,从未中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各种术数在民间社会流播的盛况同正统的官方教化相比毫不逊色。以至于许多朝代不得不对有些术数加以禁绝。如唐宋时期厉行的“天文之禁”(如周太祖颁有《禁习天文图纬诸书敕》)(《全唐文》第二部,卷一百二十四),宋仁宗时曾有官员对“传习滋多”“假托禨祥”的“尚巫”习俗,上书“宜颁严禁,以革祆风”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一)等等。历朝历代研习术数者绍继不绝,且从业者甚众。以宋代为例,除陈抟、邵雍、徐子平等术数大家都各有著述外,据《宋史·艺文志》所载,其术数类文献有:神仙类三百九十四部,一千二百十六卷;五行类八百五十三部,二千四百二十卷,其中包括风水、相书、命、神怪、占候、禁忌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蓍龟类三十五部,一百卷。宋代不仅从事术数的术士数量惊人,信奉的人更是多如牛毛。王安石曾记载,仅在开封一地,卜者“以万计” (《临川文集》卷七十)。而南宋临安的术士,在御街上摆摊的就有三百多[11]。宋仁宗时(天圣元年),江西洪州的师巫多达“一千九百余户”;宋神宗时(熙宁初),江西虔州的师巫更多,有“三千七百家” (《宋史》卷三三四)。由此不难看出,术数这一职业在宋代民间广有市场。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术数盛行,吉凶文化广泛传播的一个实例。
总之,就中国传统社会吉凶文化言,以《周易》的“象”“数”“卦”为基础衍生出的各种术数是其核心。而各种术数在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广为流播,从未中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既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层面吉凶文化传统绵延不绝的体现,也透显了《周易》对这一传统的生成铸就之功。
五、结语
《周易》一书,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原始基因,其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绝不限于本文所说的三大传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周易》于华夏文明不啻为万学之宗。之所以只提及三大传统,一方面因为这三大传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支撑,另一方面也因为三大传统于《周易》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由此也想进一步表明,《周易》对于华夏文明的形成和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