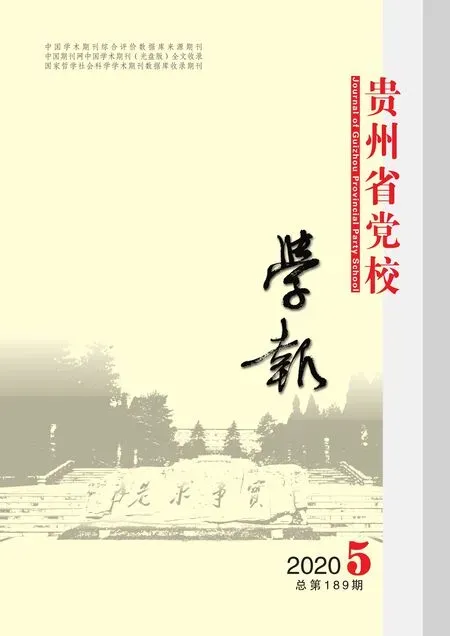监狱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国家赔偿问题
——基于22份裁判文书的考察
侯孟君
(浙江省司法厅,浙江 杭州 310025)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监狱作为相对封闭的场所也未能幸免。例如,山东、湖北、浙江等地几乎同时公布监狱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疫情。[1]我国《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造成损害的,监狱管理机关应当承担刑事赔偿责任。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是,当监狱服刑人员受到病毒感染而遭受人身权损害时,是否可以提起国家赔偿之诉,并且如何具体适用《国家赔偿法》。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围绕关于监狱服刑人员感染病毒及因病致伤致亡申请国家赔偿这一主题,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收集整理22份相关案例,以此对上述问题作实证研究。
一、监狱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法》实行法定赔偿原则,只有符合其第17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条件,才能获得国家赔偿。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持严格审慎的态度。例如,在(2016)鄂委赔13号、(2018)最高法委赔监18号裁判中,法院明确申明“国家赔偿实行法定赔偿原则”,在(2018)皖委赔12号裁判中,法院特别强调“刑事赔偿实行严格的法定赔偿原则,只有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与之相对,若不符合法定要件,则不产生国家赔偿责任。例如,在(2013)辽法委赔字第8号、(2014)辽法委赔字第11号裁判中,法院认为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事项或者其赔偿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5项规定的法定赔偿范围和条件,判定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项的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显然,从字面文义解释角度来看,监狱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不必然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但是,如果从《国家赔偿法》立足尊重与保障人权,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出发,宜将上述规定中的“等”字解释为“等外等”。实务中,当判断国家机关造成公民伤害或者死亡的特定行为能否列入该“等”字时,“应当给予扩大和有利于受害人的解释。”[2]
根据司法实践中有关国家赔偿的案例,法院已经将该“等”字的外延扩充,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未尽法定职责”“贻误救治时机”等不作为型侵权行为,这类行为同样可能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例如,在(2018)皖委赔12号裁判中,法院认定《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项中的“等”应当作扩大解释,侵犯人身权的行为不应当仅限于法律条文本身的列举,还应当“包括监狱对患病的被羁押人不及时救治等未尽法定职责的情形”。在(2019)桂委赔13号裁判中,法院同样认定,“监狱贻误救治患病服刑人员时机的不作为构成了该规定的‘等’字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在(2019)最高法委赔监68号、(2019)最高法委赔监97号裁判中,其裁判主旨指出,监狱存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情形,造成服刑人员被感染××病毒的损害结果的,应对其承担赔偿责任。
随之,该做法形成了制度性共识,被赋予更强的实践生命力。在201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调研会议纪要》(法〔2019〕290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其第2条第1款规定,赔偿请求人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对罪犯改造中具有《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5项规定情形,或者存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等情形为由提出的赔偿申请,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因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监狱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存在不作为型侵权行为,导致狱内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其人身权受到侵害,并发生人身损害后果的,此种情形应当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二、监狱发生疫情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作为情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赔偿必须具备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个要件,且只有符合全部要件才产生国家赔偿责任。具体而言,监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监狱管理机关行使职权时侵犯了监狱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人身、财产等方面的实际损害结果,且其职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监狱应当对其作为型违法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在(2017)黔委赔1号裁判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明,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有法定的赔偿范围内的侵犯人身权行为。本文探讨的是监狱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情形中,监狱的不作为型侵权行为类型及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监狱管理机关监管职责的不作为
“怠于履行职责,简单地说,是指公务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依其职责,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特定的作为义务,但在有能力、有条件履行的情况下,不履行、拖延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作为义务的情形。”[3]根据《监狱法》第7条和《国家赔偿法》第17条的规定,罪犯的人身安全权利不受侵犯,监狱管理机关依法应对被监管人的生命健康权予以保障,否则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可见,“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的赔偿责任机理,是在于国家机关没有防止、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和没有消除或减轻损害后果的发生、延续。”[4]因此,监狱管理机关应当提供安全的监管环境,从而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这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义务,同样也构成监狱管理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前提要件。
在(2019)最高法委赔监97号裁判中,申诉人赵荣辉因申请吉林省四平监狱(以下简称四平监狱)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吉委赔再2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四平监狱对感染××病毒、××患病服刑人员负有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的法定职责,但是“四平监狱并未对赵某伟出入赵荣辉的房间加以严格管理及有效阻止”,以至于在赵某伟具备传染条件的情况下与赵荣辉形成接触,并造成赵荣辉被感染××病毒的损害结果,认定“四平监狱存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情形,对赵荣辉感染××病毒存在监管过错,该过错与赵荣辉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因此,判定“四平监狱应根据其过错对结果所起的作用,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肯定,其裁判理由称:“原决定认定四平监狱存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情形,应对赵荣辉感染××病毒承担赔偿责任正确。”
参照上述裁判,若监狱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其违法履职的不作为行为导致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侵犯了服刑人员的人身权,且狱内发生传染病疫情与监狱行使职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监狱应当根据其过错以及其职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作用程度,承担相应比例的国家赔偿责任。
(二)监狱管理机关救治义务的不作为
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生命健康负有保护职责,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患病后,监狱应当及时履行给予其相应治疗的法定义务。根据《监狱法》第54条及《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的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应当做好罪犯疾病预防控制管理、罪犯医疗管理等工作,对患病罪犯及时诊治。《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监狱管理机关依法应对被监管人的疾病及时救治,否则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我国监狱服刑人员的疾病诊治费用由监狱全额承担。监狱均配备有监狱医院,向服刑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对于后续救治行为是否满足合法性和合理性要求,需要综合考虑救治时间、送医程序、救治措施、医疗条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赔他字第3号《关于监狱管理机关怠于行使法定职责是否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答复》中指出,“巢湖监狱怠于履行职责,未尽到及时转院救助义务,与解某某患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2019)桂委赔13号裁判中,黄明军、丘小梅以不履行法定职责致其子黄仕海死亡为由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监狱(以下简称桂林监狱)国家赔偿。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认,“桂林监狱工作人员在黄仕海服刑期间患病后有及时给予相应治疗的法定职责”,根据查明事实,“黄仕海在2016年12月12日就已有病状,12月14日凌晨就开始呈现出了明显的病情加重状态,并多次呼喊救命,桂林监狱管教人员仅对其问诊和给予药物口服,在上述治疗措施无效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将黄仕海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至14日中午才将其转送至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据此,法院认定桂林监狱贻误了黄仕海的治疗时机,未尽救治义务。法院认为桂林监狱的不作为构成了《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项规定的“等”字情形,其未尽法定职责行为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结合本案事实,评判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本院赔偿委员会酌定赔偿义务机关承担5%的赔偿责任。”与之相同,在(2016)陕委赔7号裁判中,陈德龙、惠雪琴、陈朝阳以陕西省崔家沟监狱未尽医疗救助义务致人死亡为由申请陕西省崔家沟监狱国家赔偿。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定崔家沟监狱的部分误诊属于未尽救治义务情形,鉴于该误诊行为是陈宝军死亡的次要原因,判定崔家沟监狱承担20%的责任。
参照上述裁判,如果服刑人员在狱内感染新冠病毒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治而导致伤亡的,则属于监狱怠于履行救治义务的不作为,应当按照监狱怠于救治行为对受害人伤亡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比例的国家赔偿责任。
三、监狱发生疫情承担赔偿责任的例外情形
我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属于不可预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从疫情暴发至今,我们对病毒的认知仍处于探索过程。监狱只是相对封闭的场所,当社会上发生重大疫情时,仍然存在疫情传染的客观风险。狱内服刑人员感染患病,监狱不一定存在过错,且其损害结果与监狱的职权行为之间不必然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而监狱出现了服刑人员被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形,并不必然产生国家赔偿问题,还存在一些监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监狱管理机关无侵权行为
1.监狱管理机关已履行法定职责
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国家机关有无侵权行为的主要标准是其是否已经履行监管职责和尽到救治义务。然而,法律不强人所难。依据《会议纪要》第3条第4项之规定,“对于服刑期间发生的突发、意外情形,经审查监狱对罪犯的监管、处置、救治等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者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合理、及时注意义务的,应当认定为依法、正当履职,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得仅以是否造成损害结果作为判断应否赔偿的标准”,即怠于履行职责的违法阻却事由是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因此,如果监狱管理机关事前已经严格履行了监管职责,采取了必要的防控措施,且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后,经及时、合理救治的,不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
(1)监狱管理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得当。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生命健康有保护职责,其履行监管职责得当包括日常监管行为合法,以及狱内发生突发、意外情形后处置措施及时、合理。在(2018)鄂委赔11号裁判中,赔偿请求人刘甜因其父被殴打、虐待致伤、致死申请湖北省汉阳监狱(以下称汉阳监狱)国家赔偿。该案焦点为汉阳监狱是否存在虐待行为,是否存在监管不力、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被监管人的行为。首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刘远高在服刑期间的就诊病历,认为“在刘远高患病期间,汉阳监狱均按规定对其进行了治疗,不存在虐待行为”。其次,根据事发当天的现场监控视频内容,刘远高与服刑人员蔡仲军斗殴事件发生30秒后,执勤民警詹飞就已赶到现场将昏迷的刘远高用担架送入监狱医院急救。再次,从抢救记录记载的内容看,监狱医院值班医生彭祥辉先后对意识丧失的刘远高进行了四次呼吸面罩加压给氧和胸外心脏按压,并进行静脉注射急救药物的急救处置,监狱同时启动了紧急预案,及时将刘远高送至同济医院中法生态城分院急救。据此,法院认为“上述事实足以证实汉阳监狱的值班民警对事发当天的服刑人员斗殴和刘远高突发昏迷事件处置及时恰当,汉阳监狱医院在抢救和紧急外医的过程中没有拖延,对刘远高的监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即汉阳监狱履行监管职责得当,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处置及时到位。最终,根据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并结合该案案情,法院判定刘远高的死亡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
(2)监狱管理机关履行救治义务合理。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监狱是否履行了合理的医疗救治义务,主要判断要素为日常的健康管理和患病后的医疗救治。尤其以后者为重,其中包括救治时效、救治措施和救治态度。
第一,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日常健康管理。在(2017)苏委赔4号裁判中,赔偿请求人何洪彬入监后,边城监狱即按规定对其进行身体检查,检查出何洪彬患有“2型糖尿病史6年”“高血压”“××”等病史。服刑期间,边城监狱考虑何洪彬的身体状况将其安排在老残监区,以休养为主、偶尔参与轻微劳动,同时专门为其建立了健康体检档案。在(2016)湘委赔23号裁判中,唐刚祥被邵阳监狱决定收监执行后,该监狱根据唐刚祥身体情况安排其在出监监区服刑,没有从事劳动。
第二,服刑人员患病后,监狱对其的医疗救治时效是否及时。在(2014)鄂高法委赔监字第00013号裁判中,法院查明,胡军在服刑期间因上呼吸道感染患病,湖北省孝感监狱根据其病情状态,先后将其送至孝感监狱医院、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总医院住院治疗。在(2015)粤高法委赔字第30号裁判中,法院查明,阳春监狱在发现廖忠祥精神行为异常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七次心理治疗及两次司法鉴定,在廖忠祥摔倒及身体不适时能及时予以医治,在发现廖忠祥有卧床不起的情况时及时送院治疗并通知亲属。在(2016)辽委赔40号裁判中,法院查明,赵磊在康平监狱服刑期间出现咳嗽等症状,康平监狱医院多次对其进行X光检查,均诊断为肺内感染并给予了对症治疗。在(2016)湘委赔23号裁判中,法院查明,唐刚祥患病后,邵阳监狱先后数十余次送其到本监狱医院治疗。××危时,邵阳监狱先后送唐刚祥到湖南省监狱总医院、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和抢救。在(2017)苏委赔4号裁判中,法院查明,2013年5月6日至2014年12月1日,何洪彬患眼疾,边城监狱先后4次将其送至监狱医院、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对症治疗。在(2017)黔委赔1号裁判中,法院查明,贵州省安顺监狱在彭金全患病后及时为其提供诊治,并请社会医院专家入监会诊,直至送往贵州省司法警察医院、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诊治。
第三,服刑人员患病后,监狱对其的医疗救治措施是否合理。如《会议纪要》规定,法院审查监狱对罪服刑人员的救治行为是否依法、正当,并非仅仅考虑救治的最终结果。具体而言,其判断标准有二:其一,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二,是否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合理、及时注意义务的。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为监狱的两项作为义务,一是必要的病情检查,二是科学的诊断治疗。在(2014)鄂高法委赔监字第00013号裁判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孝感监狱对患病服刑人员的救治过程事实,判定孝感监狱对患病服刑人员的救治措施合理,尽到了救治义务。其裁判理由称:“胡军在湖北省孝感监狱服刑期间,该监狱医院对胡军采取了检查、拍片、转院等积极的治疗措施,已履行了监管和救治义务。”在(2017)鄂委赔1号裁判中,法院查明王某作为××人,言行异于常人,难以向监狱医院求医问诊,蔡甸监狱在发现其异常体征后,积极安排其于监狱医院就诊并住院观察,对其进行了血检、影像检查等多项检查并开具相关药品,依法合规保障其接受了医疗救治,在监狱医院检查显示其存在两肺感染××病变后次日上午即将其送往汉阳医院救治。据此,法院认定“蔡甸监狱在其职责范围内已尽量为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及采取相应措施”。在(2018)皖委赔12号裁判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白杰发病后,宿州监狱医院及时对其进行了救治,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转入具有三级甲等资质的地方医院接受治疗,最后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宿州监狱在此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救治的责任”。
第四,服刑人员患病后,监狱对其的医疗救治态度是否积极。通常,从监狱对患病服刑人员的救治时效和救治措施中,法院判定监狱的救治态度是否积极。在(2016)辽委赔40号裁判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赵磊在康平监狱服刑期间出现咳嗽等症状,康平监狱医院多次对其进行X光检查,均诊断为肺内感染并给予了对症治疗。康平监狱对赵磊的救治态度是积极的、主动的,尽到了相关义务,履行了监狱的职责。”在(2017)辽委赔4号裁判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查明,自2011年4月22日,张月艳称“疲劳后自觉双眼疼痛”在省女子监狱医院就诊以来,省女子监狱先后派人带张月艳到监狱医院、沈阳四院诊治数十次,并为张月艳眼部疾病进行了手术治疗。由此法院判定“省女子监狱对张月艳的救治态度是积极的、主动的,尽到了相关的义务,履行了监狱的职责。”
2.个人侵权责任
国家赔偿侵权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并非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有的侵权行为都适用国家赔偿。“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国家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引起的,属于民事赔偿,而不是国家赔偿。”[6]此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行为主要包括“犯罪行为和公务执行中的个人过错行为”[7]在监狱工作人员故意隐瞒往返疫情重点地区行程,以及自身患有或者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情,回到监狱正常工作而导致监狱内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情形中,监狱工作人员违反了监狱管理机关的内部工作纪律,但监狱管理机关并无明显过错,不能直接、当然地归咎于监狱管理机关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而且根据《刑法》《传染病防治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上述情形中的监狱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与执行公务无关的个人犯罪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宜由监狱工作人员个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监狱管理机关无过错责任
“国家机关的违法,说到底都具有过错性质。”[8]过错归责标准与违法归责标准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对其在具体适用中的一种补充弥合。“在侵权法意义上,违法原则和过错原则是相互涵盖、互为表里的,在国家赔偿法中,两者的机理也是相通的。”[9]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监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时,不仅要审查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还要审查其在履行监管职责和救治义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过错。
1.监狱管理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无过错
关于监狱对服刑人员在狱内感染病毒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法院主要审查的是监狱履行监管职责有无过错。在(2018)最高法委赔监18号裁判中,申诉人梁军称辽宁省铁岭监狱(以下简称铁岭监狱)未隔离羁押致其被传染肺结核病。法院审查后,认为铁岭监狱监管行为合法得当,并无过错。其裁判理由称:“本案中,不存在铁岭监狱有以上规定的侵犯梁军人身权的情形,且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监狱疏于管理而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或者故意将梁军与肺结核病人羁押在一个房间,致其被感染。”
2.监狱管理机关履行救治义务无过错
在(2017)鄂委赔1号裁判中,赔偿请求人王小红、王利娟以其弟王某因湖北省蔡甸监狱(以下简称蔡甸监狱)虐待致死为由向蔡甸监狱申请国家赔偿,该案的争议焦点是蔡甸监狱是否对王某怠于履行医疗救治的职责、医疗过错致其死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蔡甸监狱发现王某病症并及时采取救治措施,虽然监狱医院的医疗条件受限,但其实施的医疗救治行为到位。其裁判理由称:“监狱医院对王某做了胸部正位的医疗影像检查,报告单载明王某胸部右侧大量胸腔积液,左侧不除外少量胸腔积液,两肺感染××变,不除外其他性质病变,建议CT进一步检查并结合临床综合考虑,即监狱医院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检查,不存在漏诊行为。”且蔡甸监狱在检查确定王某病症后,“次日上午即将王某转入汉阳医院住院”,不存在未进行院外会诊以及及时转院的过错。因此,认定蔡甸监狱履行救治义务得当,且救治过程中无过错。
与之相似,在(2014)辽法委赔字第11号、(2017)鄂委赔18号裁判中,服刑人员发病后,锦州监狱、咸宁监狱对患病服刑人员采取了积极合理的诊疗医治措施,法院据此认定上述监狱在履行救治义务过程中无过错。
(三)职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
国家赔偿中的因果关系是国家赔偿责任存在的前提,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既是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与受害人实际损害结果之间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又是“立法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10]。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监管和救治职责是为了保护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若监狱违背法定职责和义务并造成特定服刑人员实际损害,则监狱的侵权行为与服刑人员的损害结果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1.关于服刑人员狱内染病情形的因果关系判断
在(2018)最高法委赔监18号裁判中,申诉人梁军因申请辽宁省铁岭监狱(以下简称铁岭监狱)未隔离羁押致其被传染肺结核病赔偿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2017)辽委赔36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关键在于梁军患肺结核病与铁岭监狱的管理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法院认为,首先,梁军在铁岭监狱住院治疗期间未发现患有肺结核,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铁岭监狱采取的治疗措施不当。其次,梁军自2010年1月6日出院至2014年5月6日被抚顺市第四医院诊断为肺结核,在其离开铁岭监狱4年后出现肺结核症状,即使肺结核有潜伏期,也无法确定其于何时何地被传染,“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梁军所患肺结核与铁岭监狱的医治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再次,铁岭监狱无侵犯服刑人员人身权的情形,“且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监狱疏于管理而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或者故意将梁军与肺结核病人羁押在一个房间,致其被感染,即不能证明梁军患肺结核病与铁岭监狱的管理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关于患病服刑人员死亡情形的因果关系判断
在(2016)鄂委赔13号裁判中,汤玉莲以湖北省武昌监狱对服刑人员张顺发放任病情、遗弃、虐待致使其子张顺发死亡为由申请国家赔偿,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玉莲之子张顺发的死亡与武昌监狱的监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武昌监狱“在服刑人员张顺发突发病状时,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并未耽误张顺发治疗”,履行救治义务得当,患病服刑人员张顺发的死亡属于因病致死,“故赔偿请求人汤玉莲之子张顺发的死亡与武昌监狱的监管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此外,在(2012)川法委赔字第5号、(2014)辽法委赔字第11号、(2017)鄂委赔18号、(2017)辽委赔4号、(2018)粤委赔37号、(2018)辽09委赔3号、(2018)皖委赔12号等相同类型的裁判中,法院也认为监狱的职权行为与服刑人员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进而判定监狱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可见,若监狱的职权行为与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而导致的患病或者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则监狱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监狱管理机关的举证责任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鉴于监狱和服刑人员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对于二者的举证责任分配,司法实践中相对侧重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服刑人员,通常要求监狱承担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
例如,《会议纪要》第4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的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监狱应就其履职行为与罪犯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该规定精神在(2019)最高法委赔监68号裁判中已有体现,法院认为赵荣辉虽然不能证明其是如何感染××病毒的,但四平监狱同样不能举证证明赵荣辉感染××病毒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即不能排除其与赵荣辉感染××病毒之间的因果关系。其裁判理由称:“考虑到四平监狱与赵荣辉之间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且赵荣辉系高位截瘫服刑人员,活动受限,长期在监狱医院接受监管治疗等因素,四平监狱应当对其与赵荣辉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负有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
因此,考虑到监狱与服刑人员之间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等实际因素,在本文探讨的监狱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国家赔偿问题中,若染病服刑人员主张监狱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或者实施违法侵权行为导致自身的损害结果,由此申请国家赔偿的,监狱应当对其职权行为与服刑人员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负有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即监狱如不认可赔偿请求人的主张,则应当举证证明监狱实施了严格管理和具体措施,并实际上有效的防控了狱内疫情的传播以及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否则,监狱管理机关就应当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五、监狱管理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类型
(一)侵犯生命权的赔偿责任
首先,关于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4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在(2016)陕委赔7号裁判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关于陈宝军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63241元(2015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x20年=1264820元。
其次,关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4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权造成死亡的,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在(2016)陕委赔7号裁判中,陈德龙、惠雪琴、陈朝阳以陕西省崔家沟监狱未尽医疗救助义务致人死亡为由申请陕西省崔家沟监狱国家赔偿。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①(1)①“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将陈德龙的生活费计算为565元(2015年西安城市低保标准)x146个月=82490元、惠雪琴的生活费计算为565元x175个月=98875元。因陈德龙和惠雪琴共有两个子女,其均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故陈德龙和惠雪琴的生活费应减半计算,分别确定为41245和49438元。陈朝阳的生活费计算为565元x1个月=565元。
(二)侵犯健康权的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34条②(2)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明确规定了侵犯健康权的赔偿标准及其计算方式,但并非受到人身损害就有权获得相应标准的赔偿,其具体情形的认定需要进一步分析。以赵荣辉申请吉林省四平监狱(以下简称四平监狱)国家赔偿案,即(2019)最高法委赔监97号裁判为例。首先,关于医疗费、护理费,需要以服刑期间已经发生的明确的实际费用损失为准。法院认为,赵荣辉在服刑期间并无实际费用损失。“赵荣辉入监服刑以来,包括其感染××病毒之后至今仍在服刑,其生病治疗及护理工作一直由四平监狱负责,已经实际发生的治疗费用和生活饮食也全部由监狱负担,而且国家对于××患者实行终身免费治疗,在其刑满释放前,不存在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损失。”而且,赵荣辉刑满释放后的后续治疗费用因尚未发生而不能确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2款③(3)③“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规定,法院认为“赵荣辉刑满释放后可能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及营养费等尚不能确定,可在实际费用发生后另行主张”。其次,关于残疾赔偿金,受害人残疾事实必须是赔偿义务人造成的,且属于法定的伤残评定范围,并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根据查明事实,赵荣辉在服刑期间感染××病毒,并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且××病不属于目前国家规定的评定伤残等级范围,其虽是肢体二级残疾,但该残疾事实发生在入监服刑之前,四平监狱不是该项残疾的赔偿义务人。因此,法院判定“赵荣辉主张残疾赔偿金、残疾生活辅助具费,于法无据”。再次,关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受害人此前应当具有承担扶养的能力,并实际履行了扶养义务。根据法院查明事实,赵荣辉于2001年因坠楼造成腰部以下截瘫,属肢体二级残,靠低保和做手工零活收入及其父母、哥哥照顾生活,其与张某红1999年非婚生子张某俊至今已成年,自其入监服刑后实际并未履行相关抚养义务,且亦无法承担赡养义务。参照民事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其自身情况属于减免承担抚养责任的情形,其主张赔偿受其扶养人的生活费无依据。因此,法院认为“对赵荣辉该项主张,不应支持”。
(三)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精神损害是指基于侵权行为致使他人产生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不安及精神状况的异常,或者使受害人之尊严、威信和社会评价降低。”[11]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侵权责任性、抚慰性和补充性,主要适用于受害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权利受到侵害的场合。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弥补国家赔偿数额不足的角色。[12]“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特性决定了对于没有造成精神损害结果或精神损害后果轻微的,一般不适用金钱或物质的精神损害抚慰方式,只有国家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才适用物质或者金钱的精神损害抚慰的方式。”[13]
首先,关于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要素。《国家赔偿法》第35条①(4)①“有本法第3条或者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原则性强,并没有相对明确的界定或者列举,因而实践中的难题在于如何认定“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要素具有综合性。“严重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轻微精神损害而言的,应综合损害的性质、程度、损害持续时间长短等各种因素进行判断。”[14]司法实践中,认定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的具体操作规范通常借鉴侵权责任中的成熟经验。例如,2010年9月18日《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10]47号)第2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国家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赔偿义务机关违法程度、侵害情节和后果等因素确定。在(2011)最高法委赔字第4号裁判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朱红蔚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认定其“精神损害后果严重”。第二,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要素具有间接性。“直接判定精神损害的大小虽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通过侵害造成的其他后果来间接地判定精神损害的大小。”[15]在(2019)最高法委赔监97号裁判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赵荣辉在四平监狱服刑期间感染××病毒,属于《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的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其次,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酌定原则。《国家赔偿法》未明确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的是酌定原则,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量。例如,在(2016)陕委赔7号裁判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查明事实,认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应酌情予以赔偿”。在(2011)最高法委赔字第4号裁判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朱红蔚被羁押875天,以及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的损害后果,结合广东省当地平均生活水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在(2019)最高法委赔监97号裁判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赵荣辉在四平监狱服刑期间感染××病毒的损害结果,综合其精神受损情况,以及日常生活、家庭等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六、结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持续,监狱作为人员密集度高和空间封闭性强的特殊场所,尤其应当注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监狱的风险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狱内服刑人员的生命健康权。若监狱发生疫情,则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医疗救治方案和隔离管控措施,同时还要做好相关法律事务的处置,尤其面对潜在的诉讼和赔偿,全面审查自身是否尽到法定的监管职责和救治义务,并做好相应的应诉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