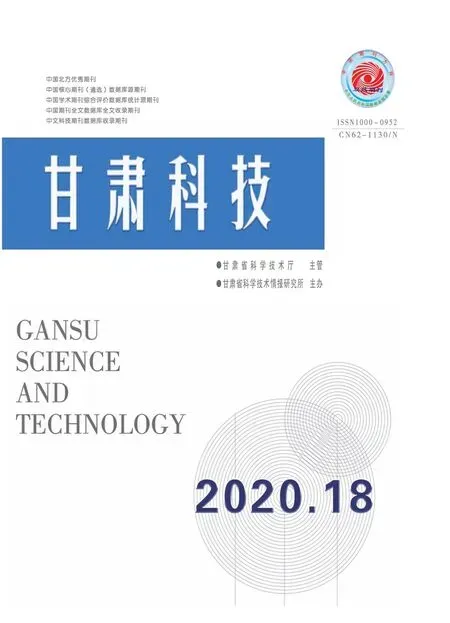经方治疗脾胃病验案
孙雪妹,田旭东,王军平,边小平
(1.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2.甘肃省中医院,甘肃 兰州 730050)
田旭东主任医师是甘肃省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常委、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田老师对本病有其独特的见解,笔者跟随田老师学习,亲聆教诲,临床治疗脾胃病重视运用经方辨治,认为在整体观指导下的中医经方辨证运用应有提纲挈领,当首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八纲为目,辨清病性;其次,根据脏腑、经络生理功能,认识疾病的部位,对多个症状加以综合分析,运用“一元化”思维综合归纳出主证,即疾病的根节点,使辨证更加准确,效果显著。同时兼顾地域、季节、节令气候、病人体质等在疾病中的影响。
田老师认为北方多寒,寒邪侵袭,入于肌腠,在半表半里时,往往使少阳胆经受邪,寒邪入里化热,胆汁疏泄异常,影响消化功能,症见口苦,心烦,咽干、食欲差、寒热往来,舌质红,苔黄、脉弦等症状,证属胆热犯胃证,方选小柴胡汤加减。邪气不除久则多郁,郁而化火,阴火流于肾,上乘土位,加之平素饮食不慎,损伤脾胃,症见口苦、心烦、胸胁胀满、胃脘疼痛、泛酸、烧心、纳差、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舌暗红、苔黄、脉弦等症状,证属胆胃郁热证,方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郁火日久不除,邪气实则致虚,脾胃运化功能受损,寒邪内生。证见泛酸、烧心、胃脘疼痛胀满、嗳气、食少、纳差、乏力,舌质淡,苔黄、脉弦数、兼关脉弱,证属寒热错杂,方选半夏泻心汤;久病多虚,脾胃病日久,虚劳诸不足者,症见:食少、纳呆、胃脘胀痛隐隐、偶有泛酸、食积不化、嗳气、乏力、手足不温、身怕冷、舌质暗淡、苔白厚兼水滑、脉沉弱等症状,证属脾胃虚寒、方选黄芪建中汤、运脾汤加减。下面兹举验案与同道学习。
1 胆热犯胃证
患者李某,女,50岁,2018年1月19日首诊,自诉胃脘疼痛伴泛酸、恶心半月余,咽部不适,口舌生疮,自觉时冷时热,口苦,心急,夜间手脚发烫,自服“小柴胡汤丸”、“莲花清瘟胶囊”未见缓解,舌暗红,苔薄黄,脉细弦。既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病史。中医诊断:胃脘痛;中医证型:胆热犯胃证;治以清胆和胃,方选小柴胡汤。处方:柴胡10g黄芩10g半夏10g太子参15g甘草5g炒麦芽15g 4剂,每日一剂,饭后分服。
二诊:自诉服至第三剂时,即感泛酸、咽部不适明显缓解,时冷时热症状减轻,现仍感口苦,舌边疼痛,两手发烫,夜间尤甚,心急,睡眠差,舌暗红,少津,脉弦。原方易太子参为党参20g,黄芩加量至15g,加玉竹15g,嘱服7剂。七剂后诸证悉愈。
按:详查患者病史,未诉有明显外感因素,但自觉时冷时热,患者以为“感冒”,自服“小柴胡汤丸”、“莲花清瘟胶囊”,服后症状未见明显缓解;思之,患者病发于冬至节气,冬至一阳生,是阴阳交替之时,此时处于阴阳消长平衡阶段,机体应天感召,也会依时而动;因患者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病史,久病舌质暗,正气不足,冬至阴寒之邪依然势强,侵袭人体,里虚表不实,直中少阳,即有寒热往来,心烦,口苦的少阳证,但胃气不足,极易传变阳明,阳明和少阳同病,但本证虽有阳明病变,但阳明证不显著,未见口渴,喜饮,脉洪大或阳明腑实;胃津虽已亏,邪气仍在少阳,郁久而化火,火邪伤阴,当“保胃气,存津液”,故清胆和胃。方选小柴胡汤,方中用大剂量太子参以益胃生津,炒麦芽健胃消食,补胃气以加强祛邪之力。二诊时少阳证和胃脘不适症状已明显缓解,而阴虚证仍然明显,改补为消,加玉竹15g清热生津,黄芩加量至15g,恐太子参滋腻有碍胃气,故易太子参为党参。小柴胡汤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全方具有清热利胆之功效,明显抑制胆汁反流,减轻胃细胞浸润及腺体增生性改变[1]。
2 胆胃郁热证
张xx,男,41岁,2018年1月 4日首诊,自诉夜间胃中泛酸,胸骨后烧灼,口苦1年,曾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及张掖市中医院反复住院治疗,住院时症状有所缓解,出院后复发如故,食少、失眠、多梦、平素怕冷,舌质暗红,苔黄厚,脉弦数。电子胃镜检查示: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中医诊断:吐酸病;中医证型:胆胃郁热证;治以和解清热,方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化裁,处方:柴胡15g半夏10g党参20g黄芩10g龙骨30g牡蛎30g川芎10g白芍10g,7剂,每日一剂,饭后分服。
二诊:自诉烧心、泛酸减轻,睡眠改善,但觉服药后嗓子,鼻干;药对症,守方继服,14剂后诸症明显改善。
按:患者泛酸、烧心、口苦,胆气上逆,是邪气实所致,邪气实则病,病邪循少阳经直达胆腑,胆腑贮藏精汁,有赖于木气疏散,木气疏泄失常,相火旺于内,李杲曰:“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乘其土位。”阴火上冲则心烦、失眠,乘土位则泛酸、烧心、食少,故而使胆胃不和,应和解清热,方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中柴胡、黄芩、半夏和解内外,祛除贼邪;党参补脾胃气虚;龙骨、牡蛎镇静安神、引火归元;白芍酸酐化阴,以阴制阳,养肝柔肝,合血中气药川芎以强肝用,奏疏散之功解郁。全方共奏和解清热之功。
3 寒热错杂证
刘xx,男,52岁,2018年1月12日首诊,自诉间断性烧心、泛酸,伴夜间盗汗10余年,平素稍活动后即自汗出加重,矢气后有少许稀便从肛门流出,大便稀,平素怕冷,舌质暗淡,舌苔黄腻,脉弦略数,兼关脉沉弱。中医诊断:吐酸病、汗证;中医证型:寒热错杂证;治以平调寒热,方选半夏泻心汤化裁,处方:半夏10g黄芩10g黄连5g干姜10g党参30g甘草5g薏苡仁30g山药30g,7剂,每日一剂,饭后分服。
二诊:烧心、泛酸明显减轻,活动后自汗出较前已少,仍盗汗,薏苡仁减量至20g,继服10剂,诸症已愈。
按:患者患病已久,久病脾胃损伤,阴液暗耗,阴虚则盗汗;胃阴不足,阴虚则热,故泛酸、烧灼;胃阳不足不能达于肌表,腠理不固,则自汗出,阳虚则寒,故怕冷;中气不足,则肛门失约,有矢气后有少许稀便从肛门排出,脾虚生寒湿则大便稀;故而属寒热错杂,当寒热平调,使阴阳调,胃气和;方选半夏泻心汤化裁;半夏燥湿化痰醒脾,黄连苦寒,燥湿清热,泻阴火;干姜辛温,温中暖胃,散寒气;黄连、干姜辛开苦降,一升一降,寒热并用,恢复脾胃气机升降;党参健脾益气,合山药健脾生津;薏苡仁利湿健脾;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共奏寒热、阴阳平调之功。本病西医属胃食管反流病,指胃内容物反流至食管而引起的一系列食管症状或食管外症状的疾病。典型症状反酸、烧心,亦可有胸骨疼痛等[2]。半夏泻心汤出自《伤寒论》。有研究显示,半夏泻心汤组的总有效率为95.0%,明显高于西医组的80.0%。由此可见,半夏泻心汤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方面疗效显著[3]。
4 脾胃虚寒证
丁XX,女,71岁,2018年1月16日首诊,自诉间断性胃脘部烧灼样疼痛3年余,夜间疼痛加重,晨起觉胃中有困重感,食后饱胀,打嗝,怕冷,手足不温,平素喜热饮,舌质暗淡,有瘀斑,苔薄水滑,脉沉细。中医诊断:胃脘痛;中医证型:脾胃虚寒证;治以温中散寒,补虚止痛;方选黄芪建中汤化裁;处方:黄芪30g桂枝15g白芍15g干姜10g石菖蒲10g麦芽15g元胡15g川楝子5g枳壳15g。7剂,每日一剂,饭后分服。
二诊:疼痛未见明显缓解,其余症状不同程度减轻,加丹参10g、檀香5g,继服20剂后,诸症皆安。
按:余师以为疼痛无外乎不荣则痛、不痛则痛;夜间疼痛者责之于寒或瘀,夜间阴气盛,阳气相对不足;阴盛则寒,阳虚则寒,不足者瘀;患者胃脘疼痛,以夜间为重,是脾胃虚寒之故;呈烧灼样,是贼火郁结与胃;脾胃虚寒,胃阳不足,气机升降失司,饮食停滞胃内,故晨起觉胃中有困重感,食后饱胀,打嗝,平素喜食热饮;脾胃中焦虚寒,中轴之气不能通达四末,故手足不温;虚寒之气凝滞,不能上乘,故舌暗淡,有瘀斑,苔水滑。《金匮要略》云:“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故方选黄芪建中汤以温中补虚,合金铃子散止痛,辅以石菖蒲化痰醒脾;麦芽消积化食;不足者瘀,外加丹参饮化瘀止痛。杨群平[4]研究证实,黄芪建中汤可调节胃蛋白酶活性,以及拮抗氧自由基,同时对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作用,最终促进胃黏膜的修复。
5 脾胃虚弱证
孙某,男,30岁,于 2018年5月17日因“间断性腹痛腹泻2年余,加重3天”就诊。诉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腹泻,遂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给予西药治疗后,症状稍有缓解。之后反复发作,3天前再次出现上述症状,平素疲乏、饮食欠佳、自汗、气短。现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遂就诊于田师门诊。查舌淡,苔白,脉细。中医诊断:泄泻,证属脾胃虚弱证。治宜益气健脾、化湿止泻。给予运脾汤口服,处方:党参30g,炒白术10g,茯苓 15g,清半夏 10g,陈皮 10g,佛手 10g,炒枳壳 15g,莱菔子 20g,干姜 5g,焦六神曲 15g,焦麦芽15g,甘草5g。7剂,水煎服,日一剂,饭后温服。嘱患者避生冷油腻及辛辣食物。
二诊:服以上中药7剂后患者大便每日3~4行,腹痛稍有减轻,胃口渐佳,出汗减少,舌红,苔白,脉细。故将原方茯苓加至20g,焦麦芽改为20g,加浮小麦10g,继服12剂。
三诊:诉服药后腹痛明显缓解,大便每日1-2行,疲乏、出汗、气短好转,舌淡红,苔薄白,脉细,临症加减后,嘱患者再服半月,心情舒畅,以巩固疗效。
按:田老师认为患者素体脾胃虚弱,湿邪蕴盛,以致泄泻。脾虚则无以化湿,即本病基本病机为“脾虚湿盛”。方中重用党参,健脾益气,脾气旺则湿去,炒白术益气健脾,燥湿健脾,茯苓利水渗湿,清半夏燥湿和胃,为四君子汤,陈皮,佛手,炒枳壳三者理气健脾,莱菔子,焦六神曲,焦麦芽,三者合用健脾和胃,干姜温中散寒,甘草调和诸药。
6 肝郁脾虚证
胡某,女,45岁,于 2018年4月17日因“间断性腹泻1年余,加重一周”就诊。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腹泻、便质稀溏、无明显规律,遂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给予西药解痉、止泻、止痛等对症治疗好转后出院。后间歇性出现上述症状,尤其在心情不畅时更易发生。1周前因与邻居争吵后再次出现上述症状,大便每日4~8行,伴肠鸣、矢气频发,腹痛腹胀,嗳气食少,烦躁,胸胁闷胀,小便可,夜寐差,舌质红,苔薄白,脉弦细。自服“肠炎宁胶囊”,症状未见缓解,遂就诊于田师门诊。中医属泄泻,证为肝郁脾虚证。治宜疏肝健脾。给予痛泄要方合柴胡疏肝散加减,处方:白术15g,炒白芍 15g,陈皮 6g,防风 15g,茯苓 10g,柴胡10g,木香 15g,香附 10g,郁金 10g,炙甘草 5g,石榴皮5g,大枣10g。6剂,水煎服,日一剂,饭后温腹。嘱患者时刻保持心情愉悦。
二诊:服以上中药6剂后,患者腹痛稍缓解,大便每日3~4行,胸胁闷胀稍有减轻,胃口渐佳,睡眠好转,舌红,苔白,脉细弦。遂将原方防风改为10g,加焦六神曲15g,炒麦芽15g,酸枣仁10g,继服12剂。
三诊:诉服药后腹痛腹胀缓解,饮食可,睡眠可,大便正常。临症加减后,嘱患者再服半月,心情舒畅,以巩固疗效。
按:《素问·举痛论》言:“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飱泻”。田师认为患者平素脾胃虚弱,加以肝气不舒,脾失健运而致本病的发生,且在情绪变化后症状加重,由此可见情志不遂,可致肝气郁结,疏泄失司,肝木犯脾土,脾胃运化失职,清浊不分而为泄泻。方用白术健脾燥湿,白芍柔肝缓急,二者合用共奏补脾柔肝之功用;防风升清止泻;柴胡疏肝解郁;木香、香附、郁金疏肝理气止痛;陈皮理气醒脾,茯苓健脾益气,实土以御木乘;少量石榴皮涩肠止泻、顾护正气;炙甘草、大枣顾护胃气。诸药合用,共奏疏肝健脾、涩肠止泻之功。
总结:脾胃病临床经方运用灵活,辨证时在于准确掌握辨证要点,即证的根结点所在,通过以八纲为提纲挈领,结合脏腑经络生理关系,明确病性及病位,三因制宜,将症候做“一元化”分析与总结,使证完全显现,辨治时理法方药统一,会使临床疗效倍增。
——水溶性维生素泛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