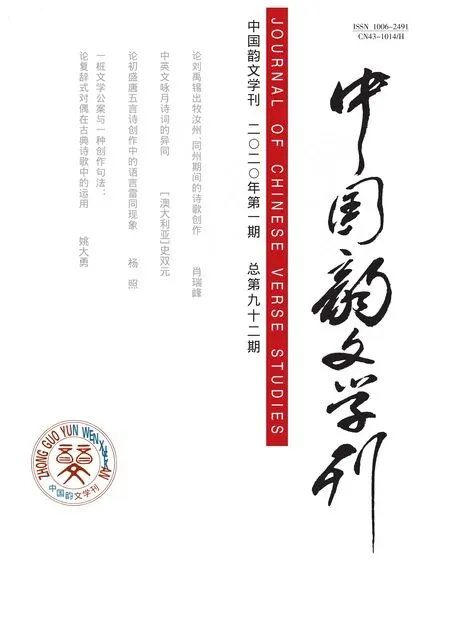姜夔《鬲溪梅令》中“鬲”的音义问题
王彤伟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一
“鬲”在《汉语大词典》中有三个读音:lì、ɡé、è;姜夔自度曲《鬲溪梅令》中的“鬲”到底读哪个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当读ɡé,理由如下:
一、从异文的角度看当读ɡé。《钦定词谱》卷七:“姜夔自度曲,一作‘高溪梅令’。”“高”字中古读古劳切,与读作古核切的“鬲”相近。当然,这个异文更有可能是因字形近似之误而造成的。
二、其实,异文“高溪”之义欠明确,且于史无据。姜夔在《鬲溪梅令》的自序里写道:“丙辰冬,自无锡归,作此寓意。”据《白石道人年谱》载:“白石于淳熙甲午(按即公元1174年)至丙午(公元1186年),十三年间辞家为客,北历江淮,南游湘浦,固岁无宁处。即自沔东来,依千岩,居苕上,八易星霜,亦年年行役。惟丙辰(公元1196年)移家杭州,嘉宾贤主往来优游。”可知自无锡归处当为杭州。然查《中国历史地图集》[1](P63),并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检索二十四史等二百余种历史资料,南宋无锡、杭州附近并没有叫“高溪”者。(1)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有个“高溪”在荆湖南路永州境内湘江之畔,今永州和祁阳之间。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集部五三·词曲类存目》收录有《白石词集一卷》,其中早已指明异文“高溪”不正确:“安徽巡抚采进本,宋姜夔撰……然其中多意为删窜,非其旧文……《鬲溪梅令》毛晋汲古阁本注曰:‘仙吕调’,此本乃讹作《高溪梅》,又讹注为‘仙宫调’。”
三、此“溪”当为无锡西门之外的梁溪。《白石词编年笺注》在《鬲溪梅令》之前有一首《江梅引》,其下小序曰:“丙辰之冬,予留梁溪,将诣淮而不得,因梦思以述志。”夏承焘笺注:“梁溪,在无锡西门外,相传以梁鸿居此得名。”[2](P64)从时间和顺序上看,《鬲溪梅令》紧承《江梅引》而作,故《鬲溪梅令》所言之“溪”当即“梁溪”。
四、“鬲溪梅”即“隔溪梅”,义为“隔着溪水(梁溪)的梅花”。隔溪看梅,花既不可得,所见亦朦胧,与词句“好花不与歹带香人,浪粼粼”的意、境正合。
五、“鬲”通“隔”的例子早已有之。如《管子·明法解》:“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其中“鬲”即“隔”的通假字。《史记·匈奴列传》:“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其中“鬲绝”即“隔绝”。《汉书·武五子传》:“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颜师古注:“鬲与隔同。”更有说服力的是姜夔自己作品中有“鬲”通“隔”的例子,姜夔《解连环》:“道郎携羽扇,那日鬲帘,半面曾记。”
二
《汉语大词典》中“鬲”的“lì、ɡé、è”三个读音中lì、ɡé来自《广韵》,è来自《集韵》。然而,来自《集韵》的è音并不可信,我们先看看《汉语大词典》è音条的原文:
【鬲3】è《集韵》乙革切,入麦,影。通“搹”。以手扼物。《仪礼·士丧礼》:“苴绖大鬲。”郑玄注:“鬲,搤也。”贾公彦疏:“鬲是搤物之称。”(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士丧礼》:“苴绖大鬲”。校勘记:“《要义》同毛本,鬲作搹,下同。”可知此处的“鬲”实当作“搹”;若写作“鬲”,即为“搹”的通假字。“搹”即“扼”,“大扼”犹今言“一大拃”。
《汉语大词典》注明此音来自《集韵》,查《集韵·入声二十一麦韵》作:“軶鬲枙《说文》:“辕前也。”或作鬲枙。”[3]按照《集韵》的体例,被训字为“軶”,“鬲枙”是两种异体。查《说文·木部》:“槅,大车枙。从木鬲声。古核切”[4]《说文解字系传》补充例证曰:“臣(徐)锴按,张衡《西京赋》曰‘商旅连槅’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槅,《考工记》作鬲。”据段注可知“槅”在《考工记》中有写作“鬲”的,然而此“鬲”乃“槅”的借字,由徐锴按语可知在其所见的《西京赋》中表示“大车枙”时还是写的本字“槅”,而非通假字“鬲”。《说文·车部》:“軶,辕前也。从车戹声。于革切”段玉裁注:“軶,隶省作轭。《毛诗·韩奕》作厄,《士丧礼》今文作厄,假借字也;《车人》为‘大车作鬲’,亦假借字;《西京赋》作槅,《木部》曰:‘槅,大车枙也。’枙当作軶。”[5]
可见,古籍里“軶、枙、槅”才是异体关系,写作“鬲”是假借的缘故。也就是说,并非“鬲”有è音,而是书写时因为有用音近形简的“鬲”代替“軶、槅”的情况,编字典的人就囫囵而将其放在一起了;《集韵》收字时将假借字和异体字混收在一起,这或许是体例所限未做说明;后人不明其故反倒认为“鬲”有è音,《汉语大词典》也因此误立【鬲3】条目。其实《汉语大词典》应将此项置于【鬲2】后的通假义项中,没有必要单列为【鬲3】。
三
那么,《汉语大词典》中“鬲”的lì、ɡé两读是怎么来的?查《广韵》,发现其中“鬲”已经有两个读音:一是见纽麦韵开口二等,古核切,折合今音为ɡé;一是来纽锡韵开口四等,郎击切,折合今音为lì。[6]那么《广韵》中的这两个读音又是怎么来的?是由一个古音分化来的,还是历史音变中语音讹变的结果?
《广韵》“麦”韵“古核切”除“鬲”外有九个从“鬲”得声的字(隔、膈、搹、槅、、、目鬲、魚鬲、嗝);“锡”韵“郎击切”也不只“鬲”一字,除“鬲”之外至少还有四字(蒚、镉、馬鬲、酉鬲),可见这种变化不是单独的,而是成系统的,因此不是历史音变中语音讹变的结果。
现在看来,这两个读音的声母区别最为明显。然而,这些字既然同以“鬲”为声符,那么它们早期的声母应该是相同的。在上古声母的构拟中,高本汉等构拟的有gl类复辅音声母,郑张尚芳在《上古音系》中也举了不少类似的例子,如“糗kh-:臭khj-;墨m-:黑hm-;聂n-:摄hnj-”等。郑张尚芳进一步说:“从古文字说,‘各’是‘彳各’的初文,经常写作二等的‘格’,‘各’并作‘洛’的声符,所以含有l不成问题。……现在按结构分析一下,高氏所举gl、kl、sl、bl、pl等十一种cl结构及sn是常见的,可无疑。”[7](P121)高本汉把上古来纽拟音为l、gl[7](P226),其中的复辅音gl[kl]正是“鬲”声字分化的来源。
韵母方面又是怎么变化的呢?段玉裁在《六书音韵表》中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可知上述以“鬲”为声的两组共十三个字其韵亦当近同。郑张尚芳《上古音系》认为“鬲、厄、历”等字上古同属“锡”部,拟音作[ek],到中古分化成了麦[k]和锡[iek]两韵。
综上,我们可以把“鬲”字的语音分化情况简单图示如下:

上古《广韵》反切及拟音使用情况↗鬲[kæk]古核切鬲穴(穴位名)或隔、枙之假借字。鬲[klek]↘鬲[liek]郎击切鼎釜之属。
因此,《鬲溪梅令》之“鬲”当读ɡé,是“隔”的假借字,“鬲溪梅”即“隔着溪水的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