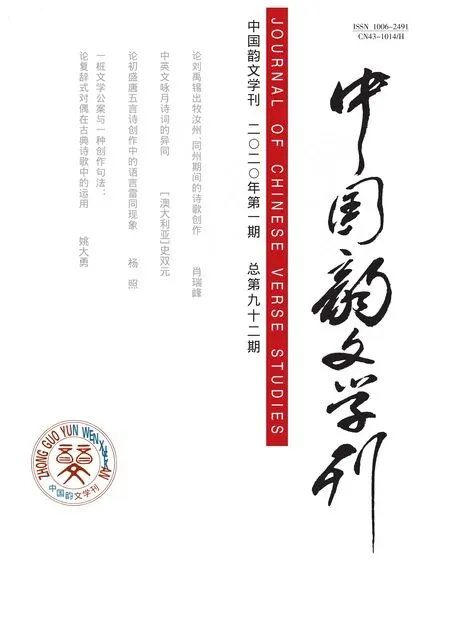《玉栖述雅》与况周颐的女性词论
徐新武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玉栖述雅》是况周颐的遗著,生前未刊,后由弟子陈运彰发表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1941年第六期,是书专论清代闺阁词人,集中体现了况周颐的女性词论观。经统计,《玉栖述雅》收词话33则,涉及清代的闺秀词人28位,涉评女性词作105首,况氏直接或间接评语至少35条。陈运彰为《玉栖述雅》所作跋语曰“而论词精语,有足与词话相辅翼者。残膏剩馥,沾溉后人,政复不浅”[1](P120),此处“论词精语”即指况氏评女性词的精言胜语,而“足与词话相辅翼者”则道出了况氏的女性词论与其词学思想相辅相成、自成一脉之关系。
一 况周颐词话中的女性词论
况周颐一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尤以词学理论享誉词坛,其著名词话《蕙风词话》,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和王国维《人间词话》并称“晚清三大词话”,其主要论词观点体现于《蕙风词话》第一卷,建立了以“重、拙、大”为核心的词论体系。况氏论词上及晚唐五代,尤对花间词人推重,下至有清一代、晚近词坛,对前辈乡贤和师长友朋词亦有评涉。在况氏各种词话、笔记、序跋和考辨文章中,亦对少为人关注的闺秀词特别是有清一代的闺秀词给予很高评价,这在同时代其他词人的词论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由于其闺秀词论比较零散,本部分首先对况氏女性词论在其著述中的分布情况作简单考察。
在况氏主要词论著作《蕙风词话》一书中,有数则论及女性词人。如《蕙风词话》卷一第六一则提及戈载夫人金婉《宜春舫诗词》,卷二第八八则评得趣居士词:
得趣居士词(1)“得趣居士”为丁宥侧室周氏号,《阳春白雪》卷七有其和丁宥《瑞鹧鸪》一首,《全宋词》亦有收录。,喁喁昵昵,致绣细熏。[2](P50)
卷四第六则考辨花蕊夫人词及其事迹,第十则考证西施投湖而死事迹,第十一则至十四则,分别考证了朱淑真事迹及其词作情况,第十五、十六则记获李清照小像、石头事[2](P91-99)。卷五第二则评论李清照词为“《淑玉》之绵丽”,第十三则论及陆宏定妻周氏事迹及其词,第十七则论明代女词人郑如英词及其详细事迹,并选录其《红豆词》中词作。[2](P112、117、119)
唐圭璋辑《蕙风词话续编》二卷(2)唐圭璋教授在况氏逝十年后,据况氏《餐樱庑词话》《选巷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众香集》《香东漫笔》《香海堂馆词话》中辑出《蕙风词话续编》三卷,分期发表于1936年《艺文月刊》。后因卷二仅数则,1960年王幼安在校订《蕙风词话》时将唐辑二、三卷并为一卷,厘定为两卷,后唐圭璋据以采录入《词话丛编》中,并于各条加上小标题。详参孙克强《况周颐词学文献考论》,《文史哲》2005年第1期,第98页。,其中亦有数则涉及闺秀词人,有几则直接关涉到况氏闺秀词的评价标准。《蕙风词话续编》卷一第四三则,记载聂氏与李之问、马氏与朱瑞朝情事,录聂氏《鹧鸪天》、马氏《减字木兰花》词各一首,并评论聂胜琼《鹧鸪天》词云:
纯是至情语,自然妙造,不假澡琢,愈浑成,愈秾粹。于北宋名家中,颇近六一东山。方之闺帏之彦,虽幽栖、淑玉,未遑多让,诚坤灵间气矣[2](P114-115)。
第六三则引张芬回文词,开篇即对论闺秀词“无庸以骨干为言”的陋说进行批评,并举证论述闺秀词不仅仅只有那些搓酥滴粉、讲究辞藻而无实际内容的闺阁无聊之作,亦有俊发巧思、情蕴灵动而自然的妙笔。《蕙风词话续编》卷二第九则完整载录顾太清《东海渔歌》词四首,认为其词“直窥北宋堂奥”,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在其《东海渔歌序》中有更清楚的评述;第十九则据《众香集》载录高丽权贵妃词三阙,评其词“林下雅音,异邦尤为仅见”;第三四则载尼静照曹氏《西江月》词,评其词“体格雅近北宋”。[2](P166、169、174、180)可以说,女性词很早就进入况氏关照和评价的视野,他通过考订女性词人词集,抄录相关作品予以品评,除了保存文献的考虑,亦是为女性词人正名。
《玉栖述雅》一书则专门辑录清代闺秀词人。据陈运彰《玉栖述雅跋》,“玉栖”得名亦有渊源,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漱玉词》,与李氏同时而稍后的另一著名女词人朱淑真,号幽栖居士,有《断肠词》,“玉栖”盖由此来(3)陈运彰跋语云:“玉栖述雅一卷,临桂况先生未刊遗著之一。玉栖云者,漱玉、幽栖,闺彦词家别集存世之最先者也。今评泊闺秀词,因刺取以为名。”又说“此稿成于庚申辛酉间,随手撰录,聊资排遣”,可知此书大致作于1920到1921年间。。由“玉”“栖”二字亦可看出况氏对女性词人的关注和重视。此书集中反映了况氏的女性词论观,后文将详论之。
另有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其主要据《玉栖述雅》一书,参考况氏其他笔记、随笔、序跋等,专门辑录况氏载录女性词及其事迹,汇成《蕙风词话补编》卷二,载录女性词人词事计六十九条。(4)屈兴国所辑《蕙风词话补编》卷二共计69则,其主体部分辑自况氏《玉栖述雅》一书,其他部分辑自况氏笔记、随笔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零星碎语,奈何屈兴国先生在辑录时并没有明确标注辑录出处,亦没有就本编辑录作详细的说明,这为查找原文带来了困难。但屈氏对况氏论女性词及事略作了集中辑佚,为考察况氏女性词论提供了很大帮助。其中包含了许多论女性词人词作的精辟之见,如《蕙风词话补编》卷二第四则,况氏论李清照《漱玉词》中屡用叠字之妙,“叠法各异,每叠必佳,皆是天籁肆口而成,非作意为之也”。[3](P428)第五则论李清照悼亡词《孤雁儿》《浪淘沙》,谓“其清才也如彼,其深情也如此”。[3](P429)第四八至五〇则专论顾太清词,如论太清咏花词“极合宋词消息,若多看近人词,一中其病,便不能如此纯粹”,《贺新凉》词“不必以矜炼胜,饶有清气,扑人眉宇”,《寿楼春·送春》词“肆口而成,毫不吃力,似此功候,碻从宋词中得来”,将顾太清词与宋人词格相比拟,极加赞赏。[3](P456-468)第五一则论山阳闺秀顾伯彤《惜春阁词》,开篇即论:
填词有三要,曰重拙大,非于此道致力甚深不办……《惜春阁词》庄雅不佻,于重字为近,得之梱闼中,信未易才也。[3](P469)
用“重”字来评述顾伯彤词的艺术功力。第六二至六四则专论俞因词,评其《清平乐·为君木制客枕绣此词其端》曰:“此词情深一往,昔人‘寒到君边衣到无’之句,未足以喻。歇拍尤见慧心。”[3](P480)又论其《点绛唇》词浑成圆融,可达宋人境地。
除以上各书辑录况氏论闺秀词者,在况氏为许多词集所作的题跋序言中,亦有多则涉及对女性词人的品评。如他为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作的序中,明确指出对闺秀词的珍视与挖掘,而不可轻忽。又为顾太清《东海渔歌》词作序,并专门为其词校勘,作《东海渔歌校记》,赞赏顾春词的艺术渊源及内涵:
太清词,得力于周清真,旁参白石之清隽。深稳沉着,不琢不率,极合倚声消息…纯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烦洗伐,绝无一毫纤艳涉其笔端……太清词,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3](P589-590)
又其《断肠词跋》说“词学莫盛于宋,易安淑真,尤为闺阁奇才”,称颂李清照、朱淑真为闺阁奇才,将闺秀词亦作为两宋词繁盛景观的一部分。
二 《玉栖述雅》与况氏评女性词的主要标准
在《玉栖述雅》一书中,况周颐详细论述了黄月辉、钱餐霞、关秋芙、顾太清、萧月楼、吴小荷、朱葆瑛、储啸凤、吕寿华、席道华、杨古雪、熊商珍、伦灵飞、严端卿、柯稚筠等28位清代女性词人,并对其人及词集存录情况作了考辨和辑佚。其中关涉到女性词人词集17部,涉评词作105首,大半是完整摘录其词。这些词作多不见于当时已刊刻的大型词集中,为况氏累积多年艰辛搜寻而得,具有很高的词学文献价值,对研究清代闺阁词人大有裨益。况氏对具体女词人词作间或有评语论之,其中可窥探出况氏论女性词的一般标准。
《玉栖述雅》第十九则,况氏论席道华(佩兰)《长真阁诗余》时说:
《长真阁诗余》虽仅十七阙,就其佳构言之,在闺秀词中却近于上乘。评闺秀词固属别用一种眼光。大略自长真阁以上,未可置格调于勿论矣。[4](P4613)
明确提出了“评闺秀词,固属别用一种眼光”,批评“评闺秀词无庸以骨干为言”的陋见,从性别视角上,对闺秀词予以重视,这倒不一定是评闺秀词时须大加赞赏,而是关注女性词本身及女性词人的创作环境和心理,毕竟女性词人一向被正统词家所轻视。况周颐的呼吁,代表了一位词学家的远见卓识。
邓红梅在其《女性词史·绪论》中从风格美感、情蕴内容、创作心态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女性词人不同于男性词人的美感特征:
就女性词的总体面貌来看,渊源于大体已被改造过的不同性格天赋,受激于总体相同的生存背景下有所不同的生活遭遇,她们对于生活和词艺所形成的‘兴奋点’彼此差异,词的内涵和美感也是各如其面。[5](P2)
并以“纤婉”和“清慧”作为女性词的总体审美特征。况氏作为晚清词论大家,不限于对男性词的品评,而提出“评闺秀词,固属别用一种眼光”,看到女性词的独特价值,实属难能可贵。那么况氏所说的“别用一种眼光”,又是怎样一种“眼光”呢?
况周颐评女性词的“别用之眼”之一即是“轻清婉丽”。《玉栖述雅》第二则论钱餐霞《雨花盦诗余》“轻清婉约,思致绝佳”,并论其词“慧心人语,有碧耦玲珑之妙”[4](P4606);第二四则论熊商珍(琏)“女史词诗俱妙,出自性灵”,并评其《澹仙词》“清疏之笔,雅正之音,自是专家格调。视小慧为词者,何止上下楼之别”。[4](P4616)其将词品与人品联系起来,从女性的主体性特质从透视其词作的内涵。又如第八则论萧月楼(恒贞)《月楼琴语》词“疏秀清灵,兼擅其胜,似此天分,自进于沉着,可以学北宋,未易期之闺秀耳”[4](P4608);第九则论吴小荷《写韵楼词》“轻灵为闺秀词本色,即亦示易做到行间句里。纤尘累累,失以远矣”[4](P4609);第十二则论朱葆瑛(玙)《金粟词》“篇幅无多,笔端饶有清气”[4](P4610)。由此,“清”作为闺秀词的本色特征被况周颐提炼出来。其他如第二一则论杨古雪(继端)《蝶恋花·春阴》《买坡塘·西泠送春》“两词佳境,渐能融婉丽入清疏”[4](P4614);第二八则论伦灵飞(鸾)词“尤清婉可诵,气格渐近沉着,不涉绮纨纤靡之习”等[4](P4618)。无论是“清疏”、“轻灵”、“清气”还是“清婉”,况周颐都试图以某种轻倩婉约的概念来总括女性词的柔婉特质。
“轻”即“轻灵”,“轻灵为闺秀词本色”;“清”即“疏秀清灵”,词笔有“清气”,“清疏之笔,雅正之音,自是专家格调”;“婉”即“婉约”“清婉”;“丽”为“婉丽”,不是俗丽,“丽而不俗,闺词正宗”。同时“轻清”“婉约”密不可分,它是衡量闺秀词的基本审美标准。“轻”与“清”相联系,代表了女性词轻巧疏秀、清灵自然的独特风格;同时“清”与“婉”、“丽”又紧密融合,“融婉丽入清疏”,方可“意自深婉”,这都表明况氏注意到闺秀词人纤细诚挚、婉丽动人的心理特征。实际上,词体诞生的环境本身与歌儿舞女有密切的联系,唐五代北宋的文人词下笔多涉闺阁生活,词笔清婉妍丽。而词论史上也多以清婉柔媚为词体本色,将花间正声作为词体艺术内涵的重要评价标准。但以往闺秀词多属男性代笔,女性只是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进入作品,他们很少主动发生。况周颐单独拎出女性词来品评,无疑是注意到女性作为创作主体的特殊意义,他们笔下的词作更能代表词体婉约柔美的本色内涵。
况氏评女性词的“别用之眼”之二即是“真情”。《玉栖述雅》第四则论关秋芙(瑛)词《高阳台·送沈湘佩入都》“情文关生,渐饶烟水迷离之致”。第五则开篇即说道“词笔微婉深至,往往能状难状之情”,再论关绮(侣琼)《清平乐》歇拍“却又无愁无病,等闲过到今朝”是“其辞若有憾焉,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翠袖天寒,青衫泪湿,其揆一也”[4](P4607);第十则论吴小荷词,首先即说“吴媛盖性情中人也”,其《写韵楼词》多思亲之作,如《碧桃春·己亥元旦》云:
烛消香透晓来天。东风入绣帘。一声恭祝画堂前。椿萱眉寿添。 调凤律,献羔筵。斑衣学古贤。融融春色报丰年。书云快睹先。[4](P4609-4610)
况氏评“此词近凝重,有精采,又非以轻灵胜者,可同年语矣”,盖因此词本色清婉,结句“书云快睹先”尤能突显相思之切,以乐事衬哀情,可谓精彩。又评吴氏《鹧鸪天·甲辰秋舟次全州寄怀李凝仙姊》及《双调南乡子·永乐署寄怀湘君四嫂》词为“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惟有真性情者,为能言情,信然”。又第十七则论吕寿华(采芝)《秋笳词》词“情文惋恻,词称其名”[4](P4612);第十八则论席道华(佩兰)《声声慢·题风木图》词“道华此作,尤能缠绵悱恻,字字从肺腑中出。虽浑成稍逊,不当有所轩轾也”[4](P4613),以上皆是对作品自然真情的强调。又如《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论聂胜琼《鹧鸪天》词“纯是至情语,自然妙造,不假澡琢,愈浑成,愈秾粹”[2](P145),亦是对女性词至情至性的要求。
以上所论表明,《玉栖述雅》及况氏其他词话著作,都注意从“真情”或“至情”这一标准去透视女性词背后的情蕴内涵。“惟有真性情者,为能言情”,只有具备一往而深之真情,词作才能达到“情文关生,渐饶烟水迷离之致”,才有“近凝重,有精采”的深沉内涵,才有“缠绵悱恻,字字从肺腑中出”的摄人心魄。“真情”即“至情”,愈是真情至情,愈是“自然妙造,不假澡琢,愈浑成,愈秾粹”。从“真情”这一情感内蕴出发,使得况氏对闺秀词人充满同情与关注,故能在评涉具体词作时感同身受,极度赞赏闺秀词人在抒情上的“情文惋恻”、细腻幽深,从而发现并载录那些自然流露、不加雕饰的女性词作,考辨她们的生平事迹,搜寻她们的词集作品,为女性词在词史发展上的地位添上重重的一笔。
“沉着”和“以宋词为旨归”的审美期待,亦可算作况氏对闺秀词持有的“别用之眼”。《玉栖述雅》第八则论萧月楼(恒贞)《月楼琴语》词“疏秀清灵,兼擅其胜,似此天分,自进于沉着,可以学北宋,未易期之闺秀耳”;第九则论吴小荷《踏莎行·遣怀》词,谓“此阕后段,渐近沉着,视轻灵有进矣”;第二八则论伦灵飞(鸾)词“尤清婉可诵,气格渐近沉着,不涉绮纨纤靡之习”,并引朱彊村语“先生盛称之,谓雅近宋人风格”。[4](P4608、4609、4618)这些都对女性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沉着”是况氏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仅如此,《蕙风词话续编》卷二第九则论顾太清《东海渔歌》词“直窥北宋堂奥”;第三四则载尼静照曹氏《西江月》词,评其词“体格雅近北宋”。《蕙风词话补编》卷二论顾太清词“咏花四阙,极合宋词消息,若多看近人词,一中其病,便不能如此纯粹”,论《冉冉云·雨中张坤鹤过访》谓“质而拙却近宋人,政复不俗”。[3](P465)又论太清《浪淘沙慢·久不接云姜信用柳耆卿韵》谓“朴实书情,宋人法乳,非纤艳之笔、藻缋之工所能梦见”,“西林太清春《寿楼春·送春》,肆口而成,毫不吃力,似此功候,碻从宋词中得来”。[3](P466-468)可见,在况周颐眼中,两宋词或确切地说北宋词代表了其心目中词的至境。
“沉着”是“轻灵”渐进之状态,是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故有“自进于沉着”“渐近沉着,视轻灵有进”“深稳沉着,不琢不率”。“沉着”是词境渐近浑成、气格厚重之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审美特质。只有达到“沉着”之境,方可与宋人词相接融。所谓“自进于沉着”“气格渐近沉着,不涉绮纨纤靡之习”,最终指向都是“雅近宋人风格”“极合宋词消息”“直窥北宋堂奥”。只有“沉着”,才能“质而拙,却近宋人,政复不俗”。况氏女性词论的最高标准也只能用“沉着”来概括,不管怎样,宋词代表了词体发展的最高峰,只有达到“沉着”之境,方可接近宋词堂奥。在具体品评女性词时,况氏亦时时与北宋名家词相参照,这就说明况氏对女性词境的最高期待是“宋词”,尤其是北宋名家词。而要合“北宋消息”,首先则要合“沉着”之境。但闺秀词总体来说,少有能达到“沉着”之境的,故况氏对女性词的最高评价也只是“渐进沉着”“直窥北宋堂奥”,这种对女性词的审美期待颇值得玩味,其背后暗含了况氏词学思想与其女性词论之间的某种关联。
三 况氏女性词论与其词学思想之关系
以上主要就《玉栖述雅》和《蕙风词话》、《蕙风词话续编》等著述集中考察了况周颐的女性词观,大致从四个方面简述了况氏对女性词论所持之评介。但通过论述发现,况氏女性词观与其主要的词学观念是统一融通的,其对闺秀词的“别用之眼”并无特殊之处,反映了其论词理路的内在统一。这比单纯的重视“闺秀词”更进一步,将闺秀词纳入其总体的词学评价体系中,实际上,对女性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轻”“丽”之辩
此处须辨析“轻”与“丽”二字。前已论述“轻清婉丽”是况周颐评价女性词的基本出发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轻”并不违反况氏的“重拙大”之旨,尽管况氏《词学讲义》开篇即指出“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但此处的“轻”并不等于况氏论女性词时所使用的“轻”(5)李慧认为“闺秀词的‘轻灵’本色显然是不符合‘重’的气格”,因而得出“她们很少会拥有男性那样的性情和襟抱,表现在创作上她们就不太会选择那些重而大的内容题材,在意象的选择上也多为丝雨、落花那些轻灵优美的意象,语言亦是轻巧灵动为主”这样的结论,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没有看到况氏论女性词之“轻”与“重拙大”之“轻”有“气格”上的根本不同。况氏并不反对“轻”,这里的“轻”只是相对于“重”而言,反对“气格”上的逼仄轻巧,流于清浅滑俗,达不到寄托和情感上的“沉着”之境,况氏反对的是这样的“轻”。至于“轻灵为闺秀词本色”则是看到女性词轻灵谐婉,灵动自然的独特审美内涵,二者立论与审美内涵的指向都不同,并非李慧所说的“闺秀词的‘轻灵’本色显然是不符合‘重’的气格”。[6]。在《蕙风词话》卷一第四则,况氏就指出“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中就此则评道:
盖重者轻之对,拙者巧之对,大者小之对,轻、巧、小皆词之所忌也,重在气格。若语句轻,则伤气格矣,故亦在语句。但解为沉着,则专属气格矣。盖一篇词,断不能语语沉着,不轻则可做到也。[7](P4585)
故与“轻者重之反”相对应的则是“气格”上的“轻”,有气格方能“沉着”。邓乔彬《况周颐‘重、拙、大’说析论》一文指出“所谓重,正是沉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气格”[8](P65),而对应的“轻”则达不到“沉着”之境,亦无法体现词人沉挚的情感与深婉的思想。很明显,况氏论女性词所提出的“轻”是“轻灵”之意,是女性词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审美特征,与“气格”无关,故不是“轻者重之反”之“轻”。况氏看到女性词轻灵要妙、婉约动人的独特审美内涵,因而指出“轻灵为闺秀词本色”。
再论“丽”字。“丽”是“清丽、婉丽”,不是“艳丽”。况氏并不反对“丽”,在《蕙风词话》卷二第九十则中,况氏对词笔“丽”与“艳”作了区分,“艳如芍药、牡丹,慵春媚景;丽若海棠、文杏,映烛窥帘”。[3](P104)在同卷第四十则论魏文节《虞美人·咏梅》词“只应明月最相思。曾见幽香一点未开时”评道“轻清婉丽,词人之词”。[3](P78)第九七则中论刘辰翁《须溪词》“间有轻灵婉丽之作”[3](P108),由此也可说明况氏并不反对“轻灵”,只是反对“气格”上的“轻巧”。“丽而不俗”亦是况氏论女性词的一条标准,此处的“丽”当时“清丽、婉丽”,与“艳丽、纤丽”不同。况氏是反对“纤艳”的,在《蕙风词话》卷二第十七则批评“明已来词纤艳少骨,致斯道为之不尊”,[3](P64)大抵“纤艳”则落入俗套矣,词不朴厚,词品亦大大降低。这与对闺秀词“丽而不俗”的要求是一样的。
实际上,“轻清婉丽”也不独是况氏论闺秀词的标准,在《蕙风词话》卷二论魏文节《虞美人·咏梅》词时亦评道“轻清婉丽,词人之词”。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况氏论词,无论男女词人,在某种程度上持相同的评价标准,这就比单纯重视女性词更进一步,而把男女性词人放到同一评价体系中,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更加客观全面。
(二)“真情”不限于闺秀词
况氏在品评闺秀词时,对“真情”的重视,这与况氏通常论词的情感理念是一致的。在《蕙风词话》卷一第十五则,况氏即指出“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在同卷第二七则有“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在《蕙风词话》卷二第一七则论清真词句“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落泪”时,评道“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明确提出了“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这与况氏论闺秀词时持“真情”论的情感内蕴是一致的。都是从“真情”出发,探讨词人真实深婉的情感状态。并由此揭示“真字是词骨”,“情真”才能写出“吾心之万不得已之情状”的佳作。
“真情”亦与况氏的“重拙大”之旨相合。只有真性情者,才能写出符合“重拙大”之旨的作品,“真字是词骨”,唯“真”才能达到“至情”,从而发自肺腑,出而成章,所作自然厚重深沉,思致玄远,风格浑成圆熟。“真情”并不限于闺秀词,大凡佳作巨制,背后都有深挚的情感内蕴作为支撑。对词作“真情”的重视,一向都是况周颐词学理论的情感基点。从“真情”出发,况氏看到了闺秀词的“微婉深至”,亦提出“情真、景真,所作必佳”的作词方法,其背后的论词理路是贯通融合的。
(三)“沉着”是况氏论词的最高标准
如前所述,“沉着”之境对女性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考察况氏的主要词论时,我们亦可发现,无论男性女性词人,“沉着”都是况氏论词的重要标准。或者说,在况氏“重拙大”说为核心的词论体系中,“沉着”一直是其论词的内在理念。《蕙风词话》卷一第二十则,况氏论学词程序要“先求妥帖、停匀,再求和雅、深秀,乃至精稳、沉着。精稳则能品矣,沉着更进于能品矣”,这就揭示了学词的最高境界是“沉着”,与论女性词时的审美期待是一致的,能“沉着”,则词能品。在此则词话中,况氏还详细诠释了“沉着”二字,“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掷地作金石声矣。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之诠释也”[2](P7-8)。
在《蕙风词话》中,况氏每每以“沉着”论词,与此则对“沉着”的诠释紧密契合。邓乔彬《况周颐‘重、拙、大’说析论》一文中总结道:
沉着厚重既是为词者所追求的目的,又是成词的基础,是气格的根本保证。进而则求神韵与空灵,使沉着与远致、凝重与空灵得到辩证的统一,这就是词的佳境。[8](P66)
沉着厚重是况周颐评词的最高标准,作品能达到沉着之境,自然也就达到况氏重拙大的三个要求。只不过沉着厚重是况氏对词作审美评价的终极参考,更具形上层面的观照,而重拙大之旨是形而下的,更为具体,它指向更为基础的创作层面,更具实际的指导意义,但终极归宿亦要求能达到沉着之境。况周颐论闺秀顾伯彤《煕春阁词》时,曾再次重申其填词三要之旨,并论顾氏词“庄雅不佻,于重字为近”,[3](P469)此处的“重”接近“沉着”之义,要求词作不能轻佻浅近,而能于庄雅之中见性情学养。所以“沉着”之谓,在批评男女性词作上是贯通而统一的,都是评论词作的最高标准。
四 结语
综上,况周颐率先提出“评闺秀词,固属别用一种眼光”,对女性词予以特别重视,具有相当开阔的词学眼光。在具体评述闺秀词的“别用之眼”时,主张“轻灵为闺秀词本色”,“丽而不俗,闺词正宗”,佳词应是清婉可诵,真情贯注,同时要“融婉丽入清疏”,追求“轻清婉丽”的艺术效果。另外,在《蕙风词话》卷二况氏论魏文节《虞美人·咏梅》词时亦评道“轻清婉丽,词人之词”,可知“轻清婉丽”并不单是论女性词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词体特质而为众多词人所讲求。又如况氏重视女性词“真情至情”背后的情感内蕴,对女性词“情文惋恻”,“意自深婉”极为赞赏,但“真情至情”论并不限于闺秀词中,《蕙风词话》卷一明确指出“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这说明况周颐重视的是作品本身的真情实感,与论词对象无关。与此同时,词体的艺术特质与创作主体的情感特质相结合,即“重拙大”之旨与“真情”论相相合,才能创造出在审美上浑融厚重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况氏推崇两宋词为审美高境,只有具备“沉着”之境的作品才有可能近于“宋人消息”。《蕙风词话》中况氏屡次提到“沉着”这一概念,并且说“重者,沉着之谓”,把“沉着”与“重拙大”论结合起来,明示了况氏论词内在理路的一致和连贯。简言之,况周颐虽强调女性词“轻清婉丽”等特质,但其心中早已形成“沉着”和以宋词为旨归的终极评价标准,故无论是闺秀词人还是其他著名词家,他都只关注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这实际上对女性词人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况氏一生治词,其论词之精微,在晚清词坛无人能出其右者,《玉栖述雅》中况氏提出的女性词观,亦是其沉厚博大的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况氏虽未必与之,但其关注点却与社会思潮暗合,显示了一位词论家的敏锐和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