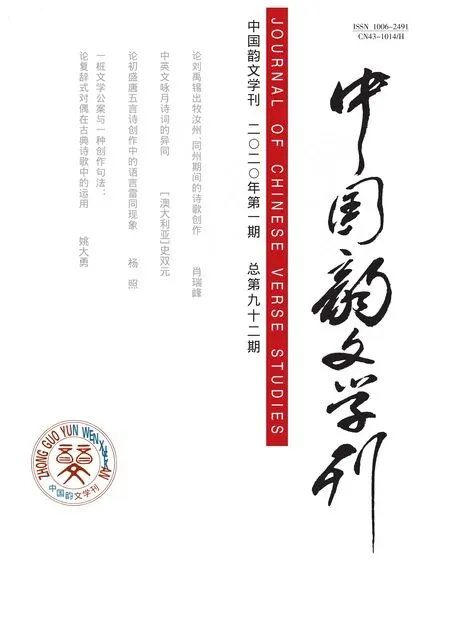临安末照中的禅僧诗变容:觉庵梦真《籁鸣集》《续集》
王汝娟
(复旦大学 出版社,上海 200433)
临济宗虎丘派僧觉庵梦真(1214?—1288),宁国卢仁乡人,俗姓汪,字友愚,号觉庵,嗣法大歇仲谦,曾住永庆寺、连云寺、何山寺、承天寺等。梦真也是一位热衷于笔墨的诗僧,有诗集《籁鸣集》二卷、《籁鸣续集》一卷存世。此两种诗集在中国已经亡佚,仅在日本存有古抄本(尊经阁文库藏)。然《全宋诗》未收录其人其作,金程宇从日藏《籁鸣集》《籁鸣续集》抄本录出所载诗二百三十五首[1],朱刚、陈珏《宋代禅僧诗辑考》据他书补辑十三首[2];《全宋文》亦无其人,据笔者目前所见,梦真撰有《月磵和尚语录序》[3],此文或当补入。
梦真生活的宋末元初时代,禅门文学已臻于烂熟。然梦真的创作,以对政治和社会的强烈关怀、对国家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为我们清晰地展现出禅僧诗的另一种面貌。
一 亲历宋元鼎革
祥兴二年(1279),崖山被蒙古军攻破,陆秀夫负幼帝投海,至此国祚延续了三百余年的赵宋画上了句号,一个王朝终于谢幕。梦真在人生的暮年亲身经历了宋元鼎革,目睹南宋山河为异族铁蹄践踏、无辜百姓在战火硝烟中饱受种种苦难,尽管他是方外之士,也不免为之动容唏嘘,用一首首诗歌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所思。这类作品为数不少,在他的集子中所占比例颇重,无论是对于我们今日研究南宋诗歌嬗变还是宋元之际的社会面貌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关于这一点,许红霞在其《珍本宋集五种》之《〈籁鸣集〉、〈籁鸣续集〉整理研究》中已经指出。譬如以下三首诗:
瓜州望金山有怀
何许金笳发,边兵早禁城。
夕阳收塔影,疏雨湿钟声。
旧俗淳风泯,新春白发荣。
大江东去急,犹带犬羊腥。[4](P159)
闻宣城为虏所据
山川旧俗晋风流,花满东溪月满楼。
胡骑北来云气黑,王师南溃剑光收。
岂无石鼓刊龙德,安有金城贮犬酋。
昨夜梦魂归最切,腥风吹雨湿松楸。[4](P179)
送人游金陵归九华
西风吹断吴山云,长空万里玻瓈明。
扁舟未解北星缆,清梦忽堕长干城。
城头呜呜吹画角,城下嘤嘤奏胡乐。
风前一曲断肠声,几人血泪□珠落。
麒麟脚底春雷动,是谁耕破前王冢。
玉杯依旧出人间,白骨自生秋草梦。
君家住近江水东,山开九朵青芙蓉。
苍崖鬼火照夜雨,古洞□乐延秋风。
吁嗟世路惊蛇绕,危机杀人当面笑。
归欤荒田宜早锄,愿无旱潦雀鼠相侵渔。[4](P172)
这三首诗描写了瓜州、宣城、金陵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战事频仍,到处血雨腥风、民不聊生的凄惨场景。梦真所作《籁鸣续集跋》曰:
呜呼!孰无生?生于治世;孰无死?死于正寝。生非治,死非正,率为冤□□□。丙子予客四明,三月九日,北帅奥鲁赤部马步五千,由会稽入四明,躬责归悃。越三日,搜兵四掠,穷山绝顶,例不免祸。继此黄世强合刺正副招讨出兵为口,搜劫不已,民生哀号,毋所赴愬。奉川盐□□□素秉忠义,气盖一方。奋臂一呼,万□□□□集,痛与之角。开合三月,北兵日增。即□□□□泯灭无闻。北兴问鼎,乡民十杀□□□□□□血厌原隰,焚荡掘伐,野无完□。□□□□□地西山,日寓于目,多以诗纪之。□□□□□□之音,哀怨乖囷,非盛时雍容和□□□□□□日既久,积成若干篇,荐入诸梓。□□□□□□今老矣,必有极治之时,予不得□□□□□□。知我罪我,准此集乎!戊寅中秋寅□宣城觉庵梦真友愚书。[4](P204)
从这篇跋文可以看出,梦真亲历了兵火中的颠沛流离,他用诗歌记录下自己体验和见闻的种种,并“积成若干篇”,收入自己的诗集中付梓。在此我们不可忽视和忘却的是梦真的“禅僧”身份。虽然与唐代、北宋相比,南宋禅僧诗在题材上已然明显扩大,与士大夫之诗渐趋接近,[2](前言)但在反映社会、反思现实这一点上,仍然是与士大夫诗歌有相当差距的。而梦真的诗歌创作,正如上引其跋文所云,他主观上就有非常强烈的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意识,所以才有这类数量丰富的反映现实的诗作之诞生。
二 对昏君奸臣的直言痛斥
虽然目前学界对所谓“江湖诗派”“江湖诗人”等的界定颇有歧见,但如果仅从身份上说,无一官半职的禅门诗僧自然属“江湖诗人”无疑。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将江湖诗派创作的主题倾向概括为“忧国忧民之怀”“行谒江湖之悲”“羁旅之苦”“友谊之求”四种;其中在“忧国忧民之怀”中,作者以主要收录江湖诗人诗歌的总集《南宋六十家小集》为例,指出在其5340首诗中,具有忧国忧民情怀(即政治内涵)的诗作有180首以上,并将其政治内涵总结为忧国(主要是渴望收复)和忧民(主要是关心农民)两类。[5](P44-58)那么梦真的这类诗作,和其他江湖诗人有何不同呢?
首先从直观的数量上来看,《籁鸣集》《籁鸣续集》所收230余首诗作中,具有明显政治内涵者有近60首,所占比率约为四分之一。相较于《南宋六十家小集》(180/5340),这个比率显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其次,《南宋六十家小集》中的这类诗作主题多是渴望收复失地以及关心农民,直白露骨地抨击黑暗时政之作并不多,而《籁鸣集》《籁鸣续集》中这类政治题材的诗作往往多毫不隐讳地揭露时政之弊。以下从《籁鸣续集》之组诗《家国丧亡,自昔有之,不有不道颠覆之君,则有奸伪卖主之臣。以今日事体考前代国史,盖大有难言者,使人扼腕,泪不之禁。杂咏十二绝以纪此时,于诗何有哉》中选取数首为例来做分析。该诗由十二首绝句组成:
(一)
风流十万羽林郎,生死唯知义所将。
丞相指令都解甲,伯颜徐步藕花塘。
(二)
海风推上伍胥魂,怒气何时罢吐吞。
欲问春秋吴越事,胡儿骑马入修门。
(三)
绮罗巷陌管弦楼,人在华胥国里游。
胡马一嘶天地黑,蜀关无路幸龙辀。
(四)
花市灯残漏曙光,千官拥阙六街香。
莫嫌过眼繁华歇,元是春闺梦一场。
(五)
湖水粼粼接御沟,春风吹起满城愁。
□□□□通蛮徼,此日金珠委虏酋。
(六)
葛仙坡下藕花庄,水阁风亭处处香。
师相厌听歌管乐,半年一度入都堂。
(七)
宫梅苑杏感无言,夙沐先皇雨露恩。
北客爱花犹畏禁,袖笼一朵出黄门。
(八)
银烛煌煌洞火城,六街香雾拥香尘。
胡儿马上横孤笛,吹落关山月一轮。
(九)
马城西畔百花林,一树茶丹一两金。
花自南开人自北,春风那有两般心。
(十)
西湖花柳又逢春,别馆旗亭草积茵。
陌上相逢不相识,语音多是北来人。
(十一)
野塘春水绿于醅,无主山花落又开。
日暮鸬鹚无处泊,衔鱼飞上拜郊台。
(十二)
西林春雨草青青,牧马应须趁晓晴。
惭愧胡儿相戒饬,岳王坟近莫高声。[4](P186-187)
这十二首诗一气呵成,读来颇有酣畅淋漓之感。从该诗题中的“不有不道颠覆之君,则有奸伪卖主之臣”一语,即可见出其内容为抨击导致国家走向覆亡的昏君和佞臣。首先看第一首。“羽林郎”为汉置禁军官名,掌宿卫、侍从,(1)《后汉书·百官志二》:“羽林郎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这里指南宋军士。首二句写这些军士为保家卫国而奋勇御敌、舍生忘死。第三句之“丞相”所指似为南宋末宰相陈宜中。伯颜(1236—1295),蒙古军将领。《宋季三朝政要》记载:
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至桐关,去杭百里,我师败绩。独松关告急,召文天祥入卫。天祥自吴门还,遣守独松关。时天祥军三万,张世杰五万,诸路勤王师犹有四十余万。天祥与世杰秘议,今两淮坚壁,闽、广全城,王师与之血战,若捷,则罄两淮之兵,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世杰大喜,遂议出师。独宜中沮之,白太皇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说。遂止。[6](P422-423)
此诗乃根据史实而作,毫不留情地直接痛斥了当朝宰相为苟且偷生而将疆土拱手相让的懦弱行径。
第二首首句用了伍子胥的典故。伍子胥身为吴国功臣,忠心耿耿,但吴王却听信奸臣太宰嚭谗言令其自刎,后吴国终为越国所灭。这里以吴越春秋之历史,影射南宋由于小人当道、贤臣良将不得重用甚至惨遭迫害而导致国家沦亡于异族之手。从“海风推上”一语来看,具体所指当为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宋端宗南逃至井澳(今南海),海上忽起飓风,端宗落水染病;在元军追击下,他又从海路逃往碙洲(今硇洲岛),不久即驾崩。赵昺被拥立为帝,陆秀夫为左丞相。陆秀夫与伍子胥一样同为楚人,祥兴二年(1279)崖山被攻破,“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7](P13276),至此国祚延续了三百余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画上了句号。《宋史》评论道:“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7]( P946)而宋末秉政的正是上一首诗所抨击的陈宜中,因此第二首与第一首有一定的承续性。
第三首批判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在江南的和风细雨中沉溺于冶游享乐,不励精图治,与林升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末句“蜀关无路幸龙辀” 以唐玄宗作比况,安史之乱中首都长安沦陷,玄宗逃往蜀地,躲过性命之劫,之后唐王朝仍延续了百余年。而宋末蒙古军攻占临安后,虽然端宗和赵昺也乘船外逃至南方,却没有玄宗幸运,不久就彻底国破家亡。
第六首主要是讽刺南宋权相贾似道。《宋史纪事本末》记载:
三年二月,贾似道上疏乞归养,帝命大臣侍从传旨固留……特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赐第西湖之葛岭,使迎养其中。似道于是五日一乘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时蒙古攻围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与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虽朝享景灵宫,亦不从驾。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8](P1128-1129)
这首诗中所述贾似道之情状与史实是一致的。它非常直白地痛斥了贾似道耽于淫乐、不理政事,以至于朝纲废弛,国家终走向灭亡。
第十一首通过写景来寄寓亡国之情。首二句不难令我们联想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作者眼前的景象比杜甫当时所见更为凄凉,因为南宋才是真正的“国破”,“无主”一词饱含着多少兴亡之感。这里的“拜郊台”既是眼前实景,可能也双关了吴王之拜郊台,《中吴纪闻》载:“吴王拜郊台,在横山之上,今遗迹尚存。春秋时,王政不纲,以诸侯而为郊天之举,僭礼亦甚矣。”[9](P63)吴王拜郊台是“王政不纲”的象征,以此暗讽南宋末年的腐朽朝政导致了亡国。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梦真对于国家、时政等的深切关注,对为君、为臣之道的深刻反思。这种关注和反思,并不是隐晦的,相反可以说非常直白和显露,这是他与当时其他江湖诗人创作的显著差异。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对南宋遗民诗人的地域分布做了考察和归纳,大致可分为“阵容庞大的故都临安群”“诸社联袂的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的联合群”“以方凤等为首的浦阳群”“以桐庐为中心的严州群”“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群”“以建阳、崇安为中心的福建群”“以赵必为首的东莞群”。[10](第三章)可以看出,南宋灭亡后浙江一带是遗民诗人尤为集中的地区。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宋室南渡后随之而来的文化中心之转移,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积淀,浙江一带已成为当时的文人渊薮之一;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南宋驻跸临安,周边地域长年来历经皇城雨露的熏沐,文人的家国意识尤为强烈,故而在山河沦亡后更易生发出万般悲慨。
方勇在该书中,认为对于“南宋遗民诗人”的界定,不应该“把是否出仕新朝作为裁决是非的依据”,而应当“主要看他在内心深处是否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10](P8)按照这一判断标准,梦真虽然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出任承天寺住持(关于梦真住持承天寺的时间,参《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之《〈籁鸣集〉、〈籁鸣续集〉整理研究》对梦真生平的考证),但从其诗作反映的心境来讲,他无疑可归于南宋的遗民诗人队伍。梦真毕生大部分时间都活动于浙江地区,和该地的不少士大夫文人和江湖文人也有密切交游,因而他以这样一种“遗民”心态创作出政治色彩、入世色彩此般浓重的诗歌自然是不足为奇的。
三 禅僧诗之变容
《宋代禅僧诗辑考》之“前言”中,将宋代一般的禅僧诗题材归结为五类:第一类与士大夫所作之“诗”无别,如唱酬之作、山居诗、乐道歌等;第二类是偈颂;第三类是针对前代某一公案发表见解、体会而撰成的“颂古”;第四类是赞、铭等;第五类是与严格的“诗歌创作”距离最远的“有韵法语”。显而易见,其中后四类题材与禅僧的身份最为契合。而第一类题材,僧人因为生活环境和佛门戒律的局限,创作的此类诗歌往往会落入“陈词滥调”的窠臼。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11](P266)
这个故事常为后人引用,借以指摘佛门文学单调、陈腐、枯槁之弊病。其实这些字亦常常出现在士大夫的诗歌(尤其是山水诗)中,并不唯僧人诗作所独有,诸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等等,可是这些字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可见,这些字(或后来所谓的意象)本身是无所谓优劣的;问题在于在僧诗中,这些意象所承载的内涵和情感往往被固定化,这些语词所指向的,无非是山林、幽居,无非是闲适、寂寥。人人如此,内容便显得空洞无物;读者读多了,不免味同嚼蜡。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序章指出:“中国诗歌发展到南宋后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卑弱、雕饰的‘衰气’。然而,蒙古铁骑的突如其来,却无情地惊醒了宋末士子的酣梦,使他们真正体验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与悲哀。”南宋山河易主,自然会有不少士大夫为之痛心疾首,以笔墨书写一腔悲愤。其实,被蒙古的铁骑惊醒的不仅有“居庙堂之高”的士人,也有“处江湖之远”的下层文人。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亦不免深深触动梦真的诗笔,诚如在《籁鸣集序》中所云,他创作诗歌是由于“遇物感兴”“风激林籁”:
诗与禅俱用参,参必期悟而后已。参须参活句,不当参死句。活句下悟去,迥然独脱。死句中得来,略无向上承当。知诗、禅无二致,是必曰悟而后已。唐之名家者不下三百余辈,皆从参悟中来。王建《宫词》有曰:“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学者多作境会,既不求意于言外,又不求悟于意外,徒诵之哓哓而卒无成功,是岂后□□□扬子云者用心之不苦耳。予结发从□□□□,及其长也,讨论湖海名流,凡四□□□□□□疲。飒然白首,虽未臻阃奥门墙,□□□□□□能强使之为也。必也遇物感兴,而□□□□□诸中必形诸外,如风激林籁,自然□□□□□鸣也。故名是诗曰“籁鸣”。[4](P137)
“遇物感兴”之“物” “风激林籁”之“风”,理所当然包括作者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正是在这种诗学理念的支撑下,梦真才创作出了如此之多的见证历史、见证现实的诗歌。这一创作风貌,不难令我们联想到在宋代获得“诗史”之誉的杜甫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12](第五章)虽然梦真的《籁鸣集》《籁鸣续集》中并无明确提及杜甫、白居易的文字,但从其具体诗作来看,他应该对杜诗、白诗颇为熟稔并有意模仿之。例如这首《卖炭翁》:
伐薪南山窑,烧炭通都鬻。权门炙手热,焰焰莫轻触。阍人买炭不与直,炭翁缩缩僵门立。手皴足裂面黑漆,此时力不胜寒。呜呼炭翁汝知否,炭是汝烧寒汝受。明朝天地春风酣,炭无人买□□安。[4](P163)
该诗无论是标题、诗体,还是内容、语言等,都显然有白居易《卖炭翁》一诗的影子。此外,在《籁鸣集》《籁鸣续集》中,有不少出自杜诗的典故或化用杜诗的句子,例如“巡櫩索共梅花笑”“忆昔太平无事日”等。显而易见,杜诗、白诗的“善陈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梦真的创作影响极深。
经历宋元鼎革的方外禅僧,当然并非仅梦真一人。然而,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当时禅僧的创作中,唯有他用如许丰富的作品来记录了在当时风云变幻下的外在景况和内心思索。《籁鸣集》《籁鸣续集》在内容上表现出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强烈现实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梦真的诗歌创作,可谓是传统禅僧诗的一种变容。这一内容上的开拓,矫正了传统禅僧诗语言、题材、思想等单一化、趋同化的倾向,带来了禅僧诗的崭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