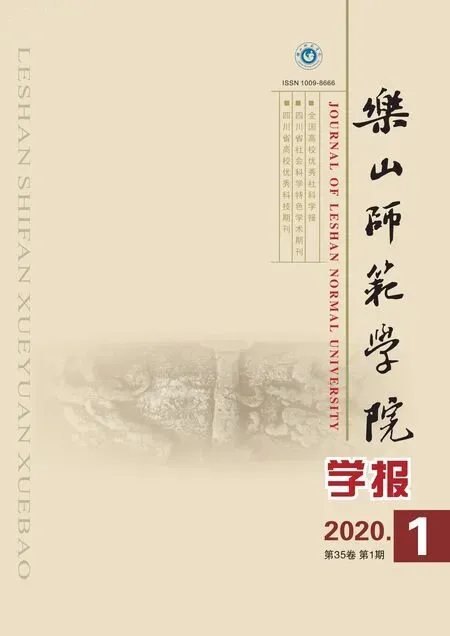《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重现的价值和意义
乔建功,王文一
(1.郏县财政局,河南 郏县 467100;2.河南郏县宾馆,河南 郏县 467100)
“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是元代为郏县三苏坟所树立的一个标志性设施,但因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却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2015年春拜读平顶山市苏轼研究学会会长杨晓宇先生《从“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的发现谈苏轼、苏辙葬郏问题》一文(见2014年/专号《三苏》),获悉郏县薛店镇一农户藏有光绪二十二年重修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之后多方探寻,几经周折,终于2016年秋如愿以偿,见到了久违的“神道碑”,随后又与友人一起对其进行了拓片、拍照处理(见图1)。

图1 光绪二十二年重修二苏神道碑
神秘的“神道碑”静静地平躺在这家的东厢房门前。据主人介绍,“文革”期间,其父亲在村修桥工地旁发现这块石碑,觉得毁坏了实在可惜,就冒着风险在夜间将其运回家,保存至今。我们来到碑前,揭去覆盖在上面的毛毯,只见居中八个盈尺篆书大字“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分列两行,字字端庄典雅,笔笔规范有致,通篇显示着篆书的柔和之美和力量之刚。石碑左边是端庄寸楷题跋“苏文忠、文定两公神道碑岁久损裂,郏县知县山左夏联钰重为立石,按旧题篆书之,守苏坟僧智慧双钩上石并书跋”(其标点为笔者所加),另行落款“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四月立 石工朱修成刻字”。通篇文字完好无损,石碑的下部虽缺碑榫,现有尺寸仍达244 cm×70 cm×20 cm。
从跋文可知,此碑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经郏县知县夏联钰重修的。算起来重修该碑距今已有123年。石碑历经沧桑,频仍战火,能够保存如此之完好,的确十分难得。
山左者,是山东的古称。夏联钰,山东济宁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进士。郏县民间至今还流传有关于夏大人的故事传说。所谓双钩上石,就是将书法作品覆盖在石碑上,循笔画两侧外沿以细线钩勒出空心字,再对勾出的空心字填上朱色或黑墨,然后再摹刻到石碑上,以求达到接近真迹之效果。这是古代摹刻名人书法的一种技法。
这通重修“神道碑”的发现,充分说明元代以降六百余年,此“神道碑”一直围绕苏坟屡毁屡修,生生不息,绵延流长,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它早已不复存在的错误认识,从而也将廓清此前苏坟历史上所产生的诸多疑点,无疑是三苏葬郏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一、谁之篆书?
这通重修的“神道碑”自2014年被发现公之于众四年来,不少学者认为碑上“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八个篆书大字,是元代书法家虞集原来的手迹,且频频为之称道。也就是说,这八个篆书大字是苏坟寺主持僧通过双钩上石从原来旧碑上复制过来的。然而,如果仔细品读跋文“苏文忠、文定两公神道碑岁久损裂,郏县知县山左夏联钰重为立石,按旧题篆书之,守苏坟僧智慧双钩上石并书跋”,你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以上理解大相径庭。从语法角度讲,其中的“重为立石”和“按旧题篆书之”,均为夏联钰所为,即夏联钰是这两句的主语。后者中的“旧题”和“篆书”属古汉语中两个名词连用的情况,且这两个名词不是并列、偏正、同位、判断的主谓关系,故“篆书”在这里应该用作动词,即“用篆书书写”。而“之”,很明显是指代这八个大字。查《词源》“旧题”,为“过去所题,多指诗词题跋之类”,这样“按旧题”就构成动词“篆书”的介宾结构状语。因此,对跋文正确的解读应该是:“神道碑”年代久远,碑体损裂。郏县知县夏联钰重新为之立碑,并按原来所题的内容,用篆书写下这八个大字。苏坟寺住持僧智慧将其双钩上石并题写跋文。也就是说,因原碑体“年久损裂”,无法恢复其原来的字迹,才由夏联钰用篆书写下了这八个大字。然后由苏坟寺主持僧将夏联钰所写的这八个篆书大字通过双钩上石的方法摹刻到这块石碑上。

图2 夏联钰书法团扇
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八个篆书大字,是由时任郏县知县夏联钰书写的,而不是虞集的手迹。由此可见,我们的夏大人书法水平之高。近日,在网上查找夏联钰信息,得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联钰任武陟县知县时,在《创建武陟万花庄青龙神祠东西厢崇祀风云雷雨之神记》碑上落款“知府衔在任后补直隶州知州大计卓异武陟知县夏联钰篆额”。特别是网上还开办有《夏联钰书画艺术网》,拍卖的团扇(见图2)上,有遒劲的篆书题字和清晰的“夏联钰”署名。凡此种种,均表明夏联钰不愧是篆书高手。
那么,光绪二十二年是根据哪个“神道碑”重修的呢?原来这八个大字是什么书体呢?
二、原碑之谜
略懂苏坟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三苏坟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中收集有时任郏县教谕孙友仁撰写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阴记》(以下简称《碑阴记》)。此《碑阴记》是当年首次所树该碑的背面刻记,后收入《成化河南总志》流传至今。《碑阴记》开篇载“至顺改元秋,汝士刘端伯捧礼部侍郎符文及奎章阁学士虞中奉楷书八字,下汝之所隶郏邑。”[1]47从中可知,此碑原立于元代至顺元年(1330)秋,距今已有689年的历史。
《碑阴记》告诉我们,“眉山两苏先生神道”是由奎章阁学士虞集书写的八个楷书大字,并且是从北京写好后带到郏县来的。“虞中奉”者,时虞集为中奉大夫也。虞集(1272—1348),字伯生,元史有传。虞集祖籍四川仁寿(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系初唐楷书大家虞世南之后,南宋丞相、抗金名将虞允文五世孙。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其母为国子祭酒杨文仲之女。宋亡,为避战乱,虞集随父迁临川崇仁(江西省崇仁县)。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虞集至大都(北京),被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深受赏识,任太常博士,后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泰定四年,随泰定帝至上都(元朝皇帝避暑夏都,也称开平府,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用蒙语和汉语讲解经书,诸大臣深为折服,升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为怀王时,已知虞集之名,即位后授之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世大典》,书成后进翰林侍讲学士,升通奉大夫(从二品)。卒谥文靖。其诗文有“元诗四大家”之称。虞集早年与弟虞槃同辟书舍为两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曰“邵庵”。故世称虞集为邵庵先生。有《道园学古录》传世,故一称道园先生。推算可知,此“神道碑”八个大字是其五十八岁时的作品。

图3 虞集书法
“碑阴记”明确告诉我们,首次树碑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八个大字为虞集所书之楷书。查《中国书法全集》等典籍,均介绍虞集受先祖虞世南影响,善楷书、行书,有“古隶第一”之称,而很少见其篆书作品。现在所看到重修的“神道碑”,是平放埋在地下的,无法看到其背面。笔者一再追问李姓主人,背面是否有刻字?他十分肯定地说,背面没有任何刻字。说明后代在重修该碑时,只双钩上石正面的八个大字,没有重刻背面的《碑阴记》。这样,就造成文献中的《碑阴记》与实物碑刻长期分离,致使《碑阴记》中记载的“楷书八字”,而今看到的“神道碑”正面是篆书大字,两者得不到相互佐证,乍看起来不免使人困惑。其实是光绪二十二年因原碑体损裂,无法复制虞集的楷书手迹,才由郏县知县夏联钰篆书代替之。
三、正《县志》之误
道光四年(1824),河南督学吴慈鹤(字巢松)曾主持对苏坟进行大规模维修,竣工后吴有长达八百余言的长诗《谒苏坟 并序》。郏县举人魏谦六(道光六年进士及第,后出任顺天府文安县知县)看到后,写下了《和督学吴巢松先生<谒苏坟>原韵》(以下简称《原韵》),记述修葺苏坟的盛况。其中有“龙溪新铭元卿撰,螭蟠鳌伏苍穹摩”句。以上两长诗均收入同治三年《郏县志》。1983年郏县志总编室在整理校注同治三年《郏县志》时,对“龙溪新铭元卿撰”注释为:“龙溪,水名,在苏坟南八里许,北岸有元赵孟頫书的‘元巩国武惠公哈拉神道碑铭’。”[2]848笔者认为,虽然薛店与苏坟之间树有赵孟頫书写的元朝大将哈拉神道碑,但诗中的“新铭”决不是指哈拉墓碑而言。其理由有三:(1)历史上哈拉神道碑从来没有重修过,何来“新铭”!(2)魏谦六明明是为庆贺修葺苏坟而咏,没有理由颂扬元代将领的墓碑。(3)同治三年《郏县志·古迹·金石》中已有“二苏神道碑 题曰: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元 虞伯生书”的记载”[2]400,说明同治三年(1864)之前“神道碑”已经存在。因此,在两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原韵》作者所歌颂的只能是“神道碑”。而这个“神道碑”就是道光四年(1824)所重修的,并且像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上有碑额,下有碑座,“螭蟠鳌伏”,雄踞龙溪之旁,直指云天,蔚为壮观。
据当年主持校注郏县志的同志回忆,虽然同治三年《郏县志》有关于“神道碑”的记载,但因没载明其所处的位置,更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信息,谁也没有引起注意,认为这里只是附庸所记罢了。当时的确是在不知道“神道碑”存在的情况下,把诗中的“新铭”误当作赵孟頫书写的哈拉神道碑了。今天看来,同治三年《郏县志》中,对“龙溪新铭元卿撰”的注释应改为:“龙溪,水名,流经薛店附近,岸边有道光四年重修的二苏先生神道碑。其上书:‘眉山两苏先生神道 元虞伯生书’。”
既然这里明文题款“元 虞伯生书”,那么就可断定此时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是八个楷书大字;也可以推断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前,上溯至元代至顺元年(1330)首次树立此碑以来的566年间,该碑正面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八个大字都是虞集所书的楷书;只是到了光绪二十二年因碑体“年久损裂”,遇到了篆书高手郏县知县夏联钰,才由楷书变为篆书了。难怪光绪二十二年重修的“神道碑”不再有“元 虞伯生书”的题款了。行文至此,不觉为看不到虞集手迹,小有遗憾;同时,也为因夏联钰的篆书,才使“神道碑”能够得以保留至今,而大为庆幸。
四、找回一段历史
目前有文字可考清代曾对苏坟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修缮活动。其中最后一次就是上述道光四年(1824)在吴慈鹤倡导下,由郏县令李虎臣主持进行的。然而,今天我们走进三苏坟院飨堂内,清晰地看到其东的西山墙上工工整整地镶嵌着数十块清代碑刻,其中时间最晚的是同治十年(1871年,距道光四年后47年)十二月汝州训导孙德祖的《谒苏坟六首》,和光绪元年(1875年,距道光四年后51年)十月汝州知州舒亨熙的《谒苏坟》。这两块碑刻的存在清楚地告诉我们,道光四年之后曾经对飨堂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缮。那么这次修缮活动发生在哪一年呢?光绪二十二年重修的“神道碑”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纵观苏坟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维修活动,都需要进行动员、募捐、筹资、勘察等长时间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进行一系列的修缮活动,不可能仅为某一项单个工程搞一次维修。因此,“神道碑”和飨堂内东墙上的两块碑碣共同证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夏联钰的主持下曾对苏坟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活动。这次维修距道光四年后整整七十二年; 这次维修才是清代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维修; 这次维修在修缮坟院飨堂的同时,还重修了“神道碑”。也可以说,重修“神道碑”仅仅是这次维修活动的其中一项。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二十二年维修苏坟其他项目的蛛丝马迹还会有逐步显现出来,有待我们进一步留心观察,努力发掘,认真考证。
五、碑立何处?
最后我们关心的是,这个“神道碑”原来立于何处?遗憾的是原碑的《碑阴记》中,对此只字未提。就在首次树立此碑的二十年后,即至正十年(1350),新任郏县知县杨允祭拜苏坟,倡建三苏祠堂。两年后祠堂落成,曹师可撰写了《三苏先生祠堂之记》(以下简称《之记》)。幸喜《之记》文中明确记载曰:“至顺间,以礼部符文行下郏县,于坟之东南仅十里有薛店,当东西冲要,树石以表之曰‘眉山两苏先生神道’。”[1]13从文中得知,首次刻有《碑阴记》的“神道碑”树立于苏坟东南十里薛店的东西大道之要冲。树碑与建造三苏祠堂仅相隔不到二十年,《之记》文中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图4 正德汝州志
然而,薛店距苏坟现在足有二十里之遥,为什么“之记”文中却说“仅十里”呢?难道说元代的“里”与现代不同?无奈,笔者上网查找“元代一里等于多少米?”,回答是:“陶宗仪《辍耕录》中说,元代240步为一里。单士元《故宫史话》(58页)说,元代一步为五尺,元一尺合0.308米,那么就是一步合1.54米。按此标准换算一里=1.54米×240=369.6米”照此推算,“之记”文中的“10里”只相当于现在的7.4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来,“神道碑”所处的位置,须符合距苏坟“仅十里”(即七八里)的交通要冲,和以上《原韵》诗中“龙溪新铭元卿撰”所说的“龙溪”之畔两个要素。
有人认为,古代雨量充沛,贯通东西的许洛古道是北移十多里沿山脚而行的。苏坟东南七八里处有个使郎庙村。古老的许洛古道就沿村南边经过。该村北有一通往苏坟七八里的小道,百姓称之为饮马路。附近有一黑龙潭,从中流出的溪水名曰龙溪,亦称洪渠,常年溪流不断。“神道碑”应立在许洛古道与饮马路的交叉口的龙溪旁。此东去二里许便是“元巩国武惠公哈拉神道碑”。凡此种种,似乎暗合了“仅十里”与“龙溪”之旁的两个条件。
然而,近来坊间又传一种说法,认为许洛古道历来就是穿薛店而过的。其证据是元代的《之记》文中早已言明,“神道碑”居于薛店东西交通之要冲处。尤其是,明正德元年(1506)修的《汝州志· 铺舍》中记载“郏县西路四铺(半坡铺、苇渠铺、薛店铺、韩夏铺)至汝州,接长阜铺。”[3]43“汝州东路四铺(仁义铺、车渠铺、赵落铺、长阜铺)至郏县,接郏县韩夏铺。”[3]42汝州东、郏县西的八铺相连就是许洛古道(当今洛界公路)的轨迹。正德《汝州志·郏县之图》更清晰载明,许洛古道穿郏县城而过,薛店铺处于郏县西路的四铺之中(见图5)[3]3。

图5 明代正德元年郏县
以上三者相互佐证,表明元、明时期的薛店均为许洛古道上的要冲。再者,发源于使郎庙附近的龙溪,迤逦东南流经薛店古寨西门,至今仍溪水潺潺。传说古代从这里可船行至郏县。古老的“神道碑”应立于薛店通往苏坟的龙溪之旁。再说,光绪二十二年重修的“神道碑”本就发现于薛店,更加强了该碑原立于薛店的佐证。至于“之记”文中说距苏坟“仅十里”很可能是二十里的误传。目前两种说法各执一词,神秘的“神道碑”究竟立于何处,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地考察和论证。
六、余韵悠长

图6 夏联钰撰文“义学功德碑”
就在本文杀青之时,郏县一高退休教师王宪斌先生传来消息。他编纂《王氏家谱》发现,苏坟西南八里许的冢王街王氏祠堂中树有“皇清诰授文林郎锦屏乡县丞委署兴义县知县南园王公神道”碑(世称“王凯神道碑”)和“冢儿镇前寨王氏捐置义学记”碑(世称“义学功德碑”)(见图6)。两碑均上有龙凤呈祥碑额,下有螭蟠鳌伏的碑座,高达丈余,气势恢弘。两碑所署时间均为“光绪二十二年季春”,表彰的是王凯(字布和,号南园,曾任贵州省锦屏乡县丞,兴义县后补知县)一家三代数十年连续举办义学的事迹。其中“义学功德碑”落款署名为:“赐同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钦知同知衔郏县知县河南壬午科辛卯科甲午科乡试同考官加五级记录十次 夏联钰 撰文。”
可见,这是光绪二十二年,我们的夏大人所倡修的又一项文化教育事业。以上得知,夏联钰于光绪六年考中庚辰科三甲进士后,至少在河南连续任职知县二十六年(前述光绪三十二年任武陟县知县),同时先后于光绪八年(壬午科 1882年)、光绪十七年(辛卯科 1891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科 1894年)兼职河南乡试的同考官,并曾加五级记录十次。从中可见,夏联钰资历之深,用心之专,行政之勤。在那风雨飘摇的光绪年间究竟他还做了哪些事,有待予以继续关注、发掘和整理。
综上所述,“神道碑”的重现不仅澄清了历史上的有关疑点,更重要的是找回了苏坟乃至郏县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行文至此,不禁由衷感佩李姓朋友当年抢救保护“神道碑”的义举,否则,就没有“神道碑”的存在,和今天对苏坟历史的再认识。李姓朋友功莫大焉!从而,也彰显了抢救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不禁吁请有关单位应高度重视,发动群众,积极抢救保护散落民间的历史文物,尽快采取措施做好“神道碑”的善后工作,尽早将久违的“神道碑”回归到应有的去处。
据有关人士透露,当年修建距苏坟不远的构树张水库和山头赵水库溢洪道时,曾使用不少苏坟的石碑;现在穿行其间,还依稀看见石碑的身影。另外,1972年发掘苏仲南夫妇合葬墓所出土的百余顶墓砖,被拉到苏坟东南五里许的竹园沟村修造了一座桥。有朝一日,如能将这些石碑、文物抢救发掘出来,必将大大丰富苏坟的实体文物,充分发挥其重大史料价值,进一步推进苏坟的深入研究,廓清有关历史疑云,更将功莫大焉!
注 释:
① 同进士出身: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宋代进士试始分五甲。为一甲赐及第,二甲赐同及第,三、四甲赐出身,五甲赐同出身。明太祖洪武四年始明定一甲限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清代沿用。
②奉政大夫:清代沿用宋元明之阶官(一称散官)以定品级。清初的封阶名称屡有变迁,到乾隆时,奉政大夫为正五品。凡一品至五品授之以诰命,六品至七品授之以敕命。
③同考官:清代科举制度,乡会试时,在正、副主考官下有同考官。同考官分房阅卷,故又称房官。会试同考官,康熙后额定十八人,为十八房,乾嘉后,例用翰林院编修、检讨及进士出身的京官。乡试同考官自乾隆后,专用在本省服官科甲出身的州县官。
④加五级记录十次:清代对官员的议叙(奖励)有三种方式:一是记录,又分三等,记录一次为一等,其余类推。二是加级,也有三等。从加一级、二级直至三级。把记录和加级合在一起,又分十二个等级:第一等,记录一次;第二等,记录二次;第三等,记录三次;第四等,加一级;第五等,加一级记录一次;第六等,加一级记录二次;第七等,加一级记录三次;第八等,加二级;第九等,加二级记录一次;第十等,加二级记录二次;第十一等,加二级记录三次;第十二等,加三级;其余类推。三是即升,就是升官。一旦即升,俸禄就随之增加,顶戴也会随之改变,官职也会随之提高,但要得到皇帝批准。官员有过,受到罚俸或降级的处分。如果有记录或加级,可以用来抵消处分。文中可以看出,当时郏县知县资历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