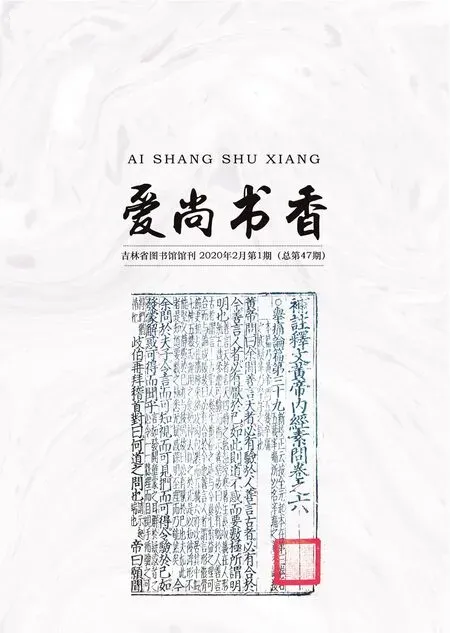翻译家查良铮的诗路历程
石 华
查良铮(1918-1977),又名穆旦,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曾用笔名梁真,是清代著名诗人査慎行的后裔,也是九叶派诗人的主要代表。穆旦少年时便展露诗才,曾写下《哀国难》这样的诗篇,愤怒控诉日寇铁蹄蹂躏中华的累累罪行。1935年,他入读清华大学外文系,继续探索和写作诗歌。据同学王佐良回忆,穆旦爱诗,他的诗歌散发着雪莱式的浪漫抒情气质。后到昆明,发表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等作品,他的诗风转入现实主义,语言渐趋硬朗,成为著名的青年诗人。
大学时代的穆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深受左翼文化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炽热的爱国情怀。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作为诗人的穆旦命运也经历了悲怆的转折。为了与英美盟军合作开辟印缅战场,他投笔从戎,作为第一陆军副司令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的翻译,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可是由于盟军协助不好且指挥不力,在激烈的对战之后,盟军溃败,各支军队仓皇撤退,穆旦一部陷入崇山峻岭之间,与淫雨疠疫、遍野尸骨为伴,惨绝人寰,九死一生。王佐良在《中国的一个新诗人》中有这样一段讲述曾被广泛引用:“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沉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这段惨烈经历给穆旦的心灵造成强烈的震撼,在他的经典名篇《森里之魅》,副标题为《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中,他写道:“……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身心……”。
穆旦常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天赋异禀的诗人,他却又如何走上翻译的道路,以翻译家查良铮的身份广为人知的呢?
1937中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撤出北平,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抵达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南岳的衡山圣诗学院重新开课。后来,随着南京失陷,日军紧逼武汉、长沙,临时大学只好从衡山湘水再迁云南昆明。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长途跋涉68天,3000多里,才到达昆明。“长征”路上,他竟然学习不辍,背完了一本英汉词典。在昆明,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建,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这里有众多中国诗歌史上的精英人物,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等,也有袁可嘉、郑敏、王佐良等青年爱诗者,他们一起探讨中外诗艺、切磋交流。当时,他还选读吴宓教的《欧洲文学史》和威廉·燕卜荪教的《莎士比亚》和《英国诗》等课程。威廉·燕卜荪,这位来自英国的讲师,给穆旦以很大的影响和启示,穆旦英诗文论的领路人中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位英国诗人。在西南联大两年期间,燕卜荪独特的教学方式和人格魅力,无疑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到穆旦及其同学,塑造了一大批现代诗人,使西南联大成了打造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基地。燕卜荪毕业于剑桥大学,从数学专业转至文学专业,曾师从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瑞恰慈,写出《复义七型》这部经典著作,开创了“细读”批评典范。当时,燕卜荪给二年级外语专业讲授《英国诗》,从史文朋、霍普金斯开始,一直讲到三十年代的奥登,引介了当时英国文学史上主要的现代主义诗人。此外,他还在1937-1938年主讲《英国散文及作文》,以及四年级专业必修课《莎士比亚》。王佐良回忆说:“燕卜荪是位奇才……他的那门《当代英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情、实况,加上他对语言的精细分析。”在当时的西南联大,生活艰苦,教学条件极端匮乏,没有现成的教材,燕卜荪用他的便携式打字机凭记忆打出戏剧与诗歌作品,他对英语文学的稔熟程度令学生敬佩不已。总的说来,诗人燕卜荪对穆旦的诗学影响可追溯至题材、思维范式、表现手法上,如题材中的现实主义内容,玄学的思辨方式,朦胧手法的运用,在两人的诗歌中都能找到连接点与契合处。
穆旦在联大接触的西方诗歌与文论,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他的语言和风格都折射出西方诗歌的影子,而他的语言才能又是得天独厚的,是一个成功的诗歌翻译家的必备条件。1948年,穆旦漂洋过海,赴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国文学,同时选读俄语和俄语文学。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汇集了一批来自中国的优秀留学生,其中有理科的李政道、杨振宁、周与良(后为穆旦妻子),文科的邹谨、卢懿庄、周珏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穆旦在邮局打夜工,搬运邮件,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1952年,穆旦夫妇放弃在国外工作的机会,力排周围朋友的劝阻,踏上归国的旅程。 之后,在南开大学外国文学系工作,陆续翻译出俄语文论,如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和《怎样分析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文学作品。他先后译出普希金的抒情诗500余首、叙事诗10首,从《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到《叶普盖尼奥涅金》。此后,他转入英国浪漫主义,拜伦、雪莱、济慈各有诗选译集。他的译名渐以查良铮而广为传播。回国后的查良铮放弃大规模诗歌创作,却从事了翻译活动,背后当然有其政治原因。“……现代派诗歌在建国后的文学格局中没有栖身之地,政治意识形态对其深恶痛绝,将其隔绝在译介推广的藩篱之外,因此,主流话语对现代派诗歌译介和创作的代表人物穆旦采取了有意忘却的策略,虽然穆旦主动归国,但起先几年,在中国新诗创作史上仍尽量去除他的一切身影。”尽管他有意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译介了许多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1957年,他的诗《葬歌》和《九十九家争鸣记》仍被批为“毒草”,“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穆旦失去了创作的自由。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他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收审,开除公职,处以三年劳改徒刑。从此以后直到1977年去世为止,大约二十年时间,其作品、翻译、研究论文等被禁止公开发表。劳改期满获释,降级降薪,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但他每天回家以后,仍伏案埋头于翻译工作,尽管他知道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拜伦的诗《唐璜》的翻译是从这时开始的。穆旦醉心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也曾专心研读艾略特、奥登等人的现代诗歌,但他的翻译作品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莫过于拜伦的《唐璜》。拜伦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影响都很广泛,许多文豪,如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等,都曾表达过对拜伦的敬仰。在中国,拜伦也以“拜伦式英雄”而闻名,他多首诗歌曾被不同翻译家反复翻译,仿佛成了一决高下的标杆。长篇叙事诗《唐璜》结构宏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是拜伦最著名的代表作。全诗充满悲壮、幽默、讽刺、挽歌的音调,夹杂着政治的议论、田园诗式的爱情;全诗结构松散,叙述人时而写景状物、时而嬉笑怒骂、时而抒情怀旧,用口语体对当时的保守派、正统派加以嘲讽。可想而知,这样一首长诗,要准确传递内容信息、要表现拜伦时而庄严文雅、时而诙谐俏皮的语体,这对翻译者将是多么严峻的挑战。更何况,译者身处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的手稿或被抄走或焚烧,六口人被赶到一间十七平方米的小屋居住,家贫如洗。穆旦被押往天津郊区大苏庄农场强制劳动,每周只准回家一次。1971年,强制劳动解除,穆旦得以重返南开大学图书馆,每晚与儿子住在学生宿舍楼一间十平方米的宿舍里。他每天除了在图书馆工作八小时外,还被罚以其它劳动,很晚才能回家。在家里吃过饭后,又骑车返回学生宿舍,伏在黑木饭桌上,在昏暗烛光下,一直翻译到深夜。《唐璜》翻译始于1962年,1965年完成初稿,1972年经过三次修改,到1973年完成《唐璜》的翻译及注释时,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了。而这部浸透译者十年心酸的译稿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以,不妨说,作为“九叶派诗人”的穆旦在1958年就已经死亡,剩下的则是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在无法进行诗歌创作的情况下,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诗歌的译介,在翻译《唐璜》的过程中,查良铮变得更加成熟老练,促使他的诗歌语言也更加流畅,达到了无论是诗人还是翻译家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如果说对英美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热爱是成就著名翻译家查良铮的内部因素,那么极端的政治环境就是穆旦隐身,借翻译以容身的外部因素。诗人的隐身,翻译家的出现特别令人想到穆旦的长诗《隐现》:“白日是我们看见的,黑夜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看不见时间/未曾存在的出现了,出现的又已隐没……”这一隐一现之间投射出人间许多无奈,隐现似乎最能暗合他悲凉却丰富的人生。
王佐良在《穆旦:由来与归宿》中写道:“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能译《唐璜》的诗人才能写出《冬》那样的诗。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