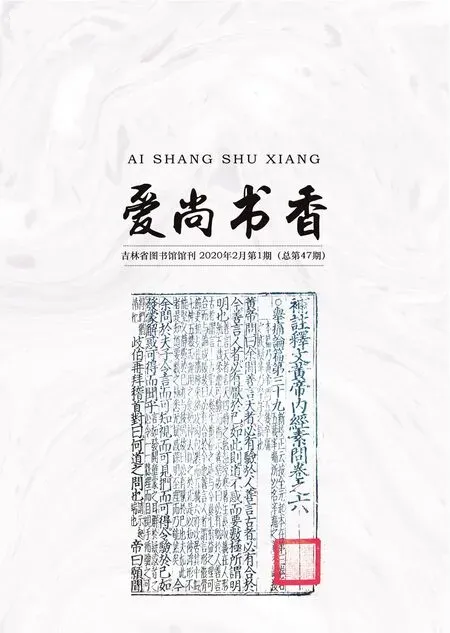约翰·缪尔:荒野的意义
马永波

在美国生态文学有“山约翰”之称的便是约翰·缪尔。他的巨大贡献在于给人类对荒蛮自然的激情、荒野的意义提供了直率的文学表达,而这些在美国文化讨论中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牵扯到环境,没有任何文学人物对美国政治与历史的现实起到过更大的影响。作为1892年山岭俱乐部的奠基人,缪尔在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他重要的环保立法也具有直接的影响。作为美国环境运动的奠基者,约翰·缪尔是最具有肯定力量的美国作家。在他的典型文章中,叙述者(缪尔本人)通过学习、冒险、困难或危险,朝向万物永恒联合的理解前进。自然的美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签名,人类领略野性之美的能力表明他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种“肯定”的哲学贯穿于缪尔的全部作品。
像爱默生、梭罗一样,缪尔也习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自然现场中的所见所感,他的日记是他写作的素材。他一生共记了六十本日记,他的日记非常随意。而他以日记形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山间夏日》,完全以日期为线索。
缪尔非常反对人类纯粹实用性地对待自然,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是生态文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山间夏日》6月7日的日记中,他批评了牧羊人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在6月13日的日记中,缪尔描绘了他长时间坐在高高的叶子下面,享受这野生叶子搭成的凉亭,“仅仅一片叶子铺展在头上,世间的烦恼就被赶走了,随之而来的是自由、美好和安静”。无论怎样坚硬的心,都难免要被这些神圣的蕨类植物打动。然而,在这么可爱的时刻,他发现牧羊人经过一片最美的蕨类植物时,竟然没流露出比他的羊更多的感动。而当他问牧羊人会把这些庄严的蕨类植物想象成什么,他得到的回答就是,“啊,它们不过是大——大刹车闸。”意思就是能让羊群一下子停住,贪婪啃吃的食物。
要想破除人类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通病,首先就要认识到万物依存的道理,正如缪尔所言,“当我们试图把任何一个事物单独摘出来,我们发现它与周围的事物密不可分。”混沌理论告诉我们,所有事物最终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甚至要真正深入理解澳大利亚白蚁肠子中的一种原生动物,也需要理解它整个的演化史及其所处环境的整个动态。而对我们人类自身也是如此,要全面了解自身,实际上需要弄清整个宇宙。我们越是试图查明自己,我们碰到的外在于自我的非线性的复杂关联就越多。因此,我们对他人的认识,亦只能图方便地简化、类型化,从而剥夺了对象的微妙变化和个性。
人类也不过是万物交织而成的生态整体网络中的一员,他绝不处于进化的最高梯级。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幻的优越心理,导致了人对其他物种的不平等对待。可事实上,如果不仅仅以人类智慧为唯一判断标准来认定“智慧”,我们就会在自然界许多物种身上发现智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人类。承认自然中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就是承认其他物种的存在有着不以人类利益为转移的、自身具足的目的。
古语云,天予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予天。人不但不能为“天”(自然)增加什么,反而因为欲望的无限膨胀成了最让自然母亲伤心的不孝子,甚至是最大的敌人。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类制造垃圾的惊人能力,对环境的污染,都大大超过其他物种。大自然“把百合的美艳分送给天使和人类,熊和松鼠,狼和羊,鸟和蜜蜂,但是,至此我看见只有人和他驯养的动物们破坏这些花园。堂告诉我,在炎热的天气里,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熊喜欢在百合丛中打滚,蹄子尖尖的鹿在散步或觅食的时候,也会一次又一次穿过花园,然而我发现,没有一棵百合受到熊和鹿的践踏。恰恰相反,鹿似乎像园丁一样侍弄着它们,把土压实或者在地上挖坑,而这刚好是百合所需要的。无论怎样,没有一片叶子或花瓣被它们弄乱”(7月9日)。人不但是制造污染的专家,本身也是最容易弄脏的动物,而其他动物在保持自身洁净方面却有着人所不能的诸多巧妙。缪尔写道:“7月7日/似乎只有人类是唯一容易被食物弄脏的动物,因而制造出大量需要洗涤的用品、像防护罩似的围兜和餐巾纸。相比之下,生活在大地里的鼹鼠们,靠吃黏糊糊的蠕虫为生,却像海豹或鱼一样干净,它们洁净的生命是一种永久性的洗涤。而且我们发现,在这些含树脂的森林里生活的松鼠,它们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纯净;你看不见它们身上有一根毛发是黏糊糊的,即使它们接触过有油脂的松果,而且显然是无所顾忌地到处爬来爬去。鸟类也非常干净,尽管它们似乎总是煞有介事地洗澡,清洁身上的羽毛。”
粗犷严酷的荒野,在缪尔的写作中有突出的体现。他的真正家园是荒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山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在山区的勘探上,他认为每一堂荒野的课程都是充满了爱的课程。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也并未感觉到孤单,“正相反,我完全不需要更多人的陪伴。因为整个荒野似乎是有生命的、为我所熟悉的、充满人情味的邻居。那些真正的石头似乎是健谈的、热情而亲切的,当我们想到我们共有同一个自然之父和自然之母时,这些石头就是我们的兄弟。”(8月30日)当夜色深沉,安静的宿营地里,虚弱、疲惫的人们都已入眠。缪尔会独对星空,遗憾于人们在这宇宙永恒而美好的运行中睡去,却不能像星星一样永远凝视天地间的万物。
于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去了内华达山脉,离开了人工的环境,被基本上是非自我主义的自然所环绕,他的智慧开花了。他意识中非历史的、整体主义的、直觉的和伦理的一边就位了。有趣的是,这种意识开放的最初的实在结果,是一本日记的写作。传统上,写作和语言是与“左脑”、与意识的线性模式相联的。当然,缪尔经常抱怨词语,它们排列在书里,无法复制出山峦的全部荣耀。“我发现文学事业非常令人厌烦,”他在1873年曾这样说过,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种困难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对书的看法很差,认为它们仅仅是一堆石头,堆起来向未来的旅行者显示其他人的思想在哪里,卡德摩斯和其他的文字发明者得到的尊重超过了应得的一千倍。多少文字都无法让一个灵魂了解这些山峦。尽管对文字如此怀疑,缪尔最好的作品依然表达了两种主要的意识模式的综合。尽管受限于英语的线性形式,他的句子依然能够传达出自然非线性的丰富。
缪尔最成功的一些意象似乎是从简单的感觉中涌现的,它们仅仅被“报告”出来。它们强调运动中的自然万物,没有进行第二级的形容词或状语的修饰。这些意象使分类前的感知时刻戏剧化了,具有激发经验本身而不是描述和判断的效果。经验所发生的情境因此具有了持续发现和展开的感觉。读者与缪尔同在,分享未加修饰的感觉。在后期,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和公众人物,缪尔的生活离他的野性自然经验有一定距离了,他努力消除他写成的作品中的形容词。这种修正过程可以理解为他试图重新捕捉在源头存在的感觉。毫不意外,日记往往能记录相对来说未加渲染的时刻。一种朴素而直接的叙述能与伦理内容产生共鸣,对精确的追求使得作家尊重眼前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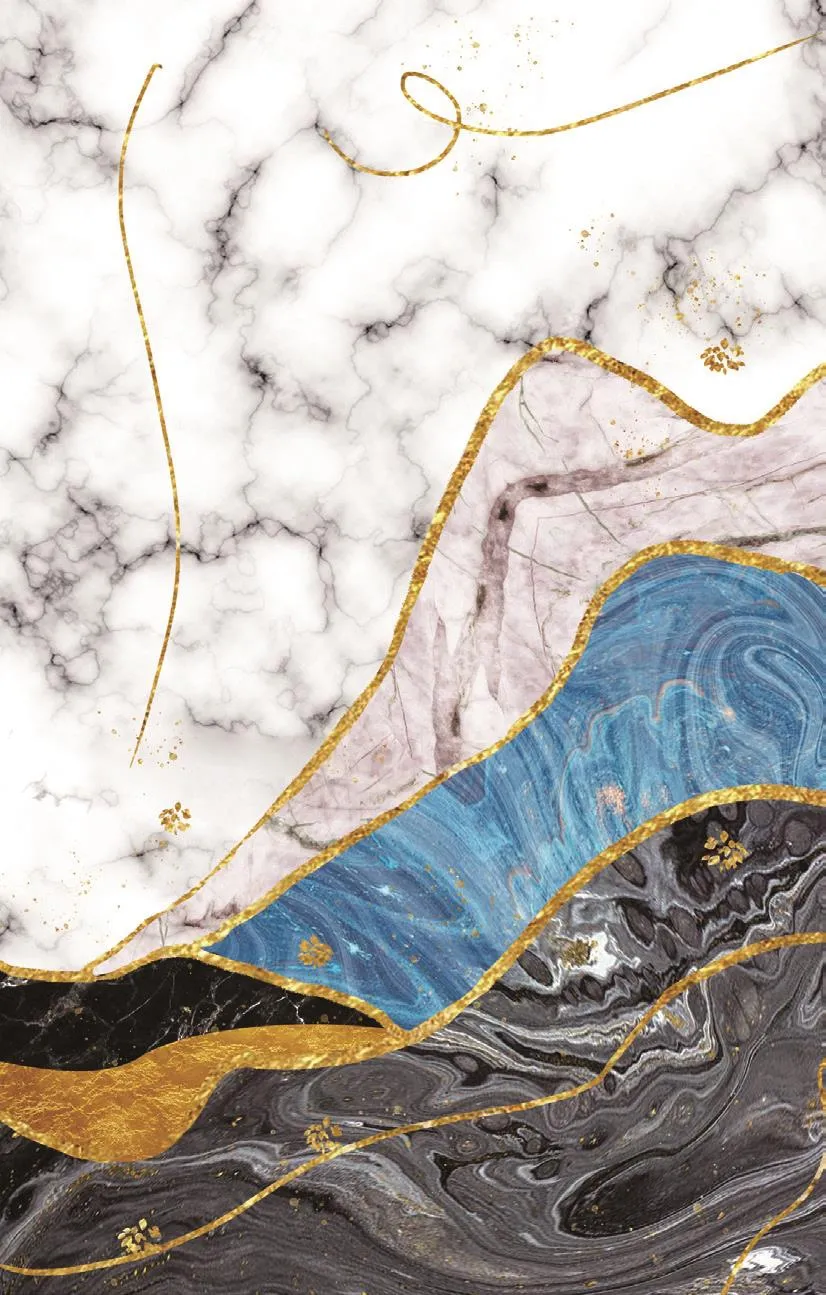
在缪尔的写作中,意象和运动远比静态的风景要典型和紧迫。这种意识似乎是内在于他对自然生动鲜活性质的敏感。他并不简单地将自然看成一个静态对象的集合。他的思想显然是不受约束的,它参与着野性自然的运动和生机。作为读者,我们对缪尔与其周遭事物的动态关联的反应,就和对他独特主题的反应一样,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被更新了。重新获得感觉和经验可能是当代生态写作的主要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