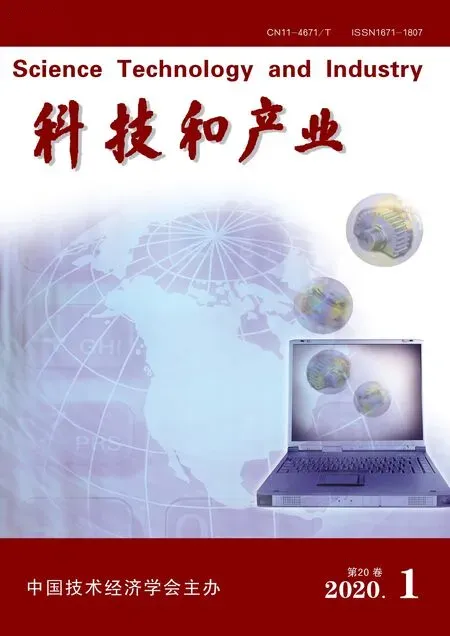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徐 云
(三峡大学, 湖北 宜昌 443002)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来规范企业的环保行为,来维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绩效之间的平衡[1]。但是在企业看来,环境规制压力构成了企业的一项财务负担,具有负外部性的环境污染治理如果由企业自身承担,企业须从生产正常的生产运营中抽掉资金采购环境保护设备,研发环境保护的新技术,以及替换环保型生产材料,减少了企业正常投资运营的资金量,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收益水平[2],这让企业的高管和企业实际控股的大股东缺乏主动投入环保的热情[3]。因此,来自政府部门的环保要求,成为企业从事环保投入的主要驱动力[4]。
同时,从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落实到企业的环保行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5],高管的决策是在不同选择间对自身利益考量后做出的决定,以使高管自身获得最大利益,环境规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具有内在联系[6]。具体而言,高管面对来自政府的强制性环保主张,企业会根据业务特点、产品内容、财务实力和企业规模等具体情况[7],同时还会根据来自大股东诉求和高管层的利益诉求[8],选择环境保护行为的方式与环保投入的数量。因此,本文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的同时,探讨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之间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检验了高管激励与环境规制的协同强化作用;二是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下,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环保投入显著,但环境规制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下变得不再显著,说明在本文研究年限里,来自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承担者来自于国有企业,为政府环保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环境规制作为约束企业环保行为的制度,会对企业形成较强的约束力并影响到企业的行为[9],企业出于合法性目的,企业会从事环保投入,来减少的环境污染水平,来达到政府的环境保护指标,和媒体大众与投资人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从而减少来自政府环保部门环境监察频次,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10];另一方面,不参与环保投入的企业,在环境保护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就会成为政府和媒体公众重点关注的对象,会受到公众和投资者的抵制[11],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然而,环境规制存在着最优水平,当环境规制强度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的环境保护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的提高,企业的环保投入反而会出现减少的情况[12—13]。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存在着倒“U”型关系。
1.2 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
企业高管作为企业所有决定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高管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起着关键作用[6],对高管激励的水平会影响到企业高管面对环境规制时的决策与行为[14]。环境绩效表现较差的企业会受到政府和媒体公众的特别“关照”,政府的环保部门会频繁光顾检查,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也会受到目标客户的抵制与竞争者的攻击,这种负面影响会波及到企业的经济绩效与市值,最终,高管自身的职场声誉,以及高管的薪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环境保护已经深入人心的环境下,理性的企业管理层会将环保投入纳入到经营决策中。获得的薪酬激励越高,越在乎自身的社会形象的高管,会倾向于经营环境的稳定,不愿意冒环境违规的风险,给自己带来潜在损失[5]。据此,提出假设:
H2a:高管薪酬能促进企业对环保的投入。
H2b:高管在职消费能促进企业环保的投入。
H2c:高管持股比例能促进企业环保的投入。
H2d:高管激励能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
1.3 企业性质与企业环保投入
在我国的市场体系中,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持政府财政税收、稳定市场和增加就业等社会责任,也是政府各项政策的直接先行者.在环保方面,国有企业的环保行为会成为市场环境规制政策的指示器[15]。同时,政府充当控股股东的国有企业,在企业经营中的各方面都会受到优先照顾,会优先获得银行的贷款,经营财务绩效也是软约束指标,也会因国家资本信誉的背书而获得大众与投资者的信任[16],因此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拥有更稳定的财务支撑,环境规制下国有企业会有更大的环保投入。据此,提出假设:
H3:相对于民营企业,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作用更强。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定义与测量
企业环保投入VEPE。本文将VEPE设置为虚拟变量,企业有环保投入记为1,否则记为0。其中有无环保投入的依据是先将企业所披露的所有与环保有关的环保投入数据汇总,包括以环保投资、环保运行费用、环保税、排污费、绿化费等词条披露的环保支出汇总。取虚拟变量是因为上市公司中披露了环保投入信息的企业很少,如果排除这些买有披露环保信息的企业数据,会造成样本量的不足,造成估计误差,同时会造成样本选择性误差,随时了样本的随机性。
环境规制强度ER。本文在参考沈坤荣等[17]对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废水处理率、一般固体废物利用率和危险固体废物利用率两个指标,采用加权线性和法,合成ER指标。
高管激励。高管激励变量本文用高管薪酬的对数lnDTR、高管在职消费对数lnEDC与高管持股比例ESR三个指标表示。其中,lnDTR用的前三位高管的薪酬加总求得;lnEDC参照陈东华[18]的做法,将企业财务报表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和会议费等8项管理费用的总和表示,ESR比例用的是前三名董事、前三名监事、前三名高管所持有的企业股份的总和占企业总股数的比值表示。文中将lnEDC纳入模型中,是因为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受到了“限薪令”的约束,在职消费扮演着“隐性薪酬激励“的作用[19]。
企业产权性质。借鉴多数学者的处理方法,将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归为一类,记为SOE,是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将民营企业作为一类,记为PE:是民营企业记为1,其他企业为0;其他变量设置的具体情况汇总见表1。
2.2 模型设定
1)为检验假设H1,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模型中引入ER的平方项,与ER一次项同时引入模型回归,构建模型(1)如下:

(1)
2)为检验假设H2a、H2b与H2c,高管激励能促进企业的环保投入,本文构建模型(2):
VEPEit=δ0+δ1EXEit+∑2δicontrolsit+μi+εit
(2)
3)为检验假设H2d,高管激励能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本文构建模型(3):

(3)
4)为检验假设H3,相对于民营企业,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将在模型(1)、(2)、(3)的基础上将数据按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类回归。
2.3 样本选取和来源
本文以环保部强制要求披露环保信息的16类重污染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范围,筛选出2012—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中符合企业行业条件的企业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以下操作:①剔除了2016年以后上市的企业中数据不完整的企业数据;②剔除了股票名称前带有S、ST、SST 与*ST的企业的数据;③因为环保数据的缺失,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上市企业的数据。最终得到2 850条记录进入本文的研究。本文数据通过Excel2016与stata15进行预处理和回归分析。

表1 变量定义表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①上市公司的环保投入数据来自于笔者从企业披露的环保信息中摘录而得,这些披露信息包含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与可持续发展报告,这些信息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巨潮资讯网以及企业官方网站;②污染物排放处理数据来源于SPE数据平台的《中国环境数据库》,为补充该平台部分数据指标的缺失,笔者同时补充了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③本文运用到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与国泰安数据库。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环保投入VEP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235 6与0.424 6,样本中有环保投入的企业占比为23.58%,标准差大于平均值与中位数,表明企业环的保投入分布较为分散;环境规制强度ER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有较大差距,说明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有显著差异;高管薪酬对数lnDTR与高管在职消费对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比较小,均值与中位数一致,但是高管持股比例ESR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异巨大,说明以高管持股作为激励高管的方式,在我国并不普遍;2 850条数据中,国有企业占了43.33%,民营企业占比为48.66%,占比相差不大。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 将环保投入按照是否为国企分类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环保投入VEPE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在表3中,国有企业的均值为0.253,非国有企业的均值为0.222,企业有环保投入的比例近似。在非国有企业中,民营企业均值为0.211,集体企业、公共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均值为0.294,在污染上市企业中,非国营与民营企业的其他企业的环保投入比例显得更高一些。

表3 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环保投资差异分组描述
3.3 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展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变量间相关性系数均小于0.5,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无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Pearson检验的结果看,环境规制强度ER与企业环保投入VEPE之间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关系,高管在职消费对数lnEDC与企业环保投入VEPE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相关关系,假设H1与假设H2b得到了部分验证。
3.4 多元回归检验分析
3.4.1 全样本回归分析
表5展示的是全样本logit回归分析结果,第1列展示的结果是环境规制和控制变量对企业环保投入的逻辑回归,第2列展示的是高管激励和控制变量与企业环保投入的逻辑回归,第3列展示的是环境规制、高管激励和控制变量一起逻辑回归的结果。因模型引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为避免带来严重多重共线问题,文中对二次项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

表4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0.01、0.05与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先分析表5第1列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强度的一次项系数为0.92,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系数为-0.16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证明了假设H1,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第2列中,高管薪酬对数对企业环保投入的系数为-0.34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假设H2a相反;高管在职消费对数对企业环保投入的系数为0.0843,且在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假设H2b得以证明;但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不显著,假设H2c未得到证明。高管薪酬的对数的系数为负,可能我国高管薪酬普遍较低,高管薪酬充当着高管层”基本生活收入保障“的角色,高管层认为环保投入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到自己的薪酬收入[5],但企业的环保行为,需要企业从事一系列采购、招聘与培训活动,这些获得能够给企业高管很大的在职消费空间,能够获得更多的隐性津贴。第3列中,因为回归方程有高管激励的加入,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的系数分别从0.920和-0.162变为0.956和-0.168,系数分别增大了4.9%和3.7%,p值分别从0.003与0.017变为0.002与0.013,p值减小了33%和23%,足以说明高管激励加入模型,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系数变得更加显著,说明高管激励能够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H2b得以证明。
再分析3个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中的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出口业务与企业股权结果都高度显著,其中企业规模、企业出口业务的系数为正数,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和企业有出口业务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入,同时出口业务的存在,企业有机会接触到发达国家的环保制度,学习到外国企业的环保经验[20],最早开始通过国外的环保认证体系的认证,所以面对环境规制,企业早有预期,因而更乐意增加环保投入[21];企业年龄与企业股权结果系数为负:企业的年龄越长,表明企业越具有财力,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越好,也会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重点政策保护对象,在环境规制政策没有系统化,环境保护没有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硬指标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对大企业排污采取默许行为[22];企业股权集中度体现着企业受大股东意志影响的程度,该指标越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在企业中得以强化,在国家的环保行为还没用形成完整的法律约束力,以及政府官员没有被强制执行环保政策的时候,环保投入是一笔很大的财务支出,会损失股东的利益而遭到大股东的消极对待[23]。而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企业销售利润率、运营能力的资金周转率、偿债能力的权益系数和成长性能力的托宾Q值与企业环保投入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从总体情况看,市场上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的财务指标的联系不大,参与环保多是出于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考虑,免于被政府和媒体公众的关注而受到潜在损失。

表5 二值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0.001、0.01与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型标准误。
3.4.2 分类样本回归
表6反映的是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的结果,因为样本中除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外,剩下的诸如公共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与校办企业,仅仅只有228个数据,样本量太少,故本文遵照学者的一般处理方法,将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与分国有企业两类。表6展示的第1列是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回归的结果,第2列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回归的结果,第3列展示的是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回归结果,第4列展示的是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回归结果,第5列展示的是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高管薪酬一个模型回归的结果,第6列展示的是非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高管薪酬一个模型回归的结果。
比较表6的第1列和第2列,在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依旧显著,但是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不再显著,这一结论部分的论证了假设H3,同时也说明了在样本分析年份内,国家环保政策的压力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因为大股东和高管层对环保的消极对待,环保投入在统计回归中并不显著[15]。控制变量中,国有企业中的企业规模、年龄、出口业务、股权结构依旧对环保投入显著,但是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从侧面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多来自于国家环保规定的政策性承担[16];非国有企业中,企业销售利润率变得显著,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会使非国有企业采取环保投入行为的一个考量因素;第3与第4列高管激励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回归中,非国有企业中的高管薪酬对数对企业环保投入不再显著,高管在职消费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性从0.1%下降到5%,而国有企业中高管激励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基本不变,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受到外部政策性监管的约束,但高管会以环保行为大开在职消费之门,获得隐性薪酬[24];但是,因为非国有企业股东对高管约束更强,薪酬与在职消费的激励明显逊色于股东的约束。控制变量中,企业销售利润率在非国有企业中以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说明在环境规制政策性要求外,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依据还来自于企业当期的利润水平部分决定。在表6的第5列与第6列的分企业产权性质环境规制强度与高管薪酬共同对企业环保的回归中,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强度的显著性变弱,非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显著性依旧不高;高管薪酬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都不再显著,说明在分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影响之后,高管薪酬对高管从事环保行为变得不再起激励作用;控制变量中,股权结构不再显著,资金周转率开始在国有企业中显著;除销售利润率外,托宾Q值也开始在非国有企业中变得显著。部分原因来自于,离开了国企环境保护的政策性承担拉高了整个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分开回归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对高管从事环保行为的作用不再有效,企业从事环保行为除环境规制的强制性约束外,民营企业会根据企业的当期财力来决定。

表6 以企业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0.001、0.01与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型标准误。
3.5 稳健型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以下稳健性检验:①为验证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借鉴张中元和赵国庆[25]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采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SO2)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INW),用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这一指标,代替模型中企业环保投入这一虚拟变量;②为验证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用企业环保投入对数这一绝对数值代替模型中企业环保投入的虚拟变量。稳健性检验得出与前面一致的结果,可以证明本文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环境规制强度和高管激励作为解释变量,以企业环保投入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加入按企业产权性质为分类标准的分类回归。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采取环保行为的企业占比还比较低,企业的环保行为具有很强的个体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具有倒“U”型关系,高管激励能够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加强企业采取环保投入的可能性;企业规模和出口业务对企业环保投具有正向作用,企业年龄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进行环保投入产生具有负向作用。分类回归后发现,环境规制仅对国有企业显著,环境规制在没有形成系统性约束法规之前,国有企业成了环境规制政策的主要承担者,而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是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财务情况综合做出的结果。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总结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紧环保立法,尽快形成环保领域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政府环保执法的同时,也为企业对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稳定的预期,促进企业主动从事环保行为;第二,加大政府的环保执法力度,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落地环保政策,将环境状况纳入到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体系中;第三,环境规制措施应充分关注企业环保投入的临界点,考虑地方实际环境和企业现实状况,为企业提供多项环保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