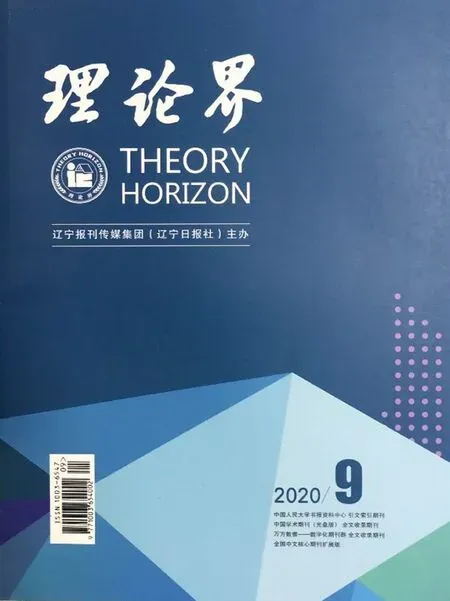容纳情感:玛莎·纳斯鲍姆的美善生活观
左 稀
玛莎·克拉文·纳斯鲍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兼职神学院、哲学系和古典学系,古典学训练出身,研究贯通古典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情感哲学、法律哲学、刑法理论、教育理论等等,擅于运用古典学资源解决在哲学、法律、教育等领域中凸显的现代性问题。在情感问题上,纳斯鲍姆持有一种认知主义观点,认为情感本身包含认知性内容,绝大部分典型的情感类型都关联于确定的评价性判断,因而人们可以据此对情感状态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此外,人们对情感的态度常常与他们信守的好生活观密切相关,由此可大致划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善的人类生活必须是绝对自足的,它应当完全处于个体掌控的范围之内,无需遭受外在运气的任何影响,在采取这种策略的同时,人类情感通常成为被彻底根除的对象。犬儒学派和斯多亚派是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善的人类生活即便不是绝对自足的,也应在极大程度上体现某种自足性,这种自足性会使得人类生活基本处于个体掌控之下,外在运气不会对其构成实质性影响,为此,人类应抑制自己的情感以获取最大程度的自足。柏拉图是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第三种观点并不否认,人类对好生活的追寻从来都是以某种自足性为其目标的,但这种观点同时强调好生活始终具有脆弱性。这意味着,美善的人类生活无法从根本上免除运气的干扰。不过,正是脆弱性的存在使得这种生活成其为属人的生活,并呈现出人类生活的美好与价值。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玛莎·纳斯鲍姆)往往认为,情感是包含多元价值的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人类实践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迷恋绝对自足的生活
1.自足源于有德性的状态
公元前5 世纪,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便提出,美德是唯一的善、自足的善。除了美德以外,其他都是恶。美德与幸福是一致的,有美德的人便能自满自足,无所欲求。这种观点在斯多亚派那里得到长足发展,这个学派认为美德对于一种美善的人类生活而言是充分的,除此之外,任何事物本身都无所谓善恶,只不过是非道德领域的价值中立物。美德的获得与保存均无需外在善的参与,因为美德就是按照人的理性的本性来生活,而一个人是否遵循理性的指引过一种有道德的、圆满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道德意志。一个人可以很穷,可以一无所有,但他却可以拥有高尚的道德,即便他完全没有实践这种道德的可能;你可以把我流放、关进监狱,甚至砍下我的头,但你不可能扰乱我宁静而高贵的灵魂。我的幸福是由我做主的,确切地说,是由我那无论如何都不被任何外在的痛苦和灾难所击溃的心灵状态说了算。总之,自由意志本身足以确保有德性的生活,从而也保障了自足的、圆满的生活。
2.根除情感
斯多亚派认为,为了追求道德卓越与自足生活,人们应当根除一切情感。尽管情感包含评价性判断,但这些判断都是虚假的,它们不正确地赋予外在事物以重要价值。事实上,诸如生命、健康、快乐、美貌、强壮、财富、声誉等外在善,既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幸福的构成部分,它们只是非道德领域的价值中立物,不具有任何内在价值,只有美德才出于自身之故值得被追求。当然,将这些外在善视为价值中立的,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值得追求。斯多亚派主张将价值中立物区分为“受偏爱的”和“不受偏爱的”。长远来看,受偏爱的价值中立物确实具有某种“选择性价值”或“谋划性价值”,因此,我们仍有理由去追求诸如饮食、健康这类事物。就当前状态而言,享有或丧失某种价值中立物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需待之以“冷漠”。无论我们对价值中立物采取何种态度,“情感”都不是一种正确的心理动机。激发我们追求受偏爱的价值中立物的动机是“选取”,促使我们躲避不受偏爱的价值中立物的动机是“不选取”。总之,承认外在善之价值的情感不仅给人树立不恰当的生活目标,而且使人面临丧失个人完整性的危险。(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来说,“善是一个人属己的、不易被拿走的东西”( 《尼各马可伦理学》1095b26),〔1〕可一旦承认外在善的价值,维护情感生活的重要性,一个人就相当于承认作为他自身核心的人格可能遭遇外界环境的入侵和控制,个体尊严和完整性便由此受到威胁。)有鉴于此,寻求道德卓越与圆满生活的人必须坚决根除一切情感。
首先,情感无法充当重要的行为动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会发怒,他也就不会自卫,而忍受侮辱或忍受对朋友的侮辱是一种奴性的表现”(《尼各马可伦理学》,1126a6-7)。〔1〕塞内卡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卫和保护他人的行为并不需要依靠愤怒这种动机,好人的行为是安全的、一贯的、可靠的、冷静的,它的可靠性来源于义务感。
其次,在推动行为方面,情感只具有负面效用。情感尤其容易导致强烈的痛苦和机体的激变,受制于它们的人通常觉得自己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中,完全丧失行动的动力。不唯如此,情感还具有过度倾向,具有一种摆脱理性控制的偏好,时常引发骚乱并走在理性的计划之前。〔2〕
最后,情感绝不是理性自制的行动者理应持有的正确的反应性感受。以同情为例,如果美德与幸福是一致的,且使得一个人幸福的原因完全掌握在这个人自己手中,那么他不幸的根源就只能从其自身中寻找。对待此种不幸,正确的反应是责备而不是同情。当然,一个有美德的、自足的斯多亚式好人可能表达一种仁慈的关切,但他会以家长式态度来看待他人的不幸,将抱怨苦难的人们看作是丢失玩具的孩童。〔3〕
二、沉迷高度自足的生活
1.自足源于沉思活动
犬儒学派和斯多亚派之所以将自足理解为一种有德性的“状态”,而不是“活动”,是为了排除运气对人类生活施加的影响。然而直觉告诉我们,不活动的人生算不上幸福的人生。柏拉图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相信好的、自足的生活应当在“人类活动”的意义上来谈论。不过,在他看来并非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都具有真正的价值。根据纳斯鲍姆的理解,柏拉图倾向于从以下三点来衡量活动的价值:第一,真正有价值的活动所涉对象必须具备一种“纯粹性”。第二,真正有价值的活动,其整个过程和所涉对象都必须具备一种“稳定性”。第三,真正有价值的活动必能指明“真理”,并且能够为万事万物提供充分恰当的说明,绝非一种似是而非的猜测。〔4〕在柏拉图那里,只有理念是自在和自为的实体,它们构成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并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我们的感官只能感知到不完善的、变动不居的个别事物,不能把握理念的意义,也无法理解完善且亘古不变的理念整体,只有思辨理性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了解理念体系的内在秩序和关联,从而指明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这般的真理。〔5〕这种运用思辨理性的活动就是哲学家说的沉思活动,由于满足“纯粹性”“稳定性”和“真理性”要求,它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
2.抑制激情和欲望
沉思生活是最纯粹、最稳定、最自足的生活,它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外在运气的干扰。不过,对沉思活动的干扰也可能来自灵魂内部,因为人的灵魂并不像神的灵魂那样纯粹,除了包含纯粹理性以外,它还具有激情和欲望的部分。如何摆脱激情和欲望的束缚,让理性占有伦理的至高地位呢?柏拉图告诉我们,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灵魂尽力回忆起原有的知识。这种回忆据说起始于一种“爱的迷狂”,要注意,柏拉图所理解的“爱”并非两性之爱,也非容纳个体分离性和独特性的爱。在这种癫狂的爱中,每一个独特的美的个体终将被视为单一的、普遍的美的理念的复制品,它们的异质性因理念本身的同质性而彻底消解。由于灵魂将这些美的个体看作千篇一律的东西,并相信它们可以相互比较和替换,那种通常与对特定个体的爱相伴随的紧张、忧虑、恐惧和同情将在极大程度上遭到抑制。柏拉图通过“爱的迷狂”说传授了一种抑制激情及欲望的方式——取消对象的独特性,这种方法不仅最大程度为理性思辨活动扫清障碍,同时也基本拔除了人类生活的脆弱性根源,使得一种好生活在最大意义上为个体自身所掌控。
三、接受美善生活的脆弱性
1.有德性的状态不足以使人幸福
在回答“哪些活动或价值是人类好生活的构成性要素”这一问题时,纳斯鲍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受益良多。她不同意犬儒——斯多亚派将有德性的状态与幸福等同起来的做法,并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点:幸福取决于实践活动而非有美德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行动得好和生活得好与幸福是同义的,而行动与生活都意指功能和活动。(《优台谟伦理学》1219b1)〔6〕他指出,“好状态说”可能导致一些直观上不可接受的后果。例如,认为一个自成年之后就开始一睡不醒、毫无作为的人具有良好品格且生活得好是反直觉的。换言之,具备一种优良的品格只是美德活动的准备,它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得到实现和繁荣,把这种活动性从中剥离会使得此种好状态变得毫无意义。反对者可能争辩说,“好状态”不是意识和活动完全停滞的状态,而是一种内在的思想活动状态。即便一个人受到奴役、监禁或折磨,只要他具有良好的品格,其认知机能与伦理意识依然存在,那么一种内在的思想活动状态足以使他像一个其活动从未受到妨碍的人那样,过上美善的人类生活。纳斯鲍姆辩护道,这种观点之所以被认为有道理,是因为人们把一个遭受折磨的人想象成具有某种复杂的内在生活的人。事实是,绝大部分经受折磨之人的内在活动会受到痛苦和剥夺的阻碍,人的思想、情感和反应均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外在的折磨和伤害很可能使它们无法达至完善。〔4〕
2.沉思活动的不充分性
在柏拉图那儿,只有沉思的活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至善”是通过沉思纯粹永恒的理念,超越一切现象和经验来实现的。在纳斯鲍姆看来,此种策略存在极大缺陷:如果一个人站在超越一切现象和经验的立场来评估何种因素构成一种好生活的根本性要素,那么他不可能捕捉到真实的人类生活。要真实地界定出好生活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就必须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现象”(phainomena)收集者。所谓“现象”,指的就是人类日常的信念和看法,它不仅不是与“真理”相对的东西,反而是人类获得一切真理的起点。〔4〕对任何存在者的好生活的说明都必须立足于那个存在者独有的生活和活动的本质要素,否则我们就不会把那种好生活看作是属于那个存在者的生活。因此,美善的人类生活必定是一件相对物种而论的事情,对真正和内在具有价值的东西的鉴定也必定是相对于人类语境的,并且不可避免地需要参考人们广泛持有的日常信念。那么,如何鉴定出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构成性意义的诸要素呢?纳斯鲍姆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借鉴亚里士多德有关人类功能的论证。〔7〕
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功能”(ergon)一词与“活动”(praxis)一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已然道明,对任何一个具有某种功能或活动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尼各马可伦理学》,1097b25-28)〔1〕亚氏这里所讲述的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功能或活动,而是对一个人而言具有本质性的功能或活动。关于这种活动是什么,他的分析如下:
生命活动也为植物所有,而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特殊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把生命的营养和生长活动放在一边。下一个是感觉的生命的活动。但是这似乎也为马、牛和一般动物所有。剩下的是那个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践的生命。(这个部分的逻各斯有两重意义:一是在它服从逻各斯的意义上有,另一则是在拥有并运用努斯的意义上有。)实践的生命又有两种意义,但我们把它理解为实现活动意义上的生命,这似乎是这个词较为恰当的意义。(《尼格马可伦理学》1098a1-8)〔1〕
从这段文字看,人类所特有的那种活动表现为灵魂遵循或包含理性的实现活动,即一种理性的实践的生命。那么何种生命形式会是理性的实践的生命呢?纳斯鲍姆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其含义的过程中反复运用“……的生命”(the life of E-ing;古希腊语表述为the-ikēzōē) 这类表达方式。她认为,对这种表达方式的理解有助于澄清“理性的实践的生命”的含义。她把亚里士多德研究者对“the life of E-ing”的解释归纳为两种。第一种解释方式是将它看成完整的生命的一个部分,这部分的生命就在于E-ing。按照这种理解,生长、营养的活动以及感觉的活动都只是隶属于一个完整复杂的生命的不同部分的活动,它们与人类最主要、最具特色的活动——理性的实践活动——是截然分离、毫无关联的,人类可以甚至应当抛开这些活动来寻求一种真正的、恰当的人类生活,即一种理性的实践的生命。第二种理解方式是将它看成一种围绕E-ing组织起来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E-ing构成最具独特性和引导性的特征,它赋予生命总体一种独特的形态。依据此种解释,一种E 形态的生命同样包含G 形态和H 形态,但决定这种生命属于E 形态而非G 形态或H形态的原因在于,E-ing 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此种独特生命的组织原则,其他构成性活动将围绕E-ing建立起来,E-ing也会渗入这些活动当中。也就是说,G-ing和H-ing是以E-ing的方式、遵循着E-ing来实现的。以此方式理解上段文字得出的结论是,理性的实践是人类生命最独特、最本质性的特征,一种理性的实践的生命同样包含生长和营养的生命以及感觉的生命,后两种生命会听从理性的指引,理性也会渗入它们之中,使它们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得以实现。
纳斯鲍姆采纳了第二种解释,并陈述了理由。首先,亚里士多德从未说过人类特有的活动就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活动,最准确的表述应当是“灵魂遵循或包含着理性的活动”。其次,第一种解释将颠覆我们对本质性的功能或活动的日常理解。以一位古筝演奏者的善来说,按照第一种解释,我们必须抛开她与其他乐器弹奏者所共享的那些活动,以及一般性的乐器弹奏技巧,仅仅关注于使她有别于其他乐器弹奏者的最独特的活动,如弹拨、压弦的活动。这看起来很是古怪,当我们判断一个古筝弹奏者是不是好的古筝弹奏者时,我们不只是看这个弹奏者弹拨是否到位,压弦够不够力度,而是关注整体的弹奏活动,即她如何通过弹拨、压弦的方式来展现一般性的乐器演奏技巧。这种看法更符合第二种解释模式。最后,第二种解释与亚里士多德后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试图开展的工作是融贯的。亚氏在后几卷中屡次谈到节制这种美德,他认为“节制与放纵是同人与动物都具有的、所以显得很奴性和兽性的快乐相关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118a25),〔1〕合于节制这种美德的活动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质言之,亚里士多德并不打算将生长和营养的生命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只要它以理性的方式来实现。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功能的论证表明了,除非一种生活首先隶属我们人类自己的生活,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好生活。既然属于我们的生活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理性的组织,在其中,生长和营养的活动以及感觉的活动同样得到理性的引导和渗透,那么人类幸福就必须在这类活动中寻求,而不是在无理性地耽溺肉体快乐的活动中,或无关理性的消化系统的活动中寻求。凭借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功能论证,纳斯鲍姆得以表明,一种美善的人类生活绝不仅仅取决于纯粹思辨理性的活动,容纳情感的实践理性的活动以及满足基本的生长及营养需求的活动都构成好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人们可以批评此种解释,认为它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因为从一些文本来看,亚里士多德似乎也得出沉思活动构成完善的幸福这一结论。(《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20-1177b33)〔1〕纳斯鲍姆并不为此忧心,她认为她只是在说自己想说的,如果那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想法,她完全可以借此批评亚里士多德。〔8〕
3.容纳情感
纳斯鲍姆认为,接受好生活的脆弱性便意味着容纳情感,因为有关人类生活脆弱性的认知往往通过情感来昭示。对情感的积极表态促使纳斯鲍姆对斯多亚派情感观展开全面的审查。她首先认为,我们不需要像斯多亚派那样,在外在善的评价上采取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立场。如果外在善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伦理理论本身是否存在便是可疑的。斯多亚派虽有意借“受偏爱的价值中立物”和“不受偏爱的价值中立物”之区分来解决上述问题,却始终不承认外在事物具有真正意义的道德价值。有些斯多亚主义者可能走得更远一点,他们会认可某些外在善的道德价值(比如,塞内卡就敦促奴隶主要尊重奴隶,并谴责对奴隶进行肉体折磨和性虐待的行为),并尝试用不同方案解释受偏爱的价值中立物与美德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思想家往往通过极其任意的方式决定哪些外在事物具有真正的价值,最终不得不倚重于自然目的论或神命论的思想。〔9〕其次,纯粹的敬重或义务感不足以推动一项道德行为,一些涉及情感与欲望的反应性感受是道德动机的构成部分;从道德价值的维度看,剥离主体反应性感受的道德价值也值得怀疑。〔2〕最后,斯多亚式好人所怀有的那种类似情感的仁慈关切并不具备现实性,如果施惠者不承认外在事物的内在价值,确保他人获得外在善的承诺就建立在十分脆弱的基础上,它会因为施惠者本人对价值中立物的感受而受限。甚至由于认识不到那些事物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对受惠者具有价值,施惠者根本满足不了受惠者的需求。〔10〕
当然,并非所有的斯多亚主义者都倾向于将享福之人描绘成毫无感受的冷漠无情之人。譬如,芝诺便允许斯多亚式“好人”怀有三种良好感受(eupatheiai)。然而,由于斯多亚式好人仅仅将善恶价值分别赋予美德与邪恶,因此,这些感受绝不等同于对外在事物赋予重要价值的情感。塞内卡曾在类比的意义上说,这种愉悦的产生就类似一个婴儿降生在母体内部,从未离开母体的子宫进入真正的外在世界,因此,它与欢欣、高兴这类现象毫无关联。与其这样说,“它是从兴奋和欢乐走向顽固的自恋;从惊奇和自发走向有计划的谨慎;从对分离性和外在世界的好奇走向在自身和属己物之中寻求安全感”。〔2〕
容纳情感并不意味着全面拥抱情感,斯多亚派反对情感的诸种理由也并非全无道理,情感确实具有不可控的一面。但正因如此,对情感的认知结构和叙事结构的分析才变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避免将情感视为纯粹生理性的冲动和力量,那么我们距离恰当应对甚至控制过度的情感就更近了一步。除此以外,承认好生活的脆弱性也并不意味着甘愿接受运气的支配。纳斯鲍姆确实期望人们能够在容纳情感、尊重价值丰富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种微妙的慎思,去寻求具有较高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善。这种慎思将确保我们不会过分脆弱,也不至过分自足。无论如何,敌视情感、拒绝承认善的脆弱性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它非但不利于真实地看待人类生活,反而使人陷入真正意义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