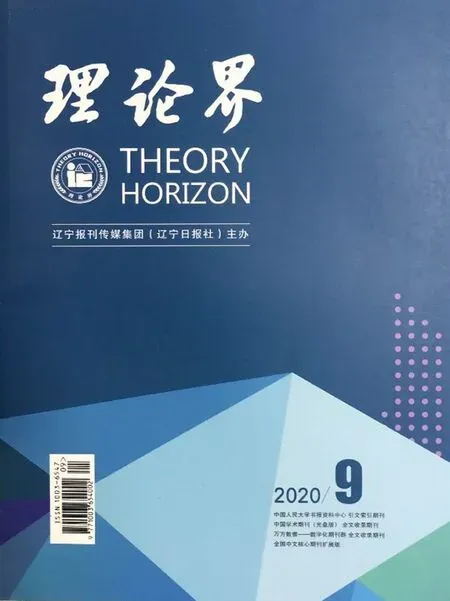老子、庄子死亡观比较研究
徐 文
在《老子》和《庄子》中,都有关于死亡的哲学问题的重要讨论。庄子阐述了诸多关于死亡问题的观点,其中既有对死亡的专门论述,也有在涉及死亡的其他议题中表达的对死亡的看法。老子也提出了很多涉及死亡问题的论述,但他较少单独讨论死亡,而是常常把死亡放在与其他问题的关联脉络中进行探讨。老子和庄子的这些论述,都表达了他们对死亡这一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死亡观既有相似性,也存在重要差异。这些差异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结构中有其成因,而且透显出老庄在基本的哲学观念上也隐含着深层差异。
一、老庄对待死亡的观念异同
无论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生而至于老,老而至于死,是自然过程中的必然。这表明他们对于死亡,在事实描述层面上具有相通观念。
老子认为,事物内部蕴含着否定性因素,事物只要不断向前发展,就会在超过一定程度后向其对立面转化,即“物壮则老”,〔1〕“兵强则灭,木强则折”,〔2〕“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据《列子》引老子)。这种趋势背后的总原则是:“反者道之动”〔4〕(此句中的“反”历来有两类解释,一是将其释为反面,意为转变到自身的反面;二是将其释为反方向,意为向本根的复归。在本文语境中是取前一种含义),即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会转变到自身的反面,这是道的运动方式的体现。人的生命同样也处在这一原则下,《老子》第五十章说: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5〕
人在生命过程中先处于出生后离生较近的阶段,之后经过壮年而逐渐衰老,进入不断趋近于死的阶段,“生长发育的过程占十分之三,衰老死亡的过程占十分之三”。〔6〕可见,老子认为生命向自身对立面即死亡的趋近是必然的过程。
类似地,庄子也认为,生与死都是命定的必然现象,《大宗师》中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7〕
庄子认为,死生的变化如同昼夜的变化,具有先天性的源头,是由超出经验世界之上的天所规定,人无法“与”于其中,即人的意志无法参与进这个过程中发生影响,因此,由生向死的变化具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必然性。可见,对于在超验的天或道规定之下死亡所具有的先天必然性,庄子和老子都有相似的体认。
虽然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死亡是不可逃避的必然现象,但他们对这不可逃避者的评价和思考却有显著的不同。
老子崇慕具有无限性的超卓的“道”,力求超越经验世界的种种有限性而趋向与道的境界的同一。而生命过程的有终,正是经验世界中的存在者与生俱来的有限性的典型体现,因此,老子认为死亡是一种意味着局限性和缺陷性的不可欲状态,从两个层面对之给予了负面的基本评价:
首先,在本体论层面,老子把对死亡的超越归于作为世界之本原的绝对者,从而在根本上赋予对死亡的超越以高价值,也即相当于赋予死亡以低价值。《老子》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8〕
谷神是不死之道的一种存在样态,司马光说:“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穷,故曰不死。”〔9〕它是化生万物的母体,故称为玄牝;天地也以之为本原,故称为天地根。谷神绵绵长存,无始无终,超越了死亡所体现的有限性而达到了没有起点与终点的无限。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经验世界中的有限存在者即人和万物的最终根源。老子将不死性归于绝对者,也就间接将有死性归于了经验世界中的存在者。通过将不死性和有死性分属于绝对本体和经验世界,老子就在本体论层面,将对死亡的超越放在了极高位置,而将死亡判为远低于道的状态。
其次,老子不但在本原性的绝对者与经验世界中的万有之间,将死亡作为一种属于后者而不属于前者的低价值状态;而且在经验世界的层面,还进一步将死亡与世间各种负面现象而非正面现象作紧密联结,体现出对死亡的负面性和不可欲性的凸显。《老子》中说:
强梁者不得其死。〔10〕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11〕
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12〕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13〕
强梁、坚强是与“弱者道之用”〔14〕相反的行为,“生生之厚”是对生的过度追求,勇、广、先是对慈、俭、后这“三宝”的舍弃。这些都是老子眼中与道相违的负面行为,老子将这些行为与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将招致比一般的死亡更痛苦的非正常之死(“不得其死”),或更易发生、更快到来的死亡(“死之徒”“动之死地”“死矣”)。这说明,老子把死亡看作经验世界中违背道的行为的惩罚性后果,是有限存在者可能遭受的状态中尤为负面的一种。
老子以上论述主要涉及经验世界层面个体行为的问题,而在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时,老子同样也将死亡与负面现象关联在一起,如: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5〕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16〕(据傅奕本)
前者描述了执政者将死亡用作威胁民众的手段,死亡成为了推行暴政的工具。后者指出死亡的常态化、轻率化是暴政的结果,因为当在上者为了满足自己各种生命欲望而对民众聚敛压榨时,民众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只能不再在意死亡,把死看得很轻。这两段论述,从不同侧面刻画了死亡与暴政的紧密关联。与此不同,在良好的社会,死亡则会被看得很重,被极力避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17〕
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中,人们会把死亡看得很重而绝不轻冒死亡的危险。这说明,与暴政下的社会不同,良好状态的社会会在整体上尽力拉远与死亡的距离。由老子对两种社会状态与死亡的关系的讨论可见,老子认为死亡与负面社会状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死亡的普遍化和轻易发生,总是指示着一种恶劣的社会状况。
由于对死亡的负面评价,老子希望尽可能延宕死亡的来临,即使不能真正超越死亡,也尽量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死亡。老子探讨了两种规避方式:
一是通过对死亡的概念细分来建构对彻底死亡的规避: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18〕
死亡被再细分为“死”和“亡”,“亡”是比“死”更彻底的进一步消逝。通过这种区分,便建构出一种死而不亡的可能性,亦即虽死而并不彻底消亡,从而避免了完全彻底的死亡:
二是通过修道来达到如同柔弱婴儿般的状态,从而像婴儿一样远离死亡,如: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19〕
为天下蹊,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20〕
修道有成的“专气致柔”“常德不离”的境界,与充满盎然生意的婴儿状态最为相似。老子认为,进入这种境界就能像婴儿一样离死亡最远。老子对规避死亡的尝试,深深体现了其对死亡怀有的反感和恐惧。
综上可见,老子在本体论上将死亡放在低于道的位置而归于经验世界之后,再在经验世界范围内,将死亡紧密联结于负面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状态,并努力探讨了规避死亡的可能方式。可见,在生——死两端之间,老子对生赋予了极高价值,对死则赋予了浓厚的负面意义,对之怀着拒斥心态。
庄子对死亡的态度则与老子有很大不同。他以非常达观、坦然,有时甚至是欣然的态度对待死亡。
首先,庄子认为既然死亡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无法逃避,那么就应安然接受。《大宗师》中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21〕
《养生主》: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22〕
庄子认为,生死代换是命定的必然,是如同昼夜交替的恒常自然过程,人的意志无法参与其中。这一过程来自于比父和君更高的道的规定,所以人们应当遵从。而且在这个由道所规范的世界的运行中,贯穿着根本性的“时”的节律,事物的生长消亡都处于这样的先天性时间节律之中。因此,应当将生看作应乎时而来,将死看作顺乎时而去,安然顺应这样的时间节律及生死代换,从而不再被哀乐所侵扰,获得从一切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悬解”。
在《大宗师》中,庄子又借病重将亡的子舆、子来之口阐述了为何不应抗拒天命对生死的安排:
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23〕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24〕
庄子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向来皆不能胜天,天命是无法抗拒而只能顺从的;而且天道阴阳对于人来说如同父母,因此,应当恭敬听从其所安排的死亡。
其次,庄子除了指出死亡是天命的安排故无法逃避外,还着重提出对死亡其实也没有必要逃避。庄子给出了两方面的理由:
第一,生和死属于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的自然过程,二者并没有截然的不同,无需将死亡从这个过程中专门区别出来对之加以恐惧。《大宗师》中说:
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25〕
庄子认为,死生存亡具有一体性,犹如身体的各个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因此,不必人为地在生死之间建构断裂性以致恐惧死亡。在同篇中,庄子又借仲尼之口,赞许遭逢母丧的孟孙氏对生死的泰然态度:
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26〕
孟孙氏不关注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不把生死区分为一先一后的起点和终点而有选择地趋就,而是将生死视为不分彼此地同属一个绵延无尽的连续性的“化”的过程。在这个浑然的“化”的过程里,生和死等各环节互相转化、循环往复,因此,生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第二,死亡之所以没必要逃避,还由于死亡可以为人们在当前所处的充满痛苦的生活之外,提供存在方式上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因此,庄子不但以泰然无惧的态度对待死亡,甚至更近一步,以憧憬的心态来欢迎死亡。他提出,活着的人既然没有经历过死,不知死后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为何要预先厌恶死亡,焉知死后不比活时快乐。《齐物论》以丽之姬的故事说明这点:丽之姬被掳至晋国而“涕泣沾襟”,后来却发现在晋王身边的生活比原来的生活更快乐,“而后悔其泣也”。〔27〕庄子以此喻指死亡虽是令人极不情愿的强行降临之事,但说不定死后的状态比生前还更愉快。之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庄子在理论上作出了两个解释:
一是在《大宗师》中说,与人生在世的劳苦困顿、疲惫憔悴相比,死亡能让人卸下无尽的奔忙而得到恒久的休息: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28〕
二是《至乐》中进一步提出,死亡还能让人获得在世间不可想象的巨大自由: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29〕
庄子借髑髅故事提出,死亡可以让人摆脱君臣上下的森严压抑的权力秩序,也摆脱一年四季不得不从事的各种事务,在政治领域与个人生活两方面都为人去除了束缚,故死亡是一种如同王侯般自在逍遥的状态,十分值得向往。
不过,这则寓言也显示出,庄子的死亡观蕴含着一定的矛盾因素。庄子看似热情接纳死亡,但这种接纳又不是完全彻底的。髑髅处在一种能深切感受死后逍遥自在之乐的状态,既然能有所感受,这种状态其实就并非完全的死亡,而是在死之后进入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亦即另一种生。这说明庄子虽然有着把死亡视为最终休憩亦即最后的终结的观念,但有时也潜在地希冀死亡意味着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避免真正的死亡。这与前述老子对死亡的规避倾向具有相似性。不过二者的规避方式又是不同的:老子是以设想一种死亡的不彻底状态,即“死而不亡”,来避免进入完全的死亡;庄子则是将死亡建构为与生前生活不同的另一种存在状态,从而将死亡的实质意义隐蔽地进行了变换,把死变换为了另一种形式的生。
二、老庄死亡观差异的思想成因
老子和庄子同为道家哲学创始者,都表达了相近的对道与自然的推崇,为何对死亡的态度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在老庄各自的思想结构中有其内在的成因。
首先,老庄都认为事物皆有其相反相成的对立事物,但他们在看待相对立的事物时采取了不同方式。老子看待对立双方时,实际上带有区分性视角,更认同柔弱、冲虚的一方,而贬低与此相反的另一方。这是由于老子认为“弱者道之用”,〔30〕即柔弱体现了道本体在世间的发用方式。而生和死正是非常典型地分别体现了柔弱与坚强的状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31〕因此,老子在生和死这两种对立状态中,认同生的状态,尤其推崇充满生意的婴儿状态,同时贬低和拒斥死亡,希望能通过修道达到类似婴儿的状态而远离死亡。
而庄子对于对立和差异事物所持的基本原则是齐同万物,通过“以道观之”〔32〕而一以视之,即“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33〕“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34〕在这种观念下,生与死就具有了“死生存亡之一体”〔35〕的同一性,故庄子不会对它们抑此扬彼。对于生死的一体性,庄子还从气论的角度给予了解释,认为生和死同属于气之变化聚散的过程而相通为一:“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36〕“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37〕即死与生都是气的某种变化形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必乐生而哀死。
其次,老子和庄子追求的境界存在微妙的差异。庄子追求摆脱一切限制而获得绝对的逍遥。《逍遥游》中,大鹏高飞千里,宋荣子不为举世毁誉所动,列子御风而行,已诚极自由,但庄子指出他们仍“犹有所待”,进而标举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38〕的彻底无待之境。为了达到这种境界,需要超越因存在于经验世界中而受到的各种物理性和社会性的限制,而死亡正是一种能让人脱离当下所处的世界,从而脱离其加之于身的种种限制的独特方式,正如《至乐》中髑髅所说,死亡可以让人获得极大的自在。于是,死亡在庄子那里就成为一种值得尝试的状态。
老子则并不追求这种摆脱一切限制的彻底逍遥。他追求的是无为、冲虚的境界,这种境界致力于让人融合无间地契合于道,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9〕可见,老子所认同的境界本就以自觉接受自然律则的规范为原则,而不像庄子那样追求对一切律则的突破。再结合老子对虚怀守弱的倡导来看,老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主张在自然律则和其他外在制约面前尽量缩小自己,使自己处于柔弱卑下之地,以达到与各种先在的制约性力量的相协相融,在这种状态中获得自然自在以及永续之生。因此,老子不会设想通过死亡来脱离一切限制,相反会认为死亡意味的“坚强”状态背离了其主张的柔弱无为和与外界的相协相融。
第三,老子和庄子对现实世界的取态不同。老子一方面批判现实世界,指其“大道废”“六亲不和”“国家昏乱”。〔40〕但另一方面,这种批判又是有保留的批判,老子仍对现实世界持有期待,希望其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行。这显著地表现为他殷切于向世俗权力提出治理原则上的建议,如“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41〕“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42〕“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43〕等。这些都表明,老子希望借由现实世界中的侯王实现他的“道”的理念。可见,老子在批判现实世界的同时,又试图用道的原则引导其转变为合乎道的理想社会。由于老子对现实世界怀有这种期待,他就必然希望这个世界能持久长存以作为实现其理念的载体,因而其思想中充满了对生的崇尚和对死的厌恶。
而庄子对现实世界乃至人性本身采取的是彻底的批判态度,强调它们已在根本上败坏而难以挽救。他认为,人世社会的实际运行规则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44〕如同无道义可言的丛林世界,只奉行强力和伪诈。他又指出:“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45〕“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伐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46〕即历来被宣扬为高才懿德者,都做了种种凶残暴虐之事。作为这种败坏的社会状态的基础的,是已完全被对物的争逐所异化的人性:“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47〕可见,庄子“批判气势之猛烈在先秦是绝无仅有的”。〔48〕由于庄子对整个现实世界从运行方式到人性基础都不再抱有期望,那么能使人脱离这一世界而进入另一种可能性的死亡,在庄子哲学中就成为了值得向往的状态。
三、由死亡观透显出老庄哲学的深层差异
老庄通常被笼统地视为持有相近思想的道家鼻祖。但其死亡观的不同及其思想成因,透显出他们在基本的哲学观念上其实隐含着关键性的深层差异。
首先,从老庄对于生——死过程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到,老庄都阐述了事物存在方式上的辩证法,但这两种阐述有着似同实异的内容。当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时,是对事物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向反面转变的辩证趋势的洞察,这是一种事实性描述,并未表述其价值立场,亦即这一陈述并不意味着老子期望这种“反”的趋势的发生。那么老子对此的价值立场为何?从其“物壮则老,谓之不道”〔49〕等论述来看,他将事物经由壮而向老变化的物极必反过程视为“不道”,可见他对这种向反面演变的辩证趋势,实际上并不乐见其发生。所以老子力图延缓这种趋势的进程而持留于原初的起点,即柔弱如婴儿般的状态。老子对死亡所持的负面态度和规避死亡的尝试,正体现了这种延缓辩证变化的思想,即希望能延缓乃至避免事物向死亡这一最终的反面状态的演变。
庄子同样也指出了事物有着向自身反面演变的辩证趋势,但他并不对这一过程的起始阶段和其后逐渐趋向反面的阶段持有差别化的爱恶,而是把这整个过程看作一个连续性的“化”的自然过程,认为这一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是自然的,都是道的运转流行的体现。而且庄子抱持“齐物”的基本思想,在“道通为一”的观念下,对于辩证变化过程中的无论哪个阶段,都认为应当齐一无别地对待。因此,庄子对事物向反面演变的辩证趋势怀有十分开放的态度,并不认为这种趋势是需要避免或延缓的,而认为可以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在某些语境下甚至还对这种辩证变化持欢迎和期待的心态,例如在对死亡的态度上。
其次,老庄对事物向反面演变趋势的不同态度,与他们自然观的不尽相同有紧密的关联。老庄皆极为推崇自然,但二者的自然观并不像表面上显示的那么近似。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倡导将自然作为最根本的原则来遵循,此时老子是把自然当作一种规范性原则,对之采取无保留的依循态度。但当老子把自然作为其可能处身其中的状态时,实际上又对自然的内涵作了一种隐而不显的限定,而非认同所有类型的自然。这体现在,事物向反面演变的趋势既然在老子看来是“反者道之动”,那么这种趋势就是一种源出于道之活动性的自然过程,但老子在承认“反”的趋势是自然的“道之动”的同时,又将这一自然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坚强”“死亡”等状态看作是非自然的,将之排除在他所愿意处于其中的自然之外,而只希望处身于那种呈现为柔弱、冲虚、淡漠状态的自然。可见,老子的自然观蕴涵着某种内部张力,其对事物由柔弱的初生状态向刚强僵硬的衰亡状态演变的趋势的排斥表明,他既主张依循自然,又不认同全部的自然,而是希望通过依循自然,来避开某种特定的自然(作为自然过程一部分的壮老和死亡);同时葆身于另一种特定的自然(呈现为柔弱冲淡状态的自然)。
而在庄子那里,对自然的内涵并未作出像老子这样的限定。庄子对于个体身上的自然变化、包括向反面的变化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显现出无保留的拥抱,以至觉得作为这种自然的体现之一的死亡也不妨尝试。但庄子对于自然的内涵,是否彻底不加任何限定?也并非如此。庄子在《马蹄》《胠箧》《在宥》等篇中,对于强有力者对他人的宰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体现出对自然的两方面限定:一是把在群体层面会自然而然出现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排除在其所认同的自然之外;二是主张自然必须是普遍的自然,不允许出现一部分个体的自然(自然禀赋、欲望)对另一部分个体的自然的压抑。不过,虽然庄子和老子都对自然作了限定,但二者的限定处在不同方向上。庄子对自然所作的限定,是在群体层面、政治层面的,对于个体层面的自然变化则未作限定,所以对个体会遭逢的死亡持积极的开放态度;而老子对自然的限定是将向壮老、死亡的演变排除在自然范畴之外,这种限定主要是在个体事物层面上的,在此基础上才类比性地也将这种限定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如主张持守于小国寡民的原初社会状态。
再次,老庄对事物向反面演变的不同态度,不仅体现出他们自然观的差异,而且体现出他们在思考自身所处世界时的不同思想方法,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不同价值断定。庄子思考这个世界时运用了解构的方法,通过阐述彼——此、是——非之间的相对性、互渗性和相互转化,以及揭示苦乐美丑等日常感受因人而异的主观性,而拆除了让事物和观念得以自我固持的基础,由此显示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观念和感受都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和价值。在庄子看来,这个世界“道术将为天下裂”,〔50〕“天地之纯”〔51〕丧失,浑朴而整全的一散落为纷杂而各自局限的多,故一切事物都只具有局限于一隅的相对意义。因此,庄子并不看重这些事物及它们所构成的这个世界,也不看重它们的原初状态或现有状态,故他对事物朝自身反面的演变,包括朝向死亡的演变,都不会感到焦虑,甚至期许这种演变开启一种使充满缺陷的当下生活状态得到更新的可能性。
而老子思考这个世界的方法则不是解构的。老子在事实描述的层面揭示了内在于这个世界的辩证结构,即世界中的事物蕴涵的向反面演变的趋势,但他并不用事物的这种自我否定趋势来解构这个世界,而只是在描述这种趋势,同时希望延宕这种趋势,以尽可能延长事物在生的状态中的存在。可见,老子并不像庄子一样消解这个世界及其中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希望持久地保全这个世界。在此基础上,老子试图对这个世界运用引导转变的方法。《老子》中许多篇章都体现出希望引导政治实践的用世之心。这说明,虽然老子对这个世界的现状也并不满意,但他并不因此对这个世界进行解构和否弃,而是意欲以其设想的政治方案影响权力执掌者,使这个世界往其认为理想的方向转变。“德经”中阐述的诸多“君人南面之术”,正是老子为了引导这种转变而建构的中介环节。
最后,老庄哲学的上述差异,在更根本层面上共同指向了他们在本体论层面的差异,即二者对待道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方式。在老子那里,一方面,道作为这个世界的形上本原而在根本上高于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道的这种形而上的超越性基本上只起到作为理论上的前设的作用,而在道的实际运用上,老子又将道非常紧密地重新拉回世间,将道作为一种可以对接到具体生活的规范性原则而应用于人世,导引人们的存在方式和政治实践,以期促成小国寡民、少欲无为的社会和政治状态。因此,《老子》有一半篇幅,即“德经”,是主要关于道如何在世间显现和运用的内容。由于老子需要将道的原则运用于这个世界,故对其而言,这个世界就成为值得留恋的,世间事物的衰亡成为不可欲的,事物的最佳存在方式是长久保持离死亡最远的婴儿般状态。
在庄子那里,道同样也是既有形而上的本原性,也有道“在屎溺”〔52〕的与经验世界的相即性,但对于道对人们的存在方式的作用,庄子体现出与老子很不同的思考。在庄子那里,道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引导世间生活向特定状态转变,而在于让人通过修道、体道而达到对这个世界的超越,即让人超离这一遍布是非纷争和强权宰制的世界,将自己拔升至与道同一的无待境界。《逍遥游》中的至人形象即充分体现了庄子的这种理想。由于对庄子来说,世间一切都是通过道来超越的对象,故世间事物无论朝何种状态演变都不必挂怀,甚至对朝向死亡的演变也可以乐见其成。
可见,虽然老子和庄子的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中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相即的特质,但在老子那里,形上之道与形下世间结合得比庄子那里远为密切,道可以直接转化为导引政治实践的具体原则而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亦即在“道”“术”关系上,道可以比较容易地下沉为术、特别是治术,因而在思想史中,老子思想在后世流衍出了与现实政治有着复杂交互关系的“黄老之术”。而在庄子那里,形上之道在与形下世间相即不离的同时,又始终保留了较强的对于人世的超越性,从而在道与世俗世界之间形成一种常常有所彰显的张力。在后世的许多时期如魏晋、晚明等,这种对世俗世界保持着张力的哲学,不断为人们采取一种疏放不羁、凌虚高蹈的生活方式提供着思想资源。在不同情况下,这种生活方式既有可能构成一种对名教礼俗进行反叛、对权力秩序进行消解的尝试;也有可能成为对压抑性的既定现实秩序仅具姿态性意义的超越,获得的只是假想性的独立于当下秩序的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