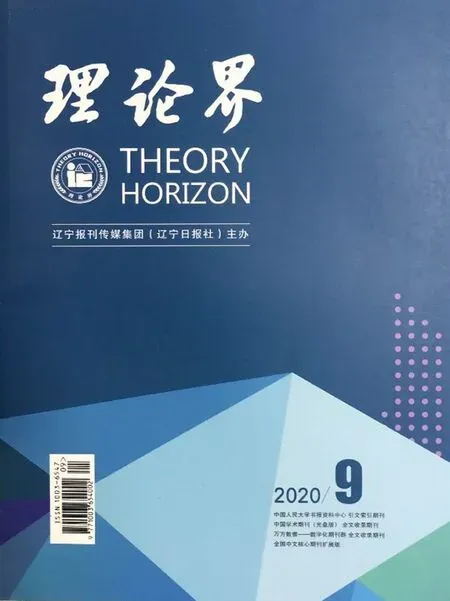“自我理解”的四个维度
——从康德批判哲学的视角看
徐正铨
“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初衷。其实,对于一切严肃的思想家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理解我们自己”。自苏格拉底开启“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以来,哲学的后续就成了对这一命题的注解。当人们对自我的理解出现偏差时,其对自身的认识也就会有问题,并且很容易将日常的实践引入歧途,给人们的生存造成灾难。正因为如此,“如何理解自我”,对于人之存在自身的“善在”〔1〕来说,就成了根本性的命题。而身处近代启蒙时期的康德深悟其中的道理,把人的“自我理解”命题作为他思虑的重心,通过其批判哲学来呈现他对此命题的思考:确定人“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对他的“命运和前途”做些什么样的判决和规定。〔2〕康德尝试以批判的方式纠正人们在自我理解上的偏误,期望探寻到一个正确实现自我认识的窗口,进而把握一条能够合理地将这样的理解与认识引向实践的路径。在他看来,“认识自我”不仅仅是去“看到”的一个来自“被见”世界的对象,而且还需要内观和反思,由事实层面进入到价值层面。而时间恰恰是两个层面的中介,它兼具自然时间的事实性与生命时间的价值性,成了人的生命和意义展开的同一性之流。时间作为人们自我理解之窗口的属性蕴涵在康德的批判哲学运思中。
在借由时间开启的自我理解命题中,康德通过精神之维澄清了“什么是人”还是“人是什么”的不同指向,凸显出自我理解中所应把握到的人之存在的价值;通过道德之维明确其整个哲学体系一以贯之的目的论思维,开掘出自我理解中所应蕴藏的人之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实践之维彰显其批判哲学强烈关注现实的实践旨趣,扩展出自我理解中所应包容的人之存在的可行性。康德守护“人之尊严”的崇高理想,坚持“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基于时间窗口的自我理解的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有了持续生成更新的可能;透过这个窗口所铺陈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既指引着实践又落实于实践,使得人类的实践有了方向和动力。
一、时间之维——自我理解如何可能?
时间是自我理解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才能切入存在自身,无论是作为族类存在的人,还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我们都借助于时间之维来表征自身存在的外在长度和内在深度。甚至空间就是时间的片段性或者说是片段性的无限叠加,如此而言,则借助于时间之维还能表征人之存在自身的宽广度。康德在其“时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中就说,“只有在时间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想象一些东西存在于同一个时间中(同时),或处于不同的时间内(相继)”,“只有在时间中现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不同的时间只是同一个时间的各个部分”。〔3〕在时间的前提性基础之上我们展开了自我理解的可能性之旅,在人类的历史和自我的生命中留下印记,标出路标,有了回望过往与展望未来的驿站。时间以其本身的无限性确定了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每一个时间中的对象,而这种确定性又奠定一切对象之理解的基点,无论这种理解是人们通过时间窗口的向外投射,还是面对自身的向内省察,都促成了自我理解的深化,自我认识的扩张,自我行为的落实。
在自我理解的命题考察中,康德提出“一个主体如何能够由内部直观自己”,〔4〕认为“时间和空间作为一切(内部和外部)经验的必然条件,只不过是我们一切直观的主观条件”,〔5〕“在时间和空间中,不论是外部客体的直观,还是内心的自我直观,都是如同它们所显现的那样来表象它们的”,“因而是像它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而不是它所是的那样”。〔6〕“如其所显现”与“如其所是”的差别正是康德所谓“哥白尼变革”的核心内涵,“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7〕的背后是,作为知识拥有者的主体,对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的地位反转。他对“现象本身不能够在我们之外发生,只能实存于我们的感性中”〔8〕的强调,也表明了其认识论对主体性的高扬。而先验时空观作为康德认识论的基础性部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主体性色彩,即使是“先验”概念本身也是一种主观预设,而预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一个认识得以可能的时间性前提,因为“先验”所标明的就是一种时间维度。
在康德所呈现的“先验”概念里,我们能够触及时间的端倪。从“先验——先于经验——先于人的经验”的概念解析中发现:一方面人类以族群的方式繁衍,即使个体的消逝也不影响整体的延续,因此,在时间上以第一个人的出现为界呈现出一种向后的无限性,并且还设想了人类出现之前的无限性,从而在时间之维上刻度出正负两个方向上的无限性来实现对有限存在的理解;因为另一方面人们总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世,每个人的生命体验是任何一个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人类存在样态的个体化就表现为以生死为界限的有限性,而从生到死也即是个体生命的完整时间,由于这个生命时间的长度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恐惧,这使得每个人具有与生俱来孤独、无力与绝望的情感。为了抵抗这些生命感觉,摆脱个体有限性造成的压迫,人们只能寻求在族群的延续、后代的繁衍中获得个体情感的寄托、人生价值的附丽。“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9〕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如何可能的?经由时间之桥。时间越过了个体之死与族类之生的边界,揭开了从不可能到可能的秘密。以时间之终止为别名死亡,透过时间绽露出最为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始于在时间中筹划未来的生之可能。所以说,时间的无限性设定是为了便于打开对有限性存在的自我理解的窗口。从个体存在的生命意义上而言,其存在与时间一体两面的,存在的生灭以时间的始终来刻度,对存在的理解也以时间为窗口而展开。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明的“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10〕他所无意或有意不言明的是:人之存在狡猾地隐没在时间背后,让坚硬的时间去抵挡岁月的无情以包裹住温柔的人心。
二、精神之维——“人是什么”还是“什么是人”?
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处境具体展现于:人既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自然存在;既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又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尽管这种“非理性”并无存在论意义,但我们到底不能否认这样的存在论事实)。两者共居一体,既在个人身上形成勃勃生命之源,又使人类共存于普遍的相互关系之中。人之存在介于物之存在与神之存在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性、精神性、思想性的东西使人逐渐地摆脱纯粹的动物性,踏上了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作为一种动物被文化(人化)之后已不再只是动物而是人(成其为人)了。甚至可以说,一方面,神之存在就是人之精神性的思想化,是人之精神文化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之存在正是借助于神之存在来彰显与提升人的精神性。人类期望通过继续向神性靠近的方式来守驻人之存在的底线。尽管在这一靠近的过程中,肉身始终是其沉重的牵绊,一再地将人拖入人间地狱。但是人之存在的神性之维,依然是生活世界中的人们追求“好生活”的价值源泉之一。所以精神性是人之存在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根本属性。物性是一切存在所共有的,本能是所有生物所共有的,意识是全部动物所共有的,唯独精神性是人所独有的。
正是基于对人之存在的精神之维的把握,我们认为有关“人是什么”和“什么是人”的提问方式是有深刻差别的。对于前一种提问的回应,著名的命题有:“人是高级灵长类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机器”,以及“人是目的”。那么,到底人是什么?人是面向世界所看到的“所见”之对象,还是内观与反思所想到的“所思”之根据?这样的提问方式能够撑开人之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吗?无论是“动物”“机器”,还是“关系”“目的”,都不能涵盖人的全部意义。而“什么是人”的提问却敞开了一切可能性,让人去成其所是,成其所应是。并且以“……是人”的语式强调了人的终极性,即将对人的问题的思考最终都落实到人本身上来,警示出不但要杜绝“动物”和“机器”对人之存在本身的掩盖,也要避免“社会关系”和“目的”对人之存在价值的遮蔽,所导致“社会关系”和“目的”对人之存在终极性的僭越。从康德批判哲学的运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原本要表达的意思是“目的是人”。因为康德对“什么是人”的问题的思考,正是源于对人的精神性坚持,人的精神性具体可以细化为其道德戒律的两个假设: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的人应以人为目的地活着。理性的人活着(存在)的“目的是人”。人从作为“物”的存在到作为“人”的存在的过程,正是人被人伦理化的过程,也是人类的不断的“应然”追求使人的理性(神性)不断克服非理性(物性)的过程。而人的理性(希望成为人欲求)发源于人的精神性,精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这种属性最初或许是缘于信仰,信仰人之为人的不应如何而又应如何——即原初戒律、基本人伦。而人类实践的目的终将落脚于人自身,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目的是为了人,而人不是为了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在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与认识的问题上一直就磕磕绊绊,自“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之后,历经了数千年的哲学迷途,将认识的主题逐渐转向人之外的自然世界,在宗教神学强大的影射之下,对主体自身的认识成了哲学观照的盲区。直至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给哲学重新定位,而到了康德才全方位地把哲学重新拉回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反思、警醒,回归哲学的为人之幸福生活的价值属性,尤其是将几千年来哲学对于本体论问题的纠缠与纠结,从现象界的实践理性中推离开去,使之归于自在之物,留待信仰去看顾。从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中把“人”置于人的认识问题的中心,以时间为认识的自身与身外之世界的窗口,用时间定位经验与先验的界限,将以知识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的认识——异化了的知识,只是知识的知识——还原为人的知识,铿锵有力地发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人透过人围着人也为了人的认识的成果,而且由于个体人的有限性,个人之于人类历史的转瞬即逝,个人之于人类社会的驻留无定,人的认识必定是有界限的,人的理性也必定是要受到其自身有限性的制约而归于有限,而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而唯有借助于“大我”之历史时间对“小我”之生命时间的融贯,才能达成有限生命个体对自身的超越,使个体的有限性足以扩张成类的有限性,类的有限性借助于时间的无限性而达到永恒,并以信仰为名,在希望中成就人类不断改善的事业。毕竟,人居于其中的实践世界毕竟又大大区别纯粹的理性世界,如果人因其个体的有限性而停留于其有限性,在人世的实践之中不去做那应当做的事情,不去做出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神性(精神性)追求,那么人永远也无法成为人,而只能称其为欲望之物,自然也无法“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11〕
三、道德之维——“目的论”还是“义务论”?
所有的哲学都因人的问题而产生,最终归于人的问题,而这“归于”途中必要过“伦理”的桥梁。在人的道德伦理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协调,实现其哲学思想最终所希望达成的对人的价值引导。康德哲学自然也是如此,他说,“人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12〕“我们只有当自己按照使道德律作为终极目的托付于我们、因而使我们负有义务的东西来行事时,才能把自己视为这种终极目的”。〔13〕在此“道德”不但作为“目的”被托付而且还使“义务”成了让自己成为“终极目的”的道路。在康德的伦理命题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其第二道德规律:“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14〕“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者的意志”。〔15〕也就是说,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是自己对自己颁布规律,所以每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目的,不把别人看成是工具;每个人都有通向自己目的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每个人都不把别人当作自己的铺路石。这样,人们各自也就都有了自己的尊严,都有了自己的人格,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平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实践理性”办事,不接受外来的控制,因而每个人都得到自由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意志自由”,也就是所谓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
正是基于在“什么是人”的问题上,“人不是为了目的,而目的是为了人”的考量,康德选择了具有强烈义务论倾向的道义论伦理,而不是幸福主义的目的论伦理。这样的选择为的就是保证其“应然世界”的出现,也就是在其向往的“公民体制”之下,以“权利原则”狙击“幸福原则”。〔16〕他认为,“如果幸福(幸福原则)取代自由(内在立法的自由原则)被确立为原理,其后果便是一切道德的安乐死(和平的死亡)”,〔17〕从而“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18〕其意图就是摆脱个人非理性因素对普遍立法的纠缠,以权利观划出每个有限存在所不应逾越的边界,力图以基于自由权利的道德律令,来应付有限个体在追求各自的幸福时,不至于妨碍其他个体对幸福的追求。正是因为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德性自在地本身就构成一个体系,但幸福却不是如此,除非它精确地按照道德性而被分配”。〔19〕这样的表述,无疑也透露了以“道德”约束“幸福”的主张,而“精确地按照”的具体化就成了他的义务论的道德伦理,并在他的“论在道德上理论对实践的一般关系”〔20〕中予以阐述。康德所指出的“实践自由的前提在于,虽然某物并没有发生,但它本来应当发生”,〔21〕非常着意地强调了“应当”的道德要求,期望在义务论的护佑下实现由“应然”向“实然”的转化。而且,康德通过其道德戒律的提出,就人之为人的伦理问题简化提纯为“人应如何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直接从人的“实然”状态跨入“应然”追求,抵近人的“成人”问题的实质,即人是一种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历史确定性又具有偶在的无限可能性的存在。
同时,人之存在面向未来、向死而生。作为一种具有极强可塑性甚至超越性的存在,人们现在的“应然”追求极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实然”状态。他既是他认为的现在的那样,也可能是他愿意成为的将来的那样。人在时间中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未来,推向他希望成为的样子,而且时间逼迫着他,不让他停歇,让他活着,直到他死为止。并且要使人人都明白只有他自己才能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负担起来。〔22〕否则,人从自由滑到任性就是一步之遥,其间可以凭靠的就是道德责任。在人之为人的伦理问题之中,持续不断的“应然”追求使得人的“实然”状态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提升,我们现在的“实然”状态就是过去的人们的“应然”追求的结果。可以说,人从作为“物”的自然存在到作为“人”的自由存在的过程,正是人被人伦理化的过程,也是人类的不断的“应然”追求使人的理性(神性)不断克服非理性(物性)的过程。而人的理性(希望成为人的欲求)发源于人的理性本身,理性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这种属性最初或许是缘于信仰,信仰人之为人的不应如何而又应如何——即原初戒律、基本人伦。只有对非理性的人以理性的期许与追求,人的理性才得以可能;只有相信人的理性之可能,理性才得以在人身上生成存驻,才得以实现对人的非理性的限制。正是由于人的可以“不断成为”的属性,使得人之为人因信而生——首先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可能)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其次是你想让其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就(可能)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使得唯有在人的身上信仰的力量才能如此的强大,信仰之于人是如此的重要。
四、实践之维——自我理解归于何处?
人之道德可能性的探寻最终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归于实践。而人之存在本身恰恰又是人的最大实践。“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23〕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创造了人自身。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众多创造中的一个伟大成果,“其目的是要对人类理性的范围和限度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算,通过揭示理论理性的限制来突出实践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24〕对康德来说,“实践维度”既是他关于人之道德可能性追问的最终出口,也是他有关自我理解命题的落脚之处。如果说理论理性所关注的是有关某些既定对象的知识,那么实践理性关注的则是根据对象的观念来创造对象。〔25〕康德对于后者的关注显然多于前者,甚至可以说对前者的关注是因于后者。这也是人“为自然立法”“为自身立法”之说法的缘由。通过获得“既定对象的知识”,再“根据对象的观念来创造对象”正是人类实践的本质。康德自己也说,“纯粹理性单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它提供(给人)一条我们称之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则”。借助于这样的“普遍法则”展开人们的实践活动。
经时间的窗口展开自我理解的可能性之旅。通过“什么是人”而不是“人是什么”的不同提问方向,突出了人在时间中的对自身理解的厚度,由此凸显出人之精神维度,抵近人之存在的核心: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一种依照道德观念而创生可能性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才是人的存在方式?对于这一问题,答案就在人的自我理解命题之中。“什么是人”中的“什么”是段有待填充的空白,是种无限可能性的展开,是基于不同的“自我理解”的各自生命的绽放,是根据不同观念所开创出来的丰富人生。最终“什么”能够是什么样的,只能在实践中由实践生成。
根据时间观念,康德锚定人之存在坐标,开掘人之存在的价值。借助时间的同一性之流,人的生命和意义渐次展开。伴随着这样的展开,人类个体与族类的实践都获得了充盈的活力,使人的实践活动拥有了连绵不绝的巨大能量。在一次次的挫折失败中反身自问,在一段段的艰难困苦中深化对自我的理解,从而不断地在由时间观念开启的存在之价值和生命之意义的追寻中明确实践的方向。这样的方向感,对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人而言,尤其关键。因为人之存在的时间性,使得始终伴随着一种可能性的选择与其他可能性的同时丧失。存在在自我理解中的人们,常常在自我的理想中展开自我理解。而自我的理想恰恰又是由时间所开辟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所灌注的。如此,时间成了理想与理解互动的场域。这样的场域生成为一个自我理解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得以寻见自我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价值与意义既指引着实践又必落实到实践之中。否则价值与意义就是无所附丽的“无”。因此,一种赋有价值与意义的自我理解的所归之处必然指向实践,在实践中理解自身,在理解中展开实践。
根据“人是目的”的观念,康德经人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的提问,过渡到他所设想的一整套政治构架。这个构架由以组成的“普遍共和主义”和“永久和平”就成了康德政治哲学的两个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两个中心问题康德把自我理解的命题落实到政治实践之中,主张道德应以某种方式限制和支配政治实践。这种方式就是以“人是目的”为核心的三个道德律令,并通过公民社会的中介,告诫人们:“普遍的共和主义和永久和平应该存在,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人类的道德进步。”〔26〕人类的道德进步就表现为对人的自主性的维护,对人类尊严的守护。而这样一些有关人自身之自我理解的观念,在落实时却需要通过进入到政治实践层面。因此,康德认为“人类终极的目的乃是要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27〕而这个“最完美”的国家制度是人类在其实践中批判性反思的产物,作为“最完美”之观念的描述,我们根据它去创造一个完美的国家制度,或者说尽量在实践中去创立这样完美的国家制度,以实践“人是目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自我理解。
总之,时间以先验的名义将经验架设其中,以实现人对自身存在的理解。通过对人自身存在特征、存在处境、存在价值、存在方式的体认,深刻领会“什么是人”。依托于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自我理解”命题,透过时间之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时间即是我”,人类的历史性时间即是“大我”,个人的生命时间即是“小我”,而两种时间的错位与断裂就造成了人之存在的悲剧。为了尽量避免存在悲剧的发生,就需要我们从“精神”与“道德”之维来呵护人的存在,以精神性来提升人之存在品性,以道德性来守驻人之存在底线。我们要充分理解人之存在的自主性、精神性、道德性特征,深切把握人之存在易于物役化、手段化、工具化的艰难处境,认真对待人之存在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唯一性(基于时间的一维性)价值,始终坚持人之存在只能“启于实践而归于实践”的方式;坚定地沿着康德批判哲学所指名的实践旨趣,使人之存在在理性光辉中,在梦想的指引下,在各自的人生“实践”中实现每个“自在”于“共在”中的“善在”与“永在”,抵达康德所召唤的“永久和平”的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