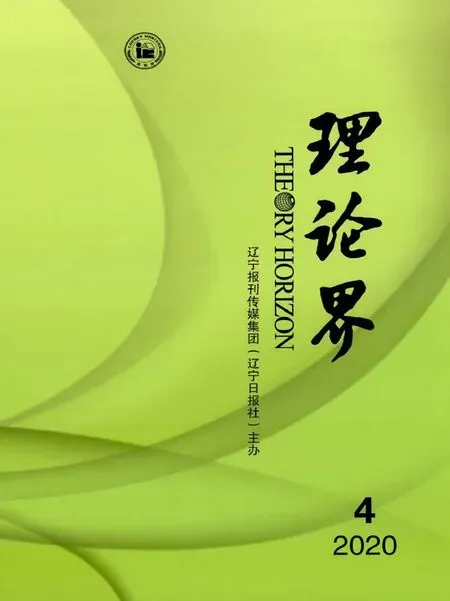帛书《要》篇“虽周梁山之占也”新解
——兼谈易占在战国时代遇到的挑战
王亚龙
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非常重要的简帛文献,其中包括《易经》和《易传》。与今本《易传》不同,马王堆帛书《易传》共有六篇,即《二三子问》 《系辞》《衷》 《要》 《缪和》和《昭力》,其中有部分内容见于今本的《系辞》 《文言》等篇,但还有很多内容是传世文献中所未见过的佚书。帛书《要》篇就是这样一种佚书,其主要内容在于论述《周易》的精要绝妙之处,以及孔子对待《周易》的态度,还有孔子对于《损》 《益》两卦的解读等。由于帛书残缺,有些内容已难以确知,但帛书《要》篇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要》篇的成书年代,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篇成书于战国晚期,也有学者认为其成书于秦末汉初。但是《要》篇中一些思想和内容至少在战国时期应该就已经形成并且流传开来,则是没有疑问的。〔1〕因此,帛书《要》篇是研究先秦易学史和易学思想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
一、关于“虽周梁山之占也”的解读
《要》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很值得我们重视:
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虽周梁山之占也,亦必16下从其多者而已矣。”17上〔2〕(释文用宽式)
在这段话里,子贡问出了一个我们都十分好奇的问题,那就是孔子究竟信不信筮?当然,这里的“筮”就是指利用《周易》进行的占卜,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卜筮行为。一般人们都认为,《周易》原本就应该是卜筮用书,正是经过了孔子的努力,《周易》才变成了形而上的德义之书,升格为儒家经典之一。那么孔子又是如何看待易占这种行为的呢?《要》篇的这段对话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很不好懂,那就是孔子说的“虽周梁山之占也”,研究者对此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如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指出,《孟子·梁惠王下》有“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淮南子·泰族》 《史记·周本纪》 《吴越春秋·太伯传》以及《尚书大传·略说》等典籍也都载有大王亶父“踰梁山”同类的传说,且又有《诗经·大雅·绵》“爰契我龟”的记载可供参考,所以他认为“从本篇的文脉来推测的话,这‘梁山之占’,好像是指‘大王’‘去邠踰梁山’之时,为卜知周可否在那个地方的‘岐山之下’坚果而进行的‘占’”。〔3〕其他研究者如李学勤、廖名春等亦持类似的观点。〔4〕不过,郭沂则认为“周梁山”为山名,“当为孔子周游列国所经之地”。也就是说,“周梁山之占”是指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所进行的一次占卜。〔5〕刘彬同意郭沂的看法,他认为“周梁山之占或许是孔子经过周梁山时所进行的一次占筮”。〔6〕刘大钧又指出,若将“周梁山之占”与大王“踰梁山”之说结合起来,似有不妥,因为《诗经·大雅·绵》“爰契我龟”的说法讲明了是龟卜而非“筮”,所以他认为“周梁山”也可能是人名。〔7〕
可以看出,学者对于“周梁山之占”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将其与典籍中记载的“踰梁山”传说联系起来。最近还有学者另辟蹊径,指出“周梁山”应该分开作解,所谓“周”即周朝之周,有“亲周”“尊王”之义,《论语》载孔子曰“吾从周”,正可看出孔子对西周王道的向往;而“梁山”则是指晋国的梁山,《春秋》经记载成公五年“……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即此梁山。这次“梁山崩”乃是一件大事,“周梁山之占”即关乎周天子性命的梁山崩之占。〔8〕
笔者认为,将“周梁山”解为山名或人名均有不妥。一则目前所见与孔子有关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周梁山”的人名或地名,二则将“周梁山”解为人名或地名与整句话语意不合。另外,赵文将“梁山”解为晋国的梁山,将“梁山崩”与“天王崩”联系起来,亦显牵强。不过,赵文将“周”与“梁山”分开,则颇有启发。
据此,笔者认为“周梁山之占”应该就是就是典籍中多见的“太王踰梁山”之事。因为孔子此处特意举出“周梁山之占”的例子来,可见此事之重要,且在当时应该广为众人所知,“太王踰梁山”之事正符合这些特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之前学者对整段话的理解有些偏差。学者往往将孔子前面说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和“虽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分开来理解,将前者解释为“我自己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没有疑问的”。而后者则解释为“即使像周梁山那样的占卜,也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有学者所谓的“共筮”制度。〔9〕但是仔细分析之下,这样的解释其实并不符合逻辑,“百占而七十当”跟“共筮”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从语境分析,孔子所谓“百占”显然不是指就某一件事情进行一百次占卜,而是指的一百次不同的占卜行为,在这其中有七十次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孔子虽未直接回答子贡的问题,但言下之意也是说自己是“信筮”的。而信筮的理由,很显然就是因为“七十当”在“百占”中是占多数的,这才是后文“从其多者”所指的内容。也就是说,之前学者对孔子这句话中的三个分句之间关系的理解有误,导致整段话的意思出现了隔阂。
二、从语法的角度重新思考“虽周梁山之占也”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知,所谓要“从其多者”的,并非“周梁山之占也”,而是孔子,因为孔子“百占而七十当”,“七十”就是“多者”。那么“虽周梁山之占也”这句话就被独立了出来,在整段话中似乎扞格不入。所以笔者认为,要想彻底弄懂帛书《要》篇中孔子的这段话,还需要从语法上对其加以分析。
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上古汉语语段话题对语篇中的省略起着很大的控制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语段话题控制下的与其同指小句主语的省略”。比如《左传·宣公二年》有一则关于“晋灵公不君”的记载: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
董秀芳就指出:“此例中,语段话题是晋灵公,这一话题控制了后续小句的主语省略,虽然‘宰夫腼熊蹯不熟’这一小句中的主语‘宰夫’与语段话题不同指,但这一小句的出现并没有阻止语段话题控制其后几个小句的与其同指的主语的省略。”〔10〕
我们再来看《要》篇中的这段话。很显然,“吾百占而七十当”句中的“吾”既是这一个分句的主语,同时又跳过中间一句,而作后文“亦必从其多者而已”这个分句的主语,也就是说“从其多者”也是孔子自道,是说自己要“从其多者”,而不是“周梁山之占”要“从其多者”。所谓的“多者”就是“百占而七十当”的那百分之七十,孔子认为自己占卜多数时候都是“当”的,所以才选择“信其卜筮”。
这样一来,中间这句“虽周梁山之占也”单独作为一句,笔者认为应该将其断作“虽周,梁山之占也”,意思是“即使周朝,也有梁山之占这样的事情”。可以看出,这句话中省略了“亦”或“亦有”之类的谓语。古代汉语中“虽”字可以作为表示“纵予”关系的联结词,〔11〕这种情况下的“虽”字往往组成“虽……亦……”的结构,表示“需让——转折”的搭配,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就是“即使A,也B”。根据学者的研究,用“虽”字表达的纵予句式在汉语发展史中呈现越来越高的出现频率,而且其雏形“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12〕
我们可以在古代汉语中找到类似的省略谓语的例子,如《左传·庄公十年》记载曹刿论战之事有这样一句: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其中“再而衰”也就是“再鼓而衰”,“三而竭”也就是“三鼓而竭”,后两句中均承前省略了谓语“鼓”。再如《论语·卫灵公》有一句: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其中“躬自厚”之后也是省略了谓语“责”字,这是承后而省略。〔13〕
根据这些例子,我们再来看孔子的这句话:
吾百占而七十当,虽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可以看出“周”字后面承后省略了谓语“亦”,而“亦必从其多者”之前则承前省略了主语“吾”。若将整句补全,就应该是
吾百占而七十当;虽周(亦) 梁山之占也;(吾) 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所以“虽周,梁山之占也”就应该理解为“即使周朝也有梁山之占的这样的事情”。这是周初的一件大事,被孔子用来作为自己“信筮”的根据。也即是说,孔子在这里为自己信筮提供了两条根据,一是从俗(从其多者),二是从古(周梁山之占),这也是比较符合孔子的思想特征的。
三、帛书《要》篇所反映的孔子与易占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向来为大家所关注,《论语·述而》中孔子自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是对于这句话,古往今来的学者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如《经典释文》 卷二十四于《述而》 “学易”下就说:“如字, 《鲁》 读‘易’为‘亦’,今从《古》。”《鲁》是指《鲁论语》,《古》指《古论语》,也就是说如果依照《鲁论》,“易”应该是“亦”字,属下读,作“亦可以无大过矣”,那么便与《周易》无关了。清代学者惠栋在其《九经古义》中就说道:“《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以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力主“易”应该是“亦”,并认为孔子说自己“五十以学”是自谦之辞。
不过,经过学者考辨,《论语》中的“加我数年”一章,仍应该看作“孔子同《周易》有学术思想关系的明显证据”。〔14〕现在,通过对帛书《要》篇的解读,我们更可以明确孔子与《周易》关系密切。《要》篇说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5〕又记孔子之言曰“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此与《论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一脉相承,从中可见孔子对《周易》的重视程度。
一般认为,孔子对《周易》的态度是重德义阐发,而轻其卜筮应用。而帛书《要》篇则记载孔子对易占也有其兴趣。但是我们是否就能根据《要》篇简单地推断孔子与《周易》及易占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首先,《要》篇只有这一条孔子说自己信筮的记载,而且还不是明说,《要》篇中更多的还是孔子对于德义的重视和对卦爻辞的解读。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要》篇作为一种史料所形成和反映的时代。
前文已经说过,《要》篇的创作流传应该是在战国以至秦汉时期逐渐形成的,其中虽然有不少“孔子曰”的内容,但这篇文献的形成年代不可能早到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所以《要》篇就不能看作是有关孔子的第一手材料。很多学者根据帛书《要》篇撰文讨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以及孔子对易占的态度,如刘大钧就认为,孔子所传易学应该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依传统而言《周易》占卜,即‘幽赞而达乎数’,亦‘《易》为卜筮之书’的内容;二是孔子晚年于《要》篇所言‘《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的‘明数而达乎德’的内容”。〔16〕孙航则提出所谓“孔子易学思想”这一问题,并试图结合《要》篇与相关文献对其进行讨论。他认为,“孔子易学思想产生以后,其所关注的范围扩展至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万物之化生,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拓展”。〔17〕笔者认为,这些结论还是有些武断,因为《要》篇里面与孔子有关的内容也可能是经过后人加工甚或根本就是后人假托的。所以与其说《要》篇反映孔子的易学思想,不如说它反映的是这篇文献形成并逐渐流传的战国至秦汉时代的思想观念。
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孔子易学思想,更准确地说就应该是战国秦汉时代人们所认为的孔子的易学思想。当然,刘大钧也注意到了文献在后世流传中可能会存在的人为选择和删削,所以他认为孔子传《易》系统中得于卜筮的那一派由于没有取得官学的地位,从而渐渐湮没了。这种看法应该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易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周易》一书确实经历了从实用到义理的阶段。《周易》作为一本卜筮用书,决定了它与其他典籍的性质不同。《周易》首先是一部实用的作品,甚至秦始皇为控制思想而采取的焚书措施都将其排除在外。但是为什么《周易》到后来又能成为一部儒家经典呢?正是因为从战国开始人们对易占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周易》才从卜筮之书逐渐升格,其中的思想和义理越来越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周易》一书也完成了从卜筮之书到哲学经典的转变。而帛书《要》篇正是这一转变逐渐发生之时的反映,所以其中才包含了所谓“孔子信筮”的记录,但同时又有更多篇幅讲述对易占的质疑和否定。
四、易占在战国时代遇到的挑战
事实上,《要》篇中子贡的提问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西周和春秋时代,人们把卜筮行为尤其是易占看作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会发出“信不信筮”这样疑问的。这一点从很多早期文献的记载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如《诗经·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尚书·召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等,可见当时对待占卜都是很郑重其事,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左传》中也有很多占卜记录,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十八年春,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令龟有咎。二月丁丑,公薨。”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占卜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制度。梁启超早就指出过,先秦时代有所谓“司历之祝”,其职掌中有一条便是“占星象卜筮以决吉凶也……降及春秋,此术犹盛,如裨灶、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为一时君相之顾问;而《左传》一书,言卜筮休咎、占验灾祥者,十居七八”。〔18〕卜筮就是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但到了战国以后则不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人们开始思考一些从前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易占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儒家的兴盛,“德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就形成了对易占卜问吉凶的冲击。帛书《要》篇中,子贡提到孔子平日对弟子的教导,有言“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将“德义”“智谋”与卜筮行为对立起来,表达了对卜筮行为的质疑。孔子也明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帛书《衷》篇也有言:“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对“德义”的推崇直接导致了占卜信仰的动摇。丁四新指出:“《周易》由占筮以求利而变为以德义为重,兼顾福利的经典,经过了比较漫长的过程。不过这一过程,推测起来应以《易经》成书后不久即已开始,到春秋后期,形成了一个以‘德义’研几玩易的高潮,今《国语》 《左传》 《易传》,以及出土的帛书都可以作出证明。”〔19〕
除了“德义”思想的冲击以外,易占地位的动摇也跟易占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易占与其他卜筮方式不一样,它根据《周易》占断吉凶,而《周易》有完整的卦爻辞系统,这就给了人们很多解读阐释的空间。《要》篇既记载孔子“老而好易”,但又说孔子是“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已经可以看出《要》篇作者试图改造《周易》的企图。他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对易占的否定和对卦爻辞的重视,这与前举《论衡》中的例子不谋而合。并且《要》篇明说《周易》卦爻辞是“古之遗言也”,是为其“乐其辞”的行为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
到了汉代,这种“乐其辞”的行为更加得到发挥,如王充《论衡·卜筮篇》中有一条记载:“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20〕所可注意者,这一条也是孔子与子贡讨论易占,这与《要》篇十分类似,很可能来源于同一系统。刘大钧认为,这条筮例“显然是经过了后世儒生的加工,从而体现出一种‘乐其辞’的精神”。〔21〕这是可信的,因为《论衡》此篇的主旨是要说明卜筮有时不可靠,关键是在与审卦之人“失其实也”。所以《论衡》下文说“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材,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可见,对于卦爻辞的解读逐渐超过通过易占得到卦象的卜筮行为本身,易学的阐释学成为人们更感兴趣的内容,以至于原本的易占之法都逐渐失传了。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卜筮在战国时代仍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中还明言“卜筮”也是圣人之道之一。但从帛书《要》篇来看,孔子虽然表现出“信筮”的意思,但是却又不愿明白无误地将这一实情讲出,而是以“吾百占而七十当”这样比较含糊的语言来回答。《要》篇的作者特意将这段文字编排进来,正反映出易占逐渐受到挑战,但又没有被彻底放弃的真实情形。
事实上,当时应该还有不少维护易占、以卜筮之书解《周易》的文献流传。如与《要》篇抄写在同一张帛书上的《衷》篇中就有“……文王之危,知史说之数书”一句,丁四新认为,此处的“数书”即同于《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术数类书籍,“依此,则可知《周易》之作,与术数、卜筮关系密切。”〔22〕廖名春也认为,孔子说“从其多者而已”,就说明孔子也信筮,但这是顺应社会风俗,即《荀子·天论》所谓“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所以“先秦儒家重德轻筮,但并不完全否定卜筮”,〔23〕这都是很有道理的。可见,在战国至汉初,易占虽然受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其延续传统的力量,仍然具有不小的影响。
五、余论
进入秦汉以后,易占受到冲击越来越严重,逐渐被边缘化,汉代文献中出现了更多的对卜筮行为的反动。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论衡·卜筮篇》有更详细的记载:“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韩诗外传》记载这件事则谓:“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轭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现在看来,这些记载大概都出于战国至秦汉间人们的改造,正是当时卜筮行为逐渐边缘化的表现。
再回过头来看帛书《易传》,六篇《易传》基本都形成于战国至秦汉之间,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这一时期的易学发展,正如丁四新所指出的:“占筮与义理之学分流,其中象数仍贯通于二者之间。”〔24〕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易学重象数,并形成了具有汉易特色的卦气说。事实上,帛书《易传》中就已出现了卦气说的雏形,井海明指出“帛书《二三子》《要》 《衷》篇中含蕴的卦气思想与孟喜、京房的‘卦气说’是一脉相承的”。〔2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帛书《易传》在战国至秦汉易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正是易学转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