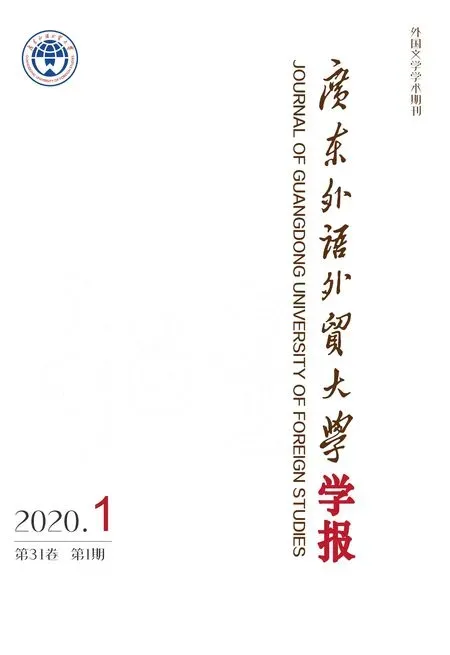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论的英译阐释与中西诗学会通
——以《二十四诗品》英译研究为例
秦中书
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话题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文论引进热潮的丰硕成果相比,中国文论面临着边缘化的局面,中西文论对话失衡。无论是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还是推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都离不开翻译阐释的助推之力。然而,“整体上说,在文论的互译上是以西译中的多,而以中释西的少。在翻译上,西方文论被大量译成汉语,介绍到中国来,几乎是应有尽有,而中国传统文论著作不可谓不丰,但翻译介绍到西方却十分有限。在阐发上,则基本是以西释中,少有以中释西者”(曹顺庆、李思屈,1996)。针对此种“失语症”,曹顺庆(2010)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当前,学科间的交融互鉴势在必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输出和对外传播理应成为文论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
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译介最早可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对《论语》等典籍的译介活动;十九世纪理雅各英译了《论语》全文,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思想也随着文化文学典籍的英译而西传;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著作被广泛译介传播,《文心雕龙》《沧浪诗话》《文赋》等传统文论经典均已有数个英译本,译者既有西方汉学家,也有中国本土学者和华裔外籍学者,中西文论的交流对话日趋活跃。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言说方式独特,文艺思想丰富,是较早被译介西传的古代文论作品之一。在梳理其百年译介史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宇文所安和王宏印的全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兼及翟理斯和杨宪益译本,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考察中西译者的翻译策略差异以及不同译本样态产生的历史文化动因,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文论英译阐释以及中西诗学会通的理解。
《二十四诗品》百年英译之史
唐末诗人司空图的《诗品》集中论述了诗歌的多样风格意境,是中国传统诗学和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品》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特殊的文学和文论价值,“上承《尚书》‘诗言志’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发轫和独立期,下启严羽《沧浪诗话》和叶懿《原诗》的高潮和完成期”(王宏印,2002:序言2),严羽的“妙悟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和袁枚的“性灵说”都能在其中找到启迪回响。原文由二十四首优美诗篇连缀而成,每首十二联,每联四言,形式均齐,音韵铿锵,“空灵疏淡,优美回环,诗句极富哲理,物象淡雅柔美”(张智中,2004)。这种以诗品诗、以诗论诗、诗论合一的独特言说方式使得《诗品》“既有诗的意境和情趣,又有论的哲理和深度”(王宏印,2002:5),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化、哲学和美学渊源深厚的传统。司空图力主“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认为诗歌应追求超脱的情致、韵味和意蕴。他通过虚实并用的手法,既将“神”“气”“真”“道”等抽象的哲学术语用于解说诗理,又以“风”“云”“水”“月”等自然物象取譬设喻,道出了诗歌再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李泽厚,2009:162)之奥妙所在。
《诗品》的英译历经百年,最早始于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一九○一年所著《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中收录的全文翻译。一九○九年,克兰默·宾(L.Cranmer-Byng,1872-1945)的中国诗歌英译集《玉琵琶》(ALuteofJade)选译了“纤秾”“精神”“豪放”“清奇”“冲淡”“典雅”“悲慨”“绮丽”“沉著”和“流动”十品。一九一六年,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以《诗品》研究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并翻译了《诗品》。一九五○年,红学家周汝昌英译《诗品》并传至欧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叶维廉节译《诗品》,杨宪益的《诗品》全文翻译发表于英文期刊《中国文学》;此外,方志彤也曾翻译过《诗品》。一九九二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译写《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inChineseLiteraryThought),其中包括对司空图的《诗品》《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的翻译和阐释。一九九四年,王润华出版《司空图诗品:翻译及评介》(SikongTu’sShiPin:TranslationwithanIntroduction)。一九九六年,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1961-)与周平编译《写作艺术:中国大师语录》(TheArtofWriting:TeachingsoftheChineseMasters),其中收录的《诗品》英译曾发表于美国的《文学评论》杂志。二○○二年,中国当代学者王宏印对《诗品》及司空图展开专门研究和翻译,成书《〈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
在众多译本中,翟理斯、宇文所安、杨宪益和王宏印的全译本颇有代表性,而宇文所安和王宏印的译本最具研究价值,充分体现了中西文论会通历程中不同译者身份主导下的翻译决策和译本样态差异。十九世纪,英国是汉学研究重镇,翟理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被称为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文学的作品,具有开山之功。该书首次让司空图进入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关注视野,但翟氏将《诗品》当作诗歌而非诗论进行译介,对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独特价值的作用有限。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汉学迅速崛起。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精深研究,用力甚勤,他的中国文学史巨著、唐诗研究和翻译以及中国文论研究系列作品在北美汉学界影响巨大。《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旨在向西方学生和汉语爱好者介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古代文论思想,该书后来成为美国多所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权威教科书,对传播中国古代文论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文译本在国内文论界产生重大影响。宇文所安(2003:335)将《诗品》视为“17世纪以来唐代最重要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作”,他沿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思路,采取“原文+译文+评论+注释”的方式解读原作。译文并未刻意遵循原文诗歌的形体特征,诗行长短不拘,不追求押韵,采用“亦步亦趋”的直译法,目的是让文本说话,展现中国文论思想的本来面目。
宇文所安和翟理斯都具有宏大的史学观念,《诗品》因各自所在的专著而获得广泛传播。翟氏首次为十九世纪的西方读者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代表了早期海外汉学家了解中国、沟通中西的美好愿望和积极尝试,其作品“填补了中英两国关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缺”(刘亚迪,2016:7)。早期中国文论以文学的形式被翻译传播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文论翻译和中西对话得以发展。宇文为二十世纪西方读者构建了中国文论史,与翟理斯时代西人仍不省中国文学的状况相比,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对话热烈、美国汉学兴盛,他对《诗品》的文学和文论双重价值均有清醒认识,其翻译具有强烈的文论自觉意识,始终以中国文论思想为核心展开英译阐释,同时会通中西视角,成功地将中国古代文论传译到英语世界,其传播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此时,西方的中国文论英译研究已进入独立自觉的阶段。
王宏印是中国当代翻译家,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和文学典籍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在分析原文的诗学、美学特征基础上,他以汉语今译和英译对《诗品》展开阐释。译文每品十二行诗按三个四行诗节排列,隔行押韵或连续两行押韵,体现了译者的用韵追求。在具体翻译中,译者体现出较强的文本操控力,句式和用词均灵活多变,化虚为实,将司空图亦诗亦景的玄奥之语转化为诗意、诗境和诗艺的直接表述,译文中多次出现“poetry”“poetic flavor”“verse”“style”“composition”“craftsmanship”“image”等与诗歌创作相关的词汇。正如郑振铎等人曾对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选录司空图颇有微词的情形一样,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人对传译包括《诗品》在内的古代文论的价值普遍重视不够。王宏印的《诗品》翻译研究彰显了传播中国文论的目的,其汉语今译和英语翻译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读者意识。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对《诗品》的英译阐释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中国文学》因历史原因而停刊,中国文论也并非其译介重点,因此杨宪益的《诗品》译文甚少有人关注。随着重建中国文论研究的深入,文论英译阐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王译《诗品》是新一代学人重估古代文论价值的一个例证。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任重道远,《诗品》的英译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缩影和个案,由此引发诸多翻译思考。如何开展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发掘整理和英译传播?译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有效地促进中西文论对话?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十四诗品》英译策略之异
(一)品名的翻译
《诗品》“诸体毕备,不主一格”,品名是司空图的高妙之处,以汉语二字词语提炼各品风格意境,简约中蕴涵深意,用语虚实相间,兼具抽象玄虚与形象可感二重特点。此外,诸品含义多交叠类同,如“绮丽”与“纤秾”“劲健”与“雄浑”。以上种种,均是翻译难点。
对于品名英译,早期译者多“以词译词”,译文简洁但恐失之准确。研究型译者宇文所安和王宏印的品名译法则有了较大改进,但二人又有明显差异。宇文对汉字的巨大组合功能极为敏感。除少数几品外,他大量采用分拆译法,辨析每个字的具体含义,以名词和形容词为主,采取并列或偏正结构进行翻译,如“雄浑”(potent,undifferentiated),“冲淡”(limpid and calm),“纤秾”(delicate-fresh and rich-lush),“绮丽”(intricate beauty),“飘逸”(drifting aloof)。该译法的优点在于汉字间的微妙差异得以凸显,但却又因语义过于实切而与原文内蕴多有出入。中英文语义差异加上文论风格的抽象含混使得译文难与原文完全对等。
王宏印(2002:82)从译诗角度出发,认为“英诗的标题不适合用抽象术语,尤其忌讳组诗众多标题的单调和统一”,与宇文式的拆字译法不同,其译文不拘泥于原文的词语形式,通过提取诗中的主旨思想另铸新语,标题与诗行内容往往形成呼应,如译文“with some words,ready for composition”与品名“沉著”(ready for composition)直接对应,“telling,but not saying,and do it with a crack style(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阐明“含蓄”(telling,but not saying)之意。这种不胶着于一字一词,看似不忠实的翻译却能激发读者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让人耳目一新。
(二)译本注释与译者文本观
《诗品》与中国古代美学、哲学存在较多互文性,如“畸人”见于《庄子·太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者也”,“黄唐在独”见于陶渊明《时远》诗:“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劲健”源自《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西文学交流初期,文论翻译尚未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翟理斯和杨宪益的译文注释较少,而对中国文论文本进行翻译和阐释相结合是宇文所安和王宏印专著的最大特点。“作为对文本意义的一种理性认知与审美体验,阐释活动不仅融汇着文本接受者对文本既定意义的客观再现、理论提炼及其价值评判,同时也蕴含着接受者自身基于文本意义之上的思维意识乃至情感层面的主观拓展与能动创造”(王婉婉,2018),译者因此有更大的空间对原文中的关键词进行详尽注释。宇文尤为重视注疏传统,认为注释是补救译文的良策,其译文总体倾向于直译,注释繁复,一个词语常常列出多个注家的解释及自己的见解和疑问。对于语义含混之处,他会向读者坦诚以告,将文本置于一个开放的阐释空间;同时,他将西方文论术语用作参照评析,这种与读者对话、中西互照的阐释模式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观。王宏印(2002:69)主张“从文本注释和翻译入手,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意见而进入作品。只参考各家注本做文字解释,从中发现语言线索、文本结构并注意体悟诗人的思想、风格和一般倾向,不轻易扩充发挥,也不轻易下结论。保持文本的开放系统和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宇文不谋而合,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司空图,他在参照其他互文解释的基础上也对原文进行了充分的注释,但与宇文考据式的释读不同,王译及注释更多地体现了他作为阐释者和译者的理解自信。
(三)译本人称的使用
《诗品》中隐而不显的人称所指究竟是什么?是作者、理想的诗人、诗中描述的对象、读者还是兼而有之?人称是翻译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汉语诗歌中人称代词使用较少,有时通篇不见“人”,但丝毫不影响诗意传达。译文中人称的选用取决于译者的观察视点,也决定着诗人、读者、诗中人物等各主体间的亲疏关系。《诗品》各译文中三种人称均有涉及,但不同的译文各有侧重,其深层原因是译者对司空图诗学观的理解疏异。
宇文所安具有强烈的英汉对比意识,在保存原文句式的基础上,不刻意追索确切的人称所指。他认为“译文往往具有欺骗性:英文要求我在祈使语气和陈述语气之间,在主语‘他’与主语‘它’(文本)之间,在并列句与条件句之间做出选择。以上种种选择在汉语中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往往可以随意游移,同古代汉语常见的情况一样,它们往往真的是无关紧要的”(宇文所安,2003:334)。但另一方面,他仍摆脱不了主客二分的英式思维,代词“one”的使用便是一例,在“返虚入浑”(Revering to the empty brings one into the undifferentiated)和“遇之匪深”(One encounters this not hidden deeply away)中均以“one”为行为主体。第三人称“he”是宇文使用最多的,如“In air he stands long in spiritual simplicity”(虚伫神素),“He drinks of the pure,/feeds on the forceful”(饮真茹强)。第三人称用于指代司空图论诗中的理想诗人,这种客观明晰化的表达方式与汉语诗歌“不隔”的效果似有出入。由此可见,宇文的英式思维和他对《诗品》的独特理解构成了译文丰富的人称变化(they,one,he等)。
与翟理斯一样,王宏印较多使用第一人称以强化《诗品》的创作论观点,译文气势恢宏,体现出强烈的主体创作意识,如“I am ONE with the universe,/And everything is at my serve”(真力弥漫,万象在旁),“My eyes sweep the world./My mind marches unhindered”(观花匪禁,吞吐大荒)。以第一品“雄浑”为例,通篇以“I”主导行文,充满动感,描述诗人积极追求诗艺中如何从万物周遭获取能量的过程,“Zest for Poetry”较好地概括了二十四品的主旨;同时使用“the poet”点明主旨,补充人称缺省,将语义明晰化。
(四)术语和典故的翻译
《诗品》是一部道家艺术哲学著作,以道哲为指导,论述了二十四种诗境风格之美(郁沅,2011)。作为晚唐诗人,司空图跌宕起伏的一生见证了唐朝的衰亡过程。他晚年托病去职,遁入中条山王官谷,徜徉山水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其人生哲学中浸润着丰富的老庄思想。
古代文论家往往感时伤怀,将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感悟和文学创作融合熔铸,“司空图则显然继承了老庄的文道观,写出了著名的《二十四诗品》,大力倡导符合于自然之道的冲淡自然之文采”(曹顺庆,2010:60)。《诗品》借用道家术语来描述玄妙的诗学理论,由哲学术语衍化而成的文论范畴有“道”“真”“气”“神”“象”等。先秦本体论哲学以“道”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杨星映,2011),“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荀子·哀公》),“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系辞》),《诗品》与之相关的表达有“由道返气”“道不自器”“大道日丧”“俱似大道”“少有道气”等。“道”被译为“Tao”(翟理斯),“the Way”(宇文所安,杨宪益)和“the Great Tao”(王宏印)。
文论术语在涵泳中不断获得新意。宇文所安尤为重视术语,在译文中力图保留术语的本义,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译文,书末所附“术语集释”便于读者随时检索查阅,加深对术语的理解。对于含义丰富、难以诠释的术语他则采用汉语拼音加注释来表达,如“qi” (气)。此外,他的译文时有创新,独具匠心,如“The Way is not bound to vessel-shape”(道不自器)将“器”的本义完全展现出来的同时不乏新意,“妙造自然,伊谁与裁”中的“自然”指一种纯然状态,译文“It subtly produces the So-of-itself(自—然)”中的复合词“So-of-itself”虽难与原文完全对等,但可激发读者联想。
王宏印的译文颇为灵活,不拘泥于字面意义,具有道哲学色彩的词汇“真”或“道”并无固定译法,而是结合上下文作变通处理,将意义内化后重铸新词,译文意蕴深刻,如“饮真茹强”译为“Great Nature nourished his physique”。“Take the way that nature goes,and /Draw on its source and make it surely yours”(俱道适往,著手成春)指出了诗人吸收自然灵气化为自我创造力的过程,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深刻理解。
对于典故,宇文所安以直译为主,并在解说部分补充说明文化内涵,王宏印则采取直译加注释的处理方式,旨在给读者提供详尽的文化背景知识。为求“可接受性”,翟理斯运用归化手法,将“God”“salvation”“leviathans”等词语用于解释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诗境诗意与自然造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将中国哲学思想术语转化为具有西方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词语。
《二十四诗品》译本差异之因
翻译是目的驱使并受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和诗学规范所制约的跨文化活动,译者行为和决策服务于某种翻译目的,并遵循相应的翻译规范。作为汉学家,宇文所安以向西方读者介绍“异质文化”中的文学思想为目的,尽力展现原文本面貌,传译中国文论精神。他倾向于“充分性”的翻译,以文本为核心,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翻译和阐释《诗品》,提供了一个在中西诗学关照下产生的译本,其翻译策略与翟理斯颇为不同。翟氏的《诗品》译文流畅,诗味浓,抒情性强,但论诗成分不及其他译本深入,有的诗行充满浓郁的西方宗教色彩。受历史条件、英国汉学发展状况和西方诗学的影响,这种“可接受性”的翻译追求是早期汉学家译介中国文学的必然选择。
对原文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尊重使宇文认为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译文往往具有欺骗性”(宇文所安,2003:334)。他对《诗品》中的玄妙神秘与命题式表达之间的悖论有深刻认识,当翻译无法传达原文的多义性时,注释和解说便成了他的法宝。其译文后的阐释不是告诉读者一个确定不移的答案,而是不断提出在浩瀚的注疏传统中译者的理解和翻译缘由,引导读者思考和判别。阐释中不时出现西方诗学概念,但他只是将之作为参照以对比中西诗学异同,并不是用西方理论框架来硬套中国思想。宇文在处理文本时的细致和耐心令人钦佩,在“典雅”一品中,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诗中多个季节特征的描绘,因此将“书之岁华”翻译为“He writes down the seasons’ splendor”,其体察微妙之境的功力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杨宪益、翟理斯的“season”和王宏印的“wonderful hour”不及宇文的翻译。“阐释既是对历史的还原和对传统的回归,也是一种现代的发现,是让传统的东西进入到当代人的视野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毛宣国,2017)像宇文所安这样具有深刻的文论批评意识的译者是中国文论焕发生机的幸事。
翻译家王宏印对司空图《诗品》研究的主要动因是让读者领略中国古典文论的风采,同时通过翻译传播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他视野开阔,在有意识地批判取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诗学、文化学、解释学等跨学科的方法来开展“翻译型研究”“阐发性研究”(王宏印,2002:序言4),对司空图其人、其事、其诗都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他关于司空图的文化人格模型,《诗品》的美学、文学特征和价值的诸多论断可谓精辟中肯。对于《诗品》的核心思想,王宏印取综合之意,译为TheRealmofPoetry,即“诗歌境界”,应该是比较正确的理解。
就翻译而言,王宏印具有开放的现代翻译观,同时采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种手段来解读《诗品》,以今译和英译对照补充,强调译文的“现代气息”,认为“英译是原文本的延伸或转换”,是“加深对原文的现代认识”的重要方式(王宏印,2002:70-71)。重视文学性的翻译效果也是其关注点,他认为文学性研究要求在翻译上至少要“以诗译诗,译诗像诗,诗中见论,论仍然是诗”(王宏印,2002:4)。译文遵从英语诗歌形制,但内容上却化含蓄为明晰,与原文诗学规范迥异,译者主体性得到彰显。虽用词简洁,但语气强烈,词语色彩饱满,句法灵活,有“脱胎换骨”的效果,这种“创造性背叛”翻译是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必然结果。王宏印之所以在翻译中凸显诗人主体性与他重视司空图的诗学本体论以及诗人个体道学修养不断进阶的三个阶段不无关系(王宏印,2002:24)。同时,他是一位有明确翻译目的和自觉反思的译者,将原诗、今译和英译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中文与英语的在诗歌中的用语规律和变化趋势。“传统话语需要在进入现代的言说中完成现代化转型”(曹顺庆、李思屈,1996),王宏印的阐释与翻译兼具“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体现了古今、中西的对话精神。
结语
译者总是遵循一定的翻译规范。“‘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极处于一个连续体中,因为没有哪一种翻译是绝对‘充分性’或‘可接受性’的”(Munday,2012:173)。译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循相应的翻译目的做出翻译决策,从而产生不同的文本样态。研究型译者宇文所安和王宏印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的选择差异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烙印。宇文以呈现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为出发点,以文本为中心,以中西文论对话为论述方式,以译文“充分性”为翻译策略,探讨《诗品》的文论思想内涵,为读者打开了广阔的解读空间。王宏印以传播中国文论为出发点,以文学性传译为重点,以古代文论思想的当代阐释和翻译为论述方式,兼顾译文“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探讨《诗品》的当代文学和文学思想价值,不断深化前人研究。
继翟理斯顺应西方文化和诗学传统,体现“可接受性”的《诗品》翻译之后,宇文所安对《诗品》的研究式翻译着力再现原文的“充分性”。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国汉学家,他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和学术修养,其文论翻译实践表明二十世纪末叶西方汉学家已形成更为开放和多元的文本观和翻译观,见证了中西文论进行更为深入对话的可能性,即“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宇文所安,2003:序言5)。两代汉学家的文论翻译之异无疑体现了中西诗学交流会通的发展历程。当代翻译家王宏印秉持“翻译之法就是师法自然”(王宏印,2002:103)的观点,译文灵活多变,不取诸形,突出诗人创作主体性的发挥,较之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倾向于保守的译文具有更强的阐释力。中外译者对《诗品》的阐释和翻译是中国古代文论翻译传播的一个历史缩影,从中可以窥见西方汉学如何不断深入发展,中西诗学会通之下对原文的不同阐释方式,不同时期文论传播效果等诸多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是一座宝库,其阐释和英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研究课题。陈伯海提出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的方法论原则是“双重视野下的双向关照与互为阐释,既要站在西方和现代的角度,用新的观念审视中国的传统,更要回过头来,立足传统本位以反观西方和现代”(徐俪成,2017)。这一方法正是宇文所安和王宏印两位译者对《诗品》进行英译阐释时不约而同的选择,《诗品》英译研究是中西诗学会通的极好范例。由此可见,比较中外译者的翻译决策和译文样态差异能深化对中国文论的理解,由研究型译者开展跨学科视域下的翻译阐释是中国古代文论传播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