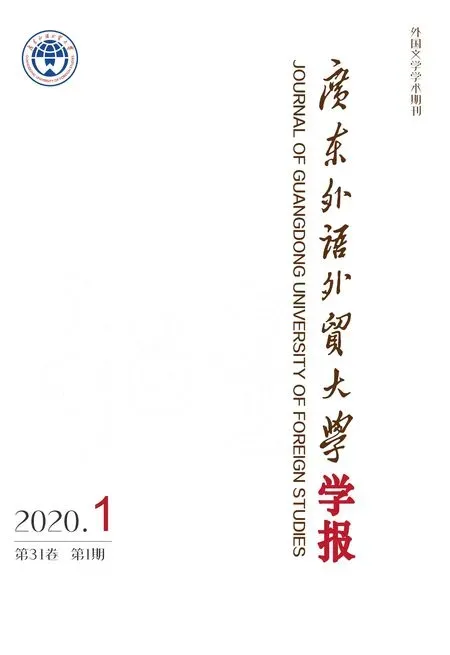伊拉克战争悼歌的回响
——评艾哈迈德·萨达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
任宏智
引 言
二○一八年正值美国入侵伊拉克十五周年,这场现代战争史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入侵将伊拉克推入无底深渊。回望近些年的世界文坛,一批以此为题材应运而生的战争文学作品悄然进入大众视野,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如美国作家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的《黄鸟》(TheYellowBird)突出个体生命的战争遭遇,揭示战争的残酷与无意义;菲尔·克莱(Phil Klay)的《重新部署》(Redeployment)凸显士兵的疏离感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这些作品成为美国战争文学的一个全新分支(吴宏宇,2015:39)。它们无疑都以伊拉克战争作为叙事背景,以创伤叙事、后殖民主义研究、历史研究等为范式对这场二十一世纪的中东之殇进行文学再现,探讨当代人的异化与疏离、社会的无序与病态等深层问题。然而,上述作品大都以入侵者视角和战争具体执行者的叙事声音进行叙述,从战争进程主宰者的视域聚焦并反思有关生命、死亡、国家主权、全球化正义等涵旨。放眼处于战争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一批仍坚守家园的伊拉克作家正以超现实主义笔法、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视角对这场讳莫如深的灾难进行生命书写。艾哈迈德·萨达维(Ahmed Saadawi)便属其中翘首。一九七三年,艾哈迈德·萨达维出生于伊拉克萨德尔城一个什叶派聚居的贫民窟,大学毕业后便投身写作。早期文学作品多为诗歌散文,内容主要描写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两河流域人民的生活。二○○三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维审时度势,以战争和伤痛为主题创作小说,抨击人性的自私贪婪、伊拉克当局的昏聩颟顸、美军的凶虐残暴等现实,陆续出版“伊拉克三部曲”——《美丽国度》(TheBeautifulCountry)、《他在做梦,游戏,或死亡》(HeDreamsorPlaysorDies)和《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美丽国度》于二○○五年荣获迪拜阿拉伯小说一等奖,《他在做梦,游戏,或死亡》使其入选二○一○年英国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 of Literature &Arts)四十位杰出阿拉伯青年作家名单。二○一七年,他继续以战后伊拉克局势为题材创作并出版小说《涂鸦之门》(TheChalkDoor)。《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inBaghdad)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多元的叙事主题获二○一四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阿拉伯布克奖”——“The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并被翻译成十七种外语译本,其英文译本入选二○一八年国际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短名单,这也是历史上首部入选该奖项的阿拉伯国家小说。
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的写作灵感源于英国科幻小说之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经典之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故事源于二○○五年巴格达城内发生的一次爆炸,居住在该城的拾荒者海迪从爆炸现场收集人体残骸,并拼装成一具完整尸体。之后,一个无处可归的游灵进入尸体,令其“复活”并拥有了不死的能力。海迪(Hadi)将其称作“西斯麦”(“The Whatsitname”,伊拉克方言中意为“他叫什么名字”),当局给其编号为“罪犯X”,更有人直接称其为“弗兰肯斯坦”。复活之后,面目丑陋的怪物开启了他的复仇行动,誓言要向杀害组成自身每一个器官的恶人索命。死亡、暴力、血腥、荒谬、怪诞充溢于字里行间,引得读者不禁发问:作者为何要通过雪莱笔下的“科学怪物寻仇”为叙事模型来建构伊拉克战争问题之界阈?作者如何以被入侵者身份和战争亲历者视角回应西方“他者化”的主流战争语境?小说指涉的叙事意蕴以及伊拉克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境遇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有助于对本土伊拉克战争文学有更深刻的认识。
伊拉克新生代作家的群体书写
纵观伊拉克近现代文学发展史,诗歌一直占据着文学表达的主流形式(仲跻昆,2010:723)。二十世纪初,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伊拉克文坛应运而生了一批以鲁萨菲(Rusaffi)为代表的新古典派诗人,他们沿用古诗的模式抨击新的社会问题。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一批新生代诗人不断涌现,他们以现代派的手法描绘中东动荡的局势和令人担忧的社会状况。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伊拉克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许多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迹于九十年代的伊拉克作家或固守家园,或流散至其他国家。后者虽羁旅异国他乡,但用笔端抒写着对故土的眷恋,在与异国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中心系祖国命运的跌宕。二○○三年美军入侵伊拉克,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历史创伤,两河流域旁的文明沃土顷刻间化为了一片连贯冲突区域。而与此同时,战争的炮火声也唤醒了作家的民族意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真实的素材。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政界对文学创作的干预逐渐式微,许多作家开始尝试触及不同题材,伊拉克文坛应运掀起了一股“战争小说”创作潮流。萨达维在回复笔者的邮件访谈中,介绍了伊拉克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背景:“我正属于这一类作家,我们从九十年代中叶开始创作,十年后,也就是二○○三年前后,我们的作品陆续开始发表。虽然诗歌历来都是伊拉克民众乐于阅读的文学体裁,但当今的伊拉克小说创作更需要一种开放的环境,一种远离政局观点的对历史的全新解读。”①
二○一○年底,“阿拉伯之春”以强劲势头席卷了多个阿拉伯国家,而幸免躲过一劫的伊拉克却仍在美军入侵带来的伤痛中反思。从外部来看,伊拉克数年的民主化成果以及政治生态相对良性发展是度过此次浩劫的一剂良药,但在伊拉克内部,敌对的民兵组织、境外武装集团均以人民的代价谋取私利,时局稳定遥遥无期、恐怖主义泛滥和教派仇杀的愈演愈烈使得伊拉克民众不禁怀念起那个“不幸福却很稳定”的时代。二○一六年七月六日,英国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了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原本可以以非武力方式介入伊拉克战争,采用军事行动在当时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手段。随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为发动伊拉克战争道歉。无独有偶,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当年作为国会参议员投票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她最大的政治遗憾。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惨重的人员伤亡使得西方社会纷纷掀起伊战反思浪潮。
从两伊战争(Iran-Iraq War)到科威特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伊拉克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生活了近三十年。许多伊拉克作家立足当下,着眼于这片焦灼之地,陆续创作了一批以上述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按叙事主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以萨达姆为首的独裁政权的历史追问,如伊卜提萨姆(Ibtisam)的《镜中的他者》(TheOtherinTheMirror)、哈蒂娅(Hatia)的《爱过之后》(Afterthelove)、茵娜姆·克贾姬(InaamKachachi)的《塔沙里》(Tashari)等。《塔沙里》以伊拉克方言“塔沙里”(意为经射击后而形成的分裂状)一词为题,提喻战争对社会和个人的造成创伤,借此抨击萨达姆政权的暴虐与冷漠;第二类从人性反思和道德关怀角度对参战伊拉克士兵的战争体验和个体生命形态进行书写,但该类文学作品大多遭政府封禁,最终未能出版发行;第三类是近些年一批新生代伊拉克本土作家通过创作或翻译等方式,向读者展现后萨达姆时代和联军入侵时代伊拉克的各种社会乱象及人们长期处于伤痛、暴力、死亡、挫败的残酷现实。此类作品的数量在近些年呈快速增长态势,并屡获阿拉伯国家及各类国际文学奖项。据统计,仅二○一四至二○一八年间就有十一部伊战主题小说入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长、短名单。二○一四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inBaghdad)、《塔沙里》(Tashari)、《阿里巴巴的悲伤之夜》(TheSadNightofAliBaba);二○一五年:《拉亚姆与姬法》(RiyamandKafa);二○一六年:《枣椰树之民》(Peopleofpalms)、《脱盐水》(DecertifiedWater);二○一七年:《书贩之死》(TheBookseller’sMurder)、《尘土之日》(DaysofDust)、《卍》(Swastika)、《索引》(Index);二○一八年:《巴格达时钟》(TheBaghdadClock)。
此外,一批伊拉克裔的移民作家也将目光聚焦于伊战主题,凭借佳作在西方文学类奖项中崭露头角。旅居芬兰的伊拉克籍作家兼导演哈桑·巴拉希姆(Hassan Blasim)于二○一四年凭借其英译版小说《伊拉克基督》(TheIraqiChrist)荣获二○一四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这部包含了十四个短篇小说的合集以黑色反讽和魔幻怪诞之笔触及人类战争书写之阈限。伊拉克裔美籍作家、翻译家塞南·安图恩(Sinan Antoon)的《孤独的石榴树》(英文版称为“洗尸工”——“TheCorpseWasher”)将叙事场域置于暴力美学下,主人公贾瓦德徘徊于日常清洗充斥着死亡、恐怖元素的尸体和自己立志成为画家的艺术抱负二者之间,折射了战争背景下人的主观意愿与自然世界间的不和谐性。伊拉克裔德国作家阿巴斯·海特尔(Abbas Khider)凭借小说《一记耳光》(ASlapinTheFace)荣获二○一六年瑞士洛伊克文学奖和德国美因兹市写手大奖,作者将叙事聚焦于特定群体,以诗意流畅的语言记述因伊战而流散于欧洲的伊拉克难民形态。
显而易见,西方以伊拉克战争和九一一事件为背景创作的作品不胜枚举,而伊拉克新生代作家并非文坛名宿,其作品在销量和社会效应方面亦远逊于西方同类作品,但他们群体化、全景化、具象化、真实化的战争再现将不同的话语声音和文化背景混杂于同一空间。他们并未拘囿于同质化的语境框架,而是以多元化的创作、“他者”的角度和更为复杂深远的维度批判历史,试图打破以西方国家作为战争主宰者的单一视角叙述,为以交流沟通为媒介、以超越固有主体视角为目的的文学互通提供了有益借鉴。以《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为例,大多数伊拉克新生代作家都将西方国家的粗暴干涉,伊拉克政权的崩溃、社会失范、暴力恐怖活动愈演愈烈等现实议题浸润于伊战时代背景下,他们善于以魔幻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怪异、意识流拼贴、人物异化等后殖民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战争文学书写在伦理道德层面不可言说的藩篱。
“杀人怪物”的反叙事模型:复仇者身份的嬗变
伦理与道德规范着自然人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的“儒家伦理”和西方的“美德伦理”都处于主宰地位并影响着各自的主流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变更,作为文明社会基本尺度与依托的伦理道德之维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战争文学从诞生之初便受到读者的伦理审查与监督(但汉松,2015:33),如何在文本内部建构起能自给自足的伦理规范,并让作品中的人物在遵循这种规范的前提下表达相应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这成为战争书写的难题之一。在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中,作家并非采用西方反恐文学正典中常见的“正义战胜邪恶”的个人英雄主义模式,也未借浪漫主义之笔法弘扬民族主义精神,而是以反叙事和反伦理并行的手法另辟蹊径,以雪莱笔下充满科幻色彩和哥特风格的怪人 “弗兰肯斯坦”为原型,刻画出具有特定德行的“非正义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实现他从公众意识中的“正义人物”到“非正义人物”的嬗变,通过这种身份嬗变消解读者凭靠阅读经验和审美品位建构起的期待视野,继而引发其对小说中隐射的伦理取向进行反思。

身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从来不是完整的,而是一直处于建构中,并派生于个体在阶级、种族、性别、族群、宗教等方面(Wolfreys,2015:125)。西斯麦身份的建构与嬗变是动态的、复杂的、矛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今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局势动荡的现实诱因。西斯麦自身是杀手,同时也是被杀者;他是牺牲者,亦是复仇者。因此,他扮演了来自不同阶级、宗教、种族、性别、教派的伊拉克人的化身,正是他们将解脱与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个体之上,是他们参与并制造了这个响应时代召唤、应运而生的“救世主”,是他们不惜一切力量试图摧毁这个肆意屠戮、无所顾惜的“杀人怪物”。而小说结尾却以反讽之笔隐喻当今现实:就在七号巷民众高歌欢庆“杀人怪物”被成功捕杀之时,那个黑影(西斯麦)却躲避在高处,悠然远望这场盲目的集体狂欢。
西斯麦身份的嬗变也是战争语境下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主流话语的有力回应。在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经历了长期的独裁统治,这位中东枭雄将伊拉克拖入数次战争之中,并为此受到国际制裁。镇压、战争、起义让整个伊拉克社会财匮力尽,民不聊生。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决定以更直接的方法保障美国的中东利益。于是,美军打着“推行民主计划、打击恐怖主义”的口号强行侵占伊拉克。然而,入侵者美军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是一群不轻易屈从于他们的好战人民。在另一方,被入侵者伊拉克人民也逐渐觉知美国和西方国家并不能带来其所承诺的发展与繁荣,未能将西方民主成功移植到伊拉克。隐匿在“拯救者”“自由民主”面具背后的实则是一张贪婪、暴虐、险恶的嘴脸。这种“身份”的嬗变使美军失去对伊拉克的控制,任其走向宗派主义、内战和全面混乱。因此,西斯麦的身份嬗变隐射当下伊拉克社会混乱的现象,整个国家正如他的面孔一般,瞬息万变,难以揣摩,更如同他的代号,看似无名无姓,实则指涉深广。
污名化叙事:暴力抵抗的批判
在中西方小说叙事中存在着诸多有关道德安全的问题。例如在犯罪小说中,杀人犯以谋杀犯罪等行为宣扬他的自由道德,以剥夺无辜生命满足自身的道德快感。读者在阅读快感的影响下沉溺于犯罪满足感,并随之陷入道德迷惘。由此可见,暴力本身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字里行间充斥着暴力、血腥、厮杀、死亡、超自然等后现代主义元素。叙述者刻意不聚焦杀人罪行的残暴,反而刻意通过营造视觉化的感官体验和具象化的暴力景观渲染暴力行径。小说中的人物从自己一方的“正义”理论出发,将对方污名为“敌对方”,并为这些“敌对势力”或“非正义团体”的被屠杀找到可自圆其说的“正当理由”。
西斯麦在录音中谈及自己曾避难于一栋未完工的废弃大楼内,一些曾效忠于萨达姆政权的残兵败将慕名而来甘愿为其效劳,其中有善于制造恐怖活动的“巫师”,口舌如簧的“诡辩者”,熟谙情报搜集的“敌人”,他们各司其职辅佐西斯麦开展复仇活动。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三个疯人团伙,他们中有的将西斯麦看作是伊拉克历代以来的国民典范,有的认为他是救世主出现之前世界末日的缔造者,有的甚至认为他就是救世主,是真主安拉在尘世间的化身。于是,三股势力在各自建构的伦理内核和信念基础上不断壮大,分封割据。随着复仇活动的推进,三位助手和疯人团伙间的分歧愈演愈烈,每个人都笃信自我行为的“正义”及对西斯麦的“忠诚敬畏”,蔑视他者的“邪恶”和“背信弃义”,并打着圣战的旗号相互厮杀,但最终暴力抵抗只带来了全员阵亡:


上述“污名化”的叙事方式并未达到文学安慰生命的旨归,反而在彰显暴力美学的同时引领读者开启伦理道德的自我反思,借助凸显的伦理矛盾性、反思暴力抵抗的荒诞性。小说情节发生于二○○五年前后,这一年正是伊拉克各类武装冲突频发的一年。到二○○六年末,联合国估计大约有三千名伊拉克民众死于每月发生的宗派冲突当中(阿卜杜拉,2013:188)。教派政治在伊拉克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致使伊拉克什叶派复苏,逊尼派极端主义抬头,原本单一的政党格局被打破,地方政府和部落领袖拥兵自重,满目疮痍的伊拉克瞬时化为一个缺乏国家民族概念的真空体。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势力试图将反美斗争转变为内战,于是形成了民族、教派、党派等内外因素相互交杂的利益集团。各方都围绕权力、资源配置、话语权、政治影响力进行博弈,各类袭击、绑架、自杀式爆炸层出不穷(刘月琴,2007:177)。他们中有的根据大相径庭的评定标准判断同一事实,将他者视为敌人,视复仇为理所当然的理由;有的则打着宗教的旗号,引经据典为他们的暴力行径开脱,认为“他者”(其他派别)都是应被铲除的异端,只有通过暴力抵抗与战争冲突才能击垮敌对势力的威胁和挑衅。放眼今天的伊拉克,如今游走着多少嗜杀成性的极端组织,从伊斯兰国集团到效忠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兵组织,各方均以暴力抵抗作为战争筹码。实际上,暴力是荒诞的,个体对群体暴力负有无可回避的责任,群体暴力最终只能催化全盘阵亡,“以恶制恶”只能变本加厉地导致更惨重的伤亡。
创伤叙事:探寻个体创伤的可言说性
在西方主流话语的导向下,这场作为美国反恐战争框架下的拉锯战似乎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当今的伊拉克却仍未摆脱伊拉克战争余震的影响。自杀式爆炸的频发、恐怖袭击愈演愈烈、教派冲突的泛滥、执政者的专制昏聩、外国势力的强行干预等现象早已成为当今伊拉克社会的现实写照,“战争”逐渐演变成为伊拉克在内的部分中东国家的代名词。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来自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共同遭遇某些可怕的事情并因此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烙印在其族群意识之中,成为永远的回忆,若是遭受创伤的群体,将其遭受的事件重新整理并加以诠释、述说、传播,形成一个集体的记忆、集体的苦难,就是文化创伤”(曾艳钰,2014:6)。在伊拉克战争话语体系下,创伤的建构不仅需要以美军为首的战争发动方参与,同时也使得战争受害方中的生命个体进行必要的承担和体验。战争给一个国家民族带来的文化创伤是难以言说的,战争文学因其题材的残酷性和极限性更是饱受诟病,但文化创伤因其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的特点,还需要创伤者探究苦难的存在和产生的根源。西方众多的伊战主题作品更多将焦点集中在美国士兵创伤的书写,而对于伊拉克集体发声和个人创伤话语却置之不理。因此,萨达维在内的伊拉克作家试图承担起言说的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发声,在虚构作品中探寻个体生命创伤的可言说性。
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在宏大叙事背后聚焦战争创伤对众多边缘人物个人领域的渗透,通过营造一种哀鸣式的“众声喧哗”景象,赋予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反思与关照,以考察在暴力政治空间下个人创伤言说的可能性。在伊拉克战争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着变化,一种隐约的孤独感和莫名的恐惧感隐匿在每个伊拉克人的内心。基督徒老妇人伊莉舒(Elishva)得知儿子血洒战场后,终日蜗居在破旧房屋内,时而以猫为伴,时而与神私语。身居国外的两个女儿担心母亲安全,欲说服其移民国外。于是,教堂的固定电话成了女儿们了解母亲的唯一渠道,老妇人也终因这种拘于形式的关切拒绝通话。无奈之下,女儿们只好让外孙乔装成失散多年的儿子,以此为策诱骗其移居国外。除了孤独无助与亲情淡漠之外,每个伊拉克人都活在焦虑与恐慌之中,日常生活中弥漫着一种普遍存在的威胁感:调查局局长苏鲁尔担心因侦破案件失利而无法获得当局赏识;海迪担心自己一手制造出的实验品非但未能替他报仇雪恨,反而悍然“弑父”;房屋中介商法尔吉(Faraj)觊觎老妇人寓所多年,终日担忧当地文物保护组织将其收回充当国家财产;安全部门更是对刀枪不入的西斯麦头疼不已,于是刻意地为各类悬疑案件的侦破寻找开脱的理由。在这种焦虑、恐惧心理作祟下,人们互相怀疑猜忌,人际关系冲突不断,亲情、友情等伦理关系不断地异化与扭曲。这场战争带来的冲击不仅改变了伊拉克的发展轨迹,甚至破坏了整个民族的内在气质和精神状态,使整个民族偏离正轨,让其重蹈“西西弗斯”式的悲剧,在受辱与挫败感中无限重复,在人的内心呼唤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对抗。在二十世纪初,当伊拉克人奋勇抗击英国入侵时,他们仍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而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和悲观主义(阿卜杜拉,2013:174)。延续千年的灿烂文明在十余年的战乱中衰落式微,伊拉克人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更是罄尽无余。当许多伊拉克人面对这场举国之殇时,不禁怀念起那个“不幸福却很稳定”的时代,有的甚至觉得伊拉克如今需要一个萨达姆式的枭雄才能平复眼下的乱局。
除了创伤建构的外部因素外,小说也试图从内部视角展开寻找,对伊战背景下的政治社会症结进行思辨性的历史反思。在政治层面,以调查局局长苏鲁尔为例,他代表当今伊拉克政坛的精英阶层。萨达姆时代,他曾供职于伊拉克军情处。美军入侵后,他在围剿复兴党运动中侥幸生还,后在美军设立的调查机构担任要职。一心谋求晋升的他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介入西斯麦事件,但最终却被美军逮捕入狱。这正印证了后入侵时代的伊拉克政坛对局势的盲目乐观和过度自信。战后伊拉克最高权力从逊尼派转移到什叶派,政权由民族主义政党转移到宗教政党手中,这种转变本质上只是“施暴者”与“牺牲者”两种角色的轮换更替,二者为实现各自政治抱负互不妥协。《真相》报原主编阿里·巴希尔(Ali Bashir)代表伊拉克的中间阶级。伊战爆发后,整个伊拉克社会处于崩溃边缘,他有意扶持年轻记者马哈茂德(Mahmoud al-Sawadhi)当其接班人,并暗地私吞国家财产,最终逃匿国外。他在时局动乱中谋求私利,并成为乱世中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中间阶级利用各种犯罪活动进行某种形式的原始积累,阶级属性也逐渐发生转变。记者马哈茂德代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仍怀有信念的年轻人。他原本在家乡一家小型报社任职,但因发表了一篇讨伐当地黑恶势力、宣扬社会公道的文章而惨遭诬陷,于是被迫迁往巴格达,并在《真相》报业集团担任记者。后因报道西斯麦事件而获主编赏识,于是事业平步青云,并有幸结识了主编情人。在他看来,是上天的公道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而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主编以参会为由卷走亿元公款潜逃,他也因沉溺于事业光环和女色之中无法自拔,最终滑入深渊。他曾笃信乌托邦式的“公正”——法道、天道和世道,但欲望的恶爪却将他从幻想拉回到了现实的泥沼中。面对这样的社会,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再次受到拷问:对与错、善与恶、是与非究竟如何判断?人们都在用自身标准衡量别人,要求社会,至于标准本身则无法衡量。
结语
伊拉克文坛新秀艾哈迈德·萨达维的经典之作《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以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叙事模型批判恐怖暴力语境下的伊拉克政治社会现实,从战争受害者——西方入侵者眼中的“他者”角度出发,给予个人、家庭、社会等层面的反思与关照。随着一批伊拉克本土作家的陆续发声,伊拉克战争文学不再仅由西方主流话语所垄断,他们以更聚焦、更全景、更具象和更客观的维度对伊拉克战争进行文学再现,并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规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同类作品呈现出的话语单义性和语境阙失等问题,从而为伊拉克战争的批判与反思吟奏出东西方共鸣的和谐之音。
注释:
①笔者曾与小说作者本人艾哈迈德·萨达维就创作主题等内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本文中所引部分为二○一七年的访谈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