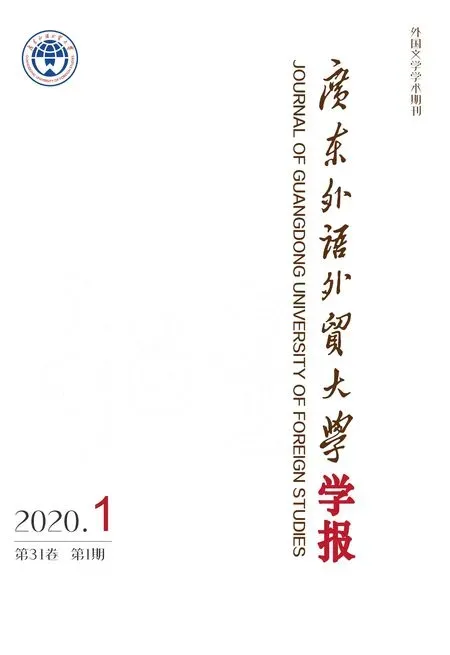歌曲翻译研究:基本范式、理论框架与前景展望
方仪力
引言
歌曲在音乐学中指“有伴奏无伴奏的短的声乐作品”(肯尼迪,2001:1096),包括歌剧、德国艺术歌曲(Lieder)、法国歌曲(Melodies)、民谣、流行歌曲、音乐剧(musicals)等多种类型。歌曲翻译研究是对上述各类型歌曲现象展开的系统研究。二○○八年以来,歌曲研究领域发展迅猛,形成了以彼德·洛(P.Low)、克劳斯·凯恩铎(K.Kaindle)、约翰·弗兰森(J.Franzon)、玛尔达·马特奥(M.Mateo)等学者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世界知名出版社争相推出相关专著,包括《译者》(TheTranslator)、《视角》(Perspective:studiesintranslalogy)在内的重要译学期刊亦推出专刊,更有专门网络空间如www.translatingmusic.com为学者、译者和传媒业提供在线资源。歌曲翻译研究正逐步摆脱过去边缘研究的地位,表现出对象多元、目的多维、方法多样等特点,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全面审视相关研究,系统梳理这一特殊翻译领域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和视角,明晰其内在问题,对推进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语言至上”还是“音乐至上”?——歌曲翻译之基本范式考察
早期歌曲翻译研究始于音乐学内部。一九一五年,《音乐季刊》(MusicalQuarterly)刊发音乐学家施佩特(S.Spaeth)的论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相关研究。论文从音乐和语言两方面讨论了歌曲译者受到的双重限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一九六四年,著名诗人奥登(W.H.Auden)发表“关于音乐与歌剧的随笔”“歌剧唱本翻译”两篇被译界整体忽视的经典论文。奥登从诗人和译者的双重视角,解析了歌剧翻译中存在的语言唱本诗性和音乐“即时性”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为后续讨论奠定了基本框架。综观之,迄今为止关于歌曲翻译的相关讨论主要围绕“语言至上”(logocentrism)和“音乐至上”(musicocentrism)两种观念展开,形成了不同的范式分野。两大范式下,学界围绕歌曲翻译的本体为何,如何理解诗性、音乐性、歌唱性、表演性等抽象概念,兼涉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历史语境、模态与媒介限制等多个视角,形成了对象多元、目的多维、方法多样的研究态势(见表1)。而这些多元视角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意义中心”还是“音乐中心”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研究问题以及歌曲翻译目的、策略、标准和解决相关问题的理论框架等也存在差异(具体参见后文)。

表1 歌曲研究基本范式
(一)音乐至上:以“音乐性”为翻译对象
“音乐至上”的观念强调音乐性,将音乐性视作歌曲翻译的主要目的。“极端”的理论家如兰格(S.Langer,1953)将音乐凌驾于语言之上,认为译者应使用“同化”策略(assimilation),用音乐吞噬语言,彰显原剧的音乐性。“温和派”理论家如奥兰多(F.Orlando,1975)却强调音乐与语言的配合,认为音乐所具有的假设性意义有赖于阐释者阐释,语言的意义影响音乐话语的阐释和表达,但诗性的材料应该与音高、音强、音长、音色、节拍等音乐结构配合。无论是同化论还是配合论,“音乐至上”的观念总体认为译者的策略选择是由歌曲的音乐性决定的,译者所受的限制不仅在于音乐结构,同时也在于原作语言结构的音乐性,对音乐性的关照应成为译者的主要任务。
以歌剧翻译为例,阿皮塔等人(Herman,1991)将语言的音乐性作为研究对象,将歌剧翻译目的描述为“翻译唱本应保留原剧中的戏剧、诗歌和音乐”,提出译者翻译时必须考虑原作韵律、节奏、音响和重复四大因素,强调“音符对音符”“重音对重音”等策略。国内学者傅显舟(2012)在分析音乐剧翻译时提出了“语音近似”原则。他认为歌剧唱词应该在“韵律节奏、音节数目、元音辅音”三个方面与原剧相似,译者可保留原曲,用目的语适配原曲。而在孙慧双(1999:304)看来,歌剧翻译仅仅是“译配”,译者还需具有“音乐功力”。所谓的“功力”在特拉文(Tråvén)看来,是关于“音乐和修辞两方面的丰富知识”(Gorlée,2005:118),当语言与音乐联系在一起时,歌剧的意义已经让步给音乐性,成为主要的翻译对象。
“音乐至上”的观念在核心概念表述上亦有所反映。包括《牛津在线手册》和《翻译研究手册》在内的翻译研究工具书常用song translation指称“所有类型歌曲翻译”,但在现行刊物中,不同学者使用自拟关键词以表达其关于翻译对象和目的的独立见解。格伦布(H.Golomb)提出“音乐翻译”(music-linked translation),认为该术语能体现语言对音乐的配合(Gorlée,2005:121);彼德·洛(P.Low,2008)使用“歌唱翻译”(singable translation),认为该术语更能突显译作的韵律;阿皮塔(Apter)和赫曼(Herman)以《以歌唱之名翻译》(TranslatingforSinging)命名其新著,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后的歌曲必须具有歌唱性。汉语语境中的常见术语有“歌曲翻译”“歌词翻译”和“歌曲配译”。其中,“歌曲翻译”概念强调歌唱性,“歌词翻译”注重歌词的语义内涵,由歌曲翻译家薛范(2002)首创的“歌曲配译”强调音乐性。概念使用的不同显现出译者和研究者的目的、立场及视角存在差异。
不过,韵律、节奏、音高、音强、音长等因素都只是音乐性的外在表征。当音乐性和语言联姻时,如何阐释“音乐性”这一概念似乎也成了问题。纽马克(P.Newmark,2013)的遗作“翻译中的艺术歌曲”从普遍主义层面对此做了相关说明。纽马克(Newmark,2013)首先否定了音乐的意义来自特定社会和文化,对他而言,音乐是自然的表征,有作为普遍语言的自为性。因此,在艺术歌曲翻译中,语言与音乐的联姻在本质上是对人文主义的迎合,一方面通过语言的诗性表现音乐的丰厚、深沉和个人感受,另一方面通过音乐增强语言中的诗性。文本中诗性的内容被融入音乐的肌理中,突出了原作的普遍主义意义。纽马克对音乐性的界定否定了艺术歌曲歌词所具有的文本或文化意义,也再一次说明,当歌曲翻译以“音乐性”为目的时,对原文本的理解或与语言的确切意义无关。
(二)语言至上:以“意义”为翻译对象
“语言至上”的观念以语言意义为圭臬,提出音乐为语言意义让步,将意义的转移和重构视作歌曲翻译的主要目的,凸显了唱本或歌词的意义转换问题。在语言成为构建确切意义的唯一方式之后,影响意义转换和生产的文本内外因素成为新的研究对象。
在国内歌曲翻译研究中,围绕歌曲翻译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歌词的语义“忠实”展开的。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国际歌》翻译讨论正是这一领域的典型。一九二三年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发表在《新青年》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九五九年,《人民日报》刊发“国际歌的故事”,引发了围绕“国际歌”翻译的激烈讨论;一九六二年经过重新审定后的歌词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多名学者撰文讨论该歌曲的翻译,讨论聚焦在歌曲译者的身份和重要概念的翻译两个问题上。论者运用翻译学和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充分说明歌曲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国际歌》的译介被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译者对诸如“起来”“受苦的人”关键概念的翻译反映了译者对中国政治主体的不同认识。显然,歌曲翻译与文化史的结合,为歌曲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阈。
无独有偶,近年来英语世界亦出现了针对歌词背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二○○八年,《译者》(TheTranslator)杂志组织的《音乐与翻译》专辑主编萨拉加瓦(.Susan-Sarajava,2008)彻底否定了此前部分学者在单纯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呼吁学界从目的语系统中的社会、文化、语言实践中理解歌曲意义,认为“从更宏观的视角考察翻译与音乐才是翻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事实上,当下音乐学、文化研究和音乐人类学领域开展的音乐属性和身份认同研究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助益,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歌曲音乐的文化属性和歌词翻译的社会文化意义上。
翻译在本质上是得失之间的博弈,歌曲翻译也不例外。正如阿皮塔与赫曼(Apter、Herman,2016:17)两位学者指出的,“想要面面俱到地保留原作的方方面面就像给翻译套上紧身衣,无法从中产生好的译作”。当保留歌曲音乐性成为首要的翻译目的时,歌曲翻译的重心被放置在语言的韵律、节奏、强弱上,歌词需根据音乐而调整,翻译策略也围绕这一目的而制定。当歌词受到译者关注后,歌词和旋律的音乐认同和文化记忆成为研究对象,歌曲翻译将现实的符号与虚构的文化空间紧密结合在一起。
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研究——歌曲翻译研究理论框架反思
如果说上文对既有歌曲翻译研究中音乐至上和语言至上的讨论是从何者优先的单一维度展开,那么从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三个不同维度来看,歌曲翻译研究又呈现出音乐性和语言性交互为用的状态。而整合音乐性和语言性的恰恰是包括德国功能目的论、符号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理论框架。
(一)基于功能目的论的文本内研究
在文本内研究层面,德国功能目的论为探讨歌曲翻译的目的与策略提供了理据。霍恩比(Snell-Hornby,2006:65)将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尤其是“译者行动模式”视作“同时应用于文学和非文学翻译的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在彼德·洛看来,“对译作功能和目的的关注有助于译者作出抉择,即译作的哪些特征需要着重凸显,又不得不牺牲哪些特征”(Gorlée,2005:186)。功能目的论彰显了歌曲翻译作为音乐作品应该具有的歌唱性、表演性和审美性,突出显示了译者在面临音乐和语言两个不同主体时可能受到的文本内外制约因素,表明歌曲译者如何处理作曲家、词作者、委托人、听众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音乐语言转换中的语言冲突。彼德·洛(Low,2005)提出“全能原则”(Pentathlon Principle),即在文本层面平衡歌唱性、意义、自然度、韵律和节奏。弗兰森(J.Frozon,2008)也赞成从功能主义视角关注译作的“歌唱性”,译者可以采取不译歌词保留原曲、改写歌词以适应原曲等策略。考虑到功能目的论的适用性,国内多名学者以此为理论框架。如陈水平、何高大(2009)提出歌曲翻译五原则,即切唱、切听、切情、切味和切意;吕锴(2011)提出“宜听、宜唱、忠诚”原则。综上所述,功能目的论为文本内层面的歌曲翻译提供了分析框架,将研究重点放置在歌曲翻译原则和标准制定上。
(二)基于符号学的文本间研究
在文本间研究层面,符号学为理解歌曲翻译中的意义生产和转移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撑。在歌曲翻译中,音乐与语言是“两个由纯粹听觉性和即时性符号组成的复杂系统”(Jacoboson,1971:701),歌曲的意义是两个特殊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将音乐和语言符号在两个不同系统中的意义生产、流通和功能纳入研究中,突出了音乐和语言文本间的交互。二○○五年由芬兰学者多尔勒(D.Gorlée)主编的《歌曲与意义:歌曲翻译的善恶论》收录了八篇代表性论文,集中探讨了语言与音乐中的意义生产,提出歌曲的意义随歌唱者、歌唱环境和受众的变化而变化。国内唯一以歌曲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歌曲翻译三符变化说”同样以符号学为理论框架。总体而言,符号学的运用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歌曲翻译中意义生产和转移,在音乐与语言两个独立系统的交互中审视译者所受的限制及其翻译策略。
(三)基于文化研究的文本外研究
在文本外研究层面,研究者借用文化研究的视角,考察了影响歌曲翻译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根据音乐文化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表征,亦是文化记忆的传承,建构了特定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二○○八年,萨拉加瓦为《译者》(TheTranslator)主编《音乐与翻译》专辑,所收录的九篇文章皆从宏观的政治文化层面探讨歌曲翻译问题,歌曲翻译被视作清除文化多元性的文化政治实践。萨拉加瓦在编者前言中特别反驳了彼德·洛的观点,认为歌曲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将研究对象限制在单纯的语言转换中将会造成研究视角的缺失。在二○一五年出版的专著中,萨拉加瓦以希腊都会贫民窟蓝调音乐(rembetika)在爱琴海地区的翻译传播为个案,探讨了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翻译策略,肯定了翻译中的身份认同建构。事实上,文化研究将翻译视作“协商”,关注翻译中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协商和交际作用,旨在考察翻译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当音乐和语言同时作为文化的负载时,翻译中所传递的“信息”远甚于单纯语际翻译,这也为译者的翻译决策带来了挑战。
总体而言,理论框架的综合运用正体现出歌曲翻译研究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也正因其复杂性,歌曲翻译仍有进一步扩展的必要。
扩大领域及把握本体——歌曲翻译研究前景展望
当下歌曲翻译研究虽已引起学界的关注,获得较大进展,但学界仍未对歌曲翻译的本质达成共识,当下研究仍可在研究范围、对象、方法和本体层面推进。
(一)深化本体研究
从元理论层面而言,明确概念内涵以及整合术语体系应是歌曲翻译研究的当务之急。当下歌曲翻译研究亟需建构以歌曲翻译研究为对象的元理论研究,以推进本体研究,形成科学研究共同体。正如弗兰森(J.Frazon,2017)在书评中指出的,歌曲翻译研究领域现在缺乏“共同的范式,也未就定义和研究分支达成一致”。歌曲翻译研究迄今未能对核心术语达成共识,工具书、专著以及重要学术期刊上仍混杂着声乐翻译(vocal translation)、歌唱翻译(singable translation)、音乐翻译(music-linked translation)、同步翻译(synchronized translation)等不同关键词。不过,歌曲翻译研究是以经验世界的翻译现象为基点,只有基于对实践的大量观察才能发现歌曲翻译研究的普遍规律,从这一角度而言,推动歌曲翻译实践也是促进歌曲翻译理论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扩大研究范围
在研究范围上,当下歌曲翻译仍需扩大研究视阈,深入挖掘歌曲翻译行为,解释歌曲翻译现象,揭示歌曲翻译本质。具体而言,虽然音乐和语言文本翻译已引起学界重视,取得一定成果,但歌曲翻译史、歌曲翻译教学、歌曲翻译伦理研究、歌曲翻译批评、歌曲翻译职业化、歌曲翻译技术等领域尚缺乏相关研究。以歌曲翻译史为例,除少量音乐史著作外,尚未出现歌曲翻译史专著。同样,当下歌曲翻译研究尚未关涉歌曲翻译教学问题,仅贝尔隆(R.Berrong,1996)和彼德·洛(P.Low,2017)编撰过专门歌曲翻译教材,但前者专涉意大利唱本英译问题,未能得到普及和学界认可,后者的普及性和适用性还需继续观察。另除休伊特(E.Hewitt,2000)讨论过歌剧翻译教学问题外,尚未有针对歌曲翻译教材教法的研究。就翻译技术研究而言,歌剧字幕翻译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音乐剧、电视歌曲字幕翻译仍无人提及,对观众接受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相对匮乏。作为多模态翻译中的一种,歌曲翻译涉及了音响、图像、文字等多种形态,从听觉和视觉方面探讨翻译过程或能更明晰地展现出翻译中的交互、转换和变通。
(三)丰富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上看,当下研究虽覆盖了歌剧、民谣、流行歌曲、音乐剧等多种音乐类型,但广告、电影、纪录片等大众媒介中的歌曲翻译尚无相关研究。除此之外,以阅读为导向的歌词翻译研究同样乏善可陈。以CD附页为例,由于所涉歌曲翻译并不用作表演或歌唱,主要用于听者阅读,翻译时需考虑附页语言简洁庄重的特点,在翻译时涉及的大量文体问题应引起研究者关注。另歌曲相关的音乐术语研究需作进一步推进。音乐术语是音乐学与翻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在术语中不仅存在概念涵义的历史变化,更有不同音乐和文化体系之间的碰撞。汉语的音乐术语外译中的问题应引起国内学者重视。一九九九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刊发专刊讨论音乐术语的问题。英国音乐学家钟思第(S.Jones,2012)也曾呼吁广大音乐研究者重视“中文音乐文献资料翻译”,但音乐文献翻译研究迄今仍无明显推进。
(四)整合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当下歌曲翻译研究仍需思考跨学科研究的方式与方法。翻译学和音乐学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结合”。当下歌曲翻译研究不仅较少借鉴音乐学中对具体歌曲音乐结构的分析,也很少挖掘音乐学内部对“歌唱性”“表演性”等核心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以歌曲的歌唱性为例,音乐学业已从旋律的调性、音乐特点等方面深入剖析了部分经典歌曲的“歌唱性”,但翻译研究者仅将“歌唱性”视作具体的翻译目的,未从详细的音乐文本分析中呈现出“歌唱性”的具体内涵。当谈论语言本身的音乐性时,也未见翻译研究对声乐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二○一○年《澳大利亚语言学杂志》(AustralianJournalofLinguistics)曾推出专刊,比较和讨论音乐和语言文本的句法和篇章结构差异,但当下歌曲翻译研究尚未借鉴音乐人类学、声乐学等视角展开讨论。
总体而言,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歌曲翻译研究还需继续深化和推进。考虑跨学科研究的实质不在借鉴和挪用,而是借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共同推进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在扩大研究领域、优化研究方法的同时,歌曲翻译本体研究或应作为首要任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结语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歌曲翻译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整体而言,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受制于“语言至上”和“音乐至上”两种主要的价值观,其中对音乐性的过分强调或导致当下歌曲翻译研究对翻译、改写、创作等核心概念的认同分歧。虽然研究似已在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三个不同维度同时开展,但研究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决定了这一领域还需加强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清理改写、替代、重写等翻译概念的模糊地带。深入研究歌曲翻译本体,扩大研究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应成为未来歌曲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