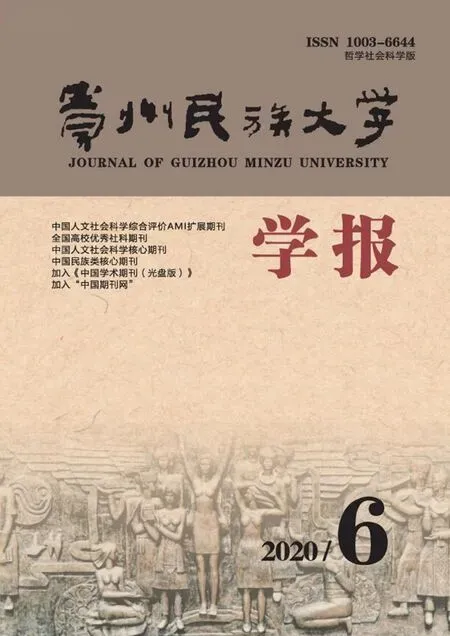《荀子》语言哲学中的名称理论阐释
戚 金 霞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用西方的逻辑学理论(主要是传统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第二,除了中国古代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的)文本中与逻辑有关的内容之外,把其与语言、论辩相关的内容都纳入研究范围之内。这样的研究不仅包括了逻辑学的内容,还包括了语义学、语用学的内容(即从语义学、语用学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古代的文本)以及与语言(名)、论证(辩)相关的内容。因为这样的研究超出了人们对“逻辑”一词的狭义理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有些学者把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说叫作“名辩学”。但“名辩学”是不是逻辑在学界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是从“名辩学”发端,所以应该把“名辩学”纳入逻辑史的研究范围之中。随着西方逻辑理论的传入,中国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用新的理论工具来尝试解释中国古代文本,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就有多篇关于名辩学的内容,但是不同的学派之间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本文以战国末期的荀子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其所涉及语言哲学中的名称问题,从而实现以语言哲学理论对荀子文本中语言的分析与思考。
荀子作为儒家的集大成者,萃取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语言最有研究的思想家之一,其有关语言(名)思想的研究达到了先秦时期的顶峰。先秦诸子对名的论述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讨论名的政治、伦理功能的。从语言的角度对名进行讨论的人不多,而荀子就是为数不多的对语言作出了较为全面、深入讨论的思想家之一。随着逻辑学的发展,逻辑学家越来越重视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方法尚无统一的认识。按照一种观点,自然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符号学。它分为自然语言的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其中,自然语言的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的意义。《荀子》中有许多关于语言的论述,荀子先后提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等观点。有学者提出,荀子的约定俗成是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具有社会性,其特点与古希腊智者对语言的讨论颇有相似性。
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了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语言哲学理论。这种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前期对语言意义理论比较注重形式化的研究,立足于人工语言,如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等均是如此。在20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自然语言学派,以牛津学派的奥斯汀、赖尔、斯特劳森等为主要代表,也包括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这些丰富的理论为我们解读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中国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荀子语言进行解读,如汪奠基提出名称形成是约定俗成的主张,“约定俗成”这一概念的含义尤其值得我们研究。同时他还论述了荀子的 “心有征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他认为“概念上的同异,是缘感觉的同异,经过心思,然后才抽得认识(征知)的。如果心征之而没有逻辑的表述方式,那也不能成为认识。凡是思维抽象的(征知)都是按感觉所留下的类,分别予以概念之名”[1]。
一、名称的形成理论:约定论
(一)约定论简述
约定论(Convention),是语言意义的重要研究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可以多次看到关于语言是约定的还是自然的讨论,其中《克拉底鲁篇》着重讨论了名称的意义问题,代表人物有赫摩根尼、克拉底鲁、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赫摩根尼持约定论的观点,主张名称形成是约定的,他谈论道“除了说它是约定俗成的和人们一致同意的,我无法相信名称的正确性还有其他什么原则。在我看来,你提出的任何名称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换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新名称也和老名称一样正确……因为自然并没有把名字给予任何事物,所有名称都是一种习俗和使用者的习惯”[2]57-58。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提出语词的形成是约定的,名词的意义是通过约定形成的,从语词和语句的用法论述语言是约定的,同时他还区分了本质和偶性,认为是本质规定了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赫摩根尼的约定主张和亚里士多德的约定主张不同之处在于,赫摩根尼的约定论讨论的是相同的事物不管名称怎么改变,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新名和旧名同样可以指称某事物。赫摩根尼与荀子不同的是,荀子认为语言约定的过程是要遵循规则和依据,强调新名的形成是依据旧名来约定的。赫摩根尼则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约定而来的,但他并未对名称的形成依据作出深入讨论。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3]101。这种任意性原则就是约定性原则。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也赞成约定俗成说,他认为名称的意义和使用,都是习惯的产物,并随着习惯的改变而改变。[4]16休谟对于语言的约定问题,认为“各种语言也是不经任何许诺而由人类协议(约定)所逐渐建立起来的”[5]531。
(二)荀子的约定俗成论
荀子主张名称的形成是约定俗成的,他在《正名》中有以下论述: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所谓“名”就是名称、概念,所谓“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这句话揭示了“名称”与“事物”的关系,名称和事物之间原本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但是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往往是由人们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确定或形成的。在荀子看来,事物的名称不是先天形成,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人们约定的结果,是社会约定和社会习惯的产物。也即是说,名称并没有本来就适宜的,而是人们共同约定来用其给该事物命名的。约定而成为习俗习惯的用法就是适宜的,和约定的名称不同就认为是不适宜。名称并没有固有的指称对象,而是人们共同约定对事物命名,约定而成为习俗以后就把它作为某事物的名称,久而久之,就成为习俗、习惯。
事物与名称是荀子语言意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荀子通过“约” “成” “宜”来诠释事物名称的形成过程,认为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而不是彼事物是因为名称是约定而来的结果,只因事物名称是人们最初在社会活动中这样约定的,也就成为这个事物的名称。比如现在我们所说的“马”,也可以叫“牛”或者“羊”之类,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名称不过是人类社会在交流中用来表示客观事物的各种语词,这些语词代表相对应的事物,即“约之以命”。事物的名称具有主观性和任意性,事物的名称是人类社会约定的产物,而不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名在最初的时候只不过是代表客观事物的语词而已。在制定名称的时候,人们根据约定俗成原则,对约定的同一事物有共同的理解,“马”才被称之为“马”,即“马”是具有“马”这个事物的名称。因此名称的意义就是事物的所指,这种所指是约定的。
荀子不仅指出“名称”与“事物”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客观事物,一旦经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确定名称以后,就会具有客观内容和社会内容,不再具有任意性,从而是具有确定性。名称与事物之间在意义表达上必须是明确的,即“径易不拂”,一个好的名称,应该具备通俗易懂、容易知晓而不产生歧义等条件。
荀子在《正名》中提出的名称约定俗成原则,在中国古代语言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荀子在先秦时期讨论名称的形成是约定俗成的,这一观点和两千年后索绪尔的观点相似:“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 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 或者同样可以说, 以约定俗成为基础基本一致,但是荀子的‘约定俗成’比索绪尔早了两千多年”[6]103。比如荀子指出语言成分中语音和语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现在有的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与两千多年前荀子的论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7]
美国学者Hansen认为荀子的语言约定论是一种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有两种说法:较弱的约定主义是将我们所使用的声音或符号视为社会之约定,只要他们被正确使用时,能够被一语言社群所相互承认。简言之,所谓马,我们亦可称之为牛。较强的约定论则主张不仅声音和符号是约定的,而且相关的区分之实践亦是约定的。将实在划分为被命名对象之方式(完全不渝社群所使用之符号或声音)也是一种共同和约定的分类或区分的实践,而为大众所接受的功能”[8]。依据上述约定主义之界定,Hansen断定“荀子之名学说是一种较强的约定主义”[8]。
二、事物名称分类的辨析
在《荀子》正名篇中,所讨论事物名称的含义,泛指语词所指的对象。 “共名”“大共名”“别名”等范畴概念构成。如像“大共名”“这样的范畴概念构成的是一个边界开放、有着多元定义的意义场,在此意义场中,每一个定义与其他定义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离开这个共同的意义场,单独谈某一个定义,“便会使人误入歧途”[9]。范畴概念意义是不确定的,“在由范畴概念构成的意义场中,各个定义虽然可以分殊,但有着内在的关联”[9]。它的每一个概念的意义可以分殊,每一个概念的意义和其他概念的意义之间也存在联系。在客观世界中,事物的形状千差万别,颜色各异,特征不同,人们怎样在这万花筒般的世界中认识事物?方法就是给事物命名,事物有了名称,便可以依据事物所具有的相同特征和属性不同而合并归类,但是这种合并归类又不是随意的,有一定的方法,比如:徧举与偏举。因而人们从合并归类之后的名称可以较清晰地认识事物。这种对事物的分类方法,在《荀子·正名》中有具体表现。荀子把范畴概念分为“别名”和“共名”等。故其曰“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共名” “别名” “大别名”等为语词的范畴概念。“共名”即为“通名”“大共名”,即范畴之意。“别名”,就是事物的“专名”,是具体事物专有的名称。关于“大共名”和“大别名”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冯耀明认为:“‘大共名’者,大约可共之名也;而‘大别名’者,大约可别之名也。所谓大约可共之名,即指遍举诸物可以共约之处而成范畴性的概念;而所谓大约可别之名,乃指遍举诸物可以期别之处而成的特质性的概念,如‘鸟’、‘兽’。前者乃范畴性的遍举,后者乃特质性的遍举,皆使异实者仍可以用同名之法也”[10]。
徧举与偏举是从概念对语词所做出的分类方法。徧举,是概括的方法,通过概括名称的内涵,抽取事物的共同性,找到其在的属,进而徧举,以此可以得到很多名称。如“牛”是一种名称,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动物”,由“动物”概括出“生物”等等,最终推出“物”的名称,“物”是最大的概念,其内涵最小,外延最大。偏举则是相反的过程,主要是通过连续性的不断扩展概念内涵,从而限制概念的外延,而增加概念的内涵,对概念每一层级的限制获得不同的名称。比如“学生”是个名称,我们可以通过偏举,得出“大学生”,由“大学生”得出“某某大学的学生”,直至最后到某一个具体的学生。因此,万事万物都可以通过徧举与偏举连接起来。如学者蔡仁厚以“物”为例解释偏举和徧举。他认为“物,是偏举的大共名,这是向上‘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而形成的最高名之纲名或类名。此处‘大共名’仍指‘物’,而‘大别名’,则当指‘生物、无生物’而言。唯荀子之时,并没有生物与无生物的名称,因此以鸟兽为大别名。又,除最高层之‘物’永为共名,最低层之个体永为别名,中间各层则皆兼具‘共名’与‘别名’双重性质”[11]440-441。
如果从概念的关系来说明“共名”及“别名”之含义,那么“共名”和“别名”是逻辑上所说的种属概念。“共名”即是逻辑上所说的种概念,“别名”即是逻辑上所说的属概念。比如:植物与乔木,植物的含义要大于乔木,植物除了包含乔木之外,还包含灌木、藤类、青草、蕨类等许多类。乔木的含义与植物相比含义较小,只包含酸角、木棉、松树、玉兰等一部分的植物,即包含植物中乔木的一部分。因此,植物相对于乔木就是种概念,乔木就是属概念。
在《荀子》文本中对概念的一种分类,可以概括为“大共名”“共名”“别名” “大别名”。大共名与大别名指称具有集合概念的事物,共名一般是指通名,别名一般指专名。荀子对此的理解,应该是对墨家概念分类的继承发展。墨家学说把名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达名就相当于大共名、类名就相当于共名、私名就相当于别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荀子对名称的分类,应该是对当时的诸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辨析事物名称本质的途径:感官和心灵
“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原理,语言具有体验性,语言是人类自身与客观外界进行感知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认知方式而形成的”。据此我们就能推导出以下结论:全人类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沐浴着相同的阳光,这就注定了全人类必定要享有部分普遍性认知方式和思维规律,各民族语言也必定具有部分普遍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体验性普遍观。这一观点在荀子的《正名》中早有述及:“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义物也同”[12]534,526。荀子认为人们的感官感知和心灵体验是分辨事物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人们是通过耳朵区分声音的异同,通过眼睛观察外形的差别,但是,这些都是作用于感官对事物的感知,而心灵的体验是建立在耳目感官之上的。对事物的认识先是感官感知,其实心灵体验才能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当你的眼睛看到不同色彩,耳朵听到的各种声音,鼻子闻到的气味等,这些都是人的一种感官感知,是建立在外部世界之上。而你的快乐和悲伤等是心灵体验,是建立在内部世界之上,也是一种身心体验。
身心问题,是心灵哲学研究的范畴,“心灵”一词可以表示不同的多种用法,在区分不同的用法上,可以归纳为五种不同的意义。这五种不同的意义既是对心身问题的解释,也是对“心灵”一词的理解。“其一,如笛卡尔用‘mens’那样使用‘心灵’,让它指称具有心理属性的东西,亦指称那种进行思想、感知、相信和欲求的东西。其二,我们也可以像现今许多人那样具有‘心灵’表示人的智能。其三,我们也可以将一个人的心灵说成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正是借助于它,他才能进行思维。其四,‘心灵’一词有时还用来指示一种精神实体,即一种具有非物质本质的独立的个体事物。其五,探究心理的与物理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去获取一种不仅是对心理世界的本质,而且也是对物理世界本质的更好理解。”[13]85
在《荀子》文本中,荀子强调人可以依据对世界的感官印象来为事物分类,但是人们依据什么来认识名称和区分名称?答案是:根据人天生的感官。荀子通过感官感知和心灵体验认知事物,用语言来表达事物的名称。这一点类似于笛卡尔对“mens”的解释,“‘mens’具有心理属性的东西,可以进行感觉、思维等,是一种具有独立性质的个体事物。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后来被称为笛卡尔心身二元论(mind and body Dualism)或交互二元论(Interaction Dualism)。笛卡尔二元论认为心智和身体(mind and body)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它们可以在大脑中相互作用”[14]。这种心身二元论体现了感官和心灵相互作用的关系。如:《荀子》正名篇中,“心有征知”表明了荀子对人类辨析事物及其名称分类的基本看法,既要靠感官感知,也要靠心灵体验。人们可以通过“心灵”与“感官”来认知名称,这种感知体验辩证观正是当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体验性”与“互动性”,“殊相(专名)”与“共相(通名)”之间的关系是重点研究内容,这两组概念的区分,对研究荀子的感官感知和心灵体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体验哲学”与传统的经验论与理性论是不一样的。就如王寅教授所讲的:“通过分析荀子的语言体验观、认知观和辩证观,我们认为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与任意性不可同日而语,他不像许多著作和教材中所说是‘唯名论者’的典型代表,而是更接近于唯实论者。”[15]
在认知语言学中,人们可以通过“现实—认知—语言”来实现。在互动体验中,有三个递进阶段:“感觉、知觉、表象。感觉指当前作用于人们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在头脑中的反映,它是认识的最简单形式,婴儿依靠它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知觉则比感觉更为复杂,指当前作用于人们感觉器官的事物的各种属性在头脑中的总体反应,是各种感觉的总和。例如婴儿在多次感觉的基础上慢慢获得了梨子的多个乃至综合性特征,包括颜色、形状、味道、硬度、温度等,在综合这些感觉的基础上就可获得对梨子的整体印象,这就是对梨的知觉”[16]。
感官和心灵是同一的,也是经验性的,人们通过感官感知接触不同事物完成外在体验,通过心灵对事物体验完成内在认知。这种经验性和荀子“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具有相似性。荀子曰:“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凝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 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荀子论述人们通过感官把相同性质的事物给予合并归类,这种事物合并归类的方法对事物名称的分类具有重要作用。人们用眼睛来区分事物的外形、色彩;用耳朵来分辨音色的音律、清浊来调和不和谐的声音;用口来分辨甘、甜、苦、辣等味道;用鼻子来分辨香、臭等各种气味;身体可以分辨痛、痒、冷、热等各种感觉;用心来区分快乐、悲伤、喜怒等各种情感。眼睛、耳朵等感官是分辨事物的基本方法,是外在的体验。而心灵对事物的认识是内在体验,这种内在的体验具有分析、感觉、辨别事物的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通过耳朵分辨声音的异同,通过眼睛看到形状的差异,而心灵的认知对辨别事物名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心灵的认知是建立在耳目等感官之上的,心灵世界虽然是不可知的,但是可以被刻画,可以被认知。“荀子把人们的认知能力称之为‘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 , 把感知器官对外界事物的正确反映称之为‘智’(‘知有所合谓之智’)。他还指出,感知器官包括耳、目、口、鼻、身和心。心除了能感知喜怒哀乐爱恶欲之外,还有获得‘徵知’的功能。徵即验证,心能验证感官获得的知识。心的徵知必须依赖感觉器官接触了某类事物之后才可得到(‘徵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如果五官接触到事物而没有感觉,或者心中有了徵知而不能用语言表达,都会被视为不知(‘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15]
在《荀子》正名篇中,“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能”即才能,指人所具有的某种心身技能;身体和智能虽然属于完全不同的事物,但人们认识事物名称的时候,是可以相互配合的。这种解释体现了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的思想。因此如果“按照名即概念的原则去思考人类心理活动的问题,我们对人类的感觉、知觉和思维过程的认识将会产生一种全新的看法,即概念的形成不仅局限在思维活动中,而且在感觉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着形成概念的问题。”[16]
四、结语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研究内容涉及教育、哲学、政治、语言等领域。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他是对语言最有研究的思想家之一。在荀子看来,事物和名称的对应关系的形成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人们约定的结果。人们在交流沟通的时候,借助语言,向别人传达意义,荀子通过对语言的诠释和运用,建立了以语言为主线的理论体系。荀子从名称的定义、名称是怎么形成的、名称的认识过程、名称的类型、名称的功能、名称的原则和方法六个方面对名称做了详细的阐述。此外,他还通过论述“心有征知”来强调感官和心灵的作用。荀子对名称的研究,尤其是“大共名”“共名”“别名”“大别名”的讨论,是先秦诸子从语言的角度对名进行讨论而为数不多的做出较为深入研究的著述之一。因此,对《荀子》名称研究或许可以从古代思想家那里得到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