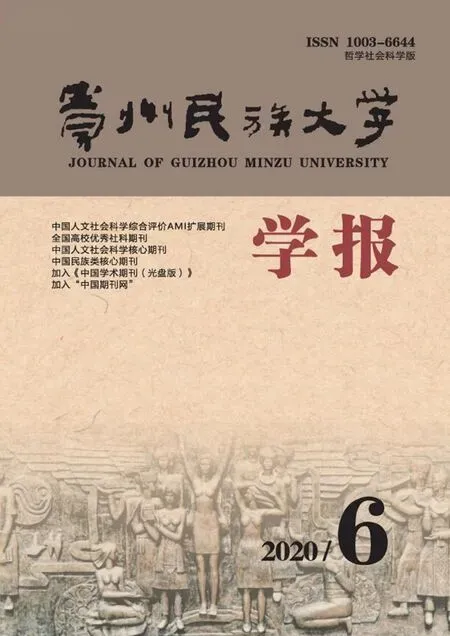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学的思考
——读刘守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
梅 进 文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无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在当下,如何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学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刘守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研究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他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献身于民间文学到后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已有六十个年头。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具有权威性与代表性的,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刘守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学的一些真知灼见凝聚在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中。该书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书系”中的一本,这套书系是在我国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在当代现代化发展的狂潮中,面临着‘摧枯拉朽’般的灾难。……许多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化遗产,我们还没来得及记录和记住它们就悄然远离我们而去;许多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的,也过早地被人为毁灭和抛弃”[1]311的境况下,作为一名具有长远眼光的学者,本着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谋有所作为与奉献”的思考下而产生的。该书系“先后推出了《民间叙事文学研究》(刘守华、黄永林主编)、《灵性高原》(林继富)、《民间文化与荆楚民间文学》(黄永林)、《红安革命歌谣研究》(桑俊)和美籍华人丁乃通先生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6种,这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就是它的第7种了。”[2]3该书是一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民间文学的专题论文集,这些论文是刘守华花费十多年之功的成果。从这部论文集里我们可以集中地看到刘守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文学的宝贵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综论,其中以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论述对象兼及其他。在这里他提出的从抓文化生态入手“活水养活鱼”的保护策略思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项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下编是对湖北省有代表性的20多项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也是本书花费笔墨最多之处,刘守华说:“我十分珍惜这些成果,一是由于相关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都是在民众中广泛流传,而又经过多次认真品评筛选出来的精粹;二是由于它们虽处于亟须保护的濒危境地,却仍以鲜活的姿态存留至今,工作重点也在于活态保护。”[2]2纵观该书,我们可以发现刘守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是立足于自己的最擅长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研究的基础上,触类旁通,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崇实品格。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特点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二、区分形态、灵活对待
我们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家,民间文学资源相当丰富,且形态各异。如果不加以科学地区分,有针对性地加以保护,而只是平均使力“摊大饼”,那么恐怕很难在实践中真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首先刘守华对民间文学的存在类型进行了一个创造性地划分,他把民间文学分为原生态民间文学、再生形态民间文学、新生态民间文学。原生态民间文学主要是指“依托相关的民俗文化背景仍然活在民众口头的民间文学。再生态民间文学指的是经过采录、整理、改编,转化成书面或视听艺术作品,以新的生命向社会传播的民间文学。新生态民间文学指的是在当代社会生活激荡下产生的民间口头创作,主要有新笑话和新民谣。”[2]7对于新生态民间文学,刘守华认为它是老百姓真实生活的一种形态,我们只需要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加以采录、评论、研究之外,不必加以过多干预,这是符合这类民间文学特点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类民间文学就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干涉,做好整理观察工作即可。原生态民间文学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表现出颓势,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整个形势是不可避免的,刘守华认为对于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但是鉴于中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原生态民间文学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存在形态,远不是我们能够按照一般性道理推论的那样。实际情况是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比如湖北省武当山“金顶”附近的范姓“口传文学家族”,类似情况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不在少数。同时,原生态民间文学中有些类型在现代社会里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比如一些传统的情歌、笑话会通过现代传媒形势不断地流传扩张,受众面更加广阔;再如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的口头文学作品在当下社会则结合文化旅游等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和价值。刘守华认为对于原生态民间文学,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用整齐划一的方式去对待。这种见解指出了原生态民间文学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真实状况,虽然说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原生态文化从总体上正在逐渐消失,但是我们也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眼光看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有些原生态民间文学保持得还非常好或者以各种形式继续存活在当下,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基本原理的。
至于再生形态民间文学,是我们在实践中花费力气最大的一类。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启动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程,它包括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耗时25年,先后参与人员达几十万之众,到2009年出版的仅省卷本就有90卷,县卷本4 000卷,总字数达40亿字,可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对于我国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来说是居功至伟。刘守华认为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应该继续下去,还有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学的采录整理并没有完成。当然仅仅进行收集整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我们优秀的民间文学资源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转化工作。刘守华认为在整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选编面向中小学和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学读本》等,使之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成为各族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2]7这是他对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守华为了一个个具体且很有价值的民间文学成为“非遗”工程所做的不懈努力。以他追踪“汉族史诗”《黑暗传》为例,从1983年刘守华开始研究一直到2011年5月《黑暗传》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前后有19个年头,他的专论也有六、七篇。整个过程既有他不断地鼓励和指导《黑暗传》最早的采集者胡崇俊继续发现和采录其他异文的细节,也有他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文化学者就该文本的属性认定的论争,且最难得的是在2008年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时候,有人认为《黑暗传》的名字不太合适,是否能改名,他据理力争认为该文本就是描述盘古开天辟地战胜黑暗混沌的神话,实在是没必要改成类似“创世纪”之名。虽然,《黑暗传》在第二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中落选了,但是刘守华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向相关部门呼吁申诉,终于使得它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学者对于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位“非遗”专家的务实品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需要发现的敏锐眼光,更要有实实在在的工作态度。
三、 重点保护文化生态
美国文化学者墨菲曾经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3]79刘守华认为:“‘文化生态’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通过研讨引起各方的关注。否则,所谓‘科学保护’就难以落到实处,不能收到应有成效。”[2]17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是单个的独立现象,一般而言,它总是依附于一定的文化生态而存在的。刘守华认为像民间故事、歌舞、笑话等样式是贯穿于在人们的生产实践和实际生活中的,我们也不能脱离这个大的背景来认识民间文化,换句话说,民间文化是老百姓真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只有用活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才是比较科学的。所以,我们要真正做到合理地保护它们,必须有一种整体观、全局观——重视整个文化生态保护,且应该针对它们的不同特点加以开发利用。
之所以要对文化生态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文化生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也遭到了破坏进而逐渐萎缩、消失。刘守华说:“关于民间文化生态的保持、恢复和重建等,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了。”[2]20刘守华以自己深入研究的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其一是长阳土家族的跳丧舞“撒叶儿嗬”,它本是当地的一种风俗,某家老人去世,邻里乡亲前来帮忙守灵,期间高歌狂舞,它充分展现了长阳人民豁达的生死观和世界观。为了保护这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在“撒叶儿嗬”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之前,长阳市政府就通过举行此类舞蹈的大赛,建立“土家族撒叶儿嗬”传习基地,认定文化传承大师,且在此项风俗最盛的资丘镇建立了撒叶儿嗬文化生态保护区,尽可能地保持这个项目的本真色彩。同时当地政府还有意识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对“撒叶儿嗬”进行录音、拍照、录像以及出版画册等进行宣传,并请不少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刘守华认为“撒叶儿嗬”的成功是得力于当地党和政府以及民众对于文化生态保护的高度重视上。这个项目随着影响的扩大,逐渐被改编成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比如“巴山舞”等。当然,任何改编都会对事物本身的性质产生影响,有的可能是积极的、正面的,但有的则有可能是一种扭曲。刘守华也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加以保护和发展,那么开发利用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利用,随意歪曲事物的性质就会对保护的对象产生严重的伤害。对于“撒叶儿嗬”同样存在的这个问题,刘守华指出,在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广场舞,许多女性也加入进来,有的地方则对跳丧进行完全商业化的包装。对此,刘守华认同长阳当地的一个文化学者戴曾群的观点,认为“撒叶儿嗬”本是长阳人民在真实的丧事期间进行的一项严肃的活动,从传统来看,它是从“军阵舞”里演化而来的。男女在古时战争中角色不同,属于传统风俗,不宜做改变。至于那种纯粹的商业化的跳丧行为更是对于这项民风的一种亵渎了。这都是不利于文化的保护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它曾经在世界上都引起过巨大反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还专门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但是在文化生态保护上却显得成效不足。刘守华认为,作为静态的保护,在采录、收集、整理等方面,“伍家沟民间故事村”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动态整体的保护上还有较长的路需要走。因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讲故事、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那种原生态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伍家沟民间故事村里以前建的“故事堂”现在也是冷冷清清,孩子忙着上学,青年纷纷外出打工,故事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向旅游转型的道路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的探索似乎也不是很成功。刘守华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指出,作为民间故事在形态上和民间歌舞是不一样的,它的欣赏性和娱乐性相对来说有时候显得和时代距离较远,实感也不强,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的类似的“昔话村”的模式来进行保护,即对远方旅游客人进行原生态式的故事讲述。刘守华在这里通过介绍实例的方式来探讨文化生态保护的相关问题。我们认为,刘守华关于文化生态保护的相关论述是十分合理的,民间文学的民间性其实也说明了它是依附于一定的生态的,离开这个生态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或者失去了其本真性,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了,对文化生态的保护也符合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于文化生态的保护的论述,文件里明确说“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护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和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
刘守华特别提到对于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两个问题: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旅游资源的转型问题,这种转型在许多地方是一个事实,有的地方开发做得很到位,收到的效果也很好;有的地方的项目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却难以见效。总结起来看,一般该项目如果在旅游热线上,搭上某个热点旅游的顺风车,且项目本身也富于表演性和娱乐性,则转化起来更加容易。比如武当山线路的吕家河民歌村即是一例。刘守华指出,我们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转化问题上要注意积极地引导,不能完全为了商业利益任意扭曲项目的本来性质和面目,否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一个灾难,且难以为继。其二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生态的修复、重建问题。现代化的进程日益改变人们的实际生活形态,有些口头文学存在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那么能不能恢复或者重建那种文化生态呢?刘守华通过论证认为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其他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来保留、恢复和重建。他建议说,我们可以通过将口头文学辑录编入教材,让民歌进入课堂,适当恢复人生节仪和岁时节日,将相关的民俗事项融入进去的办法来进行保护。这些办法我们认为都是具体而切实可行的,体现出一个真正热爱民间文化的学者的情怀。
四、活态保护、以人为本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刘守华觉得我们需要贯彻的一个总的原则——活态保护、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于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刘守华认为就是要有科学观、整体观。这里包含的要义较多,首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辨析,刘守华说:“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体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2]25这种文化应该是值得保存和发扬的,符合我们新的时代精神,是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而不能把所有的历史的、旧的东西都当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保护。刘守华以湖北某地的十月十五日的“接大王”习俗为例,这里面所迎送的大王即指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史书认为他为了谋取一人私利而出卖国家土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这种人物是不值得我们纪念和歌颂的,不应该划归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列。相反,对于有些民俗我们应该认识到其社会历史渊源,不能简单粗暴地划入到封建迷信的范畴里。刘守华通过研究清明节的风俗就发现,它的功能其实是多重的,既有后人表达对于前人的怀念,也有人们踏青赏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还有植树造林的活动。刘守华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些功能整合起来,以扫墓为主,辅之以踏青和植树。其二,活态保护里包含了“静态保护”,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前提,静态保护包括了一系列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非遗”事项进行录音、录像、制作成各种样本由档案馆、博物馆妥善的保管,以便于人们的了解、学习、开发、利用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仅有静态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得民间文化遗产真正地发扬光大,还要有“活态保护”的思维。刘守华赞同芬兰学者劳里·航柯的意见。航柯认为“民间文学财产的‘第二次生命’的标志是人们想利用它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对做成文件的民间文学,即‘从民间文学衍生出的作品’,才能实施有效的保护,而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心目中的、在演唱过程中以千变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体和思想是无法直接保护的。”[4]126这里的关键之一就是保护性地开发、利用、传播。刘守华以自己曾经研究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汉川善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湖北汉川善书历史悠久,它和北方流传的“宝卷”属于同脉,都是从古代僧侣的讲说演化而来的。但是汉川善书在传承中受到活态的保护,政府部门鼓励将从前的本子改编改造,融入新的时代因素,传承艺人也广泛收集各种资源,累积有三四百个新旧本子,改造表演形式适应现实。所以至今在汉川善书仍然十分流行活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较好的样板。
对于“非遗”的保护,刘守华认为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要做到以人为本。他根据自己多年来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了解到,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一般都是生活较为贫困,但却具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往往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疏解生活的诸多困苦。比如著名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孙家香、刘德方等就是他们之中的代表,这并不是个案,作为在现代社会里的民间文化的守望者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经济落后的表征,所以我们更应该关心、理解、爱护他们,除了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外,还要提供相应的条件使他们能够继续把故事讲下去,这才是一种真正对他们的尊重。另外,就是尽量地采录故事传承人的口述故事,进行整理研究。刘守华认为:“努力改善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生活处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建立故事传承人自己的行业协会,激励他们以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开展故事活动,改编过去完全依赖外部力量来推动的消极被动状态。”[2]39这是我们对待民间文化传承人应该有的态度和工作方法。
五、崇实的追求
上面是关于刘守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学的一些观点的阐释,在通阅了刘守华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之后,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刘守华作为一名研究民间文学和“非遗”的著名学者在追求学术真理的道理上体现出来的崇实的品格。
首先是他认定目标,坚持不懈的研究精神。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从开始发现自己的研究兴趣领域——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必然发展逻辑)就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地展开持续性研究长达60余年,且一直都笔耕不辍。或许这也正是他取得学术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守华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多面开花”,研究领域非常宽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失去了真正的专业。他一直都认为,学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术的海洋博大精深,不选择好一个方向,不长期坚持下去是很难真正有所作为的。刘守华从1956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论文《目前的儿歌创作》在学界引起关注到如今,发表论文累计达300多篇,出版学术论著10余部,已经是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权威之一。他的很多专著都受到学界的重视与好评,例如对于长达67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史》,钟敬文先生就评价该书“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第一本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5]著名旅澳学者谭达先认为“此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当前富有学术个性与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中国民间故事史科学的发展,不愧是个十分重大的贡献。它也将成为国际汉学家与民间文艺学家关注中国故事学史这门新科学创建的序幕。”[6]从小的方面来看,刘守华对于某些具体问题有着一种“钉钉子”的精神,不会浅尝辄止,而是深入下去,抵达问题的实质。例如他为了研究鄂西北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就先后多次亲赴实地考察,与故事传承人交心、谈心,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有了第一手资料后再不断地深入挖掘探索,也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使得他能在民间文学领域独放异彩。
其次,唯实的学术文风。刘守华崇尚踏踏实实地做学术,这和他的研究对象有关。民间文学和“非遗”项目本身就是来自于民众的,这里面潜在的就有一种唯实的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刘守华认为做学问的路子本就应该务实,他对于学界有些人喜欢空谈理论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在民间文化和“非遗”问题上。我们通读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可以发现这个特点,他虽然也会对一些宏观的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但不是泛泛而谈,更多是结合了实际问题的。例如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问题时,他就列举了自己曾经采访和交流过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孙家香等传承人的具体问题来谈。在刘守华的书中,我们随处可见的是一种平实的叙述风格,鲜有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用通俗语言表达清楚,不故作高深,这不能不说具有大师风范。
——李福清汉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