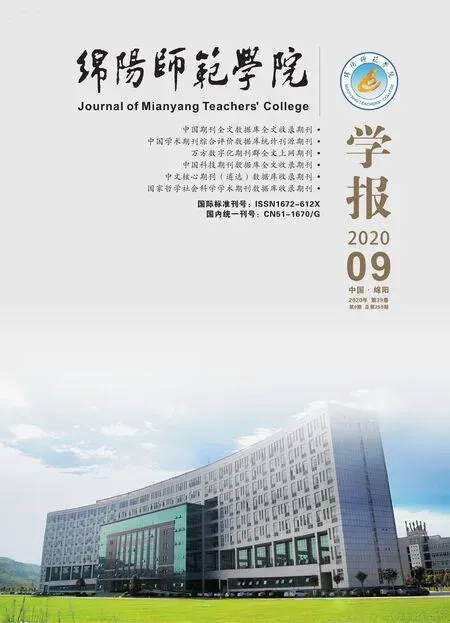论不可靠叙述风格的编码:一个符号学的分析
刘 娜
(1.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2.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404100)
作为叙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于1961年由韦恩·布斯首次提出。在其专著《小说修辞学》(TheRhetoricofFiction)中,布斯将不可靠叙述视为一种与可靠叙述相对立的叙述类型。在布斯正式提出这个理论范畴之前,不可靠叙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如《左传》《荷马史诗》中前后自相矛盾的叙述。不可靠叙述不再强调对真实与客观规则的遵从,叙述者刻意打乱叙述的清晰性和逻辑性,具体表现为叙述策略的多元化、叙述话语的模糊性、叙述结构的杂乱和松散。从可靠叙述到不可靠叙述,实则是从传统叙述的“说什么”转向现代叙述的“怎么说“,即叙述的重心由内容的讲述过渡到形式的展示。例如,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恐怖、暴力、变态的情节,就内容而言似乎与其他小说并无差异,然而正是由于麦克尤恩对不可靠叙述的深刻领悟与娴熟运用,使作品的叙述形式与思想表达都远远超越了其他同类小说,在文学界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不可靠叙述对叙述形式的革新,不仅赋予了文本复杂多变的风格,也为受述者解读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任何叙述都无法回避风格,叙述风格必然通过叙述形式来表达,叙述形式则是叙述者为构建一定的风格所做出的选择。然而,不可靠叙述的风格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对“不可靠”的界定不无关系。布斯基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对不可靠作了如下判定:“可靠的叙述者在语言和行动方面与作品的思想规范(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否则该叙述即不可靠。”[1]158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学界对“不可靠”的判定标准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两大学派——以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作为准则的修辞学派和以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认为不可靠是“阅读假设”的认知学派。两个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是都承认不可靠叙述主要是叙述者的不可靠。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叙述者不可靠并不是叙述内容的不可靠,而是表达形式的不可靠。国内较早研究不可靠叙述的学者赵毅衡教授再三强调:“叙述者不可靠是叙述的一种形式特征,是表达方式的问题。”[2]225不可靠叙述关注的是意义表达的形式,而风格则关系着意义表达的特点,二者皆属于形式层面的研究。因此,从风格的层面探析不可靠叙述再正常不过了,而不可靠叙述的独特风格也使其成为风格研究的绝佳样本。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对叙述者、隐含作者等的过度关注显然掩盖了对不可靠叙述风格的探索。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前人对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基础上,从风格的构成及意义、风格的编码主体、风格的编码途径三个方面分析不可靠叙述的风格问题,由此来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
一、不可靠叙述风格的构成和意义
风格是所有符号文本的特质,是具有区别性的形式特征。任何一个文本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基础意义,二是表现方式。例如,小说、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是基本意义的表达,而与之对应的表现形式包括语调、视角、音乐、色彩等因素。基础意义是符义性编码,表现方式则是风格意义的编码,对基础意义进行的补充编码。为此,里法泰尔曾将风格界定为“后符码”(code a posteriori)[3]78。这里所说的后符码实际上是将风格视为在语义文本之上追加的符码。巴尔特更是明确指出风格 “几乎在文学之外”[4]4。巴尔特对风格的定位有着清晰的认识,但现在风格已延伸至文学之外的其他表意领域。因此,赵毅衡从符号学的视野对风格的一般性规律进行了总结,将其界定为“文本的附加符码的总称”[5]1。这个界定简洁明了,直达风格内部,更具有普适性。
根据这个界定,不可靠叙述是文本内的建构形式,而风格则在文本之外,即风格是在文本基础表意之外进行的附加编码,赋予文本附加的品格,使文本从形式上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不可靠叙述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可靠”, 这当然不是同义反复,恰好说明“不可靠”是文本的风格标记。“不可靠”本身就可以用来区分虚构与纪实两种体裁。赵毅衡明确指出,“‘不可靠’,永远是虚构叙述中计算周到的叙述策略”[2]235,而与之相对的纪实叙述不可能不可靠。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附加”仅是指风格的编码方式,并不是说风格不重要。相反,风格很大程度上比文本的基础信息更能影响文本的意义解读,在不可靠叙述中,尤为突出。作为表意的重要成分,风格对于不可靠叙述文本意义的表达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首先,不可靠叙述风格是一种接收程式的期待,引导着受述者解释文本的方向和模式。不可靠叙述的过程就是叙述者设置陷阱的过程,叙述者以一种不可察觉的方式来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叙述,将自己伪装成可靠的身份,干扰受述者的文本体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叙述者所选择的叙述方式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但是不可靠叙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欺骗受述者,反倒是为了激发受述者的兴趣。为此,叙述者在文本中刻意植入风格意向性的叙述方式,使风格成为受述者解读文本的基点。一般情况下,接收者首先会注意到风格是来源于表层的感知。阿恩海姆指出,“人观看对象的过程是把知觉形式与所观看的符号对象形式相对照的过程”,即“视觉形式的接受”[6]54。虽然这里强调的是视觉形式的接受,但对风格同样适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电影、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这些叙述总是倾向于淡化甚至是割裂情节,如《罗拉快跑》中碎片化的描述使受述者从对故事的迷恋转向对梦幻风格的关注。
其次,不可靠叙述风格是文本意义的组成部分。符号并不总是与所指对象直接对应,反而经常越过对象本身,沉入无限衍义之中。风格引导接收者通过叙述形式进入内容本身,从而延展了文本的符号化表意的过程。受述者由此展开对文本深层表达的探索,重新审视文本的内容与旨趣。因此,风格意义的生产对于叙述者和受述者来说更为重要。不可靠叙述并不是仅为了形式进行的符号堆砌,更多的是出于对意义开放性和丰富性的追求。不可靠叙述文本由此形成以叙述为经线、以风格为纬线共同编织的意义体。
再次,不可靠叙述风格模糊了文本的实指。对不可靠叙述风格的追求必然是要牺牲叙述的清晰度。叙述总是被风格所搅乱,受述者难以看清文本的符义编码。J.M.库切的《内陆深处》将不可靠叙述发挥到了极致,诗意化的叙述风格掩盖着交错混杂的真假叙述。叙述者玛格达的思绪飘忽不定,穿梭于现实与臆想之间,虚实难辨,需要受述者拨开层层迷雾,回到元叙述层方能分清真伪。《内陆深处》并不是库切专门为形式进行的叙述实验,反倒是借助极端化的不可靠叙述表示出对后现代形式虚无的嘲讽。风格成为库切意图意义传递的窗口,受述者在进入文本之后,关注的重心已从符号本身的编码转向符号所指的对象及解释项。
受述者在分析不可靠叙述文本时,需要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探索,在阅读中重组事件,反思叙述者是否可靠,建立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体验过程,即从对风格意义的感知过渡到对风格背后深层意义的领悟与认知。风格—叙述—意义的解读路线实际上是意指的层层递进和意义的步步深入,这也回应了皮尔斯的符号三性论。皮尔斯认为显现性是符号的第一性,接收者的感知和解释使符号拥有了第二性,而第三性则是接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的判断[7] 25-27。
二、不可靠叙述风格的编码主体
一个完整的符号表意过程的两端是发送者和接收者。皮尔斯认为符号交流的过程必然包括以下三个条件:
(1)一个发送者和解释者;
(2)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某物的交流;
(3)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交流的某物能够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某些共同解释项[8]249。
风格自然是符号的交流,其意义在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对话中生成。风格由发送者通过媒介将携带有发送者意图意义的文本传递给接收者。最理想的表意过程就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文本的风格意义、接收者的阐释意义达成一致,对风格形成统一认识,也就是形成所谓的“共同解释项”。
在不可靠叙述中,风格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分别对应叙述者和受述者。不可靠叙述风格的意义正是叙述者和受述者共同编码而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叙述者的意图意义与文本语境、叙述者的意图意义与受述者的回溯意指之间的冲突。既然叙述者的意图意义是风格意义的起点,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叙述者到底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在文本中?长期以来,叙述者都是小说研究的重心,以人格化的形态出现,但人格化的叙述者对于小说之外的叙述体裁却不适用。对此,赵毅衡将人格框架扩展至“框架—人格”二象,即各种叙述体裁的叙述者都是以人格和框架两种形态同时存在,体裁的不同导致在具体的叙述中会在框架与人格之间滑动,这也是本文论证的立足点。“框架—人格”二象的提出打破了对叙述者人格形态的传统认知,是将叙述者扩展至广义形态的一大拓展。在此基础上,赵毅衡指出:“所有的符号文本的意义立足点,是这两个人格或拟人格(框架—人格二象)的距离问题:如果文本的再现者与隐含作者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9]
叙述者的不可靠具有很强的意图和目的性,引导受述者去发现文本的深意。叙述学家费伦认为:“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绝对不是随意投射出来的,而是预设存在着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动因,这个动因把大量的具体信号和推测邀请赋予文本和叙述者,让读者注意到叙述者的愚蠢的自我暴露和不可靠性。”[10]99叙述者一方面将意义判断的权力让渡给受述者,另一方面又设置陷阱,混淆受述者的认知。与传统叙述相比,叙述者走下道德权威的神坛,游移的话语使叙述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以隐蔽而非明言的方式展现给受述者,这就需要受述者自己加以判断[11]。影响接收者判断的是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布斯曾说道:“不可靠叙述的巨大作用主要来自于其所产生的微妙效果,而非对读者的简单迎合或诱导,当作者向读者传达某种隐含的信息时,他会有意构建一种针对故事内外所有不解之人的谋略。”[1]304
由于叙述者有意对阅读设限,文本内符码的不确定性增加,随之带来受述者对风格阐释的多义性。例如李洱的不可靠叙述作品《应物兄》抛弃了《花腔》的创作手法,整个叙述脉络清晰、情节分明,表面看似与传统叙述手法无异,因此对该作品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应物兄》是在向传统致敬;另一种却认为这是一种迂回的写作风格,貌似回归,实则颠覆。出现不同解释项的原因在于《应物兄》文本内部语义的丰富性和表层朴实的叙述结构之间的冲突。毛尖用“二重奏”来评价《应物兄》的风格,他认为书中充满了相互呼应或沉默、相互肯定或否定的概念,彼此的对应关系共同演化了总体性幻觉的风格[12]。
这里所说的“二重奏”其实是不可靠叙述的风格,是叙述者有意为之的结果。申丹指出不少叙述作品都是双重叙述进程的结果。其中,在主题意义上对文本叙述情节起到补充或颠覆性作用的叙述被称为隐性进程[13]。不可靠叙述中几乎都有这样一个隐性进程,文本表层的叙述与隐含叙述之间形成强烈反差,冲击着受述者的认知。“面对事物时,自觉到有认知差,需要获得意义来填补。”[14]当受述者意识到与叙述的真实意图有距离时,会主动获取意义。受述者一次次进入叙述者的陷阱,又一次次逃离这个陷阱,这是一个逐步否定和阐释意义的过程。文本的风格意义在叙述者的意图意义与受述者的阐释意义中得以丰富。
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与受述者不断建构与解构的交锋,双方关于意义的认知冲突进一步强化了风格,深化了意蕴。叙述的不可靠表现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的不可靠,价值规范隐含在文本内,来源于叙述者的叙述过程以及受述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过程。叙述的不可靠暗含了叙述者和受述者关于价值规范的叙述话语的冲突。
三、不可靠叙述风格的编码途径
风格的编码来自于风格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共同努力。对风格的发送者而言,双轴操作是风格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双轴是符号文本展开的两个向度:组合轴和聚合轴。前者是指“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15]156;后者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有可能代替)的各种成分”[15]157。以着装为例,衣服、裤子、鞋是服装系统的组合,衣服的款式、颜色等的选择就是聚合。
双轴操作实际上就是对内容和表达方式的选择过程。符号选择的主动性,使文本出现宽幅和窄幅的区别。所谓宽幅和窄幅是指对聚合轴选择的幅度。任何显现的符号文本背后的聚合段都是宽窄不一,因此选择的范围有大有小。宽幅可以使得文本具有多样的风格,窄幅所产生的风格单一。不可靠叙述呈现的风格超出了接收者的认知或经验范围,对接收者而言显得陌生而新奇,这就是宽幅选择的结果。
由于对聚合段的选择面更广,不可靠叙述摆脱了可靠叙述风格单一的局面,有意为之的不充分叙述的方式打破了叙述与表意之间的常规表达,也违背了受述者的经验期待,让文本浮现出虚实相间的风格。例如电影《盗梦空间》中的梦中梦、《追随》中的局中局都是在叙述形式上下足了功夫,嵌套的使用让受述者耳目一新,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情感和审美的期待。小说《密室中的旅行》则选择了回旋跨层的叙述,产生了别样的风格。布兰克先生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桌上文稿中有一份未完待续的囚犯自述。他续写了那个囚犯的故事,却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也早已被记录在手稿中。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更是一种反传统小说的叙述形式,结构凌乱、时间交错,如同迷宫一般让人难以捉摸。影片《太阳照常升起》的叙述也是形式的创新,影片的结尾才是现实世界的开端,如同一幅被打乱的拼图,呈现碎片化的风格。
对叙述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意味着叙述者对风格的预设。在不可靠叙述的众多叙述形式中,有一种极为不可靠的表达方式——低调叙述。低调叙述指的是叙述委婉,叙述者几乎完全隐身,拒绝帮助隐含作者确定价值,如同一个冷眼相观的旁观者,不会进行叙述干预或评论。低调叙述的目的是营造一种客观的叙述风格,受述者因而会误以为所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其实落入了叙述者预先设计的阅读陷阱。加缪的《局外人》是低调叙述中的杰作。主人公默尔索兼叙述者以极为冷漠的语调描述了自己的生活,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面对母亲的去世毫无悲伤的反应,甚至到最后自己面临死亡时也是无动于衷。看似客观、冷静的描述却给受述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根据加缪的创作观,形式和内容需要统一在风格的范畴里,而风格是需要适度表现、含而不露的[16]121。加缪所说的适度风格其实是由低调叙述带来的零度风格。零度风格并不是没有风格,而是风格的一种变体,是“一种有意指作用的欠缺,一种纯区分性状态”[17]160。 越是刻意追求无风格, 风格与无风格之二律背反就越明显。无风格,或称零度风格实则是附加编码中情感附加符码的故意减少,由此给受述者在情感上的冲击力更强,零度风格证实了“符号系统可以有‘从无中’创生意义的能力”[17]160。
如果说叙述者力求进行“不可靠”的风格编码,那么读者所进行的则是从不可靠中寻求“可靠”的信息,以此对文本进行二次编码,形成二度风格。受述者的风格编码刚好是对叙述者编码的回溯。符号过程的完成实际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符号信息的文本意义、接收者的解释意义一步步把前者具体化的过程。但是在不可靠叙述中受述者的解读和二度编码刚好是对前者的一步步否定,这点类似于皮尔斯的试推法。叙述者编码越不可靠,留给受述者二次编码的空间越丰富,对风格的二度编码也就更加多样化。
受述者进行的二度编码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有文本的秩序进行重组,对原有文本意义的重建。同一个叙述文本面对复杂的受述者群体,解码方式和意义的生成会相差甚远。风格意向的文本容易把受述者的解释引向风格本身,受述者由于受到元语言的限制,对同一风格会有不一样的二度编码方式,得出不一样的二度风格。例如,有的受述者仅注意到风格本身,而有的却能关注到风格背后的隐喻。因此,受述者通过协商式解码、不足解码或过度解码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再次解读所形成的二度风格不一定与发送者的意图一致。
四、结语
不可靠叙述一直以来都是叙述学的核心命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风格为切入口,从符号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会发现不可靠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更是意义表达方式的反思与实践。意义是不可靠叙述的核心,由叙述和风格共同编织而成。风格意义形成的双重动力是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共同编码。叙述者有意营造文本表层“不可靠”的叙述风格,引导受述者进行“可靠的”二度编码,二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冲突,丰富了叙述的张力,彰显了不可靠叙述的艺术魅力。不可靠叙述现有的研究主要锚定在文学领域,布鲁诺·泽维克认为“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最终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策略”[18]。目前,文学领域之外的不可靠叙述正蓬勃发展,其风格的研究具有广大的前景,有待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