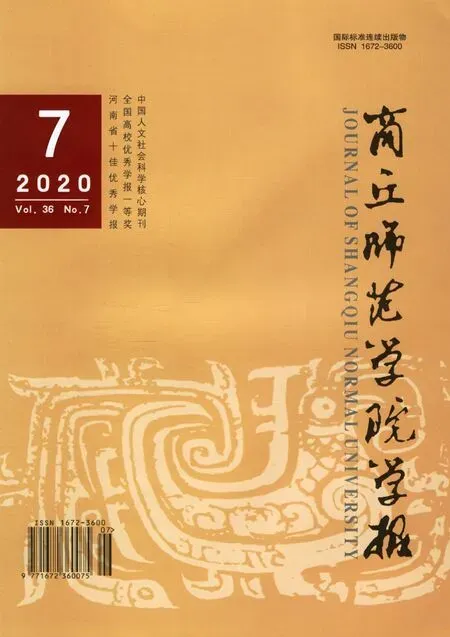从拉铁摩尔到“新清史”学派:西方中国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新范式”的渐立
王 建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东亚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更是举足轻重,特别是在古代,中国的发展甚至决定了东亚历史的走向,其发展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东亚历史的主线。基于这些事实,史学界在书写东亚历史特别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史时,通常都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为中心,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史学界是如此,国外和西方史学界也是如此。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在考察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史方面,西方史学界部分学者的视角逐渐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内亚”概念的引入。在引入这个概念后,西方史学界逐渐出现了一种趋向,即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在考察上述两者间的关系时,将着眼点放在北方少数民族上。在此基础上,到了近代,以“新清史”学派的出现为标志,西方史学界逐渐确立了中国史书写的“新范式”,即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体考察某些时段的中国历史,甚至不将这些时段的历史当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将其看作是独立的异族史的一部分。这种倾向应引起我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主张,我们必须予以明确、有力的回应,因为很明显,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还涉及很多实际的问题。
一、“内亚”概念及其新视角
西方史学界视角转换和书写“新范式”确立的进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拉铁摩尔那里,而拉铁摩尔的影响则在于他对“内亚”概念的发挥与运用,即从“内亚”视角出发形成的一系列独到的新观察。在拉铁摩尔之前,“内亚”概念已经被提出,它出现于19世纪上半期,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特提出的。之后,这个概念为西方学界所接受,许多学者在解说亚洲地理时都会运用该概念。比如,俄国学者布罗卡蒙斯1900年就运用过这个概念,他认为,亚洲大陆所有内部闭塞的地区都可以被称作是“内亚”[1]。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内亚”一词只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被使用,并未被引入历史领域。进入20世纪后,该词才逐渐为西方历史学界所接受,而且在历史学家们的使用过程中,其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它也由一个单纯的自然地理概念变为一个含义丰富的历史地理概念。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内亚”的提法十分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含义,更在于其视角。就其本身来说,它的出现频率虽然很高,但其含义却十分模糊。关于它所指代的具体范围,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学术界对该概念的运用是相当混乱的。不过,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一点,即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有关。“内亚在涉及传统中国的地理范围上,最大的区域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最小的范围则是19世纪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2]很明显,这个概念涉及许多中国边疆地区,也自然会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些地区,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以说,不论这个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如何混乱,它都代表了一种观察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的新视角,这种新视角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在“内亚”概念的运用和推广上,许多20世纪的学者都曾发挥过作用,其中拉铁摩尔的影响尤为显著。拉铁摩尔是一个眼光独到的田野调查者,他曾在中国北部作过广泛的游历和考察,足迹遍布新疆、东北等地。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对古代中国的四个边疆区即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上述四个地区在生态环境、历史发展和民族成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间也存在一定的互动依存关系。在观察上述地区和审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拉铁摩尔还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原王朝的历史循环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循环有着密切的联系,“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国循环的结果”[3]377。但他也没有忽略北方少数民族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拥有参与历史的能力,草原民族的参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在拉铁摩尔的观念中,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主动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也将他们的一些特征打入到中国的肌体中。
拉铁摩尔的许多观察都是独到的,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视角。可以说,拉铁摩尔持有一种典型的“内亚视角”,虽然他是从解释中国历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古代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但他的聚焦点无疑是所谓的“内亚”。他集中分析内陆边疆地区,这实际上是在作一种一分为二的考察。他指出“内亚”各地区间的共同属性,指出内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缺乏共生的有效机制,这实际上也突出了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内陆边疆地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种强调也在有意无意间突出了上述地区的“主体性”。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是明显的,从这种视角出发,他可以得出从许多其他角度难以取得的新认识,但也存在过分强调所谓的“内亚”的倾向。
拉铁摩尔的很多见解是极富见地的,也并无过多不当之处,其视角也不应受到批评,但仍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实际暗含着一种将“内亚”和中原对立起来的倾向。其中的危险之处不在于拉铁摩尔的论述本身,而在于后来者对他论述的进一步解说。这些解说存在着在与历史实际脱节的轨道上越走越远的可能,而且一旦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它们就可能对人产生误导,甚至会在现实中产生消极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拉铁摩尔之后,“新清史”学派扭曲了他的观点,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十分不恰当地解释。
三、“新清史”学派与西方中国史书写“新范式”的形成
在拉铁摩尔等人之后,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解释在总体上沿着三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一些人继承传统的立场和做法,在书写中国古代历史时,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当作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书写中原王朝的历史时一并提及。另一个方向是一些人继承了拉铁摩尔的立场,即将所谓的“内亚”地区视作是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区,进而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审视其历史,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强调古代边疆地区的“内亚特性”。同拉铁摩尔一样,在强调与中原地区的差异的时候,他们实际凸显了边疆地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他们仍在中国的大框架下审视“内亚”,其注意力已更多地投向边疆地区,其视角也与拉铁摩尔一样开始向“内亚”转移。还有一个方向是一些人则沿着拉铁摩尔的方向越走越远,以至于超出了必要的界限,完全偏离了传统的立场,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谓的“新清史”学派。
20世纪90年代,“新清史”学派在美国兴起。这个学派标榜全球视角,强调清朝历史发展中满洲因素的重要性,提倡在相关研究中运用满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声称其研究多依据满文史料[4]。应该承认的是,“新清史”学派在许多方面是有其成就的。比如,由于在研究中提倡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他们在历史细节方面有过不少新发现;其视角也有可取之处,从“内亚”的视角来审视和解释清朝历史,无疑也会取得一些从其他角度出发难以获得的新发现。但在史实考证方面的成就无法掩饰和替代其立场的根本错误之处,因为如果对历史的整体解释与历史实际背道而驰,即使其对历史细节的揭示再正确,也是于事无补的。“新清史”学派的谬误之处在于他们的基本立场和根本主张,而不在于其对历史细节的考证。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严重偏离整体历史进程的“内亚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内亚”概念在他们那里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概念[5]。“新清史”学派认为自己在学术思想上是追随拉铁摩尔的,这或许是因为拉铁摩尔的视角给了他们以启发,特别是在重视内陆边疆地区独特性、强调北方少数民族的“内亚特性”等方面。但应该指出的是,“新清史”学派与拉铁摩尔等人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虽然对后者的某些观点有过继承,但实际上又作了很大的发挥,以至于其历史叙述在总体上已严重偏离了历史实际,甚至达到了歪曲、虚构历史进程的程度。比如,他们刻意突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主体性”,甚至不认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总的来看,两者间最主要的分歧是立场和视角上的分歧,可以说,拉铁摩尔所持的是一种以中原王朝为中心、侧重考察“内亚”的立场和视角,而“新清史”学派的学者则大多持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内亚中心论”的立场。两者孰对孰错,不言自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虽然不容忽视,但包括清王朝在内的诸中原王朝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尽管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立场,不得不承认的是,“新清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了对传统范式的突破,在此基础上,他们还确立了一种中国史研究和书写的“新范式”。“新清史”学派自出现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随着该派学者的努力,用“内亚视角”审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和清朝历史的学者已变得越来越多,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假如说存在一个用传统立场解释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的学者群体的话,那么“新清史”学派已壮大到能够向他们发起挑战的程度,甚至许多原本持传统立场的学者在该派的影响下也已改换门庭、加入其中。如果追溯一下相关的学术史,其源流也是清晰可辨的。如果说拉铁摩尔等人代表了视角转换的开始,那么“新清史”学派的出现就代表了视角转换的完成。不仅如此,该学派对历史的解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标志了一种“新范式”的形成。这种“新范式”的总体特征是,一些人认为自己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寻找到了新的对象,发现了新的“历史主体”,并用这种新的“历史主体”来解释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进程,尽管这种“历史主体”在实际上并不存在。
“新清史”学派的立场和其所确立的“新范式”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涉及许多实际问题。它涉及历史的主体问题,涉及历史解释的话语权问题,甚至还涉及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在这方面,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将满族与中华民族区分开来,将清帝国与中国区隔起来,显然具有一定的分离主义色彩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嫌疑。”[6]很显然,如果任由其发展,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将会陷入被动境地。对此,我国学者必须直面挑战、勇于回应。
——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