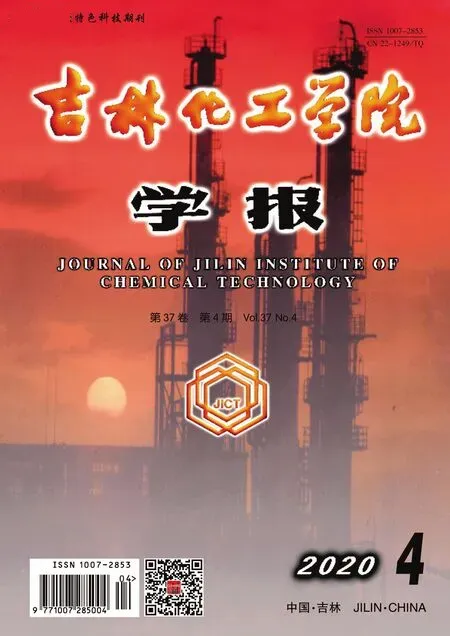试论“翻译”对中日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影响
何 荷
(1.无锡太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23001;2.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两国均通过引入西洋文明、西洋理念,以寻求实现 “近代”的变革。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皆借助“翻译”这一手段引入西洋文明。而中日两国不同的翻译实践,鲜明体现出近代中国和日本在面对西洋文明、西洋理念时不同的接受方式和处理思维。试图通过比较近代日本“明治翻译”以及近代中国“晚清翻译”的翻译主体、翻译手法的不同,以及“明治翻译”对“晚清翻译”的影响等,分析近代化过程中的“翻译”,经由对近代 “言文一致”的推动,进而对中日两国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产生的影响。
一、“语言”对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影响
如若探讨“翻译”对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影响,首先要明确的是,如何定义“近代民族国家”,它由哪些要素构成,或者说它是如何被建构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详细阐述了“民族”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说明了该词在近代经历的各种语义变迁。该书指出,1925年的《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对“民族”的解释是近代关于“民族”的最初定义:“拥有共同族群根源的人群,他们说着共同的语言,承袭相同的文化传统”[1]。按此解释可知“民族”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共同的群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然而事实上,“民族”并不能够直接跟“国家”画上等号,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由复数民族构成的国家,也有很多由同一民族分裂出的不同的国家。然而日本却显得极为特殊,岛国性质(即边界较清晰)的日本一直以 “单一民族”[2](大和民族)自居,并以天皇的子民为豪。可以说日本的“单一民族”属性,让其拥有了“国家”=“民族”的均质结构。而与这种单一性和均质性相对,中国则是多民族构成的复数民族国家。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要素中所谓“共同的语言”一项。1866-1869年,欧洲陆续发表研究报告,称“语言才是决定民族归属的唯一指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同样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被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语言的本国化[3]。这自然是因为“共同的语言”除了可以彰显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之外,也同时会加强共同语言民族内部的集体认同。当然,“语言”与民族国家也并非一致重合的概念,但在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却同样呈现出了相当高的同质性。由此看来,如果说“共同的群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是建构民族国家的三要素,那么“大和民族”、“标准日本语”、“日本文化”的三位一体则共同构成了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然而这一大和民族的单一性以及日本语的同质性,再加上明治以后力图通过对传统汉文化的否定而进行的日本文化主体性构建,极易产生强有力的排斥他者的思想与话语装置。不少学者认为,这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想象,配合日本以皇道思想和神国观念为核心的历史观,强化了天皇崇拜和日本国家崇拜(皇国、神国)的思想,进而催生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最终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4-5]。而这一过程中,明治时期对西洋书籍的大量翻译所推动的“标准日本语”的诞生,在“语言”的层面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二、“近代化”场域中的“明治翻译”
18世纪以前,日本幕府闭关锁国,直到美国的坚船利炮将其国门打开。与中国对西洋文明由抵抗至妥协的“始而漠视、继而仇视、终而师视”不同,日本因为对固有文化(主体为儒家文化)执念不深,迅速开始学习西方文明,很快就把“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成了卓有成效的行动,于1868年展开明治维新,倡导文明开化,迈向近代社会。而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主要是通过翻译西方的科技、医学、哲学、教育等书籍的方式来进行的。简言之,西方文献的翻译是日本导入“近代观念”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然而这一对“近代观念”的引入却是在否定传统儒学,解除长久以来中国文化的支配和禁锢的基础上进行的。1876年,素有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之称的福泽谕吉写下《劝学》(『学問の勧め』),以求开启民智,但同时对儒学和封建阶级意识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主张吸收欧美近代的民主精神和实用主义思想,并强调独立和自尊的重要性[6]。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以欧美近代文化为师,批判日本儒学主义与国粹主义;认为日本为求自身的近代化,必须摆脱精神形态上的“亚洲固陋”。可见,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始终试图从深受千余年中国思想文化支配的精神桎梏中挣脱出来,并意欲创造新的西方精神形态。
然而与日本举国上下对西洋文化的全盘接受不同,中国的革新则因自古以来的作为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对西方文明进行抵抗,在多种意识形态相互角力而产生的接连“阵痛”之后,终于在“晚于日本30年的1898年(戊戌变法)才真正开始进入到‘近代’的体制变革进程中”[7]。村田雄二郎认为:“这30年的时差,反映出了中日两国近代质的不同。让日本在亚洲成为了近代化的‘优等生’和‘领导者’,而中国则沦为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的近代化的‘差生’和‘被动者’”[8](中国通过“翻译”引进西方文明也同样比日本晚了近30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尽管两国均感受到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并力求引进西洋文明走向近代,然而不同点则在于日本致力于用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和科学思想,清除中国汉文化或者说传统儒学对国民精神的禁锢,创造与近代化相一致的国民精神和民族主体性;而彼时中国尚未进入到抛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道德旧思想)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中,用张之洞的话来说便是强调儒家学说重要性的同时,吸收西洋文化以补足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这一特征也反映到借由“翻译”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中去。
三、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的矛盾
日本明治初年,为适应“文明开化”的需要,知识分子们大量翻译西方文献典籍,意欲塑造西方的精神形态。明治头十年甚至被称为“翻译的时代”[9]。哲学、文学、政治、宗教、生物、医学各领域的西洋书籍均被译成日语,西洋社会的思想、观念、风气无孔不入。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翻译欧美新概念的过程中,日本人没有使用大和语来进行翻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双音汉字词被创造了出来,如“社会”、“个人”、“恋爱”、“存在”、“自由”等词汇均为此类明治翻译的发明[4]。那么,为什么要创造新的汉字词而不用日本原有的“大和语”呢?小森阳一认为这是因为在日本原有的大和语中没有诸如“恋爱”、“进步”等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概念,无法使用日本原有词汇或按照原有的大和音训读之;此外,如果将新造的双音汉字变成罗马字或假名的话,由于无法想象声音背后汉字的表意性,声音所代表的意义变得无法把握。显然汉字词成为了日本近代翻译西方新概念、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并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汉字新名词的大量创造为晚清的汉译日书提供了便利;然而,不得不说这一翻译理念与明治时期全盘西化否定东方传统的维新主张之间充满了矛盾。
与西洋文献翻译过程中汉语词汇的大量创造相对,在明治初期的“言文一致”运动中,“汉字废止之议”(前岛密)、“汉字消减论”(福泽谕吉)、“假名文字论”(假名文字会)、“罗马文字论”(西周)被提出并受到广泛关注。支持者们认为近代中国因循守旧,不知进取,中华文明毫无可取之处,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洋的原因主要在汉字的使用上,因而日本使用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汉字”不仅暗示着日本的‘野蛮性’和‘原始性’,更会阻碍“日语”的近代化。基于上述原因,“汉字废止之议”的提出者前岛密主张将汉字排除到日本文字之外,单纯使用假名文字,以便于更好地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步入近代化[6]。柄谷行人认为,言文一致是建立近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事项,然而日本的言文一致却始于有关“文字”的新概念,其根本在于文字改革和汉字的否定[6]。显然,上述理论将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汉字作为异质性的他者,而假名则似乎具有构筑日本文化的纯粹性,支持者们将汉字和本土化了的假名置于二元对立的系统中,并试图通过汉字的废止来强化本国文字的主体性地位。“汉字废止之议”等文体改革论的提出无疑迎合了文明开化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蔑视和否定,而汉字则首当其冲成为了排斥中华文明的手段和试图被革命消解的“他者”。这里姑且不问有关文体改革的诸论调最终是否成立,明治翻译过程中大量汉字词汇的创造与言文一致运动中的汉字消解论所构成的二元对立则显而易见。并且有趣的是,“汉字消减论”、“假名文字论”、“罗马文字论”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几乎是明治时期从事翻译,创造汉字词汇的同一批人。
毋庸讳言,明治初期的翻译人员大多为具备西洋文化知识,并拥有深厚汉学修养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西周、中村正直、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均为明治翻译领域的佼佼者,正是他们将仅存在于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中的新概念套上汉字,创造出大量双音汉字词汇。阅读西方文献,理解西方文献,并将存在于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中的新概念翻译过来的翻译人员不如说正是吸收、解释、传播西方文明、挺进西方文明的主力和先锋。并且,他们在作为真正挺进西方先进文明的开拓者的同时,也成为了日本“近代日语”的创造者。然而,用东方汉字罐装西洋文明的“近代日语”总让人觉得有些自相矛盾,充满悖论。在翻译西方新概念时,翻译人员似乎未能贯彻明治维新过程中,消除汉字,摆脱“精神形态上亚洲的固陋”这一理论主张。提出了“汉字消解论”的福泽谕吉自不必说,同为明治翻译先锋的二叶亭四迷在《我的言文一致的由来》一文中说:“我自己的规则,是不使用没有得到国语资格的汉语”[9]。这里,二叶亭四迷用“资格”来界定近代日语,同样意欲将自古以来作为日语表记方式的汉语驱除到近代国语系统之外。大批知识分子将“国语问题提到‘关乎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认为‘一国之语,为该国独立之要素’,忧心忡忡地陈述日本文体的重要性”[4]。可见,翻译者们一方面为图翻译之便创造着汉字词汇,一方面又吵吵嚷嚷意欲将汉字排除到日语之外,强调大和语作为国语的重要性。如果说“汉字”的过度输入是汉语对日语殖民地性质的殖民,那么翻译人员为了翻译欧美新概念而大量创造汉字词汇,无疑是一种用汉字代表的汉文化来进行自我殖民的过程。然而这一矛盾却似乎被日本知识分子看似无意的忽视了。小森阳一这样解释明治翻译人员自我主张与自身翻译文体之间的矛盾:“因为翻译文体的主要概念是‘欧文直译体’,即‘醉心于欧化主义’的行文方式,所以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始终未能意识到自己实践过程中的言行不一致……这一时期甚嚣尘上的殖民地无意识结构导致了他们不将‘矛盾’视为‘矛盾’,或者不愿视之为‘矛盾’。而是自欺欺人第把它搁置起来。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回避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思维停滞的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翻译人员并没有办法将作为欧美列强‘文明’‘进步’证据的一些新概念翻译成大和语。欧美的新概念只能通过对身为表意文字的汉字进行重新组合去表达。结果,本应从书写体系中被排除出去的、被蔑视为文字‘化石’的汉字反而加剧了自我殖民化的现实”[4]。
而这也恰恰说明,由汉字彰显的汉文化渗透到了“近代日语”的生产过程中,试图“废止”汉字,或者说“消解”汉字的提议和尝试最终输给了在生成“近代日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翻译”这一实践活动,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可以说“近代日语”始终未能成功挣脱来自汉文化的影响。关于这一时期翻译文体的具体样式,王晓平引用了《东京日日新闻》主笔福地英痴在1875年8月发表的文章:“当时翻译西洋书籍的人使用的是:全文的结构——英;使用的词语——汉;接续的语法——日,这样一种三不像文体”[10]。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日语”似乎成为了融合东西方文明的载体,而用代表着东方文明的汉字罐装西方文明概念的翻译者,不如说是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文明揉入了东方文明的“近代日语”的创造者。
四、明治翻译文体的产生以及对晚清翻译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日语是一种“汉字假名混合体”,它既保留了汉字,又有完全是表音符号的假名,“汉字废止之议”、“汉字消减论”、“假名文字论”、“罗马文字论”最终只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层面,在翻译实践中被淘汰。即便如此,明治翻译对作为国语的“近代日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抛开为引入西方概念而创造出的大量汉字新词汇,“明治翻译基于西洋翻译句式产生的翻译文体,解构了传统汉文体的句法结构,导致了汉文体的崩溃;同时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建构了全新的文章感觉基础”[4]。小森阳一在《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中,以森鸥外翻译的《即兴诗人》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与夏目漱石并称为明治文坛双壁的森鸥外,自1892年至1901年倾注全力翻译了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并在翻译过程中付诸实践欲创造‘调和国语与汉文,融合雅言与俚词’的新文体。事实证明,森鸥外将汉字控制到最小限度,而业已定格为大和语言的表达均以平假名表记的文体创新是成功的,日语版《即兴诗人》被认为是超出原作高于原作的‘创作’,而非简单的‘翻译’。青年知识分子们盛赞森鸥外的翻译文体,感动于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迄今为止未曾存在过的新型文章结构的‘日语’文体,并且深信诞生于翻译的近代‘日语’同构筑了原文的‘德语’具备了对等的地位”[4]。
简言之,可以对抗西方语言的“日语”,通过对西方语言的翻译而作为实体被创造了,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将近代“日语”作为优秀国语的自我认同。小森阳一称这其中隐藏着近代日本“翻译民族主义”曲折精神的典型结构[4]。另一方面,关于翻译文体对传统汉文体以及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赵京华在《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考察:“均质的翻译文体句式为日本知识阶层塑造了全新的文章感觉基础,传统汉文体的创作思维和叙事方式不断变形直至崩溃,明治知识分子们或模仿翻译文体进行文学创作,或因无法逃脱翻译文体的影响,这期间的创作带有强烈的翻译文体的风格,叙事模式逐渐向西方文章结构为基本模式转变,并形成了新的近代语言叙述形式。作为日本近代‘言文一致’标的的小说《浮云》,甚至是二叶亭四迷先用俄文写成后,再以口语将其译成了日语。在此基础上,配合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大众媒体报纸的出现,并在读者阅读行为的积极参与下,日本近代“言文一致”的叙事方式得以形成”[4]。显然,明治翻译作为方式、手段和媒介,对经由“言文一致”运动得以确立的近代日语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并且,事实证明,通过“翻译”引进西方文明,迈向近代的举措是成功的,日本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便已摆脱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一个贫穷落后封建割据的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完整统一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而中国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没有进行任何新的社会变革。
目睹日本走向近代的现实,梁启超把日本人的成功看成是他们翻译西洋书的结果。并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今不迅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10]。欲效仿日本,通过翻译西洋书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此外,梁启超认为,因日本已将西方语言翻译成了日语,中国只需将日书译为中文即可,因为“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开四万万人之志”[10]。由此,晚清开始了日书汉译。不容忽视的是日书的大量翻译及由此产生的反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名物、新概念、新表述,对晚清文学语言、文体和文风造成不小的影响。“从1899年到1904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后来的《新民丛报》上,以所谓新文体,发表了一百多篇幅文章和专著。这种新文体即是指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书籍以及当时报刊上登载的议论文字,和青年人仿作文章所采用的一种半文半白、半中半洋、长短相间的一种文体。从文字角度来论,“社会”、“民主”、“经济”、“人民”、“科学”等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均为晚清文人通过对日语译名的借用,从而进入中国。类似日语借词多达890个,遍及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11]。值得关注的是,同时代颇具话语权的严复,同样进行了大量的西洋术语翻译工作,其翻译的译名虽具有与日语译名同构的文化想象,但因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日本化以及日本教材的译介和引进,最终在与日语译名的对抗中,被历史淘汰[12]。由此,日本明治翻译对晚清翻译产生的影响可见一斑。
五、结 语
中国和日本开启近代的30年的时差,造就了中日两国近代的“质”的不同。而这一“质”的不同或许正反映在中国对西洋近代文明一边抵抗一边接受的磨砺和复杂,与日本式毫无抵抗感地全盘吸收的简单粗暴所构成的两种近代化的方式上。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还是戊戌变法中的守旧与维新,面对西方文化,中国的抵抗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恰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展开知识、技术及权力的对话交流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西方文化融入到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之中。或许这正是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保有主体性的关键所在。晚清翻译,通过汉译日书,在保持东方儒家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走出了一条富有包容力的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日本的近代“翻译”,以及由此展开的“言文一致运动”,无视翻译理念(消除汉字)与翻译实践(创造汉字新词)之间的矛盾,在对支配日本文化近千年的东方儒家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排斥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文明,从而迅速成为与西方国家比肩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一条被批判为是“丧失主体性”的“西洋崇拜”的日本式近代化道路。而这西洋崇拜中包裹着的殖民性和侵略性,以及“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的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幻想所产生的排斥、歧视他者的话语装置,配合日本以皇道思想和神国观念为核心的历史观,使得日本陷入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泥沼,最终走向侵略扩张的道路。毋庸讳言,晚清翻译因直接使用日译新名词,传统文体发生改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通过融合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方式进行近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尚未进入到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中;而日本则用否定东方,抛弃东方,将东方他者化的方式完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