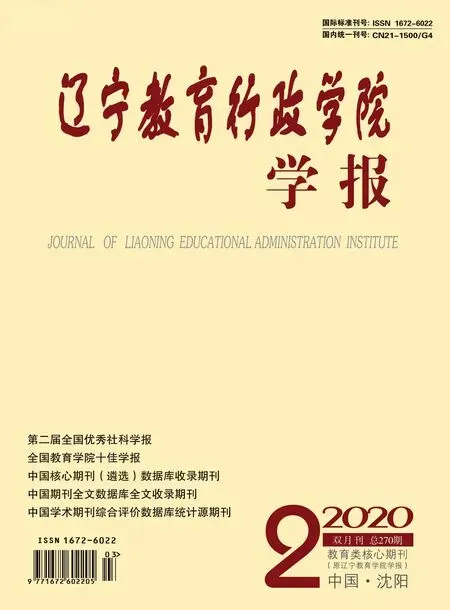总结、比较与致用
——“风骨”范畴四十年研究路径探析
林佳锋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541000
一、近四十年“风骨”范畴研究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文艺工作者们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1]自古以来,“真”“善”“美”即是教化与审美的和谐统一。陈望衡认为刘勰的“风骨”说正是审美与教化统一而完善的标志,[2]习总书记提出“真善美”的价值观要求恰与刘勰在“风骨”论中提出的“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对“风”所要求的教化、感召和规谏不谋而合,这就为回顾四十年来“风骨”范畴相关研究成果并做出述评,提供了契机。回顾梳理并反思这四十年来走过的路,选择对“风骨”范畴的研究进行述评是符合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要求的,或许能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新时期发展有所启发。
涂光社认为早年学界对“风骨”内涵的研究讨论开了范畴研究之先河:“古代文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是范畴研究。从早年对风骨内涵的论争,逐步扩大到对和、气、体、势、味、韵、意象、境界……的阐释,”[3]“风骨”范畴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关研究百花齐放。
学界关于“风骨”的第一次大讨论发生于20 世纪60年代。廖仲安、刘国盈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年01 期的《释“风骨”》对黄侃的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风’是情志,‘骨’是事义”,引发理论界的讨论。陆侃如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 年02 期的《〈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书〈释“风骨”〉后》、寇效信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 年06 期的《论“风骨”——兼与廖仲安、刘国盈二同志商榷》则对《释“风骨”》的说法提出了一系见解。王运熙于1963年3 月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提出自己的看法,再驳“情志事义”说。这些论文都发表于改革开放前,不在笔者本文研究范围内,但正是这一些学界的探讨,使得“风骨”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使近40 年来,相关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自1978 年开始,仅篇名、关键词均为“风骨”并且属于文论研究的论文,发表于中国知网上可供查阅的篇数就已达138篇,如此苛刻的搜索条件就已至一百余篇,更遑论其他与“风骨”相关的论文了。
在如此大量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实为没有新意的累叙之作。这些重复前人观点化为自己的“研究”,此则古代文论研究乃至文艺学理论研究的一大问题。一方面在于“风骨”范畴具有高度的成熟性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方法与眼光的局限。按谭佳的说法:“研究者往往‘悬置’了当代语境,忽略了阐释的现实意义,拘泥于单纯的古代文本解读,并常常对自己的研究有着绝对把握和对权威地位的期望,”他认为古代文论的“终极目的”在于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以建立具备中国特色的相应的文学理论体系。[4]
总的说来,“风骨”这一范畴的研究在近40年来是有一定建树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困境。在新时代的今天,“风骨”研究依然可以有所发展,可以有所突围,笔者认为研究“风骨”在古今文论衔接中的角色,并将“风骨”范畴纳入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中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观建设中,并作实际应用是突破“风骨”研究困境的方向。
二、总结、比较与致用
(一)“风骨”内涵的总结问题
纵观相关理论研究著作与文献,笔者发现近40年来“风骨”的内涵研究,是相关研究中最热门的,其中尤以引用或反驳黄侃、刘永济、罗根泽、寇效信等学者之观点最为常见。陈耀南发表于1988 年的《〈文心〉“风骨”群说辨疑》,通篇以表格形式列举了10 组60 余位学者的观点,其中既有作为“基础”的黄侃等老先生观点,又糅合了后来者的观点,的确做了些整合的工作,细看来其将观点应有尽有地罗列出来,但如文中将舒直、王达津乃至李建钊等人统归一组,以“唯有统归一组了”无奈结尾,未免有点虎头蛇尾。[5]近40 年间,学者们对于前人理论的阐释与总结有着各具特色的梳理:
如蔡育曙总结了五种阐释“风骨”的说法:黄侃提出的“文意文辞”说;傅庚生“想象作用”说;刘永济“情思事义”说;罗根泽、炳宸、詹瑛的“风格”说以及牟世金的“总要求”说。[6]
张海明则仅将“风骨”内涵的说法分为三种:以黄侃、范文澜为代表的“文辞文意”说;刘永济、廖仲安、刘国盈等的“风为情思,骨为事义,采为文辞”;寇效信、郭绍虞、詹瑛等人将“风骨”作为提纲挈领、总领文章内容、形式的“要求”。[7]
俞香云认为“风骨”内涵的“代表性”阐释大致有十三种之多:黄侃、范文澜的“风意骨辞”说;刘永济的“情志事义”说;王运熙的“风格说”;徐复观的“刚柔之气”说;宗白华的“情感思想”说;罗宗强、牟世金的“感染力”说;张少康的“精神风貌美”说;寇效信的“内容形式”说;周振甫的“美学要求说”;陈耀南的“风”为风趣、气韵,“骨”为文采、辞句、题材的说法;童庆炳的“风清骨峻”说;李壮鹰的“动静之美”说;张海明的“认为‘风’是作品的情感倾向,‘骨’是作品的思想倾向”观点。[8]
周才庶将论及“风骨”内涵的说法分为两大类:分论“风”“骨”以及整体性阐释“风骨”。周才庶以“阐释场域”对风骨的含义进行划分,分别进行“风”“骨”的语义还原,认为“若再用现代逻辑和现代化与来给‘风骨’一副固定的解读,实则是对想象的禁锢”也有一定道理。[9]
绝大部分相关论文的行文模式是以列举几类或几种“风骨”内涵的前人说法,几种常见的说法在上述例证中可以轻易发现,如黄侃、范文澜为代表之“风意骨辞”说等,再从这几类说法中寻求一种作为作者立论的立足点并进一步作自己的“新诠”“新释”“新论”“再阐释”,等等,但实际上所论述的观点都相差不多,以至于“风骨”论研究的同质化成果较多。
郁沅于1998年排除了四种其认为是与《文心雕龙》相冲突的说法,认为可以成立的说法仅能分为三种派别,即“风意骨辞”派:如黄侃、范文澜、王运熙、周振甫、寇效信、牟世金、张文勋等皆为此派;一种为“情志事义”派:如刘永济、廖仲安、刘国盈、郭晋稀、张少康等持此说;再有一种郁沅本人所持的“‘风’是一种情感的力量,‘骨’是一种逻辑的力量”观点,代表人物则是罗宗强、叶郎、涂光社等。[10]假设以郁沅的立场出发,我们能发现在上述引据的论文中的诸种分类显然是错误的,是具有误导性的,更毋论其中好几种说法都被郁沅所排除了。
“风骨”内涵的总结混乱,既有可能容易将两个没有关系的阐释化为一谈,如将“风骨”的涵义与内涵混为一谈,又有可能徒增两位学者的阐释意义的错误对立。而随着时间推移,新的语境下提出新的内涵阐释是正常的,新加入阐释队伍的有亮点的阐释自然需要被总结,如上述论文中俞香云将张海明的观点列入其总结的几类说法之中。郭外岑认为“即对古代某一文论概念的解释,往往是和当时人们掌握知识或接受的文艺观念密切联系着的”。[11]
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本身就具有含糊的特点,有学者称之为“浑成性”。涂光社认为“西方的理论范畴是高度抽象的,理论家一般都为自己运用的范畴做出定义……中国古代范畴几乎都不曾有过严格的定义,古代作家和书画家常常以艺术的而非逻辑的话语表述其感悟、体验和追求,许多范畴概念全由他们随机运用”,还提到“风骨之类内涵模糊,变异性较大,其意义就很难界定……恰恰是民族特色最鲜明、最具代表性的一类”。[12]
部分学者治学不谨,既不对自己引用的前人阐释负责,仅引用到使自己的论点能立得住脚的或支持或反对或能够笼统包括的理论即可;又不愿耗费字数对诸种阐释的分类标准作述,将“风骨”释义、内涵、审美特质等化为一谈,如此行文难免自说自话,并再以另外的表述表达前人意思又作成所谓“新解”,已经谈过的内涵、特质、价值竟又成了“新意”所在。
(二)“风骨”的比较研究
笔者研究发现,“风骨”作为古代文论的范畴外延,对其作比较研究是近40 年来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且该类型研究于近20 年来愈来愈多。这些比较研究有的如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形成了与“崇高”作比较的体系;有的则通过打开新的文化视角去理解“风骨”,如从印度文化、彝汉诗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些问题或能够给予学界一些启示,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三类: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东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比较研究。
1.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
(1)“风骨”与“崇高”。将“风骨”体认为阳刚之美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之一,在詹瑛看来,“风骨”是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在于鲜明生动、雄健有力,与朗吉弩斯的“崇高风格”可算不谋而合;王运熙以为:“具有风骨的文学作品,除掉具有思想感情表现的明朗性和质素而劲健有力的语言之外,还有两点显著的风格特征,其一是刚健,其二是精要和体要”;[13]郭绍虞认为“风骨”的表现在于“力”,所以又可以说成“风力”,刘禹昌指出“风骨”相当于后世批评家所说的“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这类阐释大致是将“风骨”以“风格”论,同时注重“风骨”的“气——力”转化,强调了“风骨”中阐发的生命力。
其一,是与康德之“崇高”作比较。蔡育曙认为阳刚与阴柔恰可以对应崇高(壮美)及优美(美),在文中将“风骨”与康德论“崇高”以“力”结合比较,认为“风骨”作为一种阳刚美是“‘力’的美”“‘动’的美”;他认为对“风骨”的要求实际上既具有康德式崇高的体积、力量,更有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的“典雅华美”。[14]
其二,王圆圆以酒神精神的悲剧内涵与“风骨”的悲剧性意蕴作比较,同样是将“风骨”引向“崇高”,认为“风骨”的诗学精神内涵即“教化、情感的感化”能够触发灵魂的“净化”,与悲剧的效果一样,能够引起“崇高感”,酒神精神与“风骨”两者都分别是中西文化“面对精神危机时的精神自我救赎与超越悲剧的方式”。[15]
其三,是以朗吉弩斯之“崇高”为比较对象成为较主流并成体系的研究。曹顺庆发表于1982 年的《“风骨”与“崇高”》认为朗吉弩斯所说的“崇高”才可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互相印证、发明,而不是康德等人所说的属于审美感受的“崇高”,得出结论:“崇高与风骨不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朗吉弩斯和刘勰所做的许多具体的论述上也是相同的”。[16]2007年,曹顺庆、马智捷在前文的基础上扩展思路,重点论述了两者的不同特质:中庸与极端、融合与对立、实用与理论、内在之气与外在之形,得出“‘崇高’背后的价值诉求,主要是主体的自由与认识的优越,而‘风骨’之诉求,则是对人的艺术性存在的诗意构想”的结论。[17]延续此思路的还有陆弈思对“风骨”与“崇高”的论述,并阐发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风骨”与“崇高”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风骨”强调古典和谐美,而“崇高”强调对立的张力;二是“风骨”作为实践理论偏向创作论,“崇高”转向哲学探讨属鉴赏论;三是“风骨”以“气”为根本,“崇高”以“理性”为形而上的支撑。与曹顺庆、马智捷一文类似,陆弈思一文亦将“风骨”与“崇高”的共通点归于追求德性精神的旨归。在比较中,陆弈思提出了一个较有挑战的问题,同样作为古典美学范畴,“风骨”论逐步定型,而“崇高”则经历了几次转化,如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崇高美学”,这种现象值得探讨。[18]
(2)中西文论比较的其余视野。在比较中谈“风骨”问题的构成时,郭外岑将克莱夫·贝尔的经典见解“有意味的形式”以苏珊·朗格的阐释、发展与“风骨”范畴的审美内涵作剖析、比较,以“意味”对应“风”“形式”对应“骨”,认为“风骨”应是“一种对美的知觉和意味的直觉”,大胆提出了“风骨”应属于美学哲学层次的范畴,而不是一般的创作论层次,认为前人学者正是因为长期局限于创作论层次的阐释,才使得“风骨”论无所进益。[19]
李国辉认为意象主义诗人大多将中国看成新诗学的重要来源,意象主义中的精确观念与“风骨”非常接近。[20]闫雅萍将“风骨”论的诠释问题以诠释学作整体关照,认为并不一定需要确定一种说法为“正确理解”,立足于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研究视角看到古代文论范畴在跨文化诗学对话中的意义生成可能性,“风骨”中蕴含的丰富生命力正是中国古代文论“人化文评”的生动表征。[21]
与前人学者取不同视点,刘颖以“风骨”的英译与阐释为例,引入海外学者如吉布斯(Gibbs,Don⁃ald.A.)与英文论著学者如施友忠(Shih,Vincent Y.C.)等人的相关论著及观点,跨专业、跨语言窥见“风骨”问题所在:中西文论话语不可调和的异质性、翻译的创造性以及话语秩序的建立相关。[22]
同样对前人研究思维提出批评的还有杨文虎,其将“风骨”之所以论争不停的原因归咎于“人们使用的西方文论那种严密的逻辑方法”。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感兴的特点,与西方文化重分析、理性的特点形成对比,借用西方研究方法时,最重要的立足点应是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强制融入西方研究方法的语境之中。[23]闫霞则将目光放在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的隐喻性特征上,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与“言意之辩”解说“风骨”阐释的难题。[24]徐扬尚则点出“风骨”现代解读的问题爆发于“内容与形式二元说”,恶化于“文采与风骨的风格说”,隐伏于“文意与文辞两分说”,同样是认为如此植根于20 世纪中国文论“西化”语境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时代失语”[25]。
2.东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
李远喜将“风骨”与“物哀”作为中日文学的本质区别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风骨”作为中国自建安以来各个时代的主要文学风格的观点,“物哀”作为日本文学的总体特征。该文主要论证还是将重点放在“物哀”上,对“风骨”的理解与阐释不深,但是的确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视野。[26]林祁以“风骨”与“物哀”作为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作者的此岸与彼岸,在论述中其亦将“风骨”视为中国文学传统,将“物哀”对应为日本文学传统,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作者在此间确立新的美学原则。[27]
徐燕来则在以“气”为“风骨”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印度《奥义书》“阴阳和合的三分模式”探索了“风骨”的审美内涵,认为“风骨”的审美内涵“体现了宇宙万物和人的生命的和谐和律动”,[28]并以此延展生发出“对中国艺术的生命境界的体悟”这一要求。
3.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近四十年“风骨”范畴研究中唯一一篇从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薛涛比较了彝汉诗学中的“风骨”,文中举南北朝末至隋初的彝族诗人、文艺理论家阿买妮《彝语诗律论》及宋代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等彝族文艺理论著作中的“风骨”内涵与刘勰之“风骨”进行比较,得出了“彝语诗学里的‘风’‘骨’多是单用的,汉语诗学里的‘风’‘骨’经历了一个……由单用到合用的过程”[29]的结论。
(三)“风骨”之致用
刘勰希望以《文心雕龙》袭用儒家的“文质”观点去抨击六朝萎靡文风,“风骨”范畴反映了刘勰文学思想的“尚用”“尚质”。钟嵘继刘勰之后对“风骨”进行阐释发扬并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之中,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评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刘祯“真骨凌霜”,评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等等。唐初陈子昂再继“风骨”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风骨”论的发展自有其脉络,今天该如何运用“风骨”范畴进行符合其特点的实践?以谭佳的话说:“我们还应考虑‘风骨’作为文论术语,应当如何介入到当代的文学理论中,又如何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广泛有效的应用。”[30]学者曹顺庆曾发数文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症”问题的解决途径——需要靠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古代文论范畴转换至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更是首当其中。蔡钟翔在《范畴研究三人谈》中提供了一套古代文论范畴实践转换的思路:首先用于古典文艺作品的批评,其次用于当代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的评析,最后再用于现当代文艺作品。涂光社则强调了古代范畴的应用更要紧的应该是对进行创作实践、批评实践的主体的素养提升与价值巩固。[31]依现实而言,大多数的“风骨”实践回到了人格力量评价、道德层面的品评等,但仍不乏有些依然沿用“风骨”致用古径的学者。
刘建国在《‘风骨’浅尝》的文末以模仿《文心雕龙》中赞的模式,作了三首四言小诗以说明“风骨”的特点,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创作实践:
其一 风·气
如符如契,惟气惟风。
无风乏气,气爽风生;
风力遒劲,意气凌云。
其二 风·情
情美生文,文美生风。
情因风显,风以情深。
雄风浩浩,情思云蒸。
其三 骨·辞
文而无骨,辞且安陈?
义杂辞繁,无骨之徵;
辞经百炼,文骨天成。[32]
袁鼎生则将“风骨”范畴应用于山水美学的研究中,在《论桂林山水的风骨美》中提出“正因各种风骨论都属美学范畴,风骨概念从人物品评外延道画论、文论,也就有可能引进山水美学研究之中”,[33]论证桂林山水的“风骨美”特点亦是“风骨”论的外延实践,但较多采取直观体验的方式进行论述,的确抱有理论性不足的缺憾。邓经武在《“新风骨杂文”论》中提出以“新风骨杂文”命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杂文,将“风骨”应用于对某时期某种文学作品类型的归类是一种文学批评实践,具体描述为“作家们的人格独立意识的萌发和创作主体精神的日渐强化”,[34]虽然提供了一种理论实践的视野,但是其立论的依据与论证过于草率和简单,因而此后并没有理论继承。
当前,能够在理论层次上对“风骨”进行“致用”的研究尚少,这也为我们进行古代文论研究指明了方向,究竟以何种方式能够将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美学范畴古为今用?是否可以做到理论与实践兼备,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呢?依然是古代文论范畴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结语
学者张利群提出中华美学精神五要素“根、本、魂、学、用”,[35]“风骨”范畴容纳于其中,笔者认为,“风骨”范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参与建构的文学批评范畴和审美范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组成部分,更在于其“用”,即价值作用所在。张利群强调:“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面对未来发展导向的意义,”正是“致用”才能做到“风骨”范畴的实践,使刘勰的“风骨”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范畴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这也正是进行“风骨”范畴研究的意义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对“风骨”的研究正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风骨”的文艺工作者,作有“风骨”的文艺批评。这不仅是为了治疗所谓“失语症”而开出的心理药方,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胸襟。
更广泛而言,古代文论范畴中体现出的诸如生命力、德性、价值基础等特质,能否在当下这个万物皆可“虚拟”的时代中,在世界开始逐渐由“冷冰冰”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接管的时间节点,使人类依然有其精神复归的落脚点,使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这是我们学习人文、研究人文应该探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