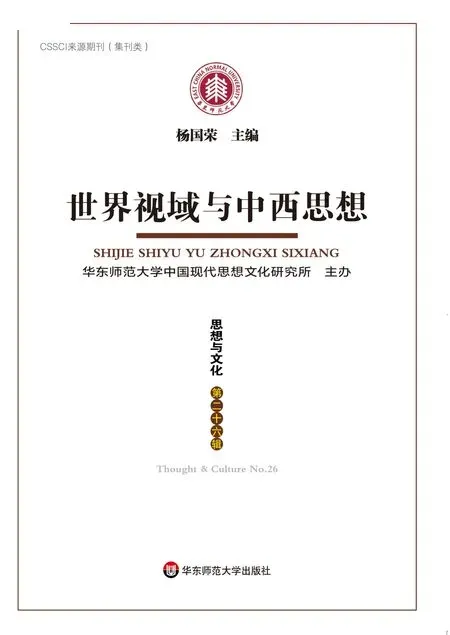论科恩的共同体思想
●
纵观国内外学界,尽管科恩(G.A.Cohen)的作为平等的正义理论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共同体精神、仁爱思想的探讨却并不充分。科恩的学生弗利萨里斯(Nicholas Vrousalis)在对科恩的政治哲学研究中专门论述了科恩的共同体思想,并指出科恩对共同体以及友爱的论述,是其重要但被忽略的人道主义思想。①参见Nicholas Vrousali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A.Cohen:Back to Socialist Basics,Bloomsbury Academic,2015,p.99。本文通过重构科恩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和其社会主义理想的建构,指出共同体思想始终贯穿于科恩对自由、平等等价值的讨论之中,并构成科恩平等思想的出发点。在科恩那里,分配平等与关系平等,平等原则与共同体原则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理想的前提与基础。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科恩对罗尔斯差异原则进行批判的特殊视角,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的“隐秘线索”
罗尔斯称其平等理念为“民主的平等”,并把它与自然的自由体系和自由的平等相区别。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只要满足某些背景制度的约束,任何由此产生的有效率的分配都被承认是正义的。②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2页。自然的自由体系的最初分配仅向有才能者开放,并不调节任何社会偶然因素。而自由主义的平等,则是在此基础上加上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进行限定,因而自由的平等不仅指形式上的地位平等,而且也包含所有人有机会达到地位的平等。③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73页。这意味着,对于具有同等能力和志向的人,其对生活的期望不应当受到其社会出身的影响。相比于自然的自由体系,自由的平等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但是,自由的平等仍然具有局限性,它允许人的能力和天赋的差异对财富与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而并未完全消除道德任意性因素的影响。基于对自然的自由体系、自由的平等体系的局限性的分析,罗尔斯提出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民主平等体制。罗尔斯与自由主义的平等理论的区别体现在差别原则上。通过差别原则,基本结构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将得到消除,较不幸运者的利益得到保障。④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76页。因而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更强的、更激进的平均主义的观念。此外,罗尔斯还强调,差别原则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中的“博爱”。与自由、平等相比,虽然博爱观念在民主社会中似乎地位较次要,但博爱使我们看到了民主权利所表现的价值,也被认为是体现了某种社会评价方面的平等。博爱原则表达了这样一种道德意识:如果不是有助于状况较差者的利益,任何人就不欲占有较大的利益。①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106页。
在罗尔斯看来,博爱是一种善,并强调公平的正义与博爱之间的关系是相容的。他认为,人类之爱,或者仁爱,包含强烈的行使正义的欲望,但除了正义的义务,仁爱还促使人们准备履行所有的自然义务,甚至超出这些义务的要求。②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190页。基于此,罗尔斯说:“虽然作为公平的正义一开始就把原初状态中的人们看作个人,或更准确地说是看作连续的线段,但这对解释那些使人们联为一个共同体的较高层次的道德情感来说并不构成障碍。”③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190页。换言之,尽管博爱不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出发点,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差别原则除了体现正义的要求,也包含着超出正义的博爱精神。
问题是,罗尔斯的“博爱”观念既没有包含在他的理论前提之中,也没有体现在他对差异原则的具体解释之中。罗尔斯认为,在原初状态中,各方是互相冷淡而非相互同情的,在这样的设定下,如果不平等能提供刺激从而引出更有成效的努力,处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就可能将这些不平等视作鼓励有效表现的必要手段。他还认为,如果不承认这些不平等的正义性,那么各方就是目光短浅的。④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150页。科恩对罗尔斯的批判针对正是这一点。他认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能一贯地支持其博爱观念,而是有违共同体精神的。
柯恩首先对罗尔斯的激励论证进行了批判。科恩区分了对差别原则的两种不同解读。在对差别原则严格的解读中,只有当不平等严格说来是必要的时候,即与人们的选择意图无关的时候,差别原则才把不平等当作必要的。在对差别原则的宽泛解读中,差别原则也支持与意图有关的必要性⑤参见G.A.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9。,例如这种不平等需要满足有才能的生产者的自私自利的欲望他们才愿意工作。这两种解读在罗尔斯的作品中都能找到支撑材料。一方面,罗尔斯信奉对差别原则的严格解读,此时这种激励是应当被谴责的,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明确地信奉差别原则,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必要使用特殊的激励来激发有才能的生产者。①参见G.A.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p.69。另一方面,宽泛解读中的差别原则要求激励性政策。当激励论证仅由有才能者提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通过人际检验②人际检验:如果一种论证由于谁在说和/或谁在听而无法证明一项政策是正当的,那么不管它在其他的对话条件下是否同样成立,它都无法(简单地)全面地证明该政策是正当的。科恩的共同体指“辩护性共同体”,仅当一项政策论证通过了人际检验,相关的人们为该政策提供的论证才满足辩护性共同体的要求。而如果对该政策的所有论证都没有通过那种检验,那么无论还可以说什么来支持该项政策,它都表明辩护性共同体的缺乏。参见G.A.科恩:《激励、不平等与共同体》,载吕增奎编:《马克思与诺奇克之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3—275页。的。换言之,激励论证只是由于有才能者提出才是正当的,但无法将提出该政策的主体换作其他群体,这就表明了激励论证是缺乏共同体精神的。概言之,宽泛解读的差别原则或者是常见表述的差别原则与罗尔斯的尊严、博爱和完全实现人的道德本性这些理想相悖。
除了激励论证,罗尔斯认为其差别原则也支持作为效率原则的帕累托更优原则带来的不平等,而这种效率原则意味着,如果不存在改善至少一个人的状况而同时不损害另一个人的再分配方法,那么现有分配方法是有效的。③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67页。但科恩对此发起了挑战。科恩表示,如果帕累托论证支持不平等,那么有才能者运用具有道德任意性的天赋才能进行剥削是正义的,也就是道德上的任意性被认为是契合于平等的。他把具有社会基本善方面的平等和才能的善方面的不平等的状态称为D1,把有才能的人不仅享有其初始优势,而且享有更大的社会基本善集束中的深层优势的状态称为D2。D2对于D1是帕累托更优状态。假定D1的工资的平等水平是每小时的工资率,即W,在D2的情况下,才能突出者和才能欠缺者的工资率高于W,如前者为Wt,后者为Wu,那么Wt应该大于Wu。在罗尔斯的帕累托论证中,Wt和W 二者的差别是产生W 和Wu的差别所必须的,也就是说才能突出者的高收入是提升才能欠缺者收入所必须的。然而,科恩认为有一种逻辑上可能的分配情况D3。科恩认为,D3中生产的数量等于D2,但D3的工资是相同的,有才能者和无才能者的工资率都是We,而Wt>We>Wu>W。在D3状态下,有才能者的工资少于D2状态下的工资Wt,但高于D1状态下的W;但对无才能者来说,D3状态下的工资We且大于D1状态下的工资W。这意味着D3比D1帕累托更优,但比起D2,D3维持了平等。科恩认为,如果D3可行,并且在其中才能突出者在收入为We时愿意像在Wt时那样工作,我们就不能反对D3。他得出,帕累托论证并不要求不平等,或者说,把有才能者的行为当作前提条件,所要求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
科恩认为,差别原则的道德任意性立场与差别原则的内容有一种根本的张力。道德任意性主张把偶然造成的不平等视为不公正,差别原则所主张的平均主义观念正是要克服这种任意性。但罗尔斯又用帕累托法则容许了那种不平等。于是,道德上的任意性主张就与差别原则的内容相矛盾。具体而言,激发罗尔斯式平等出发点的理念,即正义反对人与人之间由于道德任意性的原因而在财富上的差异,因为它们是不公平的,就预设或者蕴含了正义已经(至少部分地)涉及不同的人们所得之间的关系。但是,差别原则在相关的和基本的意义上对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视而不见,并因此容许了那种不公平。
最后,科恩对罗尔斯主张正义原则只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观点提出批评。首先,从纯粹的结构解释中,差别原则并不反对市场利益最大化者的利己动机。第二,如果正义只是与结构有关,那么处境较有利者则倾向反对平等,处境最不利者的地位低下就是因为处境较有利者对私利的追逐而成为必然。第三,罗尔斯认为在公正的社会中人们依照正义感而行动,并试图在自己的选择中运用这些原则,但如果人们随心所欲的选择已经能满足正义,那么他们不得不按照正义原则而行动就显得不具有说服力了。①参见G.A.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pp.130-131。最后,科恩区分了两种对基本结构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指一种粗略的强制性纲领,如法律;而第二种理解则是指较多依赖于惯例、习俗和期望但较少依赖于法律的基本结构,如家庭。对于后者,个人选择是否正义会起到较大的影响。罗尔斯的理论矛盾体现在:“他关于正义评判对象的标准和他把与结构相符合的个人选择的影响排除在正义评判范围之外的渴望之间的不一致之处。”②G.A.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p.132.换言之,如果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强制性结构,那么他关于正义判断的标准就会出现任意性,而如果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惯例,那么将正义限制于社会强制结构这一点就不能成立。基于此,科恩认为,我们必须改变对强制性基本结构的过度关注,倡导一种影响人们的个人选择的正义风尚。这种风尚促进一种比正义原则所能够保证的更加公正的分配,并且更好地体现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爱的精神。
由此可见,科恩从平等的角度切入,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进行批判,激励论证与帕累托论证均会因为支持天赋差异而造成重大不平等,而这违背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博爱精神,更有损共同体观念。事实上,科恩拯救平等的根本出发点是人类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观念下,道德偶然性造成的结果不平等是不被允许的。
二 从自由主义平等到社会主义平等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罗尔斯的理论有一种社会偶然性和自然运气不应得的立场倾向,但在科恩看来,罗尔斯的帕累托论证又容许了这种不应得的存在,因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是不充分的。罗尔斯的立场被德沃金所阐发,从而为运气均等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运气均等主义者主要致力于对两个问题的考察,谢弗勒总结为:“第一个问题是平等主义者希望追求什么东西的平等。这个问题经常被表达为一个关于平等的正确‘度量’问题。人们已经讨论的平等化目标包括福利、资源、福利的机会和可及优势等。第二个问题是何种形式的不平等应该以平等的名义获得补偿。这里人们讨论的是生理残障、医疗需要、有限的禀赋、不利的社会地位、不成功的赌博、昂贵嗜好、昂贵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受欢迎的性情,等等。”①Samuel Scheffler,“What is Egalitarianism,”Philosophy&Public Affairs,1(2003):13.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运气均等主义的理论尽管有不同变体,但核心理念是相同的,如谢弗勒所指出的那样:“即人们拥有的利益的不平等如果源于人们自愿做出的选择,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这些不平等源于未经人们选择的环境因素,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非正义的。”①Samuel Scheffler,“What is Egalitarianism,”Philosophy&Public Affairs,1(2003):5.运气均等主义通过对选择与环境做出区分,消除纯粹的运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而实现其平等的理念。
科恩对运气均等主义持有同情的态度,并认为运气均等主义比罗尔斯更好地体现了平等。然而,他对资源平等以及能力平等两种进路的论证并不满意,并主张用“可及优势平等”去取代资源平等以及能力平等,以更好地实现平等主义的理念。他把“福利”当作一种典型的平等物,并且涵盖了享乐式福利以及偏好满足两个层面。他认同罗尔斯对昂贵嗜好的批评驳倒了福利平等主义,但他认为罗尔斯的理由也使其对平等主义的维护陷入了自相矛盾,即对昂贵嗜好的反驳诉诸个人责任,但个人的努力却只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不受个人控制的天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罗尔斯的矛盾正在于,对公民是否负有“责任”的划界并不明晰。虽然科恩承认福利平等主义有种种缺陷,但不认为应该走向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主义。主要原因是科恩并不认同德沃金式的资源与选择或社会环境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划分。在他看来,第一,德沃金只要求对资源不足进行补偿,但没有对不幸本身进行补偿,比如对疼痛的补偿;第二,德沃金没有把责任的缺失作为正当补偿的必要条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②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19.科恩认为,一个不用负责任地需要(或无可指责地选择发展)昂贵嗜好的人与一个不用负责任地失去(或无可指责地选择消费)宝贵资源的人,从平等主义者的角度看来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差别。③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20。他认为,人们应该给予补偿的是一个人无法控制的不利,因而不应该把不幸的资源天赋和不幸的效用功能区分开。④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20。他试图用“可及优势平等”来取代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从而更好地坚持运气均等主义的初衷:没有人应该因为坏的、纯粹的运气而受苦。他的“可及优势平等”可视作对“福利平等”的一种修正和延伸。“优势”包括福利,但比它更广泛。“可及”则比“机会”更为广泛,它关注个人能力的不足,个人能力不足“即使没有减少获得有价值之物的机会,它们还是减少了对有价值之物的可及性”①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20。。科恩承认,他并没有用一种很系统的方式概括“优势”的定义,但他尝试通过“可及优势”来避免资源平等主义以及福利平等主义的不足,从而实现平等的激进化。他认为,对一个平等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消除剥削和纯粹的运气对分配的影响,因而根本的区分是在影响人们命运的选择和运气之间。②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4.而按照可及优势平等,当不平等(或平等)反映出可及优势不平等时,人们的优势就是不正当的不平等(或不正当的平等)的。③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18。简言之,不反映出主体选择的不利需要被纠正。
科恩的平等观念里最为突出的是对可受控制的个人选择以及不受控制的纯粹的运气的区分,并把消除纯粹的运气带来的影响作为其激进平等观念的目标。科恩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原则和三种相应的对机会的障碍。第一种机会平等原则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消除了由社会造成的地位对生活机会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包括正规的地位限制,也包括非正规的地位限制。第二种原则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原则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是对社会的不利条件的纠正,而不是对天赋的或生来的不利条件的纠正。而科恩所推崇的是第三种原则,即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它纠正的不平等是由作为非正义的更深层根源的天赋差异所引起的,它超出了由非选择的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因为天赋的差异亦是非选择的。一旦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实现,结果的差异就只是反映在爱好和选择的差异上,而非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与权力的差异。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相应于罗尔斯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平等”,而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则主要相应于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科恩的“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则是一种相较于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更为激进的机会平等原则。
但科恩也意识到,他的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原则如同运气均等主义的平等观,仍是不彻底的。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它与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相容。第一种不平等是由于生活方式选择的偏好多样化造成的,这可以获得可比较的外观,但不是真正的“不平等”。第二类不平等包含总的益处上的不平等。它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因使人悔恨的选择(因选择者的疏忽或不在意)而产生的不平等,和因选择上运气的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但它使得当事人产生抱怨,损害了共同体原则。在这三种与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相容的不平等当中,除第一个之外,其余两个虽然并不为正义所谴责,但当它们在足够大的范围得以流行,会使社会主义者反感,并将共同体原则置于严重考验之下。
在这个意义上,科恩认同一些对运气均等主义的批评。对于运气均等主义,谢弗勒认为,在选择和环境(或者运气)之间作区分,在哲学上是困难的,在道德上是行不通的。从哲学上看,“就对人们至关重要的同一性(identity)而言,实际上未经选择的人格特征和个人出生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也是自我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通常意义上的‘自愿’而言,人们的自愿选择通常深受不可选择的人格特征、性情和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①Samuel Scheffler,“What Is Egalitarianism,”Philosophy&Public Affairs,1(2003):18.。科恩承认,区分出什么代表真正的选择是格外困难的,他的划分会受制于那些或许不可能得到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但他认为,“真正选择”的区分是一个程度问题,通过选择者所拥有的相关信息的数量可以对这种程度进行评估。因而这种“真正选择”的区分并非不可能的②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32。,即便可能因现实的复杂性而缺乏可行性。谢弗勒又进一步指出,这种选择与环境的区分在道德上缺乏说服力。运气均等主义将以一种强烈的“内部审视”作为判断责任归属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因为某种不利情况,要求以平等的名义获得补偿,这有赖于对这个人的不利来源进行甄别,即考察其不幸是来自于她自身的选择还是环境造成的结果。因而,要知道她是否有资格获得补偿,就要理清她的意志以及未经选择的才能和环境各自产生的结果,而与此同时,理清她处于不利状况的过程。因为这个原因,运气均等主义者鼓励这个不幸的人决定她是否对其他人有一个合法的补偿主张,换言之,鼓励人们去详细地省视自身的不同层面的不利状况,并判断人们对自身的不幸状况承担责任的程度。①参见Samuel Scheffler,“What Is Egalitarianism,”Philosophy&Public Affairs,1(2003):21。在关系平等主义者看来,这种做法违背了平等主义者的初衷。追求平等原本反对的是压迫、等级、特权,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是,一种鼓励他人去揭示自身不幸情况的做法,使不幸者面临家长式②家长式行为:如果一种行为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但却违背他的意愿而做出的,并且该行为从意图上来说实际上确实有利于他,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家长式行为。参见G.A.科恩:《自我所有权、世界所有权与平等:上篇》,载吕增奎编:《马克思与诺奇克之间》,第130页。的威胁,未能得到足够的尊重。针对这些平等原则会带来的问题,科恩认为应当用共同体原则来调节,因为共同体的核心是人们之间的互相关心。
弗利萨里斯认为,科恩的共同体思想破坏了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因为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容许破坏共同体精神的不平等,那么照此可以推导出,科恩的共同体思想也破坏了运气均等主义的立场,包括科恩自己的平等观念,因而是自我矛盾的。③参见Nicholas Vrousali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A.Cohen:Back to Socialist Basics,p.110。弗利萨里斯其实误解了科恩的立场,事实上,这种“破坏”是科恩自我扬弃的尝试。诚然,科恩的共同体思想会“破坏”其平等主义,但平等主义并非科恩的最终目标。科恩的“可及优势平等”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对话的语境下提出的,立足于个体,属于分配平等的范畴。但在科恩的理论体系中,为社会主义辩护才是最终目标,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而平等主义是实现其共同体精神的基础与前提。
三 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与共同体原则
科恩对共同体更为详细的论述体现在他对其社会主义理想的辩护中。他描述了两种不同的野营旅行模式。在一种野营模式中,人们接受平等和互惠的规范,并认为这些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差异尽管大量存在,但人们相互理解,这种精神保证了不存在任何人可以在原则上反对不平等。而在另一种野营模式中,人们遵循市场交换和对所需用具的严格私有的原则。科恩认为,大多数人会被第一种野营模式吸引,也就是被一种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之所以第一种野营模式是吸引人的,是因为有两个原则在野营中得以实现,一是平等主义原则,二是共同体原则。
如果说科恩的平等原则只是对左翼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了推进,那么共同体原则的补充则是与后者更为重要的区分。共同体的核心要求是人们互相关心,必要且可能的情况下照顾彼此,也在乎他们是否互相关心。①参见G.A.Cohen,Why not Socialis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34-35。根据这一定义,科恩讨论了两种共同关心模式,第一种共同关心模式是抑制那些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原则所导致的某些不平等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倡导一种互惠的纯粹道德风尚。共同体互惠性是非市场的原则,不是工具性的,需要一定的奉献精神,按照这种原则:“我之所以为你服务,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得到的回报,而只因为你需要我的服务,而且你因为同样的原因来为我服务。”②G.A.Cohen,Why not Socialism?,p.39.在这种共同互惠的精神中,人们相互之间视对方为人类同胞,这不同于市场动机中所期望的互惠互利。
在此基础上,科恩探讨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可行性和可欲求性。对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科恩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能够使其运行的机制。人有自私和慷慨两个倾向,应该利用人的慷慨倾向使这种机制得以运行。现实的困难是,人们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私,但不知道如何利用慷慨来推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可欲求性,科恩从共同体的视角来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第一种关心模式用于抑制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带来的不平等;而第二种共同体关心模式则是指一种互惠风尚。这种互惠风尚要求人际间的关系是一种同胞的责任关系,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际关系有着根本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互惠关系出于贪婪和恐惧的结合,贪婪是因为他人被视为致富的源泉,而恐惧是因为他人被视为威胁。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作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而存在,他者仅仅被视作作为主体的个体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精确的利益算计,而并不存在真正的相互关心与共同发展。由此出发,科恩向市场社会主义者发难。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克服了资本和劳动的划分,工人获得对公司的所有权,不存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仍旧保留了市场的竞争方式。在竞争中,工人所有的公司彼此相互竞争,并导致了 赢家和输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减少甚至取消了传统社会主义对经济平等的重视,也损害了共同体的价值。无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交换还是资本主义的交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作为市场交易核心的关乎利益的互惠性。尽管科恩承认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次优选择,甚至在大概不远的未来是合理的乃至最好的选择,但科恩并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的标准。在他看来,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在一种对那些偶然拥有异常天赋并组成高级生产合作社的人报以高额报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非正义,而且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交换与共同体价值相冲突。
如上所述,科恩的社会主义理想涵盖了平等主义原则和共同体原则,是分配平等理念和关系平等理念的有机结合。平等主义原则主要体现的是分配平等的理念。马克思对这种平等理念有所讨论。在马克思看来,就平等权利的内容而言,“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权利。”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平等权利只是一种形式,它以平等的个人为基础,以某种关系或因素为尺度。而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使得现实存在的个人总是不同等也不平等的。因而法权关系所奠基的是抽象的平等个人而非现实中具有多样性的人。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分配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科恩的平等主义原则就是这样一种以“可及优势”为尺度的分配平等理念。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科恩不再确信地球的资源允许出现马克思所相信的极大规模的生产力,经历了苏东剧变后,更认为无产阶级队伍难以承担革命的使命。③参见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8页。因而科恩的社会主义理想讨论的其实正是这样一种需要分配维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必然要关注分配平等,并且这种平等是不彻底的。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科恩关注到权利平等带来的不平等,并通过平等原则去纠正这些包括天赋在内的自然与社会偶然性带来的不平等。就科恩的平等原则而言,他汲取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者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尝试去维护其马克思主义立场。
但作为一个正义的外在论者,科恩又清楚地意识到作为正义的平等具有不彻底性。这与科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关,也是他和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者的根本不同之处。马克思对平等的批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道德理念、法权理念的平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的压迫以及人的异化现象,人丧失了自主性。只有追求人最高本质的实现才是平等的真正实现。在拒绝马克思对未来所持有的乐观态度的前提下,科恩更看重的是通过道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在其晚年未完成的文章中,柯亨提到他对平等的看法:“并非拥有任何特征的任何存在者就可进入这种关系:有一些特征、能力甚至动机是进入关系的条件,但他们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系本身。……你平等地对待他们,因为你认为他们是平等的。”①参见G.A.Cohen,Finding Oneself in the Other,M.Otsuka(ed.),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194。也就是说,人们是平等的并非指人们描述的价值是平等的,而是即便描述的价值并不平等,人们也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人们把对方看作是平等的,是因为人们寻找、重视关系的本质。对关系本质的重视,也意味着关系本身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他支持一种黑格尔式的保守主义:即接受被给定的东西,重视有价值的东西,重视宝贵的东西,在这三种情况中,主体与客体和平共处;他致力于探索“在他者中发现自身”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自由也得以实现。②参见G.A.Cohen,Finding Oneself in the Other,p.143。共同体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体本身的内在价值是值得追求的。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人们和谐共处的共同体中,人们的自由与平等都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科恩从共同体思想的视角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辩护。尽管科恩的共同体思想还未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但仍为我们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提供了借鉴与反思。一方面,我们承认对分配正义和平等权利的需要,因而需要借鉴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去发展切合社会现实的正义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坚持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追求,从抽象的平等个人回归到共同体中的现实个人,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放在正义理论的根本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