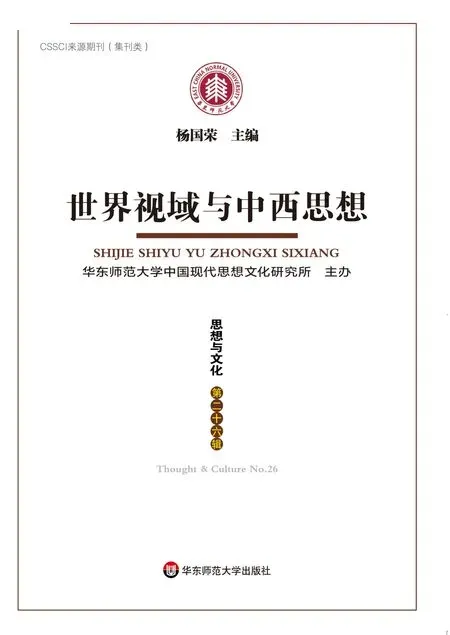对于美国之中国哲学研究生项目的现状反思
●
无论在哲学专业的博士项目里,抑或在面向大众的哲学期刊中,中国哲学都是鲜有问津的冷门。最近,布鲁雅(Brian Bruya)和奥伯丁(Amy Olberding)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①Brian Bruya,“The Tacit Reje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merican Philosophy Ph.D.Programs:The Case of Chinese Philosophy,”Dao,Vol.14 No.3(2015):369-389;Amy Olberding,“ChinesePhilosophy and Wider Philosophical Discourses:Including Chinese Philosophy in General Audience Philosophy Journals,”Newsletter of the APA Committee on Asian and Asian-American Philosophies and Philosophers,Vol.15 No.2(2016):2—10.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哲学的确是一门十分守旧的学科,学科革新较之其他诸多学术领域更为缓慢。加之美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类学科不景气,哲学二级学科的现行模式又多少有些根基,出于务实的考虑,设有博士点的院系及其院长或系主任势必不会招聘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者。近日刊登在《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一篇讨论风险规避的文章指出,研究人员承受着为自身所在大学吸引资助款项的压力,这使得科学领域也日趋保守。②Paul Voosen,“For Researchers,Risk is a Vanishing Luxury,”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December3,2015;网络版参见http://chronicle.com/article/For-Researchers-Risk-Is-a/234437。催生这种压力的一个方面,便是针对资助项目进行同行评审。对于学术团体而言,由同行评审分配研究资金可以降低风险。这似乎可以和布鲁雅所指出的以下一点相印证:《哲学评估报告》(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按声誉确定哲学研究生项目排行榜,而项目的声誉究竟如何,则由所挑选的评估专家来确定。
中国哲学要改变现状道阻且长,只能设法在哲学共同体中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信誉”。奥伯丁提出,应当在面向普通大众的哲学期刊上下点功夫、做点工作,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布鲁雅指出,分析哲学是当前美国学界的主流。习惯了分析哲学研究进路的人,往往很难注意到中国哲学的重大价值。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的诸多重要典籍并不热衷于与相左的观点正面对峙,而主要是以间接的和隐喻的表达来描绘对世界的理解与生活的方式。并且,这些典籍所表达的,乃是睿智的哲人花费毕生心血才获得的切身经验。
但这并不是说分析哲学家就无法领悟中国哲学,尽管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很难取得更广范围内的哲学界同行的支持。我相信,分析的进路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儒释道的文本作出清晰缜密的思考与评价。例如,孟子和荀子以人性为道德之根基,相关隐喻就可以运用分析的方法来讨论其价值;再如,用分析的方法研究孔墨之辩能够提供一些新颖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有关公正道德观(如功利主义)的争议。
虽然过去一直接受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但我却日渐欣赏中国哲学,因为它重新激起了我最初迈进哲学大门时内心的冲动:渴望理解并把控那些铸就我的人生经历。中国哲学如此注重探讨这样的人生体验,这正是它卓尔不群之处。①Jiang Xinyan,“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Philosophy Compass,Vol.6 No.3(2011):168-179.中国哲学谈论这些问题时常采取间接、隐喻的言说方式,有时只是展示而非直接论述;而且,即便直接论述的时候,也可能不是对着一般读者说的,而是对着文本中所描写的某一特定人物说的(《论语》等文本中常有这种情形)。当然,要对这样的论说作出明晰精确的解读,其难度不容低估。不过我相信,如果分析哲学对这些论述努力做点澄清工作,而不只是回应那些只有专业的哲学家才能理解或感兴趣的时新话题,那么,它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而且,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对修身极为注重,在诸如身心一体、礼乐教化、人伦关系在成己过程中的重要性等理论命题中,总是蕴含着对人之心理的洞察,因而,我们在克莱因(Erin Cline)、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萨金逊(Hagop Sarkissian)以及斯林格兰(Ted Slingerland)等哲学家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在道德心理学领域和经验性研究方面的对话与会通是一个显著的动向。②相关的经验性研究参见:Erin M.Cline,Families of Virtue:Confucian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Owen Flanagan,Moral Sprouts and Natural Teleologies:21st Century Moral Psychology Meets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Aquinas Lecture),Milwaukee,WI: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2014;Hagop Sarkissian,“Minor Tweaks,Major Payoffs: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Situationism in Moral Philosophy,”Philosopher's Imprint,Vol.10 No.9(2010):1-15;Edward Slingerland,“The Situationist Critique and Early Confucian Ethics,”Ethics,Vol.121 No.2(2011):390-419。
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中国哲学如何不断探究那些使我们注目的人生经验。奥伯丁的著作研究《论语》中孔子及若干弟子等典范人物所发挥的作用,将之与普通人思考伦理生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人们不仅择其善者而从之,同时也从负面例子中吸取教训。譬如,子贡尽管怀抱着良好的初衷,却终究在德行上难获进益,因为他害怕坦承自身弱点,而且还试图用技术上无可指摘、但却缺乏同情与情感的合乎礼的行为来掩盖这些弱点。①Amy Olberding,Moral Exemplars in the Analects:The Good Person Is That,New York:Routledge,2012.我一边读奥伯丁的这些文字,一边想,我自己和其他人也都有这样的缺陷(尽管和行礼活动不会有那么多关涉)。信广来在文章中写到了朱熹对于发而中节之“怒”的分析,当我们遭到中伤构陷或其他不公正对待时,就如同旁观某个与自身毫无瓜葛之人的遭遇,理之当怒则怒,是义理之怒而非血气之怒。这不禁使我联想起现实生活中那些能够不过度关心自身的人,他们着实难能可贵。②Kwong-loi Shun,“On Anger— An Essay in Confucian Moral Psychology,”Rethinking Zhu Xi:Emerging Patterns within the Supreme Polarity,David Jones and He Jinli(ed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最后我想谈一些振奋人心的学界动态。不久前我开始在美国哲学协会理事会任职,令我立马感到震惊的是,理事会成员超过半数是女性。同时令我感动的是,协会成员已在不遗余力地促进哲学专业的多样化发展。此外,近年来,特别是在Ruth Chang 与Tao Jiang 等人的推动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筹办了一系列中国哲学学术会议,哲学系很多教师(他们均非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纷纷就中国哲学相关研究论文作了深入评析。最后,我还发现,在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者中,既具有必要的分析能力又对中国哲学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所占的比例确实还很小,但这个比例正在持续上升。如前所述,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令人振奋的迹象,因为,促进哲学研究的多样化,包括拓宽我们对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促进性别、种族、性取向等方面的多样化,将有助于拓展哲学的内容与研究进路,同时,多样化无疑应当作为目的本身来追求。我所要指出的就是这项艰巨工作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