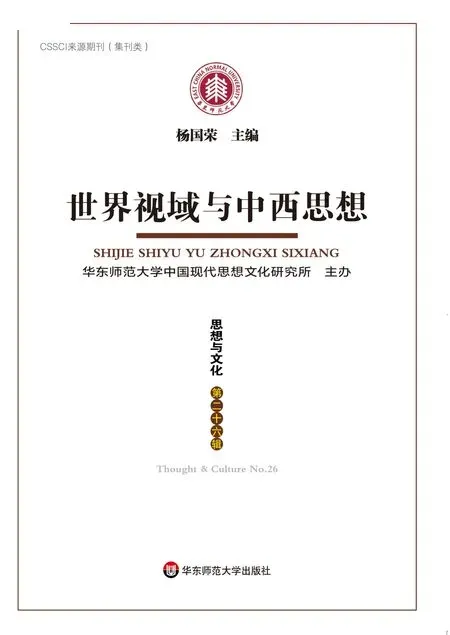戴维森“理由因果论”的困难与出路*
●
“我们是出于理由而行动(acting for reasons)的理性存在”,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直觉,但如何用歧义较少的术语将之精确地表述出来,理由与行动之间是什么关系?所谓的“出于”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便构成了行动哲学的核心问题。
从理由的角度看,有理由的心理—事实主义之争以及理由的内在—外在主义之争;从行动的角度看,有行动因果论—目的论之争。这些争论,往远了说可以追溯到康德与休谟,往近了说可以追溯到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行动理论。戴维森认为,如果我们是出于理由而行动,那么理由必须能够解释行动中所展现出的意图(intentions)。心理事件将意图因果地传递到行动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回答,这种立场被称为“行动因果论”,但由于戴维森将理由视为行动的原因,所以他的理论属于“行动因果论”中的“理由因果论”。
其实,“理由因果论”与其竞争立场多有重合之处,或者说有兼容的可能。例如,“理由的事实主义”强调理由的客观属性,“行动目的论”强调理由的规范属性,这些属性与“理由因果论”所强调的意图都是构成理由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理由因果论”遭致的一些批评是不公平的。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将从“理由因果论”内部突破,尤其是戴维森的论证,揭示其融贯性上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由因果论”的一条可能的出路。
全文的论证将围绕“理由本身是否具有因果效力(causal efficacy)”与“如果有,则这种因果效力是什么意义上的”两个问题。具体分成五节:第一节评析戴维森对“理由因果论”的论证,有两点结论,一是能够解释行动意图是理由的必要条件,二是该必要条件不足以论证理由本身便具有因果效力。第二节表明,不能从类型上(type)理解理由本身的因果效力,因为这样无法与“理由倾向论”区分。第三节表明,如果从标记事件(token events)上理解理由本身的因果效力,可以回应对“理由因果论”的几个经典批评。第四节表明,顺着金在权(Jaegwon Kim)的批评思路会发现,标记事件意义上的理由缺乏实质的语义内容,这使得理由失去了解释功能。第五节简要地为“理由因果论”设想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即将“理由导致行动”视为一条“范导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一、戴维森对“理由因果论”的论证
日常生活中,对同一个行动可以有很多解释,但一个什么样的解释才算是满足了解释行动的基本要求呢?戴维森给出了一个必要条件:“理由要对行动做出合理化解释,必要条件(only if)是理由能使我们看到当事人在其行动中所看到的或认为他所看到的某事——行动的某种特征、结果或方面,它是能动者需要、渴望、赞赏、珍视的东西,并认为对之负有责任、义务、能受益、能接受的东西。”①唐纳德·戴维森:《行动、理由与原因》,储昭华译,牟博校,载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牟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86—387页。简言之,一个合格的行动解释必须能够解释行动中所彰显的行动者的特质。例如,小明在2018年12月28日做出了一个行动“参加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考试”。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考研利于找工作”,但该解释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并没有解释小明在“参加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考试”这一行动中所展现出的意图(intentions)。如果不加上“小明希望通过提高学历找更好的工作”或“小明认为提高学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则“考研利于找工作”这一事实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选择考研而不是直接找工作。通过更具体地分析小明的意图,能解释他为何考华东师大而不是复旦大学。在戴维森看来,意图是行动中最彰显行动者特质的属性,甚至在有的学者看来,意图是区分不同行动(acts)的标准,一个行动解释的最低要求是能够解释行动者的行动意图。
假设戴维森提出的这一必要条件是站得住脚的,但意图仍是个宽泛甚至模糊的概念。戴维森将意图分析为支持性态度(pro-attitude)与辅助信念。支持性态度包括欲望、冲动、情感、价值观等,辅助信念是实现支持性态度的中介。二者构成基本理由(primary reasons)。例如,小明“参加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行动可分析为目标“找工作”与信念“考研利于找工作”,由此构成“参加考研”的意图。更具体的心理分析将揭示该意图的更多细节。但是,这足以论证理由与行动之间是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理由是行动的原因,行动解释是因果解释吗?诚然,为了解释行动中所展现出的意图,思路之一是将行动视为结果,意图被因果地传递到行动中。但是,并不是只有将理由视为心理实体一种思路。
来看竞争对手“倾向论”的主张。根据迈克·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说法,欲望与信念等心理状态的本质是倾向(dispositions),可分析为“在条件c1下做a1;在条件c2下做a2……”①Michael Smith,The Moral Problem,1st ed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14.。例如,小明具有“好学”的倾向,可分析为“如果出现困惑,则进行相应的探索;如果老师回答不了,则自己主动探索”等等。更一般地说,可将倾向视为输入-输出结构,“报考华东师大研究生”便是某种倾向的输出。
注意,尽管倾向的实现离不开实现结构,而倾向的实现结构具有因果效力,但似乎很难将倾向本身视作是有因果效力的。小明具有“好学”的倾向,我们只能说“参加考研”是“好学”的一个输出,其与某个输入共同构成了“好学”的例示(instantiate)。然而,不能说“好学”本身导致了“参加考研”,因为二者之间是例示关系,正如不能说加速度定律导致了物体加速一样。这是“理由倾向论”与“理由因果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后者主张理由直接导致了行动,理由本身便具有因果效力。“理由倾向论”能够以一种不同于“理由因果论”的方式解释行动意图吗?
戴维森认为不行,他的理由是倾向描述是外部描述,他举了一个开车转动方向盘的例子:“如果这种关于‘发出信号’的描述,通过交待他的理由而解释了其行动的话,那么发出信号就一定是有意图的(intentional);但是,根据上面的阐述,它可能并不是有意图的。”②唐纳德·戴维森:《行动、理由与原因》,载《真理、意义与方法》,第396页。我们知道,在元伦理学与行动哲学中通过输入与输出刻画倾向的思路受到了行为主义对心智的研究的启发,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正是通过外部描述来理解意图等心智状态,所以戴维森的这一论证有循环之嫌,已经假定行为主义是不充分的。
以上便是对戴维森有关“理由因果论”论证的评析,有两点结论:第一,能够解释行动意图是理由的必要条件;第二,该必要条件不足以论证理由本身便具有因果效力。接下来的三节将表明,如果理由本身便具有因果效力,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二、类型层面的“理由因果论”
让我们假设戴维森的论证是成功的,理由本身便具有因果效力,但这种因果效力是类型层面的还是标记事件层面的?
标记与类型相对,虽然二者在不同学科中的理解各有差异,但都在特殊与个别的意义上使用标记,都在普遍与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类型。根据某种属性或原则将若干标记归入的集合称作类型,标记未必占据时空坐标,所以不能理解成类型的发生(occurrence)。类型的发生称作标记事件,指占据一定时空坐标的标记。①有关token与type的具体辨析,请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search/searcher.py?query=token例如,“参加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考试”是类型,“小明参加2018年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考试”是标记,“小明参加了2018年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考试”是标记事件。注意,无论标记还是标记事件都不是戴维森本人使用的术语,他用的是“特殊(particular)”与“个体(individuate)”,但语义学与心智哲学前沿似乎多采用标记与类型这对术语,笔者将遵循该惯例。每一个具体的行动可以视作一个标记事件,可称之为“行动标记事件”;每一个导致行动标记事件的理由,可称之为“基本理由标记事件”;相应的,二者在类型意义上可分别称作“行动类型”与“基本理由类型”。
戴维森反对在类型的意义上理解基本理由,他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无法预测,而如果要得出可用于预测的概括,则需要给出一套科学方法:“任何依据理由预见行动的严肃理论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评估各种愿望和信念在决策孕育过程中的有关效力;任何严肃的理论不能把有望来自于单个愿望的改铸过的形式当作评估的出发点。”②唐纳德·戴维森:《行动、理由与原因》,载《真理、意义与方法》,第403页。再看一段:“然而,如果在用解释与被解释的事件之间明确的定义上的联系(definitional connection)来代替这种可溶性的时候,我们能参照某种其与水中溶解之间联系只能通过实验来认识的属性(比如说一种特殊的水晶结构),那么这种解释将更有意义……所谓可溶性,我们假设是一种纯倾向性属性:它是根据单个检验(single test)而得到定义的。但是愿望则不能按照它们可以合理化地解释的行动来界定,即使愿望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经验性的。”①唐纳德·戴维森:《行动、理由与原因》,载《真理、意义与方法》,第401页。不难看出,戴维森所谓的预测是“严格律则(strict laws)”意义上的②戴维森有关“严格律则”的论述参见Donald Davidson,“Thinking Causes,”Mental Causation,John Heil and Alfred Mele(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8-9。,但问题是“严格律则”恰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似乎只有可表达为数学的科学才具有“严格律则”的初步资格,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内部的一些科学也不是类型意义上的了。
现在笔者将抛开“严格律则”有可能不适用多数科学部门的担忧而提供一个新的论证,来说明为何“理由因果论”不能接受在类型意义上理解基本理由。假设基本理由与行动之间能够概括出某种“类型意义上的关系”,那么起解释作用的就不是基本理由标记事件而是“类型意义上的关系”加上基本理由标记事件,由此才可套用科学解释“D-N模型”。然而,“理由倾向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解释模型。倾向分为两部分,倾向性质本身与倾向性质的实现结构。以“好学”为例,从倾向性质本身来看,在日常观念中,“好学”的语义与其他倾向性质(如“较真”)的语义由社会评价体系决定。因此,当以“好学”来解释行动时,起解释作用的是背后的评价体系。从倾向性质的实现结构来看,“好学”的例示需要通过能动者的心理-生理-物理机制来实现,起解释作用的是相关科学因果律则。可见,在类型意义上,“理由因果论”与“理由倾向论”没有区别,其解释模型都是“D-N模型”。
三、标记事件层面的“理由因果论”
如果不能从类型层面理解理由本身的因果效力,那么只能从标记事件层面理解。戴维森的“非律则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因果作用原则(principle of causal interaction)”、“因果关系的律则特性原则(principle of the nomological of causality)”、“心理的非律则原则(the anomalism of the mental)”。③唐纳德·戴维森:《心理事件》,牟博译,载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牟博编,第435—436页。
根据“因果作用原则”,基本理由标记事件与行动标记事件之间具有因果作用,该因果作用是本体论而非认识论意义上的,或许一时无法被我们认识进而纳入“严格律则”,但根据“因果关系的律则特性原则”该因果作用关系在原则上可纳入“严格律则”。“心理的非律则原则”的意思是“非严格律则”与“严格律则”使用的是两套不可通约的语言描述系统。从“非律则一元论”来看,戴维森的意思是“理由因果论”与“理由倾向论”不在一个层次,前者属于常识心理学,后者属于“严格科学(对应于‘严格律则’)”,“理由倾向论”是“理由因果论”的“严格科学”形态。
如果在标记事件的意义上理解理由的因果效力,则不难回应几个对“理由因果论”的著名批评①这三个质疑的直接靶子是亨普尔(C.G.Hempel)写于1962年与1965年的两篇文章。:第一个批评认为理由与行动在逻辑上不是独立的,例如“我想参加考研”与“我参加了考研”,后者能从前者中分析出来;但我们知道,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应是综合的而不应是分析的,因此该批评又被称作“逻辑关系不同”。戴维森的回应是:“根据事件的原因描述一个事件,并不等于把事件与其原因混为一谈,通过重新描述而做出的解释也不排斥因果解释。”②唐纳德·戴维森:《行动、理由与原因》,载《真理、意义与方法》,第400页。从上面的形式化结构便很好理解,e1与e2是两个本体论上独立的事件,因而逻辑关系是不同的。第二个批评认为对行动的解释与对自然界的解释虽然都是合理化活动,但后者依赖“严格律则”而前者不依赖。但戴维森的本意就是“非律则”,他区分了“因果性(causality)”与“因果陈述(causal statements)”,在《因果关系》一文中他将之表述为“单称因果陈述未必例示律则”③Donald Davidson,“Causal Relations,”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Donald Davidson(ed.),New York: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61-162.。第三个批评认为“理由因果论”与自由意志无法兼容。戴维森在《行动、理由与原因》一文中只有简短的回应。从“非律则一元论”来看,根据“物理世界因果闭合原则”,标记事件之间只有因果关系,没有自由意志的余地。但是,“理由因果论”可以说标记事件与自由意志是不同范畴的存在,因而不存在兼容的问题;况且,由于基本理由标记事件与行动标记事件之间是因果关系,这反倒说明行动并不脱离行动者的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没有讨论“认知途径不同”与“异常因果链条(deviant causal chains)”两个批评,因为这两个批评与“理由因果论”无关,前者讨论的是自我知识,后者讨论的是意图能否还原成基本理由。
四、从金在权等人的批评看标记事件
上一节表明,如果从标记事件的角度理解理由的因果效力,则“理由因果论”能够与“理由倾向论”相区分并且能够较融贯地回应几个批评。然而,“非律则一元论”的三条原则至少在字面上是矛盾的。换句话说,即便“理由因果论”能在“非律则一元论”那里得到更有力的阐释,但“非律则一元论”本身稳固吗?
从心身视角来看,基本理由标记事件具有心理属性(命题态度),因而属于心理事件;行动标记事件兼具心理与物理属性,因而属于心理-物理事件。现在问题来了,是什么导致了心理-物理事件(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物理事件)?“理由因果论”会说是基本理由标记事件(即心理事件),但如果基本理由标记事件之间无法概括出“严格律则”,有什么理由说基本理由标记事件具有因果效力呢?
金在权指出:“注意,根据非律则一元论,仅当事件例示物理律则(physical laws)的时候才能成为原因或结果,这意味着事件的心理属性无法带来因果上的不同(make no causal difference)。”①Jaegwon Kim,“The Myth of Nonreductive Materialism,”Supervenience and Mind,Jaegwon Kim(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69-270.反过来说,根据“物理世界因果闭合原则”,每一个物理事件都由另一个物理事件导致,心理事件便成了多余。“承认心理事件m(在t时出现)是物理事件p的原因同时又否认p在t时有物理原因,这明显违背物理世界因果闭合原则,将会陷入笛卡尔的交互二元论,即一个单一因果链中的物理事件和非物理事件的混合。但是承认p在t时也有物理原因p*会引出一个问题,留给m 所归属的因果工作是什么呢?”②金在权:《物理世界中的心灵》,刘明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8页。以上批评可重构为如下两个论证:
正面论证
(A1)事件成为原因,仅当其例示了因果律则
(A2)心理事件不能例示因果律则
(A3)心理事件不能成为原因
反面论证
(B1)物理事件无法被非物理事件导致
(B2)心理事件是非物理事件
(B3)心理事件无法导致物理事件
这两个论证的基础是金在权的“功能还原模型(the functional model of reduction)”:
(C1)M↔Pi↔(P1∨P2∨…∨Pn),其中P1↔(R1∧…Rn),…,Pn↔(Rn∧…Rn+1)
(C2)M→P
(C3)(P1∨P2∨…∨Pn)→P
不难看出,基本理由标记事件所承担的解释功能被还原为某类型的(或所有类型的析取的)实现结构,这些实现结构可使用清晰的公共语言进行描述,这使得“理由因果论”又变得无法与“理由倾向论”相区分。
戴维森如何回应这种批评呢?他不承认正面论证的(A1),他说:“金在权让我们‘注意’的是,‘根据非律则一元论,仅当例示规律事件才能成为原因’。这完全不是我所主张的。我没有这样主张,由于我所给出的事件概念与因果概念,说一个事件‘作为’什么便成为原因是没有意义的。AM+P+S的预设是:事件是非抽象的个别对象,因果关系是这些事件之间的外延关系。”①Donald Davidson,“Thinking Causes,”Mental Causation,John Heil and Alfred Mele(eds.),p.6.在戴维森看来,反面论证(B1)里的物理事件是标记事件意义上的,而(B2)里的心理事件与(B3)里的物理事件都是类型意义上的。不难看出,金在权与戴维森二者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标记事件”与“因果效力”的理解。前者认为非内涵性地谈论标记事件的因果效力是没有意义的,后者认为是有意义的。就此而言,二者的争论似乎不在一个层面。
然而,不能说戴维森躲过了批评,因为金在权在内涵性层面谈论因果效力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因果关系应具有实质的(intelligibly and informatively)语义内容。①Jaegwon Kim,“Can Supervenience and ‘Non-Strict Laws’Save Anomalous Monism?”,Mental Causation,John Heil and Alfred Mele(eds.),pp.21-22.据此,陈晓平进一步指出戴维森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说的。②参见陈晓平:《心灵、语言与实在——对笛卡尔心身问题的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让我们回到“理由因果论”的形式化表述。所谓的“caused”仅仅是“真值函项联结词”,只有逻辑功能而没有语义内容。但是,为什么说金在权对因果关系的表述有语义内容而戴维森的没有语义内容?从二者的形式化表述上很容易看出区别:戴维森的形式化表述可简化为“e1(…)causede2(…)”,仅指标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所谓事件被如何描述,即便描述是假的,甚至没有任何描述,都不妨碍标记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是有因果效力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上的)。反观金在权对因果关系的形式化表述“P1↔(R1∧…Rn)”,显然这是对属性的描述,描述依赖于某个描述系统(例如物理系统),而描述系统一定蕴含实质的语义内容。如果改变“(R1∧…Rn)”中的任意一项,则P1便不是对M 的物理还原,因而Pi也不是对M 的功能还原,这使得Pi无法取代M,因而Pi与P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无从谈起了。概言之,戴维森的因果关系更像是一种本体论承诺,至于该本体被如何描述那是认识论的事情,描述的真假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金在权的因果关系更像是一种认识产物,描述的真假决定了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至于戴维森为何要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因果关系,这涉及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本文不予以讨论。
即便戴维森这样理解因果关系在形而上学上是有道理的,甚至在心身问题上也是深刻的,但作为一种解释,这样理解因果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基本理由标记事件与行动标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实质的语义内容,那么基本理由标记事件还有资格被称作解释项吗?要知道,理由的基本功能是解释,没有语义内容的解释还是解释吗?
总的来说,顺着金在权等人的批评会发现,如果理由本身具有因果效力,那么会陷入一个“如何理解理由的因果效力”的两难,要么从类型意义上理解,要么从标记事件理解。前者失去了核心主张“理由本身具有因果效力”,从而无法与“理由倾向论”区分;后者虽然保住了核心主张却没有内容,从而失去了理由的解释功能。如果以上论证是正确的,那么“理由因果论”还有意义吗?出路在哪里?
五、“理由因果论”的一条可能的出路
站在“理由因果论”立场,回应上节两难困境的第一种思路是仍然在类型意义上理解理由的因果效力,然后以各种版本的非还原论为参考,一方面研究连接基本理由类型与行动类型之间的“严格律则”,另一方面说明基本理由类型在解释行动类型上为何是不可替代的。虽然,该思路被戴维森否定,但注意,他并没有说心身关系在原则上无法概括出“严格律则”。笔者更倾向这样的解释,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基于“深度学习”与“大数据”的算法尚未出现,所以难以想象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律则关系,但“非律则一元论”承诺了行动解释在原则上可以纳入“严格律则”。该思路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方法上的或技术上的,而是如何在坚持因果律则的同时,避免基本理由沦为“副现象(epiphenomena)”甚至被取消。
笔者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思路,这需要从澄清一个误解开始。我们误以为“行动a是因为理由r”、“行动a是出于理由r”这类表述中的“因为”与“出于”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需要提供实质的语义内容或认识论内容。但如果将之视为一条优先于语义学与认识论的“范导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则不会遇到两难困境,甚至能令“理由因果论”与“理由倾向论”各得其所。
戴维森对因果关系的形式化表达恰好构成了“范导原则”的逻辑基础。现在的问题是,“范导原则”的范导性如何体现呢?换句话说,对标记事件的描述为什么一定要以因果解释为目标?例如“小明参加了2018年华东师大考研”,既可以从常识心理学解释,也可以从社会规范与道德原则解释,还可以从脑科学与神经运动学解释。这些分属不同描述系统的解释凭什么都奠基于“因果性”呢?这要求一个极强的形而上学层面的说明,尚待专门的讨论,戴维森的这条形式化表述只是逻辑形式,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笔者认为这正是“理由因果论”今后的工作,以下仅谈三点作为“范导原则”的“理由因果论”的意义:
首先,在解释行动的层面,“范导原则”要求对行动的常识心理学解释必须以因果关系为前提。但请注意,这不意味着所有的解释都以因果关系为前提,仅指对行动的解释,一些解释(如数学解释与文学解释)不是。每一个行动标记事件都不是固有的而是激发的,因而是标记事件与标记事件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认识论层面,“范导原则”为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解释预留了空间。“范导原则”并不否认基本理由类型与行动类型之间在原则上可以概括出因果律则。①Donald Davidson,“Thinking Causes,”Mental Causation,John Heil and Alfred Mele(eds.),pp.9,11.这要求我们对行动的解释不能与科学解释相冲突。如果有一天神经科学表明“欲望”与“信念”这些心理状态其实是共外延的或根本没有对应的实体,那么我们的日常用法应有相应的调整。当然,这会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对标记事件的各个描述系统都奠基于“因果性”,那么各个描述系统中的因果律则应处于连续统中,如此一来还有“严格律则”的说法吗?
最后,在实践层面,“范导原则”预设了每个行动标记事件都是被导致的,尽管不清楚它们是如何被导致的。例如,小明与小张都参加了华东师大考研,尽管不清楚他们分别出于什么理由参加,但清楚的是这两个行动标记事件一定分别由两个基本理由标记事件导致。这为追究行动(道德)责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