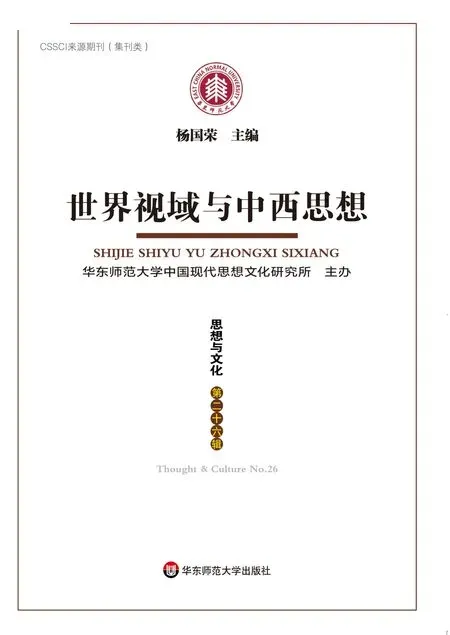不当之名: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主题*
●[美]德安博、[德]康 特、[德]梅 勒 著 沈今语译 李家明
一、引言
本文将追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多少有些颠覆性的主题之轨迹:名与其所指并不匹配,而随之而来的“不当”(incongruity)可能是富有哲学意义和成果的。
《庄子》这部早期中国文本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即名应当与实或形相符,从而是得当(congruent)的。《老子》认为,最重要的名,即道与“圣人”,并不与一个指涉物相对应。基于这样一种不可说的哲学,《庄子》进一步主张,尊贵的社会等级和角色标识是不当的,因此不应该被采纳。这导向了一个更激进的一般性看法,即一切(社会构造的)名都隐含着基本的不当;它们不可能恰当地标识特定的实或形,或任何特定的指涉物,相反只会助长虚假与伪善。
之后,玄学家对不当之名所造成的伪善深感担忧。他们没有试图以新的名实相符理论来增强名实关系,而是通过道家特别是《庄子》来沟通不当理论与道德。何晏采用《老子》与《庄子》对名与道之间不当的论证来阐明儒家圣王的伟大。王弼比何晏更进一步,认为儒家德性乃至一般的道德不可言说,故而德与名之间存在不当。郭象阐述了《庄子》中关于变化的理论,进而得到更一般的主张:所有的实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名仅标识实的所留之迹。
最后,在早期中国佛教哲学中,中观学对二谛的区分意味着,人们感知到的名与物之相当并不意味着名实相符。僧肇诉诸道家语汇,将这一区分指认为“名实无当”。吊诡的是,这种不当却意味着,佛的教法与“解脱”的不可说义是相合的——这正是中国中观学的不二义。
二、得当之名与社会政治规训
古代中国文本往往阐发一种名学,即名或命名的哲学,而非语言哲学。古典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中,存在大量对名的重要性,以及名与其所命名之物(即名的指涉物)的关系的反思。这些反思继续占据了之后的哲学论辩,并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开创性研究《早期中国思想中的名与实》(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中,梅约翰(John Makeham)尽管专门着眼于不甚著名的汉末学者徐干,却提纲挈领地展示了早期中国名学的哲学与社会政治维度。梅约翰研究的核心是分析名与名之所指的“实”或“形”之间的关系。①我们同意梅约翰的观点,认为形名是“法家所讲的名实”,并且“在很多意义上形名机制反映了名实并与之相类”。参见John Makeham,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79。然而我们要补充的是,形名与名实相类,这一“法家”运用并不限于与法家相关的文本,而是也可以在同时期其他文本中找到。本文将证明,中国思想家对“实”“形”关系的论述渐趋复杂。
梅约翰区分了古代中国关于命名的两种观点,他分别称为“关联论”(correlative)与“唯名论”(nominalist)。②梅约翰认为,命名的关联论主张,“特定的名与特定的实之间有着恰当或正确的关联,它是天之所授或由‘自然’所决定”。John Makeham,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p.xiii.相反,命名的唯名论主张,“是人任意地或遵从习俗规定了哪个名应用于哪种实;即除了人为规定之外,特定的名与特定的实之间并无恰当或正确的关联”(同上)。古代中国文本中没有与这对区分相应的术语,而且,根据这对范畴对文本与思想家进行的分疏有时会受到挑战。然而,梅约翰无疑正确地指出,决定名与其所指如何相符对于很多中国哲学家来说都至关重要——无论他们的潜在倾向是关联论还是唯名论。有些哲学家——尤其是梅约翰所讲的“关联论者”——通过坚持名与其所指的自然对应来找到这种相当;而另一些哲学家——尤其是梅约翰所讲的“唯名论者”——致力于以不同方式的“名的恰当应用”,或者说“正名”来实现并/或保持合宜的相当性。“正名”出自《论语·子路篇》(13.3),可以说是这一进路最知名的表述了。
梅约翰认为,对徐干来说,名实之间的理想关系是“它们彼此相应,名忠实地反映实,而实赋予名意义”③John Makeham,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p.xiii.。在我们看来,这一立场不仅总结了徐干对命名的规范性观点,而且代表了中国古代名学的“主流”立场:受到普遍追求的是得当之名,即准确符合所指(如实或形)的名,而不当之名则被认为是成问题的。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论争通常并不质疑这种相当是理想的,而是在以下方面有分歧:(1)这种相当的基础,或被感知到的不当的基础,以及(2)实施这种相当的最佳方法。换言之,尽管得当之名的理想性被广为认同,对其哲学基础、伦理功能及社会政治影响却有相当大的分歧。
根据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的观点,有序的社会政治须有得当之名,而名实不当则说明社会政治混乱。所以,尤其在儒家作品中(但在法家文本中同样如此),名通常关联着家庭或国家的社会角色、等级与官职(如“父”或“君”,《论语·颜渊》[12.11]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要求君要做得像个君、父要做得像个父)。与之相应,“实”或“形”表示一个承担特定角色、处于特定等级或供职于特定部门的人之真实品质或表现。“名”还可以指称一个人的名誉或社会“标签”,如“仁人”,或与之相对的“盗”。诸多儒家文本,如《论语》或《孟子》,都表述或暗示了一种典型的期待:社会秩序依赖于那些以德著称的人实有其德,以及居有显赫社会等级和官职的人实有其行。于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人们希望得当之名能保障和谐的家庭生活与高效的政治管理,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这造就了一种道德使命,每人都应该“真诚”(诚)地满足其社会角色、等级与名誉的期待,从而创造正当合宜(义)的社会结构。结果,得当之名的学说实际上催生了用来推行这种得当的个人与社会规训机制。
个人德性、社会等级与名誉之间可能存在完全相当的理想状态,这种想法为猜疑、伪善、欺诈,以及可能最成问题的自欺打开了空间。社会现实一再表明,身居高位者并不必然是实际上的贤人。一旦名之得当成了规范性命令,现实中的不当就闯入视野。儒家对治这一困境的办法,则是坚持“冷酷”的道德修养;要求从社会政治和个人内在两方面,进行持续不断的道德省察,以确保每个人做到善如其名(例如,父亲应该一直劳心于尽到父亲的责任)——倘若是坏名誉,则一个人应当着意改变自己的恶行,以便重获社会认可。
从儒家视角看,通过道德培养,实现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等级(即他的名)与其真实品格和行为表现(也就是他的名的现实所指)之间完美而真正的相符,这终将(有望)导向一个良善稳定的社会。然而,其他思想流派则在方法论层面有不同见解,认为需要运用道德修养之外其他更“实用”的手段来实现得当之名。例如,法家制定严格的赏罚机制,以确保社会角色之名与角色承担者的行为之间实现可能的最佳匹配。对他们而言,要实现社会政治上的得当之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严格监管所有角色的行为、严厉规训一切名实不当的情形。
针对得当之名的范式所带来的实践上的困境,《庄子》的哲学立场在中国早期哲学中显得与众不同。它并没有费心寻找个人规训或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以实现得当之名。在《庄子》那里,我们惊诧地看到,中国古代得当之名的主流理想往往被另一种不当之名的哲学所颠覆、解构和挑战。
三、《庄子》中的三种不当之名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庄子》中的名学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不当的理论——至少部分如此。①之所以说“部分如此”,那是因为我们承认它是多维度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并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异质性的文本,混合了不同来源的材料,表达了多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立场。我们认为,它是作为对得当之名的理想的反对立场出现的,尤其是以一种批判、讽刺的方式回应了将这种得当加于他人,并最终加于自身的不良社会政治机制。简言之,《庄子》将得当之名的要求视作产生社会政治压迫、欺骗或伪善以及个人压抑、自满或傲慢的根源。
3.1 “道”与“圣”:不当之名
简言之,《庄子》文本中有三种不同却相关的名学进路。首先,通过坚持对道之无名无形从而不可说的否定性理解,进至一种不当之名的终极哲学。这一理解在风格与内容上都让人想起《老子》,并回响着“道常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与“无名天地之始”(《老子》第一章)这样的名言。《庄子》中“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与“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诸说强调,除了可用殊别的名与形以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与任务来辨别的万物之世界外,还有作为一切活动非特定的创生中心的道。它在社会中就是圣王。这一无名无形的(力量)中心没有任务或等级,从而有别于一切名/形。这里用哲学架构区分了道和(仍是得当的)形(或实)名之域,前者因其无名无形而构成后者的内在源泉,并为之提供秩序。这一哲学在《老子》及《庄子》相应部分中都有明显的政治内涵。简言之,一方面,它跟主流哲学一样,认为秩序等于名实(或形)相当;另一方面,它则认为,秩序的源头无名无形(或实),因而并不从属于名实相当。由此而来的道之不可说性,可以说是构成了道及其名之间的不当。吊诡的是,尽管存在形名相当,但这种相当止于道与圣人。最重要的名,即“道”与“圣人”是不当的。
3.2 荣耀之名的不当
《庄子》中名学的第二种进路更具特色,而且跟《老子》没有直接关联。它将道的不可说性及相应的“道”与“圣人”之名不当的观点应用于社会政治批判。《庄子》中的许多有名的叙述指出,一位道家圣人不是成为无名无形的君王,而是不为显名高位所动。道家会尽力避免担任官职,尤其要摆脱对社会名誉的欲求。
将无名无形的道家哲学具体运用于对儒家追求社会名誉和认可的社会批判,《庄子》内篇中有一个段落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庄子·德充符》中,叔山无趾,一个“夫无趾,兀者也”的刑余之人,在与老子的对话中说孔子“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庄子·山木》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孔子未能在道德上教化当时的政治家而处于饥饿边缘。于是与孔子对话的道家解释说,他的祸患是由于追求功绩与名誉,故而不如“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
强调不可说之道的进路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安置形名相符,《庄子》名学的第二种进路则显然与此不同。它隐含了对得当之名这一理想的质疑,强调通过承担强有力的政治或社会角色来追求美名是徒劳的(或无意义的)。它指出,这种追名逐利与对社会赞誉的渴求会败坏一个人,并最终通过社会诡计与机制的终极消耗来毁灭此人,故而一个人应当尽可能保持“无名”无誉;不仅如此,它还触及了名实(形)之领域本身包含的某种不当。与荣耀之名相应于一个人的现实品格的假设相反,《庄子》中反对追名逐利的叙事指出,社会等级与名誉本就是人为造作的,试图与它们相一致是一种徒劳的、且终将导致毁灭或败坏的努力。
3.3 名与实/形之不当
《庄子》中反对追名逐利的叙述,为第三种最为激进的名学进路铺平了道路:一种明确主张名实(或形)不当的哲学。这一进路明确地颠覆了追求得当之名的主流观念。而且,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反响。
一般说来,名实不当——这一观念在《庄子·至乐》中简洁地表达为“名止于实”。杨国荣认为,这句话所反映的名实观与《逍遥游》中的另一句话相联系:“名者,实之宾也。”①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虽然不确定这两句是否真的囊括了《庄子》名实(或形)观的全部,但它们以缩略的方式表达了《庄子》在别处以叙事勾勒的洞见:事实上,社会称号既没有描述人或物的“真正”所是,也没有规范其所当是。
关于道家式的名实不当,最有名的故事之一见于《庄子》内篇《大宗师》。在这则想象的故事中,孔子的爱徒颜回问孔子,孟孙才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无涕、中心不戚,为何在鲁国(孔子的母邦)却被认为“善处丧”。惊讶的颜回想知道何以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在这里,颜回讲出了一种标准的儒家式期待,认为一个人实际的“存在状态”(“实”)应当合乎其社会角色,在这个故事中也就是父母去世之际居丧者的角色。以一种《庄子》特有的反讽,孔子一反儒者的角色期待,极为不当地从道家的角度答复颜回。简言之,他指向一种“物化”的道家宇宙论,主张万物都处在持续不断的生死历程之中。孟孙才领悟到,万物本性的无常构成了生命再生产的核心。于是,就像《庄子》中诸多其他道家式人物一样,他能够沉着冷静地面对死亡。
儒家对父母去世的儿子有着极其严苛的角色期待。父母的丧礼更是“孝”的试金石。因此,从儒家视角看,居丧不哀是最严重的伦理过错,违反了被奉为社会秩序之支撑、共同体之纽结的最基本的规范性基础。孟孙才表现出的不当对儒者而言是极其离经叛道的。然而,反讽的是,在故事中孔子赞扬孟孙才,如此离经叛道的不当反而成为某种更高智慧的表现。同时,这揭露了儒家社会规范与角色期待的虚假与伪善。在至关重要且充满道德与情感的丧礼中,有着对生命的极度无知;同时,这也给那些努力使自己的人格(或“实”)与儒家之“名”相匹配的人施加了不必要的哀伤与沮丧。
孟孙才的故事表明,基于对彻底转化的承认,一切社会角色之名所指示的“形”或“实”——尽管它们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在本体论和生存论上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样,道家对“物化”的洞见就意味着否定儒家社会之名的“诚”,也就是说,否定用社会之名为自我奠基,将社会之名作为自我的本质之形或实。彻底转化(transformation)的观点在本体论上意味着,没有形(form)能够真正与名相配。
在不那么本体论或生存论的层面上,名实(或形)不符被人格化,这在《庄子》中随处可见。《德充符》介绍了数位“残疾”的人物,他们或有身体疾病,形体不正,或像上文提到的叔山无趾一样遭受法律惩罚带来的残疾。然而,《德充篇》中的残疾人和刑余之人大都有引人瞩目的社会成就。他们由此驳斥了社会等级与名誉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内外之“形”的儒家期待。实际上,借用艾文贺(P.J.Ivanhoe)对篇名“德充符”的刻画,这些人物都可被理解为“对孟子理想人格的有意戏仿”①Philip J.Ivanhoe,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The Thought of Mengzi and WANG Yangming,Indianapolis:Hackett,2002,p.188.不过,我们无意暗示,《庄子》早期篇章的作者必然知道孟子其人其书。。作为名实不当的荒诞典型,他们削弱并嘲弄了人们通常的期待:取得社会成功的人都是健康、善良、“正常”的。主要人物之一哀骀它便被描绘为“德不形者”(《庄子·德充符》)。
尽管避免社会等级与名誉并保持“无名”是有益的,也应当意识到名与名誉之“无形”(《庄子·德充符》便如此描述第一位主人公王骀)。儒家的社会政治教义暗示社会权力反映着有德之“形”,而诸如《德充符》中的刑余之人与残疾人这样的反讽角色却表明,成功的外表下空无一物。社会成功是“无形”的。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使自己的“存在状态”忠于社会构造的角色与名誉,从而真正成为好人,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庄子·盗跖》中,孔子见盗跖的诙谐故事花了一定笔墨来勾画社会性的名实不当。有论者认为,《盗跖》篇名已见于《史记》(卷六十三)的庄子传,它甚至可能比(某些)《内篇》更古、更可信。①Esther Klein,“Were There‘Inner Chapters’in the Warring States?A New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about the Zhuangzi,”T'oung Pao,96(2010):299-369.或许,《史记》提及它并认为它带有反儒家的论辩或讽刺意味,这清楚地表明它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极具代表性的庄子式作品。故事中充满了不当。它将盗跖与孔子相对照。盗跖强壮、健康、聪慧、勇猛、帅气,同时却邪恶、残暴、态度恶劣,换言之,完全不道德;而孔子则是国家权力、社会秩序、规范伦理的代表,但却表现得相当愚蠢、可笑、荒诞、造作,像个马屁精和十足的伪君子,但同时他也被描绘地极其礼貌、谈吐得体、善解人意。对话围绕孔子对盗跖的(显然失败的)提议展开,孔子对盗跖说只要他加入国家权力机关,他将获得爵位、封地,并且再也不被名为“盗”(这在孔子眼里是最重要的)。盗跖无比生动地揭露了孔子的伪善,且愤愤然曰:“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这个故事可被解读为一种对社会腐败的激烈批判,而社会腐败的根源,正是要在社会角色与个人品质相当的基础之上建立规范这一不可能实现的期待。直白地说,那就是:名导致腐败,绝对忠于名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篇的道家立场,显然不是主张放弃儒家为达到名实相当所做的失败尝试,并代之以可能会成功的、道家式的“真正的”名实(或形)相当。②如所周知,《庄子·齐物论》反复地极力主张避免此种努力。相反,《庄子》不断以反讽的形式颠覆树立代表此种名实相符的典范人物的努力。它的人物是反模范的,由此表明按照社会等级与名誉加诸己身的要求来形塑自我的尝试,何以是造作与伪善的根源。因此,《庄子》不是试图达到名实相当;相反,通过诸多叙事,通过诸多名实不当的人物(包括盗跖,《德充符》中的残疾人与刑余之人等),《庄子》主张“名止于实”。故而,重要的不在于奋力达到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符合社会身份规定(所以不仅仅是要避免身居高位),而在于最终保持“无名”、“无形”,从而在社会的“虚荣之火”中保持清醒。
四、玄学中的三种不当
根据汤用彤的说法,对名实之辨的哲学理解是魏晋学术或曰玄学的核心。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2页。玄学家发展了上述《庄子》中名实不可能相当的观念②尽管名实之辨在魏晋思想中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同,这一话题却并未被彻底深究。大多数学者毋宁关注或许同样重要的言意之辨,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Rudolf Wagner,The Craft of the Chinese Commentator:Wang Bi on the Laozi,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Rudolf Wagner,The Language,Ont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ina:Wang Bi's Scholarly Exploration of the Dark(Xuanxu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暴庆刚:《反思与重构:郭象〈庄子注〉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才清华:《言意之辨与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对魏晋言意之辨的再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或关注言与理的关系,如,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暴庆刚:《反思与重构》;尚建飞:《魏晋玄学道德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对后来中国佛教文本的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数何晏、王弼与郭象。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并不清晰地关联于上述三种不当。或许最切近的直接阐发在于道的不可说性。
何晏与王弼援引《老》、《庄》所讲的“道不可道”来支持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的一个说法:尧是不可名的。何晏主要关注道之不可说,而王弼则比他更进一步,认为儒家的德性与道德在一般意义上也是不可用语言表达的。这一论说的进一步发展见于郭象的作品。郭象基于对《老子》、《庄子》与王弼作品中的“迹”一词之体认,以一种与佛教观点不无相似的方式指出③魏晋研究者激烈地争论,佛教最初何时被引入中国,在不同时期又被接受到何种程度。例如,贾静华认为,郭象紧紧追随《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汉译本。见Jia Jinhua,“Redefining the Ideal Character: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Concept of Detachment,”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14 No.4(2015):551。任博克(Brook Ziporyn)等其他学者则主张,郭象哲学“根植于中国古代(前佛教)的本土哲学”。见Brook Ziporyn,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4。,名总是固定的,而名之所名(也就是实)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名实不当不可避免。
魏晋哲学对名实之辨的关注基于汉末对广为存在的社会、政治与道德伪善的担忧。④许多研究魏晋哲学的著名学者都注意到,导致汉代社会、政治和道德伪善的名实相符之破裂,对诸多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来说都是关键问题。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余敦康:《魏晋玄学史》;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他们常常使用《庄子》中“有其名而无其实”一语来描述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名无实对《庄子》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如王符与徐干就将名之滥用视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根据徐干的说法,《论语·阳货篇》中孔子对伪善“乡愿”的评价就已意识到名之误用的危险。徐干论曰:“今伪名者之乱德也。”①徐干:《中论》,载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2页。英译参见John Makeham,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pp.107-108。对王符与徐干来说,解决之道在于靠孔子的教导来重建名实相当。魏晋时期的思想家则在不同程度上怀疑建立此种相当的可能性。在这一问题上老庄的影响格外深远,尽管儒家概念依然是许多理论家的支柱。②人们普遍认为,何晏、王弼与郭象就其政治、道德与社会信念而言终归是儒家。见Brook Ziporyn,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余敦康:《魏晋玄学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尚建飞:《魏晋玄学道德哲学研究》。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试图重构《论语》中的主题与《老子》及《庄子》中的主题之间的关系。③人们通常认为,玄学家试图“融合”、“整合”儒道两家。参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余敦康:《魏晋玄学史》。不过,笔者认为,至少玄学家很有可能确实相信他们所指出的儒道之间的相似点。参见Alan Chan,“Introduction”,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an Chan and Lo Yuet-Keung(ed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0;D'Ambrosio,“Wei-Jin Period Xuanxue‘Neo-Daoism’:Rewor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and Daoist Themes,”Philosophy Compass,11(2016):1-11。这种重构和得当与否问题之间存在哲学关联,这一点从名教与自然之辨中可以看出。④汤用彤使这两个术语被推广开来,比如他写道:“孔子贵名教,老庄崇自然。”(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107页。)之后的学者,如杨立华,便将这两个术语的流行归功于汤用彤。(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第36页。)几乎所有当代研究魏晋哲学的学者都讲“名教”和“自然”。这对术语往往分别散见于儒家和道家⑤例如陈金梁(Alan Chan)便通过有力的论证将“名教”关联于儒家正统,或至少尝试建立这样的正统。Alan Chan,“Introduction,”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an Chan and Lo Yuet-Keung(eds.),pp.3-4.,尽管对名教与自然的讨论可以(也往往应当)把握它们更加微妙的内涵。⑥当然,这一联结在哲学上多大程度是适当的,这主要取决于论证的语境。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这一问题可不予深究。重新设想自然与名教之关联的主要动机在于,将对名教的盲目遵从与一般意义上对名的依赖,替换为一种社会、政治与道德的关键观念之不可说的哲学理论。魏晋思想家试图由此从根本上消除伪善的可能性。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需要论证名实不当。何晏首先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尝试。
4.1 何晏:名不当于道
何晏现存的两篇主要作品《道论》与《无名论》都解释了道何以不可说。何晏在文中论曰,一切有,包括一切实在,都来自道。这也包括所有的“特性”(也是“有”)。①对何晏及许多其他中国哲学家来说,没有“物的特性”或“属性”与所谓“物自体”或“本质”之间的区分。而创生这一切者,其本身是全,囊括了一切分别或对待的实在,因而是无名的。在《道论》中,何晏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
则道之全焉……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②英译参见Alan Chan,“Sage Nature and the Logic of Namelessness:Reconstructing HE Yan's Explication of Dao,”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an Chan and Lo Yuet-Keung(eds.),p.25。
道生成了形及其相应的名,但自身保持在名的领域之外。名与形相当,因为它们指示了形之特性。然而没有什么能使道成为特定之物。它没有特定的形,故而没有名。③这不一定是一个本体论论证。说道无“形”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也不表示道外在于“存在”或“有”(见前注)。何晏推论,这表明了道之全,进而发现道与孔子在《论语》中所描述的至善模范,也就是尧,是相通的。在《无名论》中,何晏说:
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则强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德遍以天下之名而名之。④英译参见Alan Chan,“Sage Nature and the Logic of Namelessness:Reconstructing HE Yan's Explication of Dao,”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an Chan and Lo Yuet-Keung(eds.),pp.27-28。对何晏来说,道之“无名”就类似于《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尧“荡荡乎”从而不能名的称赞。正如可以取任何一个名来命名尧,也可以取任何一个名来命名道。玄、素、方、圆都是描述道的词,但它们只触及道有限的某部分,因而并不能充分地成为与“道”相当的词。道“无名”,因为虽可以“德遍以天下之名而名之”,却找不到一个完全得当之名。何晏由此断定尧之无名与道之无名有着连续性:尧是全德的,故而包含了一切可名的德性;道是万物之母,所以囊括了所有的名(及可名之形)。用语言描述尧或道只能触及他们整体性的某些方面;二者都足够完满,不能受限于任何一个名。
4.2 王弼:将不当扩展至名与德之间
从哲学意义上看,王弼对《论语·泰伯》中的尧的评论与何晏相似。然而,王弼运用了一套直接触及本文主题的语汇。王弼说,孔子对尧“荡荡乎”且不可名的描述是“无形无名之称也”①王弼:《论语释疑》,载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26页。。借助《老子》的逻辑,王弼推论说,尧作为至善,没有与善相对之“恶”,这就意味着他是无法描述的。王弼写道:“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②王弼:《论语释疑》,载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626页。换言之,尧之善作为至善,不是那种被描述成与恶相对的善。于是,因其完美的德性(即不掺杂任何恶),尧不能以任何名与指称的方式来触及。这里,王弼开始把德本身解读为不可说:
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③王弼:《论语释疑》,载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626页。
王弼由此超越了何晏,将名与尧之德之间的不当扩展为更一般的名与德本身之间的不当。在《论语》举的有德的例子中,孔子给出的名与描述并不触及他所谈论的对象之“大”与“至”。像道一样,孔子所讲的德本身处于名与实的领域之外。德之名与德本身不可能相当。
由此,王弼指出了名形之不可说的根源和名形本身之间的不当,这也是贯穿《老子》和《庄子》的主题。①在道德和政治领域之外,王弼以为“凡名生于形”。但是这一关于名的说法,是为了为批判无形之德与道皆不可名。可进一步参见Jude Soo-Meng Chua,“Tracing the Dao:WANG Bi's Theory of Names,”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an Chan and Lo Yuet-Keung(eds.)。德是不可名的,正如道不能用语言充分地描述。给道或德命名,就会把它们化约为片面之物。二者都没有能够被语言充分表达的固定特性。这进而说明,为什么道德因时间而变,或者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表达。
在《老子指略》开头几段文字中,王弼在道德实践(或规范)与道之间建立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用孔子之德不可名的论点来解释不断转化的道德表现。这里,王弼把“名”与“象”(借自《易经》的术语)关联起来。王弼以诗意的表达阐述了作为道之显现的道德何以不在形名之域:
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用大音则风俗移也……风俗虽移,移而不能辩也。……圣行五教,不言为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②王弼:《老子指略》,载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195页。英译参见Richard John Lynn(trans.),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30—31。
名与象都处在言与形的领域之中。道与道德可能将自己投射到这一领域中,但终归在此领域之外。德可以显现于形之域,但不可能完全敞开自身于形之域。因此,孔子的教诲对道德的阐明是有局限的,正如用“道”或任何其他标签来阐明道是有局限的。事实上,王弼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只用“无形”、“无名”、“此”,而非用“道”,从而比《老子》中(大家都接受)的“强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更进一步。此外,王弼发展出了一套与此相应的对《论语》的理解。在《论语》中,孔子很大程度上通过例子来说明道德。王弼用德名不当的理论来解释为何孔子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给语词下定义。按王弼的观点,孔子在判断道德是否恰当时关注人与情境的特珠性,由此可以发展出德名不当的理论。
在对《老子》的注解中,王弼用术语“迹”发展了这一理论。“迹”在郭象那里至关重要,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佛学。它出自《老子》第二十七章:“善行无辙迹。”①英译参见Hans-Georg Moeller(trans.),Dao De Jing,Chicago:Open Court,2007,p.67.王弼注:“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故物得至,而无辙迹也。”②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载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71页。反观他对德性与道德的评论,“迹”的角色就变得清楚了;它是自然的行为所留下的印记。③任博克认为,“迹”在哲学上最好译作“trace”。参见Brook Ziporyn,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他的这一主张很有影响。汉学家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则持不同的看法,他更青睐于用“footprint”来直译“迹”。参见Richard John Lynn(trans.),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对王弼来说,善与德的特征在于不留下这样的印记。可命名的那部分“自然”只是已逝之物留下的痕迹。故而德或道德之名指向的形只是痕迹而非“自然”之德或道德本身。名只相应于作为德之痕迹的形。
4.3 郭象:名与一切实之间的不当
郭象比王弼更强调“自然”概念。对郭象来说,一切都已经是自然,无一例外。就不当而言,郭象一方面关注名的固定化问题,另一方面关注一切形与实恒常的模糊短暂。在郭象看来,一切名实关系都是不当的。
王弼强调不可说、无形无状的无,郭象则转向《庄子》中另一重要主题:变或化。《庄子·大宗师》郭象注:
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④郭象:《大宗师注》,载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9页。英译参见Brook Ziporyn,Zhuangzi: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Indianapolis:Hackett,2009,p.195。
我们在下一节将会看到,这段论述与后来的中国佛学有一些共同的术语。⑤僧肇《物不迁论》开篇就引用了此注部分文字,但僧肇的结论却与郭象相反。参见下一节。然而重要的是,这是《庄子》强调“化”的逻辑发展。在郭象注所对应的原文中,《庄子》论说了死生之变化与日夜之更替,并进而考察万物的不断转化。就人而言,“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在郭象的哲学中,万物转瞬即逝的本性构成了一切名与一切实的关系。
如果实永远是不同的,如果它们无时不变,那么任何固定它们的尝试,尤其通过命名来固定它们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原初的行动、自我或实留下了迹,但它一出现就消逝了。剩下的只是已经转换成他物的某种东西的印迹。任何已成之事、已存之物都永远消失了。对郭象来说,任何事或任何物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一切都紧密相联。①这就是郭象所讲的“冥”。在郭象看来,万物相“冥”:一方面,物不再是其所是;另一方面,物都受他物的影响。参见Brook Ziporyn,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pp.85-99。每一物、每一行动都是其环境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是构成这一环境的其他一切物与行动的一部分。故而,一个因素的变动意味着其他一切因素的转化。
这里的困难在于,迹往往不被认作迹;它们被错认为留下迹之物。就命名而言,这一问题就表现为预设名实可以相当。名是固定的,顶多不过能相应于已逝之物的迹——而不是实本身。郭象总结道:“名法者,已过之迹耳,非适足也。”②郭象:《则阳注》,载郭庆藩:《庄子集释》,第879页。英译参见Brook Ziporyn,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p.53。
在道德领域,郭象的名实不当理论或许接近王弼;然而,郭象对名实不当的论证并不基于全或无形的不可说,而是基于承认恒常变化。郭象写道:
仁者,兼爱之迹;义者,成物之功。爱之非仁,行迹仁焉;成之非义,义功见焉。存夫仁义,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犹未玄达也。③郭象:《大宗师注》,载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93页。英译参见Brook Ziporyn,Zhuangzi:The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p.204。
这里,郭象区分了兼爱之“实”与通常所谓的“仁”,以及成物与通常所谓的“义”。这些名不能触及实的原因,并非像王弼所说的那样,是有德之人处于无形无状的领域,而是所有的实都不断变化。所有的名,如郭象所言,都是“寄名”。④郭象:《大宗师注》,载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36页。任博克把“寄名”翻译成“borrowed names”(Brook Ziporyn,Zhuang Zi: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p.192),这适用于所引这段话的语境,但是为了避免与同样可以理解为“borrowed names”的佛教术语“假名”相混淆,我们用“adopted names”来翻译“寄名”。它们与变动不居的实不当。①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第260—262页。在下节中,我们将看到,佛学理论如何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代表了《庄子》之名实不当论证的另一种转化。
五、中国佛学思想中的不当
5.1 中观二谛观中的不当与不二
魏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作了四篇文章,是为《肇论》,并作《维摩诘经》注。他将道家与玄学中关于不当的观点与表达融入对般若与中观思想的阐发。
龙树中观学通过鸠摩罗什的汉译传入中国。它主张缘起故空,强调真、俗二谛之分。俗谛需要诉诸语言,因而无法与真谛的不可说义相当——后者不能被任何语言构造所扭曲。简别不当的俗谛与不可说的真谛,这意味着,人们感知到的名物相当并非名实之间真正的相当。僧肇用道家语言将佛学的二谛分别表述为“名实无当”。
需要注意的是,此种不当却关联着僧肇讲到的另两层相当:(1)“不当”不等于说世俗意义上的名物完全分离或任意相合——相反,为了能够交流,我们的日常言说预设了名与所指(物)的相符,二者在语言建构的世俗领域中须是“相待”的;(2)吊诡的是,此种对不当的洞见,对我们领悟佛经中的教言与“解脱”的不可说义之间的一贯性来说却至关重要。此种一贯相应于中观的“不二”,而这也只能借助我们对不当的洞见来认识到。②一位匿名审读者指出,僧肇对“不二”的理解不容许“不当”。实际上,僧肇用了“不当”二字。而且,与审读者的主张相反,僧肇在他的著作中从未明确讨论“不二”,虽然我们认为他的论述(像在所有大乘佛教文本中一样)总是隐秘地涉及“不二”。不过,有一位叫吉藏的中国中观大师,明确处理了“不二”的概念,他对僧肇的作品多有借鉴。他故意用一种悖论的方式论及“不二”,曰“二表不二”。在这一语境中,“二”意味着二谛的分殊,故而正是我们所讲的中国中观思想中的“不当”。为进一步阐明作为二谛分殊(不当)与“不二”的一贯性,中国中观倡导者,如僧肇、三论宗吉藏大师、天台宗智顗大师,诉诸“迹本”——这对中国中观学概念极有可能是从郭象《庄子注》对“实”与“迹”的解释发展而来。
这表明,大乘佛教一般区分日常言说与佛言。根据这一观点,日常言说的语言构造通常产生物化,它会误导人并有欺骗性,掩盖其之所是,使人们“颠倒”,误以不真为真。相反,佛陀的经典教言却创建了一种富有教益的构造,促使我们意识到与一切语言表达紧密交缠在一起的虚假。这种语言通过经典的经和论的形式来传达,并经常用悖论来揭示其与不可说者的一贯性。①鸠摩罗什等人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这种语言的典范,例如:“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T08,no.236,p.758,a24)所以,对中国佛教大师们来说,语言是矛盾的。他们在注解印度经论时,往往试图阐明原文中富有启发性和典范意义的语言策略,这种语言策略使人们摆脱语言的误用,同时暗示佛陀洞见的不可说义。
大乘佛教的教义包含两个主要方面:(1)它试图探查一种不可感知的欺骗的束缚,这种束缚根植于一切概念化的思想,并产生了内在于诸种语言指称中的物化;(2)它探索如何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洞察和意识到根本的、不可避免的虚假,这能促使人们最终洞见到,意向行动的指涉都是空的(真谛),由此最终从一切内在的欺骗与颠倒中解脱出来。这种意义的空与解脱超越了语言与思想,但并不意味全然非存在,尽管它确实否认事物固有存在。任何一物的产生都不分离于、独立于他物,任何一物都不是内在地是它看起来的样子。依中观学,特定一物的同一性完全由外在关系所决定,因而并无真正的基础;它是由缘起构成的。固有存在的空——对独立存在之实体的否定——意味着事物终究是不真实的,但同时也不是非存在。不真实不同于非存在,因为不真实可能对我们的生存产生或具启发性或具欺骗性的影响,故而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重要性。
基于这一观察,龙树指出缘起并不超出人们生存的世俗领域,不应与真谛的(不可说的)领域混为一谈。不真渗透于我们世俗存在的方式,并在特定意义上持存、栖居于真正的空:否定独立存在而又不等于非存在的空,最终维持着我们这个虚幻流变世界中诸法的缘起。空意味着真与假不可分割——中观意义上的不二。然而根据《中论》——鸠摩罗什对龙树Mūlamadhyamakakārikā的翻译——真正理解空不能混淆二者,因此必须区分(不当的)俗与(不可说的)真两个领域。①俗的领域由建构与不真所构成,它不合真谛,后者没有建构故而是不可说的。《中论》指出:“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T30,no.1564,p.32,c16-p.33,a3)二谛的此种分别认识到并表达了以下洞见:语言的虚假不可避免,即便我们阐述真正的空的时候也必须依赖此种虚假。
通过揭示不当,此种分别也引发了对佛陀教法的文本传达的自反审察:教法本身不断地将第一义的、不可说的解脱区别于偶然、暂时、不当的形式,通过后者,教法所传达的也只是世俗层面的东西。通过不断地区分,对不当的理解让我们看到第一义只能以一种区别的方式而存在,它同时也揭示了俗与真的不二即不可分割。故而中国中观学家如吉藏指出,不断区分二谛是佛陀教法的特点和语言策略,而不二则是佛陀解脱的特征。最重要的是,除了经由教法中的这些区分的痕迹,别无解脱之方;正如除了佛陀解脱中的不二,别无教法的根源。于是,通过对不当的认识,这种分别旨在将我们的理解从我们或其本身的欺骗性物化中解脱出来;这就相当于将不可说义揭示为不二(也就是空不离缘起、真不离假、俗义不离第一义)。
5.2 僧肇论名实不当
僧肇试图弘扬在鸠摩罗什时代尚不为中国学界所知的中观思想。僧肇认为,《庄子》中对名实相当的否定有助于澄清佛学对语言指称的讨论。然而,与《庄子》不同,僧肇无意于批判,人类生存领域中的实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与建构。他采纳道家名实不当之说,却无意真正考虑其社会政治意涵。他的论说意在结合道之不可说的概念,以本土思想传统阐明佛教的不思议解脱义。他的格言“实不当名”似乎是仿照“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而作。
在此语境中需要注意,僧肇的格言意味着对汉字“实”作了新的阐释。前文所讲的“实”指实在之物,对应英文“actuality”。除了这个含义之外,“实”在僧肇那里似乎还被用来传达在印度佛经的汉译与解释过程中产生的新义。例如,“实”出现于汉语佛学新术语“实相”中,它通常被英译为“real mark”或“mark of reality”,相应于梵文dharmat等表达。①参见程恭让论鸠摩罗什对“实相”的翻译及天台宗对这一术语之使用。程恭让:《鸠摩罗什〈维摩诘经〉实相译语及天台疏释之研究》,《华梵人文学报》,2013年第23期。它们都表示中观意义的空。此种空乃终极的真实,却否认被认为与名相符的真实存在或实在之物。依佛教空观,可名之“实”不真而空,而“实相”脱离语言指称,并例证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真谛。在佛教语境中,“实”意味着一种“reality”(真实),它不能被认为是与任何名相符的“actuality”(实在之物)。
僧肇的第二篇论文《不真空论》阐发了一个复杂的观点,认为名与物的相符并不意味着名与实的相符。表达这一观点的命题来源于一则改编自《庄子》的引文,它主张对现有之物的世界保持漠然与平静。《庄子》中的原文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山木》)僧肇以极其相似的措辞修改了其意涵,并将其跟佛学对语言意义的讨论关联起来:
夫以物物于物,则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虽物而非物。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实,名不即物而履真。然则真谛独静于名教之外,岂曰文言之能辩哉?(T45,no.1858,p.152,a24-27)
尽管语境的转换十分明显,就内容而言两个段落还是有所交叠,这可由僧肇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即物顺通”(T45,no.1858,p.152,b3)。②这让人想起郭象注“无心以顺有”(郭象:《大宗师注》,载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68页)。然而,二者在本体论进路上几乎是相反的。僧肇强调,为达到自如的境界,看到物之不真是很重要的,此不真又不同于物之非存在。
另一方面,《庄子》则持一种漠然平静的立场,它并不要求检视名所指之物的本体论地位,因为它只是指向一种摆脱任何指向由分殊之物所构成的世界的强制性关联的心灵境界。这一视角要求人的心灵境界与物的自然过程相契。
但是,僧肇似乎认为,道家经典以及后继玄学家发展的哲学可与佛学话语相容。他为名所指之物的不真与空提供了两种论证,并解释了将不真区别于非存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并不否认脱离语言指称的“真物”。在阐发那些由中观思想而来的观点时,他不断诉诸道家或玄学的意象、修辞与观点。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一切意向行动之所指的不真与空的论述中。
他的第一个论证运用了动静的话题,这一话题往往被玄学传统下的学者讨论。它清楚地反映了变与化的观念。如上所述,对郭象而言变与化也极其重要。僧肇观察到,语言所理解的是普遍性,且语言趋向于物化,这就意味着建构与虚假。在对语言的运用中,我们通过忽视和取消特定事物的时间性,而平齐、同化了差等的、殊别的事物。在《肇论》四篇之首论《物不迁论》中,僧肇从“静”的方面描述了特定事物的时间性维度,“静”并不排除变动不居,但又和“空”一样逸出我们概念性的理解。只有从个别的时间点来看,一物才不变地、真正地是此特定之物。从另一个时间点看,就不再有这同一个物了。结果,僧肇主张,一个特定之物尽管不断变化,却常存于个别的时间点上。
此种静否认时间之流的持续性,却不否认“真物”的连续性。它们不能真正地被表现或指涉,因为从另一个时间点看,无论真物还是它的表象都不再是同一物。由于这种意义上的时间性,我们无法谈论真正存在的事物;并且与通常的预设相反,名也是无常的——我们在不同时间所使用的并不真的是同一个名。尽管同样基于对持续不断、不可逆转之变化的论证,僧肇却和郭象不同,他并不将不当视为变动不居的实与静止不动的名(如同遗留下来的迹)之间的差别。①对郭象而言,名与迹就其不能得当地指称实而言并无差别。相反,僧肇的不当基于他对时间性的看法:不仅实(指涉物)具有时间性,而且名(符号)也具有时间性。这一视角揭示出,一切指称关系包含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隐秘的虚假。结果,他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使用“物”:与必须依俗、真二义区别阐释的“真”相似,这个字既可指“真物”也可指“不真之物”——可名的物是不真的,真物则逸出了语言指称。
僧肇《物不迁论》的标题中,“物”意味着“真物”。与这一永不移易的真物相反,我们的日常言说必须预设相反的观点,即可名的物可以在时空中移动而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对名的使用中,我们假定可以从不同的时间点指涉一个自我同一的物,这就以名实可以相符的设定构成俗谛的特征。而从标题暗含的真谛的视角来看,这一预设意味着建构与虚假。然而,僧肇的讨论又是遵从中观二谛的不二义。他试图通过“动静”这对不可分割的概念来阐明二谛的悖论式关系,而“动静”则很可能是他从王弼的作品中吸取的。
在我们看来,一物在连续的、不可逆的时间之流中的有限历程叫做“动”。实际上,这不过是不齐之物的不断变化,它们在各自分别的时间点是保持不动的。此种静只在一瞬间具有压倒一切的充盈,这就等于说——也正解释了为何真物不能成为我们指涉的对象。当我们试图指示此种静时,向我们显示的只有动,尽管无物真的在动。换言之,静并不超出表面的动,正如动并不超出真正的静。在这一层面上,动却是静,正如世俗层面的静向我们显现为动。这并不矛盾,因为僧肇所说的动属于(俗谛的)不真之物,而(第一义的)静只关乎真物;就像二谛一样,表面的动与真正的静并不互斥。
再一次,僧肇与郭象观点相左,前者认为不当来自真物的静,后者则强调不当是因为物处在不断的动中。实际上,僧肇颠倒了郭象的观点,尽管是通过同样的观察。他的颠倒是受到佛教二谛概念的启发:第一义谛是真实的,它是空与静;俗谛则代表不真实的、虚幻的、变动的方面,这些都关乎动。在僧肇看来,动静不分正如俗真不二。于是,他用前者来说明后者,同时隐秘地批判了郭象讨论不当时没有意识到不二。僧肇的阐述表明,不意识到不二,对不当的议论仍是不完整的。
僧肇“物”概念的模糊性特点也见于其他从道家与玄学资源中借用的术语。他的第二篇论文将“有”视作既真实又虚幻的存在,“无”则既是空也是非存在。就连此文的标题“不真空论”也是模糊的,因为空的解构意义也适用于这个表达本身。“空”通过否认其所指而揭示其真正的意义;正是以这一悖论的方式,名实不当得以彰显。在第三篇论文《般若无知论》中,他解释与平常的知识(或世俗的知识)相反的中观的般若,但他却用“知”同时指示高妙的智慧和与之相反的平常的、虚假的知识。
就此种模糊性而言,“物”、“有”、“无”、“知”这四个术语可以发挥像“空”这一自我指涉的表达一样的指称功能。为了揭示中观学意义上不与任何名相当的真实,这四者都必须证伪自己。僧肇对道家与玄学术语有意的模糊性使用是悖论式语言的基础,他必须采用这种语言来揭穿我们概念化思想中的欺骗性力量,揭示可思议领域的界限。若没有对自身局限与虚假性的认识,我们就不能理解真正意义的空,即中观学意义上的“真谛”。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僧肇否定名所指之物的真实性的第二种论证。在《不真空论》中,他在互相依赖的关系中讨论不真。“相待”包含了由“能所”两个因素构成的指涉关系。在文中,僧肇指出我们对言说和语言的运用将名归于物,以使二者构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此种关系中两种因素都被当作真实存在的实体。似乎没有名能够离开其所指称的真实事物而持存,也无物能够离开代表它的名而出现。二者(名与物)本于相互性与相待,都同样没有真正的基础。但是,我们运用语言之所以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恰恰又依赖于此种不真。①参见论述名实无当的段落(T45,no.1858,p.152,c18-p.153,a3)。
僧肇关于一切指涉物都是不真的说法反过来意味着真物不能被指涉。无物可真正被认为是一物,甚至意在指向特定物的符号也缺乏真正的基础。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不真,它的本体论地位不可否认,并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事实上关联并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吊诡的是,甚至“不真”这个名也因此只是个不真实的“假号”。如果一切指涉物都是不真的,可名之物的此种不真就像盲点一样逸出了我们的认知-命题式的指称。在世俗层面的认知中(及在对语言的世俗使用中),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僧肇的讨论所表明的虚假或不真是与世俗的语言使用相伴而生的盲点。
于是,通过不断地意识到不真,我们以解释学循环中进行自我修正的方式,形成了一种通达真实本性的理解。对一方(不真)的进一步洞察会修正和增进对另一方(真实)的体察,因为二者彼此不可分离;就像我们对治疗与疾病的知识相互关联一样。相互修正带来双方的增益:意识到不真意味着领会到真实,反之亦然。修行者从不觉到觉醒的转化,要求意识到并充分认识到这一演进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进步的或转化的循环,并促进修行者的改变。这是中国中观佛教之修行、觉醒与转化的核心。
在自省的基础上,我们的领会不断更新,并使我们在本体论层面,形成对不可避免却又不断逃逸的不真的洞察,此种不真构成了我们真实关联并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方式。对名实不当的体认极大地丰富了这种不真义。同时,这一体认也带来了对真俗不二的理解。
基于对不二的理解,僧肇、吉藏、智顗试图彰显不可说的解脱与经论经典形态的佛言之间的一贯性。如前所述,他们的做法是采用郭象与其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那里已有的术语“迹”和“本”。不可说的解脱被认为是构成了经论所传达教义的不可见之“本”。此种教义又包含了佛的种种“迹”,“迹”又反指并揭示不可说之本。“迹本”首先在僧肇对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经》的注解中成对出现,以解释沉默与言说的相互循环与不二。它也成为吉藏与智顗解经的重要工具。①参见僧肇《注维摩诘经》中常被智顗与吉藏引用的段落:“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T38,no.1775,p.327,a27-b5)在支谦所译的现存最早的汉译本《维摩诘经》第一品中,“迹”与“本”这两个术语就成对出现了(T14,no.474,p.519,b2 3)。然而,此时它们还不具有僧肇、吉藏、智顗后来所赋予的不二意义。鸠摩罗什和玄奘所译的《维摩诘经》(以及现存的梵本)中并不包含这对术语,它们都有支谦用“迹”与“本”别译的那段文字。中国古代佛学从本土的玄学传统中借鉴了这对术语。
吉藏特别强调“迹”意味着二谛的分别,它印证了俗名与不可说之真谛不相符的洞见,从而传达了经论的整个教义即佛言。“本”包含于对不二的理解中,蕴含着真不离假。与龙树的二谛义相应,他强调本的不二只有通过迹的分别才能被揭示。换言之,除了通过分别而洞见到不当,不二无从领会。
尽管来源于道家与玄学,“迹”却在佛学语境中得到不同的评价:郭象强调,对固定之迹的执着可能妨碍我们和实在永远变动不居的自然过程保持一致;中国中观学却强调,离开了迹,本无从开显,因为正是本构成了所有的迹。但另一方面,佛家也和郭象一样,认为我们对迹的执着会带来负面效应。因此,中国中观学的不二义就在于,迹是虚幻之物,但离开迹,就无从通达第一义;本是第一义,但离开本,迹就无从构成。最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不二的循环理解中,中国中观学意义上的名实不当揭示了一种超越道家与玄学对不可说之论述的面向,后者本是这种启发的来源。
六、结语
本文意在重构一个哲学主题的历史脉络。这一主题首先在《庄子》中作为一个多少有些颠覆性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被思及。尽管存在重要差异,“古典”时期诸多哲学家都在伦理上要求,社会角色、政治功能应与这一角色和功能的实际表现相当。比如,孔子宣扬道德意义上的“正名”,法家则提倡“名”严格符合“形”(“实”)以服务于政治目的。如我们所论,《庄子》在这种符合的要求之外提出了另一种有代表性的道家方案,并进而发展出一种“解构”理论,即解构那种要求人献身于实现指定角色的理想。对社会角色期待的满足或许只会导致生存意义或社会意义上的空虚、伪善和/或腐败。《庄子》提出了无形无名的可能性,主张远离社会给自己规定的身份,并时常建议完全拒绝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一社会政治态度和生存态度关联着道家对更一般的不可说之“道”的理解。道没有具体的特性,故而无形无名。在社会政治语境中,它的不可说性反映为并不认同社会给定之名的道家式抵制。
魏晋玄学关注道家与儒家的重要主题之间的关系。至少三位重要思想家,即何晏、王弼与郭象,继续探讨《庄子》中已经出现的名形(实)不当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名实之辨是玄学文本的中心关切。何晏与王弼试图调和儒家的道德教诲与道家所理解的不当及不可说。在何晏看来,儒家圣王尧之德与道家的不可说之道相似,因为它是完满的、没有具体规定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道德论说有其语言的界限。不能界定的善是不可命名的。这样,道家的不可说主题被用于伦理之域,而道德术语一般说来都是不当之名——王弼在《论语》注中指出了这一点,解《易经》时又予以更广泛的讨论。最后,郭象探讨了《老子》和《庄子》与王弼作品中的“迹”这一道家概念。这一隐喻代表着万物不可捉摸。既然万物是不断转化的,名只能指认某种(总是)已经进一步转化之物的某个瞬间。因此,名及其所指的关系中有着内在的悖论。名是静止的“迹”,是变动不居的“自然”的遗留物。于是迹的意象象征着固定之名与动态之实的内在不当。
道家的不当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可说概念,在中国佛学的转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观学大师僧肇导夫先路,大量运用道家观点与术语来阐释与发展佛教哲学。与吉藏和智顗等后来其他重要的佛教大师一样,僧肇指出了不二:一方面,佛陀教法的真谛呈现了不可说的“不思议解脱”;另一方面,世俗的语言表达,例如在佛教文本中,因为语言的物化而产生虚假。尽管在世俗意义上,语言对交流与构成人们的经验性存在是必要的,但它同时带来了固有实体的幻相,从而蒙蔽了对万法缘起的解悟。为揭示仅从世俗角度理解真理是片面的,僧肇对“名实无当”作了道家式的批判。然而,不同于道家和玄学前辈,僧肇的批判既不是社会政治的也不是道德的。他运用道家的概念框架及其相关的不当和不可说等术语,旨在阐明一种佛教本体论的复杂性,并提出一种救赎的觉醒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