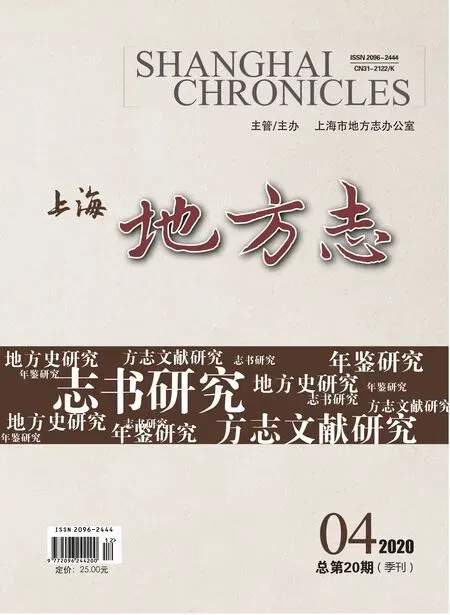名声之外:宋代福建的私家出版业
宋代私家刻书非常普遍,刻书数量很多,根据后世传本以及各家书目考证,两宋的私人刻书家见于著录者40位左右。私家刻书底本完好,校勘细致,雕印质量较佳,私刻“紧紧抓住了选底本、校勘、书写、刻版(包括印刷装潢)等出版印刷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所以才印出高质量的书籍”。①肖东发:《私家刻书的源流及特点》,《编辑之友》1991年第6期。宋代福建作为当时印刷和出版中心之一,其私家出版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宋代福建的私家出版业
在宋代福建印刷出版事业中,私刻是与官刻、坊刻鼎足而立的另外一个刻书系统,私刻本一般冠以“某宅”“某斋”“某府”“某家塾”等字样。特别是家塾本,是宋代福建私刻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版本。
家塾是以家中子弟为教学对象的一种教育形式,对家中子弟的教育和培养起到重要作用。如朱熹杰出弟子之一蔡元定的成才,就离不开家塾教育。建阳人蔡发早年游学四方,后“杜门扫轨,专以读书教子为事。子元定生十岁,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语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号‘牧堂老人’。朱文公称其所以教子者,不干利禄,而开之以圣贤之学,其志识高远,非世人所及”。胡安国培养他的侄子胡寅也是很有办法,“少桀黠难制,安国闭之空阁中,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日:‘当有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寅悉成诵,不遗一卷。寅早闻道于家庭,与弟宏磨砻薰染,所学粹然”。②张琦:《建宁府志》,南平地区方志委标点本1994年,第616页。此外,胡安国家塾还培养了胡宏、胡宪、胡宁等名震一时的大儒。
宋代各级统治者尊师重教尤为显著,知识分子地位高过历代王朝。许多名门大族、官僚士绅家里都设有私塾,聘请先生教育子弟。这些先生都是饱学之士,在教书之余,还从事编书、校书活动。主人或出于对先生治学精神的敬佩,或出于附庸风雅,或为了培养子弟读书兴趣,往往会出资赞助先生刊刻书籍。叶德辉先生认为:“宋时家塾刻本,其名姓亦甚繁多,今所最著如岳珂之相台家塾刻《九经三传》,廖莹中之世彩堂刻《五经》、韩柳集,皆至今为人传诵。”①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当,合诸本参订,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宝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复存。尝博求诸藏书之家,凡聚数帙,仅成全书。惟其久而无传也,爰仿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画、如注文、如音释、如句读,悉循其旧,且与明经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证以许慎《说文》、毛晃《韵略》,非敢有所增损于前。偏旁必辨,圈点必校,不使有毫厘讹错,视廖氏世彩堂本加详焉。旧有总例,存以为证。②岳珂:《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序》,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2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岳珂对此书的流传做了一个总结和评价,认为“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称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当,合诸本参订,为最精”,廖氏本刚刚刊刻之初,“天下宝之”,随着时间流逝,元板几不存在。岳珂访求诸多藏书之家,收集整理,重编此书,“偏旁必辨,圈点必校,不使有毫厘讹错”,编毕,“命良工刻梓家塾”。可以说此书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作品。
家塾本就是富贵人家的私塾教师依靠主人财力刊刻的书籍。“在封建社会里,官僚、地主及富商大贾,往往都设立家塾,聘师教授自己的后辈。这种被聘的教师虽未必有什么科第功名,但往往具有真才实学。他们在教书的过程中,常常就自己的志趣和所长,或自己著述,或校勘、整理、注释、阐明前人的著作,并依靠主人的财力,刊刻成书,故家塾本也属于私刻之一种。而且是私刻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版本。”③肖东发:《私家刻书的源流及特点》,《编辑之友》1991年第6期。
宋代福建家塾本一般都标有“刘元起家塾”“魏仲举家塾”“黄善夫家塾”“蔡琪家塾”“蔡子文东塾”“建溪三峰蔡梦弼东塾”“陈彦甫家塾”“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虞氏家塾”等字样,“在这些所谓私宅家塾中,有的也许不过是以家塾之名,行贩卖之实”。福建得天独厚的印刷条件,吸引制作木版的刻工们“直接来到原材料的产地,就地采购,现场加工……随着刻工的云集,其技术也流传开来,出版于是成为当地的固定产业,书商借此营利,家塾借此扬名”。④清水茂:《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97页。现仅举有代表性私刻详述之:
刘元起,字之问,庆元元年(1195年)刻《汉书注》一百卷、《后汉书注》一百二十卷,目录后均有“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据谢水顺、李珽先生考证,刘所刻《汉书注》与黄善夫所刻《史记》《后汉书注》,“很可能同出一家写刻工人之手,只不过是由刘、黄两家分别出资而已”,因为“黄、刘本同时人,又同居住在麻沙”。⑤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魏仲举,字怀忠,庆元六年(1200年)刊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李致忠先生认为:“至于所题‘五百家注’,两书注者哪部也没有五百家。之所以要题五百家,乃是广告性质的宣传,目的是为拓展市场,扩大营销,牟取利润。”⑥李致忠:《昌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1页。
黄善夫,字宗仁,庆元年间刊刻《史记》一百三十卷,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是《史记》三家注的最早刊本,“将三家说解分别列于《史记》正文之下,使读者阅读能兼采诸家之说,大大方便了学习,故传播甚广”。⑦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3—74页。黄善夫还刻有《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王状元就是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王十朋编纂,王十朋在《增刊校正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中道:
况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予旧得公诗八注、十注,而事之载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窥豹之叹。近于暇日搜诸家之释,裒而一之,刬繁剔冗,所存者几百人,庶几于公之诗有光。虽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繁言。盖以一人而肩乌获之任,则折筋绝体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虽未能舂容乎通衢,张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难到。此则百注之意也。若夫必待读遍天下书,然后答尽韩公策,则又望诸后人焉。①王十朋:《增刊校正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0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92—393页。
王十朋谈到了自己编纂《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目的,认为“虽未能舂容乎通衢,张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难到。此则百注之意也”。可以说,黄善夫所刻书籍是建本书籍的代表,为历代藏书家所推重。
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樵隐,乾道七年(1171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是现存最早的《史记》集解和索隐合刻本。宋人俞成,字元德,东阳人,他在开禧元年(1205年)八月《校正草堂诗笺跋》一文中说到了他对蔡梦弼的认识:
吾党蔡君傅卿,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了无留隐。至于少陵之诗,尤极精妙。其始考异,其次辨音,又其次讲明作诗之义,又其次引援用事之所从出。凡遇题目,究竟本原;逮夫章句,穷极理致。非特定其年谱,又且集其诗评,参之众说,断以己意,警悟后学多矣。②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9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从当时人俞成的文献记载来看,蔡梦弼还做学问,尝注韩、柳之文,特别是对于杜诗研究很有兴趣,造诣极深,专门撰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他在嘉泰四年正月《草堂诗笺序》中详细地记载了此书编撰过程:
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参校,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作诗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每于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离为五十卷,目曰《草堂诗笺》。凡校雠之例,题曰樊者,唐润州刺史樊冕《小集》本也;题曰晋者,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官书本也;曰欧者,欧阳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苏者,乃子瞻也;陈者,乃无己也;黄者,乃鲁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系王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鲍钦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梦符、薛苍舒、蔡天启、蔡致远、蔡伯世,皆为义说。其次如徐居仁、谢任伯、吕祖谦、高元之、暨天水赵子栎、赵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师古、师民瞻,亦为训解。复参以蜀石碑。诸儒之定本,各因其实,以条纪之。至于旧德硕儒,间有一二说者,亦两存之,以俟博识之抉择。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览,口诵心惟,不劳思索,而昭然义见,更无纤毫凝滞,如亲聆少陵之声謦欬,而熟睹其眉宇,岂不快哉!③蔡梦弼:《草堂诗笺序》,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9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34—235页。
文中所说“嘉兴鲁氏”是指鲁訔,字寄钦,号冷斋。蔡梦弼是以鲁訔十八卷本作为底本来编撰,最终编成五十卷本。“录诗及校勘所用之本,多达二十六七个传本,显然是要编成一个最完备的会笺本”,材料“虽未明言为谁所刻,但蔡梦弼有丰富的刻书经历,故此本完全有可能由他自己梓行”。①李致忠:《昌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0页。
蔡梦弼对杜氏家族族谱也做过精确的考证,这在他的《杜氏谱系》一文中有清楚的叙述:
谨按《唐书·杜甫传》及元稹《墓志》,晋当阳县侯预下十世而生依艺,以监察御史令于河南府之巩县。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京兆府奉天县令。闲生甫,左拾遗、尚书工部员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梦弼今以《杜氏家谱》考之,襄阳杜氏出自晋当阳县侯预,而佑盖其后也。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三子:诠,愉,羔。式方五子:恽,憓,悰,恂,慆。从郁二子:牧、颛。群从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与佑既同出于预,而家谱不载,何也?岂以其官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东塾蔡梦弼因览其谱系而为之书。②蔡梦弼:《杜氏谱系》,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9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蔡梦弼兼具出版家和学者两种身份,“盖是学问家兼刻书家,既能严肃对待学问,又能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因而在南宋初中期能独树一帜”。③李致忠:《昌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9页。
二、宋代福建私家出版的两大目的
私家刻书,是私人出资、主持刊刻书籍。对私家刻书的目的,肖东发先生在《私家刻书的源流及特点》一文当中给予了非常明确的说明:
私家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更重要的在于名。这一点是私刻与坊刻的根本区别,尽管某些私刻也有售书活动,如毛晋等,但这不是私家刻书的主流。因为私刻主人多为官僚、地主、富绅,他们不需要依赖刻书来赚钱,刻书不过是为了提高名誉、声望、地位的手段。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来分析,名门望族,士大夫阶层历来瞧不起营营逐利之辈,是不屑于与商贾合流的,这也是决定私家刻书非商业化的重要因素。从对古代著名私人刻书家的刻书内容及刻书活动的分析中,也不难看出私家为名而刻的特点十分鲜明。他们以刻书为荣,有的刊刻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刊刻乡土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校刻行世,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刻书,抬高自身,也利名人荐举。④肖东发:《私家刻书的源流及特点》,《编辑之友》1991年第6期。
肖东发对私刻和坊刻目的做了对比,认为最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以赚钱为主。坊刻纯粹是为了卖书赚钱,而私刻主一般不是为了钱,“更重要的在于名”。
宋代福建私家刻书除了为名声外,有时还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授习需要。比如,叶采刊刻《近思录集解》就是如此。叶采,字仲圭,号平岩,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曾师从蔡渊、陈淳、李方子等人。他在淳祐八年(1248年)五月《近思录集解自序》一文中道:
时则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四先生之书,条分类别,凡十四卷,名曰《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采年在志学,受读是书,字求其训,句探其旨,研思积久,因成《集解》。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参与升堂纪闻及诸儒辩论,择其精纯,刊除繁复,以次编入。有阙略者,乃出臆说,朝删暮辑,逾三十年,义稍明备,以授家庭训习。⑤叶采:《近思录集解自序》,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叶采在这篇自序中,记载《近思录集解》这本书刊刻,主要是为了家庭训练和学习。叶采花三十余年时间研究所获心得,都在《集解》这本当中。这里也有叶采个人阅读《近思录》的经验和感受。可以说,《集解》这本书,也是作者个人的阅读史、心态史、精神成长史。
还有的家刻文集是为了让自己家族的书籍流传后世,传播文化。比如郑嘉正刊刻郑侠《西塘集》就是出于这个目的。郑嘉正,“南宋初期福建福清人,知建昌军”。①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郑侠孙子郑嘉正编纂与刊刻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此集传之后人:
隆兴甲申,先生之孙出守旴江,挺承泛泮宫,一日辱宠示家集,挺伏读至《望阙台记》,乃知先生于流离困踬之余,而忧国爱君之心有加无已,其视遗佚则怨、厄穷则悯者,贤否何如也?既而贰车龚侯览之,谓先生之文,浑全博雅,片言单辞悉存教诫,乃白使君,请镂版以垂不朽。公从之,属挺参订舛讹,仍输赀鸠工。越三月告成,命以所刊版置之学。俾诸生获观前辈之言,知典刑之大略,而有所矜式,岂曰小补哉!②廖挺:《西塘集题识》,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2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6—47页。
从廖挺文中看出,郑侠之孙守旴江时,刚好廖挺在旴江泮宫任职。廖挺从郑侠孙子那里读到了郑侠的文章,并为他的举动和精神所感染,建议郑侠之孙将其家集刊刻以垂不朽,使“诸生获观前辈之言,知典刑之大略”。可见,此集刊刻,就是为了让书籍历代传播下去,使得后之学者读其文,知其人,既传播了文化,又可以缅怀先人。《西塘集》的刊刻花了三个月时间,是在旴江学宫刊成,书版也放置在学宫。
三、结 语
宋代福建的私家出版活动,不同于其他地方,刻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首先,福建家刻尽管某些时候冠以“家塾”字样,实际上,本身已经带有坊刻的性质。家刻与坊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彼此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就是说,宋代福建私家出版既具有非商业性质,又具有商业性特点。“私刻是一种不纯粹的坊刻,也就是尚未彻底商业化的营利性出版。”③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其次,宋代福建家塾出版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名声,还有家庭授习、传之后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