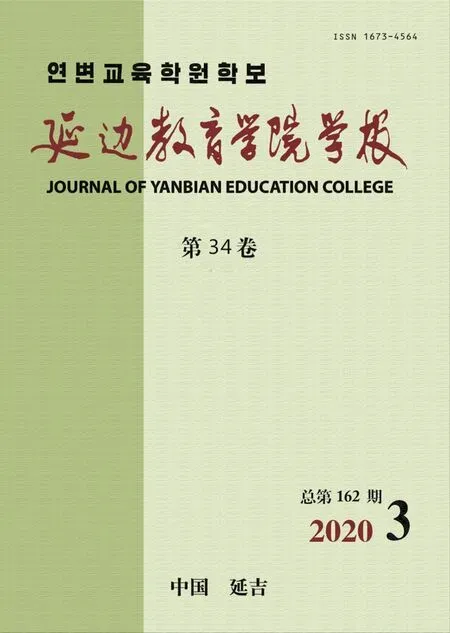走下神坛的母亲——金仁顺《桃花》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
孙淑芹 侯 悦
走下神坛的母亲——金仁顺《桃花》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
孙淑芹侯悦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金仁顺的《桃花》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性书写,消解了母亲的神性,还原其作为女人的一面。作品多角度地折射出了颠覆性书写背后的文化哲思,即对男权中心文化的解构,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审,以及对当代母女关系的反思。
金仁顺;桃花;母亲形象;父权文化;女性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母亲向来都是被赞颂的形象。由父权体制书写出来的“母亲神话”,竭力宣扬母亲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宝贵品质,消解和剥夺了母亲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和存在价值。在男权话语的遮蔽下,母亲成为被利用和改写的对象,沦落为失语的“他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开启了解构“母亲神话”的潮流。金仁顺的《桃花》发表于2005年,以一种颠覆性的书写,将母亲身上人性瑕疵与个体欲求尽情展露,使母亲由承载伦理道德的抽象符码,回归到真实的人。通过对“母亲神话”的解构,反映出金仁顺自身对男权中心文化的解构,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审,以及对当代母女关系的反思。
一、母亲与妻子:女性身份的现实叛逃
在《桃花》中,金仁顺塑造的母亲形象,打破了人们千百年来虔诚膜拜的“母亲神话”,将母亲拉下神坛,剥掉母亲华丽的外衣,让我们看到母亲作为人的一面。小说中的母亲季莲心,在对女儿夏蕙的养育过程中,冷漠又疏离,大多数情况下处于缺席的状态。她将丈夫驱逐出卧室,继而拒绝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还声称女儿并非父母爱情的结晶,而是丈夫运用强力种下的种子,在女儿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原罪意识”。
小说的开篇便展现了母亲季莲心对于女儿夏蕙的嫌恶。在女儿身上,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情,她都不满意。这也直接造成了母女之间的隔阂。在夏蕙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总是满腹牢骚、无理取闹。而父亲总是隐忍包容,任由母亲的无事生非。在母亲整日的抱怨声中,夏蕙自觉与父亲站到了同一阵营,以装聋作哑对抗母亲的无理取闹。不堪女儿的冷落,加之外界的诱惑增多,季莲心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此,作为妻子的贞洁和忠诚被委婉地消解了。丈夫意外离世后,季莲心将曾经的三室一厅卖掉,在一处黄金地段购置了一套一室一厅,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间独具女性气质的单身公寓。这无疑为她往后的日常社交提供了充分的便利。然而,因为住校,本就很少回家的夏蕙,在母亲换房的过程中,彻底失去了由父亲维系的家。这位母亲在追求个人生活的过程中,疏忽了女儿正常的亲情需求,为原本就裂痕斑驳母女关系,平添了万丈沟壑。
传统的母亲形象总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即使面对无爱的婚姻,她们也会选择妥协隐忍,把孩子作为维持婚姻的精神支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的学习与成长之中。她们还会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有爱的家庭氛围,努力改善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求得一个贤妻良母的美名。如果不幸遭遇丈夫意外离世的变故,她们会谨慎维护自己作为妻子的身份,遮蔽自己的个体欲望,从一而终。这是传统母亲形象的神圣之处,亦是她们身上可悲的地方。
尽管季莲心的婚姻肇始于屈服强力,但是,她并不甘心就此妥协,如同中国传统道德规训下的母亲,沦为父权文化的“他者”。在妥协与反叛的抉择面前,季莲心听从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选择,挣脱了中国传统道德对于母亲的压抑和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作为人的情感诉求和个体欲望。在小说中,失去丈夫的季莲心,用实际行动来反抗传统道德施加在母亲身上的枷锁,她拒绝沦为丈夫的遗产、女儿的保姆和管家,她要成为她自己。
金仁顺笔下的季莲心是一位为了追求自我欲望的实现,而主动放弃妻性与母性的母亲,剥离了传统母亲身上的神性光环,找回了真实而又复杂的人性,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画廊中的母亲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反叛与同谋:女性身份的文化隐喻
在《桃花》这部小说中,隐含着“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小说中的母亲季莲心是由女儿夏蕙的视角呈现给读者,女儿夏蕙亦是由母亲季莲心的视角呈现给读者,两者均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打量着对方的存在。父权话语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夏蕙的意识中,因此,她始终以父权文化的价值标准打量着母亲。季莲心与父权话语规约下的母亲形象格格不入,使得夏蕙对季莲心充满敌意。季莲心显然是一位女性意识觉醒的母亲,这就导致她的许多行为在父权文化主宰的价值观中显得离经叛道。她也清醒地觉察到,女儿并不是自己的同盟,而是父权文化的同谋者。从本质上来讲,季莲心与夏蕙之间的裂痕,来源于父权话语对女性的压迫与规训。在小说中,表面上是母女关系的紧张对峙,实际上却是觉醒的女性与父权文化的抗争。
1.母亲:父权文化的反叛者
季莲心与丈夫的婚姻并非源自爱情,而是源自丈夫的强力在她体内种下了种子。婚后,季莲心将丈夫赶出卧室,拒绝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实际上,她在报复丈夫当初的强力,也即对父权文化的抗争。在她的心里,女儿不是爱的结晶而是孽债。因此,她的疏于母职成为一种对抗父权体制的延伸。后来,季莲心从家庭中出走,对作为妻子的忠诚与贞洁提出挑战。季莲心对传统妇德的谮越成为一种对无爱的婚姻、屈辱的历史的现实反抗。在这一过程中,她丢失了传统道德赋予母亲的光环,不再是女儿的精神庇护所。而女儿夏蕙用父权中心主义的眼光打量着母亲,自觉站在由父权统治的文化阵营,与母亲对峙。母慈女孝的神话,在此消解。丈夫意外离世后,季莲心好似一位恢复单身的少女,立即投入到全新的生活之中,她恣意挥洒着自己的女性魅力,掌握着生命的主动权,丝毫不像传统母亲那般守身如玉、从一而终。夏蕙目睹了母亲的欲望,无法接受母亲对传统妇德的僭越,遂以道德审判者的目光审视着失德的母亲。但是,季莲心看似放荡的行为,实际是女性对自身情感欲望的主体性表达,是对母性神话束缚、压制自我的现实性反叛。金仁顺把母亲还原为一个剥离父权谎言的世俗女人,她不再是父权文化规训下毫无情欲的道德符码,而是具有主体人格意识的人。金仁顺通过塑造季莲心这样一位另类的母亲形象,对父权文化中有意遮蔽母亲生命原欲的道德标准进行了大胆地否定,并且积极肯定了女性欲望存在的合理性,揭穿了母亲无欲的谎言。金仁顺把女性对主体欲望的追求与张扬,作为打破禁忌的突破口,表达了女性自我主体的觉醒。
2.女儿:父权文化的同谋者
在小说中,夏蕙始终用一种父权文化对母亲角色的价值认同,打量着自己的母亲。当她发现母亲抛弃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毫不掩饰自我的个体欲望,于是在心底与母亲彻底决裂。父亲老夏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父权文化的缺席,女儿夏蕙顺理成章地成为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和共谋者。她痛恨季莲心母职的缺失、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和对父亲的不忠,因而恼羞成怒,甚至产生了弑母的行为。同样作为女性的女儿,从未探寻过母亲离经叛道的真正原因。季莲心说:“难怪女儿跟自己这么隔阂,她根本就是个阴谋的产物,是老夏用强力种下的一粒种子。”在此,作家埋下了巧妙的文化隐喻。老夏作为男权中心主义的化身,运用强力征服和占有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个体。女儿夏蕙在这场较量中,是父亲血脉的延伸,承载着浓重的父权意识,成为了父权文化的同谋者,也是父权文化对女性外在压迫的内化。在小说的结尾处,夏蕙躲在屏风后,目睹了母亲与自己男友的偷情,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不满,幻化成一头猛兽,冲出了理智的牢笼,她将一把冰冷的匕首刺向母亲。“夏蕙想,季莲心终于发现她跟老夏在一起了。从夏蕙的五官、身材、表情里面,老夏活回来了。一反往常的窝囊相儿,变得锋利、尖锐了,就像二十八年前的某个夜晚,这天夜里,老夏再一次变成侵略者,不过,这次不是身体,而是一把刀。”夏蕙弑母的背后,是父权社会对丧失了社会属性的女性的无情剥离,父权社会借女儿之手惩罚了放弃母性、妻性的母亲。在这部小说中,父权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得力的帮凶都是由女性来充当的,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和悲剧意味。
三、解构与自审:颠覆性书写的文化哲思
金仁顺抛弃了对母亲歌功颂德的写作传统,直面母亲的生命本真,是对父权话语霸权的反抗,以此为依托,实现对男权中心文化的解构。但是,作家对于男权中心文化的解构并不是意味着向男性复仇,以此建立女性话语霸权,而是着力于消除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生命本体的压迫,并在这一过程中,力图激发女性的自审意识,促进女性不断完善自我,使女性可以与男性共建两性和谐的文化空间。
1.对男权中心文化的解构
在由男权话语主导下的传统写作中,母亲是依附于父权文化的“他者”,是父权文化塑造出来的道德符码。因此,女性形象进入了两个极端,她们不是天使就是妖妇。天使和妖妇都是以父权文化的价值标准对女性做出的评价。在这里,女性沦为被父权文化任意涂抹和篡改的失语者,属于女性独有的情感体验被父权文化所遮蔽,女性个体的情感诉求、生命原欲受到男权话语的残酷镇压。由父权文化一手打造的母亲神话,并不是崇拜母亲本身,而是崇拜母亲背后的父权统治。金仁顺对母亲原始欲望的披露,解构了男权中心文化的话语霸权,并从女性独特的立场出发,将母亲置于人的位置,揭露母亲被遮蔽、被隐瞒的原始欲望和情感诉求,超越性地展示了女性个体的生存境遇,为母亲形象增添了崭新的内涵。在小说中,作家通过释放母亲的原始欲望,展现了母亲对于母性与妻性的叛逃,张扬了母亲在对抗父权文化中觉醒的一面,也揭露了母亲在实现自我时自私、冷漠的一面。
2.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审
金仁顺的《桃花》是一部审视女性灵魂的力作,作家以一种独特的女性体验,揭示了女性灵魂深处的隐秘,剖析了女性自身所存在的顽疾与弱点。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作为父权文化同谋者的夏蕙,还是作为父权文化反叛者的季莲心,她们的女性意识都存在着瑕疵。
小说中的女儿,作为父权文化的同谋,一手促成了母亲的生命悲剧。季莲心的婚姻肇始于丈夫的强力,这是父权文化在她身上施加的第一次迫害。女儿将那把冰冷的匕首刺向她,这是父权文化在她身上施加的第二次迫害。在与父权文化的对抗中,这位母亲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她的第一次悲剧是由男性社会的压迫所致,第二次悲剧则来自同样作为女性的女儿。在这里,女儿化身为父权统治的帮凶与同谋,代替父权体制惩罚离经叛道的女性。在母女关系的紧张对峙中,女儿成为父权秩序的捍卫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话语的压迫下,女性寻求自我的艰难困境,横在她们面前的巨大阻力不只是来自男性,还有她们自己。
作为父权文化的反叛者,季莲心的女性意识觉醒得并不彻底。季莲心对于美丽的追求,处处迎合男性对于美的认定标准,丢失了作为女性的独立判断,沦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季莲心依靠自己的美丽,与女儿身边的男人暧昧不清。母女之间争夺男性的爱慕,彼此之间产生的忌恨与敌意,正是父权文化的价值标准在女性主体观念中的内化演变为女性群体间的相互迫害。并且,从破碎的母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季莲心在对抗父权、张扬自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走向了自私的极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正是通过颠覆性书写,暴露了母亲与女儿灵魂深处各自的缺憾,唤醒女性读者的性别觉悟,试图启发广大女性读者自觉探索一条重新构建自我之路。
3.对当代母女关系的反思
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在剥离父权话语造成的紧张对峙之后,暴露在读者面前的是冷漠与疏离。在老夏死后,季莲心和夏蕙心照不宣地逃离彼此。每周五的会面,在女儿看来就像遵守某项法律,在母亲眼里倒具有了一种表演的性质,母女之间的那种自然亲情却无迹可寻。金仁顺将走出家庭的母亲与缺失母爱的女儿所遇到的真实困境,反应在在小说创作中,使读者可以关注到女性在开辟自我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守与牵绊。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物质欲望开始萌芽,并且影响到了当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加之,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女性的思想得到解放,女性个体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骤变。大多数女性选择挣脱家庭的藩篱,走向社会,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与权利,因而传统的家庭伦理结构受到冲击。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伴随着母性的弱化与缺席。母亲通过实现自我价值,在与男性的对抗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给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但是,女儿在母爱的缺席中成长,其精神的缺失,却永远都无法弥补。
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牺牲品,就是同样作为女性的女儿。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人们满足了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最需要的就是爱与归属感。每一个人,从婴儿时期便渴望来自家庭的关爱。对于女孩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女儿的精神导师,也是女儿的原点与皈依。母爱的缺席使女儿寂寞地度过青春的岁月。经年累月,无法避免地造成了母女关系的淡漠与疏离。金仁顺在此通过揭出苦病,希望引起广大女性读者的注意,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找到平衡家庭的方法,不要让孩子的成长沦为成功的代价。在《桃花》这部小说中,金仁顺就母女关系的亲情淡漠,生发出对新时代女性生存现状的严肃思考,反映了金仁顺对女性生存困境及其命运流变的关怀。
在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颠覆性书写的过程中,金仁顺肯定了母亲作为人的女性欲望和情感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挣脱父权文化的伦理枷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女性重新构建自我的必经之路。但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人类延续自我生命的过程中,母爱是一种不能缺席的情感,它亦是人性之美的表现。女性作家在解构“母亲神话”的过程中,反对的应该是父权文化强加在母亲身上的伦理枷锁,而不是美好的母性本身。当女性作家将由父权文化制造的圣母拉下神坛之后,要如何去建构既富有人文母性,又兼具自然母性的理想母亲,是作家留给读者的深邃命题。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3]王学谦,刘森.“母亲神话”的解构——论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书写[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67-71.
[4]寿静心.母性神话的解构与重建——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5):59-64.
[5]王虹艳.解构“母亲神话”与重建“母性关怀”——切入女性文本的一种视角[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3-37.
2020—03—15
孙淑芹(1965—),女,汉族,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女性文学。侯悦(1994—),女,汉族,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
I247
A
1673-4564(2020)03-0048-04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