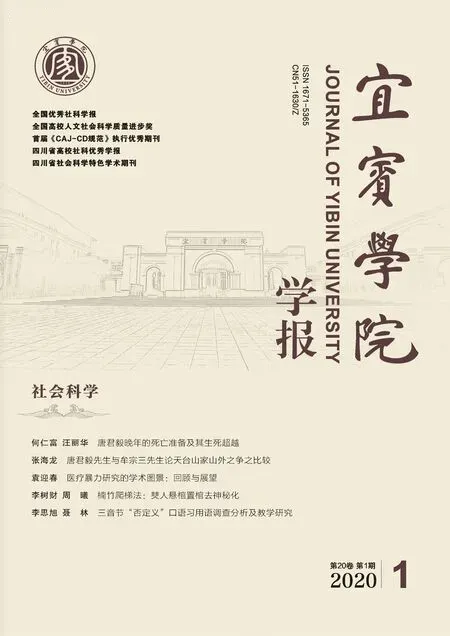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论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之比较
张海龙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山家山外之争是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一次重要论争,论争虽始于《金光明经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但实际上双方论争的焦点与吃紧处主要是:天台宗的观行实践是以观妄心还是以观真心为入手,山家派主张观妄心,山外派主张观真心。山家山外之争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唐君毅先生(1909-1978)和牟宗三先生(1909-1995)都曾有专文探讨这一佛教公案①,但二人的诠解进路和结论却大相径庭,在现代佛教哲学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本文将围绕妄心观与真心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具与性起、别理随缘及缘理断九等问题以对唐、牟二先生关于山家山外之争的不同诠解予以比较和再诠解,以期为这一问题在现代哲学语境中重新诠解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视角和进路。
一、性起与性具
性起,即称性而起,是华严宗思想的基石。“性起”一词语出晋译《华严经》“宝玉如来性起品”。其视佛性为一纯善清净觉体。性具,又称理具、体具,其基本内涵就是性具善恶,即本觉之性悉具一切善恶诸法,是天台宗的重要思想,性具思想最早见于隋代智者大师的《观音玄义》,其后湛然、知礼均对其有所发挥,山家派更是依性具来区分自宗和他宗。
唐君毅先生认为,华严宗主张“性起”,天台宗说“性具”,从根源上来讲,是由其各自所宗的《华严经》与《法华经》的性质不同所致。根据华严宗和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前者是佛证道后最开始宣说其自证境界,如日照高山,是直接地说;而后者则是导三乘会归一乘的最后说教,是间接地说。虽然“性起”与“性具”都说“性”,但其“性”之意义却不同。华严宗直指法界性起心性,此心性是一存在的实体,所以,此性是体性之性,换句话说,它是性体,有其体,必有其用,能依体起用。天台宗性具之“性”是从《法华经》所说的“十如是”中的“如是性”中转出,即最早是对十法界的种种范畴法相而说的,它实际上是表示“本性”,所以,其最基本的意义非体性之性,即非性体。至于《观音玄义》《大乘止观法门论》中的染净善恶之性也非一种实体之性,而是就佛与众生皆有善恶二法门而终不改变上说的,他说:“此种之法门,有如房屋之门,中虚而无实,而可供人出入……众生在染恶门中,佛化度众生亦在此门中。此门不改,则众生与佛同此一染恶之性。”[1]176所以,此“性”实际是一种虚而无实的法门轨则不改变自身的一种特性。唐先生进而指出:性具之“性”远离一切实体实用,它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之“性”,同于一般所说的“法性之性”,而非性体,故它不能起用,但是它本身内在的含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佛为了方便度化众生,而不断其所了知的恶法门,迹同众生,随机度化。
对于华严宗性起之“性”与天台宗性具之“性”之不同,牟宗三先生亦有深刻的分析。牟先生认为,所谓性起之“性”,是指“清净真如心”,也可称为“法性心”或“法界心”。此“清净真如心”随缘起现一切法,称为性起。此缘可以是净缘,也可以是染缘,因此,随缘而起之法,或净或染,而“清净真如心”自身之“自性清净”不变。需要指出的是真如心起现万法,是一种间接的起现。牟先生说:“染净法之起现,其直接生因只是执念,但执念亦凭依真心而起……实则真心并不起。真心只是执念起现之凭依因,而非其生因。因凭依真心而起,随间接地说真心随染净缘起染净法。”[2]350所谓性具之“性”有虚实两层含义:“虚说是本质义、原则义……实说即指法性说。”[2]357所以,在牟先生看来,性具,即“即具”,也就是说,佛性具菩萨界以下九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之恶法及佛界之善法,总具十界三千之善恶诸法,从这个意义来看,佛性就是法性,佛与众生之性平等无二,此自然不同于华严宗,华严宗所说的佛性远高于其他九界众生之性。
基于华严与天台对“性”的理解侧重不同,在宗教旨趣上,华严宗对现实世界乃至九界众生更多地显示的是一种超越色彩。而天台宗念兹在兹是佛与众生同居染恶、相即不离,从而显示出更为浓郁的苦难意识和现实关照性②。这种义理性格和宗教旨趣的差异,落实到实际的修行实践上就是真心观与妄心观之异。
二、妄心观抑或真心观
山家派与山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观心,而是观妄心还是观真心?山外派主张“真心观”,而以知礼为代表的山家派主张观妄心,真心不能成观。对此,唐先生指出:妄心最宜当下成观,但真心也不是不能成观,他说:“盖能本三谛圆融之理以观妄心,而见此妄心之即假即空即中者,即是真心或妄心之呈现,即可转而为所观,如宗密所喜言之珠光照他,还能自照是也。纵谓此中无能所之相对,真心不可称为所观,然可自悟……而山外之唯以真心为所观,此观之义可同于自悟。”[1]175在唐先生看来,真心亦可成观,而且同妄心观一样,真心观也可以在智者大师和湛然之言找到根据,他说:“智顗、湛然皆言观一念无明妄心即山家观妄心之所据,然能此无明心而破之之心,则亦可说为法性真心,亦可为可观者,是山外观真心之所据。”[3]851不但“真心亦可观”,而且妄心观与真心观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两者可以相即相涵,观妄、观真皆由当前的一念心而起,真心、妄心都可以作为观心的入手处。唐先生认为,山家派的知礼之所以重视以妄心起观,主要是因为:“吾人平日妄心正是妄心,若须别观真心则工夫不切。今只拣此现前之妄心为所观,则工夫自切。”[3]855知礼所说的观妄心是依三谛而观其假空即假即中,此中人省知其即空即假即中之心,又是一真心的显现。所以,若在此真心显现处再起观,则妄心观可以归于真心观;若在此真心显现处起贪染执著,那么,真心又复归于妄心。实际上,正如唐先生所指出的:“能观妄心而知其妄者,应即一义上之真心;而真心之所观,亦原可是妄心。则真妄相即相涵。”[3]856因此,在唐先生看来,以真心观来非议妄心观,或者以妄心观来责难真心观,实则均属戏论。观真心还是观妄心不是一纯哲学问题,实际上应该根据人的气质、心态、所处的情境以及其修行时的实际需要而定,他说:“大率人之气质笃实,而能面对其妄染而修行者,必多契于为天台正宗之山家,至其气质高明,而能直契其一念清净而修者,必多契于山外及山外所摄之华严宗人言一空寂灵知之心之旨”[3]857。
唐先生并没有囿于性起与性具义理性格上的差异而说观妄心还是观真心,而是最终将其归于实践上,具体说是实践者身上。其消弭、会通山家山外的分歧的做法,我们可以有仁智之见,但这种即非山家、也非山外的诠释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唐先生平视宋代天台宗受华严宗影响的事实,他认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山家山外之争后的天台宗义理的发展实际代表了中国佛学思想一新的发展方向。[3]858-861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唐先生把山外派的“真心观”之“观”释为自悟,准确地说是禅宗(南禅)所说的顿悟,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宋代天台宗与禅宗的关系,其中自然也蕴含着唐先生会通天台宗与禅宗的苦心,就哲学上来讲,不失为一种慧见卓识,将“观”释为“自悟”自有一种“洒脱”“明快”在,但就实际的观行工夫上来讲,则容易滑入轻浮和狂放之域,从而使行人放弃实实在在的修行,这与智者大师实际确立的平实精进的修行体系似乎有些相违,也没有体察到以知礼为代表的山家派 “要以妄心观来保证天台宗的精进修行”[4]166,对治和纠正禅宗给当时佛教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良苦用心③。
与唐先生超越地反省④妄心观与真心观诸问题,重在会通山家与山外、华严及禅宗等思想旨趣不同,牟宗三先生依天台真实圆教的立场,严辨天台与华严之别,山外与山家之异。他说:“山外之所以为山外,即在以华严思路讲天台,视‘介尔一念’为真心。此是根本错谬处。山外诸家自居为天台,然不解天台之基本思路,此其于天台之基本文献为读通也。根本观念已差,而于一家文献又不精熟,故于辩论中自有许多错谬处,未能如知礼丝丝入扣,左右逢源也。其为‘堕负’自甚然。”[5]888
如所周知,山外及后山外吸收华严宗思想以助天台宗思想的弘传,“盖因天台久经衰微,章疏不备。虽由高丽以还中国,而久生难熟,故读者一时不能明也。因此,当时天台宗方面,其钻研弘扬自家教义者,各不自觉袭取华严之思路,尤其圭峰宗密之思路,以释天台。”[5]870除此之外,华严宗的创立晚于天台宗,在判教理论等方面借鉴和吸收了天台宗、唯识宗的思想,似乎更加完备!所以,用华严宗的思想来解释天台宗,可视为天台宗思想的一大发展。实则不然,牟先生对魏晋至隋唐佛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指出:唯识宗、华严宗都属于分解的思路,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经验分解(心理分解),后者是超越的分解,而天台既不走经验分解之路,也不走超越分解之路,而是“即具之诡谲的思路,此显然是消化一切分解,依以独特之心灵,而圆成者。”[5]892牟先生认为,分解的思路到华严宗为止,若要再向前发展,只有进入到“诡谲”的思路,因此,若按佛教思想发展的路向来看应该是唯识—华严—天台,这显然和天台宗创宗早于严华宗的事实不符。对此,牟先生解释道:“惟此一大系统(天台圆教—引注)把握实属不易,非若华严宗之易入。若贯通观之,则知此一圆教系统实具一特别之劲道。具有深绝之智慧。其消化经教,立言抒义,实为高一层者,为其他宗派所不及。勿以华严宗为后起,便视之为最高之综和;亦勿以为天台宗为先出,便视之为尚不圆备也。天台固先出,然亦系最后者。”[5]891在牟先生那里,只有天台圆教才是真正的圆教,这是由于天台宗所讲的圆,它是一种存有论的“即具”之圆,即“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一切法不可得,而又不舍不坏一法,存有论地即具一切法,法法平等[5]895。从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看是一种诡谲的思路,“它不与任何权教为对立,而是开决了亦即消化了一切权教而说以说者者,无立以立者。”[6]214而非分解的思路,因为:“凡是分解地有所说,有所立者,皆可起诤……凡分解地有所说有所立者皆是方便权说,权假施设。”[5]893依此来看,唯识宗、华严宗走的都是分解的路子,相对于天台宗皆是方便权说,皆可会归到天台宗的圆成实教。
由此,我们也不难推断:在妄心观和真心观的问题上,牟先生应该是不会同意唐先生为山外派所作的辩护,而是严守知礼等山家派的妄心观立场了。
三、别理随缘及缘理断九
“别理随缘”的思想是知礼在《十不二门指要钞》中明确提出⑤,并在《别理随缘二十问》中予以集中阐述,知礼认为,随缘义通于圆、别两教,不仅圆教有随缘义,别教也有随缘义。圆、别二教随缘义的差别,在于体用是否相即,只有体用不二,全用即体,才是相即。若单说真如随缘,不谈理具,不是相即。依此来看,华严宗的随缘义只相当于天台宗的别教,其成佛方式是“缘理断九”,即缘依清净真如之理而隔断九法界之无明,独观念佛界之真理而成佛。对于“别理亦可随缘”的说法,唐先生是认同的,但若依此把华严判为别教,这是唐先生所不能同意的。他认为别理与圆理有相反的一面,但也有相成的一面,他说:“(山外—引注)谓佛性断九界恶,而只证一真理,此理亦能随缘者,乃是意谓此断九界恶之佛,亦能以其悲智,随缘而下彻于九界之众生,则此佛实未尝断九界,而必能依其悲智,以通达九界恶,方便为恶事,现恶相,亦有通达恶而现此恶相之性。则其断九界恶之性,即是断而不断。若非‘断而不断’,则此佛之悲智不足,其善非全善故。则此全善之佛之所以成佛之性之理,亦可同时为一不断九之圆理,而非一别理。则山外之义,亦涵山家之义。”[3]855别中有圆,圆中亦可摄别,即山家亦可涵山外之义。山家派所主张的佛不断九界恶的圆理,恰恰是为了成就佛的全善[3]855。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唐先生对于山家派对山外派及华严宗的说法,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孰是孰非上,而是就华严宗教义之本身作超越的反省,与异中更见其同,所以在圆别问题上,他同意华严宗的立场,即华严属别教一乘圆教,天台为同教一乘圆教。
但是,在牟先生看来,圆教无二、亦无三,圆教只有一个,即天台圆教。他亦同意“别理随缘”之说,并把华严宗“缘理断九”的成佛方式称为“宝塔式的层层升进”[2]351。依据牟先生的意思,别理随缘义是智者、湛然哲学思想中的当有之意,知礼将其明确地揭示了出来。但在圆别问题上知礼的论述尚有进一步清晰化的空间。他认为,别教有两种形态:始别教和终别教,始别教如唯识宗,终别教如华严宗。
山外派及华严宗认为,别理不能随缘,若说“随缘”便是天台圆教,牟先生认为此之大谬。他说:“山外诸家视别理不随缘非必定非。盖指唯识宗而言也,唯不知别理亦有随缘者(华严宗、《大乘起信论》—引注),而视随缘者为圆教则误。”[5]876所以,“随缘”义并不能区别圆、别,因为“圆不圆根本是即不即底问题,即则为圆,不即为别;性具为圆,性起为别。”[2]361牟先生进而分析指出:华严宗的成佛方式之所以为“缘理断九”,是由 “性起”系统自身为一分解的体系所限,即“(此真心—引注)随缘到处可有法起现,随不到处则无法起现,是则于一切法之存在无圆足保证也。”[6]210由于自身的限制,所以华严宗在成佛之工夫上似乎多了一层转化、提升(九界众生)之过程,不如天台宗即九法界之每一界之当下成佛直接、通彻。牟先生说:“华严偏指真心为准,必于随缘方能说明一切法也,而于还灭显真心,则必破九(九法界之妄心—引注)而后显,即有前起之性生于后返之灭之两来往,故不圆也。”[2]357所以,在山家派及牟先生那里,判断圆别的标准并非山外派所说的“随缘”与否,而是“性具”与“性起”。
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并不认同以“性具”与“性起”作为判断圆别的标准和依据,他认为,根据智者大师之意,判定圆别的标准在于修道功夫与修道之体是否相即相融,而非“性具”和“性起”,他说:“只要此所依之体能直显于修道工夫,与此工夫真正相即相融不二,即皆是圆教,故《法华》《华严》《楞严》《圆觉》《涅槃》等经,《维摩诘经》之一部,以至如智旭所说之《大乘起信论》,同是圆教经典。在宋代天台宗之山家山外之争中,则山家坚持性具为圆教之标准。实则智顗初于此无明说。”[7]305直至他在临终前不久写给张曼涛的信中,仍然措意于此,他推测牟先生之所以贬华严为别教,可能是牟先生对华严的义界问题不清所致[8]197。客观来说,唐先生此言有失周全,判华严为别教,并非牟先生所创,而是山家派的看法。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天台山家山外之争的诠解上,唐、牟二人大异小同。虽然二先生采取的都是一种哲学的进路,但唐先生援引黑格尔“对立统一的思想”⑥,用“超越的反省法”的哲学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以哲学范畴研究的形式,以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的思想为前见,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以求会通,特别是给予山外派以同情的理解。而牟先生依天台圆教的立场,援引康德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思想对山家派的思想作哲学式的论述,使其更加的清晰、精洽,新意迭出。他严守圆、别之界限,对山外派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批评。另外,若隐去唐、牟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不论,其关于山家山外之争的论述,又何尝不是公元十世纪那场争论于千年之后在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投影呢?
注 释:
①牟先生在《佛性与般若》下册第二分“天台宗之故事”专辟第四章“宗之分山家与山外”、第五章“辨后山外之净觉”专论山家山外之争,对双方论争过程中的观妄心与观真心、别理随缘、理毒性恶、蛣蜣究竟(旨趣同于无情有性)、生身即尊特等问题予以哲学式的疏解与论述,新意迭出。除专文之外。牟先生在《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亦有论及。唐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第三编第十五章“湛然以后之天台宗之佛道与他宗交涉”中之五、六及附录部分直接来论及山家山外之争,另外他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九章“华严之性起与天台性具及其相关联问题”、《谈中国佛学中之判教问题》的讲词 及给张曼涛先生的最后两封信中直接或间接论及山家山外之争的问题。
②按:但凡卓越的宗教家对现实世界的苦难都有痛彻的体验,现实的苦难与遭遇与其宗教哲学理论及实践一般来说是相应的。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顗(538-598),生逢乱世,经历坎坷、对人世间之苦难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佛教处境艰难、佛法思想激荡的形势下,自觉担负起统一南北佛学的重任,对中国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理论立足于日常生活、重视止观,透显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平实性。与智顗相比,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法藏(643-712)与武则天的渊源颇深,得到了武则天的极力护持,其弘法环境远较智顗为优,所以,其佛教哲学理论气象恢弘,透显出理想的超越性,颇有盛唐气象。另外,从主要施教对象来看,智顗主要的施教对象主要是社会中下层。而法藏的施教对象主要是皇室及士大夫阶层。
③此处笔者并无有意贬斥禅宗之意,就佛教思想发展而言,禅宗固然有如唐先生所说的它较天台、华严、唯识而言自有一“向上一着义”,(具体请参阅唐君毅《原性篇》第十章“禅宗与佛学他宗及惠能坛经之自性义与工夫”)但同时它确实也给当时的佛教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关于此意,具体请参阅: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上),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61页。
④超越的反省法是唐先生重要的哲学方法,唐先生说: “所谓超越的反省法,即对于我们之所言说,所有之认识、所知之存在、所知之价值,皆不加以执著,而超越之; 以翻至其后面、上面、前面、或下面,看其所必可有之最相切近之另一方面之言说、认知、存在、或价值之一种反省。”唐君毅《哲学概论》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26页。唐先生认为,超越的反省法是一切哲学方法的核心,一切哲学方法中都预设超越的反省,他在研究包括佛教哲学问题在内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时经常使用这一方法,具体亦可参阅张海龙《唐君毅的哲学史方法论》,载于《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⑤随缘义本出自于华严三祖法藏的《大乘起信论疏》。湛然在其著述中多次引用,在《止观大意》:“随缘不变故为性,不变随缘故为心。”又《金刚錍》:“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但湛然并未明确提出别理随缘的说法。
⑥唐先生曾借用黑格尔的哲学名词(思想)来论及自己对佛性问题的看法。他说:“众生心之无明法性之矛盾的统一、其展开而对立,及其矛盾之超化而唯显法性”之“全部历程中之道”,即众生之佛性,则天台之论佛性,乃原其“始”之论;华严之论佛性,则要其“终”之论;而唯识宗之善恶染净法对立之论,则居间之论也。唐君毅《原道篇》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861页。黑格尔的矛盾对立统一之思想对唐君毅疏解佛教哲学思想的有很大的影响,如他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之发展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此过程整体上升、发展,所以其自然就得出了山家山外之争对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