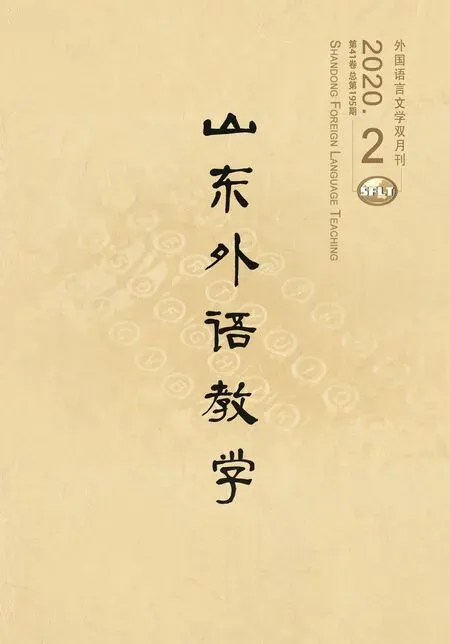从文化形态史观看翻译的文化价值与中国翻译史的“译入”动向
袁帅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1.0 文化形态史观
文化接触带来翻译的需求,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20世纪90年代,Bassnett &Lefevere(1990:12)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侧面证明了文化从来就是翻译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形态史观是20世纪一种重要的历史学理论。许多现代中国史学家都对文化形态史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对中西文化接触及中国文化演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翻译密切相关(钱穆,1994;雷海宗、林同济,2010)。尽管国内有关翻译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还鲜有学者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和价值进行探讨。
历史观是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李大钊(1920/1981:244)在《史观》一文中说道:“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也就是说,历史上发上过的事是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对过去的解释则是生动活泼的历史知识,这种解释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就是人类不断变动的历史观。秦晖(2001)提出,近世以来对世界性长时段宏观历史的解释主要从四种视角出发,即进化论的全球史观、文化类型史观A、文化类型史观B以及非进化的“世界体系”观①。文化类型史观A与B都是基于文化类型学说,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文化”的共时态并列否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时态演进;不同之处在于,史观A主张“文化”有优劣之分,持有某一种文化本位的立场,史观B则有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即不强调也不明确否认文化有优劣之分,认为文化都要经过类似的起源、繁荣、衰落和灭亡的“生命历程”。
文化形态史观是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A.G.Spengler,1880-1936)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等提出的一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分析理论,属于文化类型史观B的范畴。斯宾格勒把文化视为一个具有生、长、盛、衰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体。他认为揭示文化的兴衰需要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中的比较形态学方法”,即“文化形态学方法”(转引自李帆,1993:52)。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斯氏的理论,在历史学界和整个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提出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在人类文明(文化)近6000年的历程中曾出现的数十个文明是等价和平行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时代的。汤因比也把文明视为有机体,并认为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四个连续的发展阶段(转引自张广智,2004:31)。
20世纪诞生的文化形态史观具有重要的史学理论革新意义。把文化看作有机体进行研究是一种把生物界的发展规律搬进历史学领域的全新做法。此外,文化形态史观强调文明具有共时性和哲学上的等值性。例如,汤因比认为,如果把短暂的文明史与数十万年的人类史相比,所有文明其实都处于同一时代,是横向并列的关系,任何文明都不比其他文明更为高明。这种史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具有“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转引自秦晖,2001)。
文化形态史观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界,尤其表现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战国策派”及其文化主张上。“战国策派”得名于学派成员创办的文化杂志《战国策》半月刊和在重庆《大公报》设的《战国》副刊。林同济(1906-1980)和雷海宗(1902-1962)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1940年,林同济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指出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要有机会充分发展且不至中途为外方所摧残而夭折,都要历经封建、列国、大一统帝国三大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史迈入一个“大战国时期”,强国间展开决斗并企图吞并弱国,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雷海宗、林同济,2010:56-67)。林同济称他的历史观整体是从“历史形态学”方法论中形成的,而战国重演不过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同上:5-6)。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同济提出战国时代的重演学说,呼唤民族竞存的意志,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雷海宗把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由华夏文化肇基至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纯粹由华夏民族创造文明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较为边缘化。第二周由公元383年至其立论之时,是北方各胡族屡次入侵、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同上:312)。雷海宗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任何文化均有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阶段,为什么中国文化独能例外?他的答案是,接受外来因子促成了本族文化的再生,是胡汉混合与佛教文化的传入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二周”的奇迹。“若勉强作一个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地延长生命”(同上:30)。身处内忧外患的年代,雷海宗持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立场,以极大的热情呼唤中国文化,使其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
2.0 文化形态史观与翻译
服膺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现代史学家对翻译活动表现出极大兴趣。林同济认为,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才有着容纳和消化他者优秀文化成果的无穷潜力;文化熔融非但不会导致民族文化被冲淡或受到损害,反而能够大大促进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在研究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过程中,他提出依仗汉语音韵铿锵丰满、简洁舒展的优点,以及历史悠久技艺精妙的舞台表演传统,完全有条件发展出别具一格的莎剧艺术流派(转引自赵守垠,1981:89-90)。林同济晚年完成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是一个能再现原作精神风貌和艺术特色的优秀译本,反映出译者对莎剧以及孕育了莎剧艺术的西方文化扎实深入的研究。
雷海宗曾著专文阐述翻译问题,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目的和作用、译品的分类、翻译的方法等几个方面。“由全部人类历史看,翻译,较大规模较有计划的翻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介绍新的思想”(雷海宗,2009:637)。此外还能丰富译入语的语言与文体,具体表现为:创造新词,赋予旧词新的意义;丰富文法、结构与语法;以及促生新的文体(同上)。雷海宗(2009:637-644)把翻译的文字分为三类,即需尽可能逐字逐句直译的,如政策、法令,宪典一类的文字;需特别灵活译出的,如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还有中间类型的,如思想性的作品,这也是大部分译品所属的类型。他认为处理第三类文字时,译文应当通顺明了,硬性的直译应当避免,应合理处理语义结构不对应问题。雷海宗对翻译目的及作用的认识,着眼于新思想的输入及其对汉语的丰富,尤其体现出他一贯所持的文化形态史观立场;而其所论具体的翻译方法则建立在这种对翻译目的及作用的认识上。
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中国翻译词典》的序言中表示自己“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季羡林,1995:2)。这个“从来没人提到过的角度”,其实就是文化形态史观。对于雷海宗的疑问,季羡林(1995:3)这样说: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追踪季羡林的个人学术史,他应该很早就接触过汤因比的历史著作,并对其产生兴趣。《历史研究》前3卷出版的1934年,季羡林刚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不久即赴德国留学。作家徐迟和金庸的求学时代与季羡林大致相同,他们回忆当年的读书经历时,都表示对《历史研究》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李孝迁,2011:142)。上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汤因比作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受到批判(同上:144)。而到了80年代,国内出现所谓的“文化热”,汤因比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同上:150)。季羡林即使不是在20世纪前半叶接触到汤因比,当汤氏再次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时,其振聋发聩的历史思想也不可能不引起这位中国文史大家的注意。
3.0 翻译的文化价值
借助文化形态史观这个历史学方法论,我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文化价值。文化形态史观把文化看作有生命的有机体,认为文化生命过程的维持也与有机体生命过程的维持一样,有赖于新陈代谢作用。通过新陈代谢,有机体从周围环境中获得营养物质,将其转化为自身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同样,文化需要与外部环境交流、与其他文化互通有无,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养分,获得自身演进和革新的动力。翻译的文化价值在于它能促成文化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是文化演进和革新的重要途径。
法国文学批评家斯坦纳(Steiner,2001:312-319)认为,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翻译的过程。在人类最基本的思想交流中翻译是内隐的;在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共存与互相接触中,翻译则是一项外显的活动。不论内隐还是外显,翻译的过程都可以分为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ititution)四个步骤。
从有机体新陈代谢的角度审视翻译的过程,“信赖”就是相信外部环境中存在有机体自身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这种营养物质对翻译来说就是翻译的原文本,译者必须相信原文是有意思的,并加以理解。“侵入”是因为有机体的自身构造与外部环境不尽兼容,要摄入外部营养必然会与之发生冲突;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模式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吸收”就是把俘获的营养分解转化为自身所需要的能量,翻译的吸收表现将原文的含义和形式移植到目的语中。前三个步骤必然破坏有机体内部结构的平衡,导致部分功能紊乱,故需通过第四步“补偿”恢复先前打破的平衡,让有机体回到自然、健康的生长状态。在翻译中,译者首先因“信赖”倾向于原文而失去平衡;接着通过“侵入”在认识上理解原文的意思;尔后对原文进行索取,“吸收”其中可能在目的语中导致不同后果的新成分,于是再次失去平衡;最终的“补偿”是为了恢复上述过程打破的平衡,以达成翻译的目的、实现翻译的理想。
一种语言、象征系统、文化体引入新成分时,总会冒着自身被改变的风险。这里有两种譬喻,即要么是领受圣餐或道成肉身,要么是感染病菌。…… 吸纳远古或异域文化会引发机能感染。一段时间之后,本土有机体便会起反应,竭力中和或排斥异物。(同上:315)②
斯坦纳认为,语言本是一种符号或象征系统,是文化体的构成部分。他用“领受圣体”和“感染病菌”来比喻文化体输入新血液时发生的两种反应:“领受圣体”或“道成肉身”是宗教概念,表示翻译这个过程的积极意义;“感染病菌”则是过程中的消极反应。由于构造差异,新因子给有机体带来不适,吸收和转化自然伴随着中和或排斥异物的过程。“目的语要接受‘异’,需以‘认同性’为基本条件,通过加工、改造,融入新的环境。这种加工或改造,既有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对其的客观限制(或者说对其提供的客观的可能性),也有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文本的语言关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许钧,2003:288-289)。有机体通过新陈代谢吸收和转化外界营养物质,文化体通过翻译吸收和转化外来因素,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同构关系。
对那些在霸权文化的压迫和渗透下谋求自身生存空间的弱势文化,文化的新陈代谢作用更具重要意义。面对咄咄逼人的外来文化,巴西学者主张将“食人主义”作为推进本土文化发展的手段,认为只有吞食欧洲文化,才能摆脱欧洲的殖民;这种吞食可以理解为对欧洲语码的尊敬和违背(方梦之,2011:30)。近代中国的文化学者也表现出同样的关切。例如,贺麟(2009:522)认为:“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家之一部分。……这乃正是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而决不是埋没个性的奴役。”可见知识分子们采取了一种主动吸收转化、而非拒斥外来文化的立场。
近代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化价值的重视以梁启超和鲁迅最具代表性。梁启超(2014:191-192)论述佛经翻译的意义时谈到:“盖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淹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漫长的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家们不满足于囫囵吞枣地对待外来观念,大胆创造了大量新词汇,令本土学术和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鲁迅(2009a:346)则非常提倡“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方法,以求借助翻译为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2009b:330)进一步解释道,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这种文化上“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翻译目的和理想,体现着鲁迅一贯的“拿来主义”的文化立场。
当代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体系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亦包含一种文化形态史观的视角。将翻译活动生态翻译学描述成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以“译有所为”为题,探讨翻译多方面的价值,如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促生社会变革、促进生态文明、塑造国家形象、推动译学发展等。尤其在激励文化渐进方面,“是通过翻译活动,才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的艺术流派和新的表现手法,丰富了译语文化,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化进步”(胡庚申,2013:246-262)。
4.0 中国翻译史的“译入”动向
翻译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显示出译界对于翻译史研究的重视(祝一舒,2018:110)。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则”,是“在历史中业已成形或重复出现的成分”,是“历史可被认知的一面”(汤因比,2005:19)。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有一个时期,世界文明忽然有了某种突破式进展,出现了所谓的高级文明(王宏印,2017:19)。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的古印度、古希腊和中国等几大人类文明几乎在同时奠定了各自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中国文明的突破发生在春秋战国——历史上社会激剧变革,思想最为活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其核心表现为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之间的相互对立和补充(李泽厚,2009:51),即雷海宗所说的第一周中中国文化的主要个性。第二周中,尽管外来文化成分占据重要地位,这种个性也一直没有丧失。
诚如季羡林所言,中国文化一直未曾中断③。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冲突和调和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部翻译史。马祖毅(1998:1)认为,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④——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五四”以来正在蓬勃推进的新一轮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若从文化形态史观的长时段眼光来看,中国翻译史的发展表现出两次大的“译入”动向,即季羡林说的“两次活水”。“从印度来的水”指汉晋到唐宋的佛经翻译,“从西方来的水”指明末开始的西方思想及学术翻译。季羡林之前,梁启超等亦曾表达过这一观点:“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梁启超,2011)。
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极具规模的“译入”动向表现为对印度佛教文化的译介。这一进程延续近千年之久⑤,改变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格局,促成儒道释三教并立的局面。对古代中西交流史有精湛研究的历史学家陈寅恪(2011:283)曾总结道:“自晋朝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中,儒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制度、法律典章和公私生活等方面,其学说思想层面不如佛道两教深;中国自秦以后,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变革就是儒家学说受佛教的影响衍生出“新儒学”。提出“大历史观”的黄仁宇(1997:90)认为佛经翻译“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同时他重提雷海宗的历史观点,即“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同上)。这说明文化形态史观对当代史学家仍有吸引力。
第二次“译入”动向体现为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译介。这一进程被称为“西学东渐”,明末便已开启,晚清民初变得更加迫切。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以“安足”为目的的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上,近代的中国文化面临以“富强”为目的的西方商业文化的侵袭,若欲生存下来,就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冲出去,从西方文化中拿进来(陈旭麓,2008:210)。冲出去和拿进来不仅依然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也是当代翻译活动应努力实现的目标。以翻译为媒介,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并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但从根本上讲,翻译缘起于人类相互交流的需求,交流的结果拓展了人类自我发展的空间。“任何一个民族想谋发展,都必须走出自我封闭的窠臼,无论自身的文化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正是翻译,促使了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拓展,在内涵上的丰富”(刘云虹、许钧,2017:58)。促进文化交流,拓展自我发展空间,仍是当今世界中翻译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5.0 结语
根据译者是把外语译成母语还是把母语译成外语,翻译存在“译入”和“译出”两种模式。“有关文学与文化的译入和译出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要求对翻译和传播在多个层面都做出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许钧,2015:117)。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译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对一个国家形象的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文化的“译出”自然也有其发展的历史动向,即译向何种语言,这是可以另文专论的话题。然而,立足文化形态史观的视角,译介外来文化始终应该是翻译活动的重点。闻一多(1993:21)曾言:“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因此他认为“译入”对自身文化的发展意义更大,“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才能“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闻一多,1993:21)。闻一多这一饱含民族感情的思辨性论述,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与复兴,仍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 进化论的全球史观是一种源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进步”观念的史学模式,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信念基础上。非进化的“世界体系”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提倡从全球角度看历史,反对“进步”观念;世界体系中各部分的区别,只被看作某种原因不明的长周期或超长周期循环带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秦晖,2001)
② 本文对外文文献的直接引用均为笔者自译。
③中国文明是否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学界对这一命题多有讨论。张绪山(2014)提出,中国文明“未曾中断”的表现包括:其一,少数民族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保存和延续。但同时,他认为古印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一定程度上也在延续,所谓“世界上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说法不能成立。陈民镇(2017)则指出,“未曾中断的文明”是就“原生文明”而言,而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延续的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是次生文明。古印度文明中断,指的是距今约4300至3750年哈拉巴文明的消亡。古希腊文明也是一种次生文明,此前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早已消亡。
④我国的翻译史分期尚无定论,主要的观点有马祖毅“五四”之前“三次高潮”说,周作人“三期说”,陈福康“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说。参看《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国翻译史分期”条(方梦之,2011:334)。
⑤据《中国译学大辞典》“佛经翻译史”条,从148年(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安世高译经到1037年(北宋仁宗景祐四年)译场停顿,凡889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印度佛教大小乘之经、律、论三藏几乎全部被译成汉文(方梦之,201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