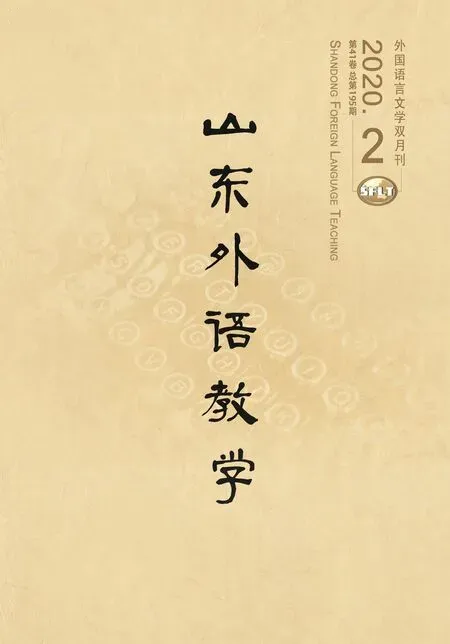一个特写:论大写的你—内/外部读者
李圭; 翟乃海 (译)
(1.延边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纽约 NY10019;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1.0 “永远不要忘记”
美国总统于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参观了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Yad Vashem)。他在访客留言簿中写道:“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也是他发在推特中的一部分内容:“非常荣幸能与众位好友来这里参观—真是太棒了,永远不会忘记!”(Silverstein)
不忘记什么?答案可能是大屠杀或者是参观博物馆,但语法上的宾语和语境中的对象明显缺失了,这很能说明问题,或者使人产生了联想,有些东西似乎在“永不忘记”中被遗忘了。这个祈使句常常与历史相关,“有意地”被用为最高级,但这次听起来—也确实如此—更像是“忘记它”。此外,“它”是什么?是谁要忘记或记住,是谁的记忆或遗忘?对黯然失色的主客体(sobject)(主体和客体)而言,丧钟在为谁而鸣?
这是我在瞎编吗?还是我读得太细,轻易把太多东西读了进去?或者说,更细致的阅读实际上是否能帮助人们理解转来转去而消失不见的“事物”,和主客体撤退时走的神秘环路?好奇的头脑在阅读之门上的推动与拉动,无论多么令人不安或微微,至少会给飘忽不定的眼神带来某种稳定性,让它即使心不在焉也能停在某处。
可以肯定,阅读会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或者说必须继续下去。作为个人,我既不是总统的敌人亦非他的朋友,只是被逼着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也不是一位隐含读者或心存怨念的读者,而只是一个为垃圾邮件程序和虚假账号自动点赞的“粉丝”。这些人数量众多,在一天的任何时段都在不断变化。我是无数的人类眼球之一,追踪着互联网平面图表后面的集体意识,记录它和转发它,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记录这个“很棒的”文本的过程。不管喜不喜欢,相不相信,我是个一闪而过的读者,碰巧进入了一个包括超阅读(hyper-reading)在内的阅读电磁场中,走进了一个媒介化的环境,这里的一切都是被输入的和大肆炒作的。碰巧?嗯,在沉迷推特或反欺骗的心理政治戏码中,在涉及到即时媒体化(imMEDIAted)文本事件时,我作为一个跨生物接收方/阅读者(transbioreceiver-reader),恰巧以某种方式出现了而已。尽管注意力的“持有者”虽然是仓促的、临时的角色,无论积极主动还是在拓扑学意义上的重复无用,不管愿不愿意,仍然必须或被要求承担接收者的角色,他已经被铭刻在结构之中。通过“接收者”,要处理的内容被传递过来并处理为可被存储/浏览/引用(site/sight/cite-specific)的二进制单位。在这里,就是那一小节引述(soundbite)。
正如哈克·费恩所说,“你不认识我,但不要紧”,只要以道德的、社会政治的、心理的方式对着“你”讲话即可:
你要是没有读过《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可能不认识我。但这不要紧。那本书是马克·吐温先生写的,他讲的大多数都是实话。他在有些事上夸大其词,但总体上还是说了实话。这没什么大不了。(Twain,1994:1)
换句话说,重要的是讲述行为,在讲述某事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传递信息:
伊斯梅尔直接向我讲话(“叫我伊斯梅尔”),尽管我有时站在伊斯梅尔的身边,但在其他方面,我却高于他……或者说,他对着一个普遍化的“我”即读者讲话……一本小说邀请我们运用技巧解读,但同时也引起我们思想的漂移。在阅读中,想象力会产生一种散乱的联想,但它并不是胡思乱想。(Mendelsund,2014:296)
还是那样,在叙述中,“邀请”听上去与人际有关,但与其说是个人的或非个人的,倒不如说是自我(异性)情感化的。请注意,顾客们!我们很高兴为你服务,我们爱你。然而,这个用得很混乱的“你”只有从在媒体心理学进行拓扑分析,才能得到理解。它与你这个正在阅读的血肉之躯毫无关系,在某个文本中设定一个情境,把你与第一、三人称联系起来,把你作为第二人称讲述的时候尤其如此。“玩具反斗城”(Toys R Us)(Johnson,2010:5)的敏锐读者芭芭拉·约翰逊(1998:46)观察到,在充斥着普鲁斯特式欲望和矛盾自恋的话语剧场中,“自我客体”(selfobjects)在媒介横向转移过程中发出的信息,常常变成(对于爱的)既新又“过时的要求”。每次言说时,这都成为一种诠释上的“未愈合的伤口”。它本身始终是空洞的,它是任何形成此类文本的社会契约中的常数。
再进一步讲,史泰凡·马拉美(2009:226)有一句常被引述的话,如果“世界万物最终都会成为一部书”,将会有一两个读者—— 一组和另一组。如果如罗伯托·博拉尼奥(Roberto Bolano)(2009:666)末世史诗《2666》中的年轻人汉斯所述,“万物都是被烧毁的书”,如果每本书都被翻炒成数据,成为马拉美意义上的书(电子书?),每本书都变为关于自然、文化和可编码、转换、传输的联网之物(IoT),那么所有漂动的、流通的字节信息,可以用谷歌检索和谷歌处理的、用半大写字母写的、不会被遗忘的信息块将被“记录”在某处,或者被终结。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在隐喻上说,书进入我们的手机里还是骨头里,或者进入某些明暗交界的区域,是一个关于读者的问题,对读者而言也是个问题:如果读者以某种方式保留了最低限度的能动性“感受”,读者是什么?读者是谁?读者在哪里?而且,还有如何称呼、定位、记录“你/大写的你(you/U)”这一读者和主体的问题。一切都在变动与传输之中,他见证了不停息的起源、形成、崩解的瞬间。我们还要问如何、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三个问题。
2.0 继续阅读—像德·曼般“细读”(DeMandingly)
一个人可能有阅读的天赋,但没有人一出生就会读。出生后,人们就无休止地阅读下去,他们会不顾一切去读,会漫不经心地读,会以闻所未闻的方式读。他与黑格尔的狮身人面怪一样,是“象征本身的象征”的另一面(Hegel,1975:360;Derrida,1985:99),是一个从根源生出潜在后代的父亲形象,它将以幽灵的形式返回父身,这是在美好光明的本体背后进行的无声爬行。忘记根源,也忘记“父辈”,就像在继续前行时,要说“忘记”。把头部与其它的身体分开,移动的头部就变成了只剩空洞(完整)的“事物”的剩余部分,这就是头部的辩证法。阅读作为一个事件或事后的行为(互动),在两者之间成为一个事件或者表演,阅读承担了桥梁的作用,即使这一任务无法命名。在这里,我回想起保罗·德·曼(1986:70)讨论黑格尔论史芬克斯谜题的内容,在那里,所有读者都盲目地前行,因为他们被加工成“语法主语与意识分开,诗歌分析与解释功能分开”的声音标记。“它”是围绕这些比喻(头脑)的阅读链条而形成的互文本(环境、交通或次大陆)—是的,请原谅我(主人,如果您愿意,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多括号)。
无论如何,只要“纯粹地阅读”(Gasché,1998:24),就可以重新打出德·曼在阅读中使用的“万能牌”(wild card)(Gasché,1998:7)。德·曼本人是一位莽撞的读者,有人说他的“微笑”介于“柴郡猫笑和忍不住的肠胃疼痛引起的龇牙咧嘴”之间(Freedman,2014)。我是二手资料的读者,中间还隔着文字资料和一代人的距离。惟有借用这一方式,我才能真正地或在文学意义上进行“纪念”。我的意思是,除了记住之外,我还记得什么?除了回忆者之外,我还能称呼自己什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阐释的搬运者,我走进了移动地毯一样的阅读之中,虽然见识了阿拉伯式织物的简单复杂性(simplexity),但无法“亲自”去记住和回忆它—德·曼(1986:175)本人就使用这个比喻来形容罗兰·巴特,称他是“一只不朽的柴郡猫”。杰弗里·哈特曼(2007:187,188)也用过这个比喻,用它说明在“作品阅读过程中的虚无主义过程是……一种对现代偶像症的沉闷艺术反应的重要成分”,是“消极的序列化劳动”,是一种破坏与重建。这种超辩证的阅读艺术达到了物质晶体化和无指涉对象的元字面化程度。它也适用于德·曼的解读,它变得愈发机械,变得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前后连贯一致,但“毫无生命力”。
到了反复阅读的时候。德·曼(1986:3)将“盛期”现代主义的关注点化为对时间意识的句法和语境的自我指涉,是非常极端的,他复活了一种既强烈又连续不停的自我分裂模式和时代。二战后的现代性恢复了后康德时代的先验性,它没有完全消亡而是笼罩在时代的乌云中。它似乎有复活康德式范畴的冲动,虽然仍然依赖假肢一样的理论,但对它的抵抗已近乎先验性的了。这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人们并不清楚。无论如何,处于错综复杂和两难之中的阅读拥有不可化约的生命力,它像一本书一样发展和结束,有时在时间蹲伏的地方突然旋转、尖叫,像定时炸弹一样爆炸。在这一跨越时代的时间坐标上,对“纯粹阅读”(mere reading)的呼唤是隐秘的和追溯性的,它像“实质事件”(Cohen,2000:xv)一样发生。阅读最后的义务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持续下去,成为人们对最初回忆的终极手段。在今天,我的意思是站在今天回头去想,我发现那些解构性的、透视性的(infrared)、物化的阅读,尤其是与无关事实(post-factual)的“档案”式阅读(archival reading)仍然有效。即使一度强大的解构主义转义因为自我僵化(self-mummification)而式微,但在审视文本的每个阶段或步骤时,仍能在文本的内部和周围找到间隙空间。
归根结底,当我每日阅读各种令人沉默的故事、奇闻、丑闻和体育性内容时,我有些不明白,只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实用地”“纯粹阅读”,即在实践或深入的反实践之中阅读那些新鲜炮制的、读完即忘的新闻页面时,在知识和信息在认识论上的区分(如果仍然存在)不是那么重要或者不相关的情况下,仍然做得足够好,它的意义在哪里?柏拉图和他的伙伴们(Plato &Company),比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会气得活过来,但是,正像有些人说的,这是另外一码事。公平地说,我的观点仍然是:考虑到在表意宇宙中数不清的缝隙和漏洞,仍然需要不断的“园艺”工作(Waldrop,2016:2)(有时是(前卫地)守卫),至少对任何数据点上合时合地的特写等于做了阅读的工作——难道不是吗?
德·曼(1986:24)谈及1950至1970年代间教授阅读的教师和学者鲁本·布劳(Reuben Brower)的著作时,说过:
事实证明,纯粹阅读不必依靠任何理论就能够改变批评话语,它深刻颠覆了文学教育是对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或思想史教育的替代品的观念。文本细读常常能不经意间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不能不对语言结构作出反应,这正是文学教育的隐性目标。
此类文本细读并不完全封闭,它把自己置于介入和发现时空的形式之中,从而打开了文本空间,带来了新的视野。这种具有试验性质的文本介入模式,颠覆和重置了当时的批评实践,让文学和理论批评界尤其是在战后英美学术界释放出了批评的能量和创造力。反过来,解构主义理论和哲学仍然生活在所谓“德·曼事件”之中,它并非与“永不忘记”的大屠杀无关(记录在案的丑闻和致命时代的创伤反复重述其强大的细微性和空洞性)。这一故事和历史为我在下文中的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3.0 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的“细听”(Closely Listening)
但是,我的关注点比较小也比较窄,几乎是一种微哲学诗学,带点禅宗聚焦的意味。
诗歌更能引起我的兴趣,它使诗人、诗歌、语言本身等一切因素都成为问题。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确实有问题,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怎么读诗呢?(Fisher,2015:204)
阅读是一种“细听”(Bernstein,1998:3),它能发现,保存,产生联系。我对“细读”作为特定场域行为的位置很感兴趣。它是一种安静的、灵巧的、现象学上的但又易变的归类行为(bracketing)。在技术上的主客体消失的时代,在无线网络连接的物联网出现/消失的时代从事这样的行为,人们在微型的、多层次的事物和存在之中,能听到什么,又如何去听?在这位具有适应性和专注力的2.0版本的“纯粹读者”(mere reader 2.0)人物形象中,我突然意识到我放大了其意义丰富的自动位移性(auto-dislocationality)或者说突出了位置性本身(locatedness),它的位错分布性、可变性,包括其分布突变的实现。我想要的是一位灵活的创新者、一位跨文本、跨界面的干预者兼召集人(intervener-cum-convener)、一位处于“间隙”(Lee,2012:466)中的中间人物——内外部者(inOutsider)。它是一位游走在边缘地带的走私者型读者(reader-smuggler),而且是一位高手。
当谈及这种类型和水平的纳米级“界面”(nano-interfaces)时,亦即“任何嵌套系统中不同介质层之间的过渡点”(Galloway,2008:936),我是要发现并捕获在最小程度的过渡、转移和变化之中的某种能动性,尽管这本质上并非人类世界中的“界面”。我在这里纠结于内部和外部,都是为了给细读者或转化者寻找隐藏在当代远程通信和远程语音中的表亲,它总是以广泛的、隐喻的、外成的(epigenetically)方式被设想为某种侵入性的内部人。我想到的(也许也在我体内)是“一个位于外部的内部”(Ronell,1994:ix)。主人兼客人(host-cum-guest)或主人转化而成的客人(host-turning-into-a guest),反过来也是如此,都重新唤起了重读者(re-reader)。在多义和复调的诗化世界中尤其如此,“主人即客人,客人即主人”(Miller,1977:442)就是这个意思。读者-倾听者(reader-listener)在这个明暗相交的领域到处都是,并将继续存在下去。他能容纳、整理、经受各种各样的误读。文本在叙述中自相矛盾,叙述也讲述着自己。图像通过读者的眼睛和耳朵,也在想象着自己,它们绕过、超过了自我的束缚和唯一的意义,意义无视这个最小的事实,即读者在这里“仅仅在阅读”。
我所设想的细读读者已经接近意义理解的边缘地带,他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并恰当地、适时地留意到“语言的语文学或修辞学手段”(De Man,1986:24)。它的优点和技巧是能“集中注意力来处理单词中的细小音节、发音和如人类、植物和庙宇等语义范畴”(Wolf,2007:34)。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正在和读这篇东西的读者,一起写关于阅读的内容,并对老的“细读者”概念进行了特写。如上文所示,它刻画出了一位具备媒体素养的当代人形象。
对我中有你或反之亦然的思考,凸显了在苹果手机(iPhonic)即时媒体时代,大写的你(U-topos)能够产生间隙性的歧义和自我的模糊性。如前文所述,这里出现了一个内/外部读者的形象(inOutside reader)。他们通过“窗口”观看和被看,既未受邀也未被排斥。他们不是被假意地或礼节性地包含在内,而是被“公开”邀请成为你们(或其中的一员)。只要你们作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文学团体即可,自由地创生,普遍化地指涉,没有特定的期望或隐含的义务来促进跨界面的文本形成和扩张,这是网络的工作。再一次说明,你既没有被剥夺权利,也没有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外,如果只是处于边缘位置的话,而是从结构上以非个人化的形式被巧妙地纳入“网络中立”的开放式多渠道电信共同体中(telecommu-unity)。按照斯泰因的看法,这种频谱化的旁观者形象,亦即他者—读者(the other reader)或他者的读者(the reader of the other),如果不在那里,仍然寄居在那里,或者“相反地”以间隙或数字形式无限地存在着。它在更安静、更凉爽,甚至更宽敞的阴暗处漫游。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疯狂茶话会上,爱丽丝坐在在另一张桌子的角落,“愤慨”地指出:“这里空间很大啊!”
三月兔说:“你们没有受到邀请就坐下来,是很不礼貌的。”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桌子,”爱丽丝说,“能坐下远远多过三个人。” (Carroll,1993:70-71)
越多越好……这个“第三”(或更多)正在或互相进入、传递和丰富一个文本(互文本)的互惠性经济。像数据点一样的晶体管/读者就像是窗上的蝴蝶,具备灵活的即时性、批判读写能力和主动性,就能激活任何特定的文本或新出现的文本自身框架中的边缘地带。变化中的客人/读者变成了可塑的、流动的标记。他是数据逻辑上的连接点,占据聚集着文本和文本发送者的广场,描绘着他们“既在这里又在那里”的状态。例如,照片分享(instagram)的用户会使用着红迪网(Reddit),不论是付费或免费,专心还是心不在焉,认真还是无所谓,都以“内/外”(inOut)的方式畅游。一位喜欢社交的、系列的、中介的、复合的读者形象,在诠释中横跨自我的压力节点上,总是相互作用,分裂,分开,自我分割,自我存档。正如我希望的那样,这样的读者存在或者应当存在,他不仅在社会中甚至独处时存在,而且在战略上、在结构上……也可以在滑动中和隐秘处出现。现在,他们沉浸在文本之中,从伦理和美学层面响应文本,以更古典的姿态,深入、细致地阅读。此类人物形象融合在一起,出现在网络世界(e-merging)。他们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得更加虚拟化,变成了从“远距离”扫描“表面”的人,快得又好又慢,慢地又快又好,最后两点与当今阅览器在算法上的主客体性同步,一如“电子图书阅览器”以共同筛选的递归循环读取读者。
4.0 重新用跨界面的、填缝式的、敏锐的方式连点成线
跨界面的、灵活的雷达式读者( radar-reader)(Liu,2011)在“每个语言无法表达的隐秘场景”(Quignard,2012:7)出入,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它能够成为双向功率流的发送者,产生并调节“引述”(Regier,2010:10)带来的冲击,如乔治·桑所说,“亲爱的读者……你就是目标”(Regier,2010:10)。虽然在AI、安卓、头像、表情包、语音助手、电子游戏等多种新的形式中,这看似有些落后,但“不间断的活跃现实”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仍然与笛卡尔式个人——理性剧院中被称为小矮人的微型类人生物(micro-humanoid)——联系在一起。如柏拉图的药一样寄居的他性(resident alterity)在压力中显现(消失),与位于文本边缘但又藏在文本中心的在红外线下才能看到的内/外部读者(infrared inOutside reader)联系在一起,突然就接近了他者自我。这种令人激动的不稳定性和经历正是作者或读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的。阅读和写作互相构成,都有弹性,变得更慢,更快,更窄,更广泛,使跨界面的交流平台和网络成为可能,进一步拓展了读者的阐释视野和运用语言符号的能力。
设想一下这种“病毒式”传播的情况:一个数字化的特写镜头,还配有一个慢动作镜头,讲述着美国的第一夫人站在红毯上,反应灵敏迅捷,打掉了美国第一绅士(?)在公共场合(试图)去抓她的手。这个镜头在电视/互联网上被人们观看、分析和激烈讨论,引起了轰动的、符号化的、嘲讽的反应。显然,“相机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Mendelsund,2014:280)。这种变化具有弹性,例如,它几乎可以马上并永远地改变了公众对这两位公共人物和夫妇间隐秘关系的感知。这是一个在技术资本主义世界中经常被引用且不断更新的事例。关于这一点,《快时代慢阅读》中的第一条规则具有指导意义:
读者拿起书,书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它们对一个人说:“现在捧起我”(正因如此,惠特曼描述了和他在一起的读者,二人共同探寻他的诗中的奥秘)。书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这本书越好,传递的信息就越紧急,你就越需要耐心听。(Mikics,2013:61)
听着,我只想补充一点:在快速发展的、技术驱动的世界中,慢速阅读和细读如果仍然至关重要,借助照相机之类的技术设备来促进、强化更慢的、更细致的、更具分析性/综合性的阅读。
一个人如果能聚焦于第一夫人手势的含义,同时立即与性别肢体语言和力量差异等大数据结合起来讨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外部读者,也是一位解读充满危险的多重界面和缝隙的读者,他不仅以“既近又远”(Van de Ven,2016)的方式,而且以综合的但更快、更挑剔的方式阅读。内/外部读者能养成弗朗哥·莫莱蒂提出的“模式识别(误读)”(Steyerl)的直觉和能力,将原本只是惰性的甚至是“有毒的”(Waters,2007)数据聚合为有生命的知识树形图,使之成为“影子”(Steyerl,2016)一样的文件。希托·斯蒂尔(2016)猜想,这些碎片只能由某种简单的“格式塔现实主义”来“解读”。确实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对身体进行强制性量化和生物计量政治化的时代,无数的数字在不断地吞噬、“压缩”、加工、建构所谓的意义,同时把文化心理和社会历史的核心变为政治性内容,它们最终会被华而不实的胡言乱语遮盖,变成一种“停下来阅读”的阅读行为。只是大声地、清楚地读出来,但不是一种精致的艺术。这种行为本身是重要的,也具有一定的忠诚度,但它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然而,我今天又不由自主地重读了总统在第二天(2017年3月24日)访问梵蒂冈时对教皇所说的话,他们的会谈以总统说出下面的话而结束:“谢谢,谢谢。我不会忘记你说的话”(Landler and Horowitz,2017)。他们互送了礼物,总统送了一套马丁·路德·金的首版著作,共五本,而教皇回赠了他2015年发表的气候变化通谕(长达184页)和亲笔签名的世界和平日演讲副本。总统面对着镜头说:“我会读的。”在这句肯定之语中,我仍在寻找更有预示性的内容,人们可以用它来继续阅读和反向阅读,也能找到更多继续读下去的理由——断断续续地,在间隙间,跨越界面地不间断地读下去,即使是独自一人但或许会读地更好。我的意思是,至少还有一张阅读的王牌,“永远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