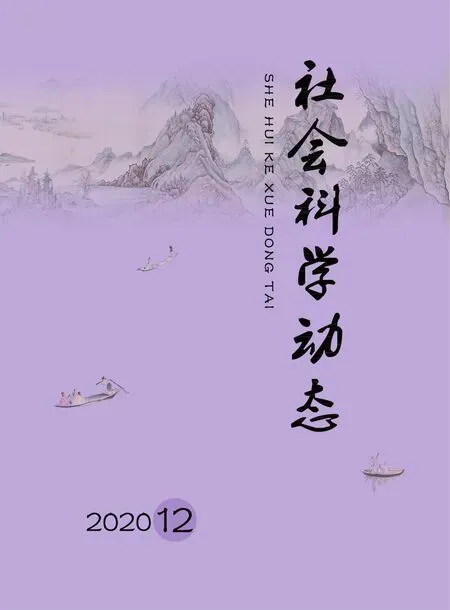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宦官问题研究及其史学特色
方啸天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著名史家。他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并称清代“三大考释著作”。其中钱、王二人惯以经学研究手段治史,多在文字训诂,句义注解,考证内容多具体细微,而赵翼则不同于此。他坦言自己“资性粗纯,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①,《廿二史札记》或可与顾炎武《日知录》相比,“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履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②,这是赵翼治史的一大特色。陈其泰认为: “经世目标和探求治乱盛衰变化的治史旨趣,正是赵翼取得卓著成就的根本原因。”③在探索历朝治乱兴替的过程中,赵翼对东汉、唐、明三代的宦官问题非常重视,并均作研究,宦官群体衍生于古代中央集权皇权体制之中,这一群体依附于皇权,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影响甚至威胁皇权,进而对国家朝政以及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故宦官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廿二史札记》中对三代宦官的研究成果虽分属个卷,实则相互联系,体现他了对中国宦官问题的通贯认识,同时与赵翼对王朝兴亡的探索紧密相连。白兴华认为赵翼的宦官研究, “在乾嘉那个时代里,是十分全面的、深刻的、辩证的,达到了考据史家在此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④。以往学者研究赵翼及其史学时,多只以其中某一代宦官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例证,佐证其治史方法与特色,尚未达到全面且系统的研究,并未注意《廿二史札记》中所体现的宦官势力与对应朝代中其他势力的冲突与联系⑤,故今总结、分析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中对历代宦官问题的研究,以求新的认识。
东汉、唐代以及明代三朝的宦官问题各有不同,赵翼虽作分别研究,但在各篇初始均有对三代宦官情势总的比较。 “宦官之害民”一条中便有总述: “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⑥至“唐代宦官之祸”一条时,也有总述: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⑦再论及明代宦官问题时有总的认识: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⑧可见他并非将三朝宦官的问题截然分开,而是用联系的眼光进行比较,即中国历史中,东汉、唐代及明代三朝宦官之祸最为剧烈,具有代表性,其中东汉宦官首先戕害百姓,后危害国家;唐代宦官权力尚在统治者之上,是千古未有之现象;明代末年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在朝时,影响不亚于东汉末年宦官危害,这是赵翼对三代宦官问题总的认识。李慈铭评价赵翼的《札记》为“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⑨。这种宏博的史观不仅在研究单个朝代时有所体现,在整体历史的把握上更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在具体问题分析上,赵翼同样观察到各代宦官势力的独特之处,以及宦官与各自朝代其他势力的联系与冲突。
一、东汉宦官问题研究
东汉一代因帝主多年幼或早夭⑩,朝局出现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的现象,外戚后族作为后党势力有把持朝政的政治需求,宦官则是帮助君主摆脱外戚专权的有利依靠,这时的宦官、外戚冲突不断,而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则发生在东汉和帝时期⑪。所以在提及宦官专权的同时,必然要提及两汉的外戚辅政。《札记》中赵翼撰有“汉外戚辅政”一条,细数从高祖吕后到平帝时王莽辅政篡位这一期间事例,紧接着在“两汉外戚之祸”中指出: “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⑫他推及根本,认为外戚祸因就是“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⑬,而两汉中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是因为君主并不假以权柄。关于外戚背后所体现的女主临朝,赵翼认为女主临朝则不得以需用兄弟子侄作为心腹,故“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辄相寻,国家俱敝,此国运使然也”⑭。而范晔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道:“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国朝臣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⑮两者看似在东汉女主临朝的用人上有分歧,但这实则就是东汉时期宦官与后党外戚之间联系的真实写照。如黄宗羲所言: “岂知后世之君,乃以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固必然之势也。”⑯故两者的联系不止于冲突与矛盾,赵翼在《札记》中虽无明确论断,但他撰写“东汉宦官”一条,称: “和帝崩,邓后临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权渐重。”⑰显然是注意到了特殊情况下后党与宦官的紧密联系。
宦官依附皇权,与之针锋相对的除了后党外戚势力,还有朝中大臣。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称党锢之祸的滥觞始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诘⑱,其时甘陵乡人有谣曰: “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近人有持疑者,如吕思勉认为甘陵之谣“特食客之好事者为之,无与大局也”⑲。日本学者川胜义雄也称: “我们不能认为,发生在狭窄之地的甘陵,而且还未摆脱私人色彩的这场对立,便是后来那场将全国一分为二的大运动的起源。”⑳赵翼则基本认同范晔的观点,但他指出汉末党禁之祸的原因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桓帝、灵帝时, “主荒政国命委于奄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国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㉑,故东汉时期清议益峻,可见他认为党锢之祸最初来源于君主对宦官的重用。不仅如此,赵翼总结出汉末党禁共有两次,其中第二次党禁起于灵帝时张俭方劾中常侍侯览,后宦官曹节又讽有司并捕前党李膺、杜密及范滂等百余人, “已而宦官又讽司隶校尉段熲,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并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㉒,从中亦可见汉末党人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赵翼在探索汉末宦官问题与党锢之祸时,指出宦官之恶虽遍天下, “然臣僚中尚有能秉正嫉邪,力与之为难者”㉓,这也是宦官势力与朝臣正面冲突的体现,他将臣僚对宦官的弹劾分为三种:廷臣之劾治宦官者、外僚之治宦官者以及小臣之劾治宦官者,并作结论: “盖其时宦官之为民害最烈,天下无不欲食其肉,而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搘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㉔然而,宦官与臣僚之间的冲突虽不断发生,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赵翼通过史料分析对宦官、臣僚关系有着辩证的思考,他发现东汉安帝在邓后崩后亲政,这时宦官李闰、江京、樊丰、刘安、陈达与安帝乳母王圣以及圣女伯荣、帝舅耿宾、皇后兄阎显比党乱政。“此由宦官与朝臣相倚为奸,未能蔑朝臣而独肆其恶也。”㉕安帝时期,宦官不能独横于朝野,尚需和臣僚相互依靠,而臣僚中除秉正嫉邪者外,也存在和宦官“相倚为奸”之辈。后安帝崩,阎显等欲在朝中争权,则与江京合谋诛杀樊丰、王圣等,后宦官孙程等人迎立顺帝, “先杀江京,刘安,陈达,并诛显兄弟,阎后亦被迁于离宫”,故赵翼作结论:“是大臣欲诛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官欲诛大臣,则不藉朝臣之力矣。”㉖且东汉时期入朝为官主要为征辟、察举两种渠道,这也受到了宦官影响, “宦官既据权要,则征辟、察举者无不望风迎附,非其子弟及其亲知”,导致“中常侍在日月之旁,形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 “是以天下士宦,无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穷暴极毒,莫敢谁何?”㉗臣僚势力在和宦官发生冲突矛盾时,也保持着紧密联系。
宦官势力并非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两汉时期,它总与皇权、后党外戚以及臣僚等多种势力保持着联系,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不能进行完全独立、封闭的探索,更不能将其与皇权、臣僚、外戚等完全对立,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札记》中赵翼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看待两汉王朝兴亡,并未将重心放置于宦官研究上,但具体的研究成果使得他对东汉宦官的思考和对外戚、皇权以及臣僚等势力的研究形成了体系化的联系与认识,有关东汉宦官的研究便更加全面与深刻。在此基础上,赵翼认为: “国家不能不用奄寺,而一用之则其害如此。”他利用《后汉书》中各传描述宦官“比肩裂土,皆竟立子嗣”、 “又广娶妻室,增筑第舍,民无罪而辄坐之,民有田而强夺之”等种种恶行,对此现象,赵翼称为“流毒”,而“黄巾贼张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㉘,农民起义的爆发与宦官“流毒”的恶行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对于宦官群体内部,赵翼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群体中仍然存在“清慎自守者”,如郑众、蔡伦、孙程、曹腾等皆是此类,这是对东汉宦官群体审慎而客观的认识。
赵翼对东汉宦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范晔《后汉书》的影响。《后汉书》是在多种东汉史籍已经成书的条件下,由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㉙而成,特别参考了《东汉观纪》和华峤的《后汉书》,其书“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 “往往不减《过秦》篇”㉚。乔治忠指出范晔“不仅笔势纵放、赐予精练,而且颇具深湛见解” “《酷吏列传》《宦者列传》对酷吏、宦官有褒有贬的评论,都具有辩证思维的因素和实事求是的精神”㉛。丰富的资料以及精审的论断,使得赵翼多直接利用《后汉书》中史料与论点,这是在后来研究唐代、明朝宦官问题时所不曾出现过的。
二、唐代宦官问题研究
司马光言: “官宦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㉜大致反映出唐代宦官政治发展的整体态势。唐代是继东汉后第二个宦官问题在正史记录中十分凸显的朝代,唐以前正史中单独列传记载当朝宦官群体的,除《后汉书·宦者传》外,还有北齐史家魏收所撰《魏书·阉官传》,记有25位宦官,但内容多为档案记载,记录当事人升迁贬谪经历,且其中近一半宦官得到了史家的积极评价㉝,而新旧《唐书》的宦官传记里,旧书记有13人,新书则扩充至21人,且绝大多数受到了批判与指责㉞。有学者指出: “唐代是中国宦官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宦官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正式和外朝官僚系统对抗。”㉟可见唐代宦官,有新的情况与特点。
赵翼也注意到了唐代宦官问题的特点,即宦官权力反在人主之上, “实千古未有之变也”㊱。这种新情况发生的原因,则归结于宦官在唐代掌握了禁军、枢密两种军事力量, “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军、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㊲,故此导致无法挽回的趋势。宦官在未掌兵权、未管枢要时,权势已然极盛,赵翼举高力士、李辅国、鱼朝恩等人以作例证㊳。到德宗时期,统治者在神策、天威等军中,设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由宦官担任,以此取代武官典禁兵㊴,从此宦官把持此职,直至唐末。后宦官又有枢密职务, “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㊵。其中神策军中尉职衔是宦官最有实力的职务之一,后如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等宦官均以神策军中尉的身份把持朝政;内枢密使也有两员,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已任宦官董秀为枢密使,至宪宗元和中期,枢密使设为两员, “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任”㊶,赵翼此处提及的应是宪宗以后的枢密使。枢密使一职也由宦官把持,一直延续至唐末,后宋代枢密院也基本承袭了唐枢密院的建置㊷。这样,神策中尉二员以及枢密二员均为宦官把持,这也是宦官专权的象征,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将此称为“四贵”㊸,可见其权势。赵翼对此评价: “是二者皆极要重之地,有一已足以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㊹
在赵翼看来,唐代宦官问题除了体现在宦官把持枢密、中尉等军事权力,宦官出使及监军也是一大弊端,他认为历朝皆有中官出使地方, “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则索贿赂,大则酿祸端”㊺。宦官出使各地, “或修功德,市鸟兽,使还所获,动巨万计”㊻,情况严重者,如辅璆琳受贿后言安禄山不反、边令诚上奏言封常清、高仙芝败退,使二将受诛、中使受藩镇贿赂而保奏君主,使德宗晚年时藩镇猖狂,无疑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更有宦官监军,唐代宦官监军主要有临阵监军和藩镇常驻监军使两种。其中前者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6),沿袭的是隋末御史监军制度㊼,安史之乱后, “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㊽。同时安史之乱后方镇兴起,为加强对地方的制约,唐政府则在方镇设置常驻监军使,用以“监视刑赏,奏察违谬”㊾。宦官监军上传下达,有时权力超过将帅,赵翼对此评价: “观此则中使监军有害无利,昭然可见。此犹是临战时用以监察,尚有说也。”㊿战时监军虽百害无利,然平时藩镇也有监军,一定程度上确实有牵制节帅、平靖其乱的作用,对此赵翼并未忽视。
监军一职虽使宦官获得极大权力,但这也是唐代不可或缺的职务。唐初实行府兵制,而到高宗特别是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各地府兵兵源枯竭,开元二十五年(741)玄宗下诏,令中书省及各道节度使“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如募,取丁壮请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51〕,即打破府兵制,实行募兵制,至此地方节度使掌军权渐重,也使得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与中央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赵翼在《札记》中撰有“唐节度使之祸” “方镇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馈” “方镇骄兵”三条内容,细数节度使、方镇渐掌兵权后, “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 “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52〕。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纠其原由,乃“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53〕。在此基础上,他对宋代文臣知州也作出评价,认为后世学者只看到这项计策使得宋代边防力薄,不足以自强,而未看到这从根本上消除了整个王朝弱干强支的隐患, “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54〕这是其独到的见解。赵翼在撰写“唐宦官之祸”后又连续撰写“唐节度使之祸”等内容,实际体现出唐代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之间的紧密联系,宦官掌枢密院、神策中尉以及监军等职,可以协助君主制约地方藩镇,他们上传下达,也可以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赵翼同样承认这一制度“是亦未尝无靖难解纷之益”,但整体上他对宦官监军基本持否定态度,即便监军可制地方藩镇, “然其中贤者百不一,而恃势生事之徒踵相接也”,且“在河朔诸镇者,既不能制其叛乱,徒为之情封请袭;而在中州各镇者,则肆暴作威,或侵挠事权,或诬抅罪戾”〔55〕。
现今保存唐代宦官信息最完备的当属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修成的《册府元龟》,此书记述唐代事迹时,武宗以前主要采用各帝实录,武宗以后基本参考贾纬编纂的《唐年补遗录》65卷,全书整体属于对前朝史料的摘抄,删减较少。赵翼研究唐宦官问题时没有利用《册府元龟》,也未利用《全唐文》《资治通鉴》等资料,而主要利用新旧《唐书》。然而,新旧《唐书》的史家立场与观点十分鲜明,这在记述宦官方面也存在区别,赵翼自己也撰有“新书增旧书处”等条探讨《新唐书》对《旧唐书》的增补删削,其中将宦官记载的增补条目也罗列了出来,但尚未涉及到两书观点的对比。李瑞华曾将新旧《唐书》中记载宦官的部分进行对比〔56〕,指出旧书认为宦官的作用取决于君主,君主的不当举措便会发生宦官乱政;新书则认为宦官本身具有生理缺陷,是阴险卑劣的小人, “残气不刚,柔情易迁,亵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迫而近”〔57〕,明君则防不胜防。赵翼在利用新旧《唐书》时,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两书编撰者的影响,而他否定宦官掌枢密、神策中尉以及监军等职的作用,认为宦官专权,积重难返,甚至穆宗以来八世君主中有七人为宦官所立,直接威胁到了皇权统治,故此可知赵翼对宦官的态度偏向于《新唐书》中的立场。而为何如此?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赵翼除研究唐代宦官外,对东汉、明朝的宦官也基本持批评、否定的态度,可见这是他从整体上看待中国历史中的宦官问题的态度;《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直至嘉靖十七年(1538)才重新刊行,但传布不广,乾隆年间才进行复刻,所以至少在乾隆以前学者对唐代宦官的认识普遍都受《新唐书》的影响,赵翼《札记》的撰成主要依靠正史,《全唐文》《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料并未涉及,在研究唐代宦官问题时同时利用新旧《唐书》,整体态度上偏向《新唐书》也情有可原。除此二点,仍有许多原由值得探索,但这复杂的因素实际构成了赵翼在看待唐代宦官问题上偏向《新唐书》立场的一大特色。
三、明代宦官研究
陈其泰指出: “明代历史是清代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58〕论断颇为得当,清初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谈迁一辈,感怀亡国伤痛,已开始自觉总结明朝历史。雍正十三年(1735)《明史》定稿,并于乾隆四年 (1739)刊行,时人对明朝的历史更加清楚。赵翼在《札记》中有关明朝历史的研究足有六卷,份量最重,足见其重视。研究主要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明朝从太祖时期到魏忠贤专权时期谏官言路的巨大转变;二是明朝中叶以后君主不理朝政、不见群臣的现象;三是明代宦官专权,特别是魏忠贤时期危害剧烈;四是明代贪污猖獗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宦官问题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且其他三部分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代宦官专权不似汉唐,宦官对皇权的威胁较少,整体上依赖皇权,即便如盛极一时的刘瑾、魏忠贤等人,在失去君主宠信后,也迅速衰落。赵翼按照明朝发展的时间,指出明初宦官虽逐渐干权,但并未到专权的地步,如明太祖时期, “内宫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 “宣宗时,中使四出,去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 “按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59〕可见明前期政府对宦官权力的控制是有效果的,这得益于明初的吏治,赵翼对此非常重视。明初重酷刑,如吴晗直接将其定性: “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刑的基础上,这个时代,这种政治,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60〕赵翼撰有 “明初文字之祸” “明初文人多不仕”“胡蓝之狱”等文,揭露明太祖朱元璋“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61〕,且因重典法,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62〕,故文人为避诛谬,多不取仕。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明初吏治虽严,但也对官吏有警示意义, “并有坐事者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今循吏传可考也。”〔63〕所以在他看来,明初吏治客观上有整顿纲纪的作用,故英宗、武宗时期朝局内外多变,“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64〕。继此他还指出“后人徒见中叶以来,官方惰裂,吏治窳敝,动谓衰朝秕政,而岂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65〕近代学者孟森也肯定道: “太祖用刑颇酷,说亦见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斯为承大乱之后,得刑乱重典之意,虽非盛德事,而于国本无伤,亦且深有整饬之效也。”〔66〕
明初吏治严苛,宦官也处于收敛的状态,而这种情况却在嘉靖前后发生巨大转变。赵翼通过一组对比反映出这种变化:永乐时期, “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而嘉靖以后,特别是正德、天启等朝时,“今则呼唤府部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67〕。余华青在总结明代宦官特点时也说道: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权专政的现象在历朝历代多有发生。但是,就宦官威势气焰显赫嚣张的程度而言,却少有如明代者。” “明代权阉的威势,远在公卿朝臣之上。”〔68〕在此基础上,赵翼进一步提出明代宦官从参与朝政到擅权,其间的转变始于宦官王振。有学者评价王振“为明朝的宦官专权开了恶劣的先例,他与步其后尘的刘瑾、魏忠贤,是对明朝影响最为恶劣的三大宦官之一”〔69〕。赵翼的观点其实与《明史》相同。《明史》宦官传分为两卷,其中王振、曹吉祥、刘瑾、汪直、魏忠贤等人被称为“口含天宪”者〔70〕,开篇便对明代宦官进行总结: “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71〕而如何判断宦官势力?《明史·阉党传》给出一条标准: “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功,虐焰不若是其烈也。”〔72〕即以党人依附的情况作为准绳。赵翼同样以此评判宦官之势,但他的研究更加细致,《札记》指出王振擅权时依附者并不占多数,至汪直、刘瑾时期,依附渐多,但朝中仍有针锋相对的大臣, “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 “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也就是王振、汪直、刘瑾三人擅权时期, “尚不敢奴隶朝臣也”,这个情况直到魏忠贤时期才发生变化〔73〕。不仅如此,赵翼还对《明史》中有关宦官的论断作出商榷,他认为宦官为祸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他们通晓文艺,与之相反,魏忠贤目不识丁,却为祸更烈。所以他总结道: “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经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74〕此外,有关宦官受贿的问题,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顾纳贿亦不必奄寺,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纳贿这一现象与宦官的身份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和背后所具有的权势有关,他又举严嵩纳贿一事证明: “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75〕这无疑是对明代宦官纳贿的清醒认识,更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朝政中的贪污腐败现象的思考。
宦官这一群体依附皇权而生,所以在讲述宦官问题时,皇权的谈论必不可少。赵翼在研究汉、唐宦官问题的同时,对皇权的谈论尚未达到批判的地步,而在研究明代宦官问题时则明显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批判。当皇权较弱时,宦官附势后肆虐专权,甚至能够威胁皇权,汉、唐两朝皆是如此。故赵翼在《札记》中对两朝统治者多报以惋惜,称宦官专权之势“积重难返”。而明朝皇权并不弱,而是统治者自身在治国理政方面出现了极大问题。赵翼在《陔余丛考》里撰有“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一条,细数自宪宗后,孝宗、武宗、神宗、光宗等朝情况,指出明代自中叶以后,君主真正治理朝政的时间只有短短数年,这样“倦权者即权归于阉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能延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蘧失,诚不可解也”〔76〕。宪宗以后,几朝君主多不临朝, “主德”出现问题,宦官自然逐渐擅权。他在《札记》中记有 “万历中缺官不补”一条,指出“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导致“职业尽驰,上下解体”,而其中矛头则直接对准统治者:“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甛,以海内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由于万历时期统治者的决策,使得朝中官员不备,赵翼认为这种决策会使“上下解体”, “观此可见是时废弛之大概也”〔77〕。且在万历帝时,民间传阜平、房山各有矿砂, “帝命中官与其人偕往”〔78〕,一时间矿监税使流遍天下。对此,孟森将万历朝缺官不补与矿监税使二事联结,指出神宗“其内外缺官实为惜俸给,其采榷必遣内监,利其非士大夫,不知法纪,而可以尽搜括之能事”,并评价神宗为“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79〕。赵翼在记“万历中缺官不补”的同时也记有“万历朝矿税之害”一条,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两件事对其时朝政、社会的严重影响。神宗时期设置矿监税使,无疑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札记》中言道: “是时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可报,所劾无不曲护之。”〔80〕这明显是对统治者纵容宦官,忽视廷臣谏言的揭露与批判,而统治者的这种行为导致“民不聊生,随地激变”〔81〕。这一结论在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便已出现: “至乃国法恣睢,人怀痛愤,反尔之诫,覆舟之祸,亦间有之。”〔82〕《明史·食货志》更明言:“明亡盖兆于此。”〔83〕可见这是有清一代学者对万历年间矿监税使事件的共识,且基本都对神宗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不仅如此,在成化、嘉靖时期,宪宗、世宗好方技,选用人才多以方技、符术得以入朝当官,对此赵翼直接对宪宗、世宗作出评判,即盖宪宗“徒侈心好异,兼留意房中秘术,故所昵多而尚非诚信崇奉。世宗则专求长生,是以信之笃而护之深,与汉武之宠文成、乐大遂同一辙”〔84〕。宦官衍生于皇权,而这一群体的干政擅权也主要来源于皇权自身出现问题。赵翼虽在“明代宦官”一条里称汪直、刘瑾、王振、魏忠贤的擅权无忌是由于人主年少,不能自主,而以上数条更是在说明:统治者不参朝政、无心国事,忽视官僚体系的完整性,同时任意用官,为一己荒诞私利从而贪国误国,这种统治者自身的昏庸、腐败,才是导致宦官专权,甚至危害社会的主要原因。在此赵翼也劝诫统治者“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85〕
在赵翼以前,清代对明代宦官有记录与研究成果的,除《明史》中所记宦官传以外,主要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该书仿《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一种尝试,早于《明史》而成,其中记有“宦官误国”一条,而内容在于整合明代宦官史料,虽在文末有作者评语,但尚未到达系统研究的地步。另外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记有“奄宦”上下两条,是对汉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宦官专权总的论述〔86〕。而赵翼对明代宦官问题既有整体的认识,更利用充足的史料对宦官势力的形成、发展及其擅权作了细致分析,研究该问题的同时更关注了明代统治者自身、明初吏治以及社会人民受到残酷压榨等各方面问题,这些方面实则与宦官专权有着紧密联系,所以整体上赵翼对明代宦官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缜密的体系,这是他突破前人研究成果的地方。
四、史学特色
赵翼研究宦官问题的方式和特点,与《廿二史札记》的治史方式保持一致。钱大昕为《札记》作序,称该书“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见识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87〕。梁启超在总结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治史特色时,对赵翼的研究成果特别赞赏,称“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88〕, “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89〕, “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90〕。赵翼擅长发现各朝代重大问题,并通过归纳、比较、分析,挖掘史料背后所隐藏的盛衰治乱,这在他的宦官研究中有充分体现。除此外,赵翼的宦官研究亦可见其发展与联系的眼光:
第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宦官问题。宦官集团会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演进出现新的变化与问题,历史发展本身具有连续性,汉、唐、明三代宦官及政局情势并非单一、独立的历史片段。封建王朝体系中任用宦官的制度一经实行,便伴随着朝代更迭而延续,这一延续便是无间断的动态发展过程。宦官群体的地位、身份以及权力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皇权、后党、朝臣等多方政治势力的状态。在对应的朝代中其先后也会出现发展与变化的态势,而《札记》既考虑到汉、唐、明三代各自宦官问题的独特性,也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宦官问题在三代中的整体态势以及各朝代中宦官势力的先后变化。
第二,以联系的眼光看待宦官问题。三代宦官虽有各自特点,但总体上属于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相对整体而言具有有机联系。不仅如此,宦官势力衍生于皇权,而与之具有紧密联系的,主要有皇权、后党外戚、官僚等,如东汉时宦官势力与皇权、臣僚以及后党外戚形成有机联系;唐代宦官势力与皇权、地方兵权以及藩镇节度使形成有机联系;明代宦官与皇权、官僚等形成有机联系,所以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与其具有紧密联系的群体或势力也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需注意的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研究汉、唐、明三代历史时,并非以宦官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是以探索各朝代盛衰治乱为研究目的,在此目的之下,影响朝代兴衰的主要因素本身具有普遍的联系性,这样客观上使得他的三代宦官研究各自形成严密的体系。
《廿二史札记》问世后,有学者批评质疑,这些声音集中于指责该书考核、议论只取正史,罕有其他史料。如李慈铭在为《札记》作题跋时评价道: “其书以议论为主” “盖不以考核见长”〔91〕,后又在《越缦堂读书记》里指出《札记》 “于其他书罕所征引” “赵见识浅陋,全不知著书之体……然于史事多是正纂集之功,无所发明,笔舌冗沓,尤时露村学究口吻,以际钱氏《廿二史札记》,故相去天壤,即拟王氏之《十七史商榷》,亦远不逮也”〔92〕。乾嘉考据学的特点在于对具体事件作实在考证,并不提倡宏观地概括,如王鸣盛所言: “书生匈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这个结论可以说是乾嘉考证时期绝大部分学者对学问之高低所自设的分界。钱、王论著以考证分析史书,但其中也存在对史事的评论,如钱大昕在《潜学堂文集》中对君主专制极力抨击,认为读书“不必横生议论”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留有大量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的文章。李慈铭对《札记》的评判,是以乾嘉考据学者的考证性成果作为准绳,而赵翼《札记》与王、钱二人作品相比,确实考证性的内容颇少,其次《札记》的撰写主要依靠正史内容,缺少其他史料作为支撑,若正史本身记载出错,或阅读正史者未详细考订,难免会出现错误。如陈垣曾校证《札记》中数条错误,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以《札记》论证史实所出现的失误为“史源学实习”课的主要课程内容,他根据阅读《廿二史札记》所得教训,提出读史时几点要则: (1)读书不统观收尾,不可妄下批评; (2)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 (3)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 (4)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 (5)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 (6)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93〕。而赵翼对三代宦官的研究主要以正史为依据,从中进行评议、分析,所以自然也在质疑的范围之中。
然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宦官问题在东汉、唐、明三代最为突出,三代宦官也反映出中国宦官历史发展的整体态势,这是近现代以来学界的共识,并且宦官问题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往往会给朝局、社会造成巨大影响,这无法通过历史书写完全掩盖,反而某些影响恶劣的宦官会在层累的历史书写中出现“妖魔化”的夸张形象,如明代魏忠贤、王振一类便是如此,而赵翼对中国宦官问题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如研究汉代宦官时指出仍有贤能的宦官;研究唐代宦官时也客观分析了宦官监军的积极意义;研究明代宦官时更是对统治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赵翼虽依据正史研究三代宦官,但能利用充足的正史资料,系统分析宦官势力与其他各势力的冲突与联系,藉此对中国宦官问题做到了通贯、深彻的研究,这是在赵翼以前的学者所未能做到的,属于新的突破。陈其泰评价赵翼是一位具有朴素进步观与经世主义的学者〔94〕,赵翼自己也曾有诗云: “搅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复将三寸毛锥尖,妄拟一柱中流砥”,待《札记》成书后,又作诗云: “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95〕他将《札记》比于顾炎武《日知录》,又以正史观治乱盛衰,可见《札记》本身便具有明确的经世致用之意,在于“治病救人”,如赵学勤所评价的,赵翼“透过封建国家外部这一臃肿浮华的皮囊,看到其内部日渐销蚀的枯骨已难以支撑这一貌似强大的躯体,为国家前途而担忧,亦有其眼光敏锐之处”“缘此,瓯北不断在追索世间之斗争产生的根源”〔96〕。宦官问题的研究本身便具有现实意义,故此从中更能看出赵翼的政治抱负以及对现实的批判。
注释:
①②⑥⑦⑧⑫⑬⑭⑰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㊱㊲㊳㊵㊹㊺㊻㊿〔52〕〔53〕〔54〕〔55〕〔59〕〔61〕〔62〕〔63〕〔64〕〔65〕〔66〕〔67〕〔73〕〔74〕〔75〕〔76〕〔77〕〔78〕〔80〕〔81〕〔84〕〔8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110、449、839、67—68、68、39、111、109、109、113、113、111、111、113—114、114、449、499、499、499、450、452、452、451、454—456、456、456、455、840、772、773、791、792、793、840、841、841、842、830、828、829、829、812、829页。
③陈其泰:《赵翼史学:乾嘉学术的珍品(代序)》,白兴华:《赵翼史学研究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页。
④白兴华:《赵翼史学研究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3页。
⑤有关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涉及宦官专权问题的研究,较突出者为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其中有一节专门研究《札记》中所见宦官专权问题,但重点在于东汉宦官专权和三代宦官问题比较,尚未有全面的分析。详见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8—53页。
⑨[清]李慈铭:《廿二史札记·题记》。
⑩自东汉和帝起,和帝即位年仅十岁,后殇帝生百日即位,安帝十三岁即位,顺帝十一岁即位,冲帝二岁即位,质帝八岁即位,桓帝十五岁即位,灵帝十二岁即位,献帝九岁即位。
⑪据范晔:《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和帝年幼,太后窦氏临朝秉政,权势过重,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密谋,发动兵变,一举铲除窦氏集团。
⑮《后汉书》卷87《宦者传》。
⑯[清]黄宗羲著、吴光主编:《明夷待访录·奄宦下》,载《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⑱《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⑲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⑳[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度社会研究》,徐古芃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㉙ [唐]刘 知几:《史通》卷12《古今正 史》,(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0页。
㉚《宋书》卷69《范晔传》。
㉛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
㉜《资治通鉴》卷263“昭宗天复三年正月庚午条”。
㉝《魏书》卷94《阉官传》。
㉞详见《旧唐书》卷184《宦官传》;《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新唐书》卷208《宦者传》。
㉟李守栋:《唐代宦官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㊴详见《旧唐书》卷134《窦文场霍仙鸣传下》。
㊶《册府元龟》卷665《臣内部总序》。
㊷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3天复三年正月条,有胡三省注: “枢密分东西院,东院为上院,西院为下院。”
㊸《资治通鉴》卷243宝历二年十二月载: “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本条有胡三省注: “唐末谓两枢密、两中尉为四贵。”
㊼《通典》卷29《职官十一》。
㊽《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
㊾[宋]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91页。
〔51〕《全唐文》卷31玄宗《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诏》。
〔56〕详见李瑞华:《层累构造下的唐代宦官历史书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1期。
〔57〕《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
〔58〕陈其泰:《赵翼史学:乾嘉学术的珍品(代序)》,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页。
〔60〕 吴晗:《吴晗说明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68〕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1页。
〔69〕 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7页。
〔70〕〔71〕《明史》卷304《宦官》。
〔72〕《明史》卷306《阉党传》。
〔79〕孟森:《明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0页。
〔82〕《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
〔83〕《明史》卷81《食货志》。
〔86〕详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载《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87〕[清]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 (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5页。
〔8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
〔8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
〔9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1页。
〔91〕 详见 [清]李慈铭:《李慈铭题记与跋语》,(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 (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7—888页。
〔92〕[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0页。
〔93〕详见陈垣著、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
〔94〕详见陈其泰:《赵翼史学:乾嘉学术的珍品(代序)》,载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页。
〔95〕详见[清]赵翼:《瓯北集》卷21《再题〈廿二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4页。
〔96〕赵学勤:《赵翼评传》 (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