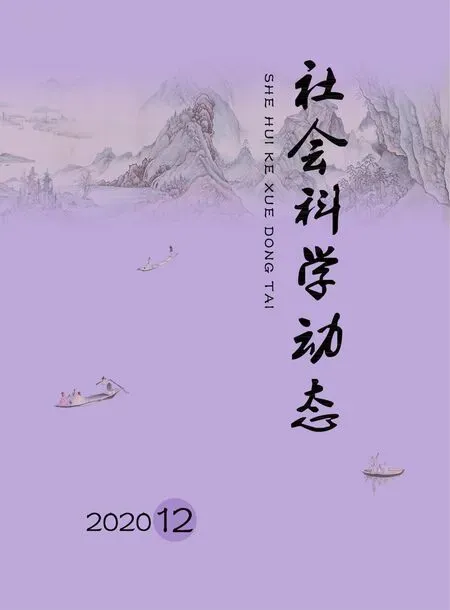梁启超文学观趋向王国维的学术考察
耿庆伟
中国社会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大变动和文学观念的大革新。作为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梁启超、王国维立场相异、观点相左的文学观念让他们分别成为功利文学观和审美自律文学观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有思想家的勇气,以谋求民族现代化为目标;一个具有艺术家的良心,以追求审美现代化为旨归。两面文学大旗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场关于功利与审美的理论之争,启发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两个维度:审美与功利的交锋、碰撞、互渗,不仅关涉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学观念上审美与功利的冲突,巧合地预演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论争主题,关于文学功利性优先还是审美性优先的龃龉几乎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争的始末。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塑造着现代文学的个性风貌,当文学深陷政治的漩涡时总有文学独立性的声音提醒人们关注文学自身的特性,不致使文学完全成为观念的传声筒。
一、梁启超功利文学观的生成与问题
1902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小说》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以一贯雄辩的煽动性赋予小说远超自身能量的强大功能,指出如果想更新一国之民、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必须借助小说之“不可思议之力”。在这份宣言式的文章中,其目的并非要提升小说的地位,梁启超看中的是作为“群治”手段的小说之“力”,从论述小说对于“群治”的重要性,将小说整体性地推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显赫位置,由此确立了小说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在传统的经史子集构成的知识谱系中,文学是混迹在集部中的一种附庸性存在。在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类等级序列中,散文因履行了释经、传道的责任,一向地位尊贵;诗歌上联 “兴、观、群、怨”也攀上了政治的高枝,地位相对重要;而处于“小道” “末技”之位的小说,通常只是文人进行娱情消遣的工具,与政治的疏离导致小说在文学的内部结构中地位并不高。梁启超比较了小说与“诸文”的关系,指出小说具有“易入人” “易感人”的文体优势和“支配人道”社会功效①,因此把小说从文学的边缘拔升至文学的中心,进而引起了文类调整。在此之前,小说从未被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来看待,文体观的变化让小说成为越居诗歌、散文之上的特权文类,小说地位的隆升引发了文学观念的重构。在近现代文化语境下,文学观念的变化可能主要不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时人追随社会变革的脚步而对文学的强行要求。梁氏的“新小说观”本意不在文学,他看中的是文学的启蒙功用,之所以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扭和在一起是为了促进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但结果却无心之中升迁了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促进了清末小说的创作兴盛,将这种历来被贬抑的文学样式侧身于文学的殿堂,服务于变革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现实需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时代巨变铸造了文学观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艰难启动的,中国近代文学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危机中载沉载浮。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就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而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都没能将中国引向强大之路,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证明直接走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之路一样行不通。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在于缺乏民德、民智、民气, “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见睹”,是因为未留意“新民之道”即忽略国民政治觉悟的启蒙所致②。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的政治觉悟,关键在于新文学,于是借道文学革新进行思想启蒙的一股潜流由此跃入梁启超的思维视野。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启蒙思想著作,梁启超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缺乏民德、民智、民气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以自下而上的“新民”来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③。鉴于中国文学一直具有服务政教的传统,民族国家利益的急迫诉求让人们自然地将目光转向文学领域,希望找到一种宣传政治思想的载体,而在改革者的视野中, “说部”之“入人之深,行世之远”远在 “经史之上”④。因此,易为大众所接受的小说理所当然地受到重视,进而成为承担启蒙大任的首选文体,即通过借助小说通俗易懂的艺术特性及其在民间的强大影响力使之成为教育国民、表达政治诉求的最佳手段。为达成这一目标,梁启超将小说拽入文学正宗的队列,并特地选择政治小说作为敞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宣传工具⑤,小说由此以符合历史正义的“善”成为时代之需的利器。当时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驱使文学不能不暂时承担起思想启蒙、动员民众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就这样,近代的社会历史变革让文学宿命地牵手政治。
梁启超认定“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小说是文学;二是小说具有启蒙的政治功用;三是小说是所有文体中最能发挥启蒙功能的文体。小说与政治的关联会让小说疏远与纯文学的关系,但文学性的前提保证小说不会离文学太远,尽管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没有产生传世的经典,这也是其小说观被人诟病的原因。时代条件的限制冲淡了他对小说文学性的要求,但不能完全忽视梁启超对小说艺术特性的精辟见解。他指出,小说文体特征是“曲折透达,淋漓尽致”,不但可以“描人群之情状”,而且能够 “批天地之窾奥”⑥。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就明确宣布,小说之所以为“文学之最上乘”,不仅在于小说体现着“文章之真谛”,而且“在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他借助 “熏、刺、浸、提”四个佛学用语分析小说具有“可惊可愕可悲可感 ”的审美移情作用以及使人“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的艺术感染力⑦。可以说,梁启超的小说启蒙主义理论一开始就潜含着审美性的自觉,不仅关注到小说的社会价值和经世功能,而且注重从文学的内部规律研究小说的审美本质和艺术特征,并不时地从审美之维来分析评价小说。难以割舍的功利性追求和艺术标准的坚持之间的矛盾在其文论中时有出现,他在《绍介新著〈新小说〉第一号》文中就指出,创作小说的旨归在于“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而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小说却是“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存之”⑧,明确的艺术追求难敌社会救亡的现实需求,启蒙功利的追究让梁启超无暇考虑文学自身的特性,政治功能的极端强调弱化了文学娱乐、审美功能的发挥,当然无法让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世界,关注审美。然而既然是文学创作就要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所以其理论主张天然地潜藏着文学功利性与艺术自律性的矛盾冲突,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他优先考虑政治功用性。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他“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载体,根本不是为了塑造人物或是结构情节,是一次为功利而非为艺术的政治书写行为。为达成政治功效,他甚至将大量的政治话语引进小说,让小说俯就于其政见,把作为自己思想化身的黄克强和李去病这两个观念式的人物生硬地塞进小说文本中,结果造成行文拖沓,理念先行,内容说教气息浓厚。小说“五回”中就有“两回”是“论辩”与“演讲”构成。阐述政治理念的功利动机导致了这部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的文体杂糅性。 “说部”里嵌“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将稗史演义成为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长卷,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显然意不在此,而是在“稗史”框架下含 “论著”,用来 “发表区区政见”⑨。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意不在文学理论的建设,因与1897年至1915年的政治革命的关联而被赋予了某种时代的性格,将革命引入文学重在利用文学的审美力量启蒙国民,传播社会理想,推进思想革命,推行政治主张,启动中国历史现代性的步伐,这种文学的工具论必然造成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匮乏乃至缺失。如果从小说向来的文学史地位来看,梁氏的文学观将文学的功用价值放在首位进行考虑亦无可厚非, “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与政治的联姻不仅使政治受惠,而且让小说一改其卑下地位,不再为文人所轻视,从而间接推动着小说文体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得到改观,就连坚持复古的林纾都承认小说的社会作用,称其译介小说是为了警醒“读吾书”之“青年” “学生”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⑩。从深层来看,小说服务政治并非仅是传统文论体系内部的换旧 “道”载新 “道”,理论基点虽依然是“载道” “教化”等为依托的传统功利文学观念,或者说将传统文学观念中文学承载的功能扩展到小说戏剧中,但却在吸取西方现代诗学精神元素的基础上嫁接了“新民” “群智”的政治意图。传统的文以载道的“道”虽并非仅指儒家之道, “道”的内容也因时而不断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还是偏于儒家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秩序失范,已无法起到整合人心、凝聚民意的作用,梁启超取法西哲新说、他国文明,大量输入并使用 “国民” “新文体”“新小说” “理想派” “文界革命”等政治话语和文论话语,努力建构救国论语境下的新文学观念,他也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将国民性改造话题引入文学研究的第一人。毫无疑问,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形成了“要救国必须先改造国民性”的共识。鲁迅、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作家的改造国民性创作母题正是对梁启超新民理论的再思考,虽然中国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但改造国民性一直是现代作家矢志坚持的创作主题。相较于传统的载道文学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经突破注经释典、代圣人立言的藩篱,将传统的服务君王(为君)转变为服务国民(为民), “民”的基点的获得让梁启超的“新民”文学观带有“人的文学”的色彩。在梁启超的政治诉求中,文学服务于国民性的现代性改造,激发民众的道德意识,促成新的价值观念的生成,让民众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新民。 “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正是现代性民主思想的精髓,在一定意义上说,梁启超“新民说”的出现表明在我国近代文学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民主主义精神。其文学观虽在形式上不脱“文学为什么”的工具论传统,但却装进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内容。借小说输送的政治理想并非仅仅是传统的“官方”话语,迎合时代的节拍,用自己关于改革社会的政治理念和未来社会的设想替换传统的儒学之道,在方式上与“五四”文学将 “载道”内容换成 “德先生”和“赛先生”有着一致之处,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教化文学观的服务方向,为现代文学的隆重出场发挥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如钱玄同就称道梁启超是“创造新文学之一人”⑪,郭沫若也认为梁启超是文学革命“滥觞时期的代表”,其文学创作虽未“摆脱旧时的格调”,但已不是“旧时的文言”,尽管受到“时代的限制”,但仍充分发挥了他的“个性”和“自由”⑫。
在中国社会遭遇生存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文学成为启蒙民众、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种将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融为一炉的整体性追求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将轻松的文学与严肃的政治目的紧密联系起来,让小说承担起传统经史的教化功能,相信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舆论动员和重整社会的功能,贴近了文学与社会政治变革的距离。任何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个人性的印记,国家的灾难让梁启超的文学理论走出书斋,可以说,现实的压力形成了他对文学思考的浅尝辄止和对文学结论的急功近利。他的文学理论在冲击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也部分袭蹈了载道文学观的内容,政治主导的动机和随意性的发挥让他的许多立论扞格于文学的事实。实际上,梁启超根本不是从纯文学的眼光来审视文学的,“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也’”⑬,小说被他视为经史子集之外的第五部,这明显是违背文学事实的。他所偏重的也是政治小说中“政治”的部分,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梁启超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用世色彩明显,小说首先是政治文本,承载的也是政治功能。梁启超所接受的政治小说其实在日本已经过时,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政治小说的接纳,他取法的是政治小说在日本推进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既然小说曾经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那么在中国引进政治小说也是必要的。
梁启超推崇政治小说的立足点在于政治,属于一种新型的政教文学观,小说的高度政治化强加必然改变小说的性质和功能。首先,他通过捏造一个有违事实的文学史事件,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将欧、美、日等国“政治之日进”之功尽归于“政治小说”,推崇政治小说的功利性动机让其理论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文学作品会产生宣传效果,但绝对达不到他期待的效果,文学创作是艺术活动,让小说承担起救国的责任也难免有点言过其实,这会让小说不由自主地完全掉进政治的陷阱,现代文学的历史也一再证明这纯粹是一厢情愿。其次,他将中国社会政治的弊端完全推给小说,小说成了“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认为“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 “江湖盗贼之思想” “妖巫狐兔之思想”皆源自于小说⑭,中国民众精神的落后归因于小说,民间陋习的形成也是因小说,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也源于小说。这里逻辑的混乱和结论的武断自不必说,将中国社会的弊端归之于文学无疑颠倒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忽略了文学与国民性的互动。文学固然可以改造国民性,但国民性对文学的反作用似乎更大。中国社会问题的形成非因小说地位不高,既然地位不高又何来这么大的影响力?何况小说根本就不可能直接带来一个风清气正的文明社会。真实的情况却是“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后,民众并未从阅读政治小说中受益,小说也并未按梁启超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种阅读危机在其提倡政治小说时就已经埋下了,他原本就是希望利用小说的消遣功能来启蒙布道,能够吸引读者的也是小说中供人消遣的因素。难怪他在1915年发表的《告小说家》中失望地说, “观今日之所谓小说文学者”, “什九则诲盗诲淫”,或“毫无取义之游戏文”,国民性也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以致“近十年来,社会风气,一落千丈”。⑮再次,他只看到政治小说的作用,从政治教化的角度绝对化地否定旧小说,他认为才子佳人、神仙狐鬼等传统小说潜藏着腐旧的思想,抑制新思想的萌生。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甚至将《水浒》《红楼》视为“诲盗诲淫”小说⑯,这种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需要而否定古代小说优秀传统的做法显然是荒唐的。时人黄摩西、徐念慈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就多有批评。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又将其看得太重,小说好像成了“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模式”⑰。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谈及依靠小说进行社会改良、进化国民思想的说法未免“誉之失当”,指出小说并不足以“生社会”⑱。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曼殊)也敏锐地发现梁启超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严重错误,提出“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还是“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的疑问⑲。梁启超的小说理论陷入了“为论而论”的随机性,“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⑳,论小说则说小说可以“操纵众生”㉑,论报纸称报纸是“文坛之王”㉒,论学术则认定学术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㉓。可见,梁氏为了论述己见而不惜走极端,在文学问题上亦是如此,在审美与政治的冲突中,他往往牺牲了文学的艺术特性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其重视的是文学的政治功能而非审美功能,文学是因其具有实用价值被作为政治代言的手段,而不是文学创作自身的价值让其青睐有加。实际上,文学美感的削弱会严重影响到文学书写的整体形态。
二、王国维审美文学观的“无用之用”
当梁启超疾呼文学的社会担当时,王国维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与梁启超不同文学观,竖起文学非功利性的旗帜。同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积极主张应该维护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介入政治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艺术自律方向的发展路径。两人文学主张的对立虽没出现水火不容的对抗,但其观点的针锋相对,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史事实。在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纯文学”观念是从王国维这里启动的,他依托现代知识体系将文学从传统的学术文章的丛林中解放出来,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文艺的独立地位。王国维的文学观以超功利主义美学观为理论基础,认为审美对象具有“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超功利性,审美主体在观美、观物时也应抱有“决不计其利用”超脱性,这样才能发现“存在于美之自身”的审美价值㉔。在王国维看来,文学不是因为启蒙有价值,文学本身就是价值。这是对文学认识的一次飞跃,传统文论虽然也部分发现了文学具有与经学不同的形式特征和审美特性,但从未有人公开承认其独立地位, “文”从未改变附庸于经、史、子的仆从地位。王国维批评“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视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㉕。这段话明显指向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轻视文学的倾向。面对非文学非审美时代语境中道德、政治对文学的欺压和文学功利主义的巨大诱惑,王国维却卓尔不群地让文学卸下舆论宣传、政治鼓动的负担,运用西方的理论将文学解释成“游戏的事业”㉖,这一提法对于听惯了“文以载道”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观念革命和理论动荡,这种具有相当程度现代主义色彩的“游戏”文学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构成了现代文学新观念产生的动力源。但静思之,如果他把文学当成像古玩字画一样的个人情趣爱好而用来把玩,那么这种文学观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文学固然需要趣味,但如果走向唯趣味论,也就丧失了文学应有的价值,那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沉迷于艳情、苦情又有何分别呢?王国维一方面通过“游戏说”主张了文学的无功利,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是无利害关系的游戏,不过这种游戏能够起到慰藉心灵的作用,所以他又指出“诗人”虽把一切的外物都视为 “游戏之材料”,但 “诗人”是“以热心为之”的,所以这种游戏是“诙谐”与“严肃”两性质“缺一不可”,建立在“热心”和“严肃”的基础之上的游戏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消遣和儇薄的戏说㉗。另一方面,对王国维来说,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现象,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人们可以通过艺术的中介达致人生的慰藉和生命的救赎,他对“‘游戏’的理解和阐释,已经上升为自成体系的哲学观,成为近代最完整和系统的、与西方观念沟通的美学思想”㉘。从人的需要和文学的审美本质出发,他认为文学创作像游戏一样发泄人的剩余精力,转化人的生存欲念,升华人的嗜好。他的“游戏说”不是简单的生理快感,而是生命的美感和精神的愉悦,是站在人类生存学的高度拒斥政治、功名利禄对文学的随意造访,他心目中的纯文学是“超然于利害”而忘却“物与我之关系”纯粹的生命活动㉙。王国维的“游戏说”否定文学的功利性,这和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非功利化取向有着相同之处。
真正的文学不是反功利,但却需要适度的超功利。王国维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反对将文学视为谋取功利的手段,绝非不关人生痛痒,他同样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联。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他将席勒所定义的“人生”扩充为“自然及人生”,并指出“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㉚。敏感的学者已经可以从这样的表述中嗅出文研会“文学为人生”的气息,可见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的文学观追求的是利用文学直接“开发民智”,而王国维的审美自治则是在维护文学独立品格的同时去间接改变“国民之趣味”。在王国维看来,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提升则需要发挥情感的传导作用,文学则具有情感满足和情感升华的作用。他似乎想绕开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最终的立足点还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说改造世界的方式包括理论、宗教、艺术、实践等方式,启蒙的维度有感性、理性和神性的话,那么王国维显然更倾向于艺术的方式。他在中国传统儒家诗教乐教文学观和现代西方美学哲学中提炼出文学的感性启蒙作用,从而链接起审美无功利和文学启蒙的内在联系。因此,王国维的“无用之用”并非真的无用,而是无形的、永久的精神满足和情感升华。王国维纯文学观的提出,既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同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王国维的身上既有康德唯美的影子,也有尼采的忧心忡忡,或者说是对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中国化转述,并将之糅合进用文学进行感性启蒙的方案中。他的文学观是其悲观厌世人生观的投影,具有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他从尼采的悲观主义哲学的他者视野出发,认为人被无法满足的欲望所缠绕是痛苦,就算人生偶然“无一欲望”,但“空虚之感”又会乘机而生,人之所以思考“种种遣日之方法”,就是为了祛除“空虚之感”㉛,为满足欲望而奋斗是痛苦,满足欲望后陷入平淡的生活也痛苦。为克服这种生活之苦,王国维开出的解决之道是借助美术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㉜。即创作和欣赏艺术可以使人摆脱人生的欲望,暂时忘却人世的不幸,让人在闲暇时心灵有所寄托,所谓“感情之疾病”亦需以“感情治之”,文学之慰藉作用既可以“慰空虚之苦痛”,又可以“防卑劣之嗜好”㉝。王国维打通了文学与人生的联系,区别了文学 “游戏说”与传统的 “载道说” “消遣说”的关系,试图让文学艺术担荷起将人类从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的职责。可见,王国维并不完全否认文学的功利性,而且一个在实用理性教养下成长起来的传统文人是无法释怀其骨子深处的功利思想的。 “无用之用”的文学发挥着将人类带入美好境界的“大用”,他通过比较美术与政治的功效,极大地抬高文艺家的地位和文艺的作用,认为美术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的事业,明确提出政治家和实业家仅能解决生活之欲,其事业“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而如果哲学家与美术家所“发明的真理与其所标之记号之尚存”,那么人类的知识和感情在“千载以下,四海之外”仍能得其“满足慰藉”㉞,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之利益,文学家与以精神之利益”㉟。他认为政治家的功用不过为人类提供物质满足,这些东西并不能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文学所关注的则是普世的真理, “万世真理”可以让文学艺术拥有穿越时空的精神效用,在填补人的精神空虚、慰藉人的感情、升华人的灵魂方面是其他事业无法望其项背的。由此可见,王国维关注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效用,而是流芳百世的至高荣誉,探究“宇宙人生之真理”的快乐绝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㊱。
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内蕴着改造国民性、塑造着理想人格的永恒功利价值。王国维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在国运衰落之际不识时务地突然抛出纯文学观,而是对中国现状理性分析和对国民弱点深刻洞察基础上提出的。在《去毒篇》中,他虽谈的是鸦片之害,实际说的是拯救国民、国运之道,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问题。他认为国运衰败的原因,除去国家方面“政治不修”外,最重要的是国民方面内心“苦痛和空虚”,因此拯救之道不仅要“修明政治”,还要养成“国民之知识和道德”。他还特别强调用“宗教与美术”净化“感情”, “宗教”用于下流社会可以鼓 “国民之希望”, “美术”用于上等社会可以供 “国民之慰藉”, “兹二者尤我国近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㊲。不可否认,王国维在论述中存有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之分的阶级偏见,但毫无疑问,他仍然不自觉地注意到了文学的现实作用,是把文学作为治疗人类精神疾病的手段,认为“我国无固有之宗教”,美术也很“匮乏”㊳。尽管宗教和美术暂时都不足以担负起解决国民精神危机的伟任,但还是要依靠美术的力量给国人提供精神的栖息地,所谓“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㊴,而诗人的著作实为“全体人类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叫之声,随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㊵。在他看来,美术具有表达和沟通人类共同感情的神奇力量,可以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向上的火炬,虽暂时还很缺乏,但仍需大力提倡美术。
王国维虽然反对将文学直接应用于政治改革,可他并不反对文学艺术用于审美教育,因此在放弃文学的政教功能后却赋予了文学新的价值,转向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对生命的形而上追问。在《论教育之宗旨》中,他说“美之为物”能够让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㊶;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他谈到在观美时脱离“嗜欲之网”,则“吾人之知识已不为嗜欲之奴隶”,从而达到“无欲之我”㊷;在《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中,他称美术文学不但是“慰藉人生”的工具,而且是宣布“人生最深之意义”的艺术㊸;在《霍恩氏之美育说》中,他认为审美的感动能引导人“进于幸福之冥想”㊹。从王国维对文学作用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超功利思想并非铁板一块,他将文学艺术的功用与审美教育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学虽不像科学那样有直接的实用性,但也并非完全无实用性。在他那里,美育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可以成为智力发展、欲望提升、感情和谐的中介,最终可以培养造就有益于民族国家的健全个体。鲁迅就认为“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就不美了㊺。王国维在理论上将文学从现实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分离开来,摆脱功利性的负重,从而获得某种独立性,但他在强调文学超越功利的同时,并没有将审美悬置在空中,而是通过美育作用的发挥让文学贴近了现实。
三、梁启超文学观趋向王国维的理据
在中国文学的坐标轴上,梁启超与王国维的文学观并无守旧与激进的区分,他们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立场的冲突,不如说是政治家和学术专家之间的对立。两者的思想分野在于从文学上理解文学还是从政治上理解文学,对立的强调消弭了内在的重叠,这时他们的文学观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在改造传统“载道观”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改良政治的服务论,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来审视文学,将责任置于首位,文学至于一边,重视文学的宣传性,自然不可能过多关注文学的审美属性。在他的文学观中,文学要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倘失去与政治的联系,也就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对于纯文学虽 “意固有所属”,但又心非所愿。 “新民”的文学基点让他很难精心营构自己的文学殿堂,沉重的历史使命粘附在文学的翅膀之上,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现实急务让文学勉为其难地背负起国民性批判的历史命题和时代使命。因政治革命的需要将文学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是对文学非常态功能的借用,开启了“五四”时期革命文学的先河。对于王国维来说,他有强烈地捍卫文学的意识自觉,并积聚全部的生命能量伸张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内在规律。针对特定时期文坛上的政治偏至和传统视野下“哲学美术不发达”而发出纯文学的呼唤,所表达的是文学在常态下的效用,助益了后来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在文学创作问题上,王国维就曾言及“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㊻,用“诗人之眼”观照文学自会注意其恒久的艺术价值。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梁启超所注重的不是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文学的政治功用和社会效果,力倡具有鲜明救国色彩的民族功利主义文学观。不同的文学观体现了新旧交替、中西汇通的变动时代中具有不同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对不同文化思潮的择取和利用,两种观点的张力关系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梁启超通过提倡政治功利主义文学观强力抬升了小说的地位,赐予文学以载道之外的改造国计民生的伟力,最终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体系,让文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对象。王国维倡导的超功利纯文学观则为文学注入了鲜活的本体精神,反对文艺等同于政治,剑指封建文学观的偏执,矫正了功利论的狭隘,形成现代意义上文学自觉意识,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
在1897至1915年这段时间内,梁启超主要是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形象出现在文学舞台的,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㊼,政治优先于文学,或者说文学只是进行其政治事业的凭借。王国维既不是宣传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所以思考问题的视角自然不同。在梁启超身上则体现了政治家和文学家两种角色混演而导致的内部冲突;当他以政治家的身份思考文学问题时,比较看重文学的思想性和功利属性,社会功利性绝对地压倒文学自主性;当他以文学家的身份思考文学问题时,岗位意识的确立让他主动偏离政治,看待事物的眼光自然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艺术自律性反而占了绝对的上风。1917年梁启超退出政坛,尤其是1920年初欧游回来后,不仅其启蒙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其改造社会的功利性尝试被西方人的文明实践证明是一个噩梦,而且其文学思想也发生了质的转变——认为能够真正救拔人类的不是西方的科学而在于美, “便抛弃了以往以人为政的念头”,致力于“改造社会的文化工作”,从而进入从“春华转到秋实的新阶段”㊽。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到,人处世间,除了“衣食住” “安富尊荣”之外,还有“更大之目的”,欧美人之“高尚之目的”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者是“好美心”,而吾中国人“多言善而少言美”㊾。他在1922年发表的《美与生活》的演讲中,视“美”为人类生活诸要素中“最要者”。就这样,梁启超又无意中走进王国维式的用美改造来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上去了。由此看来,一时的言论并不能代表其文学思想的全部,地位、环境、时代的变化会不断突破其认识的局限。思想发生转变后的梁启超与文学家的王国维之间反而类似多余对立,文学思想交集的增多形成他们对文学理解的很多相通之处。比如王国维撰写《屈子文学之精神》,梁启超也有《屈原研究》;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推崇词人李煜、苏轼、辛弃疾、姜夔、纳兰性德等词人,而上述词家也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述的对象。文人同嗜可以理解,巧合的是两人在许多观点上竟然也惊人的一致。如梁启超在《屈原研究》把“实感”作为“文学主要的生命”,并以“实感”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认为“《三百篇》中写得好的作品都重实感”,文学之能事就是“从想象力中跳出实感”㊿。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品格》中,他又提出有个性的文学家要具备“不共”和“真”两个条件,强调要把作者的实感“绝无一点矫揉雕饰”,“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出来才算“真”〔51〕。两人在文学之“真”这点上简直是心有灵犀。王国维同样强调文学要真切地描写“真景物”,艺术地表现“真感情”,提出融合描写自然人生之实和主观态度之诚的 “境界说”,以“真”与 “不真”作为衡量古今文学兴衰的标准。他在《人间词话》中就指出:“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52〕
许多学者为了确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往往不惜剑走偏锋,一旦时过境迁,自己努力提倡的一切也化为常识后,反而能够主动检讨自身理论的不足。一旦言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对文学的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他回归学术时,学术态度的沉潜让他重新反思自身的文学理念,学术理性培养出来的学术品格引导他用“唯美的眼光”品文论诗,承认文学的美的“神秘性”的价值〔53〕,反对只重内容忽略审美的错误倾向,推崇“不计较利害观念”的情感的艺术〔54〕。远离政治后,在梁启超的眼里小说似乎也没有他前期所说的那么重要。在1915年撰写的《告小说家》一文中,他引用《汉志》中的话坦率承认小说作为“小道可观,致远恐泥”〔55〕,在他眼里小说身价已然一落千丈。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甚至说,如果不作文学家,根本就“无专读小说之必要”〔56〕,一样的小说却是不一样的态度。一个梁启超,前后期判然有别,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前期对小说的重视根本就没有仔细考量小说自身的规律,只是把它作为政论家宣传思想的利器。梁启超后期明显地抛弃文学的工具化取向,转向情感主义,注目于文学的审美,非功利性色彩增强,但并非就此判断他完全远离功利。 “为做诗而做诗”与“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诗”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梁启超努力调适审美与功利的冲突,将审美与民族精神改造联系在一起,通过文化涵养人性,实现更高的层次上的“新民”理想。他曾自述 “浚牖民智,熏陶民德”是其 “初志”,也是其“终身”贯之的理想〔57〕。
梁启超以“新民”为中心的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以“审美”为中心的超功利文学观是文学观念内部的对立,观点有别但并不截然对立,在某些重要的理论层面,他们又似乎不谋而合。这两种文学观共同传达了“时代精神的两个侧面,即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封建专制思想统治的民主主义要求,表现了20世纪初民族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因而两者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58〕。梁启超将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发动了晚清的思想启蒙运动,王国维追求文学独立建立审美现代性的纯文学观念,两人分别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维度上奠定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基础,推动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两种文学观在反对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上的立场和目标是一致的,超功利的纯文学追求文学的价值独立和审美自治,功利性的文学观亦要尊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但历史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将政治与审美完美融合的舞台,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不舍和艺术至上的推崇之间的矛盾交织共同促进着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两人之间的对立和相通也向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了“如何平衡启蒙与审美”这个超难的历史命题。
注释:
①⑦⑭㉑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5、33、36、34页。
②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刊》1902年11期。
③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④参见《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刘孝严主编《中华百体文选》 (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⑤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⑥梁启超:《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黄霖、蒋凡主编《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⑧ 梁启超:《〈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
⑨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绪言〉》,冯牧、柳萌主编《隔绝的残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⑩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⑪钱玄同:《寄陈独秀》,北京大学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⑫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王训昭、卢正言、邵华等编著《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郭沫若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⑬⑯任公(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1页。
⑮梁启超:《告小说家》,张正吾等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⑰摩西:《小说林发刊词》,黄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⑱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陈春生等选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⑲刘叶秋等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⑳㊽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3、75页。
㉒梁启超:《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㉓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㉔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㉕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㉖王国维:《文学小言》,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㉗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㉘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㉙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张燕瑾、赵敏俐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清代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83页。
㉚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㉛㉝㊲㊴王国维:《去毒篇》,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132、131、14页。
㉜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㉞㊱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㉟㊳王国维:《文学与教育》,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118页。
㊵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王国维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㊶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1840—1949)新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㊷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1840—1949)新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㊸王国维:《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席勒)》,参见陈鸿祥著:《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
㊹王国维:《霍恩氏之美育说》,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1840—1949)新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㊺ 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自编文集(二心集)》, 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㊻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页。
㊼吴其昌:《梁启超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㊿〔51〕梁启超:《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90页。
〔52〕王国维:《人间词话》,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5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张燕瑾、赵敏俐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通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54〕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王修智主编《民国范文观止》,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55〕梁启超:《告小说家》,朱一玄编、朱天吉校《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56〕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孔祥骅著《国学入门》 (第3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57〕朱正编著:《名人自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58〕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