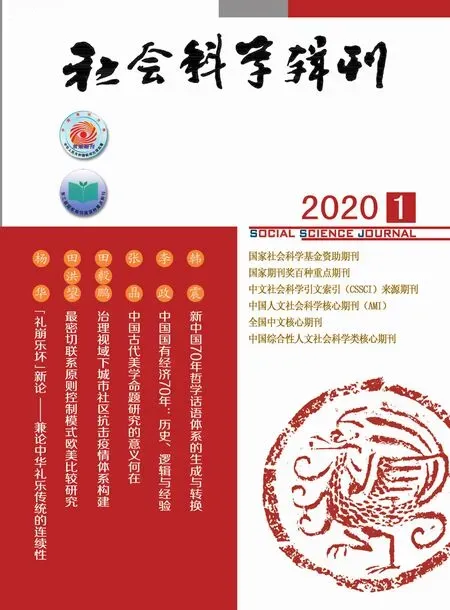从“自我”到“他者”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欧阳谦
实现从 “自我”到 “他者”所发生的现象学转向,列维纳斯有着非常直接和现实的思想动机。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的犹太人,作为一个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幸存者,列维纳斯的一生都被战争的极端暴力所困扰。让他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就是当道德被战争悬搁起来之后,“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究竟还有何意义?人类如何才能超越现实的暴力而走向伦理的正义?人类能够做到和平相处的道德基础究竟来自何处?当然,列维纳斯的暴力追问不只是围绕着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而是上升到了普遍性的暴力问题和善良问题,所以他极不愿意被人称为犹太思想家。他所提出的新现象学一方面为我们梳理了一种关于暴力的现象学分析 (即从自我学和极权主义哲学的观念逻辑出发去挖掘暴力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关于善良的现象学分析 (即从 “他者”和 “面容”的无限性出发去寻求善良的来临)。这种新现象学在融合和改造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罗森茨威格的 “新思维”和马丁·布伯的 “我与你”的哲学、犹太塔木德经和基督教伦理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之上,构想了一条人类走出暴力的伦理救赎之路。通过从 “自我”到 “他者”的现象学转向,列维纳斯极力推进了从先验论现象学到存在论现象学再到正义论现象学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一、自我学的现象学分析
在当代语境中,“奥斯维辛”不仅指称一座纳粹用来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而且还指向了惨绝人寰和骇人听闻的人类暴行。奥斯维辛这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梦魇,成为了人类浩劫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最极端和最根本的邪恶的象征,“据估计,被送到奥斯维辛的130万人中,110万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约有100万是犹太人……我们必须记得,超过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奥斯维辛被夺去生命,只因为他们在纳粹眼中犯有一种罪,那就是生为犹太人” 〔1〕。列维纳斯亲历了战争的噩梦,他被关押在战俘集中营时间长达5年,其父母和兄弟及其他亲属都死于纳粹大屠杀,其夫人和女儿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而四处逃难。这些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致使他无法不去思考伦理正义的问题。在 《艰难的自由》最后一篇题为 “签名”(Signature)的文章中,列维纳斯说他的所思所想“都受制于纳粹恐怖所留下来的预感和记忆”〔2〕。这种预感和记忆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他,并引导着他。他的两部代表性哲学著作 《总体与无限》和 《别样的存在或在本质之外》(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无疑都是关于战争和道德的反思。在 《总体与无限》的序言中,他直接指向了战争带来的道德危机,即战争不仅将道德完全悬置起来,而且让道德显得如此的荒谬。《别样的存在或在本质之外》的献词是为了纪念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同胞以及不同信仰、不同国家的数千万人,他们都是仇恨的牺牲者,都是反犹主义的牺牲者。列维纳斯的战争反思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着奥斯维辛之后整个西方的反省。诸多思想家们分别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视角去审视纳粹大屠杀的根源。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 《启蒙辩证法》,对于现代文明的野蛮行径展开了工具理性的批判。弗洛姆的 《逃避自由》和赖希的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堪称暴力心理学分析的经典作品。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着力于研究邪恶的社会性问题,他提出 “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3〕。当然,我们还可以读到汉娜·阿伦特的著述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她将恶看成是思维的缺失和泯灭,这就是恶的平庸性,也就是大恶能够成就的基础。依照德国学者萨弗兰斯基的分析,“希特勒意味着一次断裂。奥斯维辛成了一个负面的创始神话。隐藏在人类文明中的凶残和野蛮的力量史无前例地表明,一个深渊呈现了。自奥斯维辛以来,西方文化被打上虚无主义的记号……人们不再以完美的存在的观念,而是以道德地狱之可能的虚无来衡量进步”〔4〕。奥斯维辛之后所引发的道德虚无主义,一方面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幻灭感,导致了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批判思潮,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当代哲学思潮中特别显著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关于暴力的一种自我学 (égologie)分析,形成了列维纳斯独特的哲学反思进路。这条反思进路显然具有一种反自我中心主义、反同一性哲学、反智识主义的思想基调,体现了列维纳斯的暴力哲学的论证逻辑。他认为,西方哲学也可称为一种 “消化哲学”,这是因为其自我学的立场内含了暴力化的倾向。自我学总是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东西,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东西往往采取同化或者消灭的态度。在自律和他律面前,传统的西方哲学选择了自律,也就是说选择了自由。按照传统的哲学观念,哲学追求真理终究是为了达成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通过概念化和主题化的智识活动将 “他者”还原为同一,从而实现对于存在的征服。“这一还原过程并不表现为某些抽象的图式,而就是人的自我。一个自我的存在就是将多样性变成同一性。即使是发生了多少事情,即使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而自我还是岿然不动。自我、自身、自体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同被海浪冲击的岩石一般不受任何影响。自我通过把异类的和多样的情况变成一种历史即它的历史,由此做到始终如一。它开启了同一的同一化进程,它优先于岩石的同一性,因为它是构成同一性的条件。” 〔5〕简单地说,他将战争暴力和灭绝人性的发生与自我中心主义的诉求直接联系起来,目标直指西方哲学所固有的自我学。这种自我学也就是传统的同一性哲学。“我的认同——我是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就如同天然的熔炉而将他者(l’Autre)融化为同一 (Même)。因此一切哲学都是(借用胡塞尔的新词)自我学。” 〔6〕
在 《哲学与无限观念》一文中,列维纳斯还将这种 “同一至上”看作是一种哲学思维的 “自恋癖” (le Narcissisme),一种认知上的自我陶醉和孤芳自赏,如希腊神话人物那西索斯那般的自满自足。这种自恋癖往往会不断地自我膨胀,最后走向唯我独尊。尽管哲学思维总会遇到 “他者”(人和物所制造的种种障碍),但他终将克服这些障碍,这就是将 “他者”变得跟自己一致而不是对立。当心灵的独白成为普遍性并将存在的总体囊括于其中,“我思”就得到了自由。“这样西方思想常常排除超出自己范围的东西,将所有的他者并入同一之中,并宣称自律是哲学与生俱来的权利。”〔7〕对于 “我思”而言,所谓认识非我就是消除非我的他性,就是将陌生存在者的独特性变成一个主题或者对象,将其置于先验概念之下。概念的认知就在于抓住个别者和陌生者,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普遍性之中,“于是一切权力就从这里开始。人类的自由是借助于普遍性而让外在事物屈服于自己,这不仅仅是意味着对于外在事物的单纯认识,而且还是对于它们的掌握、驯化、占有。正是在占有中,我实现了对于多样性的同一化。可以肯定,去占有就是在维持被占有的他者的存在的同时又悬置了他者的独立性。在同一性哲学所反映的文明中,自由即意味着一种财富。缩减了他者的理性即代表着占有和权力”〔8〕。在传统的智识主义逻辑中,理解与权力是相互成就的关系。理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理解。
对于这种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在 《总体与无限》中得以充分地展开。列维纳斯循着自我学的逻辑路径,不仅批判了以自我化解他者的认识论逻辑 (涵盖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胡塞尔的传统),而且还特别地批判了从 “此在”(Dasein)到“存在”(Sein)的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逻辑。在他看来,西方哲学大多是一种存在论,即通过对存在的普遍化理解而将 “他者”还原为同一。认识就是同一性的展开,就是去除差异性,就是消除存在者的抵抗,“因此苏格拉底的真理理想就是立足于同一本质的自足之上,立足于它的自体的同一化之上,立足于它的自我主义之上。哲学是一种自我学”〔9〕。即使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也还是预设了同一的优先权,预设了自由的优先性,最终还是要把 “他者”还原为同一。自由的本质就是维持自身而反对 “他者”。对于 “他者”的主题化和概念化,不是与 “他者”和平相处而是消灭或者占有 “他者”。作为第一哲学的存在论实则是一种权力哲学。 “权力哲学,存在论,作为从不质疑同一的第一哲学,其实是一种非正义的哲学。” 〔10〕这种哲学不可避免地会导向一种不一样的权力,导致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专制。对于哲学而言,“他者”与同一的冲突,可以通过将 “他者”还原为同一而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在实际生活中,“他者”与同一的冲突是由国家共同体来消解的。在国家总体性的专制压迫中,战争乃是不可避免的。
列维纳斯试图从西方思想一贯的自我学中找出暴力的因子,从自我主义滋生的 “消化哲学”中找到帝国主义的根源。他明确地将存在论与权力哲学联系起来,或许这可以解答海德格尔一度加入纳粹党并对大屠杀保持沉默的所为。让列维纳斯完全无法释怀的是,这位深刻的哲学家怎么会接受法西斯主义并加入其中?怎么会对犹太大屠杀无动于衷?在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思想并没有摧毁传统西方哲学,反而是对整个西方哲学倾向的总括,这就是自我学的总体化倾向。这种总体化以追求大写的一为宗旨,因为排斥差异而严重缺乏 “他者”的维度,其特征就是缺乏对于无限性的敬畏。“此在”的有限性并不是在无限与人类有限存在的距离之中发现的,而是植根于“此在”向死而在的有限存在中。由于 “此在”是自我封闭的,它并不会遇到质疑其自由活动的“他者”。由于 “此在”的自由完全缺乏一种伦理的原则,这样就会走向纳粹主义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度野蛮。当海德格尔后期批判技术的本质时,他忘记了纳粹主义代表的现代罪孽的根源还有比技术更深层的东西。德里达对列维纳斯的这一论证给出了非常精要的概括:“由于现象学与存在论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恐怕它们会变成一些暴力的哲学。而通过它们,整个哲学传统恐怕也会在意义深处与同一的压迫和极权主义沆瀣一气。” 〔11〕
哲学作为一种自我学,其追求的真不过是自我所确立的真。如果说这种真是一种超越了意见的知识,也不过是一种排除了差异和多元的知识。列维纳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撰写的 《关于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一文中已经指出种族主义的所作所为乃是一种妖魔化 “他者”和追求纯粹同一的暴力行径,已经开始预感到存在论的帝国主义所带来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后果。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人的攻击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 (如精神分析学的本能学说)来解释战争和暴力的话,那么面对希特勒主义、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泯灭人性的历史事件,也许就会有些难以应对。如果根据列维纳斯关于自我学及其同一性逻辑的分析,其结果很容易说通。“施暴者是不会走出自身的。他只会夺取和占有。占有就是否定独立的存在。占有就是不肯给予存在。暴力是一种霸权,但也是一种孤立……认知就是理解,就是掌握一个对象——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就是抓住一个东西…… ‘认识你自己’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的箴言,那是因为西方人最终是在自身中发现宇宙的。” 〔12〕
二、面容与 “他者”
如果说列维纳斯对于暴力的自我学分析构成了一种恶的现象学,那么他对于 “面容”与 “他者”的现象学分析,则构成了一种面容现象学,也可以称之为善的现象学。“面容”(visage)作为一种 “临显”(épiphanie),“可谓是三位一体,既有神学性也有诗学性,但首先又具有哲学性”〔13〕。无限和 “他者”所具有的不可知性、不可见性以及不可衡量性,都汇集到了面容上面。首先,面容代表着 “他者”的意义,也代表着伦理的意义,它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存在的意义是在彼处的,是在高处的至善召唤。它既不在周围世界的视域中,又不在历史的总体化之中,“我不是说他者就是上帝,而是说我在他的或者她的面容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14〕,“面容是暴露出来的和受到威胁的,它似乎在诱导我们实施暴力。但是面容同时又在阻止我们去杀人”〔15〕。作为一种命令和恳求,面容显示出其神圣性的意义。面对他人的面容,是我们聆听上帝声音的方式。其次,面容是超概念的,是我们无法用表象和图像来解读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种族和人群,不属于任何的形式和分类。不是说我们在与 “他者”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的眼睛的颜色就算是看清了他的面容。面容是一种示意,其意义无法用眼睛的颜色所涵盖,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对象或者一种内容,而让你的思想能够完全把握。面容是无法用概念来把握的,它只是在引导你去超越存在。事实上,面容的含糊性就在于它一方面在临显,另一方面又在隐退。面容既显现又不显现。面容是感性的,同时又是超越感性的。面容不仅是在凝视也是在说话。然而那些试图表达面容的语言,又是在伤害面容,因为语言无法抓住面容的那些无限的踪迹。最后,为什么说我们与面容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伦理的关系?与面容碰面,不是认知式的和对象式的占有,而是需要超越认知的应答和担当。面容始终在排斥同一性哲学的总体化逻辑,它拒绝被包含和被把握,它保持着超越性和陌生性,“面容拒绝占有,拒绝我的权力。在它的临显中,在它的表达中,那些可感觉到的和已察觉到的东西是完全抵制把握的” 〔16〕。
对于如何解除暴力的问题,列维纳斯提出了一种面容抵抗的现象学分析。与我们惯常遇到的自我同一性实施的暴力抵抗不同,“他者”的面容向我们显示出一种伦理的和非暴力的抵抗。面容的矛盾性表现在,它一方面是在发出命令,另一方面又在发出恳求。就像是主人向 “我”说话,面容发出 “你不能杀人”的命令,是因为它的高高在上而将 “我”变成了倾听者和服从者。它教给“我”从未知晓的许多新东西,因此它成为了“我”的老师。作为 “解除了武装的权威”,这位老师将 “我”的主体性从主动的 “我”变成了被动的 “我”。此刻,“我”不再是万物的尺度,而是反过来成为了被裁决的。“他者”在面容中朝向“我”,但是其超越性不能被 “我”的表象所吸收。“我”只能倾听着 “他者”对于正义的呼唤,并确立起自己的责任,“面容召唤我去担负起我的义务,并且对我进行审判。在面容中表现出来的存在者有一种高度,有一种超越性的维度,它作为陌生者并不与我对立起来,如同障碍物或者敌人一样” 〔17〕。
与此同时,面容又表达出一种卑微和恳求,在其不幸和饥饿中唤起 “我”的责任。 “他者的面容是赤贫的。正是这种贫困向我要求我能够做的和我所欠下的。对于我而言,无论我是怎样的情形,我作为 ‘第一人称’都是它所寻找的应答之人。” 〔18〕正是在 “我”与绝对的 “他者”的亲近中,与穷人、陌生者、无家可归者、孤儿寡母的亲近中,“我”不得不担负起责任,不得不做出无条件的应答。正是因为 “我”处于这种人质状态,在这个世界中才会有怜悯、同情、宽恕和亲近,甚至才会有 “先生,你先请”。人质的无条件性并不是团结的限度而是团结的条件。 〔19〕当 “我”服从于善良,“我”就会成为他人的 “替代”(substitution),这就如同格罗斯曼在 《生活与命运》中所描写的那位妇人的善举: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递给了饥饿的德国战俘。当 “我”不是用知识的暴力来抓住和同化面容,而是在有限性中生出一种无限性的观念,那么在 “我”的意识中就有了绝对的 “他者”的溢出。这种意识的溢出将为“我”的心灵提供新的面向,这就是欢迎的面向、赠予的面向、慷慨的面向以及好客的面向。〔20〕
在列维纳斯看来,面容之所以是伦理关系的诞生之地,是因为面容打开了原初的话语。这种话语作为非暴力,维持着 “他者”的多元性,因而带来了和平。“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而是由“他者”的 “他性”所显露出来的不解之谜。伦理学就是由 “他者”的在场对 “我”的自发性产生质疑而确立起来的。伦理关系或者伦理经验是因为自我与 “他者”的相遇而生的。因为伦理经验是超越存在的,同时也是超越自我的,因此伦理学应该是先于存在论的。列维纳斯为此提出 “第一哲学是一种伦理学”〔21〕。战争和大屠杀给列维纳斯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而且是永远做不完的思想作业:究竟是知识第一还是伦理第一?究竟是自由优先还是正义优先?列维纳斯相信只有当我们跳出自我的 “洞穴”而成为伦理主体,即成为为他的责任主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指望人类永久和平实现的那一天。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启蒙伦理学之所以陷入了困境,是因为“人的本质并没有为理性共识提供任何稳固的支点——使得一种普遍伦理学得以由此建立”〔22〕。列维纳斯的伦理形而上学,不是诉诸普遍的理性主义原则,也不是简单地求助于人性的自然本质或者制度驯化,而是指向超越性存在的欲望,即人类对于走出恶的存在的伦理追求。当列维纳斯如此形容 “伦理学是一种精神光学”〔23〕时,我们似乎可以从他关于面容抵抗的现象学分析中找到答案。列维纳斯认为,伦理正义是由 “他者”的“在场”(présence)而引发出来的对于自我存在的自发性的质疑。从 “他者”的面容引导出来的应该亲近 “他者”的责任和义务,由上帝的 “他性”(illéité)所召唤出来的超越自我的欲望,如同一道爱之光穿透被暴力笼罩的黑暗世界,由此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是一种精神光学。列维纳斯之所以说到 “我们需要一个我们时代的特蕾莎圣女”〔24〕,这是因为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作为善良和爱的化身,确实具有一种照亮人心的示范作用。
三、无限与正义
奥斯维辛之后,人类关于至善终将胜利的许诺,似乎很难再让人坚信。在 “神正论”似乎已经终结和上帝已经死去的这个时代,在这个充斥着极权和压迫的暴力现实中,人类还有走向善良和正义的可能吗?或者说康德提出的人类永久和平只是梦想吗?奥斯维辛之后,只要我们还坚持至善的乌托邦,那么伦理正义还是有可能的,这是列维纳斯的基本信念。如果没有至善和正义的乌托邦,人类的伦理生活就一点可能都没有。在道德失败之后,我们还能够高谈道德,那是因为我们依然没有放弃西奈山上的上帝。当然,这个上帝不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伦理正义的诉求,作为一种 “别样的存在”而闯进非正义的现实之中的,尽管 “上帝被剥夺了在场的客观性和存在。他再也不是客体,也不是一场对话中的交谈者。他的远离或他的超验转动在我的责任心中:彻底意义上的非情欲……责任心总是起着作用,而要是没有这种责任心,上帝一词恐怕也不会出现”〔25〕。上帝的非实体性和非现实性也就是他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就是对于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欲望和希望。伦理生活是一种走出自我的生活,是一种超越存在的精神生活。
如果说存在论是从自我出发而走向了总体暴政的话,那么伦理学则是要回应 “他者”的质疑和服从面容的命令,从而走向 “无限的好客”。这是因为存在论的目标始终是认知、占有、掌握、垄断,而伦理学坚守的是质疑、批判、关切、超越。伦理正义不能立足于传统的 “自我人道主义”之上,而只能建立在一种 “他者人道主义”之上。理性的本质不在于为人的安全提供基础和权力,而是对人提出问题,召唤他去面对正义。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活动,必须从感觉和良知开始,这就是从质疑自我主义的同一性开始。真正的道德意识来源于无限性观念。人类身上有两种无知:一种是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遭遇 “他者”和无限的结果。一种无知会带来自负和狂妄,另一种无知则带来敬畏和责任。只有承认我们自身的有限和局限,只有亲近 “他者”和饥饿者,才能有对 “他者”的无限责任。哲学的任务是去倾听 “他者”的声音,去关注那些超越性的存在。存在是多元化的,是分裂为同一和“他者”的,这就是存在的基本结构。我们不可能使相互独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总体化,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没有关系的关系”。伦理先于自由而潜入到自我之中。在人最原初的生活经验中,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世界的外在性,也就是“他者”的无限性和不可同化性。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处理与 “他者”的关系是最紧要的,所以伦理是第一位的。关于道德的起源和基础,列维纳斯既不像康德那样依赖于 “理性的希望”,也不像功利主义者那样立足于 “利益计算”。在他看来,伦理学讲的是自我与 “他者”的关系,而不是一整套什么原则,“如果没有与他人之关系,如果没有对他的形象打出问号,那么对自我本身提出问题的可能性,灵魂与它自身展开的神奇对话,是永远也不可能的”〔26〕。
道德意识不是一种价值的体验,而是与外在存在的一种接近,“他者”就是这种外在存在的一个绝妙说法。在列维纳斯的语汇中,“他者”不是一个知识化的、存在论的概念而是一个道德化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这是因为 “他者”是在存在之外的,是比存在更好的,是超越了本质的,一句话是不可主题化的。它像是 “非存在”,如同寂静无声的黑夜,我们伸手不见五指,但又隐约感觉到什么东西,即匿名的存在,或者说是没有存在的存在。也可以说 “他者”传递着 “神秘”“踪迹”“差异”“多元”“无限”,所以也是我们能够接近上帝的唯一途径。在列维纳斯的论述中,“他者”既表现为他人 (小写的 “他者”),诸如邻人、陌生者、穷人、乞讨者、孤儿寡母等,也表现为上帝 (大写的 “他者”),即作为欲望和希望的无限,或者绝对的 “他者”。与传统哲学的同一和总体相对应,“他者”指向的是非同一的和非总体的超越性或者外在性。在一篇题为 “他者的亲近”的访谈中,列维纳斯这样说道:“我所讲的第一哲学是指一种对话哲学,这种对话哲学只能是一种伦理学。即使是追问存在意义的哲学也是离不开与他者的遭遇的……所有的思想都要从属于伦理关系,从属于他人身上的那种无限的他性,从属于我所渴求的那种无限的他者。” 〔27〕
从无限走向正义的伦理之路,就是由为他的责任所铺就的。如果说胡塞尔强调的是先验自我对于真理的责任,海德格尔关注的是 “此在”对于本真性的责任,那么列维纳斯在改造和翻转了存在论现象学之后,指向的是对于 “他者”的责任。这个为他的责任是完全不对称的,即 “我”对 “他者”负责是不求回报的,不是互利互惠的。“我”对 “他者”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我”不能拒绝这一责任,甚至 “我”还要为 “他者”的责任负责,直至 “我”成为“他者”的人质和替代。这里,列维纳斯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长篇小说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段话:“我们所有人都对人类负有责任,而我比其他人负有更多的责任。”保罗·利科认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过于夸张和极端,“根据 《整体与无限》,他者不是任何一个对话者,而是一种正义的老师类的范式形象。在此意义上,说话 ‘总是在教导’的论断是夸张的。这种夸张既是对高度的夸张,也是对外在性的夸张”〔28〕。《别样的存在或超越本质》比夸张走得更远,那就是极端甚至是骇人听闻,用 “我”替换 “他者”,伦理主体变成 “他者”的人质。“他者”不再是正义的老师,而是成为了冒犯者,“他者”要求道歉和赎罪的举动。在保罗·利科看来,“胡塞尔与列维纳斯之间的这一碰撞向我们暗示了,把从同者到他者的运动和从他者到同者的运动视为辩证地互为补充,这并不矛盾。其中,一个是在意义的认识论向度上展开自身,另一个则是在命令的伦理向度上展开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这两个运动并不相互取消” 〔29〕。
列维纳斯明确说道:“我的任务并不是为了构建一种伦理学,而只是在于发现伦理的意义。”〔30〕事实上,他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思考伦理的意义来重新探讨社会正义问题。走出恶的存在,去拥抱善的正义,这应该是他的伦理乌托邦所指。他力图走出传统哲学及其认识论逻辑,展开了关于人类和平的别样思考。在他看来,对于人类而言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自由而是正义,不是知识活动而是伦理关系。就列维纳斯的面容现象学及 “他者”伦理学而言,他似乎提出了一种实现人类伦理正义的观念路径。然而,这条路径不禁让人看到他过于理想化的因而是乌托邦的伦理形而上学逻辑。列维纳斯其实也看到了这种伦理乌托邦的颜色,只是他相信,尽管特蕾莎修女所代表的博爱的星光十分微弱,但这点星光依然可以折射出善意的力量。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自觉遵循着 “先生,你先请”的基本礼节,把你手中的面包递给饥饿者,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走向伦理正义的一点星光。因此列维纳斯的道德理想主义看似远在天边和虚无缥缈,但却又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善良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