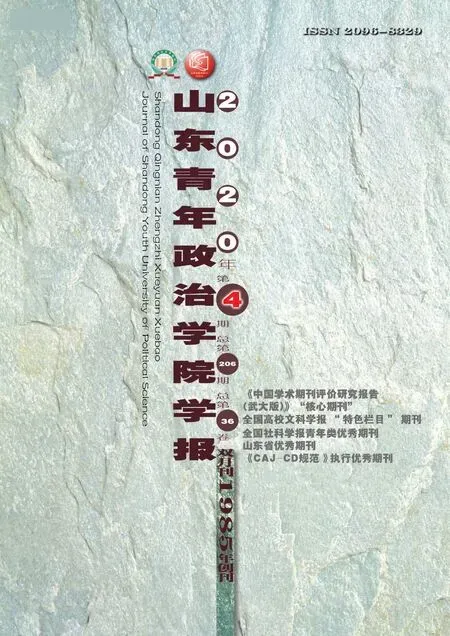庄骚融通视野下钱澄之的屈骚阐释
朱华英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州 510665)
在有清一代丰富的屈骚笺注史料中, 往往暗含着中国诗学阐释传统中的重要理论命题。清初钱澄之的屈骚阐释游走在诗学、易学、庄学之间,庄与易因时而相合,屈与诗因性情而相连,易与诗因为感应而相通,钱澄之以庄解骚、以易解骚的阐释视野,依托于他的庄学、易学宏大的学术研究背景,并且以一种深刻的比较意识,凸显了其屈骚阐释的学术新路。钱澄之的屈骚阐释,为整个清代楚辞诗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垂范意义。
钱澄之(1612—1693),原名秉橙,明亡后改名澄之,字饮光,号西顽,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的学者,诗人,抗清志士。钱澄之是明代遗民群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员,他生逢明清易代的乱世,其个人命运随着整个家国和时代的命运而跌宕起伏,被打上了深深的易代之际的时代烙印。可以说,明末,他是读书济世的志士;入清,则为客隐著述的遗民。在明清社会裂变的历史时刻,作为遗民,他坚守民族气节,入清不仕,一生颠沛流离,坎坷穷苦犹如屈子。晚年则归隐桐城故里,以遗民自处,专心著述,号田间诗人。钱澄之一生著述甚丰,有《田间易学》十二卷、《田间诗学》十二卷,另有《田间诗集》、《庄屈合诂》、《藏山阁诗存》、《所知录》等作品传世。其中《田间诗学》、《田间易学》被收入《四库全书》,《庄屈合诂》被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存目”,《庄屈合诂》是钱澄之晚年隐居田间时期的力作。
一、“庄屈无二道”:钱澄之庄骚融通思想的提出
庄子与屈原在性格、处世态度、人生忧患意识以及因理想之未能实现而产生的哀怨之情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清人胡文英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代表性的论述 :“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1]唐甄在《庄屈合诂·自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庄子与屈原,就如同“桂”与“檗”两种药物,“桂”热而“檗”寒,二者的药性是正好相反的。
但颇有意味的是,庄屈之间如此明显的差异,在明末清初庄骚兼治的学者群体的著述中,却不约而同地消失了。这一时期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庄与骚和庄与屈在“同”的基础上的融通。他们对庄、屈关系的论述思路,基本上是由庄及屈或是庄、屈并重,出现了“庄屈合诂”与“庄骚并称”的现象。 陈子龙在《谭子庄骚二学序》中较早表达这一阐释倾向,他认为:“予常谓二子(指庄子与屈原)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于死,或返于无何有之乡,随其所遇而变尔。”[2]陈子龙的观点核心点在于将庄屈均视为“才高而善怨者”,显然忽视了二者的重大不同。正如业师刘绍瑾先生所言:“这一说法却忽视了庄屈之情的重大不同。二者对人生忧患、痛苦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陈子龙所说的那个‘随其所遇’,而是决定于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3]在明末清初的治骚学者群体中,这一阐释倾向经由后来者的补充却愈发集中凸显。觉浪道盛、方以智、屈大均、刘命清学者都将庄屈并称,并尝试从思想精神层面挖掘二者之间的“同”。方以智提出“怒怨致中和”,屈大均提出“天人一贯”,陈子龙提出“庄屈皆本于‘怨’”等等,这些学者的庄屈关系之论,虽然有不同的生成背景,却体现了极力将庄骚融通的学术共性。
钱澄之首次将《楚辞屈诂》和《庄子内七诂》合二为一,题为《庄屈合诂》,钱澄之的《庄屈合诂》是这一时期庄骚融通视野下对屈骚进行阐释的典型代表,《庄屈合诂·自序》中,首先提出“庄屈无二道”的观点,其文如下:
或曰“庄屈不同道”,庄子之言,往往放肆于规矩绳墨之外,而皆为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为,固庄子所谓“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者也”。子乌乎合之?吾观庄子述仲尼之语曰:“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曰:“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而终勖之以‘莫若为致命’。”夫庄子岂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义、命自处也,审矣。屈子徘徊恋国,至死不能自疏,观其《远游》所称,类多道家者说,至卒章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太初而为邻。”而太史公称其为:“蝉蜕于浊秽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亦诚有见于屈子之死,非犹夫区区愤激而捐躯者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可以死节也。吾谓《易》因乎时,《诗》本乎性情,凡庄子、屈子之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为之也。庄子之性情,于君父之间,非不深至特无所感发耳。诗也者,感之为也。若屈子则感之至极者矣,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之《易学》、《诗学》无二义。[4]
钱澄之以庄解骚的阐释理路迂回而复杂。他先从“庄屈不同道”谈起,认为庄屈不同道的根据是二者迥然不同的文风和行为选择。庄子之文“放肆于规矩绳墨之外”,其行为逍遥自适;而屈原则言行谨守法度,表现出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且最终选择以死殉义,可以说庄屈二者迥然不同。
但钱澄之却独具慧眼,他看到了庄子思想中也有同于屈子的“亲君义命”之伦理纲常。同样,屈原的“徘徊恋国,至死不能自疏”,也非常类似于庄子寻求远游出世之思想。在此基础上,钱澄之指出,庄、屈皆为性情深至之人,所以他们的作品感慨良多,文风奇幻,同样充满着愤世哀怨之情感,而二者之所以结局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不同而己。庄与易在因时而相合,屈与诗因为性情相连,易与诗又因为感应而相通,通过这样的逻辑链接,钱澄之第一次从理论上完成了庄骚之间的会通。
二、庄骚融通视野下钱澄之庄骚阐释的基本理路
钱澄之以庄解骚的阐释视野,依托于他的诗学、易学的宏大的学术研究背景,将屈骚置放于与庄、易和诗的对比之中,凸显出一种深刻的比较意识,现将钱澄之在这一视域下屈骚阐释的学术理路梳理如下。
(一)庄本于易
钱氏出身于易学世家,其在易学方面造诣颇深,受时人所推崇,钱氏六十岁时著成《田间易学》,庄本于易,正是他在深谙易理的基础上提出,这一观点成为庄骚会通的逻辑起点,庄本于易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钱澄之认为,其前提是“易道惟时”:
自庄子以诗书礼乐及易春秋列为道术,后遂有六经之称。而其称易也,曰:“易以道阴阳”,则一语抉其奥矣。吾观其书,其言内圣外王之道,则一本于《易》。夫《易》之道,惟其时而已。庄子以自然为宗,而诋仁义,斥礼乐,訾毁先王之法者,此矫枉过正之言也。彼盖以遵其迹者,未能得其意;泥于古者,不适于今。名为治之,适以乱之。因其自然,惟变所适,而《易》之道在是矣。[5]
钱氏认为,“时”是易之道的核心,“夫《易》之道,惟其时而已。”关于易经中时与趋时的概念,它的本义是易传“爻位”说的一种,意思是卦象之吉凶因所处时机而不同。钱澄之则把它推广开来,认为一切事物皆因时而动,“因”和“时”便成为钱氏解释易道的一个关键点。在钱氏看来,与“时”相对的是“变”,没有“变”就无所谓“时”,所以“变”成为知“时”的重要判断标准,“惟变而后其道德和以顺,不变则成为乖戾也,惟变而义以理,不变则不能各得其所宜也。穷理者,穷其变也。尽性者,尽其变也。至于命,则一任其自然,变而不知其所以变也。”[6]
那么易与庄的相通点在哪里呢?钱澄之认为:
《易》之道尽于时,《庄》之学尽于游。时者入世之事也,游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古德云:“我本无心于事,自然无事于心”。斯妙得游之旨乎?七篇以《逍遥游》始,以《应帝王》终。谓之“应”者,惟时至则然也。又曰:“应而不藏。”此其所以为游,此其所以逍遥欤![7]
庄子的逍遥之“游”的思想,其核心在于“出世”,“游者,出世之事”,但是,庄子虽自命逍遥,钱澄之却仍然认为:“若庄子,固有用世之志,有用世之学,惟世不可用,而始托为无用之言以藏其身者也。”[8]这说明庄子选择逍遥游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原因并不在于其无用世的理想与抱负,而是因为其身处战国之乱世,用世之学无法实行,“生非其时”,所以才 “落得无所可用”,所以,钱澄之用“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 ”来概括庄子之“游”的真正精神。钱澄之认为,庄子内七篇虽然统于“游”,无论其入世与出世,都始终贯穿着“因时而变”的主旨,其实是庄子顺应时势所作的不得已的选择,具体是出世还是入世都因时而定,该死时求死,该生时求生,如果生时求死,死时贪生,皆为不知时。由此可见,《易经》中的因时通变之道已然在于其中。
钱氏特别指出,如果不知时,潜亢异用,那么不仅不足以知庄子,甚至还是“庄子之罪人”。
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惟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计,皆庄子之罪人也。若庄子适当其潜者也,观其述仲尼、伯玉教臣子之至论,使为世用,吾知其必有致命、遂志之忠,为其于君亲义命之际所见极明耳。潜者隐遁,亢者用世。潜亢各有其时,该隐遁时即隐遁,该用世时即用世,是谓知时。[9]
在钱澄之看来,庄子看上去是似乎抵斥仁义礼乐,而实际恰恰是遵循易之道:“夫《易》之道,惟其时而已。庄子以自然为宗,而诋仁义,斥礼乐,訾毁先王之法者,此矫枉过正之言也。彼盖以遵其迹者,未能得其意;泥于古者,不能适于今。名为治之,适以乱之。因其自然,惟变所适,而《易》之道在是矣。”[10]钱澄之认为,庄子看起来似乎与儒家的入世有所不同,他要诋斥仁义礼乐、訾毁先王之法,而实际上这都是庄子本人因时而变之举。就本质而言,庄子所效法的“自然”就是“惟变所适”,这一点也与《易》之道相通。
无论庄子《逍遥游》中的出入世之法;或是《齐物论》中的穷则变,变则通,或是《大宗师》论圣人之学乃是安时处顺、无所不因,或是《应帝王》意为因时而应居帝王之尊,庄子内篇随处可见庄子本人所崇尚的随“时”而动的行为标准,这一切均是庄子“深于《易》”者的表现。由此可知,儒者所一再批驳的庄子之避世,实际是其亢潜因时而变的“知时”。
(二)屈继于诗
屈骚与诗经之间不但有着极深的渊源,而且在钱澄之看来,屈继于诗还源于二者在诗学层面的“以感相通”。所谓“感”,就是要求诗歌要具有发人至深的情感。有感而发,抒写性情,这是钱澄之诗学观最核心的内容,“诗也者,性情之事也。”性情不仅仅是钱澄之自身诗歌创作的理论追求,也是他衡量诗歌创作的首要标准,《庄屈合诂·自序》中他对屈骚有这样的评价:
屈子忠于君,以谗见疏,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
钱氏认为,在抒发性情上,楚骚延续了自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屈子“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其文中蕴含着屈原在自身的美政困局中有感而发的深情。屈子行文为诗、沉江自逝无不是他至情至性的例证。因而,在这一点上,钱澄之断言:“庄叟似能明《易》义,《楚辞》直可号《诗》余。”
在钱澄之的整个屈骚阐释的过程中也贯穿着以“感”论诗的思路:如《离骚经》诂曰:“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谗,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九歌》诂曰:“《九歌》只是祀神之词,原忠君爱国之意,随处感发,不必有心寓托,而自然情见乎词耳。”《天问》诂曰:“屈子满腔疑情,凡人世相习而安之事,皆不可解。”屈骚之所以能够继承《诗》的传统,就是因为二者皆为“性情深至”之作,钱澄之在“以感相通”的基础上,将《诗》、《骚》连缀为一。
(三)易通于诗
庄本于易,屈继于诗,那么庄屈之间融通的最后的一环便是易和诗之间的关系。钱澄之认为诗通于易,其基础是:“《易》无体,以感为体。”[11]“圣人即《咸》四爻明感应之理以见天地人事,尽于感应,非区区人己之间此感而彼应也。凡学问之尽其事者,谓之感;有其效者,谓之应。殊途百虑,极其思虑之用者感也。所谓往者,屈也。同归一致,不思不虑而得者应也。所谓来者,伸也。往来本自然一定之理,安用憧憧哉?”[12]易无体,以感为体,这里的感并非传统易经所言的主体的主动行为获得的象的对应行为的过程,而是被钱澄之扩大为所有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天地人事包括学问学术,相互之间的基础都是感应,正如周易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交而万物通”,是感应将天地人事连结在一起,万事万物的存在之道即为感应,而易是对世间万物存在模式的全方位模拟,所以《易经》所谈主要内容即为“感应”。
而为诗之道,其精髓和要领也在于感应,“诗有音,感而成音”,“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感所致,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钱澄之认为判断诗歌好坏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有感而发,“彼无所感而吟者,无情之音,不足听也。是以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13]无感而发的诗歌,是不足听的无情之音。这样诗和易又在感应的层面完成了汇通。
至此,我们发现,钱澄之的屈骚阐释游走在诗学、易学、庄学之间,庄与易因时而相合,屈与诗因为性情而相连,易与诗又因为感应而相通,这样一来,其诗文中因都表现了至情至性的性情和因时而亢潜异处的庄子和屈原就在钱澄之庞杂的学术体系下完成了“庄屈无二道”的理论上的会通。所以,钱澄之“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之易学、诗学无二义也。”这样,庄、屈、诗、易在钱澄之的学术体系下,以一种非常清晰的内在关联,整合为一个大的学术回环网络。
三、钱澄之屈骚阐释中“庄”、“骚”融通及其意义
以钱澄之为代表的治骚学人们为何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意欲泯灭庄、屈之差异、极力将二者融通进行阐释的阐释倾向呢?这的确成为清代屈骚阐释史上非常值得追问的一个现象。
钱澄之将庄屈合二为一进行诂之,这与其说是钱澄之晚年体现在学术层面上的意义创见,不如说是其蕴蓄一生的遗民心迹的外在表白。钱澄之的前半生怀揣着与屈原一样的远大理想,本着和屈原一样对于故国君父的深至性情,经历了与屈原一样的九死一生与痛苦磨砺;其后半生,失志于时满腔的用世之志也只能如庄子一样因时而潜藏,在藏世与死节之间,钱澄之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矛盾纠结和难言的苦痛。一方面,钱澄之弘扬屈原是死节的志士,另一方面,作为前朝遗民,他固守气节而潜藏于世,等待反清复明的历史时机,然而,江山易代依然成为定局,回天无力,著书立说中,他欲意为自己藏世遗民的身份与行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合理解释。在钱澄之看来,虽然庄子内七篇统于“游”,但其中之入世与出世,都始终贯穿着“因时而变”的主旨,其实是庄子“生非其时”,“落得无所可用”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藏世的庄子与死节的屈原在入世精神与救世情怀的“性情深至”上是一致的。《庄屈合诂》中,庄骚在精神层面的会通也是这一时期钱澄之易代之际遗民心态的流露。
所以这一时期屈骚阐释中的庄骚融通之视野, 透露出以钱澄之为主要代表的明末清初的遗民学者特殊的生存困境与在此生存困境下诞生的遗民情思,庄屈合诂的诗学阐释共性背后映照出的是遗民群体的内心世界,是遗民心境的一种展露与表白,钱澄之的遗民气节也在这样的层面得到了一种学术性的演示。以钱澄之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屈骚阐释也正因为有遗民群体的生命情感的介入而具有了其它时期所无法彰显的独特诗学与美学品格。
钱澄之的“庄屈合诂”以及从学理上提出的“庄屈无二道”,为后世学者的庄屈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庄屈关系以及庄骚作为具有相对稳定理论内涵的审美范畴,越来越引起明清易代之际学者的普遍关注。明末清初的学者,除了钱澄之的《庄屈合诂》外,尚有觉浪道盛、方以智、屈大均、刘命清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开始来阐释庄屈关系。无论是方以智“怒怨致中和”的庄屈观,还是屈大均“天人一贯”的庄屈观或者是陈子龙“庄屈皆本于‘怨’”的庄屈观,都表现了从比较的视角对庄骚进行研究的努力。从与庄学、易学和诗学比较的视角对屈骚进行的阐发研究,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屈骚阐释的一个亮点和特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澄之“庄屈合诂”在清代屈骚阐释史上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具体结论的价值。
——先秦易学阐释分期断代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