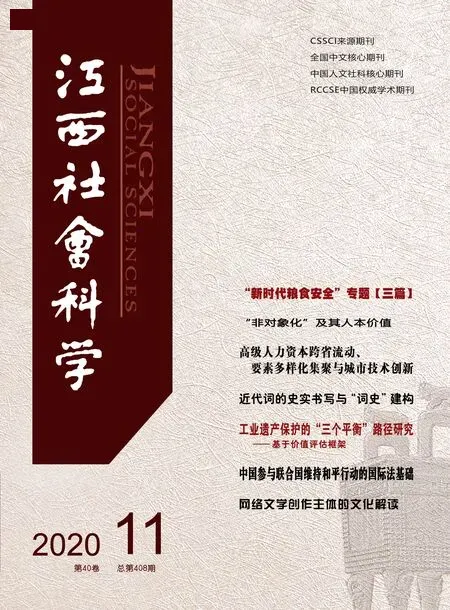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论及其实践奠基
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的社会哲学试图阐明社会实在的本质与存在方式,该理论借助集体意向性、地位功能、构成性规则和宣告式言语行动等概念装置,指认语言在建构社会实在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因而实质上是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论。语言的建构性依赖于语言的表征特性和规约特征,但语言仅具有派生的建构性,具有本源建构性的乃是马克思所说的客观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不仅形塑了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是人类形成语言和建构社会实在的基础。
对社会现象的来源与本质的探究是各哲学流派共同关注的理论焦点。分析哲学在历经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两大研究范式后,不可避免地将遗留的问题逼入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围,这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不期而遇,因此,两种风格的社会哲学研究亟须接触、比较与融合,但这个课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个例研究,桥接约翰·塞尔建基于语言的社会哲学与马克思建基于实践的社会理论,以期为社会哲学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进路。
一、建构社会实在的概念装置
在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它所指的范围是“一定的因自身的明显特征而有别于其他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现象群”[1](P23),对社会事实进行研究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1](P35)。20世纪9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后,涉身进入社会哲学研究领域,提出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理论在国外学界引起广泛讨论,产生深远影响。塞尔认为,社会哲学不应是政治哲学延伸或近似的学科,而应研究社会实在的本质及存在方式等内容,成为类似于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的哲学分支。根据塞尔的理解,社会实在又称为制度性事实或制度性实在,是社会事实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视作迪尔凯姆“物”的社会事实之发展,具体指的是需凭借人及人类社会而存在的事物,诸如货币、婚姻、公司、球赛等都属于社会实在或制度性事实的范畴,各种制度性事实共同构筑复杂的人类社会。
在社会哲学中,塞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完全由基本的物质粒子组成的世界是如何出现社会实在的?他使用的分析方法源自分析哲学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他本人的言语行动理论和意向性理论,使用的概念装置也大多出自于此,这些概念装置具体说来有集体意向性、地位功能、构成性规则和宣告式。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这几个概念装置,然后“以点带面”,分析社会实在之语言建构论的逻辑框架。
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在从事某种活动时具有的共同意向状态。集体意向性是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证成却是个难题。流行的观点是将集体意向性还原为个体意向性,然后对个体意向性进行说明,但这种还原论并不成功。作为当代意向性理论的代表人物,塞尔认为:“把集体的意向性还原为个体意向性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集体意向性是生物的基本现象,不可能还原为或替代为别的什么东西。”[2](P24)所以,他采取的策略是放弃集体意向性的还原论,径直承认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某种集体的意向性,将它看作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某种意识,比如我们相信、我们反对,等等。平心而论,塞尔对集体意向性的说明并非无懈可击,而是面临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个体大脑中的集体意向性是如何形成的。但此处我们申明的是,作为建构社会实在的概念装置,集体意向性是必不可少的。
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事物都有其功用,即它对人的有用性,经济学中叫使用价值,哲学上叫功能,功能总是相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的。按照塞尔的理解,事物的一些功能是凭借事物本身的物理、化学等特性而具有的,比如食物和各种工具的功能,另一些功能则不是凭借事物的自然功用,而是借由人类集体地赋予它以某种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需要得到集体的承认或接受,如货币的功能。因此,地位功能(status function)是指某物不是凭借其本身的物理特征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仅是通过集体的承认或接受才具有的功能。可见,地位功能的赋予依赖于集体意向性,赋予某物以地位功能是一个创造性和建构性的过程。进一步说,地位功能的存在与否是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过去我们认为人类是唯一的工具制造者,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表明,许多动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比如:黑猩猩会改造树枝,用于取食洞里的白蚁,河狸会用树木等物品修筑水坝来保障自身安全,等等。不同的是,人类不但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且可以将某种地位功能赋予某物品,而该物品本身并不具有此物理特性,比如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的权杖、王冠,以及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球赛、股票等。动物至多可以利用事物的自然属性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它们无法做到地位功能的赋予,因此几百万年来猩猩们仍然停留在用树枝钓白蚁,而人类的文明成就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塞尔在其早期的言语行动理论中将规则区分为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调节性规则指的是行动在规则之前,规则的出现是为了调节早已存在的行为方式。如日常生活中的交通规则就是调节性规则,它的存在是为了调节早已存在的交通,没有交通规则,路上行人车辆的交通也会存在,尽管可能是以一种更坏的方式存在,所以,调节性规则调节的活动在本体上独立于规则本身。构成性规则是在调节某活动的基础上进而创造或定义了这种活动的规则。构成性规则不仅起调节作用,而且定义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具有“X在语境C中算作Y”的形式。各种游戏和球赛的规则都是构成性规则,比如中国象棋的规则就创造或定义了这种游戏的可能性,试想中国象棋若没有“马走日字,相飞田”等规则,剩下的只是所谓的“棋子”和“棋盘”了,它作为一种游戏将不复存在,可见,中国象棋这种活动在本体上依赖于构成性规则。从两种规则的关系来看,所有构成性规则都属于调节性规则,反之不亦然。社会实在的建构必然会涉及构成性规则,即我们将某个X(可不存在)算作Y,赋予其某种特殊的地位功能。
依据塞尔早期的言语行动理论,宣告式(declarations)是五种言语行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唯一兼具“语词指向世界”和“世界指向语词”双重适应指向的言语行动。宣告式通过宣告某事态的存在而使该事态得以存在,这实际上改变了世界,所以成功地施行一个宣告式言语行动会引起命题内容和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得现实世界与命题内容相一致。一般说来,通过宣告式言语行动使地位功能Y的存在成为事实,这是创立制度性事实的普遍形式。由宣告式建立起具有地位功能的制度性事实就是“地位功能宣告”,而构成性规则本身即是常设的(standing)地位功能宣告,塞尔断言:“人类所有的制度性实在都是通过(具有相同逻辑形式表征的)地位功能宣告来创立和维持其存在的,包括那些不是明显的宣告式言语行动的情形。”[3](P13)所有政治法律制度都是地位功能宣告,反复地使用宣告式言语行动就可以创立和维持所有制度性事实。所以,制度性事实或社会实在就是拥有集体意向性的人们通过宣告式将某种地位功能Y赋予某事物X,从而创设出来的事实。
塞尔认为,制度性事实的存在依赖于上述四个概念装置所指称的对象,集体意向性是产生制度性事实的心理因素或主体条件,地位功能是形成制度性事实的中介因素,构成性规则是制度性事实形成过程中的规约因素,宣告式言语行动则是形成制度性事实的语言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共同形成了建构社会实在的概念装置。然而,这四个因素并不是平权的,而是分为两个层次,处于表面层次的是地位功能和构成性规则,处于基础层次的则是集体意向性和宣告式。正如前文指出的,地位功能依赖于集体意向性,即赋予地位功能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或接受才能成为真正的地位功能。其实,地位功能同样依赖于宣告式言语行动,不获宣告的地位功能将无法成为真正的地位功能,只能沦为个体的禁脔,所以塞尔说:“地位功能需要语言或至少类似语言的象征能力。”[2](P134)另外,构成性规则的存在看似不依赖于集体意向性,实则不然,试想构成性规则如果得不到集体的承认、接受和遵守,这种规则本身将荡然无存,更谈不上创设和定义行为方式了。构成性规则的形式是“X在C中算作Y”,这里的C即是语境(context),这种规则要发挥作用同样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总之,构成性规则也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单独成立。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将地位功能和构成性规则化归为集体意向性和宣告式,而是区分这几个概念装置的不同层次,揭示出其中起基础作用的是集体意向性和宣告式,进而表明语言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
根据前文的分析,集体意向性确实是人类产生制度性事实的必要条件,但它显然不是充分条件。就形成制度性事实而言,仅有集体意向性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人类的语言或某种类似于语言的东西。所谓人类的语言指的是一种外在的、具象性的客观产品,这种产品一经形成就具有离散性、组合性和生成性[3](P63),它能够表征实在及交流信息,可以为人们所理解、运算和重构。按照塞尔的理解,尽管集体意向性更为基础,语言仅仅是意向性的延伸,但深入分析塞尔理论的逻辑机理,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语言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自然界中很多社会性的动物具有某种集体意向性或集体行动的特征,但由于它们没有与人类语言相类似的交流工具,便不能产生社会实在,更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所以,语言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形成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由此,塞尔断言:“除了语言本身这个重要的例外,所有的制度性实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全部人类文明,都是通过与宣告式具有相同逻辑形式的言语行动而被创立的。”[3](P12-13)这句话至少包含三个关键点:其一是语言本身乃是一种制度性事实,但它不是一般的制度性事实,而是建构其他制度性事实的元制度性事实;其二是宣告式言语行动通过重复地逻辑运算就可以创设和维持制度性事实,进而发展出人类文明;其三是其中包含着从宣告式言语行动到一般人类语言跃升的意涵,人类的语言在进行重复操作后就能承载某种社会承诺或道义权力。根据塞尔的观点,道义权力包括“积极的”社会权利和“消极的”社会责任,“这些权利、责任等是将人类社会整合在一起的粘合剂”[3](P89)。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将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理论称为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论。
二、本源的建构性和派生的建构性
塞尔在给出上述概念装置后多次详述语言的演化及如何建构出整个人类文明的要义,从而建立起一套十分精细而又繁琐的理论,而且,他的观点几经改变,往往使人不明就里,导致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机理被遮蔽,笔者尝试归纳其中的理论要点。
塞尔认为,语言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意向性的延伸。他对语言的解释是自然主义式的,即把语言看作基本的生物现象和本能,认为语言是人类前语言的意向性延伸。关于“语言是人类本能”的观点在当代得到很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指认,也得到了分子生物学的支持。当代进化理论表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几次关键的基因突变,其中一次是人类的祖先获得了叉头框P2(FoxP2)基因,该基因又称作语言基因,可以在很多鸣禽中找到。这个基因控制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人类的祖先获得它后并将其遗传给后代,从而使得后来的人类普遍具有语言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是人类的本能”与“语言是习得的”并不矛盾,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别的动物并不具备,但这种能力是一种潜在的本能,需要后天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很多社会哲学家都把语言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并由此展开自己的论证,塞尔认为这是成问题的,在他看来,人类一旦拥有语言就具有了某种社会契约,即语言是形成人类社会的元契约,“不说明语言就不可能充分地说明社会本体”[3](P61-62)。塞尔这里的意思是,语言是我们理解社会实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文明,对此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4](P12)由此,关于语言本能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论的前提条件。
真正参与社会实在建构的是语言的表征性和规约性。语言是表征外在世界的工具,这对社会实在的建构至关重要。塞尔分析,人类的语言作为一种表征工具,最初与动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区别并不大,它们都可以传递简单的信息,如“危险”“食物”等所谓的“单词句”,而真正使人类的语言取得长足进步的是,语言能对外在世界进行丰富表征,源于语言是否真正具有语义以及它在语义上是否可判定。语言这种表征工具能够复杂地表示客观世界中的事态,“语言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构成了它们(即社会实在)。为什么呢?因为所讨论的这些现象由于它们被表征成什么就成其为什么。表征部分地建构了制度性实在,即诸如政府、私有财产、婚姻、货币、大学和鸡尾酒会,这种实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语言不仅描述,它还创造并部分地构成那些它所描述和创立的东西”[3](P85)。更进一步说,语言不仅可以表达实存的事件,它还可以表达虚假的事态,创造出虚构的名称、事件及虚构的文学作品,从而创造出一个个“虚构的世界”,正如很多语言学家注意到的,虚假地表征世界是人类语言特有的属性。
语言是社会认可的规约性工具,是以社会可以理解的方式重复和成规律地传递某些信息的声音或符号,语言的这种规约性也称作“语言规约”(linguistic conventions)。如果语词和语句固定地拥有了语义,语言就成为社会认可的规约装置,语言的使用者就可以按照惯例用语言来表征实在、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因而语言的意义是规约性的,它还能够创立一套超越语义的道义权力。对此塞尔指出:“如果我们不理解语言必然涉及社会承诺,就不理解语言的本质特征,并且这些社会承诺的必然性源自对于交流情景的社会特征、所用装置的规约特征以及说话者意义的意向性。”[3](P80)可见,超语言的道义权力来自语言之外,比如社会地位、习俗等,开战或终战需有相应社会地位的组织或人来宣布,开会休会也是如此。塞尔认为,人类只要拥有语言,就可以“随意地”创立制度性事实,这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语言之外的东西照样非常重要。再来看语言虚构的问题,我们只有承认作为元制度性事实的语言具有表征性和规约性,才可能有X算作Y的问题,因而社会实在亦可看作语言的“虚构”,不存在“丈夫”“老师”“工人”这样的实体,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语言具有的超语言的道义权力实质上是语言“虚构”的力量。
总之,塞尔的基本观点是:“所有制度性事实都是语言性地被创立,以及语言性地建构和维持存在。”[3](P93)所以,他的社会实在的建构论本质上是语言建构论。尽管该理论提出后招致很多批评,但这些批评也促使塞尔更加严密地论证该理论,从而使之具有很强的解题功能。该理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这项工作是分析哲学在其科学式哲学进路中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它凸显了语言在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具有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没有语言就没有制度性事实,也就没有人类社会。这种理论将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塞尔的一大创见。其二,这项工作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社会实在的一般本质,理解语言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对促进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诠释人类文明的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路径。其三,这项工作在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它在运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地阐释了语言在社会实在建构中的作用,为打通不同风格哲学研究间的壁垒提供了可能范式。
然而,我们的研究不应就此止步,应该继续追问的是,拥有语言的人类是否一定会发展出如此发达的文明?有没有比语言更加基础的东西?它是建构社会实在的根本,即它不仅建构了社会实在,而且建构了语言。问题不止于此,在分析哲学领域内,塞尔仅仅追问了货币、婚姻、公司等社会实在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其本质和存在方式等问题,但并未批判已经出现的社会实在的合理性,比如资本或货币统治人、奴役人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应该怎么改变它们。塞尔批评哈贝马斯等哲学家把语言看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而他自己则把这些业已出现的社会存在视作理所当然、不需批判的,这恰恰是马克思告诫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塞尔哲学的困境在于,它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将社会实在看成静止的、既成的事实,缺乏社会批判的维度,从而使其理论深度大打折扣,这也是当代分析哲学面临的普遍难题。重申一遍,笔者绝不是要否定塞尔社会哲学的理论价值,而是在坚持其理论优势的基础上援引其他风格哲学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哲学研究向前发展。
关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语言不具备根本的建构性,语言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也是被建构的,建构语言的是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为区分不同的建构维度,我们借用塞尔在辨析意向性和语言时使用的“本源意向性”和“派生的意向性”两个范畴,认为实践活动具有本源的建构性,语言仅具有派生的建构性。塞尔等分析哲学家认识到语言对社会实在的建构功能,作为派生建构性的语言在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确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客观的实践活动在其中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举例来说,塞尔认为我们使用语言能创设出超越语义的道义权力,道义权力是构成制度性事实的本质,这种创设既依赖于语言的意义,又依赖于语言之外的习俗、人的社会地位等等。我们认为,不管是语言的意义还是语言之外的习俗、社会地位等,都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换言之,如果人类仅有语言而没有真正去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那语言连同它所建构的社会实在都将不复存在。
三、社会实在建构论的实践奠基
在哲学史上,真正将人类的实践活动提升为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与一般知识论的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将实践看作人的生存方式,因而它就具有前概念或前反思的生存论意义。俞吾金在批评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时指出:“塞尔根本没有把个人或集体置于确定的生存境遇中去探索其意向性。在他那里,意向性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而不是个体之为个体、集体之为集体在生存境遇中必定会显露出来的根本特征。”[6](P34)也就是说,在塞尔那里,意向性和语言都是经验性的存在,不具备生存论意义。而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则具有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它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5](P162)。实践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所从事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是实践的首要特征,而且“实践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相统一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性活动”[7](P28)。以色列哲学家阿维纳瑞指出:“对马克思而言,实在总是人类的实在,这不是在人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人塑造自然的意义说的。这个活动也塑造了人、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它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8](P71)可见,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塑造人本身,以及创设人类社会,进而建构起整个属人的世界。没有实践活动,属人世界的一切将无从谈起,更遑论建构社会实在了。所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在理解并阐释任何对象时,始终保持着实践维度的优先性,即把实践作为观察、思索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9](P1)。如此一来,语言和实践在建构社会实在中的作用就存在明显区别了,语言作为一种元制度性事实,总是人类的制度性事实,它在本体论上无法摆脱人类。换言之,语言不可能在逻辑上先于人类而存在,而实践活动却是在逻辑上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因此,语言只具有派生的建构作用,而实践活动则具有本源的建构作用。
马克思在早期哲学中系统地阐释了实践范畴,并建立起基于实践或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后来马克思主要使用的是具有生产性特征的劳动范畴或生产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区分并不紧要,杨国荣分析道:“(马克思的)实践既旨在改变世界与改变人自身,又构成了实现上述改变的基本形式,而人的改变最终又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不难注意到,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劳动被赋予本原的意义,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均奠基于其上,而改变世界与改变人自身则构成了实践的现实指向。”[10](P42)由此看来,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实践与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或生产在建构属人世界的层面上都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
前文提及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地位功能赋予和人类语言,这没有错,但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根本所在。马克思在多处强调,实践或生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特征。青年马克思认为,动物的生产仅为了满足自身和幼崽直接需要,只是生产自身,因而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可以按照超出自身需要的尺度来生产,并能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所以人的生产是社会性的全面生产。后来马克思仍坚持这一观点,他说:“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类的本质。而且,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11](P197)而人的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可以为别的人、别的动物生产,在这种生产中,建立起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具体的社会实在,都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5](P603)马克思的意思是,社会关系建立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上,从社会关系出发又形成不同的观念体系、语言等,不管是人的社会关系,还是人们的观念体系、语言,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会发生变化。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它们都是可以被建构和批判的。
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实践活动是诠释观念体系、文化习惯和语言的基础。马克思在论及唯物史观时强调:“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5](P544)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一以贯之,即实践是分析社会关系、观念形态和语言范畴的出发点,它为社会和语言奠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言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P501)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1](P487)马克思的这段话使实践建构性的层次感跃然纸上。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不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及环境等客观条件必然会被建构和改变,作为生产主体的人也在发生变化,人们掌握的生产力和观念也会被形塑,进而建构起新的交往方式或社会关系,以及新的需要和语言。
下面我们通过考察马克思的语言观来进一步为社会实在的建构奠基,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掌握分析哲学关于语言的研究成果,但由于马克思对实践和人类社会有深刻的把握,所以他关于语言的观点显得更具历史穿透力。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语言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维度。其一,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唯心主义哲学家时说道:“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遍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2](P525)所以,语言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由于现实的需要才出现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P533)。其二,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分析道:“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他的不言而喻的存在。”[11](P482)既然语言是相对社会而存在的,那么,语言同货币、资本一样,反映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社会实在,也可能会统治人、奴役人。
四、结语
塞尔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建构社会实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马克思则认为社会实在是由意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实践比语言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他们的共同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建构本质,并试图刻画出人类社会的建构逻辑,所以二者的基本观点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不仅如此,两位哲学家在很多观点上还是一致的,就批判人类所谓的自然状态而言,塞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性事实、元契约,人一旦有了语言就有了人类社会,“如果‘自然状态’的意思是一种没有人类制度的状态,那么对于讲语言的动物而言则根本不存在自然状态这种东西”[3](P62)。马克思也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鲁滨逊之类的孤立个人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人与人之间订立所谓的社会契约也是骗人的把戏,“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1](P25),因而,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社会性动物,根本不存在孤立个人的自然状态,人类社会及人类文明都是由会语言的人通过实践活动而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