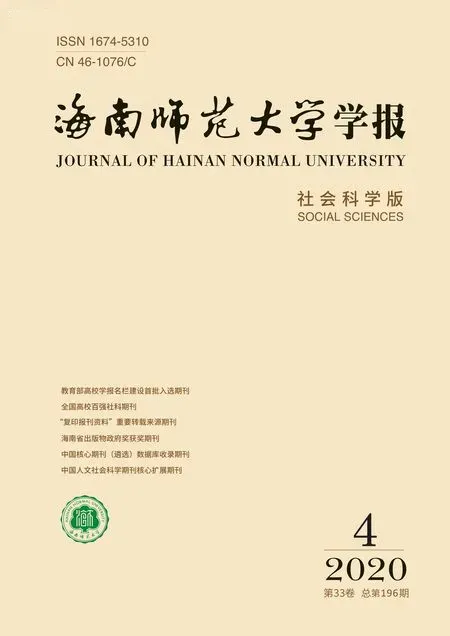误读与澄清:黄宗霑改编《骆驼祥子》事件之细节考证与本相追问
张 引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50年4月,已经回国将近半年的老舍在为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骆驼祥子》所写的序言中,大致回顾了这部小说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多舛命运。首先,“连载还未登完,战事即起”(1)老舍:《〈骆驼祥子〉序》,《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01页。,这也直接影响了该书在国内的传播;不过在国内备受冷落的“祥子”在大洋彼岸却享受到了很高的待遇。随着1945年《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美国各大报刊大都对其给予了极高关注。(2)参见孟庆澍:《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骆驼祥子〉在美国(1945—1946)》,《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祥子”在美国的异常“走红”也让好莱坞的电影从业者们从中窥得商机,于是,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进行二次传播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但由于各种原因,改编一事无疾而终,老舍对此也流露出了一丝遗憾的意味:“好莱坞一家中国电影公司曾决定采用此书,制为电影片,但未成功,而且或者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3)老舍:《〈骆驼祥子〉序》,《老舍全集》第17卷,第501页。
老舍口中这次未成功的改编经历,具体所指的是1947年底至1948年11月期间,好莱坞著名美籍华人摄影师黄宗霑(James Wong Howe)对《骆驼祥子》所进行的一次“影像化”尝试。对于黄宗霑的这次电影改编,当时国内媒体普遍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进行了持续跟进的报道。尽管改编一事最终未能成型,但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较为轰动的社会事件。遗憾的是,后人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并不充分,对此事尚存的一些误读需要被澄清。比如,黄宗霑是否是第一个试图将《骆驼祥子》进行影视化改编的人?最终促成他改编该书的契机又是什么?他与老舍对于改编剧本最核心的分歧是什么?这背后又反映出世人对他有怎样的误读?为什么会有人对这次电影改编一事持否定态度?这种舆论又是如何影响到老舍本人的?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一
或许是黄宗霑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们在回顾《骆驼祥子》的“影像化”过程时,往往也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最初试图把小说《骆驼祥子》影视化的就是黄宗霑无疑。(4)比如胡絜青曾指出:“老舍的作品被搬上银幕,说来倒是历史不短。四十年代末期,老舍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好莱坞的一家制片厂计划把《骆驼祥子》拍成电影,导演兼摄影就是国际知名的电影摄影大师黄宗霑先生。”参见胡絜青:《老舍与电影》,《电影艺术》1983年第1期。日本学者杉野元子也认为“最初试图把小说《骆驼祥子》影视化的是1948年旅居美国的影坛名人黄宗霑。”参见[日]杉野元子:《北京的骆驼祥子与香港的骆祥致——1962年香港影片〈浪子双娃〉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但据笔者考察后发现,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严谨的,因为早在黄宗霑之前,想要试图翻拍《骆驼祥子》的另有他人,尽管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初步的构想阶段,最终并未付诸于实践。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初有意改编《骆驼祥子》的竟是伪满洲国的电影机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1942年6月25日,日伪宣传刊物《戏剧报》刊登了一条名为《老舍作品〈骆驼祥子〉将拍制影片》的新闻:“文艺作品扮上银幕者,如《茶花女》,《日出》,《雷雨》,《原野》,《少奶奶的扇子》等片,演出成绩,均得好评,兹悉‘满映’,疑将文学家老舍作品《骆驼祥子》改编电影剧,拍制电影,并改名为《月明之夜》。”(5)《老舍作品〈骆驼祥子〉将拍制影片》,《戏剧报》1942年6月25日第4版。
“满映”为何有意选择《骆驼祥子》进行电影改编?限于资料的有限,其背后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当时的伪满洲国,根据文艺作品改编成电影与戏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戏剧方面,改编剧的发展十分繁盛的,“一方面移植挪用国外的文学作品改译成中国剧本进行演出,如法国莫里哀的《悭吝人》、小仲马的《茶花女》,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美国话剧《钱》等;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对或对原有话剧加以增删上映,如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曹禺的话剧《雷雨》、《北京人》、以及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剧作《家》等。”(6)何爽:《伪满洲国戏剧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电影方面,“满映”的导演也经常从现代与古典的文艺作品中汲取灵感和素材。1941年上映的《天上人间》便是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此外《豹子头林冲》(1942)与《燕青与李师师》(1943)则是根据《水浒传》的相关情节改编而来。
当然,彼时身处重庆,身心俱疲的老舍,恐怕根本无暇顾及“祥子”的命运,也并不知晓“祥子”曾有被沦为日本人进行殖民宣传的工具的“危险”。直到抗战胜利,美国那边传来消息,由伊文·金(Even King)翻译的英文版《骆驼祥子》(译本名为RickshawBoy)广受好评,“祥子”才再一次引起了老舍以及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书在被美国著名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评为“八月之选”(The Book-of-the-Month Club Selection For August)两个月后,老舍在与友人的信件交流中首次袒露出对于此事的看法:“‘骆驼’因无国际版税法,无法要美金。美国的批评极佳,销路可观,或者因此也许‘施舍’给我一点,唯无确息耳。”(7)老舍:《书信·致王冶秋(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07页。伊文·金翻译的《骆驼祥子》最早出现在国内媒体应该是在1946年5月《现代英语》杂志第6期第4卷上。也因此,1945年9月份的老舍可能还并未曾读过这一译本,自然也就不清楚其作品已经被译者强行修改,把悲剧的结尾,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此时的他所担心的只是能否拿到版税的问题。
毋庸讳言,对于《骆驼祥子》版税的争取确实构成了老舍在1946年的春天前往美国的私人动机之一,而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动机则是为了促成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根据老舍友人王敬康的回忆文章可知,老舍在动身去美国前,曾对他谈到好莱坞有意将《骆驼祥子》拍成电影,因此,他“希望好莱坞在采取他的小说摄成电影时,他能收集一笔款子,能对国内的文化人做一点有益的工作。”(8)王敬康:《与老舍先生抵足一月记》,《上海文化》1946年第3期。也就是说,在出国之前,老舍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小说被好莱坞看中,并有望拍成电影。但具体是哪一家公司,他却并未说明。不过根据其他材料的佐证似乎可以证明是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以下简称华纳公司)。首先,1946年4月到6月间,老舍和曹禺曾一起到好莱坞参观,并出席了电影文学家协会的欢迎会。在此期间,华纳公司还特意为老舍和曹禺拍摄了一部新闻短片,在美国各地上映。另据当时新闻记载,经常有好莱坞负责人到老舍和曹禺的住所让他们写剧本,所以有理由相信想要改编老舍《骆驼祥子》的正是华纳公司。
此外,1948年5月4日北京《益世报》上的一篇文章似乎也能够证明笔者的上述猜想。这篇署名为“律平”的文章披露,华纳公司确曾与老舍就《骆驼祥子》的电影改编进行过接触:“听说华纳公司曾以五万元的代价和老舍的经纪人接洽过,因为双方要价给价的距离,结果没有成交。去年(指1947年:笔者注)七月,我到好莱坞认识黄宗霑,听过他关于计划拍摄骆驼祥子的意见”。(9)律平:《黄宗霑和骆驼祥子》,《益世报·北京》1948年5月4日第3版。根据文章的描述来看,该文作者应为一名电影记者,他曾于1947年7、8月份在洛杉矶和黄宗霑有过见面,并就《骆驼祥子》的改编问题向他当面请教过。笔者认为,关于华纳公司试图改编《骆驼祥子》及未能成功的消息就是黄宗霑透露给该记者的。需要知道的是,黄宗霑在1947年底之前一直都就职于华纳公司(10)黄宗霑从1938年到1947年之间一直就职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并于1947年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解约,但具体何时不得而知,根据推算应该是在下半年左右。,因此他所提供的消息应该是确切的。也就是说,华纳公司曾在1946年到1947年间就已决定改编《骆驼祥子》,并且也已经派人和老舍接洽过,但双方因为薪资问题最终未能合作成功。好莱坞的放弃最终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身为摄影师的黄宗霑更坚定了自己去拍摄《骆驼祥子》的想法;二是让国内的电影从业者看到了“祥子”回归本土的希望。
花开两朵,黄宗霑这枝的事情暂且按下不表,先说国内这条线索。1947年的春夏之交,“祥子”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首先是1947年5月,上海《大公报》披露,“中电三厂”(11)“中电三厂”的前身为沦陷时期的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宣部组织委派徐昂千于1945年10月赴北平接收、改编该公司,并建立起当时在中国北方最具规模、最有实力也是最富活力的电影制作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北平分场;1946年1月更名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场”,简称“中电三场”;1947年4月,随着中电系统企业化改革过后,“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场”更名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厂”,简称“中电三厂”。也就是说,在1946年1月到1947年4月期间,该电影机构的名称为“中电三场”,而在1947年4月份之后,“中电三厂”的名称则取而代之。即将开拍《骆驼祥子》:“该片的本由徐昌霖改编,内定由沈浮导演,魏鹤龄演祥子,吕思演虎姐。”(12)《中电三厂即将开拍骆驼祥子》,《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7日。紧接着一个月后,《青青电影》杂志便发布消息,“文华”公司也有意于“祥子”:“最近文华公司当局有将老舍的《骆驼祥子》搬上银幕计划,这片子的导演工作大概由曹禺担任制作的可能。”(13)《文艺影片抬头!〈骆驼祥子〉将上银幕》,《青青电影》1947年复刊第1期。不论是国民党当局垄断的电影制作,还是以民营为主的进步电影力量,大家均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将目光同时投向“祥子”,恐怕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好莱坞已经放弃对《骆驼祥子》的改编不无关系。在那篇报道“文华”影业有意改编《骆驼祥子》的文章中,作者就做出了这样的猜测:“此书在美既大红,如时在战前,好莱坞正‘东方热’,也许早就买下版权,轰轰烈烈的拍成第二部《大地》之类的中国片子了。但是好莱坞在战时东方的战时片子拍了不少,因此不曾顾及此着,而使老舍坐失数万美金。但是好莱坞不拍,中国自己却要来拍。文华公司已在接洽向老舍谋购原作版权,倘若接洽没有问题,《骆驼祥子》则将列为文华公司创业的第四部片子了。”(14)《文艺影片抬头!〈骆驼祥子〉将上银幕》,《青青电影》1947年复刊第1期。
“文华”影业垂青于“祥子”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彼时已经回国将近半年的曹禺经黄佐临介绍,刚刚加入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再加上之前他曾与老舍一同在美国访学,所以传出由他负责《骆驼祥子》的拍摄任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条消息最终也被证明为是“谣言”,因为曹禺在1947年夏天所改编的电影剧本并非《骆驼祥子》,而是原创了名为《艳阳天》的剧本,这是曹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从事电影创作。至于“中电三厂”,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他们想要翻拍《骆驼祥子》了。就在一年前老舍出国前夕,就有媒体报道说,刚刚完成改组的“中电三场”有意将《骆驼祥子》搬上银幕,作为自己改组后的首部影片:“‘中电’三场即将开始拍片,预定资本七千万元。第一部戏拍老舍名著《骆驼祥子》,主要演员经审选后决定魏鹤龄。”(15)《“中电”三场即将开始拍片,预定资本七千万元》,《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2卷第3期。不过等到半年后(1946年8月),人们发现尽管“中电三厂”确实已经在着手拍摄他们的第一部影片了,但却并非是《骆驼祥子》,而是一部叫做《圣城记》的电影:“中电三厂之第一部戏剧长片《圣城记》,自七月初开拍以来,现已完成过半,预计九月初即可全部竣工,目前拍摄工作渐至紧张阶段。”(16)《中电三厂摄制〈圣城记〉,现正拍群众镜头》,《益世报·天津》1946年8月20日。情况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动,在笔者看来,恐怕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根据前文所述,此时老舍应该已经知道好莱坞有意要翻拍“祥子”,所以便拒绝了和“中电三厂”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作为从属于国民党党宣体系的电影公司,“中电三厂”选择《圣城记》而非《骆驼祥子》可能也是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考量,毕竟相较于最终上映的《圣城记》,《骆驼祥子》所反映的内容似乎并不适合宣传的需要。《圣城记》所讲述的是美国传教士、“盟邦真正友人”金神父在极度困难中仍不惜冒险呼吁,拯救被日寇抓走的女华侨朱荔而最终被杀的故事。“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是一部宣传反战与歌颂友邦人士的影片,但是正统意识的过分强调与外露,使影片中金神父的形象显得力道不足。影片中,金神父强大的保护色彩与中国民众反抗的无力,多少也显出了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17)虞吉:《中国电影史》(第2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5页。。无论如何,不论是“中电三厂”,还是“文华”影业,最终都与《骆驼祥子》“有缘无分”,均无法成为第一个将《骆驼祥子》搬上银幕的电影公司。反倒是身处好莱坞的黄宗霑则坐拥“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利,开始着手去考虑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定为《骆驼祥子》。
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接上黄宗霑的那一条线索来说。当时间来到1947年时,黄宗霑在华纳公司已经工作了九个年头。从1938年到1947年,他为华纳公司共拍摄了二十六部影片,并被借出去为别的制片厂拍摄了四部影片。可以说借助于华纳公司的平台,黄宗霑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声望,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位著名的好莱坞摄影大师。尽管在摄影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在黄宗霑的心中却仍然有一个从未熄灭的“导演梦”,他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导演一个由他自己支配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最好是与中国有关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度并未与任何公司签约的黄宗霑曾“决意忘却那些制片厂,自己来制作影片”(18)[美]托德·雷斯堡格尔:《黄宗霑的一生》,沈善译,《世界电影》1981年第6期。,他募集了所能筹到的所有资金,自己导演、制作并拍摄了一部日本影片,但效果却极不理想。黄宗霑认为应该制作一部有关中国题材的电影,但无奈“他自己只能筹到制作影片所需的一万二千元美元中的四千五百美元”(19)[美]托德·雷斯堡格尔:《黄宗霑的一生》,沈善译,《世界电影》1981年第6期。,所以他必须得服从于资助者的安排,选择一个日本故事进行改编。
在一个资本至上的时代,倘若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纵使再有才华,也很难掌握核心的话语权,更何况那时的黄宗霑还并非像十几年后那般声名远扬。而从另一方面来说,20世纪30年代也并未有一本如《骆驼祥子》那样的由中国人所写的华语畅销书流行于美国社会,黄宗霑自然也就无处觅得一个令他满意的中国故事作为剧本来进行拍摄。也正因如此,1947年这个年份对于黄宗霑来说才显得格外特别:一方面由伊文·金所翻译的《骆驼祥子》一书在美国社会中广受欢迎,这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再理想不过的故事剧本;另一方面,此时的黄宗霑与华纳公司的合约也临近期满,他即将和友人合伙成立一家独立电影制作公司,这又为其提供了一个能够更自由地施展自己导演才华的场域。(20)该公司即为“泛太平洋电影公司”,其于1948年前后成立,筹备期为两年左右,由黄宗霑联络挚友彼得夫妇一起创办而成。其资本百分之四十是私人出的,百分之六十是向美国银行贷款。再加上之前华纳公司方面也已经放弃了对《骆驼祥子》的改编与拍摄,相较于国内的电影公司,黄宗霑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抢先一步与老舍接触去购得小说的改编权。
1947年底,天津《益世报》率先披露了黄宗霑将要改编《骆驼祥子》的消息:“老舍著《骆驼祥子》将上银幕,由黎利利与好莱坞中国籍名摄影员黄宗霑合组之联营公司开拍,由好莱坞明星钟加非任主角。”(21)《东方将有“好莱坞”,〈骆驼祥子〉美式化》,《益世报·天津》1947年12月1日。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将黄宗霑和“祥子”联系在一起,不过其所述内容却有不实之处,比如黄宗霑离开华纳公司之后确实和友人一起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但却并非是和女演员黎莉莉。后者在1946—1947年美国求学期间曾与黄宗霑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黄也邀请过她扮演虎妞一角,可能正是由于两人这层特殊的关系才让媒体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至于钟加非(John Garfield)担任男主角一事,黄宗霑确实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但并未做出具体决定。尽管这条新闻失实之处颇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宗霑此时已经做好了改编《骆驼祥子》的准备。
随着时间进入1948年,改编工作的进程日益加快,国内媒体对此事的相关报导也逐渐增多起来。天津《益世报》于1月25日再次跟进报导,“《骆驼祥子》借中电三厂摄影棚可能于八月间开拍”(22)《〈骆驼祥子〉借中电三厂摄影棚,可能于八月间开拍》,《益世报·天津》1948年1月25日。。紧接着《申报》于两日后转载纽约中央社的导报,即老舍将小说《骆驼祥子》的摄制权以两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卖与黄宗霑。这也意味着持续了将近一年半的“《骆驼祥子》摄制权争夺战”终于尘埃落定,黄宗霑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去拍摄一部由自己主导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影片。但事实上由此而来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剧本改编、演员选取、拍摄环境,以及舆论风向等,皆将成为影响拍摄正常进行的一系列潜在因素。这其中,演员选取以及拍摄环境的问题已有前人做过相关研究(23)参见王玉良:《眷念与反哺:黄宗霑与早期中国电影》,《电影新作》2018年第2期。,故本文不再赘述,笔者主要就前人所没有过多谈及的剧本改编以及舆论风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再做考察。
依笔者之见,《骆驼祥子》剧本改编方面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主要是黄宗霑和原书作者老舍之间对于剧本内容存在着不易抹平的较大分歧。关于老舍本人在电影剧本改编过程中的态度,分别体现在他1948年8月到9月间与大卫·劳埃德的三次通信中。根据信件内容可知,老舍在1948年8月11日前往洛杉矶商量《骆驼祥子》电影脚本的定稿事宜,一周之后返回住处。在与黄宗霑共同商讨剧本的这一周时间里,老舍深刻地感受到:“好莱坞职业编剧改编的剧本实在是糟糕之极。”(24)老舍:《书信·致大卫·劳埃德(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45页。而在了解到老舍对剧本的看法后,黄宗霑也重新考虑再请一位剧作家或者让老舍本人来改编这部小说。不过根据老舍一个月后的叙述来看,黄宗霑似乎并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尽管他确实更换了之前的那个编剧,然而却并未邀请老舍,而是另找他人再进行改编。这也使老舍感到被冒犯,并从头回顾了黄宗霑在剧本改编上所做的“糟透了”的事:“王浩(指黄宗霑:笔者注)干的事真是糟透了。本来我该被邀请去帮他改编第一个电影剧本,可王却偏偏找了个好莱坞的剧作家。把一万五千块的剧本费都花完了之后,才想到了我。这次该请我了吧,他又另找了一个人。”(25)老舍:《书信·致大卫·劳埃德(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老舍全集》第15卷,第647页。
如果单从老舍的叙述来看,在《骆驼祥子》电影剧本的整个改编过程中,他始终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出现的,自己也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不过,以上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仅为老舍的“一面之词”。老舍究竟有没有参与改编?根据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又并不完全如老舍所言。据《大地》周报的报导称,黄宗霑在1948年4月3日接见记者采访时宣称:“《骆驼祥子》之三主角(祥子,虎姐及小福子)扮演人选,已在平初步选定……黄氏预计现在正由作家老舍及名电剧本作家温利维所通力改写《骆驼祥子》之电影脚本尚需时约八至十周始可完成,届时获得中美剧本检查机构通过,即可来华开拍”。(26)《黄宗霑与骆驼祥子》,《大地(周报)》1948年第105期。根据这一说法,老舍至少是参与了第一次剧本修改过程中,而合作对象是一名叫做“温利维”的电视剧本作家。另据1948年6月1日出版的《东亚声》报导,“这部片子故事的内容,正由老舍修改中,原著中的大兵拉伕和姨太太那几段,已完全删掉。老舍除在美讲学外,大部分时间用在改编这个故事上,现在正从事分幕。”(27)《〈骆驼祥子〉拍片难:北平难找合理想之男主角黄宗霑大伤脑筋!》,《东亚声》1948年第25期。这条消息同样也能够说明至少在剧本改编过程中,老舍并没有始终置身事外,而是参与其中的。
于是,关于剧本改编一事,在老舍信件和媒体叙述中分别呈现出了两幅不同的“面孔”。老舍是否参与到了剧本的改编?在没有更为详实的佐证材料出现之前,这恐怕永远要成为一件众说纷纭的“罗生门”事件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剧本改编这件事上,老舍与黄宗霑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且双方似乎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与底线。黄宗霑始终没有给老舍独自修改自己作品的机会,而老舍对于黄宗霑请来的好莱坞编剧们所写的剧本又嗤之以鼻,根本不屑一顾。尽管限于资料的有限,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剧本的真实面目如何,但因为该剧本实际上是以伊文·金的《洋车夫》为蓝本进行的创作。所以以此推测,老舍对于这个剧本最大的不满之处,恐怕也和《洋车夫》一样,在于它的结尾从一个令人绝望的悲剧被强行更改成了一个“大团圆”式的喜剧,而在黄宗霑那里,这种结尾则是他必须要去坚持保留的。
黄宗霑对于所谓“光明结尾”的执念,首先固然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毕竟之前经过伊文·金对结尾大幅度的改动,《骆驼祥子》已然在美国拥有了广泛的读者。因此,采用这一业已经过检验的结尾实为最保险的行为。但这其实又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黄宗霑之所以想要在故事的结尾让祥子重获自由,并给予祥子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他的“私心”。因为黄宗霑与“祥子”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产生了共情,并在后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黄宗霑曾说,肤浅的人从该书中看到的只是洋车夫如何受到各种欺辱的故事,而他却认为这部小说实际所讲的是如何通过奋斗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故事:“它说的是人生对命运的奋斗,如何希望从别人的篱下走进自己是主人的天地,洋车夫的努力,辛苦积蓄,所要求的不过是自己能有一车子,自己拉自己的洋车。不再要向车栈租车子拖,可是世界上各角落,正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自己占有自己的谋生工具,这种人生的努力,所追求的,也许不是一部洋车,而是别的东西,可是想自己为主人的目的则一致。”(28)律平:《黄宗霑和骆驼祥子》,《益世报·北京》1948年5月4日第3版。
从“别人的篱下”走进“自己是主人的天地”,黄宗霑这番话仿佛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他自己毕生所执着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尽管经过多年的艰辛奋斗,黄宗霑早已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金牌摄影师,但实际上在他看来自己依然是在为别人打工,始终处于一种“寄人篱下”的不自由状态。他从来“未能拍摄一部足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影片,没有拍成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以及从来没有机会导演一个由他自己支配的故事”(29)[美]托德·雷斯堡格尔:《黄宗霑的一生》,沈善译,《世界电影》1981年第6期。,这些无疑也成为了黄宗霑晚年最大的遗憾。也因此,当看到“祥子”在追求属于自己洋车的道路上“三起三落”时,他产生了很强烈的情感共鸣。“自己拉自己的洋车”在这里作为一种隐喻,实际所指涉的是一种自己可以自由掌控的生活方式。或许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与其说黄宗霑是在拍“祥子”,不如说他是在拍一部关于自己在好莱坞的奋斗辛酸史。因此,当他在1948年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独立拍片的愿望之时,他自然希望作为自己内心情感投射的“祥子”,也能像他一样获得人生的自由。(30)20世纪80年代,凌子风在改编《骆驼祥子》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我爱祥子,因此把有损于这个人物的章节删去了。比如虎妞死后,祥子到夏家拉包月,和姨太太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还染上脏病;甚至还有祥子为了几个钱出卖过人的描写,通通去掉,保持他作为朴实的劳动者的基本面貌。我不忍心让人们看到祥子彻底堕落,感情上不愿意。”参见王家龙:《凌子风漫谈〈骆驼祥子〉的改编和导演处理》,《电影评价》1982年第11期。从本质上讲,凌子风对祥子的处理与黄宗霑并无二致,他们都因对祥子的喜爱和共情,而对原有的故事情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动。
“改编,是一种重新解读”(31)[美]约翰·M.德斯蒙德,[美]彼得·霍克斯:《改编的艺术:从文学到电影》,李升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第2页。。一旦我们认同了这个观点,便不难理解作为导演的黄宗霑为什么坚持要让祥子重获自由,这实际是他在借“祥子”之酒杯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更是一种艺术层面的取舍。“祥子”之于黄宗霑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更像是一种理想与情感的寄托。不过作为文学家的老舍对此似乎却存在着一些“误读”,他认为黄氏更像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问题就在于所有为建立独立制片公司筹集的钱都不是他的,他这么大把大把地花钱只是想证明他是老板。我想,等他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会一走了之,到某个大公司去谋个好差事。”(32)老舍:《书信·致大卫·劳埃德(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老舍全集》第15卷,第648页。实际上,为了筹备公司,黄宗霑本人也出过一部分资金,而且在此之前他刚刚与华纳公司解约,不存在再到大公司去谋差事的理由。老舍对黄宗霑的“误读”,一方面可能与他本身对好莱坞电影及其从业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有关(33)老舍本人对好莱坞电影并无好感。旅美期间,看电影成为了他日常消遣的一项主要活动,但是据他所言,好莱坞的电影水平远不如欧洲电影:“纽约所有的好片子,全是英国的,法国的,与意大利的。好莱坞光有人才,而不作好片子,连我都替他们着急。最近纽约一城,即有四五部英国片子,都是连映好几个星期!”参见老舍:《书信·海外书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25页。;另一方面,黄宗霑较为“偏执”“傲慢”的性格和态度让老舍在与其相处的过程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也许这也间接影响了老舍对他人品做出真实的判断。
三
老舍的遭遇绝非孤例。事实上,黄宗霑的“坏脾气”在业界也是出了名的:“黄宗霑过去的同事谈起他时,称他是‘一个受挫折的导演’。在许多方面他是这样的。他在摄影棚里经常提建议、发脾气,反映了一种想在影片中更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一种想把自己的思想描绘出来的愿望——不仅在视觉上,而且同时也在内容上。”(34)[美]托德·雷斯堡格尔:《黄宗霑的一生》,沈善译,《世界电影》1981年第6期。单从这一点来说,黄宗霑确实与其所共情的对象“祥子”有相似之处,后者同样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道路上极为偏执的人。不过,相对于祥子的谦卑,甚至自卑的性格,已在好莱坞有所成就的黄宗霑在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傲慢的态度。也正是他这种无意识的“傲慢”,让其在1948年回国筹备《骆驼祥子》拍摄时引来了不少的争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拍摄的顺利进行。
自黄宗霑1948年2月回国以来,绝大部分的媒体都对他的这次“回归”报以极高的热情和期待,并纷纷撰文为其大造声势,但在一片赞扬声中也传来一些不甚和谐的声音。部分媒体刊登了一些针对黄宗霑的批评文章,这些批评首先集中在他对于国产电影的“轻视”,且这种批评在他访华期间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1948年4月出版的《电影(上海1946)》杂志上,署名为“钦贤”的作者便撰文指出,黄宗霑因其略显傲慢的言行遭到了国内一些电影界人士的不满:“黄君抵此,除‘雷电华’经理郭纯亮,‘中电’代表周克,白光,陈燕燕,及黄之故交董克毅父子等曾设宴招待及访问外,电影业方面并未重视,缘黄于宴席上曾有:你们中国电影怎样怎样,我们好莱坞怎样怎样之评语,致引起此间人仕对彼之不好感,故《骆驼祥子》搬上银幕困难尚多。”(35)钦贤:《黄宗沾此来大失所望,〈骆驼祥子〉难登影坛》,《电影(上海1946)》1948年第2卷第3期。此为黄宗霑最初抵达上海时的情形,尽管黄之所言“国产电影不如好莱坞”在当时确为事实,但这却难免会刺痛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之人的敏感神经。
而在黄宗霑即将由港返美之际,他对香港记者所说“中国缺少胜任的导演”的言论再次引来了香港电影界人士的不满与抨击。导演杨工良对此说法“极表反感”,他认为黄根本不了解中国电影的生存环境:“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理解目前中国电影的环境,如果把目前粤语片制作的情形来说,限着用三四万元港币品拍成一部片子,黄宗沾(注:原文如此)可有这种把握吗?言时大有倘我亦生长在荷里活,也必成闻名世界的大导演了之慨!”(36)海马:《黄宗沾评中国电影,香港影界的反应!》,《东风画报》1948年第23期。言下之意便是黄宗霑并无什么特殊才华可言,只不过是沾了身处好莱坞的光罢了。杨工良的这番话固然过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对于黄宗霑过于直接、不留情面的说话方式的些许不适。也许这并不难理解,自幼成长于美国的黄宗霑实属名副其实的“香蕉人”,尽管长相与国人无异,但中国话仅会寥寥几句,对于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客套礼仪”更是不甚精通,“除了皮肤不脱黄帝华胄的色彩之外,和美国人没有什么两样”(37)小勉:《黄宗沾一席谈》,《电影杂志(上海1947)》1948年第14期。。
针对黄宗霑的“傲慢”言论,演员邝山笑则由此开始揣度这位华裔导演来华拍片的“真实”动机:“黄宗沾(注:原文如此)简直是美帝国资本主义的尾巴。他这次回国实在是一种替《骆驼祥子》宣传的工具,而且不相信拍这部片子是他投资的,可能是美商投资的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因为拍黄包车夫的生活,恐怕惹起了有辱华的反感!所以便推在黄宗沾的身上,冀能掩饰中国人的耳目,避免舆情的痛击,而影响将来该片在远东方面的营业,同时,对黄宗沾以一个摄影师资格的身份,对中国电影肆意评判是很不应该的。”(38)海马:《黄宗沾评中国电影,香港影界的反应!》,《东风画报》1948年第23期。尽管邝山笑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说法在事实层面根本立不住脚,但他有一点却似乎说得不错,那就是由外国人来拍“黄包车夫”这一题材的电影确实容易引起“辱华”的争议。事实上,当时很多人都对黄宗霑将“黄包车夫”作为拍摄对象感到不悦,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华侨身份,就更容易会让人联想到这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外国人在刻意消费中国的苦难与落后。尤其是当黄宗霑因在北平找不到人力车夫而感到苦恼时,这种批评就更是接踵而来。
黄宗霑之所以要亲自回国考察取景,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真实还原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所呈现出的北京风貌,所以当他亲眼目睹1948年的北京“满街跑的都是三轮,稀稀落落的有几部洋车”(39)《〈骆驼祥子〉拍片难:北平难找合理想之男主角黄宗霑大伤脑筋!》,《东亚声》1948年6月1日。时,自然会感到有些失望与遗憾。对于一个有些“艺术偏执”的导演来说,产生这种情绪本来再正常不过,但国内一些人却拿其“美籍华人”的身份大做文章,刻意强调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鼎鼎大名的摄影师黄宗霑到北平觅取《骆驼祥子》外景,他是‘美国月亮’那里来的人,为了看不见人力车而愁眉不展。真的,我们‘泱泱大国’怎么会使离开祖国数十年的黄先生失望呢?我想黄先生要是早在十年前来的话,一定会能欣赏黄帝子孙的特别技能,用上帝赐予的力气,代替了不会哭笑的牛马;用呻吟哮喘,代替了悲鸣;坐车客人的脚,代替了皮鞭……这许多‘精彩豪华’的场面,美妙动人的镜头,黄先生来不及收进‘开麦拉’里去,岂不可惜。”(40)《黄宗霑开穷人心,他不懂黄色窝头》,《戏世界》1948年第379期。该文用词极尽挖苦和讽刺,不露声色地对黄宗霑“消费苦难”的行为进行了调侃与批评,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为了利益只盯着中国苦难的黄宗霑的负面形象。
在最初,针对黄宗霑的批评只是存在于电影领域,但当它真正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事件时,很多其他行业的人也加入到批评的行列之中。左翼作家许杰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那篇著名的《论〈骆驼祥子〉》的开头,便表达了对于以黄宗霑为代表的好莱坞从业者的不满与质疑:“前些日子,报纸上不是时常在登载着美国华侨摄影师飞来北平拍摄骆驼祥子的消息吗?这自然该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可是,听说这位摄影师到了北平之后,看见北平市上的人力车夫已经渐次的受到了三轮车夫的淘汰,而人力车的阵势,也没有祥子时代的鼎盛,这就未免使得我们这位华侨摄影师,由衷的感到不少的失望。中国的社会,竟然也会进步的,祥子时代的人力车的鼎盛气象,竟然将会化成历史的陈迹,这又怎不使那些想了解一些中国国情的高鼻子们,微微的感到一些惆怅呢?”(41)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1948年第1期。不过许杰提及黄宗霑只是将其作为引子,其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引出后面对于《骆驼祥子》小说文本的评判。纵览该文其基调以批评为主,主要对《骆驼祥子》所表现出的“政治不正确”做出了批评。
根据笔者归纳,许杰认为该作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虽“如实地报告客观的真实”,却没能把祥子堕落毁灭的真正原因明确地告诉读者;二是虽对“个人主义”给予否定和批判,却并没有给中国和中国人指出或暗示出一条正确的出路,这条在许杰看来“正确的路”也被老舍漠视和歪曲了;三是对祥子结局的处理过于主观化,缺乏合理性;四是对性生活的描写过分用力,甚至有“崇洋媚外”之嫌。如果单从前三点来看,尽管这些批评带有一定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但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文本的就事论事。但从第四点对于老舍创作动机的揣测来看,许杰显然是先入为主地受到了黄宗霑电影改编事件影响:“……中国的新生运动的潜力,反是被漠视被歪曲了,而代之而取得决定性的地位的,却是有意无意的性生活的强调的描写。我的推测,这或者就是讨得高鼻子们的注意与好感的原因吧!”(42)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1948年第1期。
尽管依笔者之见,许杰并没有明确指出老舍所谓对“性生活的强调的描写”就是为了博人眼球、创造卖点、讨得外国人的欢心,但“有意无意”一词的使用也很难让人不产生这方面的联想。宋剑华教授甚至更加肯定地认为,许杰之所以在文章开篇就提及《骆驼祥子》风靡美国的事实,其用意就是在暗讽老舍的“崇洋媚外”:“文章开篇便以讽刺的口吻,将林语堂和老舍联系起来,暗喻他们两人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流行,完全是一种卑躬屈膝、向洋人献媚的丑恶行径。”(43)宋剑华:《〈骆驼祥子〉是怎么成为文学经典的?》,《东吴学术》2018年第1期。《骆驼祥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实,在一些人的眼里竟然成为了老舍“崇洋媚外”的“罪证”,这恐怕也是老舍本人始料未及的。尽管许杰的这篇文章发表之时(1948年10月),老舍仍在美国,但相信老舍对于国内这一类的批评应该不会视而不见,甚至是有所忌惮的,这可能也是让他最终放弃和黄宗霑合作的原因之一。那段时间的老舍正与黄宗霑因剧本修改问题而发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前者内心深处恐怕早已萌生了放弃合作的念头,再加上国内对老舍本人及其作品的批评又甚嚣尘上,也许这就更坚定了老舍放弃的决心。
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老舍何时做出了放弃与黄宗霑合作的决定,但据1948年11月3日出版的《申报》报道来看,此时黄宗霑方面业已放弃了拍摄的计划:“泛美公司(指前文提及的泛太平洋公司:笔者注)以《骆驼祥子》一书业已过时,多数反对摄制,黄本人因工本浩大,亦不拟自费拍摄。”(44)《〈骆驼祥子〉上银幕成泡影》,《申报》1948年11月3日。大约一个月后,老舍在写给乔志高的信件中也终于明确表示:“电影事搁浅,nothing doing!”(45)老舍:《书信·致高克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28页。根据《申报》的叙述可知,黄宗霑最终还是没能够在改编电影一事上完全掌控全局,同伴的反对与经费的缺失,再一次成为了他“自由拍摄一部中国题材电影”的障碍;而对于老舍来说,想要自由掌控自己作品的愿望同样难以实现。在此之后,《骆驼祥子》面临着被重新修改的命运,而这分明是他在1948年参与剧本改编时就早已经历过的事情。也许那次“剧本纷争”的经历已经让老舍开始明白,当《骆驼祥子》作为一种“被争取”的对象出现时,可能就难以保留其原貌了。老舍在其后对小说内容的反复修改已经印证了这一点。或许是出于对《骆驼祥子》的爱护,抑或是顾虑类似许杰那样的批评,老舍最终放弃了把“祥子”搬上银幕的计划,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他会说出改编一事“而且或者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的原因所在吧。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误读源于人们对于事件细节掌握得不够充分,对黄宗霑改编《骆驼祥子》一事的误读便是如此。虽然这些误读并没有完全扭曲事实,但客观上造成了认知上的偏差,这使得黄宗霑与老舍在电影改编过程中的心态起伏与情感纠结无法得到还原,改编一事对于双方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自然也无法得到揭示。因此,对这一事件之中被人忽略的诸多细节进行考证,对于澄清上述误读、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的本相便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只是对于此事本相追问的一个开始,相信随着新的资料的不断涌现,关于黄宗霑改编老舍《骆驼祥子》一事的历史真相会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