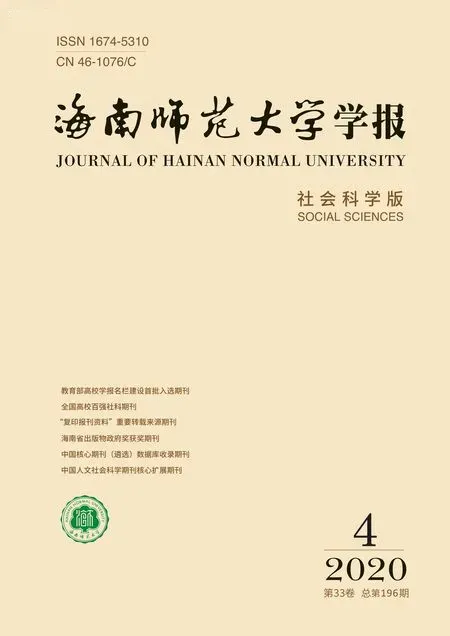犯罪与成长: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张 杰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1999年,在德国贝特斯曼文学家出版社和慕尼黑文学之家的要求下,由知名作家、评论家和日尔曼文学家各33名组成的评委会提出了一份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排名表。位居前5名的是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35票)、弗兰茨·卡夫卡的《诉讼》(32票)、托马斯·曼的《魔山》(29票)(1)前10名中,卡夫卡有两部,分别是《诉讼》与《城堡》;托马斯·曼有三部,分别是《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与《浮士德博士》。、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8票)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11票)。
这其中,卡夫卡、托马斯·曼和格拉斯对中国读者来说早已如雷贯耳,穆齐尔的作品在2000年也有了中译本,但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对中国读者来说却可能比较陌生。事实上,德布林对20世纪的德国文学影响极大,他的这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Alexanderplatz)更是被视为魏玛共和国的标志性文本,作品对文学蒙太奇手法的创造性应用以及对柏林大都会的全景式展现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虽然,他在自己的国家也曾一度被遗忘。
一、柏林的观察者
1878年,德布林出生于什切青城,在当时它是属于普鲁士治下的波美拉尼亚省的一个港口城市。父母均为归化的犹太人,父亲马克斯是一位有名的裁缝,且多才多艺;母亲苏菲则是商人之女,注重实际。两人之间矛盾重重。在德布林十岁那年,马克斯抛妻别子,与自己店内的一名年轻女工私奔到美国,苏菲则带着五个孩子迁至柏林,在工人阶级聚居的东区找到一个破旧的公寓艰难度日。不过第二年,马克斯就身无分文地回来了,夫妻二人短暂和好,全家迁至汉堡。随后,妻子发现丈夫其实是带着情人一块回来的,在此期间他一直过着双重家庭生活。于是,苏菲再次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柏林。从此,德布林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岁月。
父亲的突然消失在年幼的德布林心中构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加上社会地位的下降和生活经历的急剧变动,他成了一个具有反叛性格的学生。由父亲而遗传的艺术气质也在此时显现,他对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等哲学家、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舅舅、大哥等亲人的资助下,德布林顺利通过高中毕业会考,考入威廉大学(即现在的柏林洪堡大学)。后又转入弗莱堡大学专攻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1905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精神病医师。之后他在柏林近郊的布赫做过助理医生,并于1911年在富裕的柏林西区开设诊所。1913年,他将诊所迁至柏林东区的法兰克福大街184号(1919年又移到该大街340号)。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弃医从文的例子,如鲁迅、郭沫若等,德布林则是行医与创作并举。早在求学期间,他就开始文学创作,1912年首部长篇小说《黑幕》(DerSchwarzeVorhang)发表在表现主义杂志《风暴》(DerSturm)上,探讨的主题关乎爱、恨与性虐待狂。该杂志由赫尔瓦特·瓦尔登在1910年创办,其内容先锋而激进,对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最新的文艺思潮均大力扶持。德布林很快就成为《风暴》的主要撰稿人,并在瓦尔登的介绍下,进入了表现主义运动的圈子,由此逐渐结识诸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
1913年,德布林把短篇小说《谋杀蒲公英》(DieErmordungeinerButterblume)及其他一些作品以合集形式出版,内容大多仍以展示人的精神病态和性倒错现象为主。显然,精神病理学专业及其医疗实践是他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之后,德布林创作了几部重要的历史小说,如1916年的《王伦三跳》(DiedreiSprüngedesWang-lun),该部作品以18世纪乾隆年间的起义为历史背景,影射了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现实。《王伦三跳》为德布林赢得了文学界和公众的认可,他因此一举成名,并获得著名的冯塔纳德国文学奖(2)在此之前即1915年,弗兰兹·卡夫卡因短篇小说《司炉工》荣获该奖。。一战期间,他以德国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为背景创作了大型史诗性著作《华伦斯坦》(Wallenstein,1920)。尽管批评界对其给予了广泛好评,但德布林却觉得泛泛的肯定还不够,于是带着满心委屈写下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对批评界进行了嘲讽。1927年,他又创作了有关印度神话的史诗《玛纳斯》(Manas)和哲学著作《自然之上的我》(DasIchüberderNatur),结果公众对这两部作品都不买账。尽管此时他在托马斯·曼的帮助下进入了普鲁士艺术学院,在知识界已颇具声望,但是在文学上他并没得到他所期望的肯定,经济状况也很不如意。为此,他一度表达了自己想要放弃文学创作的困惑。
危机亦是转机。1927年秋天,德布林突然意识到自己该写什么了,那就是他日日生活在其中的柏林大都会。在柏林东区居住了三四十年,他对此地早已无比熟悉。德布林一直是个勤奋的观察者,甚至对出没于此的小偷、流氓、妓女等在内的“小人物”都非常了解。但与之相悖的是,之前他的大部分精力却投注到了历史小说的写作。当沃尔特·鲁特曼的无声纪录片《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SymphonyoftheMetropolis)在1927年9月23日正式上映时,其城市主题触动了正处于低谷的德布林。次年,朋友马里奥·冯·布科维奇以柏林为主题的摄影作品《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Berlin,PortraitofaCity)出版,德布林为之写了前言。这两件发生在当代艺术界的事件改变了德布林的创作方向。
1927年10月,德布林已开始《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写作,至1929年春,作品打印完毕,《法兰克福日报》在1929年9月8日至10月11日间分期连载。与此同时,书稿于10月得以正式刊印,首印一万册。对这部书写柏林的长篇巨著,评论家们一致表达了赞美与肯定。媒体也迅速作出回应,认为这是当年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是德语小说的里程碑之一。更有知名评论家提议德布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3)Gabriele Sander, “Döblin’s Berlin: The Story of Franz Biberkopf”, Roland Dollinger, Wulf Koepke, and Heidi Tewarson, e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Alfred Döblin.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04, p145.。由此,该作品迅速成为畅销书,而且是德布林继《王伦三跳》之后最为畅销的著作。此后,该书不断再版,至1933年已经出版了五万册。很快,又被译为意、丹、英、西、法、瑞典、俄、捷克等多种语言,并被改编为广播剧、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今日看来,《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如此之畅销着实有些匪夷所思,因为它在形式上的创新超越了人们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解能力:作者采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将圣经故事、希腊神话故事、新闻报道、天气预报、流行歌曲、科学研究、柏林屠宰场、统计数字等诸内容统统插入文本之中,这些内容之间有时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德布林有时干脆将从报纸上剪下的诗歌作品、各种绝然相异的政治见解用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直接粘贴到小说手稿中(4)Stenzel, Jürgen, “Mit Kleister und Schere. Zur Handschrift von Berlin Alexanderplatz”, Text + Kritik 13/14: Alfred Döblin ,1972,p39-44.,而小说的中心故事是一个名叫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的男人在柏林的生存经历。
二、大都市的史诗
小说主人公毕勃科普夫最初是个普通的家具搬运工,在与女友伊达吵架时将其殴打致死,为此被判入狱四年。小说从他刑满释放开始。毕勃科普夫胆战心惊地离开监狱,坐着41路电车进入柏林城,一心要重新开始,虽与拉斯蒂涅或于连要挑战巴黎城的气势相差太远,却也发誓从此规矩做人,以正直诚实立足于世。他最先是靠卖领带夹、报纸、鞋带谋生,后来因为一个叫吕德斯的小人深受打击,一度陷入酗酒与无所事事之中,并因此在柏林城内躲起来,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他重操卖报旧业,在酒馆里认识了一名叫赖因霍尔德的男人,从此被卷入一个以偷盗为主要行径的犯罪团伙。这个赖因霍尔德修长、苗条,与粗壮的毕勃科普夫恰成鲜明的对比。前者的眼睛写满忧伤,这对后者产生了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吸引力。一方面,毕勃科普夫清楚地知道赖因霍尔德的犯罪行动,另一方面,他却又迷迷糊糊地参与了对方的犯罪过程,其间又自居于道德评判者,赖因霍尔德残忍地将其推下汽车,导致他失去了一条胳膊。这惨痛的教训并没有激励毕勃科普夫去告发这个犯罪团伙。相反,仅靠左胳膊生存的他却继续与赖因霍尔德等人来往,并正式加入犯罪团伙,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偷盗行动。毕勃科普夫经济上富裕了,爱情上也很顺利,洋洋得意的他向赖因霍尔德炫耀自己的新女友——可爱又年轻的米泽,引起了对方觊觎之心。单纯的米泽想从赖因霍尔德那里知道毕勃科普夫为何丢掉一只胳膊,后者借机将她引诱到郊外。米泽知道事实真相后惨遭杀害并被悄悄地埋在树林。很长时间以后,毕勃科普夫方在知晓事情真相后精神崩溃,他被送到布赫精神病院——1906年10月至1908年6月,德布林曾在这家精神病院做过助理医生。
据说,作品在最初付梓前只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这一个正标题,后来在出版商的要求下增加了一个副标题“毕勃科普夫的故事”(DieGeschichtevomFranzBiberkopf)。毕勃科普夫无疑是一个并不高尚的小人物。在作品中他主要就是在以亚历山大广场为中心、半径一千米的范围内活动。题目将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与这样一个小人物并举,两者间的等级关系因此极为鲜明,大都市的史诗与一个普通犯罪分子的故事之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张力。(5)Gabriele Sander, “Döblin’s Berlin: The Story of Franz Biberkopf”, Roland Dollinger, Wulf Koepke, and Heidi Tewarson, e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Alfred Döblin, p143.译者罗炜先生在《译本序》中指出,对该部作品有以下几种常见的阅读方式:犯罪小说、大城市小说、宗教小说、政治小说及哲理小说。(6)[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译本序》,罗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5-7页。说其是犯罪小说,乃是侧重于毕勃科普夫的犯罪行为;而将其定性为大城市小说,则是因为作品对柏林的全景式展现。虽然毕勃科普夫殴打女友、酗酒,又拉皮条、当小偷,但如果说作品就是一部情节紧张、引人入胜的犯罪小说又似乎过于简单化。
首先,叙事者的语气非常冷漠、客观,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认为,德国剧院里使用了一种“使观众跟舞台上表现的事件保持距离的表演技术”,“演员并不用奔放无羁的感情来刺激观众的情绪,也不用亲切动人的表情来抓住观众的心神”,而是与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动作保持相当的距离,布莱希特称之为“间离效果”。为了达到这种间离效果,剧本会采取一些手段,比如“利用第三人称”(7)[德]贝·布莱希特:《间离效果》,邵牧君译,《电影艺术译丛》1979年第3期。。
1925年,布莱希特与德布林因共同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讨论小组而结识。德布林比布莱希特年长二十岁,此时前者在文坛上早已声名显赫,后者也因其卓越的剧评和剧本创作而在戏剧界有了一定知名度,并受邀担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布莱希特将德布林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王伦三跳》启发他提出了“史诗戏剧”理论(8)Schoeller, Wilfried F, Alfred Döblin: Eine Biographie, Munich: Carl Hanser, 2011, p160.,而反过来,布莱希特就戏剧提出的“间离效果”理论显然也影响到了德布林的文学创作。
比如,小说中毕勃科普夫殴打女友伊达时,她的死亡过程被叙事者一段段地分解,“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女人的以下器官首先受到了轻度损伤:鼻尖及鼻中部的表皮,表皮以下的骨头和软骨,但这些却是到了医院之后才被发现,并在日后作为法庭案卷发挥作用。此外,右肩和左肩处轻度压伤,并伴有出血。”(9)[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83页。读者会感觉到似乎有个法医在对伊达的身体做死亡鉴定。“他的手上只拿了一只小小的、木质的掼奶油用的搅拌器,因为他那时就已开始了训练并因此而扭伤了自己的手。他通过两次剧烈的挥舞,使这只缠有金属螺纹线的搅拌器同对话的女伴伊达的胸部发生碰撞。”(10)[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84页。叙事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以一种无关痛痒的语气对女性脆弱的身体承受致命重击这一惨象进行描述。“早在第一次撞击的时候,她就嗷嗷地嚎叫起来,不再说下流胚,而只顾着喊哎呀了。第二个动作是在伊达的右边,是通过弗兰茨旋转四分之一圈之后稳稳立定的姿势来完成的。”(11)[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84页。弗兰茨的殴打是毫无预谋的,殴打的结果却像是经过精心计算与规划的,一个“四分之一圈”如同记录科学实验的数据一样毫无感情。
其次,德布林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形式实验,将《圣经》、神话、流行歌曲、新闻报道等众多文本片段以高密度的蒙太奇方式嵌入文本,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情节的紧张度。
蒙太奇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最早被延伸到电影艺术中,成为电影创作的主要叙述手段和表现手段之一,即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距离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或剪辑在一起。后来,这种手法在视觉艺术等衍生领域被广为运用。运用在文学上,蒙太奇就是把语言、文体和内容等来源不同,甚至风格迥异的部分并列或拼合在一起。
前文所提及的《柏林:城市交响曲》即是用蒙太奇的拍摄手法,将运转的机器、转动的车轮、匆匆赶往工厂的工人转化成富有动感的画面,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始终流动的城市生活,一部“视觉的交响乐”。这样的手法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小说完全就是蒙太奇的产物,因此有人称之为“电影式的写作方法”。如在写亚历山大广场一带人山人海时,德布林将各种相关事物高密度地拼接在一起。
小酒馆、餐厅,水果和蔬菜交易,殖民地出产的农副产品以及珍馐美食,搬运站,装饰画,女装制作,面粉和各类磨坊产品,车库,救火组织:微型电动消防水龙头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操作简便,重量轻,体积小。——德国的民众们,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受到如此卑鄙的诱惑,受到如此卑鄙的不公正的欺骗。……——排水用具,窗户清洁协会,睡眠是良药,施奈内尔的天堂之床。——租房者保护法是一堆废纸。房租不断地上涨,中等工商阶层被赶到大街上并以这种方式被扼杀,法院工作的执行人员却保持着丰厚的收益。我们要求国家对小工商企业发放一万五千马克以下的贷款,立即禁止所有对小工商经营者的财产扣押。——以充分的准备来迎接那个痛苦的时刻是每个女人的愿望和义务……——请参加一家瑞士生命保险公司,苏黎世养老基金机构的生命保险,以使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有所保障。——您将高兴得心花怒放,如果您拥有一个用著名的赫夫勒牌家具布置的家。(12)[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104-105页。”
这段文字包含了现代都市中的日常生活、物质消费、政治演讲、广告宣传,等等,内容庞杂多样,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它们相互之间跳跃度极大,在语气、社会性、意识形态上均呈现出较大的张力,而围绕在亚历山大广场周围的世间百态也就以令读者如此眼花缭乱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于是,这些纷繁复杂的事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互文性。事实上,在德布林写作的这两年,亚历山大广场的确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挖掘机和电钻日日轰鸣,城市的内脏以前所未有的物理深度展露在公众面前。公共汽车、地铁不间断地运转,在它们的车轮下,亚历山大广场颤抖着。以这座广场及其周边的发展为代表,柏林整个就是一座充满噪音与躁动的大都市。在这样的喧嚣中,读者好像听不到作者的声音,他基本上是退隐的,只在每章开头的题词中露面。德布林甚至把力学公式放在了小说中。当可怜的伊达被毕勃科普夫打死,小说用力学定律对此过程做了分析。
这个女子的胸部在一秒钟之前的经历同僵硬和弹性、碰撞和对立的定律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不了解这些法则,就根本无从谈起。人们将借助以下公式:
牛顿(流腾)第一定律,其内容是:然后物体,只要没有外力作用推动它去改变它的状态,它就始终保持静止状态(比如伊达的肋骨)。流腾第二运动定律:运动的改变与作用力之间是成正比的,它们的方向相同(作用力是弗兰茨,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胳臂和他的握有内容物的拳头)。力的大小由以下公式表示:
……(13)[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84页。
严谨的力学定律和物理公式无疑给读者增加了阅读障碍,而且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事实上,很多批评家对这种极度的蒙太奇手法是有所质疑的,尤其是这些看似杂乱无序的材料会让读者完全无所适从。不过在制造阅读障碍的过程中,小说于无形中消解了毕勃科普夫行为的残忍和伊达遭遇的不幸。
为了提高学生主动性,我们小学语文老师可以采用丰富教学方式的办法,先吸引学生兴趣,继而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程度,最后达到提高其主动性的目的。比如说多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他可以帮助小学生理解课文中描绘的一些场景、人物和事件,因为小学生所学知识还是有限,有些即使有知道的理解也不一定全面深刻,因此我们小学语文老师可以通过播放视频、展示图画等方式为小学生创设情境,不但让小学生身临其境,也提高了其学习的兴趣,促使其主动学习。例如,在讲解《桂林山水》这篇课文时,除了去过桂林亲眼见过这种景色的学生能够回忆起见过的山水进而与作者共鸣,其他学生如果不是看了老师准备的图画和视频将很难仅凭想象有所深刻的理解。
小说的蒙太奇手段不仅表现在素材、物质的堆积上,而且还将情节、意识流、叙事者独白等糅合在一起。
按理说,赖因霍尔德杀害米泽的场景应该是典型的犯罪场景,但因蒙太奇手法的使用使整个场景充满了梦幻感。
两手冰凉,两脚冰凉,原来是他干的。“你现在躺下去,放乖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个杀人犯。“你这个不要脸的狗东西,你这个流氓。”他红光满面地说道:“看哪。你只管叫,叫个够。”你就会听话的。她在吼叫,她在嚎啕:“你这个狗东西,你想杀死他,是你剥夺了他的幸福,现在你又要来占有我,你这个下流胚。”“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
它的时日!它的时日!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时日。扼杀与治愈,打碎与建造,撕碎与缝合,它的时日。她扑倒在地,企图逃跑。他们在那个坑里搏斗。救命弗兰茨。
……
他跪在她的背上,他的一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两只拇指陷进脖颈子里,她的身体开始发紧,开始发紧,她的身体开始发紧。它的时日,出生与死亡,出生与死亡,每一样东西。
……
威力,威力,有个割草人,他拥有来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威力。放开我。她还在扭动,她在不停地扑腾,她在后面踢打。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办妥的,群狗可以来了,可以吃你剩下来的东西了。(14)[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333-334页。
1927年10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德译本出版。乔伊斯对德布林的创作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充分表现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大量使用的意识流手法。在米泽被害这一部分,赖因霍尔德与米泽的意识流和心理活动交替出现,显现出极大的跳跃性。同时,叙事者以无动于衷的悲观情怀旁观这两个拼死争斗的男女,又似乎消解、淡化了意识流的这种跳跃性。作品中还插入《圣经》中的文本,其中的“割草人”即死神,它终将取走每个个体的生命。小说中残忍的杀人过程、米泽的死因此呈现出一定的宿命色彩。对这样充满跳跃性、实验性乃至宗教性的文本,将作品定性为犯罪小说的确有些失之于浅显。
本雅明对德布林的蒙太奇手法表示了肯定。1930年,本雅明在《社会》(DieGesellschaf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小说的危机:关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提出,蒙太奇就是这部小说“主导性的文体风格”。在他看来,用蒙太奇手法堆积起来的这些材料绝对不是随意组合的,它们服务于作品的叙事,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本真的材料、材料的本真性赋予作品的叙事。本雅明认为,小说的框架因蒙太奇而发生了内爆,作品在文体与结构上都突破了小说的界限,因此最重要的是,这种创作方式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史诗性作品的可能性”。在这里,本雅明是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视为史诗,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更不要说是犯罪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品中插入的圣经诗歌、统计数字、流行歌曲等内容就相当于传统史诗中的诗行。(15)Walter Benjamin, “The Crisis of the Novel on Alfred Doeblin, Berlin Alexanderplatz: Die Geschichte von Franz Biberkopf”, Selected Writings, Vol.2, Part 2: 1931-1934.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eds., 1999, p301.
最后,主人公毕勃科普夫这个复杂形象的历变过程及其结局,也是不能将作品视为犯罪小说的原因。
毕勃科普夫完全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一个粗鲁大汉那样简单。小说一开始,被释的毕勃科普夫紧靠着监狱的红色大墙不想走,四年的与世隔绝令他对喧嚣的柏林充满恐惧。他甚至认为释放对他来说亦是一种惩罚。重新置身于喧嚣的人群中,毕勃科普夫感觉“像是坐在牙医那里,很像牙医用铁钳子钳住一颗牙往外拔,疼痛加剧,脑袋快要爆炸了”(16)[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4页。;看见一对进餐的情侣用刀叉将肉送进嘴里,他的身体立即抖作一团;走在大街上,他甚至还担心屋顶会坍塌下来。作为精神病医师,德布林无疑是相当敏感的,他能够察觉到个体在长久与社会隔绝之后会对现实产生不可避免的恐惧与陌生感。总之,柏林热闹的大街和流动不息的人群在毕勃科普夫心中呈现为充满敌意、混乱的形象,他因此惊恐害怕,神经错乱——这正是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文学版再现。显然,毕勃科普夫并不是一个动物般粗放的生存者,恰恰相反,都市对个体精神活动的影响在他身上有细腻的呈现。毕勃科普夫他天性并不坏,只是在冲动状态下容易诉诸酒精和暴力,显得无知又野蛮;他并未蓄谋去犯罪,虽然他在犯罪后也并不忏悔。在男女关系上,毕勃科普夫非常放纵。与波兰女人莉娜相处时,他趁挨家挨户上门卖鞋带的机会与一名寡妇偷欢并赚取了超额金钱。随后他将此艳遇告诉同伴吕德斯,后者出于嫉妒,跑到寡妇家打劫,毕勃科普夫再次登门寡妇家时就吃了闭门羹。他很是受挫,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莉娜,并在柏林城内消失了很长时间,应该说这次打击是他咎由自取。后来,毕勃科普夫与赖因霍尔德私交甚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后者源源不断地为前者提供女人,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不齿关系:每当赖因霍尔德对身边的女人产生厌倦想彻底甩掉时,他就让这个女人带着礼物到毕勃科普夫那里由其收留,直到下一个被赖因霍尔德厌恶的女人再来投靠毕勃科普夫。当然,毕勃科普夫也会想办法将上一个女人转手送给别人。两个男人之间这样的交易进行了很多次,简直可以说是“红火”,彼此都心照不宣,欢天喜地,兴奋不已。由此不难理解,当毕勃科普夫得到漂亮又单纯的米泽时,他为何忍不住要向赖因霍尔德炫耀。
毕勃科普夫打死前女友,这就说明在其性格中潜藏着一种致命的攻击性。后来,当米泽告诉他,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时,他将米泽也狠狠地打了一顿,且又一次差点将其打死。德布林一边将毕勃科普夫塑造为野蛮的、没有自制力的、毫无道德感的女性杀戮者,一边还插入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瑞斯特亚》中复仇女神追赶奥瑞斯特亚的片段。毕勃科普夫与奥瑞斯特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因为经典悲剧中的英雄们都是秉持道德原则、善于自我反思的(17)Gabriele Sander, “Döblin’s Berlin: The Story of Franz Biberkopf”, Roland Dollinger, Wulf Koepke, and Heidi Tewarson, e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Alfred Döblin, p157.,俄狄浦斯没有逃脱杀父娶母的命运,自残双眼而流亡他乡;奥瑞斯特亚的杀母之举受到了复仇女神的追杀,他的内心惊恐而接近疯狂。但是,毕勃科普夫在四年牢狱之刑后,却并没有带着忏悔自责之心回到人群,他甚至还很快就去找了伊达的妹妹米娜,并以类乎强奸的方式将其征服。同样犯了诛杀之罪,古典悲剧与现代都市的主人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认知与赎罪方式,显示出当代都市伦理价值观的变异。
由于毕勃科普夫的粗鲁、攻击性、偷盗等行为,德布林受到了诸如《左翼路线》这类无产阶级革命刊物的激烈批判。后者指责毕勃科普夫这个形象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目标,他虽然是工人,却谈不上任何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工人发生冲突,售卖种族报纸,还自我辩护说他拥护秩序。这样一个形象,要么会成为纳粹运动的追随者,要么会因沉迷于肉欲、暴力、偷盗而完全堕落。对此,读者和作者都应对其予以批判和否定。
不过,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却与现代大都会的精神风貌有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独臂的毕勃科普夫接受了女友米泽通过做妓女赚钱养他的现实。米泽虽然单纯可爱,但在赚钱养家上却毫不含糊,她以毕勃科普夫作为坚实的感情后盾,以一个银行家作为强大的经济盾牌,巧妙地维系着两个男人间的平衡。米泽还与卡尔约会,这个小伙子是与毕勃科普夫一起参与偷盗行为的白铁工,甚至对赖因霍尔德,她也并不反感。米泽知道赖因霍尔德对她别有用心,却仍然接受他的邀请,跟他手拉着手走进郊外森林,并允许他对自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亲密接触。小说中,德布林还曾插入一则新闻,讲的是一个女人想要通过合同解决两位丈夫的性生活,以印证米泽这种行为的普遍性。种种看似无章法的乱性行为,正是当时道德崩塌、沉迷享乐的柏林所产生的怪现状。
三、结语
由于家庭境遇的不幸,德布林在贫困的柏林东区成长、受教育。后来,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上升为中产阶级,又回这里开设诊所,病人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妓女、小贩等底层民众。尽管如此,德布林并没有效仿霍普特曼,以追求绝对真实的自然主义笔法书写底层民众肮脏、丑陋的生活。他在日常工作中治疗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疾病、精神创伤;而在进入写作状态时,又努力探索以毕博科普夫为中心的众多小人物之灵魂。由毕博科普夫、米泽、赖因霍尔德等形象蔓延开去,德布林通过解析这些个体的灵魂,进而试图把握柏林这座城市的灵魂;或者说,展示这座城市的社会悲剧和底层人物的精神伤痛,乃是他思考人类灵魂这一伟大工程的一部分。小说中有一“柏林屠宰场”片段(18)[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罗炜译,第117-124页。,题为“因为人和畜生一样;它怎么死,他也怎么死”。该片段用了大量篇幅书写动物面对被屠宰命运的无奈,只在最后一小段交代躲起来的毕博科普夫在柏林某陋室蹲了俩星期,即将被房东驱逐。人与动物共同面临不可抗拒的暴力,象征着一战后的柏林,乃至整个德国民众不得不承受的现实困境、政治暴力及他们内心的脆弱与绝望。因此,精神分析在一战后的柏林一度非常火爆。(19)Fuechtner Veronika, Berlin Psychoanalytic: 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e in Weimar Republic German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17. 其实,在一战期间很多人出现了精神焦虑、精神创伤,精神分析这门专业及像德布林这样的精神分析医生的地位与重要性随即上升。1914年12月,德布林在西线作为战地医生服务,治疗了很多染上战争神经症(war neurotics)的患者。
后世批评家在谈论大都市小说时认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标杆。不仅因为德布林以亚历山大广场为中心,将柏林的众生百态悉数囊入其中,以及他在文本形式上的大胆试验,更重要的是他塑造出毕勃科普夫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在经历了混沌、无知、纵欲、迷乱、幸福之后,米泽的死一度让毕博科普夫精神崩溃;之后经精神病院救治而康复后,他改邪归正,安安静静地在一家工厂做门卫。旧的、野蛮无知的毕勃科普夫已经死去,新的、成熟稳重的毕勃科普夫表现出生存于人群之中应具有的理性。在此意义上,本雅明认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一种承继,它可以被视为欧洲资产阶级教育小说“最极端、最令人眩晕、最后同时也是最高级的阶段”(20)Walter Benjamin. “The Crisis of the Novel on Alfred Doeblin, Berlin Alexanderplatz: Die Geschichte von Franz Biberkopf”,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2, Part 2: 1931-1934.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eds., 1999, p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