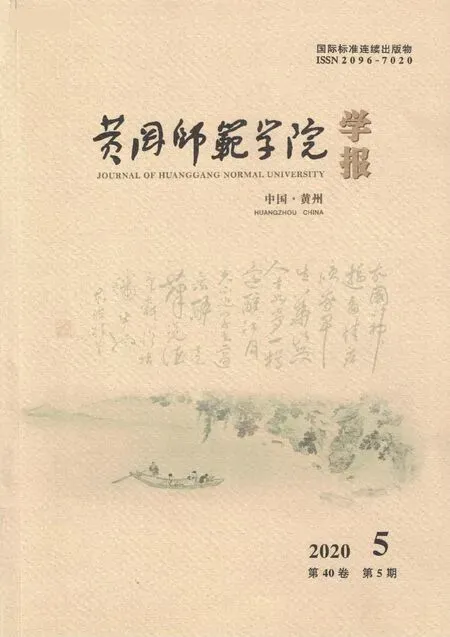旧剧革新的多重可能性
——欧阳予倩话剧本《桃花扇》的前世今生
金宏宇,李玫琦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夏衍曾说:“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1]而在三人之中,欧阳予倩又是资格最老的一位。他以伶人的身份进入戏剧界,后来又担任过导演、编剧等,涉猎话剧、京剧、桂戏、电影等诸多相关艺术领域。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扇》,因其丰富的形式和版本,恰好可以成为反映他各领域成就的典例。当代研究者提及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时,认为“在种种改编形式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其话剧改编本”[2],也有学者认为其“因为创作时代局限,作品政治功利目的过于突出,在唤起观者神圣感崇高感方面,略输原著一筹”[3],可见对话剧本《桃花扇》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本文则认为,对于《桃花扇》这样一个形式丰富、版本众多的作品而言,仅谈论其话剧形式不足以见出欧阳予倩为之所倾注的多年心血。因为早在1947年新中国剧社演出台本《桃花扇》(也即目前可见的欧阳予倩著《桃花扇》话剧初版本)出版以前,欧阳予倩已经以《桃花扇》原著为蓝本创作了诸多版本的作品:1934年,他自编自导的有声影片《新桃花扇》即是借助与原著相同的框架讲述革命故事;1937年上海沦陷期间,他修改了孔尚任原著的结局,排演了改良平剧《桃花扇》;1939年在广西桂林,他以桂戏改革为契机,又一次将其京剧本《桃花扇》改为桂剧本,上演后获得热烈回应。由上可见,《桃花扇》的电影本、京剧本和桂剧本,其实是欧阳予倩话剧本《桃花扇》的创作基础和重要来源。因此,从广义的版本学视角来说,这些形式都应纳入欧阳予倩著《桃花扇》的版本谱系,以便于更全面地梳理《桃花扇》的版本变迁过程①。从欧阳予倩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编中,我们也可以探究《桃花扇》作为一部清代戏剧得以长盛不衰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并探索旧剧革新的多重可能性。
一、夺胎换骨之作:电影《新桃花扇》
电影《新桃花扇》作为欧阳予倩编导的第一部有声影片,也是他归国后重登影坛的第一部作品。1932年冬天,他前往欧洲考察戏剧,一直到1934年秋天才回来,恰逢此时上海电影业蒸蒸日上,新的制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是他应张善琨的邀请加入对方刚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为他们编导一部新片。按照原先的剧本,这只是一部搬上银幕的古装片,然而在欧阳予倩看来,“这陈旧故事没有多大意义”[4],于是就将其改写为现代剧。而《新桃花扇》这一标题是张善琨从票房出发而确定的,所要邀请的演员名单也已大致拟定。因此,欧阳予倩实际上是在一个大致确定的框架内进行编剧与导演[5]。
从1936年刊登在《文学丛报》上的电影剧本来看,《新桃花扇》依然遵循了孔尚任原著的情节框架和大致的人物关系,但其内容却充满了革命色彩:男主人公是“北伐”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青年方与民,因创办进步报纸、鼓吹革命而为军阀所忌;女主人公是著名演员谢素芳,因受邀参演方与民编的戏而结识对方。此外,孔氏原著中左右逢源的杨文聪、奸佞腐朽的马士英、媚上欺下的阮大铖、刚正不阿的柳敬亭与苏昆生也分别可以与电影中的方与民同学孙道诚、督军张德凯、秘书刁俟轩和谢素芳师傅苏菊生一一对应。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与《桃花扇》如出一辙,然而讲述的却是“以一对进步的青年男女为骨干,斗争的对象有军阀、买办和不自爱的知识分子”[5],其戏仿用意可谓相当明显。
欧阳予倩筹备《新桃花扇》的时候,正是中国电影业的转型时期。一方面,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心理,使制片人和观众的目光离开了原先的商业类型电影,转而追求可以“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与革命文艺的倾向性原则结合起来”[6]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因此,在欧阳予倩归国的前一年,也即被后人称之为“中国电影年”的1933年,《姊妹花》《渔光曲》等优秀影片层出不穷,左翼电影达到了高潮。另一方面,以有声电影、蒙太奇技巧为主要领域的电影艺术也在1934年前后通过年轻一代的创作者而得到深入的探索与拓展。欧阳予倩就曾说自己在日本考察期间开始萌生拍摄有声影片的想法,此前他拍摄的《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均为默片,而《新桃花扇》也就成为他的首部有声影片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电影中,欧阳予倩对于孔氏《桃花扇》情节的取舍和改写,已经奠定了他今后对此剧本的改编方向。
其一即是对原著中故事主干之外的枝蔓的删减。孔尚任笔下的四十出传奇剧中有近一半都并非围绕侯李故事而展开,反而在叙述史可法、左良玉的军中场景,或朝廷上下包括弘光皇帝、马士英等人在内君臣相会的状况;而在《新桃花扇》中,欧阳予倩删除了过多政治军事的正面描写,只保留了方与民打埋伏战与谢素芳重逢的场景,而将镜头集中于方与民和谢素芳的故事上,甚至不吝篇幅地细述他们如何相遇相知相爱,还在他们俩结婚以及重逢这两幕中都各加入了一段唱词,着重突出了正面人物的精神力量。
其二则是为了凸显时代特色、形成讽刺效果,欧阳予倩改写了原著中的部分情节。例如,《媚坐》中反映的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荒淫无度改成电影中军阀张德凯在家中与姨太太玩乐的腐朽奢靡,而李香君所遭受的新官田仰逼婚、弘光皇帝选妃入宫等封建社会的压迫,则改为了电影中军阀张德凯的侵犯和保护人鲁步同的骚扰。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鲁步同这个角色,当年谢家对鲁步同欠下债务而不得不依靠谢素芳唱戏来偿还,因此鲁步同的保护人身份显然是原著中李香君所在的妓院在民国社会的表现形式。电影中,孙道诚拿着从刁俟轩处领取的支票替谢素芳还清了债务、解除了保护人关系,这正如原著中杨文聪用阮大铖的银子替侯朝宗“梳拢”②李香君一样,是用金钱在封建社会制度中为女性赎回自由。欧阳予倩在此处的改写,恰好反映了他对原著中马士英、阮大铖、李贞丽(即李香君的妈妈)的角色理解,他们分别象征着强权阶级和封建家长对弱者的压迫,因而在电影中也被改写为军阀和保护人。这正如欧阳予倩所言:“从军阀混战,尤其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真叫人气破肚子。我一拿起笔来,就想尽量发泄一番。”[5]所以他笔下的场景无不反映着现实社会的真实景象。
由于有了胡倬云、余省三等颇有资历的摄制人员以及像“电影皇帝”金焰、知名女星胡萍等演员的参与,再加上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在报刊上造势,以及编导欧阳予倩自己原本就在艺术界享有的名声,电影《新桃花扇》确实在1935年引发了一阵轰动。从筹备之时开始,报上就不断出现相关评论及跟踪报道,还有不少关于主演人员的花边新闻,后来据说“新光大剧院,开映新华公司桃花扇以来,无日不卖满座”[7],本来约定除非上座率跌至预期以下,否则不会撤档,但因为后续有众多排片,所以“新华情让《桃花扇》”[8],在连演了十几天之后决定转场前往中央大戏院。甚至直到双十节,报刊上还能看到该电影公映的相关消息,可见当年的《新桃花扇》在左翼电影潮流中至少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在报刊一片叫好声中也不乏负面评价,如认为该片纯属将“舞台电影化”的“欧阳式革命传奇”[9],只是模仿孔尚任写出了“上不悖于清议之是非,下可供儿女之笑剧”[10],但在当时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的严格管控之下,这样一部讽刺当局的电影不进行删减和改拍也是难以上映的。
二、民族形式的改造:京剧《桃花扇》与桂剧《桃花扇》
拍摄完《桃花扇》以后,欧阳予倩紧接着又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三部电影并于1936年全部上映。然而1937年,随着“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他的工作重心开始由电影转移至戏剧,并与郭沫若、田汉等组织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同年11月,上海沦陷,他在租界内组织了“中华京剧团”,配合抗战救亡运动上演了多部京剧,这其中就有他改编的京剧《桃花扇》,该团的骨干成员金素琴、金素雯、葛次江、张彦堃等人也是主要演员。1939年,欧阳予倩再次来到桂林,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大力推进桂剧改革,又把两年前的京剧本《桃花扇》改写成了桂剧本。
1937年上演的京剧本《桃花扇》仅在《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有存目,其所能找的最早版本已是1959年3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而1939年的桂戏本《桃花扇》同样不见其原版本。因此对于这两个版本的考察与还原,似乎应该借助1959年单行本以及当年的相关资料。
据《上海报》1938年3月25日的一则消息称,此次上演的京剧《桃花扇》共有十四幕,分别是“楔子、惩奸、奸计、眠香、议立、却奁、新贵、拒媒、笃筵、入宫、献宝、勤王、惨睹、思痛”[11],对比原著的四十出,欧阳予倩在改写时确实经过了大幅删减,所保留的枝干部分恰好和当年电影《新桃花扇》的框架一样,主要“借了侯李的悲欢离合而去描绘当时的儒林的巽懦,朝臣的媚外,小民的疾苦”。[12]他所删去的,是原著中柳敬亭、苏昆生、史可法、左良玉等协助抗敌的具体细节,而仅以旁人转述一笔带过,从而将主要的笔墨集中于对李香君“却奁”、“守楼”、“骂筵”等正义行为的描写。作者所要凸显的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尤其是作为一个身份低贱的妓女,李香君如何在国难当头以身作则、坚守贞节,而这样的歌颂也正好适用于教育广大普通民众如何为抗战尽一己之力,这正是欧阳予倩倡导“改良平剧运动”所希望取得的成效。
事实上,欧阳予倩是最早的改良平剧支持者和实践者之一。早在五四时期,面对周作人等的“旧剧全废论”和张厚载、徐凌霄等人的“保存国粹论”之间的论争,他就提出了改良平剧的口号并付诸实践,领导南通伶工学校进行锐意改革;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欧阳予倩又加入了田汉在上海话剧界和戏剧界组织的“鱼龙会”。他认为:“我们用戏剧来宣传,决不是徒然来几句激烈的话来博一时的喝彩,是要让民众在我们所演的戏剧中,认识革命的精神,认识社会的情形,认识自己的地位。进一步说:是要世界上的人们在我们的艺术里,认识我们民族奋斗的精神。”[13]中国戏剧有着数千年的优秀传统和群众基础,比起作为舶来品的话剧或电影,它在民众中的宣传能力显然不能小觑。欧阳予倩以自己多年的伶人经验和编剧技巧,选取了这部清代传奇剧中最具时代性的情节加以改写,从而让观众能够从一个发生于明代末年的故事中看到民国的影子。不论是对傀儡福王登基的暗讽,还是对逃难情景的重现,都能够让身处上海沦陷区的观众感同身受。可以说这是欧阳予倩在民族形式改造道路上做出的成功尝试,将形式的传统性与内容的时代性结合在一起。
不过,京剧本《桃花扇》最大的改动还在于其结局。孔尚任的作品结尾是侯朝宗和李香君重逢并双双入道,而欧阳予倩却改为两人相遇时,侯朝宗已经考取清朝科举副榜,李香君为此气绝而亡,侯朝宗不得已而离开。如果说当初的电影是喜剧结局,原著是正剧,那么欧阳予倩现在则将京剧本改写成了悲剧,其意图相当显明,就是为了抨击像侯朝宗这样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欧阳予倩的改写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因为历史上的侯朝宗最终也是为了自保而去参加清朝科举,虽然他日后为此感到无比后悔,在李香君去世后不久便郁郁而终。有学者认为,孔尚任是把握了侯朝宗的这种悔恨心理,同时也为了避清朝之讳,故而将结局改为开放式的“双双入道”,这遵循的是一种“艺术真实”[14];但欧阳予倩的写法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真实”,他也认同侯朝宗的正义感,对他后来的选择感到惋惜,然而“两朝应举的事,在当时却失了人望”[15]5,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欧阳予倩其实是借侯朝宗的经历来为当时彷徨不定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因此为了形成对比,他也在剧本中更加突出作为“秀才领袖”“公子班头”[16]的吴次尾、陈定生二人的正面形象,在文庙惩奸、妆楼商议等等场景里增加了不少他们的台词和戏份;尤其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如1956年收录于《欧阳予倩剧作选》的版本)开始,戏剧结尾借柳敬亭和李香君的对话还道出了吴、陈二人殉难的结局,更为这两个复社青年增添了英雄主义色彩,也让侯朝宗选择自保的决定在对比之下更具讽刺性。
欧阳予倩的此次平剧改良,“只以剧本内容与舞台装置及音响等等,求一划时代之转变,其他如一切旧戏之表演形式,未加删动”[17],恰能反映这位戏剧改革者在创新道路上循序渐进的坚实步伐。这部作品上演之后,因触怒日伪而很快遭到禁演,欧阳予倩本人也为了躲避敌伪特务迫害而于1938年离开上海,接受自己在留日期间的同学、现任广西省政府顾问的马君武的邀请而来到桂林。在桂期间他曾因为和马君武意见不合而离开,后来才在广西当局的邀请下第二次举家迁入桂林。真正接手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以后,他就将京剧本《桃花扇》改编成了桂剧。
关于这部作品的版本与内容的信息更加稀少。从欧阳予倩的自述中可得知,他略做了修改,“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敲起警钟;对勇于内争,暗中勾结敌人的反动派,给与辛辣的讽刺。”[15]2联系欧阳予倩当时在桂林改革桂戏的方式和感想,可知他的改写虽然在《桃花扇》的整个版本变迁中看似变化不大,但对于桂林当地戏剧风气而言却是一种震撼和革新。当时的“桂戏由于偏处一隅,交通不便,受到上海和香港的影响不多,好比一个内地姑娘,没有烫过头发,没有穿过高跟鞋,天真烂漫,得其自然之美。桂戏本身没有经过时下流行性的传染,比较纯朴,改革的工作比较易于着手。”[18]但难的是桂林当地来自上层的反对和来自剧团的不理解。欧阳予倩在着手改革之前已经对桂戏的音乐、动作、唱工、曲目等做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他的方案是在保存其地方性特点的同时吸收其他地方剧种乃至西洋歌剧的优点,清除剧中的落后思想,改变剧团常演幕表戏而不注重剧本撰写的不良习惯,因此他打算通过详细周密的排练来改进演员们的表演。但这与当局只希望去芜存菁、不掺杂外来剧种的初衷却大相径庭,因此欧阳予倩改编桂剧本《桃花扇》的阻力可想而知[19]。不过当这部剧最终取得了连演三十几个满场的成绩,且桂剧的面貌确实为之一变时,又可证明欧阳予倩的旧剧改革工作确实带来了影响。
在《桃花扇》的最初三个版本里,欧阳予倩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从中既能看到当时先进的艺术理念,又能感受到时代的需求和观众的心声,这也正为以后的话剧本《桃花扇》的改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剧运低潮时期的崛起:1947年的话剧《桃花扇》
欧阳予倩曾经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生平和朋友合作,有两回是最愉快的:一是在桂东敌后和几个朋友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一就是这回到台湾来帮新中国剧社的忙。”[20]话剧本《桃花扇》也正是他在台湾时期为新中国剧社而改编的。这部剧仅上演了两场就遇上了台湾事变,器材损失巨大,后来欧阳予倩带着新中国剧社回国内演出,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重新筹集资金[21]。然而1947年夏天在上海虹口海光剧院的演出也很快因为剧社遭迫害而暂停。次年,焦菊隐以欧阳予倩的剧本为底本,重新将该剧改为新平剧并由北平艺术馆排演。
如果将1947年出版的新中国剧社演出台本(封面注有“予倩未定稿”字样)的《桃花扇》与此前的三种版本以及建国后经过修改并收入《欧阳予倩剧作选》的版本(以下简称为1956年剧选本)进行比对,就可以发现欧阳予倩在改编该话剧时的修改轨迹。
从艺术形式来看,京剧和桂剧同属于传统戏剧,其身段手法以及台词唱腔显然都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而电影和话剧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其特点在于语言更平俗直白,情节推进更干净利落,整体呈现出更日常化的氛围。因此,欧阳予倩在改编话剧《桃花扇》时,既兼容了戏剧版本的情节结构,又考虑了作为话剧本身的表演特点,最终写成了“不是昆剧,不是平剧,当然不属于希腊戏的系统,也可以说接近莎士比亚”的历史戏[20]。以下将一一进行分析。
首先是剧本场景的增删。在京剧本中出现的逃难场景,讲述的是阮大铖和马士英逃难过程被难民暴打、本已被抓的侯朝宗也趁乱逃离,但在话剧本中则不再出现。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改编话剧时为了使其情节推进更为灵动流畅,而对传统戏曲的场次划分进行了加工利用[22],故删去了稍显杂乱的“逃难”情节。相反,作者又增加了几个象征国民党内部腐朽统治的场景,其一是阮大铖在家中与妻妾的相处,其二是阮大铖为了向马士英献媚而做的种种准备:将路边冻死的难民尸体用大雪掩盖,并从野外折下梅花插在雪堆上,以及安排两个老人作为乡民代表向马士英献礼,并针对提前设计的对白进行了演练。这些场景,在此前的京剧本乃至孔尚任的原著都是没有出现的,完全基于欧阳予倩“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反动政治的反感,把它们当作暴露和讽刺对象”。[15]2如果联系《新桃花扇》中张德凯在家中与姨太太戏耍的场景,可以发现话剧是在电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充了对敌军内部政治腐朽的想象性描写。
而《新桃花扇》中象征着封建制度压迫的鲁步同,在话剧中则依然由李贞丽这一角色来承担。虽然欧阳予倩自己说“李贞丽这个人物在《桃花扇》原作当中并不出色,……以前我也没有付以性格”[15]6,但对比原著和话剧,会发现作者还是更加突出了李贞丽作为妓院妈妈的贪婪圆滑。尤其是在杨文聪告知马士英预备将李香君作为上任之礼赠给田仰时,李贞丽先说“侯相公刚走,要她嫁人,就恐怕她不肯,最好迟一点”,又说“可是……三百两银子”[23]20,显然她的迟疑只是因为担心李香君不肯听从,又嫌弃嫁妆不够多,这样对待刚刚送走侯朝宗的李香君,确实是过于冷酷无情。而在原著中,通知这件事的是郑妥娘和寇白门,李贞丽在该场合并未出现,其贪财的性格也就没有这样突出。到了1956年剧选本的再次修改,欧阳予倩就将她“处理成一个通达世故而又很慈爱的妈妈”[15]7,将她与杨文聪的对话改为一个妈妈为自己女儿争取幸福的恳求,并通过母女哭别来进一步渲染了李贞丽代李香君出嫁时的悲壮气氛,实际上是改造了剧中原本具有象征性的“封建家长”形象,这大概也更加符合新中国的社会文明建设。
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就是杨文聪。原因就在于杨文聪一方面与阮大铖勾结,向其提供收买复社少年的计策,但另一方面又在危急时刻提醒侯朝宗逃走。并且在与奸臣阮大铖分析天下局势时,剧本中的杨文聪还这样说道:
那怕不行吧,史阁部究竟是个忠臣,他一定不会轻举妄动,万一鞑子的兵直下长江,那还了得!(杨文聪他虽然是个委蛇取容保全富贵的骑墙人物,究竟良心尚未全泯,所以他讲出这样的话)[23]30
正是这一段话备受诟病,当时报刊上有不少评论都认为这个角色被刻画得太值得同情了③。但是对于欧阳予倩而言,不这样写无法真正讽刺那些战乱时期的两面派人物,虽然他后来也吸取批评,在1956年剧选本将此话删去,又将通知侯朝宗逃走的戏份移给了柳敬亭。
于1947年首演《桃花扇》话剧的海光剧院,原本是专用于放映电影的。其时正是战后混乱时期,经济崩溃、人心不安,在抗战期间一度盛行的话剧改革运动如今处于低潮。随着上海观众演出公司与辣斐大戏院的合同到期,上海地区的话剧剧场相继结束,一群戏剧从业人员无处可谋出路[24]。在此剧荒时期,由于市教局局长顾毓秀及中央文化运动会主委张道藩的赞助,话剧团体联谊会得以将海光剧院租下,改为新式剧场,专供各剧团演出,而《桃花扇》正是海光剧院重新开张以来的首部演出剧目,因此必然备受瞩目[25]。报刊上有人直言从中“想到我们目前的中华民国,也正是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像明末一般无二的时代里”[26],同时也从侯朝宗和杨文聪的反例中感到气节的重要,“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锲而不舍的去追随正义,却在自我的私利观念下自踌满志的兜圈子,这不是智识分子顶大的悲哀吗?”[27]在剧运低潮时期,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不仅鼓舞了戏剧从业者的信心,也让广大观众重燃对话剧的热情,而这样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他此前多年在此剧本上的辛勤耕耘。
1947年7月,新中国剧社遭到迫害,《桃花扇》被迫停演。同一年底,焦菊隐就领导着北平艺术馆的校友平剧团,积极参与北平革新平剧运动,并开始以欧阳予倩话剧《桃花扇》为底本进行排练,预计于1948年2月10日上演④。焦导演抱着改革旧剧的决心,升级了舞台布景,采用了灯光道具,取消了脸谱勾画,其革新京剧的大胆举措引来褒贬不一的评价⑤。而到了1948年初,齐如山(他曾是焦菊隐的老师,其改编《桃花扇》的时间比欧阳予倩稍早)也应国剧学会的邀请开始进行排演,作为传统派的代表而与焦菊隐的改革派进行了同台对垒。与此同时,又有作为中立派的朱双云所编的《桃花扇》也参与其中,此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一时间引发了社会上的众说纷纭⑥。虽然最终结果是焦菊隐的改革派更胜一筹,但在建国前的北平能够引发这样声势浩大的《桃花扇》改编热潮,足可见这部清代传奇剧历久弥新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
本文梳理了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的历程,将《桃花扇》的多种形式都纳入广义的版本谱系中加以考察,以此为《桃花扇》话剧本的版本异动提供了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和更为丰富的改编渊源。同时,以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为典例,联系每一特定时期的时代环境,可以呈现出这位胸怀壮志的剧作家是如何与时俱进、顺时而动地推进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他一次次地冲破陈规束缚,用同一部清代传奇剧创作出了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也向我们证明了旧剧革新的多重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戏剧的多种发展路径。
注释:
①“‘版本’(Edition)主要是一个图书学或版本学的概念,它所含很具体,……它包含书的制作、印刷、载体材料、版本形态等物质性特点,也指向图像内容与文字内容。”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5-36。
②来自孔尚任作品原文,旧指妓女第一次接客伴宿。
③如:沈露.《桃花扇》小论[N].中华时报,1947-6-13(3). 叶联薰.新中国的桃花扇[N].时事新报晚刊,1947-6-19(3).
④如:北平戏校首排桃花扇[N].罗宾汉,1947-11-25(4). 闲话桃花扇[J].戏世界,1947(353):5.
⑤如:佛舒.新平剧确有新玩艺[J].戏世界,1947(353):10. 桃花扇底多少事[N].力报,1947-12-24(4). 改良平剧《桃花扇》羞煞京朝勾脸看[N].中华时报,1948-1-19(1).
⑥如:改良平剧·大摆擂台[J].戏世界,1948(358):1,12. 桃花扇何多,又将上演第三种本子了[J].星期日画报,194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