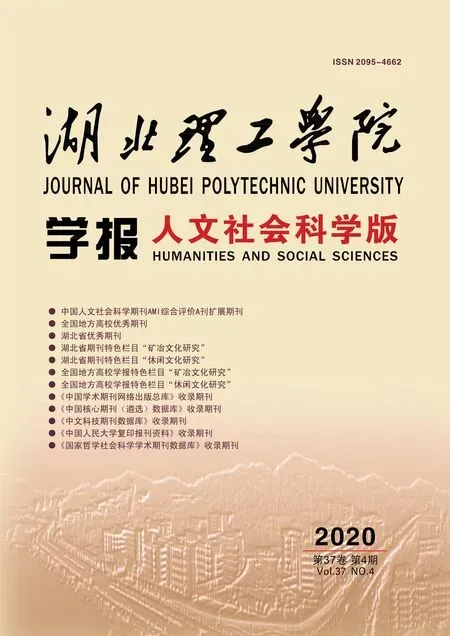晚明何白休闲观及其实践
韩利珍 汪习山
(1.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00;2.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何白(1562—1642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城西郊丹霞山南麓金溪村,自称丹邱生,晚又号鹤溪老渔,因曾居于丹霞山下,人称“丹霞先生”。何白是晚明时期温州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和书画家,在全国诗坛享有盛誉,他一生著作等身,有《山雨阁诗》《榆中草》《汲古堂集》《汲古堂续集》等众多作品问世,但大都佚失,沈洪保先生点校其遗作《汲古堂集》与《汲古堂续集》后整理成的《何白集》[1]是研究其休闲观的重要史料。
何白作为晚明温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学术界给予关注,但主要着眼于何白的诗文成就,如陈士洪在《明代温州府作家研究》中把何白作为明代温州府作家群体的一员进行考察并对其诗文成就做了详尽的描述[2]。何白曾参与创办白鹿社,白鹿社在当时轰动一时,虽名为诗社,但诗词、音乐皆有涉及。潘猛补在《明代温州白鹿社考》中对何白在白鹿社中的活动给予关注[3]。王乒乒在《明代永嘉文人音乐史料考析》中描述何白创办白鹿诗社的始末以及诗社的音乐活动[4]。纵观现有的学术成果,学者以白鹿社为切入点,考察何白的诗文、音乐成就,尚未出现专门化的研究成果,可见观照不够。何白身为晚明士绅,其休闲观以及休闲生活堪称当时士人的缩影,值得关注。然而,目前并未出现与何白休闲观相关的成果,尚有可耕之地。
一、何白休闲观溯源
(一)晚明好游之风
晚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市民意识进一步觉醒,人们更加注重精神需求,注重生活质量,渴望有“闲”的生活。风雅之士或会聚山水吟诗作对,或呼朋唤友品鉴宝物,或外出游历休闲。这些闲暇活动中,外出游历休闲最为普遍,正如学者所言“晚明时期,旅游活动十分兴盛” “旅游乃士绅之‘一癖’”[5]。卜正民认为“癖”“不独被士绅们接受,而且她更将真正有灵性的文人墨客同一般的士绅区别开来。对游历名山大川的嗜好也将士绅同风尘仆仆的商人和一般的旅游者区别开来”[6]。这种“癖”在晚明士绅身上表现得极为普遍,“公安三袁”便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名士陈继儒也非常喜欢游山玩水,他认为“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大乐”[7]。士绅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归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真我。
(二)崇真尚情思想
何白与李贽交情甚深。李贽是敢于冲破固有思想藩篱之人,他时常语出新意,发他人所未发之言论,何白很欣赏他,称他为“别凿鸿蒙”之人。除了李贽,何白与袁宏道之间也有往来,他称赞袁公之文甚好,是上上之文,“公安袁石公持论甚好,真如神僧以嘻笑谩骂作佛事,此为上机者说,难为下劣者言也”[1]9。李贽的“童心说”主张有感而发,不做无病呻吟;袁宏道的“性灵说”主张崇尚自然,不刻意效仿他人,写文章不拘格套。此二人都主张写文章要“真情实感”。在他们的影响下,何白把“真”“情”看得较重,并且体现在他的休闲观以及休闲实践中。
(三)家学源流
何白自幼与其祖母一同生活,据《李后峰先生传》载,其祖母是晚明隐逸诗人李后峰的姐姐。李后峰原名李经勅,因与湖口令章元梅分居雁荡北阁和南阁,二人时常拄杖游玩,吟诗作赋,而章号千峰,李号后峰,世人据此称其为李后峰。在祖母的教育下,何白受其舅祖李后峰作品的影响,在学诗的同时,也渐渐向往其舅祖云游山间之乐。思及此,不难理解何白布衣一生、云游四海的选择,这也造就了何白的诗情才意,成就了他的休闲人生。
二、何白休闲观及其实践
山水怡情、读书养性、种瓜收菽、柴车场圃的闲适生活对何白来说心满意足:
山水谐夙心,遗书颇能读。又复弄柔翰,抒宣中所触。土性既已谙,岁功可聊卜。燥湿本异宜,高下随種稑。东陵方种瓜,南山已收菽。柴车薄暮巾,场圃先时筑。来归息檐下,方池匝松枝。园葵未辞翦,浊醪犹可漉。流泉代弹丝,晚饭当食肉。外物任去留,乘化凭演速。人生一世间,于兹良已足[1]93。
若从晚明社会环境的视角来看,何白乃一介普通文人;但若结合作品进一步审视,其蕴含着独特而深沉的个人情怀与诉求,凸显其休闲观。
(一)何白的休闲观
如前所述,晚明好游之风、受李贽袁宏道崇真尚情的思想主张的影响、家学源流等,构成了何白休闲观的主要背景渊源。概括起来,何白休闲观体现在三点:性灵情真;为乐由心;超然物外。
1.性灵情真
“性灵”兴起于南朝[8]。“性”是其核心,指人的本性、本心、性格。“灵”则是基于“性”之上的深发。黄卓越认为“性灵”的含义是:性灵源于心性本体;性灵为一种心理的灵明或虚明状态;性灵无始无终;性灵具有心理的原真性、个体性、自适性;性灵发为一种本色的灵趣或意趣等[9]。可见,“性灵”与“情”是相依相伴的,“性灵”是情本论的表现。因此,何白提出“放情远壑”[1]451的休闲命题,为士大夫的休闲生活打开思路。何白指出:“时或振策,亦复提壶,晞发繁阴,放情远壑。听山水而怀丈人,聆杖拏而思渔父,罄老农之极悰,希先民之逸轨,可以忘死,可以乐饥。”[1]451何白借用“放情远壑”的命题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顺应自己的本心才能实现忘死忘忧的理想境界,才能体会人生至乐;第二,有寄托情感之物,放空心情,眺望远方,此心安处才是真性情的最佳安顿处。这两点为其追求“情真”的休闲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要实现“放情远壑”,就必须做到“情”。诚如《煮茶》一则所记:
茶灶匡床次第陈,竹林雅惬据梧身。军持晓汲云根碧,仙掌春开露里新。烟暝忽如山雨至,火降初破浪花匀。啜馀坐爱桐阴午,点笔诗成觉有神[1]258。
茅屋虽小,却有茶灶、藤床依次摆放整齐,不远处竹影斑驳,茂林深篁,孤身以冥神入境。茶灶里茶香四溢、烟雾袅袅升起,仿佛雨后初露,俨然山雨欲来之像。山中岁月悠长,品茶静思,“兴至则探韵为诗,诗成则逸兴遄飞”[1]401。诗中,何白向世人展现了一位士绅对休闲生活的喜爱之情,恬淡的诗风颇有陶潜之范。全诗情感真挚,无娇作之态,仅为表达意境。情为真,率真而性灵现,诚如何白所言:“夫诗本缘情,情生于爱,爱斯思,思斯永。”[1]399
除休闲诗以外,何白大量的游记也体现了真情。例如《从梅雨潭背登雷门寻龙须瀑诸胜》载:“大罗信旁魄,真源窅何穷。宁知万仞表,依然碧龙嵸。乍瞰擘双峡,隐隐云雷宫。上嘱挂飞瀑,沉沉流白虹。”[1]4“万仞”“碧龙”“挂飞瀑”“流白虹”等词,将大自然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美的欣赏之情。在大自然中身心不受束缚,情之所至,以诗抒情,进入完全自由的状态。这样的状态须借助休闲空间,若没有休闲,忙于生活的个体则难以集中精力于除工作以外的活动,何来释放压力?不能做到彻底释放,则情无从出,性灵难现。因此,休闲空间、情、性灵三者缺一不可。
2.为乐由心
如前所述,何白休闲观之本体是“情”,那么,如何实现“情”,何白进而提出“乐”。“乐”是何白通往本体之要途,是一种工夫,是休闲行为的存在方式。何白所言之“乐”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乐,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情感表现。或喜或悲,或哭或笑,皆出于本心;遭遇变故动情而哭,大喜便自然而笑,此心、理、情三者合一,即为何白之“乐”。因此,何白之“乐”是一种以追求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不局限于眼前之物,而是一种“浑然天成”的追求。诚如他在《游西湖过功德寺,至高梁桥作》中所言:
林转湖阴长,延眺极厓鄂。远水冒芙蕖,回渚纷蘅若。循轻诣招提,坛畴仍严铺。瑶水骏驭回,迹往空绵邈。犹想云罕临,香花间天乐。劫火净空王,礎莲卧丛薄。出寺遵长碕,林坰纷以漠。高柳蔽层霄,重阴若施幕。双溪贯交流,文鯈信浅跃。情宣忘带淫,目接饶欢谑。日入送归禽,怀土心靡托[1]61。
这种“乐”体现在山水诗中,其诗精妙之处在于,他将山水审美活动与人生的活泼意趣、人生感悟紧密结合;他感到将自己的人生依托、栖息于山水便是快乐之事,这种快乐发自内心。当身心完全融入山水,即使情为山水痴迷、身为山水而陷于沟壑也是值得的。通过这些活动,其灵魂化于天地之间,最终天与人、人与天和谐,天人合一。所以他甘愿放弃做官的机会,寻找心中的“乐”处。活在这样境界里的人,身上汇聚着山水之美与人生之“乐”,他的人格如何不美!诚如学者所言:“这种独特的山水美感体悟凸现了中国山水审美文化的精髓,有助于培育活泼、健全的人格。”[10]活泼的、健全的人格在何白身上得到诠释。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顺应本心即为“乐”。因此,除山水之“乐”,何白的感怀诗亦能体现其“乐”,如《别友人之长夜》所云:“万里牂牁绕夜郎,千山密篟瘴为乡。月明猿啸盘江路,不待三声已断肠。”[1]381“猿啸”哀鸣,友人分别,此一别不知重逢为何日,悲凉之情无以复加,断肠人在天涯。当听到故人离世,友人零落的消息,何白哀痛以至于“吞声赋《八哀》”[1]310。爱女出嫁,因家贫无力赠送嫁妆,何白感叹:“蓬鬓有霜愁揽镜,草堂无客懒开门。”[1]311身为父亲,既有对女儿的不舍,又有因经济拮据而愧对女儿的心疼:“家贫嫁女难留犬,病起调心已定猿。”[1]311
无论是游乐赏玩之喜乐,还是与友人分别以及嫁女时的悲“乐”,喜与悲在何白身上得到彰显,不掩饰、不躲避。他对“乐”的理解与王阳明略同。当门人问阳明先生:“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王阳明回答说:“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11]何白虽未提出“此心安即是乐也”的哲学命题,但在他的感怀诗中,他或幽默或悲痛,皆发乎情,情为本体,本体未动,工夫自然不变。
要言之,何白休闲观之本体为“情”,情到便可以忘忧、可以乐死,喜怒哀乐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状态,不会妨碍他的“乐”。因此,无需掩饰,只需跟随本心即可。如此,“情”本体便可实现。以“乐”为工夫,实现“情”之本体,其目在于达到超然的休闲境界。
3.超然物外
何白是以休闲为本的人,他无时不在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获取休闲。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休闲生活受到极大制约,但何白却能够通过创造休闲条件来达到快意人生的目的,达到“高睨纵遥请,超然肆天养”[1]108超然物外的休闲境界。何白认为,超然者是无往而不适的休闲者,仕宦之途必然导致终日劳苦。因此,面对福建黄方伯的招请,何白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的“快乐”,反而是枯坐寨中一月,如三日新妇,最终以身体抱恙为由请归。可见,仕宦之途对他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他需要的休闲境界是:“朝随沙鸟去,暮逐沙鸟还。”[1]81“超然”会导致与世隔绝,彻底地逃避世俗吗?何白不以为然:“桐林凉霭覆胡窗,柳浪晴光动女墙。莺语欲醉今日醉,客愁且摒一春狂。游蜂争绕红妆妓,细马娇驮白面郎。直遣芳尊邀胜日,莫令青镜点繁霜。”[1]219从“桐林”“红妆妓”“细马”等意象都可以看出何白之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所谓的“超然”其实是休闲的最高境界。诚如学者所言:“休闲是人类最为现实,也最为普遍的存在方式。它不等同于享乐纵欲主义,但也非禁欲主义。”[12]何白将“超然”看作是一个非常高的人生境界,但实际上他已经通过超然之道超越了纵欲和禁欲这两种休闲模式,这样的休闲境界主要体现在即世。
即世并不是游离于事物之外,而是秉持寄托于事物之中而又高于事物的休闲心理。正是因为有这种超然物外的心理,何白才可以坦然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不过分胶着也不完全逃避,以一种审美的心态来生活,达到超然物外的休闲境界。例如,病痛缠身之时,他也能做到“玉书闲就南窗读,欲灌灵根老复丁”[1]319,甚至于,即使病中,也能因为得到名酒而赋诗一首,“笔床缥帙网流尘,绝学萧然一道人。秋色任随青鬓改,世情长与白头新”[1]320,可见其超然洒脱之态。
(二)何白的休闲实践
何白酷爱休闲,并积极将他的休闲观体现于实践中,他日常的休闲活动主要集中在纵情山水、交友聚会、参禅悟道上。
1.纵情山水
如前所述,何白酷爱山水之游,好观赏山河名胜。在他80余年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山玩水中度过,其足迹遍及北雁荡山、南雁荡山、仙岩、大若岩、玉甑峰、江心寺、南麂等温州名胜古迹,客居吴门(苏州),游五茸(松江),去武林(杭州)、吴兴、富阳、桐庐、燕市(北京)等地,也曾去过武昌、庐江、陨襄、丹阳、延安等地,游过湘江、阮水,登过武当,这些地方的花草树木、山明水秀都体现在他的游记中。如《同朱在明、张邦粹、王季中宿仙岩清晖楼》中,他描写此景此情:“上逼蔚蓝下,下瞰鲛人窟。石峡长吹太始云,碧潭寒洒千秋雪。天门一线开玲珑,渊渊雷雨行秋空。空青应水碧,璇室开珠宫。峰峰秀色抟苍鹘,涧涧秋声生白虹。风习习兮行飘摇,心怦怦兮坐超忽。”[1]133如此良辰美景,唯有与好友畅饮一杯,方不负此行,“酒酣耳热气亦骄,穿云乎抟山之坳”[1]133。有美景、好友、清酒,千秋功名,何足道哉:“千载无论身与名,人生快饮差称达。”[1]133《雁山十景记》中,何白详细描述了雁荡山的十景之胜,以《大龙湫》为例,他写道:“仰见瀑流与风相鼓翕,俄顷万态,忽中为风所遇,半壁袅那久不下。忽风从下揭,辄天桥若玉虬腾掷空外。忽劲如万镞,人急走避,讵那庵瓦沟若跳千斛珠,檐端悬溜如秋雨。亭午风稍和,日脚穿云罅,斜映高避,彩虹数道,绚烂炫睫。”[1]7有学者认为《雁荡十景记》完全可以与李孝光的名篇《雁山十记》相媲美。又如《游武当山记》,何白描写武当山之景是:“夹涧绝壁,石脚插入水中,树影与潭影斗碧,作翡翠色。涧底乱石,凹者、曲者、洼者,如断洼、如残璧、如药磨、如齑臼。”[1]8于是何白想到的玩法是“可泳、可沿、可踞、可倚、可晰发、可濯足、可施酒榼、可支茶灶”[1]8,武当山之景被何白如此描写,可谓妙趣横生。
何白的游记诗文是研究其休闲活动的重要材料。与传统文人不同的是,何白的游玩不是为了躲避政治或者发泄情绪,而是完全出于欣赏,是对那种悠然之境的向往——“愿驻西日车,对此南山粲”。用这样的心态去访问名山大川、秀美山河,接近自然、感悟人生、实现自我,不仅激发了他的诗学才情,也丰富了他的休闲人生。
2.酒朋之会
“酒”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已为人熟知。士人好饮酒如李白、杜甫等人,他们因酒而诗的佳话流传千古,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何白也是一个喜欢饮酒且喜好在酒酣耳热之际吟诗作对的人,他认为自己“五十愧无闻,稍得酒中境”。正因此,何白留下了许多饮酒诗,如《竹林饮酒歌,赠项季舆》:“练成醉骨轻如烟,骑鲸好待长风起。”“轻如烟”“长风起”与庄周乘物而游有异曲同工之妙。
何白认为喝酒应该选择“醴而醇”的酒,他称酒为“醇”“醪”“绿酒”[1]93。他在对酒的描述中,“醪”出现的频率较高,可知其常饮。何白认为喝酒的方式应该快饮、痛快地喝。它不单单指饮酒的速度,重在展现一种饮酒的态度、一种情怀。“遇酒辄快饮,宁择醴与醇。”[1]120“明朝有酒能复来,家人莫问瓶中粟。”[1]136“愿将馀日送杯铛,何必浮名闭金石。夜阑醉问下江船,树杪已看斜汉白。”[1]156“浪饮能禁此夜长,一掬雄心付千古。”[1]165“酒酣挥手月如霜,马踏空壕夜未央。”[1]166这种“快饮”豪情一般出现在聚饮情况中,《何白集》中关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何白也主张慢饮,如:“寒雨闭空斋,人闲酒新熟。散发披道书,晚就北窗读。”[1]109“凉簟沁微醒,临风送延伫。湿翠晃斜光,颓云漏残雨。会心莫与同,春醪还独抚。”[1]100“及辰不为欢,何以乐当年。”[1]99“醉后悠悠忘南北,卧看沙痕落三尺。”[1]149在何白看来,空山新雨后,人闲心适时,小酌慢饮一杯,胜却人间无数。
何白喜饮酒且以清酒为主,慢饮乃文人士子尚清流之故。喜饮酒,得其性情;玄谈诗赋,得真酒性。无论是快饮,还是慢品,酒在他心中是全性之饮,是快乐,是休闲。
3.参禅修行
佛教禅宗主张关照自然、复归自然。在禅宗看来,自然万物皆是真理和智慧的体现,因此要达到“随缘人生”的境界,首先需要破除“执念”。只有破除执念,才能真正做到“自由”,因此,破执的本质是顺应,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此外,佛家还主张“高峰体验”,即尽情享受人生。佛家认为,众生皆苦,唯有入俗但不累于俗,无欲无求、无心无视,才能消除一切烦恼,才能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何白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在香山寺礼佛时,他写到:“崇殿法上玄,规拟圜仪影。千佛灌交光,怳集耆闍境。昼寂林蔼繁,日永岩花静。鞭心初地馀,忘言泯机警。”[1]59诗中涉及许多佛家意象,如“崇殿”“法”“千佛”,可见他受佛家影响之深,甚至达到“忘言泯机警”的境地。《上巳日,同王伯无入天台游国清寺,历览五峰、双涧诸胜,时西湖上人孑萍谈经方丈》描写了他在国清寺的所感:“伊予久尘境,顿缨出泥滓。问法契无生,同人云有美。”[1]69《宿高明寺,晓起礼佛,饭毕,同有门法师暨上足幻、午亭数人散步幽溪大石上,煮茗赋诗。已,登圆通洞,予书“圆通洞”三大字于石,并纪姓氏岁月,颇极世外之致》描写他在国清寺的所见所闻。在高明寺的水声、梵音中“卧闻钟梵歇,惺心揽衣起”[1]70,吃着高明寺的斋饭,他感到“斋厨饭芳香,园鲜荐清旨”,最后“散步出山门,披襟信杖履”,面对这大好山河,他“回首堕尘氛,有梦应来此”。此外,《何白集》中辑录了大量他与佛教人士间密切往来的诗作,如《同伯无从金地领过高明寺,访有门法师,寺在岭下》《登华顶,有门师送至银地岭,共探佛陇遗迹而别》《人日同扬木父、项叔慎过集云寺,访有门法师。时法师集四众谈〈法华〉玄义,午后下座,携客列坐溪上,流憩久之,晚归修净业,作四首》等诗中,展示他与佛教高僧有门法师之间的来往,可见他们之间交谊匪浅。通过这些交谊,加深了何白对佛法的了解,在丰富个人休闲生活的同时,有助于修行“超然入空观,了了见虚名”,有助于他以更加“自由”的姿态去休闲、去生活,达到“安得子庄子,相与论肖遥”的境界。
三、何白休闲观的当代启示
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等人认为:“唯有在休闲之中,人类的目的方能得以展现。”[13]可见,小到个人,大到人类文明,休闲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尤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诚如于光远所言:“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4]杰弗瑞·戈比在《你生命中的休闲》中对现实休闲生活的意义作了如下分析:“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休闲行为不只是要寻找快乐,也要寻找生命的意义。”[15]显然,去发现你热爱的活动,这一过程本身既令人偷快,又有意义。生于晚明的何白是一个有“闲”人,他一生都在追求“闲适”。历史的价值在于“以古鉴今”。因此,晚明何白的休闲观以及休闲实践,对今人的休闲生活,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一)以真为要,选择合适的休闲方式
何为真休闲?何白之真在“性灵”,性灵真则情自现。真休闲包括两层含义。第一,选择喜欢的休闲方式,喜欢才能真快乐。何白喜欢“行散步修檐,林水含深碧”的休闲方式,追求“坐久转萧爽,悠然澹忘适”的休闲境界。他喜爱自由,山川湖泊任他遨游,故而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真正的休闲。现如今,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不喜欢爬山,因为交谊而去爬山,不但不能感受山间的花鸟鱼虫、大自然的绚烂多姿,反而会劳神伤体,这样的休闲方式是负担,其出发点并非为了休闲,算不上是真休闲。何白按照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顺应本心,身心愉悦,所以他能感受到真正的休闲。因此,选择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很重要。第二,选择合适的休闲方式。休闲方式有很多种,是否适合决定了能否愉快的休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休闲质量。性格内向的人,可以选择安静舒适的休闲方式,如养生休闲;性格外向热烈的人,可以选择交友聚会类的休闲方式;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可以选择强度较小的休闲方式,如慢跑,散步等。
要言之,结合自己的兴趣与自身的特殊性选择自己想要的休闲方式,只有这样,休闲才能成为“休闲”。因此,何白的休闲观在当下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二)享受休闲之乐,提高休闲价值
何白休闲之“乐”在于其乐由心而发,无论是蜗居草屋感怀时事,亦或是邀朋游玩、对酒当歌,这些活动对他来说都是乐,是大乐。何白之“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相对而言,我们生活在比何白更加自由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各种休闲方式。工作之余上网已成为大众较为普遍的休闲方式,也因此形成网络休闲。在网络世界中,个人成为自我主体,享有主体的权利,是自我行为的执行者和管理者、选择者和调控者。自我意识自由支配,极大地彰显了人的自由个性,使个体切实感受到主体性地位的高扬,从而使主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这与职场生活中无法做主而形成的压抑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网络上,满足他们对休闲的追求。这种休闲类型被称为“消遣娱乐”,其典型特征是上网、闲聊、购物等,这些活动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便是休闲。有学者评价这样的活动仅停留在“消磨时间类或摆脱单调型”[16]的休闲体验,仅仅为了打发时间而选择的消遣娱乐,并非“创造型或积极参与型”[16]的高层次休闲,以至于他们的休闲很难得到自我满足或自我完善,从而难以发挥休闲的价值。从何白的休闲观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追求的是惬意、舒适的快乐休闲,他的休闲实践是为实现他的“乐”,但这种“乐”并非娱乐至死,而是一种心境的释放,是一种修行。由此推之,何白休闲之“乐”与当今网络休闲之乐大相径庭,何白之乐是提升,网络之乐是消耗。因此,何白的休闲观值得人们学习。
(三)追求现世之闲,无往不闲
何白之休闲观追求的是超然物外的休闲境界,是一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坦然之态,但他的超然并非游离于事物之外,而是追求活在当下的“现世之乐”,眼前景况并不能主宰主体对休闲的追求,更不能妨碍休闲之乐,这一点对当下人们的休闲生活尤为重要。现如今,人们言及休闲便想到节假日、金钱,仿佛这些都必须具备了才能休闲。然而,时间与金钱都具备,可能已经错过了最恰当的休闲时刻,尤其在这个工作压力巨大的时代,人们透支着身体,长此以往,休闲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向往。更何况,并非所有的休闲都需要长假、购物以及狂欢。真正的休闲是心灵的澄澈,精神的放空。若以长假为载体、以金钱为媒介、以狂欢为途径的休闲消耗身体,这样的活动就背离了休闲之意。相反,那些能够让人内心愉悦的休闲活动并非需要耗费过多金钱与时间,例如登山、徒步之乐,就无需耗费太多心神,更不必大肆浪费,也少了狂欢之后的空虚,如此休闲何乐而不为。虽然时代在变化,人们的休闲方式亦在发生变化,然而,休闲是以人为本的,寻求精神高度愉悦、身体放松活动的本意并未发生变化。因此,何白的休闲观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四、结语
“身同白鹿闲沧海”[1]783是郑汝璧对何白的评价,将何白的休闲人生概括得恰到好处。何白亦有诗名,叶懋敬赞他:“龙门笔札挟风霜,鸡林妙墨称琼玖。”[1]791他的诗名为众人熟知,诚如李维桢所言:“无咎诗宗李杜,文宗韩柳,其损益因革,择之精,守之不变,故四君子超六代,而无咎踵武四君子以此。夫李杜不足于文,韩柳不足于诗,无咎兼之,又善用四君子者也。”[1]10名士陈继儒认为:“无咎诗境文境气吞千秋,名走四裔,真鲁国之灵光,陈留之耆旧也。”“天际真人,山中宰相,觉无咎先生独得其全,造物岂有私哉?”[1]10。他的诗被时人竞相传抄,可见其诗名之盛。我们缅怀何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提到休闲言必称西方的时代,有必要弘扬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因为“休闲”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中。正如林语堂所言:“中国人之爱休闲,有着很多交织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17]何白休闲观及其实践留给我们的财富是多方面的,对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具有导向性作用,他向我们展示古人休闲智慧的同时,也指引了当下的休闲潮流,这对于如今休闲方式多样化的时代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