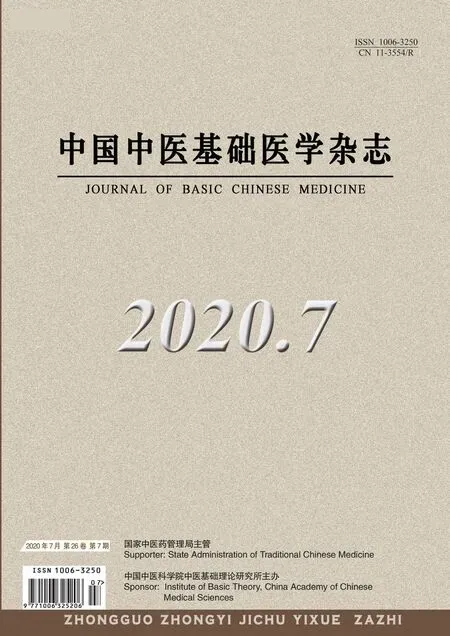复式补泻手法的历史源流与现代临床应用❋
张 阔,张一平,李 凯,丁沙沙,刘阳阳
(1. 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天津 300072; 2. 鸡泽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河北 鸡泽 057350; 3.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天津 300381; 4. 天津市南开医院针灸理疗科,天津 300100; 5. 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针灸学研究中心,天津 301617; 6. 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天津 301617)
针刺手法是影响临床疗效的一项重要因素[1]。复式补泻手法作为针刺手法的一部分,是一种操作较为繁复的针刺补泻手法。它在《黄帝内经》的针刺理论指导下,针对病情和腧穴部位的不同,将多种单式补泻手法配合应用并协同作用于机体,以调节机体阴阳,疏通经络,改善气血津液运行,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2]。这类手法多由金元时期以后的针灸医家所创立,包括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臼、龙虎交战、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等,各家论述不尽相同。目前复式补泻手法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对于众多疾病具有独特的效果。本文将对复式补泻手法的古代文献进行梳理,同时总结相关的现代临床研究概况,以期展示复式补泻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为针刺手法研究提供参考。
1 烧山火、透天凉
烧山火和透天凉法是临床常用的复式补泻手法代表,分别由徐疾、提插、捻转、九六、开阖、呼吸等单式补法或泻法组成[3]。两种手法一阴一阳、一凉一热,在《黄帝内经》论述的基础之上,经后世总结发展而成。《素问·针解篇》[4]有云:“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明确提出针刺可使患者产生温热、凉爽两种不同感觉,以达到治疗虚寒证及实热证的目的。直到明代,“烧山火”“透天凉”之名在泉石先生《针灸大全·金针赋》(以下简称《金针赋》)[5]中被明确提出:“考夫治病之法有八:一曰烧山火,治顽麻冷痹,先浅后深,用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插针。除寒之有准。二曰透天凉,治肌热骨蒸,先深后浅,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徐徐举针,退热之可凭。皆细细搓之,祛病准绳。”并在原文中散载了具体操作,对后世复式补泻手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因对操作的叙述不够详细,其后《针灸聚英》《针灸问对》《医学入门》及《针灸大成》等书中两法操作各有异同,此不赘述。
在近现代针灸临床治疗中,医家对烧山火及透天凉手法有一定的继承与改良。烧山火手法操作多遵循《金针赋》和《针灸大成》但略有不同。如陆瘦燕强调提插结合捻转补法同时操作,郑魁山强调押手在烧山火中的运用,管遵惠则将震刮法加入到烧山火手法中[6]。透天凉手法的操作同样不尽相同,仅以操作是否分层为例,陆瘦燕、焦勉斋等遵循《金针赋》原意主张分三层操作,楼百层则推崇分深浅两层操作;还有医家认为不必限于一进三退法,操作可不分层,进少出多即可[7]。在近年的临床应用方面,烧山火针法多用来治疗失眠、急性周围性面瘫、过敏性鼻炎、老年支气管哮喘、心脏早搏、中风后肢体麻木、卒中神经源膀胱、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神经根型颈椎病、腰腿痛、原发性痛经、小儿遗尿等[8-10]。透天凉针法则多用来退热,治疗咳嗽、胃痛、热痹、带状疱疹、阑尾炎、臀大肌挛缩术后患者步行障碍、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下肢痉挛[11-13]等。
2 阳中隐阴、阴中隐阳法
阳中隐阴法是在同一穴位先行烧山火后行透天凉,补泻兼施、先补后泻的复式手法。阴中隐阳法与之相反,是在同一穴位先行透天凉,后行烧山火,补泻兼施、先泻后补的复式手法[14]。两种手法,前者可治先寒后热证,后者可治先热后寒证,通过各自的手法调和荣卫,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其指导思想受《灵枢·终始》《难经·七十六难》中有关补泻先后兼施原则的影响。两法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明代《金针赋》[5]:“三曰阳中之阴,先寒后热,浅而深,以九六之法,则先补后泻也。四曰阴中之阳,先热后寒,深而浅,以六九之方,则泻后补也。”《针灸问对》对针刺的深浅部位进行了说明,《针灸大成》全面论述了两法的主要证治和具体操作。目前临床应用时,阳中隐阴法常以徐疾补法和提插补法、泻法组合而成“二补一泻”的形式。阴中隐阳法则以徐疾泻法和提插泻法、补法为主,组合而成“二泻一补”的形式[14]。
在现代的针灸临床中,阴中隐阳针刺法用于治疗眩晕、卒中后失语、老年癃闭、增生性膝关节炎、便秘、产后腹痛、月经不调、小儿食积等[15-17]。阳中隐阴针刺法则常用于治疗萎缩性胃炎、偏头痛、流感发热寒战、陈旧性面瘫、荨麻疹等,其疗效明显[18-19],适宜推广。
3 子午捣臼、龙虎交战法
子午捣臼法是以捻转、提插为主并结合徐疾补泻组成的复式补泻手法。“子午”即左右捻转,左转为“子”,右转为“午”;“捣臼”即上下提插,此手法可导阴阳之气,主治水蛊膈气,首载于《金针赋》[5]:“五曰子午捣臼,水蛊膈气。落穴之后,调气均匀,针行上下,九入六出,左右转之,十遭自平”,明确阐述了该法的主治病证及具体操作。
龙虎交战法是指在行针过程中反复左右交替捻转,结合九六之数实施补法与泻法的针刺手法。“龙”即左转,行九阳之数即为补法,“虎”是右转,行六阴之数即为泻法,“交战”即左右交替捻转,达到补泻兼施的效果,始见于《金针赋》[5]:“亦可龙虎交战,左捻九而右捻六,是亦住痛之针。”此后各代医家在手法操作及主治范围上又有所发展。如《针灸问对》[16]开拓了龙虎交战法的另一种操作方法:“先于天部施青龙摆尾,左盘右转,按而添之,亦宜三提九按,即九阳也,令九阳数足。后于地部行白虎摇头,右盘左转,提而抽之,亦宜三按六提,即六阴也令六阴数足。”其后,《针灸大成》认为施行龙虎交战针刺法,应将针刺深度分为天、人、地3个部位,在每一部位俱行一补一泻手法。在主治范围上,《医学入门》认为,该法可以治疗疟疾先寒后热、一切上盛下虚等证。
现代有医家强调,子午捣臼法操作当分三部进行频繁的提插捻转,对于九六数则不必强求。对于龙虎交战法,陆瘦燕、陆寿康、管遵惠以及现代医家基本遵从《金针赋》所述操作手法进行临床操作[17],也有医家认为此法较为繁复并提出:“简化龙虎交战手法”,操作时以凉热感觉为度[18]。在具体应用中,目前子午捣臼针刺法主要用于治疗神经性耳鸣、失语、周围性面瘫、胸胁痛、夏季吐泻、肠易激综合征、老年人习惯性便秘、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水肿、更年期综合征、焦虑症、术后肠麻痹、截瘫后尿失禁、产后尿潴留、小儿巨结肠类缘病等疾病[18-19]。龙虎交战针刺法在偏头痛、中风后丘脑痛、急性胃脘痛、原发性痛经、肾绞痛、坐骨神经痛、非特异性下背痛、带状疱疹后遗留神经痛、红斑性肢痛等疼痛类疾病及顽固性呃逆、失眠、急腹症、胃食管反流病、痛风、抑郁性神经症、神经根型颈椎病、中风后肩手综合征、肱骨外上髁炎、腰间盘突出症、慢性腰肌劳损等疾病中广泛使用[20-21],具有较好的疗效。
4 进气法、留气法与抽添法
进气法是在穴位深层进行提插补法,并配合针尖方向与吸气,以调节针感走向的方法[14],主治风寒湿痹证。始见于《金针赋》[5]:“六曰进气之诀,腰背肘膝痛,浑身走注疼,刺九分,行九补,卧针五七吸,待气上行。”《针灸问对》[16]叙述更为详细:“针入天部,行九阳之数,气至速卧倒针。候其气行,令病患吸气五七口,其针气上行。此乃进气之法,可治肘臂腰脚身疼。”至《针灸大成》时,将进气法称为“运气法”,进气法在穴位深层行提插补法,运气法则是在穴位深层行提插泻法。
留气法是徐疾补泻、提插补泻、九六补泻组合而成的复式手法,主治癥瘕积聚。始见于《金针赋》[5]:“七曰留气之诀,痃癖癥瘕,刺七分,用纯阳,然后乃直插针,气来深刺,提针再停。”后世又在临床主治和具体操作上对本法内容加以充实。《医学入门》中指出,留气法针刺入七分后行老阳数。《针灸大成》提出针刺入七分时行九阳数,得气后针刺一寸行六阴数。现代医家陆瘦燕认为,本法与“阳中隐阴”法相类似,但在分层时又有所不同。
抽添法是以提插为主或结合呼吸、捻转施行的补泻手法。“抽”即上提针,“添”即下插针,首记载于《金针赋》[5]:“八曰抽添之诀,瘫痪疮癞,取其要穴,使九阳得气,提按搜寻,大要运气周遍,扶针直插,复向下纳,回阳倒阴。”《针灸问对》进一步丰富了抽添法的手法内容,在提插补泻的基础上结合呼吸补泻、捻转补泻形成复式补泻手法。清代《金针梅花诗钞》将抽添法分为抽法和添法2种,与古法不同。
5 小结与展望
针刺疗法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刺手法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之一。复式补泻手法以《黄帝内经》为理论指导,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历代针灸医家的实践总结,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临床常用的各种复式手法。本文简要回顾了复式补泻手法的发展源流,探讨其发展演变规律,总结了复式手法的现代临床应用情况,提示针灸临床工作者应重视复式手法的运用。
然而也应该看到,复式补泻手法在取得独特临床疗效的同时,操作复杂亦无统一规范,手法时间长、刺激量大,患者不易接受,研究探讨文献屈指可数,其研究和继承远远不能满足针灸临床的需要,有些手法已经濒于失传或怠失精华。因此,掌握复式手法、继承其精华并结合现代临床实际应用加以发扬和改进,把复式补泻手法进行规范化至关重要。
此外,复式补泻手法发挥良好治疗效果的原因尚未被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复式针刺手法的特点及作用机制,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观察运针过程中物理量的变化特点,客观描述、记录、分析手法操作信息,建立量化、规范化的复式针刺手法实验研究,有助于针灸工作者掌握和破译古代名目繁多的复式手法[22],同时推动针灸学走向规范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