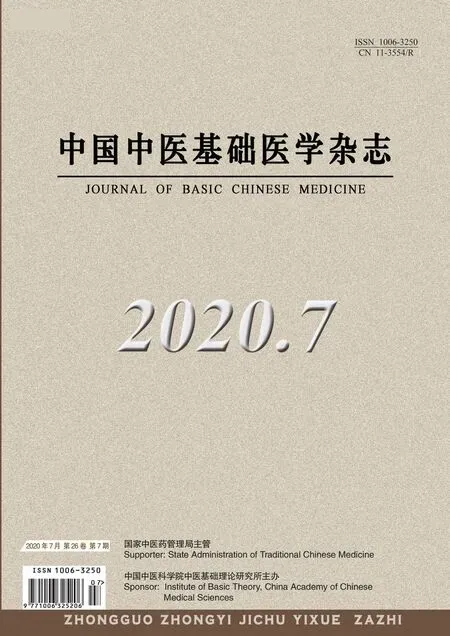脏腑-经穴相关的现代研究❋
姚 琳,杨馥铭,刘雁泽,张晨柳,胡巧巧,王 辉,刘阳阳,郭 义,王洪峰△
(1.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000; 2. 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针灸学研究中心,天津 301617)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针灸在临床中的应用具有指导意义。经络是机体运行气血的通路,具有“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沟通作用。当脏腑出现病理改变时,通过经络的联系,可在体表相应腧穴部位有所反应,即脏腑-经穴相关学说,其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脏腑-经穴相关的现代研究进行概述。
1 脏腑-经穴相关现象研究
基于经络的沟通,脏腑的病理改变会在局部腧穴上表现出不同的异常现象,主要包括以下3种表现形式。
1.1 形态和感觉异常
疾病发生时,机体相应经络或腧穴会出现体表形态异常,或对刺激敏感的痛阈值降低,对疼痛的敏感性显著增强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穴位痛敏化,这类腧穴被称为“阿是穴”或“压痛点。”“阿是穴”是病理条件下脏腑和体表之间的动态联系和规律,被认为是腧穴特异性的典型体现[1]。临床研究发现,肾性皮肤病会沿肾经循行路线出现呈带状的皮肤病损;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会在肺俞、中府、太渊等穴处出现明显压痛和条索状改变。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在足三里、上巨虚、下巨虚穴位处的痛阈值明显低于旁开处,其变化百分比高于正常人,表明穴位在病理状态下会被痛敏化,即从“沉寂”状态向“敏化”状态的转变[2]。此外,病重则穴位压痛重,病轻则压痛轻。
1.2 生物物理特性改变
疾病状态下,经络或腧穴局部的体表温度、电阻、电位及发光、磁场和声波强度等会发生改变。研究发现,疾病状态下人和动物体表的相应部位会出现循经性高温线或带,如心包炎动物模型会在心俞穴和心包经等处出现高温现象;急性化脓性胆囊炎的家兔在其躯体两侧相当于胆经循行的部位出现明显的高温带,并且其温度和长度会随病情的消长而出现相应的改变[3-4]。应用红外热像图法和体表电阻测量法发现,穴区有高温和低电阻特性,而体表温度和电阻值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5];慢性胃痛患者左右两侧足三里、梁门、胃俞穴的红外辐射不对称,且低于健康人[6];佘延芬[7]等发现,原发性痛经患者三阴交穴的电阻值失衡现象较正常人明显。
1.3 组织化学成分改变
研究发现,内脏发生病变时腧穴局部的组织细胞化学成分会随着疾病过程发生改变。局部神经纤维末梢表达伤害性神经肽P物质(SP)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8],这些物质同时作用于局部的血管,导致血流增加,血浆渗出,肥大细胞聚集、脱颗粒[9],释放致痛和致敏物质类胰蛋白酶、5-羟色胺(5-HT)和组胺等。何伟[10]等在造成胃黏膜损伤后发现,SP、CGRP阳性神经纤维及5-HT、组胺阳性细胞在非敏化腧穴处表达较少,在敏化腧穴处表达明显增多,且向血管周围聚积。同时敏化腧穴处肥大细胞聚积、脱颗粒,与5-HT、组胺阳性细胞共存。提示在穴位敏化的过程中,肥大细胞可能通过脱颗粒释放5-HT、组胺,发挥致敏的作用。多项研究发现,穴位处的钾离子、氢离子、钙离子、钠离子、氯离子及氧分压、二氧化碳等也会随疾病的过程发生改变[11-14]。
2 脏腑-经穴相关应用研究
多位医家认为,体表的特定腧穴对许多疾病具有诊断价值。王居易[15]总结和发展了循经按诊以辨经络寒热虚实的诊察方法,通过“审、切、循、按、扣”来观察经络颜色和光泽的变化,经络循行部位有无疼痛、结节或条索状物、虚软凹陷等,从而判断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总结出察经、辨经、选经、择穴的临床诊疗思路。曲衍海[16]认为,以十二经脉的标本根结理论为依据,人体头胸腹背等各部位及脏腑出现病痛时,通过经络的沟通,在人体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部位都会出现相应的敏感反应点,并且这些“反应点”与脏腑病痛间具有明显的对应规律,是经络腧穴诊断脏腑病痛的临床基础,也是治疗的最佳腧穴。盖国才[17]将募穴、五输穴、郄穴、络穴等作为疾病的定位穴,将对特异性疾病具有治疗效果的腧穴称为定性穴,二者结合用于辨病诊断,并将此总结为“穴压痛辨病诊断法。”刘天健[18]首次发现肝炎患者会在肝俞穴出现压痛,但此腧穴在解剖上与肝脏无关。在癌症诊断方面,盖国才还发现了2个特殊的定性穴,为指示良性肿瘤的“新大郄穴”和指示恶性肿瘤的“新内郄穴”,这一发现对临床诊断癌症和肿瘤有很大的帮助。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多种先进的检测仪器被广泛应用于经络诊断,包括经穴电阻探测、腧穴发光探测、经络腧穴皮肤电位测定及红外热像仪等。其中应用较广的是经穴电阻探测仪,具有腧穴定位、显示针感和反应病理作用,使用时应控制好电极压力和测定时间,避免出现假反应点。腧穴发光探测可比较病理状态下不同腧穴体表的发光特性,经络腧穴皮肤电位测定可探究体表与内脏病变的相关性,红外线热像仪可用于找寻人体背俞穴的异常反应点。
3 脏腑-经穴相关机制研究
多项研究表明,针感和针效的产生受到神经-体液-免疫网络的调控,这可能是经穴脏腑相关的重要物质基础。
3.1 神经途径
3.1.1 神经节段性分布与内脏牵涉痛 有学者将穴位主治性能与神经节段范围病症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每个穴位均有治疗他所在神经节段范围之内病症的功能[19],这一研究体现了内脏器官与体表经穴间的神经节段性支配规律。神经节段是支配内脏器官和体表经穴的中心环节,通过躯体神经和内脏神经使脏腑和体表经脉穴位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表里相关、内外统一的整体,其中研究最多的病理表现是内脏性牵涉痛的产生。研究发现,其牵涉痛区的皮神经所属脊髓节段与病变内脏的自主神经所属脊髓节段是一致的,即符合神经节段支配的规律[20]。内脏牵涉痛假说之一的轴突分支学说认为,内脏与躯体的牵涉关系是指传入神经-分支分布于内脏,另一分支于躯体的其他部分。多项研究[10,21-22]运用荧光示踪、电生理、免疫组织化学结合激光共聚焦等技术对疾病状态下动物模型的外周传入纤维在进入脊髓中枢前的分支现象进行了观察,并证明了这一学说。
3.1.2 自主神经系统的作用 自主神经是内脏与腧穴联系的重要环节,不只在内脏牵涉痛的形成中发挥作用,还是构成内脏-耳穴反射弧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观察发现,内脏疾病往往在耳廓一定部位出现压痛点、低电阻点等反应。相关动物实验对交感神经在内脏-耳穴反射弧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保留交感神经,胃与耳廓皮肤的联系正常,而切除了耳廓的交感神经后,胃与耳廓皮肤的联系减弱,说明交感神经是胃和耳廓与体表相联系的物质基础之一。
3.1.3 传入信息的中枢会聚 多项研究表明,脊髓、脑干、丘脑及大脑皮质等各级中枢存在既接受来自内脏传入信息的影响,又受来自体表传入信息的影响,或两者投射到同一部位的汇聚现象。脏腑病变时,穴位特异性反映内脏疾病的中枢水平机制包括躯体传入与内脏传入在脊髓的汇聚以及脊髓和(或)脊髓上中枢不同水平在内脏病变时功能的易化或敏感化。其中最典型的中枢机制是躯体和内脏传入信息在脊髓水平的汇聚理论[23]。国内外多项研究证明了这一学说,其中朱兵团队在直结肠扩张(CRD)模型的基础上发现,持续性的内脏伤害性刺激会对脊髓背角的会聚神经元、背柱核神经元、背侧网状亚核神经元及丘脑腹后外侧核神经元均有非常明显的激活作用,且神经元激活程度会随着CRD量的增加而增强。在CRD刺激后进行电针刺激,发现它们对电针的激活反应也明显增强,说明这些神经元在内脏伤害性损伤后的功能易化是导致穴位敏化出现动态变化的原因[24-26]。
3.2 体液途径
经脉穴位在反应病症时,也具有缓慢、普遍、广泛及全身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能与体液因素密切相关。采用动物交叉循环实验方法[27]发现,刺激家兔的内脏会引起其功能失常,并引起其耳廓测定点的平均导电量显著增加现象,解除刺激则不会出现此现象。且脏腑与耳穴间有特异性联系,这可能是通过某种体液途径进行的,肾上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4 现状与问题
脏腑-经穴相关作为中医针灸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古人早就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诊察疾病,且多注重结合经络循行、经筋及相关脏腑等病候综合辨证。现代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现象、机制的研究,研究还不够深入,且多忽视古人经络辨证的整体思想。如在现象方面,目前的研究尚停留于对穴位病理反应的观察阶段,缺乏规律性的结论;在机制方面,关于传入信息的中枢会聚部分,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直结肠扩张模型,缺乏对多种疾病的系统研究。自主神经方面研究近年来进展缓慢,在内脏牵涉痛形成中的作用尚停留于现象观察,缺乏机制研究及其与中枢联系研究等问题。
今后的研究应更全面、深入探讨现象与机制的关联性,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总结规律性,对脏腑病理情况下的相关穴位病理改变进行系统总结,探究能够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的规律性依据,使研究与临床结合有助于早期诊断;二是加深病理研究,扩大基础研究范围,探究多种疾病状态下脏腑与经穴的病理改变机制,使研究更系统全面具有说服力;三是掌握整体观念,可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的整体角度出发,探究疾病状态下穴位局部的炎性和神经化学物质的作用途径,为脏腑-经穴相关提供更可靠的理论依据。